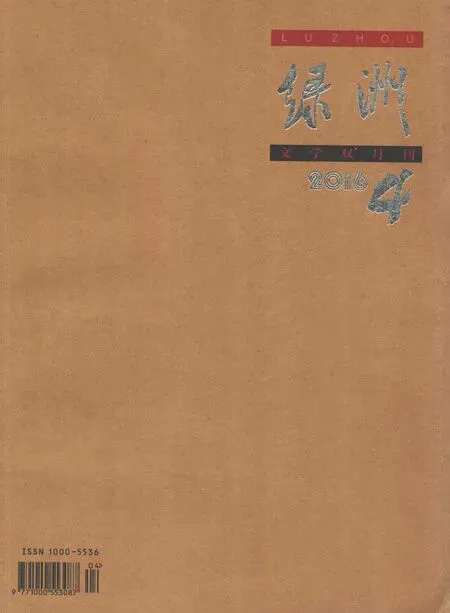岭上
向本贵
岭上
向本贵
一
“你后悔么?”钱秋香心疼地看着邹杰,柔声地问道。
“……”这么多年了,邹杰这是第一次没有把不后悔三个字说出来。
泪水就哗哗地从钱秋香的眼里淌落下来,她说:“我这就去对他说。”
“不……”
邹杰从喉咙里吐出一个字,后面的话钱秋香没有听清楚,但她猜得出他说的是什么,除了顾及郑生林的脸面,他还顾及邓荷花的日子不好过啊。
“要不,给我们家邹芳打个电话,叫她回来一趟吧。”
“不……”邹杰的眉头紧紧地拧着,脸面有些扭曲,这么多年来,他就担心哪一天自己突然就起不来了。现在,他的担心是一天一天临近了。
钱秋香已经泣不成声,说:“我去乡医院给你弄点药来。”
“不用。”
“你是担心没钱?”
“不是。”
“那我这就去弄药。”
“那点钱要留着。”
“还说不是心疼钱。要不,我们把字签了,把低保手续办了,就没有后顾之虑了。”
邹杰的眼睛就瞪圆了:“放屁。”
四十多年了,邹杰从来没有对钱秋香瞪过眼睛,说过重话。今天,他自己都被这样的举动吓了一跳。
钱秋香哭得更加厉害了:“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你说该怎么办?”
邹杰不做声,他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我现在不叫你老支书了,更不会叫你什么舅舅,我叫你邹杰。邹杰,再不签字,乡里赵书记就要来找你了。”
郑新又在禾场上骂开了。郑新是岭上村的村主任。这些日子,天天来找邹杰,恶声恶气,还骂人。邹杰只是叹气,钱秋香却是在心里骂:“没教养啊。”
“邹杰,那字你签也不签?”
钱秋香只得对着禾场回答说:“你……他又犯病了。”
郑新说:“怎么没死。”
钱秋香已经忍无可忍,吼他道:“你是畜牲啊。”
郑新在外面骂一阵,就走了。邹杰要钱秋香把他扶起来,他要起床。只是,钱秋香稍稍动了动他的身子,那腰就疼得他呲牙咧嘴了。
钱秋香说:“我去炒点食盐,在腰上敷一敷。”平时,邹杰的腰疼得受不了的时候,钱秋香就是用这种办法给他缓解疼痛的。
邹杰没有做声。钱秋香连忙生火,在锅子里炒了半碗食盐,用洗脸毛巾包好,轻轻地在邹杰右边腰间敷着。钱秋香清楚地记得,三十多年前,农村实行生产承包责任制,周边村寨的农民都吃上了饱饭,只有岭上村是个另外,水田十年九旱,人们吃饱饭还得看天。邹杰带着村里的人们开凿后垭的石壁,不惧风雨霜雪,没有春夏秋冬,用了三年时间,硬是在石壁上开凿出一条二百米长的水渠,把后山的泉水引到岭上来了,从此旱涝保收,他自己却被石头砸伤了腰,落下腰疼的毛病。每年的春天要发一次,后来年纪大了,就不仅仅只是春天发病,疼起来没个准,中药西药都吃过,却是不见效果。
盐包在腰上敷了一阵,疼痛似乎有所缓解,邹杰说:“吃过早饭,我们去油茶林看看。油茶果该采摘了。”
钱秋香说:“不用看,熟了就会掉下来,你只管好好躺着,到时候我一个人去油茶林里拾茶果就是了。”
看见男人的痛苦稍稍缓解了些,钱秋香的心才放了下来,吃过早饭,背着背篓匆匆出门去了。
九月,霜降将至,田地里的谷物早已收割进仓,一山接一山,一岭连一岭的油茶林这时又燃起了丰收的希望,油茶果成熟,透着一种油光发亮的赭红,秋阳里,满枝头像是举起一束一束烧透的火焰。
岭上村的人们盼望了一年,等待了一年,满枝头的油茶果采摘下来就是钱啊。岭上村跟别的村寨有些不一样,外出打工的人不像别的村那么多,可他们却说幸福指数并不比别地方差。岭上村的人们对幸福指数的含义理解得并不怎么透彻,不过就是那阵邹杰做村主任的时候,从乡领导嘴里学来的词儿,现买现卖说给大家听,人们把这词儿就用上了。在他们眼里,有饭吃,有衣穿,有房子住,口袋里还有钞票揣着,幸福指数就算是老高了。做农民的,知足。
小四轮打着响屁从坡下爬上来,采摘油茶果的人们就知道是郑新回来了,从油茶林里钻出来,站在简易公路旁边,等着他的到来。
岭上村就郑新有小四轮,跑运输,还跑客运。岭上村到乡场不过七八里路,人们去乡场三元,带货按重量加钱,一个来回少说也得十来块钱。人们算过账,就这一项,郑新一年就有上万的收入。
今天人们等他,是想打听油茶果的价钱。岭上村二百多户人家,有油茶林四千多亩,采摘的油茶果留下一些自己榨油吃,大部分要卖掉,价钱就成了人们特别关心的事情。前不久郑新开会说,他要跟大家签合同,油茶果由他收,钱由他付,一个价,卖贵卖贱大家就没有风险了。邹杰不同意,说还是自己卖,价钱涨涨落落,自己把油茶果交给收购贩子,一手交货,一手收钱,心里踏实。你郑新仍然还是收你的运输费,也省心啊。这些年,郑新就是这么做的,到了收油茶果的季节,他的小四轮来来回回地跑,要挣一大笔运费。现在,郑新是村主任,心里的盘算当然也就不一样了,按他的想法,把全村的油茶果低价收来,再高价卖出,赚的会更多。邹杰却挡了他的财路,已经上门跟邹杰吵过多少次架了。
小四轮的驾驶室还坐着郑新的女人刘友秀。岭上的人们说,刘友秀百样不会,但会哄男人。郑新就把刘友秀放在心肝上去了。她说要去乡场,郑新再忙,也要把手里的事情放下来,开着小四轮陪她去乡场。刘友秀说口袋没钱了,郑新借,也要给她借些钱揣在口袋里。
今天,不知道是刘友秀要去乡场,还是郑新要跑客,才半晌午,就从乡场打转回来了。小四轮还没停下,人们已经围了上来,他们不关心郑新和他女人去乡场做什么,他们只关心与自己有关的事情:“今年的油茶果价钱如何?”
郑新却是板着脸道:“要你们把油茶果卖给我,你们不干,能卖到好价钱?”
挂在人们脸上的期待,就变成了失望。但他们认准一个理,老支书不松口,他们是决不会把油茶果卖给他郑新的。
郑新这时又说:“卖不到好价钱也就罢了,我们从别的地方把损失补回来。”
“你又有什么主意了?”
“晚上开会对大家说。”
小四轮打着响屁走了,人们的心里就更加的不踏实了。
“老支书,你说油茶果卖给他郑新和我们自己卖与价钱有什么关系啊?”有人憋不住,去找邹杰诉说,“郑新还说晚上开会要对大家说什么好消息呢。”
邹杰拧着眉头说:“能有什么好消息,只怕又要折腾别的什么吧。真不知道他心里想的什么。”
人们在邹杰这里得不到答案,带着一肚子的疑惑走了。邹杰脸上的忧郁也更加的重了,想起早晨郑新在禾场上骂他的话,心里还一阵一阵地发疼。
二
“邹杰,你把邓荷花带回来做什么,我们是回家考义务兵的。”
一路上,郑生林都在抱怨邹杰,可他的心里却是对邹杰羡慕得不行,要是邓荷花看上他郑生林,死心踏地跟着他,他就不去当义务兵了。
“这么多年了,岭上村才考上两个义务兵。百里挑一。报名,只是个态度问题,能不能考上还很难说。再说,她要跟着我,我能把她赶走么,没看见人家都活不下去了啊。”
郑生林就不做声了,回头看一眼远远跟在后面的邓荷花,羡慕嫉妒恨全都有了。跟邹杰比,自己并不比他差到哪里去,可她邓荷花为什么偏偏只喜欢他邹杰啊。
邹杰和郑生林跟着田坪乡(那时叫人民公社)几百号青壮年在邻县修铁路,住在邓荷花的村子里。几天前,田坪乡的领导打电话通知邹杰和郑生林回去考义务兵,把他们俩可乐坏了,那时,农村青年要想改变脸朝黄土背朝天土里刨食的命运,只有一条出路,当兵。背着被子连夜就往家里赶。
走了一天一夜,两人才发现后面跟着一个姑娘,是邓荷花。邓荷花的父亲死得早,她是跟着母亲长大的。邓荷花家的成分有点高,村里(那时叫大队)开批判斗争大会,总要把她娘叫上台陪伴那些地主富农分子,面前挂一块牌子,一跪就是大半天。母亲经受不住折磨,上吊死了。那时邓荷花才十八九岁,举目无亲,孤苦伶仃,日子过得有多难。
邹杰和郑生林认识邓荷花纯属偶然。那天吃过晚饭,两个年轻人无所事事地在村子里瞎逛。按照郑生林的说法,他们住的这地方比岭上好不到哪里去,三十里外也能看到冒起的穷酸气。邹杰却说:“可人家这地方有发展前途,日后铁路修通了,一切都会好起来。
郑生林叹息说:“我们岭上别说修铁路,公路都没有,年轻人都成光棍了。”
邹杰叹的气比郑生林更长,更重:“我们俩也脱不了打光棍的命啊。”
两人说话的时候,突然就听到那边山脚有喊救命的声音。邹杰和郑生林拔脚就往那边山脚跑去。
天刚刚黑下来,他们隐隐约约看见山脚有一户人家,声音是从那户人家传出来的。邹杰和郑生林来到门前,郑生林还有些犹豫,邹杰却是不管不顾地抬脚把房门踢开了。一个中年男人正把一个姑娘按倒在床上,两手撕扯着她的衣服。邹杰扑上去,只几个回合,打得中年男人落荒而逃。
姑娘就是邓荷花,哭着扑进了邹杰的怀里,邹杰问:“这男人是谁,他会不会再来?”
“……”邓荷花的身子还在不停地发抖。
“你家里就你一个人?”
邓荷花点了点头,泪水把邹杰的胸口也染湿了。
“明天吃过晚饭,我还来这里。”一股英豪之气从邹杰的胸口冲起。
回来的路上,郑生林问邹杰:“明天吃过晚饭你真的要来这里给她搭伴?”
“姑娘家,没有父母,没有兄弟姐妹,孤苦伶仃,还受人欺负,可怜。”
邹杰没有失言,过后的日子,吃过晚饭他就会到邓荷花家去。邓荷花就知道邹杰是哪里人,当然也知道那个叫做岭上的山村是个很穷很穷的地方。
“荷花,你跟着我做什么?”
“跟你回岭上去。”
“我是回去考义务兵。”
“你考义务兵和我做你的女人不矛盾的啊。”
“岭上那地方穷。”
“你早就对我说过。”
邹杰就不做声了。他想,义务兵不过就三年,她不嫌弃岭上穷,愿意等自己,当然好。
邹杰和郑生林是乡武装部长带到县里去体检的,乡武装部长说:“我们田坪八十二个适龄青年,我把八十二个人的三代祖宗都查了个遍,就你们几个人最干净。其他的人不是自己家有问题,就是亲戚家有问题,有一个适龄青年身体条件和家庭条件都特别好,谈的对象家里的成分却高了点。我要他把对象吹了,他不干,说家里穷,谈个对象不容易。这样的觉悟能当兵?你们几个是我们乡的种子选手,我的想法,你们都要考上义务兵,为田坪争光,你们自己日后也才有好的前途,就像我,年轻的时候不当义务兵,现在能当国家干部么。”
邹杰当时脸就黄了,他们要是知道自己家里住着一个成份有点高的姑娘,当兵就没指望了。后来,他就想,义务兵百里挑一,不定身体哪里有问题,就回家好好跟邓荷花过日子吧。
没有想到,身体检查却是一关一关顺利地过了。倒是郑生林在第一道关口就被刷了下来。面前摆着三个瓶子,一个瓶子装的白开水,一个瓶子装的醋,一个瓶子装的酱油。邹杰鼻子没挨着瓶子就说了出来,郑生林却是闻了许久,也没有说出三个瓶子里冒出的什么气味。郑生林分辩说要不是这几天感冒,他的鼻子比狗还灵,站在自家门前,能闻到村里谁家炒菜油放得多,谁家炒菜油放得少。乡武装部长这时也不把自己当成干部了,低声下气求情说郑生林家三代赤贫,觉悟高,国家要的就是这样的人才。可接兵的部队领导却是铁面无私,说保卫祖国,来不得半点假,不然,就会亡党亡国。
两人从县里回来,郑生林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他面前的那条能改变自己命运的五彩大道已经断了,贫穷落后的岭上村将要伴随他一辈子。邹杰的样子也好不到哪里去,他心里纠结得不行。邓荷花住在自己家里的,领导知道了,自己该怎么说。承认邓荷花是自己的女朋友,当兵的机会就会失去,不承认吧,邓荷花怎么办。
邓荷花早就哭成了泪人儿,她为邹杰考上义务兵高兴得哭,她也为自己走投无路哭。
郑生林说:“荷花,邹杰娶了你,他的前途就完了。你回去也不行,我们不放心。去我家吧,我会好好待你的。”
邓荷花哭得更加的厉害,在她的心里,只有邹杰一个人。
邹杰舍不得邓荷花,他的父母也舍不得邓荷花,可是,不这样又能怎么办,邹杰说:“荷花,我爹我娘是你的亲爹亲娘,我就是你的亲哥。跟着生林好好过日子,哥就放心了。你要回去,哥就不去当兵了。”
离开岭上去部队的前一天,邹杰把邓荷花送到了郑生林家里,千叮嘱万叮嘱。邓荷花说:“哥,我在岭上落脚,就因为有你啊。我会好好跟着生林过日子的。”
邹杰当兵的第三年,父母托人给他找了个对象,名叫钱秋香,钱秋香愿意嫁给邹杰,一个主要的原因,是他在部队表现好,立过功,入了党,还提了干,就是复员,国家也会安排工作,不会回到岭上来。
邹杰当了五年兵,复员之后果然安排到田坪旁边的一个乡做民政委员,听领导的口气,邹杰日后一路往前走,去县里都不是没有可能。
谁都没有想到,邹杰在那个乡才当了半年干部,他就离职回家当农民来了。钱秋香哭得死去活来:“你不对我想,也得对我肚子里的孩子着想啊。你做干部,日后孩子也就离开岭上这穷地方了啊。”
邹杰说:“我离不得你。”
这话钱秋香只相信一半,男人对他好,她能感觉出来,但她知道男人的心里还装着邓荷花的。男人对邓荷花没有非份之想,他是把邓荷花当成他的亲妹了。邓荷花跟着郑生林,日子不好过,他这个做哥的心里疼。
“荷花跟郑生林结婚快六年了,怎么就没有生下一儿半女。有了孩子,她的日子或许就会好过一些。”
夜里,邹杰把一只手放在女人的肚子上轻轻地抚摸着,钱秋香已经怀孕几个月了,孩子在娘的肚子里蹦跳得那个欢。
钱秋香说:“荷花经常吃药,肚子却是大不起来。郑生林的母亲在世的时候,还护着她,母亲死后,郑生林动不动就打她,骂她。没爹没娘,真可怜。”
郑生林把那时的承诺抛脑壳后面去了。邹杰去找他,说:“我是她哥啊,你动不动就打她,我心里不好受。”
郑生林却是一脸的愠怒:“怎么说也得给我生个孩子吧,占着窝不拉屎,别人骂我绝代鬼。”
“是她不能生?”
“不是她,还是我?”
“不生孩子不一定是女人的问题,这是科学。”
“当了几年兵,你也知道科学了?”
“我给你们一点钱,两人一块去县医院检查一下,吃药才有的放矢,不然,药就白吃了。”
郑生林带着邓荷花去县里住了两天,回来的时候,郑生林像是鬼打一样,勾着头再也抬不起来了。邓荷花也是一脸的泪水,对邹杰说:“哥,这一路来,他对我说好话,求我,说我走了,他就得打单身。可我真的不想跟他过了啊。”
邹杰知道不生孩子的原因不是邓荷花,而是郑生林,说:“你准备往哪里走?”
“娘家没有亲人,我也不知道往哪里走?”
“那就别走。”
眼泪一滴一滴从邓荷花的脸上淌落下来:“六年了,他没有把哥的话记在心里,打我,骂我,把我不当人。”
“也许,现在他不会那样对你了。”
邓荷花抬起泪流满面的脸,柔柔地说:“回来的路上,他哄我说,我心里有哥,我哥心里也有我,他要哥帮忙给他生个孩子。”
邹杰浑身不由一阵颤抖,说:“这不行的,对不起你,对不起生林,也对不起我家秋香啊。你跟生林商量一下,要不我让秋香给你们生一个孩子吧。”
邓荷花哭着说:“不用跟他说,他由我,我不想离开哥,就只有这样了。”
“这样的大事,怎么能不对他说。我去跟他商量商量。”
几天不见,郑生林像变了个人一样,目光无神,说话也是低声下气的,邹杰的心里不由生出怜悯,哪个男人愿意说出那样的话来。他说:“生林,我们俩如亲兄弟一样,我让秋香给你们生个孩子。”
郑生林无神的眼里闪过一缕光亮,只是,瞬间又暗淡下来,说:“割的肉不亲,日后长大了,还认我这个父亲么?”
邹杰说:“不让孩子知道不就是了。”
郑生林不相信地看着邹杰,说:“你能做到?”
“我跟我家秋香不说,你们自己也不说,孩子怎么知道。”
郑生林还是不相信:“到时候孩子养大了,你又说是你的了。”
邹杰说:“我什么时候骗过你?”
郑生林嗵地一声跪倒在邹杰的面前,两行泪水随之滚落下来。
钱秋香是个贤惠女人,男人把邓荷花当成了亲妹,她也就把邓荷花疼在心里了,指着自己渐渐隆起来的肚子对邓荷花说:“头胎是我跟你哥的,二胎就给你们生。不然,你的日子不好过,你哥这辈子也别指望有舒心的日子了。”
钱秋香生孩子的那天,邓荷花一直守在她身边的。邓荷花从心里把钱秋香当成自己的亲嫂嫂了,嫂嫂生孩子,她当然得照顾啊。
一个漂亮的女孩呱呱落地,只是,钱秋香的肚子里居然还有一个东西在蹦跳。
邓荷花那个高兴:“哥,嫂嫂怀的是双胞胎。”
邹杰当然也高兴,说:“双胞胎好啊。双胞胎你就抱一个去。”
邓荷花那张愁苦的脸上流露出难得的笑容,笑容里却又淌下了两滴晶莹的泪水。
钱秋香看着面前这个苦命的女人,说:“我说了,第一胎是我跟你哥的,第二胎是你的。双胞胎,先生的是我跟你哥的,肚子里这个生下来你就抱走吧。把奶接来,让孩子吃你自己的奶长大,孩子就是你自己的了。”
邓荷花感动得泪水哗哗直流,哥是自己的哥,嫂嫂也是自己的嫂嫂啊。
一会儿,钱秋香就把肚子里的第二个孩子生了下来,是个儿子。邓荷花看着站在一旁的邹杰。邹杰说:“你嫂嫂说了,后生的这个是你的,你抱走吧,好好待他,我和你嫂嫂就放心了。”
邓荷花抱着浑身沾满了血水的儿子,说:“儿呀,长大了可别忘记你的亲爹亲娘啊。”
邓荷花抱着儿子跨出邹家的房门,跟郑生林撞了个正着,郑生林什么时候也到邹家来了,只是没敢进房去。他把嗓门提高了八度,对邹杰说:“外甥长大了,不会忘记你这个舅的。”
三
这天晚上的会议,邹杰没有去,邹杰行动不便。钱秋香也没有去。看见郑新,她的心里像是有一把刀子在剜,有生生的鲜血流出来。
这天半夜的时候,却有人来敲邹杰的门了:“老支书,郑新又有新的主意了。”
“什么新主意啊?”腰疼,邹杰在床上辗转难眠。
“卖掉岭上的五千亩山林,外地一个姓吴的老板要在岭上办中药材基地。”
“岭上的山林加一块也就五千亩,那四千亩油茶林他也要卖掉?”
“每亩三千块钱,一次性买断。”
“他怎么就放心不下岭上这片油茶林。每亩三千块钱,也就三年的收成啊。”
“郑新说过几天乡党委赵书记要带着吴老板来岭上跟大家签合同。”
“这个狗东西啊,去年,说要改造油茶林,每亩给五百块钱,由村里统一改造,今年,又说由他统一收购油茶果,现在倒好,干脆把油茶树连根刨掉。”
“他说吴老板造的杜仲林,三年成材,五年收回成本,十年大赚。”
“买断了,大赚不大赚与岭上有什么相干?”
“我们拿不准,只有来你这里讨主意了。”
邹杰叹气说:“我不是村领导了,岭上的事情我作不了主,你们自己看着办吧。我那十五亩油茶林决不会卖给他们栽什么杜仲树。每年九月,把油茶果拾回来变成钱,一年就够用了,发不了财,穿衣吃饭不愁。”
“你不卖,我们当然也不会签那个合同的。”
第二天早晨,邹杰吃了半碗稀饭,拄了根棍子,要跟着钱秋香去油茶林收油茶果。
钱秋香不让:“我一天拾一点,十天半月就都拾回来了。”
邹杰说:“在床上躺着憋得慌。”
两位老人还没有出门,刘友秀却来了。刘友秀穿着一件高腰紧身衣衫,领口却低,两个奶子高高地隆了起来,口红描得重,像猴子屁股一样。邹杰的眉头早就拧了起来,把头扭向一旁。
钱秋香问她:“友秀,你有事?”心里嘀咕说,“弄成这么个样子,荷花也不说一说。”
“我家郑新说,这次你们要是坏了他的好事,他不会罢休的。”
邹杰当然知道她说的好事是什么,嘴里说:“什么好事,我还不知道呢?”
“装吧。”
钱秋香说:“你舅这几天腰疼的病又犯了,躺在床上没有起来啊。”
刘友秀身子一扭,丢下一句话就走了:“郑新他爸说,你邹杰在,他家郑新就别指望做好这个村领导。你那腰疼病,怎么就不会死人呢。”
钱秋香和邹杰都听到这句话了。邹杰的脸面煞白,钱秋香淌着眼泪说:“不孝的家伙,要遭雷劈的啊。”
邹杰家的油茶林在村前的山腰处,离家没多远。到了八月,把水田里的谷子收了,就准备收油茶果,十月的时候外地收油茶果的老板来岭上,一手交货,一手交钱,下一年用钱就不用发愁了。
也许,邹杰早就想到有这么一天,女儿出嫁了,他们也老了,这油茶林就是他们生活的依靠。
村路上有突突的马达声响。邹杰知道是郑新找自己来了。
“昨天夜里散会之后有人到你家里了吧。你怎么老是跟我作对,我没有挖你家的祖坟啊。要挖,也得等你死后,挖你的坟。”
钱秋香气得直哭:“儿呀,清早友秀去家里骂,现在你又骂这样毒的话,你们要遭雷劈的啊。”
邹杰打断女人的话,对郑新说:“你怎么总是放心不下岭上这四千亩油茶林,你就不能弄个别的什么项目,让大家发财致富么。”
“你知道在岭上办中药材基地就不能发财致富了?”郑新心里好笑,叫你们舅,你们就真的把自己当舅了,平时叫我新儿,现在把新字也去掉了。
“办中药材基地我不反对,把四千亩油茶林毁掉,多大的损失你算过没有?”
“我不跟你说,赵书记会来找你的。”
“赵书记来找我我也是这么说。”
郑新的态度就变了,说话的声音也轻了许多,说:“我忘了告诉你,赵书记带信说,你的基层干部补贴,是可以上报的。还有你们家的低保,也可以享受。”
邹杰没有做声,钱秋香一旁说:“其实,这两件事情办不好,不是赵书记那里的问题,是你不同意。新儿,你舅这辈子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累,如今动不得了,还要拄着棍子来山里拾茶果。”
郑新说:“那阵我想做村主任,他坚决不同意,赵书记亲自来岭上开会让我当上了村主任,他还要想着法子跟我过不去,我为什么要考虑你们家的困难呢。”
邹杰说:“我不让你做村领导,因为你还不够格。果然吧,这几年,你都做了些什么,我的脸都丢尽了啊。”
郑新的脸有些发青,还想跟邹杰争辩什么,刘友秀却站在村口大声地叫喊:“郑新,赵书记打电活你怎么不接,他要你快去乡政府。”
郑新开着小四轮走了。邹杰叹气说:“真的不知道他心里想的什么,折腾来折腾去,吃亏的是岭上的群众啊。”
“你管不了那么多的。”钱秋香还有句话没有说出来,你挂在嘴边的一句话,郑生林是你的好兄弟,可你这个好兄弟却没有把你当做好兄弟。
邹杰说:“不说他了,越说心里越烦。茶果收了,你去看看邹芳吧,我们家邹芳的日子不好过啊。”
“寄点钱去就是了。你一个人在家我不放心。”
九月,秋阳高照,岭上人家收茶果的季节,满山遍岭都是欢歌笑语。邹杰最喜欢听的就是这样的声音,最喜欢看到的就是这样的情景。做了几十年村领导,给人们留下了这点财富,他心里还是感到很欣慰的。
四
“哥,嫂,生林把郑新当成了宝贝,郑新都十岁了,吃饭要把饭碗递上手,有时还要把鱼呀肉呀喂到他嘴里。”常常,邓荷花来对邹杰和钱秋香这么说。
邹杰说:“对生林说,不要娇惯郑新,要他好好读书,日后考大学,到城里去工作。”
邓荷花脸上的笑容就没有了,变成了一脸的忧愁,说:“小学三年级了,邹芳每次考试第一名,郑新每次考试倒数第一名,谁都争不去的。我对生林说,他说他就不想郑新考什么大学,离开岭上,郑新就不一定是他的儿子了。”
那天,邹杰对郑生林说:“生林,我放着干部不当,回来当农民,是想把岭上的面貌改变一下,不然,郑新他们日后长大了,老婆都难得讨到的。”
郑生林浑身不由打了个哆嗦。钱秋香生了个龙凤胎,却把儿子给了别人,是不是后悔了,说话总是离不开郑新。嘴里说:“后山的水渠修通了,岭上的水田年年有好的收成,吃饭不成问题了。你说还要做什么?只要能让我儿子长大之后过上好日子,我都愿意做。”
这话当然含有别的意思,郑新不是你邹杰的儿子,而是我郑生林的儿子。
邹杰并不在意他说的这话,说:“第一步完成了,现在得走第二步,造油茶林,每家每户造十五亩油茶林,岭上就不缺钱用了。当然还有第三步,修路。把公路修通,就不愁没姑娘到岭上来。”
“这得多长时间?”
“十年。那时我们也才五十多岁,还能帮着孩子做些事情。”
“好。这第二步第三步都实现了,岭上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郑生林知道不能把对邹杰的防备流露在脸面上来。
“爸,姐姐又打我了。”
邹杰和郑生林说话的当儿,一个男孩跑过来,他的后面跟着一个女孩。男孩是郑新,女孩是邹芳。两家虽是相隔一面小山坡,两个小孩却经常在一块玩,上学之后,两个小孩更是成了形影不离的好朋友。按他们自己的说法,两家的父母关系那么好,他们看在眼里,当然就是好朋友了啊。
郑新对爸爸告过状,转过身,又在邹杰面前告状:“舅,邹芳姐又打我了。”
郑新还在呀呀学舌的时候,邓荷花就要他叫邹杰舅,叫钱秋香舅妈,叫邹芳姐姐。
“我没打他,是他抢我的玩具。”
“什么玩具,给弟弟玩不就是了。”邹杰对邹芳吼道。
这话让郑生林心里很不是滋味,从口袋掏出一块钱,说:“别争,等会去商店买就是了。”
郑新说:“还要给我一块钱,我要给我姐。”
郑生林扬起手,打了郑新一个耳光,心里说,刚才还打架呢,心里却想着这个姐。郑新就不依不饶了,又是哭,又是闹的。钱秋香骂邹芳道:“你哪像个姐姐样。”过后在口袋里掏了一阵,掏出两块钱,各人给了一块。
郑生林的脸色变得更加的难看,把郑新抱在怀里,说:“回去,我给你两张大票子。”
郑新说:“说话不算数,你就是小狗。”
郑生林说:“只要听爹爹的话,爹爹说话肯定算数的。”抱着郑新头也不回地走了。
邹杰对钱秋香说:“往后,对郑新要冷淡一点。没看见郑生林不喜欢的么。”
钱秋香的眼泪就出来了:“我做不到。”
邹杰叹了一口气,说:“把心疼放在心里。”
这时,邹芳却是无话找话地问父母:“我怎么跟郑新同一天出生?”
“谁说的?”
“姑姑。”
邹芳说的姑姑,就是邓荷花。邓荷花要邹芳叫她姑。
邹杰板着脸说:“同一天出生要什么紧。”
“同一天出生,姑为什么要郑新叫我姐。”
两行眼泪挂在钱秋香的脸上,她说:“你比郑新早出生,他当然要叫你姐。”
“我早出生多久?”
“你早晨生的,郑新中午生的。”
“这就是说,我比郑新大半天。”邹芳的脸上流露出天真的笑。
钱秋香说:“要努力读书,你爹说了,再苦再累也要送你上大学。”
邹芳却说:“我们班上一些同学说,他们的哥哥姐姐初中没读完就打工去了。”
“谁去打工都行,你不能去打工。”
“为什么?”
“你爹舍不得,我也舍不得。我们就你一个女儿。”
“就我一个女儿你们就得心疼我,依着我。”邹芳小小年纪,却口齿伶俐,说话像个小大人。
“依着你什么?”
“现在不对你们说。”
钱秋香看着女儿,心里全是怜爱,嘴里却说:“你看看你爸,修水渠落下的病痛,变天就发。你要听你爸的话,别气着他才是。”
“我爸那阵为什么不愿意当干部,要是不回来,我就成了什么领导的女儿,我娘也不会这样吃苦受累的。”
邹杰瞪着女儿说:“你才多大,也说这样的话。”
“你做得,为什么我说不得。”
女儿的话,说得邹杰无言以对,原本痛苦的脸显得特别的难看,钱秋香嘴里说着女儿,眼泪却是更加的多了。
邹芳却不管这些,眼睛盯着郑新渐渐远去的背影,稚气的脸面显得特别生动,她一定是在想着什么高兴的事情了。
郑生林背着郑新,走在回家的路上,他说:“儿子,你知道爸为什么要打你么?”
“不知道。我爸从来都舍不得打我的。”
“记住,今后不要跟邹芳一块玩。”
“为什么?”
“没看见他们不喜欢你么。”
“没有啊。舅舅舅妈都很喜欢我,有好吃的,都要留一点让我吃,刚才舅妈还给我一块钱呢。”
郑生林的心越发地往下沉去,说:“那都是骗你的。邹芳她爸当村主任的这些年,经常欺负你爸。”
郑新就十分地吃惊了:“怎么看不出来,他欺负你,你怎么还要去他家?”
“去他家,不过是想讨好罢了,不然,他们会更加欺负我。你不知道吧,如今国家政策多好,可上面下来的许多好处,都被他给扣下了。”
郑新想了一阵,说:“我长大了也要当村主任。”
“好,我儿子有志气。”
郑生林背着郑新还没回到家,却看见邓荷花提着竹篮走出门来,郑新问:“妈,你要去哪里?”
“你舅妈说,她家的母鸡要孵儿了,送几个鸡蛋去。”
“别去。邹芳她爸最坏了。”
“谁说的。”
郑新看着爸,不做声。邓荷花就知道是谁说的这话了,瞪了男人一眼,就走了。
郑生林说:“看见了吧,你妈也怕邹芳她爸,要你叫邹芳她爸舅,不就是想拉拉关系,别让她爸欺负你爸么。平时,家里有什么好吃的,你妈都得往她家送。”
郑新说:“我在学校读书跟邹芳坐一张桌子,明天去学校,我要老师把邹芳调开,不跟她坐一桌了。”
郑生林说:“那不行,邹芳回家跟她爸说,吃亏的还是你爸,心里记着就行。”
郑新小大人似的咬着牙说:“我把恨记心里了。”
五
乡党委赵书记和吴老板是在这天中午来到岭上的。赵书记名叫赵前生,大学毕业就在县委办做秘书,写得一手好文章,做了十年秘书,从一般秘书做到了副主任,按说还是不错的,再等几年,做主任进常委也有可能。可是,他却坚决要到基层来。还说要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县委书记就让他到田坪乡来了。田坪乡在全县算得偏远落后的地方。赵前生一介书生,哪里知道农村的真实情况,下来之前曾夸下了海口,三年之内,要让田坪乡变个样子。他心里的小算盘,在农村打个转,往前走一步就不会等那么久了吧。可是,来田坪乡两年,田坪乡并没有多少变化。赵前生正在束手无策的时候,却来了一个愿意在田坪投资办实业的吴老板,赵前生那个高兴,把吴老板视作座上宾,好吃好喝,还给了他许多优惠政策,吴老板说:“行,我在田坪办个中药材基地吧。”
赵前生说:“田坪乡没有别的,山地却有,由你挑。”过后就把全乡一十八个村的情况向他做了介绍。
吴老板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我要实地看一看。”
赵书记就带着吴老板一个村一个村地走。田坪乡不富裕,但田坪乡的群众待客却特别的热情,两人走到哪里,吃的是土鸡,喝的是农民自己做的糯米酒,走的时候,还大包小包地让吴老板带。可是,走了十几个村,吴老板却是只摇头,眉头还紧紧地拧了起来。到了岭上,吴老板看着满山遍野的油茶林和油茶树上挂着的累累果实,看着油茶林旁边一栋一栋漂亮的小砖房,脸上才露出了笑容:“这个村比别的村富裕?”
赵前生说:“这个村去城里打工的并不多,日子却过得不差。”
“说详细一点。”
“这个村有四千亩油茶林,每亩油茶林每年收入一千元,每年的收入就四百多万,二百多户人家,多的人家每年有三四万的收入,少的人家每年也有一万两万。日子当然就过得比别的村滋润。”
吴老板说:“就岭上村吧。油茶林长得这么好,挂果这么多,说明这里的土质不错,用来种杜仲肯定是没问题的。”
开始的时候,赵前生还真有点为难,全乡十八个村,能摆上台面的,就是岭上村那四千亩油茶林。刚下来的那阵,他还带着县委书记来岭上村看过。毁掉油茶树,再栽杜仲苗,还真的可惜了。他说:“其实,岭下村的土质也不错的。要是当年岭下村的领导有邹杰那样的眼光,现在跟岭上村一样,也有这样的绿色银行了。”把岭上村的油茶林说成是绿色银行,是赵前生的发明,那天带着县委书记来岭上看油茶林,他就是这样说的。
“不,我就看上岭上村。五千亩杜仲林,三年长苗,五年成材,十年大赚。”
赵前生还是面有难色:“毁掉油茶林,那是断了人家岭上村的经济来源,不把他们安排好,只怕群众不同意。”
“你不是说了么,岭上村的群众富裕啊,这点小损失算什么。”吴老板掰起手指头算起账来,“要说损失,也就是第一年要花一点成本,第二年就赚钱了。”
“杜仲不是速生林,怎么第二年就有收入?”
“第二年可以采摘杜仲叶卖钱,每亩每年的收入跟油茶林的收入相同,第三年收入二千元,第四年收入三千元。”
赵书记的眼睛瞪得老大,这不是天方夜谭吧。
“我还要在岭上办制药厂,就地加工。”吴老板话锋一转,“我有两个方案,一个方案是一次性买断五千亩山地,一个方案是入股分红。”
“怎么买断?”
吴老板沉思一阵,说:“每亩三千元,岭上的男女劳动力进制药厂当工人。”
这天中午,赵书记要郑新把大家叫到村委会召开群众大会。不等吴老板把话说完,邹杰就站出来反对说:“每亩三千块钱,也就三年油茶果的收入,往后我们岭上人就都成了你吴老板的长工。油茶林的寿命少说也有三百年,多少代人不受穷。”
郑新正要发作,赵前生却拦住了他,拧着眉头说:“当工人不好么,按月拿工资,旱涝保收,还天晴在荫处,下雨在干处。”
“给人家打工能发财么?我们乡多少年轻人在城里打工,有几个人发财了,不过就挣点辛苦钱。”
赵前生无言以对,对吴老板说:“把你的另外一个方案对大家说说吧。”
吴老板的脸上带着笑,他等着的就是有人反对,说:“那就入股吧。入股就不存在给我打工了,大家都是老板,赚了钱大家有份。”
邹杰问:“入股是什么意思?”
“我在岭上办中药材加工厂,你们种杜仲,我按成本价收购,制成中药材出售,赚得的钱大家分红利。但有一条,杜仲树苗必须由你们自己掏钱买。”
“我们哪知道到哪里去买杜仲树苗啊。”
“你们就是知道哪里有杜仲苗子卖,人家把苗子价钱抬得老高不说,你们也看不出苗子的好坏啊。我的要求,这一季油茶果收完,立即动手砍掉油茶树,翻挖土地,明年二月动手栽杜仲苗,三个月完成。杜仲苗很娇贵,过了五月,就栽不活了。”
赵前生对郑新说:“就按照吴老板说的办,油茶果采摘完,就开始行动。”
吴老板说:“今年冬天,我就做一件事情,采购杜仲树苗。每苗按照四百元的苗子款给我把钱准备好,我就提着款子去买苗子。”
吴老板话没说完,邹杰又站出来反对了:“按说,你吴老板要把油茶林毁掉栽杜仲苗,办中药材基地,得先给我们风险金才是,现在,还要我们掏钱买树苗,风险就全让我们自己承担了。我家的山地不种杜仲苗,我也不想日后分红发财了,每年采摘的油茶果有那么多收入,过日子足够。”
邹杰不同意,全村的人也都不同意了。郑新看着赵前生,赵前生气得喘粗气,却又找不到说服邹杰的理由,能说邹杰担心的不对么。郑新就站起来横眉冷眼地跟邹杰干上了:“平时,我说什么,做什么,你都要站出来反对,我做村领导的这几年,什么都干不成。现在,你还敢跟赵书记对着干啊。”
吴老板连忙上前劝架,说:“谈不成,就算了,我还真没有想在这里办中药材基地呢。简易公路,小车跑几次都得短命。民风也不淳,把几千万往这里抛,收不回,我就亏大了。”说着,就要走,“我去前塘乡看看,那里的书记乡长刚才还给我打电话呢。”
赵前生拦着他说:“慢慢商量,问题总会解决的。”
吴老板问他:“真要定下来在这里办中药材基地,就得先掏钱买苗子,每亩四百,热巴巴的钱,他们愿意么?”
“资金的问题是可以解决的,他们不愿意掏钱,乡政府想办法先垫付一部分资金也行。”赵前生下了决心,这个机会是决不能失去了。
吴老板有些不耐烦:“你们商量好,不管谁掏钱,得落实。我在外面等着,等会就答复我。不然,我就去前塘乡了。”
赵书记把郑新叫到一旁,交代说,“分两步走,先造二千五百亩,一百万购苗子,乡政府负责五十万,你们自己负责五十万。”
郑新铁青着脸说:“大家眼睛盯着他邹杰的,他不拿钱,谁肯拿钱。”
赵前生想了想,说:“油茶果还没下树,要大家现在拿钱还真有点困难。我去对银行说,一百万全部贷款,先把苗子买回来。”
郑新还是有点犹豫。药材基地还只是一句话,却要每家每户背上几千块钱的贷款,月月还利息,邹杰这一关不得过。这时,他口袋里的手机却响了起来,是吴老板打给他的。吴老板说:“每亩四百元杜仲苗的报价,我给你打有算盘的。我只拿三百五十元,还有五十元是你的手续费。五天之后我来提款。年底把杜仲苗运来。明年三月底完成二千五百亩。后年开春再完成剩下的二千五百亩。”
郑新早就听说过,如今一些领导,就是靠着做工程发财,没有想到一大摞钱就从天上掉进自己口袋里了。他什么都没说,说了别人会听见,只嗯嗯了几声,就把电话挂断了,对赵前生说:“赵书记你对银行说好,吴老板什么时候签合同,我就去银行贷款。”
这时,邹杰又站了起来,说他有话要说。赵书记却不愿意听了,说吴老板还在外面等着的:“人家大老板,亲自来这里考查中药材基地,多大的面子啊。”钻进小车,下山去了。
郑新看着小车开出老远,想了想,跟在邹杰的身后往他家走去。
“舅,我一直也没有问你,腰疼好些了么?”
邹杰板着脸,仿佛还在想刚才开会的事情。钱秋香从灶屋出来说:“新儿,有什么事啊?”
邹杰和钱秋香一样,以前也不叫郑新,而是叫新儿。郑生林却不让,说:“你们新儿新儿地叫,郑新不生出怀疑么。还是叫郑新好。邹杰只得改口叫郑新。钱秋香却不,她仍然叫新儿,她说除非新儿不答应。
邹新说:“我是受赵书记的委托,来做舅舅工作的。赵书记说,舅舅是岭上村的老领导,应该支持岭上办中药材基地才是。赵书记还交代我,为了解决你们家的后顾之忧,基层干部生活补贴和低保随时可以去乡政府办手续。”
邹杰说:“给我家解决了后顾之忧,岭上别的人家怎么办?”
“担心中药材基地办不好?”
“油茶林这才有了几年好的收成,岭上村人们的日子刚刚好过起来,你瞎折腾什么。你就没听外面人说,四千亩油茶林,是岭上村人们三百年的绿色银行啊。”
“吴老板说的话,你也听见了,日后岭上村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了。”郑新想起爸爸说的话来,水渠,公路,油茶林,是邹杰在岭上村人们心里树立绝对权威的三件大事。自己要想取代他,让吴老板在岭上办中药材基地算是一箭双雕。他说,“赵书记说了,不管阻力有多大,中药材基地一定要办成的。”
郑新走后,钱秋香劝邹杰说:“你能不能替新儿想一想,让他把这件事做成。”
邹杰说:“能做成当然好,我就担心做不成。”这样说着,提着一个蛇皮袋子出门去了,“还早,拾一会儿茶果再回来吃晚饭。”
钱秋香这时却像是想起了什么,说:“我们女儿打电话来了。”
邹杰问:“说什么了没有?”
“问你的病好些了没。”
邹杰的眼角有些发湿,女儿很少往家里打电话,好不容易打个电话回来,真的只有一句问候的话么。
“也许,觉得爸妈都已经老了,我们女儿心里的气也就慢慢地消了啊。”这样说的时候,两滴眼泪啪哒一声从钱秋香的脸上掉下来。
六
邹芳考上高中的那年还不满十七岁,可她坚决不读书了,她要去打工。钱秋香说:“邹芳,你爸说了,读高中,上大学,日后找个好工作。”
邹杰一旁说:“不愿意读书,也得说出个原因吧。”
“郑新没有考上高中。”
“他没考上高中与你有什么关系。”
邹芳不再跟父亲说了,两个胳膊缠着妈,把嘴附在钱秋香的耳朵旁边说了句什么。钱秋香的脸就黄了,连连说:“不行的。”
“为什么不行,我们一块儿长大,青梅竹马,他喜欢我,我也喜欢他。”
“你们才十七岁啊。”
“我们没说现在就结婚。打几年工,挣点钱,再考虑结婚的事。”
邹杰还在黑着脸骂邹芳,钱秋香却是急匆匆地往郑生林家去了:“生林,你得好好管管郑新,我家邹芳不肯读书了,要跟郑新一块去打工。”
“郑新还跟邹芳在一起?”郑生林冲着郑新说,“爸说的话你忘了?”
郑新说:“你们是你们一辈子,我们是我们一辈子。”
“没看见人家找上门来了么。”
钱秋香对郑新说:“新儿,你们不能在一块的。”
郑新圆瞪着眼睛,寸步不让:“我说了,你们那一辈子的仇恨不要传给我和邹芳,我们不会听你们的。”
钱秋香惊愕地问:“新儿,我们两家有什么仇恨,你听谁说什么了啊?”
邓荷花一旁哭着说:“儿呀,你舅和你舅妈把你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你怎么说出这样的话来。”
郑新说:“为什么不让我跟邹芳在一起,我爸说的没错,分明两家有仇嘛。”
钱秋香劝他说:“你和邹芳才多大,屁事不知,就谈爱啊。我娘家隔房堂哥有个女孩,叫钱莹,跟你一块读书的,又漂亮又聪明,过两年我就给你说来做媳妇儿。”钱秋香心里有个小九九,儿子成了别人的儿子,把自己的堂侄女嫁给他,也算是扯着一根线了,日后老了动不得,才好唤他们啊。
郑新却说:“我只跟邹芳好,别的姑娘我不要。”说着,抛手就走了。
钱秋香哭着说:“没有别的办法,只有把他们是双胞胎亲姐弟说给他们听了。”
邓荷花看着郑生林,她也希望郑新知道这个真相,不然,郑生林说的那些话在孩子心里挥之不去,日后就成仇恨了。没有料到,郑生林扬起手给了邓荷花一巴掌,吼道:“我养郑新十七年,就这样退给邹家了。钱秋香,你回去问问邹杰,他说的话还算不算数。”
钱秋香当然知道男人曾经对郑生林的承诺。回来也不说话,只是淌着眼泪。邹杰说:“郑生林也可怜,要让郑新知道了真相,那个家就散了。”
“问题是他们姐弟俩要在一块啊。”
邹杰说:“邹芳必须得读书。读高中,上大学,她就不会回来了。”
没有料到,那天郑新和邹芳离开岭上就没有回来。两家那个急,四处寻找,才知道郑新和邹芳一块到深圳打工去了。岭下村一个初中没读完就辍学去深圳打工的同学给他们找到了一份工作。邹杰和郑生林只得坐车往深圳赶。车上,邹杰试探着对郑生林说:“这事还真的不好办了啊。”
郑生林黑着一张脸:“见了他们你别说话,我有办法把他们分开的。”
邹杰只得把要说的话又咽了回去。两人找到那个厂子,邹芳和郑新果然在厂子里打工,两人虽是没住在一块,却像是一对小夫妻,吃饭在一块,做活在一块,郑新换下的衣服邹芳给他洗,重活儿,郑新给她做。面对着一对不谙世事的儿女,邹杰等着郑生林开口说话。可是,郑生林问的却是打工苦不苦,累不累,钱够不够花。这样说的时候,从口袋掏出一摞钞票递给郑新,说:“饭要吃饱,衣服也不能穿得太差。”过后,又交代郑新,“邹芳是女孩子,更要穿好一点,有空了,就带她去商店买件漂亮衣服。”
邹杰那个气,扬起手给了邹芳一巴掌,骂道:“畜牲,还不跟我回去。”
邹芳的嘴角有生生的鲜血流出来:“我就不。”
邹杰的巴掌又要落下来,郑新不管不顾地冲过去,用身子护着邹芳,恶狠狠地说:“你说,为什么那么恨我们家?”
邹杰张了张嘴,还没有把喉咙里的话说出来,郑生林却是抢着说:“我们两家的仇恨解不开的。郑新,你要跟邹芳在一起,没有你的好日子过。”
邹杰浑身不由打了个颤,郑新张开的两手也不由自主地落下来。邹芳却是哭着说:“我不相信。要是有仇恨,你们为什么要我叫郑新他妈姑姑,要郑新叫我爸舅。”
“假的。”郑生林冷冷地说。
“爸,你说话啊。”
“……”邹杰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连他自己都不知道是否定还是肯定,过后,他用巴掌抽打着自己的脸,说,“你们要是在一块,我就死给你们看。”
郑生林对郑新说:“看见了吧,我说的能有假。”
邹芳一声声嘶力竭的哭喊:“郑新,我们来世相好吧。”冲出门,拦下了一辆从街口开过来的大巴车。
邹杰怔了怔,拔脚追赶,大巴车开过十字街口,无影无踪了。邹杰只得四处打听刚才那辆大巴车从哪里来,到哪里,旁边一个摆小吃摊子的中年女人说:“大巴车每隔两天就要在这里停一会儿,你要找他们,就只有在这里等两天了。”
“你知道那车跑哪里么?”
“长途。好像是从西南方向的哪个县开来的。”
邹杰就不管不顾地爬上旁边一辆中巴车,又连着转了几次车,赶到那个县城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的黄昏,那辆大巴车已经装满了去深圳的客人,正准备开车。邹杰问司机:“昨天爬上大巴车的那个女孩去哪里了啊?”
司机却是一片茫然,说:“我知道你问的谁呀。坐车的人多,而且大都是年轻人。”
邹杰说:“一个高高瘦瘦的女孩,才十七岁,在深圳城郊上的车。”
司机想了一阵,说:“昨天我车上坐了十二个女孩,有五个在广州就下车了,有两个在县城下的车,另外几个是沿途下的车。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个女孩?”
邹杰就认定在广州下车的五个女孩中一定有他的女儿。可是,广州多大的城市,人海茫茫,到哪里去找她?
钱秋香盼眼欲穿,盼着的却是邹杰一个人回来,眼泪就出来了:“我们家邹芳呢?”
“不知道到哪里去了。郑生林回来了么?”
“父子俩都回来了。新儿那样子是把我们当仇人了啊。”
邹杰想把郑生林说的话说给她听,想了想,还是没有说出来。
钱秋香说:“我们女儿才十七岁,在外面打工,怎么吃得了那个苦。”
邹杰无可奈何地说:“吃不了那个苦,她就会回来的。”
“你心肝上没血的啊,我们女儿的性格你不是不知道,她怎么会回来。田坪在深圳打工的年轻人多,你对他们说过么,要是知道我们家邹芳的下落,就告诉我们一声,我们去接她回来。”
邹杰说:“她不在深圳了,我再到广州去找一找,我们女儿一定在广州。”
过后的许多年,九月收油茶果卖了钱,邹杰就会去广州找女儿,口袋里的钱用完,他才回来。只是,却一直没有女儿的消息。邹杰铁打的一条汉子,说起女儿,居然也有两行泪水往下淌落。
七
郑新结婚的那年二十五岁,女人刘友秀是郑生林隔房表姐的女儿。邹杰和钱秋香都去喝了喜酒。看着郑新的结婚酒办得热热闹闹,两人也都十分的高兴,怎么说儿子在郑家的日子还是很好过的啊。
喝过喜酒从郑家回来,老两口老远就看见自家门前站着一个女人,提着一个小布袋子,面目憔悴,衣衫褴褛。两人走到门口才认出她是谁。钱秋香一声哭喊:“我的儿啊。”扑上去,把女儿紧紧地搂在怀里,“这些年你在哪里,怎么弄成这个样子了。你爹每年收了油茶果就出去找你,却总是找不到你啊。”
邹芳也哭了,一阵才说:“我已经结婚,孩子都三岁了。”
“是不是日子不好过啊,他打你骂你嫌弃你?”
“他没有打我,也没有骂我,更不会嫌弃我。”泪水却像是断线的珠子,簌簌地淌落,“他是外省人,我们在广州一家厂子打工相识相爱,我生孩子之后就去了婆家,没有料到,去年春节他回家过年,路上出车祸,一只脚被压断了,残废了。”
钱秋香就又痛哭起来:“我可怜的女儿啊,你的命怎么这么苦。”
“我回来,是要让你们知道,那阵你们不让我跟郑新好,我的下场就是这样,你们高兴了吧。”
邹芳转过身,就要离去。邹杰和钱秋香好不容易才把她拦住:“我的儿,你不能跟郑新结婚的啊。你们是亲姐弟。”
邹芳就呆在那里了:“怎么会是这样,你们怎么不早说?”
“你爸不让说。他说要是说了,你姑姑一家就散了。”钱秋香一边掉眼泪,一边把二十多年前邓荷花来到岭上的事情原原本本说给女儿听,“我的儿,你爸心好啊,善良啊,一辈子就只对别人着想啊。”
邹芳早就哭成了泪人儿,她说:“这样,我也不怪你们了。”
邹杰对女儿说:“你们的日子难过,是不是把他们父子俩接到岭上来,我跟你妈也好帮忙照顾啊。”
“他还有一个卧病在床的老娘。”
邹杰说:“那就住些日子再回去吧。”
“也不行的,我对他说一个星期就得回去,来回得坐一天一夜的火车,还要坐半天大巴车。住两天,我就走。”
两天时间,邹芳总是忙个不停,给父母洗衣服被子,里里外外地收拾,重活儿也都抢着做,一边做还一边掉眼泪,她是不放心爸和妈,她走了,这个家就只剩下两个孤孤单单的老人了。
这两天,钱秋香给女儿做了许多好吃的,看着女儿吃,夜里,老两口却是彻夜难眠,女儿那个样子,他们心里疼。
两天转眼就过去了,邹芳要走,还哭着说:“谁叫我是我爸的女儿,心里只想着别人。”
邹杰和钱秋香都没有留她。邹杰说:“儿呀,爸妈对不起你,给你一点钱,你带回去,接济一下。”
“不要。”
“你妈想跟你去看看我们的外孙,可以吗?”
“我妈去了,我不放心爸,我爸一身的病。”
“不用挂记我,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那就在我那里住几天就回来。”这样说的时候,邹芳就又哭了起来,“这一回去,可能要几年才能回来,我要去看看我的亲弟弟。”
邹杰说:“去看看你弟也好,但不能对他说你们是亲姐弟。”
眼泪从邹芳的眼里滚落下来,一阵才说:“那就不看了,看见弟弟,保不准就会说漏嘴啊。”
邹杰想送送女儿,邹芳不让,邹杰只得远远地跟在母女俩的后面,直到她们在乡场上了开往省城的大巴才回来。
“听说邹芳回来了?”
回来的路上,邹杰碰到郑新去乡场,郑新停下小四轮,这样问。
“住了两天,又走了。她男人出车祸,没了一只脚,残废了。”邹杰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要对他说这些。
“现在,你高兴了啊。”
“郑新,你怎么说这话。”泪水在邹杰的眼里晃动。
“我为什么不说这话,这个世上,我还没有见过你们这样的父母。”顿了顿,郑新说,“我想好了,今年年底村里换届选举,我要当村主任。”
邹杰问:“你真的有这个想法?”
“当然。”
“做村干部,有条件的。”
“什么条件?人家下坪村周小宝也是二十五岁做村主任。是你不想让出这个位子吧。”
“你要是做得了村主任,我能不高兴么。我做这么多年的村主任,累出一身病来,正想有个人接班啊。”
“我做村主任,会比你做得更好。”
“这些年,我怎么就没有看出来。”邹杰还有话没有说出来,郑生林把你教成什么样子了,村里几个五保老人因为没钱,去乡场从来都是走路,几里路来回要走一整天,你也看得过去。
郑新不跟他说了,开着小四轮走了。也许,他又接到什么挣钱的活儿了吧。
这年年底,岭上村换届选举的时候,乡党委书记也来了。乡党委书记对邹杰说:“你年纪大了,身体也不怎么好,做做村支部书记,把把舵,村主任让年轻人来做吧。”
邹杰说:“当然好,你看谁接这个班好。”
“郑新不是很好么。”
“他呀,太年轻了。”
“年轻有年轻的优势。”
“那就让群众投票吧。大家同意,我也没有意见。”邹杰想起郑新曾经对他说过的话,心想他在乡领导那里活动好了的,自己不同意也没有用,还是用选票说话吧。
选举结果出来,郑新只有三票,就郑家三个来开会的人投的票,其他的票,一张不少全都投给了邹杰。郑新那个气,说:“从明天开始,坐我的车涨价了,少一分,自己走路。”
这天晚上散会,郑生林去了邹杰家,说:“怎么说他是你的儿子啊,他想做村主任,你为什么要拦着他。”
郑新二十五岁了,郑生林这是第一次说这个话。在他的心里,郑新居然还是我的儿子,说:“再过几年吧,我得好好教教他。”
郑生林却又不放心了,说:“那时说过的话,你可不能忘了。”
邹杰心里格噔了一下,说:“放心,我不会食言的。”
郑生林走后,钱秋香哭着说:“后悔啊,我们真不该把儿子给郑生林的。”
“怎么说,那阵他郑生林照顾过荷花的。”
“荷花也不对郑新说一说?”
“她敢么。”
“郑生林,真不是人。”
邹杰还是想对郑新好好说一说,做村领导,就要把村里的群众装在心里,一些事情不要太计较,一些事情还得自己多吃些苦才行:“郑新,你要好好想一想,群众为什么不投你的票。”
郑新不耐烦地说:“你是我的什么人,教训我,我爸都没这么对我说。”
“我是……”嘴边的话,邹杰还是咽了回去,他说,“我的确老了,身体也不好,这副担子迟早要让年轻人来挑。往后,你对岭上村的群众好一些,开着小四轮,有时顺便给大家带点什么,不一定要收钱……”
郑新打断他的话,说:“通过这次选举,我已经知道怎么做了。”
郑新虽是一副不耐烦的样子,邹杰心里还是很高兴的,通过选举,让他有所觉悟,改掉身上的一些毛病,下一届,就让他来当村主任吧。”
八
赵前生带着吴老板离开岭上之后,邹杰越想越觉得不对。真要毁掉四千亩油茶林,换来更大的发展,让大家日子过得更好,也就罢了,可是,办中药材基地失败了呢,还有,那个吴老板什么来头,郑新知道他的底细么,八字没得一撇,却先要给他一百万买苗子,要是……他不敢往下想了。
那天拾油茶果回来,邹杰原本很累了,吃过晚饭就准备睡觉,明天还要上山拾油茶果呢。只是,想了想,他还是去了郑新家。郑新正在跟郑生林说话,一脸高兴的样子。邹杰说:“郑新,有个话,我要对你说一说。”
“要是办中药材基地的事,你就不要开口。”
“你们把协议签好了?”
“当然。钱也准备好了,赵书记弄来的无息贷款。人们说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拍在沙滩上。你不高兴了?”
“要是这样,我就没什么说的了。说了也没用啊。”
“知道就好。”郑新的脸上做着笑,“你带个头,油茶果采完,就动手把自家的油茶林砍掉。你动手了,人们才会动手。”
“我不会带这个头的。油茶林毁了,就断了我家的生活来源,两个老人,日后靠什么养老?”
“我不是通知你了么,为什么不去办低保手续。”
“村里的困难人家不止我一户啊。”顿了顿,邹杰还是把心里的忧虑说了出来,“那个吴老板,你弄清楚了,真的是大老板?”
郑新不耐烦地说:“吴老板是赵书记带来的,你问他吧。过些日子,赵书记就会住到岭上来,亲自抓中药材基地的建设。”
油盐不进。邹杰也等不起赵书记什么时候来岭上了,自己去乡政府找他。赵前生也是一副很不高兴的样子:“要说岭上能有现在这个样子,你邹杰有苦劳,也有功劳。如果你在办中药材基地的问题上做挡脚石,那就有问题了。你是不想别人超过你。这种心态要不得。”
邹杰说:“我今天来,是想问问那个吴老板何方人氏,家住哪里?”
赵前生说:“你信不过吴老板?告诉你吧,吴老板的天马投资公司在省城那是响当当的。他能到岭上投资办中药材基地,是我们县分管招商引资的邹副县长极力推荐的,不是我在这里,邹副县长不会把吴老板往田坪送。知道么,那阵我在县委办做副主任的时候,邹副县长是农委主任,我们是很铁的朋友。”
邹杰说:“我还是那句话,岭上能有这个样子,不容易。”
赵书记冷冷地说:“不要说了,回去带个头,着手把山地整理好,明年开春好栽杜仲苗子。”
“能不能把那个天马投资公司的电话告诉我?”
赵前生眼睛瞪着他,心里想,谁知道你会对他们说出些什么来啊,说:“天马投资公司的电话我有,我还把电话打到公司问过吴老板的情况。但我不能把电话号码给你。”
回到家,邹杰只对钱秋香说了一句,他出门有事,几天才能回来,提着两件换洗的衣服就走了。钱秋香问:“是不是去我们女儿那里?”
邹杰说:“把这事办好之后,我们就一块去邹芳那里。老了,不去跟女儿住,还能去哪里?”
从田坪乡到省城,其实很方便。过去走国道,早晨在乡场旁边的国道上拦下去省城的大巴车,下午四点多钟到,如今走高速就更快了,不过三个小时的车。走在省城宽敞的大街上,看着大街两旁的高楼大厦,大街上川流不息的车辆,摩肩擦背的人群,邹杰觉得有点头晕。
这么多年来,钱秋香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后悔不?”他知道她说的后悔两个字里面包含着两个含意。一是放着国家干部不做,回家当农民,吃了多大的苦,受了多大的累,后不后悔。二是把儿子给了别人,还不能说,后不后悔。他说他不后悔。回到岭上去,是因为心里放不下两个女人。把儿子给了郑生林,那个家才像个家。钱秋香说:“说到头,还是为了荷花。”邹杰说:“我对你不好?”钱秋香的眼泪就出来了:“你是个好男人,好丈夫。喜欢荷花,却把她当做自己的亲妹,让我不放心都不行。”
邹杰来省城是要寻找吴老板的那个天马投资公司。在岭上办中药材基地是拦不住了,亲眼看见天马投资公司,他心里才踏实。
可是,站在省城的大街上,人海茫茫,到哪里才能找到它啊!只得问过路的行人,有的说是从乡下来城里打工的,眼前也是茫然一片,有的把头摇得像个拨浪鼓,说不知道,有的眼睛盯着他,也不知道鼻子里哼了句什么,扬长而去。茫然里,邹杰就想起四十多年前当兵的时候,一个战友复员之后安排在省民政厅搞保卫,开始的几年两人还有过联系的。邹杰找到了民政厅,说了老战友的名字,门卫说几年前生病去世了,他儿子在民政厅工作。门卫看见这样一个勾腰驼背的老头远天远地从农村来找他的老战友,肯定有什么为难的事情吧,打了个电话,一会儿,一个三十多岁的年轻人从里面的大楼里走出来,问邹杰有什么事。邹杰没说话,眼泪先出来了,他说:“那阵当兵的时候,我跟你爸一个排,我当排长,你爸当副排长。没有想到,他却先走了啊。”
年轻人十分的感动,说:“老人家,我爸不在了,还有我呢。有什么事,只管对我说吧。”
“也没有什么事,就是想你爸了,来看看。”邹杰这么说的时候,就准备离去。
年轻人却是拦住了他,说:“来趟省城不容易,怎么说都得住一个晚上。我给你安排。”
年轻人就近把邹杰安排在民政厅招待所,说:“住宿不用你掏钱,吃饭也不用你掏钱。我负责。玩两天,你就走。我忙,不一定再来看望你了。”这样说的时候,年轻人从口袋掏出五百块钱,“这钱你拿着,想买什么就买点带回去。留点钱买车票就是了。”
邹杰说什么都不肯接那钱,说:“实话告诉你吧,我是来省城办事的,只是顺便来看看我的老战友。”
“顺便来看看也好呀,说明你还记着我爸的啊。”年轻人过后问道,“来办什么事,办好了没有?”
“问谁都说不知道。”邹杰就说起省城有一个天马投资公司要到岭上办中药材基地的事,“我就担心基地没办成,油茶林却没了,怎么得了啊。”
年轻人说:“省里的确有个天马投资公司,但没听说到乡下去投资办什么中药材基地啊。”
“听说那个吴老板很有名的。”
“别着急,我给你问问。”
邹杰在招待所住了一晚,第二天哪里都没有去,等着老战友儿子的消息。他也想开了,要是那个天马投资公司真的去岭上办中药材基地,回家就带头把油茶林毁掉算了,还要动员大家,吃几年苦,把中药材基地办好,日子就比现在更加好过了。赵书记说我是担心后来人超过了自己,真是冤枉我了啊,我怎么会有那样的想法,再说,郑新还是我的儿子啊。
那天中午,老战友的儿子来到招待所,进门就说:“我找到了天马投资公司的老总,他说他们公司没有去乡下投资办什么中药材基地。他还说他们公司以前的确有个姓吴的员工,三年前就离开了,现在公司上百的员工,姓张姓王姓李的都有,却是没有姓吴的人。我就觉得奇怪了,要是骗子,去你们那样偏远落后的农村,能骗到什么啊?”
邹杰那个急,说:“请你帮个忙,赶快给我们乡领导打个电话。就说那个钱不能付,吴老板是骗子。”
“他到你们那里骗到钱了?”
“一百万。”说着,邹杰就火急火燎地走了。
这天下午,邹杰坐上一辆开往西南方向的大巴车,天黑的时候才赶到乡政府。赵前生的办公室有许多人,乡派出所张所长也在他的办公室。看见邹杰走进来,赵前生说:“老支书啊,你怎么不早打电话回来。”
邹杰问:“怎么了?”
“那个大骗子,把钱弄走了。”
“什么时候?”
“昨天下午。中午接到你打来的电话,我就给吴老板打电话,是空号,打天马公司的电话,还是空号,我就着急了,打电话给邹副县长,邹副县长说他正准备给我打电话的,有一个诈骗团伙在本县几个地方作案,他还在落实吴老板是不是那个团伙的成员呢。我告诉他,吴老板也是骗子啊。”
邹杰直跺脚,一百万,下辈子都还不清白的啊。
天已经黑一阵了,邹杰一边往岭上赶,一边还想着那一百万的贷款,赵书记也是的,你不担保,他郑新能贷那么多钱么。
突然,眼前一道光亮射过来,邹杰抬起头,是郑新的小四轮车灯的光亮。郑新是不是也知道了吴老板是个大骗子。邹杰想拦下小四轮,对郑新说一声,赶快去找赵书记,无论如何得想办法把那钱追回来啊。
怎么的,小四轮居然对着自己撞过来了。邹杰惊骇地往后退了一步,口里却大声地说:“郑新,快去找赵书记。”
有惊无险,小四轮擦着他的身子冲了过去,他却一脚踩空,掉到路旁边的坎下去了。
九
郑新接到赵前生的电话,是在天黑的时候,赵前生也不说有什么要紧的事,只要他马上赶到乡政府去。半途中遇到邹杰,郑新就猜出了几分,又是他在赵书记面前说什么了,不碾死你,吓一吓你也解恨啊。
跨进乡政府大门,赵前生就把他往桑塔纳小车里面塞:“快跟我走。”
“到哪里去?”郑新发现派出所张所长也坐在小车里。
“去县里。”
“你在电话里也不说,什么事啊?”
“我们受骗了,那个吴老板是骗子。”
“不可能的么。”郑新不相信这是真的。
“邹杰从省里刚回来。”
“他的话你也相信?”
“邹副县长也打电话来了,最近有一个诈骗团伙在我们县行骗,用的手段就是投资办工厂办企业,已经有几个乡镇被骗走了钱。县里正在组织警力破案。我打电话给那个姓吴的,说是空号,打天马投资公司,也没人接电话。”
郑新就傻眼了:“这可怎么办,一百万啊。”
“我要县里通知有关部门,把吴老板的那个汇钱的账号给冻结了,只可惜还是迟了一步,已经取走了三十万。我们到县里去问问,看那三十万能不能追回来。”
郑新哭都没好腔了:“三十万,要多少年才能还清啊。”
小车在夜色里跑了个多小时,就到了县城。果然,全县有三个乡被骗走了钱,三个乡的领导都住在县委招待所,正在跟县公安局的人商量怎么才能把钱追回来,让损失降低到最小。
公安局的领导对赵前生说:“四个乡,就你们被骗走的钱最多。一百万,冻结的七十万是可以弄回来的,那三十万能不能追回来,还真的没有把握。你们也是,就那样容易把钱给别人。”
赵前生想说那个吴老板是邹副县长推荐去田坪的,能不相信么。想一想,又没有说,还是不能把邹副县长扯进来的好,对张所长说:“岭上村的事情,就麻烦你多费心了,出差费由乡政府给你报。”
郑新问:“你不和我们一块去找吴老板了?”心里想,姜还是老的辣,怪不得当时说好了的,你赵书记签字画押做担保,贷款的时候,却不肯签字了,现在,你当然是不用着急了。
赵前生道:“我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办呢。”他还是想去问问邹副县长,他那里有什么线索没有,凭空找那个姓吴的,大海捞针啊。
半夜的时候,赵前生果然给张所长打来电话,说他了解到吴老板的一些情况:“那人名叫吴用,你们去一趟吴用的老家,说不定他逃回老家去了。这才一天时间,总不会把三十万全都花光吧。”
郑新抱怨说:“你不把人家往岭上带,我就不会受骗,现在出事了,你却躲在一旁打电话。”
第二天清早,张所长还是带着郑新往吴用的老家去了。在那三个乡行骗的骗子不是吴用,他们则由县公安局的民警带着,分头去了别的地方。
吴用的老家在大西南崇山峻岭里面一个偏远的农村。张所长带着郑新先去了县城,坐了大半天的大巴车,然后转中巴车,然后再坐一辆小四轮,磕磕碰碰了老大一阵,才找到那个乡的乡政府所在地。张所长带着郑新去了一趟乡派出所,请求他们帮忙。乡派出所长笑着说:“我们乡没有名叫吴用的。吴用可是水泊梁山的英雄好汉,别玷污了他的英名。但我知道你们要找的是谁,他叫吴明。”对着旁边一个姓孙的年轻民警说,“天黑了,带二位去招待所住一晚,明天一早就带他们去找吴明吧。吴明住的村子离乡政府很远,不通公路,走路得小半天啊。”
张所长和郑新连声道谢。第二天一早,两个人就跟着孙民警上路了。在大山里面转来转去,大半天了,也没有个尽头。郑新越走心里越害怕,里面是一个村子啊,怎么连条路都没有。他就想起自己的岭上村来,岭上村修的可是水泥公路啊。
张所长笑着问:“岭上村的水泥公路是你修的?”
“不是。”
“岭上村的四千亩油茶林是你造的?”
“也不是。”
“怪不得毁了一点都不心疼。”
“我也想为岭上村群众办件实事啊。”
“实事没办成,却要我来帮你追讨被骗走的钱。你说,得了那个姓吴的多少好处?”
郑新心想你怎么知道啊,说:“他说每亩给我五十块钱,我心里的确有点热,但我不能要。”
张所长眼睛盯着他:“真的?”
“真的。第一次选村主任的时候,我才得三张选票,后来还是赵书记出面帮忙才当上村主任的,邹杰现在都不服气,只要有一点风声走漏出去,他还不打锣。因为这事,我老婆至今夜里睡觉还不让我沾她的身子。”
张所长不做声,像在想什么。郑新问:“我们乡还有谁会得吴明的好处?”
“赵书记应该不会,他现在想的是要做出政绩回到县里去。”顿了顿,张所长说,“我在田坪乡五年了。哪个村没去过十次八次。我就相信你们的老支书。不是他,岭上村有现在那个样子。”
孙民警一旁说:“这个吴明我认得,他也骗得了你们?”
张所长不做声,看着郑新,郑新一肚子娘骂不出来。第一眼看见吴明,他也心存疑虑呢,脖子上的领带比自己的还差,脚上的皮鞋没鼻子没眼。赵书记却是深信不疑,说这个样子才是大老板,不显山不露水。
天渐渐地黑了下来,三个人才赶到村里,孙民警对村主任说的第一句话:“快给我们弄点吃的,饿得肚皮贴背心了。”
村主任说:“我还在想呢,吴明这家伙几年没见他的影子,怎么突然回来了啊。”
听说吴明回来了,张所长和郑新都特别的高兴,问道:“他家里还有什么人?”
“父母去世了,老婆离婚了。他自己因为偷盗被判过两次刑,这才出来多久,又犯事了?”
孙民警道:“你熟悉,带我们去他家吧。”
“行。”
三个人跟着村主任在泥泞的村路上转来转去一阵,就到了山脚一栋木屋外面。
村主任说:“那就是吴明的家,屋里还有灯,说明他在家,你们去吧。我就不进去了。”
郑新拔脚就往屋里冲去,张所长和孙民警也只得跟在后面冲了过去。
吴明手里拿着几张纸片,勾着头一张一张地看,听到门口的脚步声,脸不由就黄了,嘴里说:“你们怎么来得这么快啊。”
张所长一个箭步冲过去,把吴明按倒在地,在他的手上套上了铐子。郑新从他手里抢过那几张纸片,不由就哭了起来:“这就是我的三十万啊。姓吴的,你害得我好苦。”
孙民警说:“认真看看,数字对不对?”
郑新就又把几张存折的数子加了一遍,说:“三十万,没错。”
张所长问:“你一个人弄到一百万,怎么只取三十万,你还说要给郑新钱的啊。”
吴明苦着一张脸,说:“我的头只让我拿三十万。打点的钱由他负责开支。”
“还要打点谁你知道不?”郑新不相信张所长说的那话,赵书记那样积极在岭上办中药材基地,肯定不只是想回到县里去吧。
“不知道,他们不会对我说。我说给你钱那是假话,要给钱得先给啊,钱骗到手了,逃都来不及,怎么会再给你钱。”
走出大山,已经是第二天早晨。张所长接到县公安局打来的电话,问他现在在哪里,昨天下午就开始给他打电话,就是打不通。
张所长说:“我们在那个姓吴的老家,大山里面,手机没有信号。”
“我们已经抓到了他的一个同伙,其他的几个还在逃,你们那里情况怎么样?”
张所长说:“吴明被我们抓到了,搜出了三张存折,共计三十万。”
“这样说,岭上的一百万全都追回来了。另外三个乡的几十万还没有着落啊。快把吴明弄回来,认真审一审。”
把吴明交给县公安局,郑新回到田坪已经是第四天的中午。赵前生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说:“真是不幸中的万幸啊。”过后,赵前生骂了一句脏话,不知道是骂的吴明呢,还是骂的邹副县长。
郑新回到岭上的时候,邓荷花的眼泪一直没有断过:“儿呀,要不是你爹,下辈子你也还不清那一百万的啊。”
郑新看了一眼坐在一旁默不作声的郑生林,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问道:“妈,你说的什么,那个骗子被抓,与我爸有什么关系。”
“我说的你亲爸,邹杰,他不去省里找那个天马投资公司,怎么知道吴老板是个骗子。”
郑新一脸愤怒地说:“我早就看出来了,无瓜无葛,你却要我叫他舅。我爸没用,怎么就甘愿把一顶绿帽子戴在头上。”
邓荷花扬起手,狠狠地抽了他一巴掌:“畜生,你和邹芳是双胞胎亲姐弟啊。”
郑新眼睛就瞪大了,握着发烫的脸,喃喃道:“怎么会是这样,你们为什么要瞒着我?”
郑生林一直把头勾着,不敢抬起来,说:“就想你好好跟着我们过日子啊。”
郑新对着郑生林咆哮起来:“郑生林,我恨你。”冲出门,拔脚往邹杰家跑去。可是,邹杰家门上一把锁,邻居说:“大前天老支书从省城回来,路上摔了一跤,胳膊被摔断了,这两天,你舅妈一直在清理东西,中午的时候,老支书从乡政府打听到被骗的那钱已经追了回来,他就带着你舅妈走了,可能去女儿那里了吧。”
郑新开着小四轮去了乡中心小学,儿子小宝对他说过多次,经常看到舅公舅婆在学校门口对着里面张望,也不知道他们是在看什么。
小宝果然说:“刚才舅公舅婆的确到学校来了。”
“说什么了没有?”
“没有,站一会就走了。”
郑新赶到车站的时候,长途客车已经开走一阵了。郑新嗵地一声跪倒在地,声泪俱下地嚎叫着:“我的爸妈啊……”
责任编辑王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