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文学与全球视野
——以柯尔克孜族文学为例
□ 赛娜·伊尔斯拜克
中国文学是多民族的多元的,是中华民族文化振兴的一个不可忽略的元素,是国家和民族持续发展的精神动力之一。全球化是当下的现实,多元文化,回归文化传统、寻求民族文化身份的认同成为一种潮流。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角度来看,重要的是我们拿什么对外交流,发扬我们自身的什么优势,我们的作品才会被关注、被研究、被传播?存在哪些制约我们文学发展的问题?在新的历史时期,各族人民共同书写“中国梦”的当下,我们该如何讲好中国故事,传达中国声音?

一
随着国家对民族文化、原生态文化的进一步重视,各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和文化特点得到了很好的研究。少数民族文学与汉民族文学的差异性和互补性,使得少数民族文学具备与世界文学对话的可能性。柯尔克孜族的史诗《玛纳斯》成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被保护、传承和研究,新疆民族文学原创和民汉互译作品工程等,这些与国家对保护文化多样性的扶持是分不开的。对于新世纪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特别是对人口较少的母语创作的柯尔克孜文学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中国柯尔克孜族人口不到20万,文学创作99%为母语写作。母语写作是作家对民族身份的认同,对民族文化的自觉坚守,母语作家以其民族特有的审美方式感知和认识世界,以自己的母语反映本民族社会历史生活,表达作家及其民族对世界的独特审美观照,母语写作,既是民族文化发展和中国文学全面发展的需要,也是促进国际文学交流和加强睦邻友好关系的需要。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少数民族母语写作对于保护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具有特殊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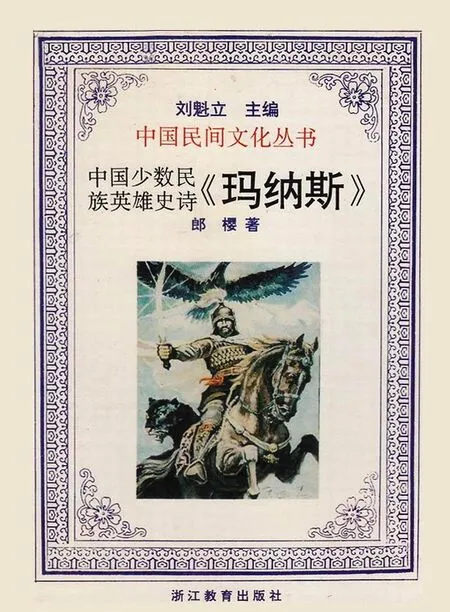
民族地区生活的差异性、思想情感的独特性是作家创作的丰富资源。柯尔克孜族文学扎根于民族生活的这片热土,从饱含民族历史文化内涵和生活气息的沃土中挖掘素材、提炼生活。如果脱离民族生存的土壤,就意味着放弃了自己的优势与位置。柯尔克孜族文学的发展之路是植根传统,坚守、丰富和发展之路。柯尔克孜族文学主要由民间文学和书面文学两个组成部分。最为著名的是英雄史诗《玛纳斯》,这部史诗是世界文学的瑰宝。除此之外,还有民间达斯坦(叙事长诗)如《交劳依汗》《阿吉巴依》《萨依卡勒》《巴额什》《托勒托依》等。史诗中诗化的英雄已成为民族审美感情的凝结体,因为她凝结着历史锤炼了千百年的民族感情,具有生动感人的艺术力量。柯尔克孜族书面文学的发展伴随着柯尔克孜族经济生活的变化,涌现出一大批诗人和作家,如:阿不都卡德尔·托合塔诺夫、阿曼吐尔·巴依扎克、艾斯别克·奥罕、吐尔干拜·克力奇别克、加安巴依·阿萨那勒、曼拜提·吐尔地、萨坎·吾买尔、阿山巴依·玛特勒、曼拜特艾山·叶尔格、吾尔哈力恰·克德尔巴依、阿不都热合曼·斯玛依、莫明·阿不都卡得尔、朱玛卡德尔·加合甫等等,这些作家在诗歌、小说、散文、评论等领域创作了一大批在国内外皆有影响的作品。吐尔干拜·克力奇别克的中篇小说《乔里潘》,植根于本民族人民的生活土壤,挖掘和表现本民族独有的生存状态、特定心理、生活特质和文化传统,塑造了具有鲜明民族性格的艺术形象。这一类的作品,占了柯尔克孜族书面文学的主流。柯尔克孜族是一个史诗民族,是用诗歌来表达自己的民族,诗歌在中国当代柯尔克孜文学中占相当大的比重。诗人加安巴依·阿萨那勒的诗集《足迹》《消失的岁月》,语言瑰丽细腻,有着纯粹的民族语言、特有的思维模式和强烈的民族特性。吾尔哈利恰·克德尔巴依的长篇小说《阿吉别克英雄》的价值不仅仅在于揭开历史之谜,为英雄立传,为草原游牧文化正名,更赋予了作品现实意义。买买提吐尔逊·玛提克的长篇小说《潇潇旷野》讲述了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一个穷山僻壤小小牧村的故事。通过描写曼别特为代表的柯尔克孜进步人士,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获得新生和荣耀的故事,刻画了一代英雄人物和有志之士的光辉形象,表达人们对自由和幸福的追求,富有浓郁民族特色。



当我们把作品作为民族文化传承和积累的一种范本,还原于它们所属的民族文化系统和民族文化语境时,许多在主流文化语境或其他文化价值系统中不被注意的文化价值便会立即凸现出来,它们包括草原文化朴素的生态意识,人性的真善美等等。在差异性与独特性中探求人所共有的普遍性才是民族文学的优势之所在,是世界上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优秀作品共同追求的属性。柯尔克孜族本身就有爱护自然、敬畏山水的传统。柯尔克孜族作家艾斯别克·奥汗的作品《大象的眼泪》、吐尔逊·朱玛勒的《猎人》、阿依别尔地·阿克骄勒《三条腿的野山羊》等都蕴含着草原文化朴素的生态意识,对贪欲无度的人们敲响了警钟,让我们看清了生态破坏和人的精神蜕变的关系。柯尔克孜族女作家古丽孜亚·瓦力的长篇小说《喧嚣的蛙沼》讲述主人公贪婪地寻求名利,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最终道德败坏,受到自然界的惩罚。小说大胆尝试以民间故事的叙事模式,以女性特有的丰富想象力,深刻反思人与自然界的关系,呼吁保护大自然和人类的生存空间,阐释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态文化理念。少数民族作家应发扬自身优势,把本民族文化的特质以艺术形式保留并传播出去,在全国乃至世界更广阔的文化背景下进行创作。
地缘因素决定了柯尔克孜族文学书写具有开放性。中国的柯尔克孜族主要聚居在新疆,新疆位于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区,与八个国家接壤,是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辽阔、影响深远的四大文化体系的交汇处。新疆与中亚山水相连。习近平主席在出访中亚四国时提出了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大战略构想。新疆作为亚欧大陆的桥头堡、丝绸之路的核心区域和横贯东西的交通大动脉,在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地位更加凸显,必将成为名副其实的我国对外开放的前沿阵地。柯尔克孜族作为跨国民族,与中亚吉尔吉斯斯坦有特定的血缘关系,共享先辈们留下的文学艺术资源。比如史诗《玛纳斯》,也出于同一母体,而后异地发展,直至今天。改革开放以来,受周边民族的影响越来越大,与境外同源民族交流的领域进一步扩大。柯尔克孜族文艺作品被翻译成汉文或外文出版,国内外的优秀作品同时被大量翻译成柯尔克孜文,中亚同源民族的文化书籍通过各种渠道进入境内。加之,互联网的发展拉近了柯尔克孜族人民与世界的距离,网络媒介的传播使得柯尔克孜族作家有了更广阔的空间。这一切都促使柯尔克孜人的思维发生嬗变,他们开始对创作方法和表现方法进行思考和探索,为自身的发展和柯尔克孜文学的振兴迈出了新的步伐。新疆柯尔克孜族与其他兄弟民族一样,正经历着自然经济和半自然经济相适应的传统文化向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型文化的转变过程,处于历史性的文化转型期。社会变革给民族地区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柯尔克孜族作家描绘出了时代变迁下的人生百态。艾斯别克·奥汗的小说《没有睡意的夜晚》、《骑牦牛的人》,反映了柯尔克孜人在改革开放背景下,在游牧文明与现代文明的猛烈撞击中真实的生存状态。市场经济的阵痛改变了他们的世界,他们的民族心理、民族气质在这空前深刻的社会变革和文化更新的过程中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特别是市场经济与竞争打破了自给自足经济形态的平衡,大大改变了人与人关系的旧有模式。从游牧到定居,改变的不仅是柯尔克孜族的生产生活方式,而且改变着传统的民族习俗和观念。揭示现实矛盾,描绘改革在柯尔克孜族人民心中掀起的波浪,是这一批柯尔克孜族作家表达的一种方式。
二
我们看到了柯尔克孜族文学的独特性、开放性等优势,看到了其蓬勃发展与长足进步。同时,我们也看到了它依然处在现代与传统、主流与边缘的夹缝中,处于一种既不脱离现实而又难以很好地反映现实,既崇尚主体意识而又不能很好地驰聘的纠结之中。题材单一、体裁比例失衡、具有深层意义的优秀作品少、翻译不足、文学批评稀少、各民族间交流不多、作家队伍数量和素质上的不足等,制约着柯尔克孜文学的进一步发展。我国传统的柯尔克孜文学体系,多是在历史上的封建社会甚至更为后进的社会政治经济形态下形成和确立的,以完全型内视习惯为主宰的保守性障碍着创作者的视野与追求。柯尔克孜族的作家群体,在民族文化被来自主流的文化以及世界性的它国文化吸纳、同化的时刻显得过于警惕,加之过于迷信“越民族越国际”的艺术观念,因而缺少超越民族界限、超越时代的气色,缺少民族精神的深度挖掘,尤其缺少对民族文化和精神实体进行文学开启的意识,在观念解放和艺术创新方面还有待突破。

针对上述症结,首先要解决文学观念的问题。随着作品审美功能的多元化,表现内容的复杂化、欣赏者的审美情趣的多样化,当今文坛已呈现多元化格局。这就要求我们创作者必须具有开放的文学观念,充分地发挥其多方面的审美功能,在满足审美享受的基础上,引导人们对人类生存发展诸多问题的思索以及在人性的恢复和完善方面发挥其作用。一部真正的文学作品,一个民族有价值的文化成果,是不应该也不可能仅仅局限在自己单一的民族利益或封闭在狭隘的思想感情之内,也不可能停留在对人类的生存状态、利益和理想毫不关心的冷漠中,它自身的发展不可避免地必然参与全国乃至世界文学的进程及人类综合的相互作用中。当代世界文学的格局中,有的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在该国也都拥有该国少数民族作家的身份。他们立足于民族命运的经验,但总是能够吸取多元文化的营养,有的书写民族生活,在文学感染力方面超越了民族的界限,对一般的、普遍的生存状态进行深刻的文学表达。加西亚·马尔克斯、奥罕·帕慕克、艾特玛托夫的作品关心人类命运,面对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每个民族都面对着共同的世界,可每个民族却又有其独特的理解世界的方式。少数民族文学在整个世界文学格局中有多大的发言权取决于对民族特殊意义世界的进入程度,能不能真正进入本民族的最隐秘的心灵史,找到并创造出一系列能够横向扩展延伸的富有世界意味和生存普遍性意味的话题。少数民族作家所依托的自身所拥有的文化背景以及民族特色浓郁的场景,仅仅是一种叙事的媒介,应该是可以寄寓象征的文化符号,重在于人类精神的普遍审视的过程和结果。当我们处理某一题材,反映某截面的生活时,要对其作历史的、人生的、文化的、人性和道德的多方面的思考,要求我们的作品主旨超越所写生活的表层,作品的思想内容不仅要有更广的涵盖面,而且还应具有更深的历史穿透力。要求作家以悲天悯人的大智慧、大爱心去观察关爱社会人生,从不同命运遭遇的个人身上看到人性的喜与悲,并以此呼唤人的良知,从而满足更大层面读者的审美需求,引起不同民族,不同派别乃至不同国度的人的共鸣。大作家一定是大思想家。
在新的历史时期,各族人民共同书写“中国梦”的当下,我们柯尔克孜作家更应进一步解放思想,树立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吸收借鉴其他民族文化的精华部分。如果说文化身份特征的认同主要是指对民族文化核心价值的认同,那么,文化身份的建构则要以文化核心为建构基点,批判地吸收外来文化的优秀成果。“为我所用”是为了更好地丰富、充实和提高自己民族的文学,是为了更好地发现、发展和表现自己的艺术个性。柯尔克孜作家要重视自己的民间资源,神话、传说、史诗等提供给我们无限的审美空间,努力把学习别人和发展自己结合起来,寻求传统中有现代,现代中有传统,书写柯尔克族的故事,传达柯尔克孜族人的声音。
当代民族文学领域,充满了竞争与挑战,也充满了机遇与选择。面对着世界文学和我国文学的迅速变化、发展,少数民族作家有责任重新审视自我文学世界,看清本民族文学在整个文学宏观坐标系统中的位置,清醒地认识到自我的优势和劣势,不妄自菲薄,也不盲目自大。我们既要坚定地保持以本民族文化特质为内核的创作主体的个性建构意识,利用本民族资源保持民族的审美经验传统,保持民族进步的精神,以开创性保持民族文化的独立个性;又要借着全球化话题获得新的增长空间和认知视角,获取文学创作的新观念、新方法,建立包容、自由、开放的心态。另外,还应进一步使母语原创的翻译、推介、传播少数民族作品常态化,加大对少数民族的翻译、评论队伍的培训力度,增强少数民族作家多元文化下的交流与对话。
(本文图片由赛娜·伊尔斯拜克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