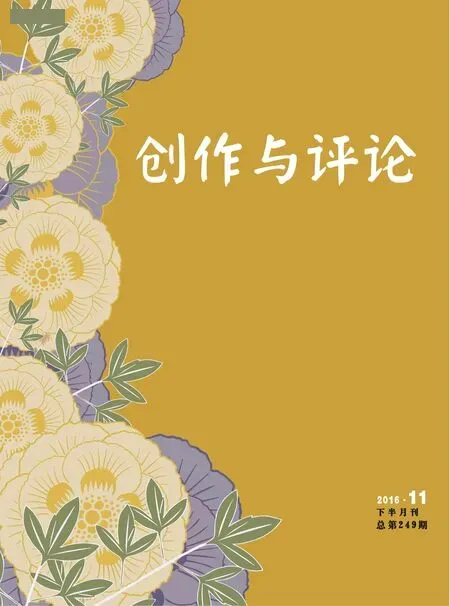『因为坚守,所以快乐』
——易彬印象
○张立群
『因为坚守,所以快乐』
——易彬印象
○张立群
说来我与易彬相识已有十年了——记得2006年春在天津南开大学参加穆旦研讨会,初次与易彬见面,这个大眼睛的朋友就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当然,若说十年间哪件事记忆最为深刻,我想2013年夏在沈阳图书馆替易彬查找穆旦《报贩》一诗原作是值得提及的。在1945年3月2日沈阳《新报》上查找《报贩》一诗,是因为易彬正在编《穆旦诗编年汇校》,需要核实每首诗的原始出处及第一版面貌,其学术态度之严谨当时就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而且,从结果上看,这件事倒是成就了本人——我后来结合此次查找,参考一些资料,写下了《沈阳的穆旦——兼及研究中的史料使用问题》一文,是以,对易彬的这次“求助”记忆犹新且深怀感念!
一、“专注开掘一口水井”
让我们从评价学术研究时一句常用语开始。“水井”而不是枯井,证明了易彬的研究颇有收获,他从井中打到了“水”;“专注”“一口水井”说明易彬目标明确。像一位极有潜质的书法家,在入门时只苦练一种书体,将其吃透,而后才兼及诸家、博采众长及至自成一家。易彬深知只有先占领别人无法绕过的领地,才能以坚实的脚步踏上研究的路径。这一点,在研究者越来越多、代际频繁更迭的当下,实属不易。由于评审体制的客观压力,多少人需要以急就章的形式快速写作、发表,以至于在急速发言中未及深入,甚至染上跟风的习气。但易彬的研究显然不是这样。他首先是研究穆旦的专家且以此闻名于学界。厚厚的《穆旦与中国新诗的历史建构》(2010年出版)、《穆旦年谱》(2010年出版)、《穆旦评传》(2012年出版)以及上下两册的《穆旦研究资料》(2013年出版)和正在进行的《穆旦诗编年汇校》(即将于2016年出版)等,既见证了易彬多年来的研究实绩,同时,也凸显了易彬多年来的研究理路及学术轨迹。从一个具体的、有价值的个案介入,一点一滴、以小见大式地开掘自己的学术进路;触及研究对象身上有价值、有意义的各个方面,并将其置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视野之中,进而在立体、繁复地再现研究对象的过程中拓展研究的深度与广度。比如,他的《穆旦与中国新诗的历史建构》就曾在言及“穆旦诗歌艺术精神”的同时,谈到了“穆旦的翻译行为”“穆旦的诗歌修改行为”之话题;在谈及“穆旦诗歌艺术精神与中国新诗的历史建构”时,易彬则相继涉及了“鲁迅与穆旦的比较并兼及新文学传统的话题”“新诗的散文化与语言质感——以冯至、穆旦、昌耀为中心的讨论”“新诗中的‘土地’叙述主题——以艾青、穆旦为中心的讨论”等以往研究中很少触及的内容;而其“穆旦的传播历程”不仅开创了穆旦研究中的传播视野,还丰富了“穆旦与中国新诗的历史建构”本身,从而使其成为一个结构清晰、有层次感、有组织的体系。至具体的研究实践,易彬亲力亲为,真正做到掌握第一手资料。即使仅限于我知道的,早在2002年,他就开始采访杜运燮、杨苡、罗寄一、郑敏等穆旦友人,后又多次采访穆旦同学及同事;在资料查阅方面,他也是颇为用力,不仅多次去过国家图书馆查找、复印资料,还曾三到南开,终获得完整的档案资料。在此基础上,他能相继完成数十万字的《穆旦年谱》和《穆旦评传》并不让人感到意外,但其中付出的努力和辛苦相信只有易彬本人才能知道。穆旦是一座富矿、一眼丰富的水井,对此,易彬有系统而宏大的研究构想。如今,他已是无可争议的穆旦研究专家,而其踏实、稳重、持之以恒的实践经验,恰恰是许多青年研究者需要学习和借鉴的。
二、“资源的占有、整合与横向的迁移”
其实,在谈及易彬的穆旦研究时,我们就已触及到这一方面:《穆旦年谱》《穆旦评传》以及《穆旦研究资料》,是易彬多年研究穆旦资源整合的结果;而比较研究、主题研究、传播研究既是《穆旦与中国新诗的历史建构》一书的特色,同时,也是易彬在穆旦研究过程中横向迁移的结果。显然地,没有大量资料的占有,《穆旦年谱》《穆旦评传》以及具有资料汇编性质的《穆旦研究资料》是无法完成的,也是无法令人信服的。正如李怡在谈及《穆旦年谱》时指出的:“其用力之深广,考证之细密,在今天的穆旦研究中可谓是前所未有的,在自我惭愧之余,我更多的则是欣喜和敬佩,因为,我们的穆旦研究从此可以说有了坚实的最综合性的史料基础,其开拓之功值得大力肯定。”①除上文提到的访谈、原始资料查找之外,在易彬关于穆旦的系列研究中,我们还读到了著者查到了穆旦在南开的档案等新材料。有了这些珍贵的资源,易彬的研究自然有了坚实的基础,但若从“资源的占有、整合”角度来说,《穆旦年谱》堪称一次具有突破性的史料工作,而《穆旦评传》则是集文学研究和创作于一体了:有评有叙、边叙边议,凭借资源占有的优势,易彬的穆旦研究已呈现出“跨界”趋向。
应当说,多年的资料搜集、整理、研究已使易彬积累了大量的实践经验,同时,也为其研究的“横向迁移”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结合我掌握的“信息”,2011年4月1日,易彬曾发给我一篇他对原“七月派”诗人彭燕郊的访谈《“民歌精神是非常真实、非常纯朴的”》,该访谈后来配以易彬和彭燕郊的合影照,发在我编辑的《中国诗人》2011年第3卷上。当时,对于这篇访谈,我的印象是:彭燕郊(1920—2008)是跨越20世纪的重要诗人,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在他去世多年之后,发表这样一篇访谈,能够给研究者留下一份珍贵的资料。晚年的彭燕郊和易彬一起生活在长沙,易彬的访谈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后来,也曾多次和易彬见面,知其正在整理彭燕郊晚年的谈话录和彭燕郊书信等大量资料,不过,仅是闲聊似乎并未产生直观、强烈的印象,直到不久前在广州暨南大学开会期间,我拿到了易彬送给我的《我不能不探索——彭燕郊晚年谈话录》一书,多年的印象或曰线索一下子连接起来:易彬已从“九叶派”的穆旦“迁移”至“七月派”的彭燕郊了!他早于2005年5月和彭燕郊商定系列访谈事宜,于2005年8月开始着手访谈,之后去过彭燕郊先生家多少次连他自己也记不清了;2011年以来,易彬又受彭先生家属委托,对其资料搜集以及藏书、遗物进行整理工作,接触到相当多的原始特别是大量的书信资料,目前已经整理成型的有数十万字之多的《彭燕郊陈耀球往来书信集》(即将于2016年出版),已着手进行的还有《彭燕郊陈实往来书信集》。藉此,易彬对对新时期以来彭燕郊所从事的众多文艺活动已然有了十分深入的了解。②他还有大量的相关工作要做,而对此,我们可以相信:一个彭燕郊研究的专家、一部甚至多部有关彭燕郊的研究力作很快就要诞生了!
三、“一个快乐的研究者”
按照最初的设想,我本想以“幸福”一词为修饰语,但后来还是觉得形容学术研究还是用“快乐”更为客观、准确:“快乐”更能体现研究过程中自我享受的状态,“快乐”只在于其本身,而与其他无关。面对“年谱”这样细致、琐碎而又枯燥的工作,易彬依然能够坚持不懈的完成;面对浩如烟海的原始资料,易彬依然能够孜孜不倦地搜集、梳理,可见,他在其中肯定获得了学术研究的快乐。据我所知,他前后已经申请下来三个国家课题,他最近的国家基金项目为《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的理论建构与实践形态研究》,其中不仅包括对现代重要作家集外文的辑佚工作,对目前学界尚未充分注意的作家如彭燕郊的文献进行发掘、整理与研究,更包括对从理论层面对现代文学文献学知识理念进行规整。可以说,上述课题是易彬多年研究积累所得,是资源整合、经验拓展的结果,既有明确的研究目的,又有鲜明的理论建构意识。对于这些研究,相信易彬在掩卷之余,也会在感到欣慰的同时体验到一种快乐——那是艺术家自己面对已然成功完成的艺术品时的快乐,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快乐”会萌生新的契机——正如多年来我一直认为,在研究过程中体味到过程的快乐才是研究本身的动力及魅力所在,此时,“快乐”是超越世俗层面的,“快乐”是一种境界,也是一种精神。像早已被研究界过度使用的术语“现代性”以及“先锋”一样,“快乐”是指向未来并呼唤、指引着研究主体不断前行。坦然地讲,我在易彬身上看到了这种高级别的“快乐”,从穆旦研究专家到彭燕郊研究专家,再到现代文学文献学的研究者,易彬总能够以全新的姿态、开拓的精神,实现学术研究的新与准、精与深,而我所言的“快乐”也必将和其结伴同行、相辅相成。
行文至此,意犹未尽。附带一点,权作此次“印象”的结尾。大致因为易彬在穆旦、彭燕郊以及现代文学文献学方面的研究过于突出,是以,他留给人的印象往往是一位现代文学的研究者。而事实上,他还是一位时常从事当代文学批评的学者。早于2001年,易彬就在《青海湖》第5期上发表了《试论昌耀的诗》一文,长达近两万字。此后,他曾解读过于坚、桑克、古马、凸凹、李少君、柳宗宣的诗,又曾论析过“朦胧诗”、北岛的散文以及博客时代的女性诗歌等,易彬在当代批评方面虽写作量不大,但均是用心之作,因此,他的这方面实践理当值得我们关注与期待。
注释:
①李怡:《追踪的意义——易彬著〈穆旦年谱〉序》,易彬:《穆旦年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页。
②具体见易彬:《晚年彭燕郊的文化身份与文化抉择:以书信为中心的讨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5年第3期,以及彭燕郊口述、易彬整理:《我不能不探索——彭燕郊晚年谈话录》之“附录”收录的两篇文章《关于“彭燕郊访谈”的几点想法》《“单纯就好!”:纪念诗人彭燕郊先生》,漓江出版社2014年版。
(作者单位:辽宁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