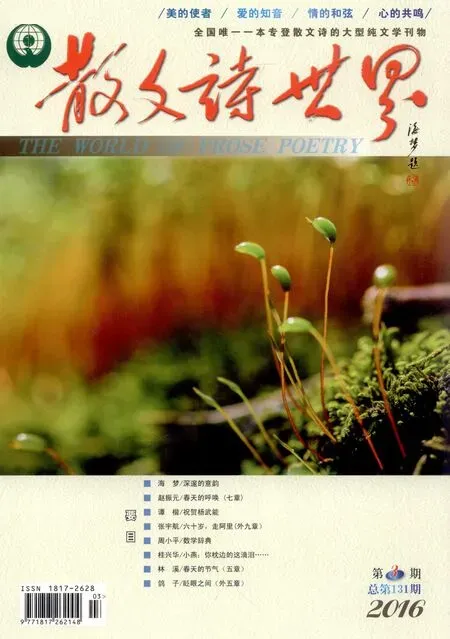山水之间(九章)
四川 徐澄泉
山水之间(九章)
四川 徐澄泉
在射亭村仰望瓦屋山
在射亭村向上仰望,瓦屋山就像一只大雕,抑或一块腊肉。
盛夏时节,雾锁瓦屋,人道凡间蓬瀛。两挂笔直的水瀑,从瓦屋山的额际垂下来,仿若两根仙人的神鞭,又如两缕飘冉的美髯,可远观而不可近渎矣。噼——啪!两道天神的霹雳,把我的胡思乱想击得粉碎——瓦屋山升级打造,闭山造景,多少远方游客,欲攀不能。射亭村里,徘徊多少射手的脚步;多少待发的箭镞,不知射向何处。射亭村里徒有亭,射亭有箭不能发;唯有一只大雕,翱翔在高空。
厚重的山影从黄昏的幻象里掉下来,把我的饥饿砸个正着。清雅农家乐史老板的晚餐桌上,一盘瓦屋山老腊肉为我治饿疗伤。我举手投箸,以箸为箭,纷纷射向想象的敌人。我的技艺炉火纯青,双箭一雕。我为自己的战绩骄傲和自豪。
雷鸣电闪,夜深无电,黑暗更加黑暗,大雕腊肉皆无踪影,正好秉烛夜读。“空持千百偈,不如吃茶去。”与赵朴初老不期而遇,恍然有悟——
瓦屋有仙求不得,
不如峨眉吃茶去!
孟获拉达的早晨①孟获拉达,彝语,意为云雾的那边,指马边彝族自治县。
比黎明起得更早。
在马边河清澈的水波里,他们汲水,垂钓,浣衣,搅乱了小凉山最后一缕月光,把孟获拉达的最初一片晨雾,撕开。
河边的卵石杂乱无章。他们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有条不紊,并借助一条睡眼惺忪的大鲵之口,向又一个赶往河边的人,献上赞美之辞——
瓦几瓦!瓦几瓦!②瓦几瓦,彝语,“好”的意思。
这一切,都在梦中进行着。
只有一个叫做孟获的老彝人(他老得不能再老,像一只沧桑的老鹰),用嶙峋的鹰爪,拨开群山与雾障,拨开传说与史籍,用敏锐的鹰眼,看见了。
铁山南麓,探寻诸葛武侯炼铁遗址
“昔诸葛武侯炼铁于兹。”
兹,此也。
四川省犍为县罗城镇青狮村11组,观斗山脉,铁山南麓,张家湾。
绿树修篁,荒草野花,鸡犬人迹。
诸葛武侯南征去也!
采铁山之矿,铸蜀汉之剑,平南中之乱,已被历史载入1790年以前的历史。
诸葛武侯,空有一世英名。
除了绿树修篁,荒草野花,鸡犬人迹,只剩一块残破的青石,依稀可辨几个孤零零的文字。犹如一块被谁遗下的骨头,在长长的暗夜,偶尔发出闪烁的磷光。
还有,五座炉!
一个在草野之间传说了1790年的地名。
一粒闪光的金子,忽然从草丛蹦出来,把我们搜寻的目光照得通亮。在一抔泥土里,一个比我更加虔诚的人,终于发现了诸葛武侯的脚印——5枚鸡蛋大小的铁矿渣。
一行人如获至宝,再也收不回贪婪的目光,急向村民打探铁山的高度——
清朝末年,李蓝义军以铁山作为大本营;
罗城“红灯教”义军驻扎铁山;
同盟会四川负责人熊克武在铁山秘密制造枪炮……
这些以清为敌的好汉,都选择了铁山这片绿林,吸铁山之氧气,养铁山之正气,炼铁山之矿石,攀铁山之高远。
太阳落入丛林,山间升起烟霞。
高高在上的铁山,燃起人间烟火。
踏寻邵伯温的遗梦
尘封的金子总在光辉处闪烁。
此时春光正艳!
随便一点光焰,比如一片绿叶之绿,或一棵青草之青,都能激醒沉睡千年的梦。
北宋大儒邵伯温,洛阳桥头听杜鹃。
举家避乱到蜀地,卜筑犍为安乐窝。
安乐窝里有风雨,雨打芭蕉不安乐。
可怜多情邵夫子,客死他乡无归路。
邵伯温终究找到了来世的天堂。埋骨犍为红花冲,居高临下,看日出日落,闻鸟语鸡鸣,感花开花落,阅人间世相。他以温情的目光抚摩肥沃的田野,欣赏纯朴的子民安居乐业。夜深了,做一回洛阳梦,温馨而甜蜜,高贵且深邃。
又一个风雨飘摇的夜晚,邵伯温的梦一片剥蚀。夫子的天堂,成为人间地狱——尸骨横陈,乱石遍野,野狗哀嚎,冤魂呜咽。
又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沿着水声和花香,踏着杂草和露水,我找寻邵伯温的遗梦。一位老农告诉我:邵伯温,百姓尊称邵夫子;红花冲,乡亲昵称夫子山。
邵伯温,不在他的坟茔中;邵夫子,活在犍为人的口碑里。
剑门关:姜维的悲喜剧
姜维的表情实在难看——
大惊失色,怨恨交加,咬牙怒目,须发倒竖,拔刀砍石。
这不是剑门关上姜维神像的表情,这是剑门关下姜维雕像的神态。
剑阁峥嵘而崔嵬。雄、险、奇、幽的剑门,自古就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可是,历史的剧情往往跌宕多姿,出乎意料。曾经统领3万兵马御敌10万大军于剑门关外的英雄,一不小心,走到了末路。
是啊!后主刘禅远在成都,不战而降。将虽在外,姜维也不能抗命拒绝投戈放甲。助主复兴蜀汉,壮志未酬,姜维岂能心甘!
姜维是忠勇的姜维,人民是善良的人民。剑阁人,为一个悲剧英雄修一座姜维墓,建一所姜公祠,把他扎营屯兵的地方命名为姜维城,就是为悲悲戚戚的历史上演一出喜剧,为黯淡的天空抹上一缕亮色,为尘世的道路树立一座丰碑。
金牛道上,有关如剑。剑呈双刃,伤上亦伤下,伤左又伤右,伤身更伤心。
那么,这样的关,守与不守,又有何妨?重要的是:自己心中那道雄关,必须坚守!
姜维切记!
在恩阳:看到一顶八角帽
《送灵狐岫宰恩阳》。唐代诗人韦应物的一首古风,把我召到了恩阳。
恩阳距今很远。1480多年的历史,一直在米仓古道上蹀躞不已。
我在恩阳古镇,逡巡不已。
走过郡,走过县,走过镇,览尽一路风光,留下一地沧桑。38条街巷朱漆斑驳,82株古榕翠绿苍劲,个个都是见证。但都是:沉默如金,守口如瓶。
只有那个倚门独守的老翁,与我最亲最近。
从他那张热情好客的豁嘴里,我获得了我想要的故事:红军在恩阳建立苏维埃,张思德在列宁学校读书……
青石铺就的街道起伏不平,并行的两双脚步歪歪斜斜。顺着老人浑沌的目光,我看到了无数醒目的石刻:“红军胜利万岁!”“粉碎川陕会剿!”“为土地归农民而战争!”“拥护红军!”红色的标语,巨大而深刻。
老翁返身回家,我又迈步前行。
猛一回头,老人头上,多了一顶八角帽。
大年初一,伏灵寺烧香所见
一条绝路向云端蜿蜒。
一缕阳光在心中灿烂。
大年初一的早晨,就是一年的早晨。
如河的车流,如潮的人流,把兔年新年的好光景,一波一浪卷向伏灵寺的深处。
车流下沉,人流上升。
如蚁的人群,怀揣一颗热锅蚂蚁的心情,像蚂蚁一样蠕动前行。西装革履,布衣草鞋,美女丑男,黄发垂髫,都有一个好表情。
我是一个例外者。
我在三界之外,静观几幅生动的场景:
——两座石狮据守山门,怒目而视众生。一个信徒磕头便拜,长跪不起。躲在身后的那个小孩,一脸惊悚,两眼迷茫。
——两个俗人,一个和尚,在吵架。高居莲台的观音,微笑不语,两指轻轻一弹,甘露,从净瓶掉下来,一滴,两滴。这是观音的眼泪吗?
——两个学生,一个乞丐,在讨钱。伸着的手,空空如也。信佛与行善,难道就是矛和盾?
——观音,弥勒,普贤,文殊,地藏,普度众生的菩萨和圣士,在普度众生觉悟的同时,也歆享着众生烟熏火燎的折磨。幸福还是痛苦?他们是否觉悟了自己?
——两只鸟,一只闪着金光,一只口吐妙音,在伏灵寺上空盘旋几圈,就乘着缥缈的云烟飘渺而去……
关于鸣沙山和月牙泉的比喻
母亲的乳房把儿女养大,大地的乳房把山川养大。
河西走廊的一把好乳啊,鸣沙山,她把敦煌养大。
她流动的乳汁,不是风沙,却是可以飞翔的金子。敦煌的白天黑夜,春夏秋冬,过去现在,都被金子的内心,照得辉煌。
假如上帝驾凌敦煌,如果上帝一觉醒来,对镜梳妆,定会惊讶发现——
鸣沙山下的月牙泉,真像他的眼睛;月牙泉浓浓的乳汁,就是他的眼泪。
睡眼惺忪的上帝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沙漠中一泓清泉,苍生有幸!
鸣沙山越长越高,月牙泉越缩越小,黯然神伤!
姓氏史:以徐为例
一个姓氏,是一个国、一个家的脸,笑容与皱纹,荣与辱,沉与浮,都被叫做历史。正如一棵树上的花,灿烂时叫花,凋零后成泥,注定都是宿命。
徐氏的宿命,源于一个叫若木的君王。他以颛顼之后伯益之子的名义,受封徐城,建立徐国,种下一棵能够开花的树苗。后嗣徐偃王据东夷之首,拥淮河之要,行仁义之政,把西周春秋的天空,搅得风起云涌,并做了一个大胆的好梦:大树参天,枝繁叶茂,鲜花灿烂。周室必欲伐之而后快。以至于后,不得不向周低下高傲的头颅,继而被楚削去虬枝,被吴连根拔起。先王的梦,亡国之君徐章禹,哪里还能续下去?
落花流水春去也,唯有最后一片树叶,躲在风的背后,承袭一缕飘不去的花香。
我们叫它姓氏。
许慎曰:“徐者,舒缓之名也。故其后虽为武未尝无君子之风。”
树已倒,猴不散。徐氏君子,如风中之花,香飘万里——
城北徐公,是美男子,也是君子。
秦人徐福,东汉哲学家徐斡、著名女诗人徐淑、徐州高士徐稚,三国谋士徐庶,唐时书法家徐浩、文学家徐寅,宋代诗人徐照,明代科学家徐光启、文学家徐渭、地理学家徐霞客,清代医学家徐大椿、科学家徐建寅,近现代大画家徐悲鸿、教育家徐特立……
弹指数我徐氏,荦荦大端,谁不君子!
一个姓氏,是一个国留给一个家的宝库和锦囊。打开,就看到了灵魂、胎记、脐带、血脉、气运。还看见:蜿蜒的根,藏宝的图,先人从未走过的路……
(正有一些后来者,在路上徜徉,逶迤如蚁。张王李赵,周吴郑徐……)
深沉的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