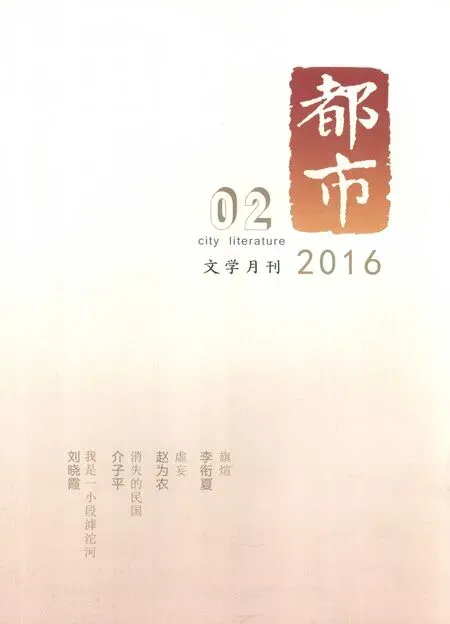粗粝的语言,精致的文本
——我看曹乃谦
杨新雨
粗粝的语言,精致的文本
——我看曹乃谦
杨新雨
一
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文坛巨擘汪曾祺就激赏曹乃谦的小说,并极力举荐他,之后还说他是“一举成名天下闻”。他的小说一起步就连续发表于国内的大刊及台港的报刊,不断入选各种选本,还被翻译到国外,许多文坛大腕也都给予了赞扬。这些我都是有记忆的,所以曹乃谦并不是现在才火,而是成名已久。
我觉得他那时,就像是我在乡间见过的一种景象:农民在山上燃起一堆小火,烤食并取暖,火堆中溅出了火星,燃着了附近的草木,借着一股上升的风,霎时间就窜上了山坡,要扑灭它已经做不到,火不停地往上蹿,蹿向山顶……
后来却有了点阻隔,使他未能彻底做大。如他后来所说的,是因服侍病重的母亲,为尽孝而辍笔。
然而他又火起来,而且这火带上了诺贝尔文学奖的气息。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马悦然,在中国大地上游荡着,他对曹乃谦的喜爱,好像是超过了其他中国作家。他说了不少话,可能是由于各媒体的重复报道吧,给人的印象好像是,马悦然逢人便问:知道曹乃谦么?回答:未知。马正色告之,他绝对是中国最一流的小说家,他与莫言、李锐都有机会获得诺贝尔奖。有记者探问,您是不是已经推荐了曹?马笑而答曰,这个不能说。如此的绘声绘色,将诺贝尔文学奖的气息营造的无比浓烈,而且指向如此具体,以至于我觉得,在某一天的清晨,从新闻中获知曹获了诺奖的消息,我也早已没有了感觉。
可是我一直没有读他的作品,当初,可能是手头没有,也懒得去找。另一种心理可能也有关,那时我好像是更愿意读现代一点的东西,另外我喜欢自然一点的没什么明确意图的写作。而当时写乡土的东西是非常流行的,实际上一直在流行,甚至可以说一直在占统治地位。我想他的小说也不过是这洪流中的一块浮木吧,也许有点儿特点。那时,写乡土的作品可能包含了不少东西,既寻找点什么又批判点什么,本土的人和外来扎根的人都在写,成了大名的也非常多,只山西就有郑义、李锐等名家。总之,他的小说我当初一篇也没读过。
而如今不能不读曹的小说了,于是我一下子读了他二十几篇小说。只得承认,我被吸引、被笼罩。
曹乃谦的小说,也让我再一次回到那个本应该是常识的问题,什么是文学,什么是好的文学。对我,这个问题好像从来没有成为常识,它总是不期而至。想清楚的一点是,任何一种理论解说,都不应是文学的出发点和规范,我们只能审视:事实上存在着怎样的文学。
只有极少数的人能够以自己的方式诠释文学,因为大多数的写作都互相雷同,甚至,都只是无意识的仿造。曹乃谦也许可以算这极少数的人之一,我说也许,因为我并不是权威,同时我也不是那种总是敢于下定论的人。
二
我看到,曹乃谦操着原封不动的生活口语和方言土话,唱着令人心颤的民歌“要饭调”,荡入了文学。这么直接,这么彻底地使用乡村语言,以我孤陋寡闻之所见,曹乃谦是唯一的。而且他显然获得了成功。奇异的感觉由此产生,他好像是并无意识也无须勇气,轻而易举地完成了一个创举,而人们还没有充分认识这意义。
他拒绝了以规范语言为媒介,他的写作直接与生活接轨,与他相比,许多人的写作,都像是主要与书本接轨。杜甫有诗云:“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可见主要与书本接轨的写作由来已久,这是我不赞成的写作路子,中国最不缺少的也就是这种路子的作品。
普通话和书面语言,缺乏表现力,而生活口语和方言土话,生动传神,却有地域的局限,这是常使我困惑的难题。我看写作者们一般采用的是折中的办法,就是有限度有选择地使用方言土语,有人认为应以大家能看懂为限度,有的是将方言作一点改造,但这实际上成了一种杂拌的不伦不类的语言。因为任何一个地域的语言,都有各自的纯正性,它们完整而有效,自足而自如,有滋有味,有情有调。
有些方言也可以溶入城市的语言,比如东北的“忽悠”,全国都理解了也学会了这个词语,而用普通话来翻译它就有点困难。小时候看电影《小兵张嘎》,日本鬼子的胖翻译官对罗金保和张嘎子说:“慢说吃你几个烂西瓜,老子在城里吃馆子都不花钱。”当时我就不知道这“馆子”是什么食品,也不知道是哪两个字,问伙伴们,也都不知道。很久以后才知道了“馆子”是指饭店,而且使用很广,我想它原本也是来自方言。我的家乡将蚂蚁叫成“麻皮夫”,这是大致的谐音,我不知道这三个字怎么写,有人说应写成“蚂蚍蜉”,我一下感到了惊奇,这不成了很文而雅的名词了?古诗有云,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书面语言的来源也应该是生活语言吧。
从一篇文章里还看到曹乃谦拒绝给他小说中的方言加注释,他说:“聪明人自会猜出那意思,看不懂的拉倒。”他这话让我佩服,这表现了他对所使用语言价值的认定和自信,还有热爱和尊重。
东北的“忽悠”人们学会了,那么,东北方言学得,我们山西雁北方言就学不得?这或许也是曹乃谦的态度。而不管人们想不想学,这都是真实存在的语言,时间总在千年以上,这本身便是价值。
从文学的意义上,方言其实不可翻译。我生活过的故乡与曹乃谦所熟悉的农村同属晋北,他小说中的方言土话,对于我完全不是障碍。以我的感觉,家乡的有些话,其微妙处用普通话是无法翻译的,硬要翻译,味道就不对了。
因此曹乃谦使用全套方言土话的好处就显示出来了:多么省事,再不用寒窗苦读,皓首穷经,生活中怎么说就怎么写,对话语言照搬上来,描述语言也用老乡说事的那种话,真正的文如其人,真正的本色。是生活中的语调,而非书面的语调;是生活中的味道,而非书面语言的味道;又有古意,是民间的语言化石。用曹乃谦惯用的复句来说,这真是太好了,这真是太好了。曹乃谦也许真的创造了一个范例?在这里,我还得说,我不是专家权威,但我不妨将这意思说出来。回想一下,我们历经的书面的文学语言是什么?文言文,韵文,白话文,古已有之的白话文,欧化的白话文,合乎语法规则的白话文,还有如今的网络语言,等等。
当然,对方言的如此使用,我也有些疑惑,比如,方言肯定不是都有相应的文字,而有些发音,普通话里好像也没有,那么,到了书里,这字该怎么写?此外还有一些疑惑,暂且不说。
一切都在逝去,一切都在变异,速度越来越快,地球越来越小,许多情形前后略一对比,常令人瞠目结舌。所以曹乃谦的真正源于生活的写作可能还有一个意义,即以文学的方式留存逐渐消亡的生活与语言。
再说他的文本形式。我所想象和追求的理想的方式,是自然天成的方式,而他是不是也轻易地做到了?由观察体验而寻求表达,源于内在的诉求渴望,流出了自然的形式,自然的曲线和波动,如河流一样。他是这样的吗?
有一位先锋写作者对我说,比如有一个作品,写得并不好,可是它创造了一种新颖的有价值的形式,那么,以后的作家可以按这个好的形式作出好的作品,这就是形式的意义。对这种理论我是大大摇头,我认为并不存在这种情形,如果作品不是好的,怎么能说他的形式是好的?如果这是一个好的作品,又管它是什么形式?好的形式也许应该是使人感觉不到它。单纯的形式探索我不敢说没有意义,但我总认为,好的作品不会由此产生。
我想,写的多了,谁都会有自己的形式,甚至自己的教条,但这教条如果是自己创造的,或者是自然形成的,那就也是好的。
三
曹乃谦的小说能有这么大的影响,除了独特,还因为确实是好看。他的描述,无不生动传神,无不真切动人,用笔简约而情景毕现。
请看《山丹丹》中的一句话:“瞭见大盖帽儿们的那辆吉普车一蹦一蹦地开走了。”不写路坑坑洼洼,只说车一蹦一蹦地,就将路面的情形包含于其中了,而且更生动形象,若说颠簸着走了,则只是状态的陈述,不是生动的描写了。用笔的节俭而有效,由此可见一斑。
他的小说让我想到两个字:准确。观察的准确,理解的准确,用笔的准确,这不是什么文字的功力,而只能是聪明和悟性。但最主要的原因,我想了一下,我觉得是因为他写的全是真的,而不是想出来编出来的,细节可能全是真的,情节和故事也多半是真的。
如《沙蓬球》中,贞贞临行送鸡蛋,后悔地大声哭喊着:“我要呀我要呀,我要那两颗鸡蛋呀”,这并不精彩,却是如此的具有真实感,那情景,如一组镜头拉近到眼前,令人禁不住热泪盈眶。
取材的真实绝对超过聪明的编造。我最不喜欢看的,就是编出来的细节,故事和情节可以编,但细节不要编,可我看大部分作品里的细节都是编出来的,或借用别人的,大家都借用,于是我们就看到许多雷同的细节,我每看到这样的细节,就不想往下看了。而我遇到了曹乃谦的小说,它给出了满满当当的真东西。
我认为他是写情的高手,好像没有人从这方面评论他。初萌的纯洁的爱情,胆怯而又幸福的让心儿发抖,他将爱情的心理情态写的如此逼真,这也是因为源于真实,当然,也源于真情。《野酸枣》和《亲圪蛋》,都写了动人的让人伤怀的爱情故事,其中的两个少女形象,让人难忘。由此我甚至想,爱情的描述可以衡量一个作家是否够格,如果心中没有爱情,如何能写的出?而心中没有爱情,又如何能算作家?描述爱情,有许多人总像是在编织花环,将爱情着意装点,浪漫、绚丽却不真切,也不动人。曹乃谦的爱情描述,都只是平常的,原本的,具有全部的细节真实,心理真实,以及时代真实,平常的人与事才形成最精妙的描写。
《小精灵》一文,充分展示了曹乃谦对人物心理情态的描绘才能,令人赞叹不已。一个活泼捣蛋翻天覆地的可爱的小女孩,一个灵透里外、内心复杂的可怜的小女孩,在曹的笔下生动无比精彩绝伦而准确无误。而其中包含的情,又是另外一种。
《忏悔难言》,也是一篇写情的文字,却可以称作是一种“弄情”。这是一篇很让我吃惊也让我奇怪的小说,一篇完全不同的小说。机心,罪孽,高级的阴谋和手段,狭窄的心胸,阴暗的心理,奇异的报复,巧妙的构思设计,柔滑如丝的描述,真实的细节,不真实的情节和故事。一篇有点洋化有点高级的小说,一篇紧紧扣住人的小说,一篇既让我喜欢读又不愿意认可的小说,脑中由此生出了“作家的复杂性”一语。
《孤独的记忆》是一篇散文,是我非常喜欢的一篇。文章写了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一次笔会,这种题材写的人不少,而有谁能写得如此生动有趣?让人如临其境,如此自然,却又如此独特?在薄冰的湖中打冰漂和划船的描写堪称美妙。看曹乃谦的描写,能想到大多数写作者的描写都是雷同的,他们看到别人写过的情景,就有了灵感了,就会模仿一番了,而面对新鲜的事物,脑子就没感觉了。且看曹乃谦面对新颖的景物和人物,写得是多么从容而精彩。他还不无矫情地写了自己在笔会上的孤独,却借机描摹了一些文人,这些看不起或嘲笑曹乃谦这个新作者的文人们,该在此好好端详一下自己的形象。最好笑的,是曹在喝了许多酒后,为了证明自己具备成为大作家的条件即自己也有很强的性意识,而追赶着要摸一位女作者的背。我觉得他这也有故意搞笑的味道,但他却显得一本正经。所以这篇文章也有半真半假亦真亦假的味道,这就更有意思了。曹乃谦随意的描述会有如此的妙味,这其实是真正显示作家水平和风貌的地方。
使曹乃谦获得盛誉的,是他的“温家窑风景”系列,总的题目又叫《在黑夜想你没办法》,台湾出版,马悦然又翻译成瑞典文,等等。所以文坛及国外对他作品的价值认定,主要依据的是这本书,我上面提到的作品都不包括在其内。我的感觉,“温家窑”系列,因语言的粗粝,用笔的简约,显出一种瘦骨嶙峋,轮廓峥嵘的气象,仅此就是大手笔。而王安忆说他的小说是“精致却天衣无缝”,真名家究竟是别具只眼。貌似粗粝,实则精细无比,又包含了柔软的心。这一组最有名的作品,我在此不细谈。
前面提到的曹乃谦的小说,与“温家窑”相比,语言明显地松软柔和了,少了棱角,多了线条,有时几乎是柔滑如丝,情调则更自然丰盈。我赞成作家有自由的情性,自然的变化,不必特意追求或坚持什么风格,总之,前后都是好作品,各有各的好看。
四
在本文的开篇,我谈到过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先生对曹乃谦作品有高度的评价,就此我想谈一点看法。首先这早已成为文学界的一个话题,一位文友说,外国人哪有中国人更了解和更懂得中国文学?马悦然那么大年纪了,对中国的当代文学,他能读多少?据我所知,持这样观点的绝不止他一个人。我是这样想,能够超越不同国度、不同的文化心理和文学认同,而打动异国的文人,这不是证明了真正的文学的力量吗?换句话说,能够经得起文化的过滤,而仍然留存动人内容的不是真正的好东西吗?谁能能对自己的作品有这个自信?而马悦然,一个老人,一个在自己国家的文化中浸润已深的老人,要打动这样一个人,是不是比打动一个中国人更困难呢?
那么,是我们民族不同的东西引起他们的兴趣,还是共同的人性内容得到了认同?我认为是后者。一个做文化研究的学者的兴趣会是前者,而一个作家的认同会是后者。
我感到,有一个东西一直在起作用。早在电影《红高粱》放映时,国人就开始了一种说法,说是我们的一些作品是靠取媚外国人的而获奖的,以什么取媚呢?是以我们的落后和缺点。开始我觉得这种说法至少在知识界不会有市场,但后来发现我错了。我至今也很费解,这种认识怎么会有这么广的人群,而且这么持久?很明显,这种认识需要有一个前提,就是外国人看到我们的落后和缺点就会高兴,而我们讨好他们的方法就是展示我们的不好。这怎么说呢?我无法不承认,这是我们在以己度人,一种根深蒂固的东西。我希望在今天,曹乃谦的作品,比如他的“温家窑系列”,已经可以脱离这种责难。
马悦然给曹乃谦的《到黑夜想你没办法》一书作序,序的题目是《一个真正的乡巴佬》,这是马悦然的感觉,而我没有这样的感觉,也不这样理解。曹乃谦七个月大的时候就离开了原籍,他的农民身份就只是这七个月,之后他就成了市民,中国山西省第二大城市大同市的市民,成年以后,他是文工团演奏员、工人、国家干部等。他不过是有时候回乡或下乡,但即使在乡下待得很久,只要他不是农民身份,就不会有真正的农民心理,这一点至关重要。他对乡土语言和文化的兴趣,对乡村人群的关注,并浸润其中,也并不能使他成为乡巴佬。而他的不修边幅、落拓不羁,粗言犷语,也只能看作是城市文人的某一种形态。他是一个有情性的真实的文人,是一个爱好广泛并多才多艺的城市文人,他歌唱得好,箫吹得好,围棋下得好,书法也很好。
我想说的是,一个真正的乡巴佬是写不出乡巴佬的,要写好乡巴佬,至多只能做个半吊子乡巴佬,同时还得是整个的一个真文人,这后一点永远是最重要的。文人可以写出自己,而乡巴佬却写不出自己。
责任编辑梁学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