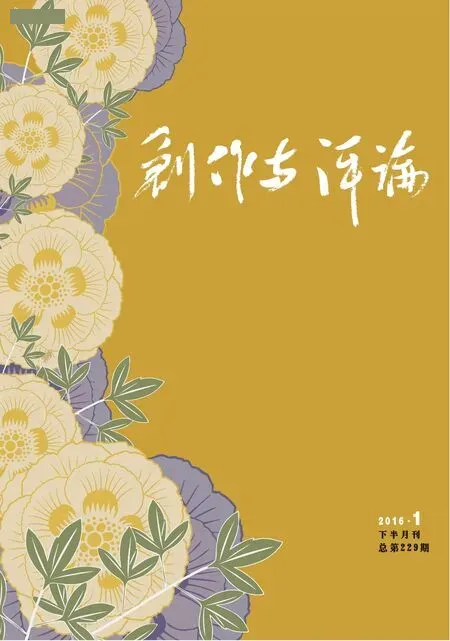“在谈论诗歌的时候我们在谈论什么”——2015年诗歌的新现象与老问题
○霍俊明
“在谈论诗歌的时候我们在谈论什么”——2015年诗歌的新现象与老问题
○霍俊明
2015年是名符其实的“微信诗歌年”(据相关统计微信使用数量已达7亿之多),诗歌正在进入“微民写作”和“二维码时代”,“人到盖棺时也很难定论/自己说不清楚,别人更不能/最简单的办法是,死后请一个匠人/把我曲折的命雕刻成二维码/算是我留给世界的最后一方印章/形状一定要刻成祖屋的窗棂/要镂空的,百年之后/就把二维码安放在我墓碑的正中/扫墓人一眼就能扫出阴阳两维的苦/扫完码后,不忍离去的那位/估计是我的亲人,也可能/是我的仇人”(麦笛《我的二维码》)。确实一年来最受关注的就是微信自媒体不断刷屏的众多诗歌活动、事件(比如余秀华事件、“回答——中国当代诗歌手迹拍卖会”)、奖项(一年来各种诗歌奖项达百种以上)、诗歌节、诗歌出版物(自主出版以及新近出现的众筹出版模式)和译介,据统计现在每天海量的集束型的诗歌产量早已经远远超越了《全唐诗》,而中国诗人的数量早已经跃居世界首位,中国成了名符其实的“诗歌大国”。著名新诗研究学者孙绍振在《当前新诗的命运问题》中就认为“没有一个时代,诗的产量(或者说新诗的GDP)加上新诗的理论研究,达到这样天花乱坠的程度,相对于诗歌在西方世界,西方大学里备受冷落的状况,中国新诗人的数量完全可以说是世界第一。”
尤其引人注目的是每天都在激增的诗歌微信公号和微信群给诗歌生态带来的不容忽视的影响,甚至自媒体被认为给新诗的“民主”带来“革命性”影响。在碎片化、电子化和APP移动临屏阅读语境下即时、交互性的诗歌写作、阅读和批评实现了即时性、日常化和大众化。由此诗歌在公众中的地位和形象有所改变——诗歌回暖,诗歌升温,诗歌繁荣,诗歌重新回到社会中来,诗人与读者之间的距离被空前拉近。面对着这些诗歌活动,我们正在迎接一个“诗歌活动”已达高峰期的时代。得出“活动多,好诗少”这样的结论是有其依据的。然而,我们必须回应的一个近乎老生常谈的话题——在谈论诗歌的时候我们到底在谈论什么?尤其是面对2015年诗歌写作和诸多现象,这个问题就会变得愈益重要和不可回避。在诗歌“活动”已达高峰期的时候研究者应对以上的诗歌判断做出审慎分析,而不要急于下结论。
与小说等其他文体相比,一百年来的新诗共识度和自信力到今天也没有完全建立起来,甚至很多时候招致大众和读者不满与批评的恰恰是诗歌。新诗一百年,其合法性在哪里呢?这似乎又到了重新为新诗辩护的时候了。这既涉及到诗歌的“新现象”又关乎新诗发展以来的“老问题”。围绕着2015新诗的一些新的现象和一些老生常谈的问题,在新与旧的对话中我们重新来面对汉语新诗的场域就显得非常必要——这既是美学的问题又是历史的问题。
一
多年来人们已经习惯了“诗歌”与“大众”之间的平行或天然的疏离关系,诗人不在“理想国”之内。但是一旦诗歌和“大众”发生关联往往就是作为诗歌噱头、娱乐事件、新闻爆点。这又进一步使得诗歌在公众那里缺乏应有的公信力。然而被专业人士指认为缺乏基本诗歌常识的大众对诗歌和诗人的印象和评说往往令人匪夷所思、啼笑皆非,但最终以失败告终的仍然是专业诗人、读者和评论家们。我们更多的时候已经习惯了将一首诗和一个诗人扔在社会的大熔炉中去检验,把他们放在公共空间去接受鲜花或唾液的“洗礼”。对于中国文学场域来说,很多时候诗歌是被置放于社会公德和民众伦理评判的天平上。而公共生活、个人生活以及写作的精神生活给我们提供的则是一个常说常新的话题——诗人如何站在生活的面前?一首诗歌和个体主体性的私人生活和广阔的时代现实之间是什么关系?
每当面对一年来的诗歌,我们总会满怀期待地想梳理它的“新面貌”,似乎今年的诗歌与去年和往年的总会有所不同、有所“进步”。实际上,诗歌正离我们远去,诗歌正在远离读者以及诗歌的边缘化、写诗的比读诗的多、大众读不懂新诗,这些声音这么多年来一直伴随着新诗的发展。很多人对2015年诗歌的最大观感就是诗歌很热闹,而且是不一般的热闹。在各种诗歌活动和诗歌事件中,尤其是微信强大力量的推动下,似乎暌违的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朦胧诗热潮几十年之后再次降临,诗歌重新又回到了“读者”和“社会”中来,诗歌再次高调地走向了公众视野,新诗与读者之间的距离被空前拉近了。确实,以微信为代表的自媒体对诗歌生态的影响已经成为现实,似乎每个人都成了毫无差别可言的“手机控”“微信迷”和“屏幕人”。近两年的诗歌在微信自媒体的推动下频繁进入到了一个个火热沸腾的社会现场,诗歌技术空前成熟,诗人的地区和国际交流(比如青海湖国际诗歌节、2015年中韩诗歌论坛、香港国际诗人之夜、第十届《诗歌与人》国际诗歌奖、首届李白国际诗歌奖,为了促进两岸诗歌互动交流于2015年12月创刊的《两岸诗》)日益频繁。这似乎成了近两年中国诗歌的标志。
那么,诗歌真的“回暖”“升温”“繁荣”了吗?
就此问题,每个人的观感和判断并不相同。
支持者高呼雀跃认为新媒体尤其是微信给诗歌带来了民主、进步和自由的福音。这方面具有代表性的例子就是《中国首部微信诗选》(团结出版社)的推出以及形形色色大大小小的微信圈。反对的声音则认为微信平台上的深度阅读已经不可能,“新诗和读者的距离,这几年虽然有所缩短,但是仍然相当遥远,旧的爱好者相继老去,新一代的爱好者又为图象为主的新媒体所吸引。”(孙绍振《当前新诗的命运问题》)而黄灿然则认为只要你想读书即使微信上也可以进行深度阅读。显然,新诗与新媒体的关系已经被很多研究者提升到了“命运”这样大是大非的程度。著名诗人北岛更是认为新媒体所带来的是新的洗脑方式和粉丝经济,甚至成了一种“小邪教”,“某些作家和学者不再引导读者,而是不断降低写作标准,以迎合更多的读者。这是一种恶性循环,导致我们文化(包括娱乐文化在内)不断粗鄙化、泡沫化。在我看来,‘粉丝现象’基本上相当于小邪教,充满煽动与蛊惑色彩。教主(作者)骗钱骗色,教徒(粉丝)得到不同程度的自我心理安慰。”(北岛《三个层面看生活与伟大作品之间“古老的敌意”》)。尤其是“传媒话语膨胀时代”的微信平台因为取消了审查和筛选、甄别机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诗歌多元化发展,使得不同风格和形态的诗歌取得存在合法性的同时也使得各种诗歌进入到鱼龙混杂、良莠不齐的失范状态,随之也降低了诗歌写作与发表的难度。微信等自媒体并不是一个“中性”的传播载体,正如希利斯·米勒在《全球化时代的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一文中所强调和忧虑的那样“新的媒介不只是原封不动地传播那内容的被动母体,它们都会以自己的方式打造被‘发送’的对象,把其内容改变成该媒体特有的表达。”所以一定条件下新媒体自身的“传播法则”会对诗歌的观念、功能、形态以及话语形式和评价标准都会产生影响。就当下诗歌来看,写作者、评论者和传播者的表达欲望被前所未有的激发出来,“自由写作”“民主写作”“泛华写作”“非专业化写作”正在成为新一轮的神话。“微信诗歌”作为一种新现象当然需要时间的检验,需要进一步观察、辨析和衡估,但是就已经产生的现象、问题和效应来看,也需要及时予以疏导和矫正。软绵绵甜腻腻的心灵鸡汤的日常小感受、身体官能体验的欣快症、新闻化的现实仿写以及肤浅煽情的“美文”写作大有流行趋势。一定程度上新媒体空间的诗歌正在成为一种“快感消费”,这与娱乐化的电视体验类节目的内在机制是同构的——每个人都能够在新媒体空间亲自体验各种诗歌讯息。微信诗歌话语的自身法则使得点击量、转载率的攀比心理剧增,也进一步使得粉丝和眼球经济在微信诗歌中发挥了强大功能。这使得诗歌生态的功利化和消费性特征更为突出,而“以丑为美”“新闻效应”“标题党”“搜奇列怪”“人身攻击”“揭发隐私”的不良态势呈现为不可控的泛滥,其中文化垃圾、意见怪谈更是层出不穷。即时性的互动交流也使得诗歌的评价标准被混淆,写作者和受众的审美判断力与鉴别力都在受到媒体趣味和法则的影响。
在“无限制性阅读”中每一个写作者都可以成为信息终端,写作的匿名和无名状态被取消,人人都可以堂而皇之地发言,每个人都可以同时充当运动员和裁判员的角色,所以微信在一些诗人和研究者那里被认为给诗歌带来的最大利益和进步就是“民主”。这一民主化的平台极大了推动和刺激了各个职业和社会阶层的普通写作者,甚至带有普及性的大众化的正在进一步扩大范围的“非专业写作”已经成为一股潮流。而微信这一“写作民主”的交互性代表性平台已经催生了“微信写作虚荣心”,很多人认为只有拥有了微信就拥有了自己的话语权,甚至滋生出了偏执、狭隘、自大的心理。与此同时电子化的大众阅读对诗歌的评价标准和尺度也起到了作用。由此引发的疑问是诗歌真正地解决“普及”和“大众化”问题了吗?碎片化时代的诗歌写作是否还具备足够引起共识和激发公信力的能力?尤其是在新媒体平台上海量且时时更新的诗歌生产和即时性消费在制造一个个热点诗人的同时,其产生的格雷欣法则也使得“好诗”被大量平庸和伪劣假冒的诗瞬间吞噬、淹没。与此相应,受众对微信新诗和新媒体诗歌的分辨力正在降低。而如何对好诗进行甄别并推广到尽可能广泛的阅读空间,如何对新媒体时代的诗歌做出及时有效的总结和研究就成了当下诗歌生态中不可回避的重要课题与难题。新媒体平台也使得新诗的跨界和立体传播成为可能,而国内首档电视诗歌跨界真人秀节目四川卫视推出的“诗歌之王”显然是要将“边缘化”的诗歌与“大众”结合,而诗人与歌手的搭台(现场作诗、现场谱曲演唱)以及全国设立预选赛站点也显而易见是迎合了娱乐化的内驱力。
二
与这种诗歌“日常化”“大众化”和“非专业化”相应,一个重要的写作趋向就是随着以余秀华、许立志、郭金牛、乌鸟鸟、老井为代表的“草根诗人”的“崛起”和大量涌现。
2900个县城,三亿左右的工人,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之众的“草根”诗歌写作群体,确实构成了新世纪以来诗歌新生态。这种自发的、原生的直接与生命体验相关的“大众写作”有别于以往的学院派、民间派和知识分子等“专业诗人”的写作美学。以“草根诗人”现象为代表的诗人与现实之间的紧密关系使得诗歌的现实感、人文关怀、及物性都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提升。这大体印证了米沃什的“见证诗学”。他们直接以诗歌和生命体验对话,有痛感、真实、具体,是真正意义上的“命运之诗”。与“草根诗人”现象相应,诗歌写作的题材化、伦理化和道德感也被不断强化,底层、草根等“非专业诗人”社会身份和阶层属性得到空前倚重。而底层经验、生存诉求、身份合法性在诗歌写作中得以一定程度地体现,这一趋向围绕着年初的余秀华事件展开并扩展开来(2015年1月13日沈睿的文章《余秀华——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在微信公号“民谣与诗”上发布,此文1月12日发在豆瓣)。余秀华诗集《摇摇晃晃的人间》首印1.5万册几天即售罄后不断加印,《月光落在左手上》更是4次加印销量突破10万册,这在新诗集中是前所未有的。而这两本同名诗集在台湾的推出更是印证了“草根写作”不仅代表了一种“新美学”,而且在社会层面更具有意想不到的“精神号召力”。此后,草根诗人写作作为一种“新媒体效应”被继续发酵增温。“工人文学奖”网站、微信公共号“中国打工诗歌精选”“我的诗篇”持续推出“工人诗歌”的作品和讨论专辑,先后在北京和天津等地举办老井(矿工)、邬霞(制衣工)、唐以洪(制鞋工)、田力(鞍钢工人)、魏国松(铁路工)、陈年喜(爆破工)、白庆国(锅炉工)、绳子(酿酒工)等几十名工人“我的诗篇:工人诗歌云端朗诵会”以及2015打工春晚。在各种媒体尤其是自媒体推动下,这些农民工诗人和产业工人的写作现象引起主流媒体和社会的广泛关注。微信公号“我的诗篇”以及同名记录电影和诗歌选本“当代工人诗典”的推出都将“工人诗歌”推到了舆论的焦点。在五一国际劳动节期间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五一特辑《工人诗篇》每天滚动播出。那么由此带来的思考则是诗人与厂区和机器之间的关系。
当年哈特·克兰曾乐观地认为诗歌在机器时代的功能与它在其他任何时代一样,“它对人的价值最综合最完满的表现力仍在本质上不受科学的侵袭”。实际情况是这样的吗?就目前的工人阶层的诗歌写作来看,机器无论是对个人生活还是整体生存境遇以及精神状态都带来了非常“现实”的影响。许立志、余秀华、郭金牛、老井等这些“草根诗人”的诗歌写作为我们重新思考诗人与时代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观察入口和美学路径。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工人诗人都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专业诗人”,而是来自于底层和生产一线的“草根”。这体现了诗歌的大众化和写作泛化趋向。这一自发的写作状态和现象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当下人民大众抒发时代精神和现实观照的潮流,不仅是“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而且更重要的是真正做到了“人民抒写”“人民抒情”“人民抒怀”。对于身处底层的工人诗人来说,他们不像其他诗人那样奔赴现实,而是直接身处现实之中。他们的写作是直接来自于自身的生命体验,直接以诗歌和生命体验进行对话,真诚质朴有痛感,是写实写真的具体而感人的“命运之诗”,展示了艺术最原初的鲜活形态。这一文学经验不仅关乎个人冷暖和阶层状态,而且与整个时代精神直接呼应。这些诗朴实、深沉,直接与生命和现实体验对话,具有打动人心的情感力量和现实主义的风格。但是,“草根诗人”写作也尤其明显的局限性,比如对现实和自我的认识深度不够,在处理现实题材和个体经验的时候没较好地完成从“日常现实”到“诗歌现实”的转换、过滤和提升。其中的写作有浮泛、狭窄、单一和道德化倾向,缺乏美学上的创造力,社会学意义大于文学意义。与此同时,人们在谈论这些“草根诗人”时又不可避免地与阶层身份、社会道德、公平正义、悲悯同情、身份焦虑、生存命运等“社会学”关键词缠绕在一起。甚至有论者提出要重启“阶级诗学”,而认为“工人诗歌”是被空前遮蔽的最具进步性和时代意义的写作代表的说法显然有失偏颇而值得商榷。对以草根诗人、工人诗人为代表的“非专业写作”的讨论至今仍方兴未艾,而诗歌的点赞、转发和刷屏更多则是依赖于诗人的社会焦点、热点。围绕着余秀华等“草根诗人”所生发的各种观点、立场不仅显示了移动自媒体时代诗歌在生产、传播、接受和评价等方面的新变,而且也揭示了不同阶层的人通过这些来自社会底层、基层的诗人所显现的对社会和人生的不同理解。诗人的社会身份被强调甚至放大的过程中体现了公众媒体和读者群什么样阅读心态和评判标准呢?在自媒体阅读、大众阅读和媒体人那里争相关注的并不是草根诗歌本身,而更多是这些诗人身份、苦难命运以及底层的生存现状和社会问题。实际上这也没错,为什么诗歌不能写作苦难?为什么草根阶层不能用文学为自己命运代言?针对“草根诗人”现象,中国作协创研部和诗歌委员会召开“草根诗人”现象与诗歌新生态研讨会,及时把脉,肯定其写作特点和意义的同时也准确分析了其中存在的问题和值得进一步疏导的写作方向,进而对大众化诗歌写作潮流的健康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文艺报》以“聚焦‘草根诗人’现象探讨当下诗歌新生态”为专题展开讨论与争鸣。吴思敬、张清华、罗振亚、大解、彭学明、刘立云、林莽和霍俊明、李壮等人在《诗歌给了他们放飞理想的另一个世界》《草根诗歌是这个时代的痕迹》《他们用灵魂书写灵魂》《成熟诗人:既是“兽”更是“鹰”》《诗歌顽强告诉人们相信未来》《寻找语言艺术的原初形态》《“草根诗人”引发了什么》等文章中肯定“草根诗人”重建了诗歌与生活的有效关系,修复了诗人的“社会发声”能力,是接地气的感动写作、灵魂写作,甚至其情感冲击力、震惊性经验和艺术水准让一些“专业诗人”汗颜,同时也强调苦难命运和生存遭际并不等同于诗歌,应该把个体现实转换为语言现实,进而指出应进一步辨析“草根诗人”背后的写作机制、文化环境,尤其是有些媒体批评过于强化和放大了“草根诗人”的阶层身份、社会属性和伦理道德感。谈文艺实际上就是谈社会、谈人生。围绕着“草根诗人”所生发的各种观点、立场不仅显示了移动自媒体时代诗歌在生产、传播、接受和评价等方面的新变,而且也揭示了不同阶层的人通过这些来自社会底层、基层的诗人所显现的对社会和人生的不同理解。草根诗人现象所引发的问题和值得深入反思的地方很多。如何维护诗歌和诗人的尊严,如何正确引导而不是沦为娱乐、狂欢和消费的事件已经成为当下中国文学新生态中亟待解决和正确引导的迫切话题。评价包括草根诗人的文学和文化现象应该是历史的、美学的、艺术的和人民性的融合的观点,而不是断然割裂并在一点上极端放大。历史上被铭记的诗人往往既具有美学的创造性又有历史的重要性和时代的发现性。无论哪个时代,不管出现多么轰轰烈烈的诗歌运动、诗歌事件和大张旗鼓的诗歌活动,最终留下来的只有诗歌文本。
由社会关注度极高的“草根诗人”写作,我们注意到诗人对现实尤其是社会焦点问题和公共事件的关注从未像今天这样强烈而直接。
这一定程度上与媒体开放度有关,比如天津氰化钠爆炸后很短时间内就出现了几十万首的诗歌,但是这些与社会新闻和公共事件直接相关的写作几乎没有可供持续传播和认可的代表性诗作,这些诗歌可能比那片废墟看上去更像是“废墟”。而对生存问题的揭示,对生态环境的忧虑似乎正印证了一句当下最为流行的话——雾霾时代诗人何为?而当下对“诗人与现实”“诗歌与生活”问题的热度不减的争议使得写作者对“现实感”的理解发生分歧。一部分人强调诗歌的“介入”“见证”“及物”“现实性”,强调每一个人都应该站在现场和烟尘滚滚的生活面前,将自己纳入到工厂甚至上千度的高温中去感受生活的残酷性;另一部分则认为诗歌应该保持独立性和纯粹性以及个体主体性,认为应该重新对“生活”“现实”“时代”惊醒衡估和再认识,也就是说难道有诗人是在“生活”之外写作吗?实际上二者各持的观点并非水火不容,关键之处是应注意到诗歌的“现实感”最终是“语言的现实”,因为诗歌的语言不是日常交际和约定俗成的,而是生成性和表现性的。而我们看到的则是微信话语、新闻话语和日常话语等“消息性语言”对“诗意语言”的冲击。而“现实”成为“现实感”必须要通过语言、修辞、记忆、经验和想象力来转换并最终完成为“文本现实”。在写作群体空前庞大,作品数量与日俱增的情势下,写作者的“整体图景”“个人风格”“公信力”“辨识度”正在空前降低。这是个体诗学空前膨胀的时代,而诗歌的现实介入能力、文体创造能力、精神成长能力以及个人化的历史想象里也相应受到阻碍。而新媒体话语对诗人个体性写作的空前鼓吹,全球化语境下诗人的“世界写作”的幻觉膨胀,这都使得私人经验僭越了本土经验,小抒情取代了宏大叙事。也由此使得口语写作、私人经验、个体抒情、消解诗意、日常叙事的无难度写作成为普遍现象,“口语”沦为“口水”,“个体写作”导向的是“平庸”和“碎片化”,“自由”“开放”导向的是“自恋”和“自闭”。换言之,全媒体时代的诗歌写作空间如此开放,而每个人的写作格局和精神世界竟然如此狭仄,每个写作者都在关心自我却缺乏“关怀”,每个人都热衷于发言表态却罕见真正建设性的震撼人心的诗歌文本。这让人们联想到当年《芝加哥论坛报》对雷蒙德·卡佛的小说评价,人性关怀是第一要素——“他这些角色可能属于混蛋、晦气鬼、失败者、傻瓜、同性恋,但每一个这样的角色又都心存关怀。”
三
中国新诗自诞生至今已近百年历史,在这期间,中国新诗从草创、实验到动荡、建设,历经众多诗人的艰苦努力,取得了辉煌成就,部分作品经历时间检验已成为经典。而本年度的诗集出版不仅数量上呈现井喷趋势,而且不同代际不同风格的诗集代表了新世纪以来新诗多向度发展的成果。代表性的诗集主要有《在天涯》(北岛)、《大是大非》(欧阳江河)、《木心诗选》(木心)、《无端泪涌》(陈超)、《外面的风很冷》(向明)、《韩东的诗》(韩东)、《滴水成冰》(伊沙)、《去人间》(汤养宗)、《骑手和豆浆》(臧棣)、《侯马诗选》(侯马)、《天上的日子》(雷平阳)、《杨克的诗》(杨克)、《灰光灯》(王寅)、《光谱》(邱华栋)、《截句》(蒋一谈)、《潜水艇的悲伤》(翟永明)、《山中信札》(路也)、《青衿》(何向阳)、《女巫师》(宇向)、《大门》(尹丽川)、《日光落在左手上》(余秀华)、《新的一天》(许立志)、《为何生命苍凉如水》(刘年)、《山岗诗稿》(王单单)。尤其是诗刊社31届青春诗会诗丛(杨庆祥、白月、江汀、李其文、天岚、张二棍、武强华、秋水、林宗龙、赵亚东、茱萸、钱利娜、黎启天、袁绍珊(澳门)、宋尚纬(台湾))集中展示了不同艺术特征的青年诗人写作景观。
但中国新诗在发展过程中也存在一系列争议颇多且仍未解决的诗学问题,这都需要从学理上予以梳理、辨析和反思。3月21日,由中国作协诗歌委员会与江苏省作协联合主办的“中国新诗百年论坛”启动。“中国新诗百年论坛”并非一次性举办的论坛,它将连续举办3年,每年举办5场左右讨论,每场讨论围绕一个特定的主题进行讨论。一年来已经完成“新诗自身传统构建及其不足”“百年新诗公共性”“新诗空间与地方性”“新诗现代性”“新诗与古典传统”“本土与西方对话”“新诗批评与阐释的迷思”“新诗的美学建构”“语言自觉与现代汉诗发展”等9场专题讨论,在诗界引起反响。在新诗百年即将到来之际,北京大学新诗研究院与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纪念新诗诞生百年新诗形式建设学术研讨会旨在立足百年新诗创作与探索经验,固化新诗形式探索成果与梳理诗体流变。百年新诗在寻找“自身传统”的情势下,伴随着文体自身的逐渐成熟,新诗正在找回自信,在强调“汉语”“本土经验”以及“大国写作”(欧阳江河)的吁求下,诗人对“本土现实”的关注、处理成为写作的内驱力。对新诗历史的总结,对经典化本文的推介,对自身传统和合法性依据的确立成为本年度诗歌诗丛、诗集、诗选出版的内在化要求,比如《中国新诗百年志》(中国作协诗刊社)、《百年诗歌》《百年新诗选》(洪子诚、奚密、吴晓东、姜涛、冷霜编选)《新诗百年纪念专号》、“标准诗丛”第二辑(作家出版社)、“中国好诗”第一季(中国青年出版社)、新陆诗丛、《中国好诗歌·最美的白话诗》《1991年以来的中国诗歌》《中国诗歌三百首》《中国口语诗选》《70后诗全编》以及诗刊社“中国好诗歌”的评选。对新诗百年的总结还体现为不同省份和地区带有“地方性”特征的“经典化”打造,如《中国当代民间诗歌地理》《福建百年百诗人诗选》《力的前奏——四川新诗99年99家99首》《中国彝族当代诗歌大系》(4卷)《四川新世纪诗选》《山东新世纪诗选》《在河以北——燕赵七子诗选》《河北新世纪青年诗典》《燕赵青年诗丛》《新江西诗派诗丛》《诗江西》《天津诗学34家》《21世纪贵州诗歌档案》,此外还有“全球语境与地方主义视域中的南方诗歌研讨会”“彝族地域诗歌写作群体”“闽派诗歌”“京津冀诗歌联盟”“中原诗歌高峰论坛”“北京青年诗会”“地方主义诗歌运动”“中国地方主义诗群大展”等地方性诗歌的强化与造势。这都旨在回溯百年新诗的历史脉络,时代状貌和美学趋向,及时梳理新诗的现状,试图强化新诗的合法性依据和文体自信力。这些既显示了专业性又带有普及性的新诗经典化工程都试图在规范和确立“好诗”的标准。这些关于百年新诗的研讨和出版都是有一定的建设性的。
2015年适逢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无论是相关诗选的出版(比如代表性的周良培编选的《抗战诗钞》)、刊物的诗歌专题(比如《诗刊》《人民文学》《中国作家》《解放军文艺》《滇池》《作家》推出的“抗战诗歌专辑”),还是从学理的角度予以历史性的梳理和总结(中国作协创研部与《文艺报》合作的《抗战诗歌作品巡礼:“思想的胜利”“美学的胜利”》)都再次证明诗歌的现实主义精神和家国情怀历久弥新的思想力量。在谈论“抗战诗歌”以及抗战胜利以来相关的诗歌创作不仅有诗歌美学的必要性(比如新诗的民族化、大众化、个人化以及现实主义与现代性等问题),而且是诗歌历史学的题中应有之义(诗歌与现实、时代、国家和民族的对应关系)。抗战期间在解放区展开的“诗歌民族形式”的广泛争论以及同时在国统区和解放区展开的大规模的朗诵诗运动都在进一步探讨新诗的民族化、大众化方面做出了有益尝试。抗战诗歌因为特殊的思想性、社会性有其不可替代的历史价值,又因处于中国新诗发展中的重要一环而具有发展的延续性。抗战诗歌以及抗战胜利结束以来70年相关题材的诗歌创作对诗歌的社会化和大众化功效予以了关注和推动,也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新诗的多样化的形态并对政治和斗争起到了宣传和教育作用。抗战时期的诗歌以及抗战胜利以来70年的各种风格的诗歌文本以艺术的丰富性和思想的厚重性印证了——诗歌的胜利不仅是思想的胜利,而且是美学的胜利。
在新世纪诗歌已经走完十五年之际,对新世纪诗歌尤其是当下的诗歌评价已经成为普遍现象(比如《文艺报》组织的西川、大解、臧棣、蓝蓝、刘立云等十诗人把脉当代诗歌:如何讲好中国故事的专题研讨)。有研究者认为在社会和文化的转型期和巨变期,诗歌仍然处于并不乐观甚至被诅咒的“乌鸦时代”(汪剑钊),甚至韩东认为1980年代以来的三十年诗歌景观整体扭曲,只与西方有关的写作观念发生联系。有论者认为当下诗歌受到传媒、技术、资本和市场的影响太大了从而丧失了知识分子立场和批判意识以及先锋精神,如欧阳江河认为当下的“很多泡沫的东西、灰尘的东西,浮在的表面、浮在记忆的表面,所以我们的诗歌会是软绵绵的,会是带有消费性质,会是有点颓废,会是有优美,很伤感很自恋很自我的一种崇高,很可能是一种幻觉。”确实,当下中国的社会与文化转型(比如城市化进程、生态危机、乡村问题)使得诗歌写作必须做出调整和应对,甚至一定程度上对赓续的根深蒂固的写作模式和诗歌观念进行校正,尤其是在新闻化的现实境遇面前,对于诗歌这一特殊的“长于发现”的文体类别,在媒体营销式话语充斥每一个人生活空间的时代,找到一首整体性的言之凿凿的具有“发现性”和个人化历史想象力的诗歌其难度是巨大的。
诗歌批评不是说好话说坏话,而是要“说真话,讲道理”,批评的高标准应该是像庞德所说的“批评不是画地为牢或制定禁律,它是提供起点。它可以使迟钝的读者警觉。”而当下的诗歌批评看起来很热闹,但是聚集于新媒体平台上的短评热评酷评并不是真正意义的批评,大体缺乏学理性和建设性,往往是没有底线的恶评或追捧,由此更要促进有意义有建设性的理论争鸣,端正批评风气。在推进诗歌批评进行争鸣这方面诗刊社下半月刊推出的栏目“锐评”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以正方和反方两个互补的差异性的声音对青年诗人创作进行批评研究,做到创作和批评的相互促进——“尖锐的真实到位的批评有助于诗人创作的提高”。《诗刊》对诗歌批评的重视程度是很多期刊做不到的,尤其是下半月刊结合“双子星”栏目设置了“同期声”,青年诗人和批评家在微信空间以对话的形式对每一期“双子星”推出的两个青年诗人的创作进行具有针对性的讨论与批评,力争做到直言不讳、实事求是、有的放矢、畅所欲言、大胆质疑、百家争鸣。2015年的诗歌批评除了持续关注诗歌的“草根写作”和底层经验、梳理诗歌的现实抒写以及新媒体对诗歌影响的热点话题之外,新诗研究成果的一大亮点是“当代新诗话”丛书(陈超《诗野游牧》、于坚《为世界文身》、赵毅衡《断无不可解之理》、耿占春《退藏于密》、沈奇《无核之云》)的推出,集中展示了诗歌批评和研究的新方法与可能性空间。
面对一年来的诗歌,我们仍然回到了文章的开头部分。诗歌的传播与生产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迅捷,而诗歌到底给普通受众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呢?这种影响到了何种程度呢?这种影响与雷蒙德·卡佛笔下所描画的诗歌“日常交流”是什么样的关系呢——“他在给她念里尔克,一个他崇拜的诗人的诗,她却枕着他的枕头睡着了。他喜欢大声朗诵,念得非常好——声音饱满自信,时而低沉忧郁,时而高昂激越。除了伸手去床头柜上取烟时停顿一下外,他的眼睛一刻也没有离开诗集。这个浑厚的声音把她送进了梦乡,那里有从围着城墙的城市驶出的大篷车和穿袍子的蓄须男子。她听了几分钟,就闭上眼睛睡着了。”(《学生的妻子》)我们必须注意到“大众”自媒体和公共媒体更多的时候所关注的不是诗歌自身的成色和艺术水准,即使关注也是侧重那些有热点和新闻点的诗,而更多是将之视为一场能引起人们争相目睹的社会事件。“媒体报道”对“诗歌现实”也构成一种虚构。时下微信等平台对诗人的“形象塑造”是值得进一步甄别与反思的。最终,人们谈论的诗歌的时候,很多情况下关注的并非诗歌本身,而往往是被缠绕和吸附于诗歌之上的“非诗歌”的东西所影响和遮蔽并进而妨害和扭曲了诗歌形象,也就是往往是在伦理学、道德感和社会学等“外围”层面谈论诗歌活动、诗歌现象和热点的诗人事件。“我们在谈论诗歌的时候到底在谈论什么”不只是当年雷蒙德·卡佛的不满,也是今天我们真正意义上的“读者”“诗人”和“批评家”的不满。
(作者单位: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