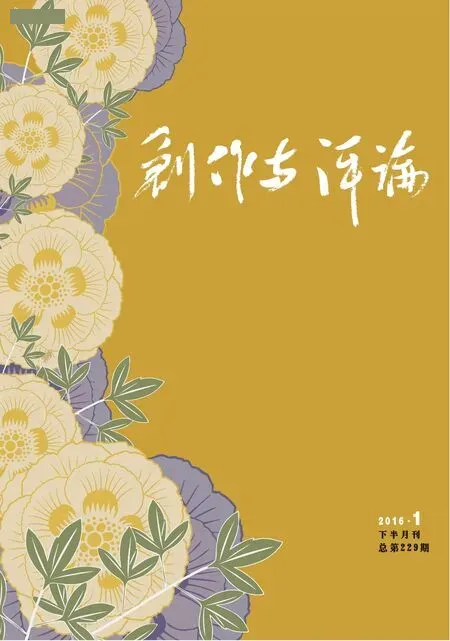2015年﹃80后﹄小说创作综论
○徐勇卞蕴雯
2015年﹃80后﹄小说创作综论
○徐勇卞蕴雯
一
对于“80后”作家而言,2015年是他们继续“高歌猛进”的一年。较之去年,今年有更多的刊物开辟专栏或专号来集中推介这股文坛的新势力,有意识地在他们与读者之间牵线搭桥。除《创作与评论》《西湖》等杂志继续推出“新锐”专栏外,《小说月报》在新年伊始的第1期增刊就推出“小说新声特集”,颜歌、孙频、文珍、马小淘、王威廉、池上、陈再见、寒郁、曹永、林森、余静如、何荣、陈崇正等多位在2014年有不俗表现的“80后”作家逐一亮相,成为重点推荐的对象。《中篇小说选刊》在今年第2期增刊随即推出“新锐小说家专号”,孙频、于一爽、李晁、文珍、颜歌、陈崇正、周李立、陈楸帆、王哲珠等人的优秀中篇小说被集中刊载,展现出不凡的写作实力。《收获》杂志更是一如既往地支持青年作家的写作,继去年两次开辟专栏(青年作家小辑)之后,今年第5期又一次开辟专栏,以鼓励青年作家的创作(其中有很多新面孔,绝大部分都是“80后”作家),同时又在两期长篇小说专号先后刊登了“80后”作家张怡微的《细民盛宴》和王若虚的《火锅杀》。
今年我们继续对《收获》《人民文学》《当代》《十月》《创作与评论》《西湖》《上海文学》《北京文学》《芒种》《钟山》《鸭绿江》《雨花》《长江文艺》《中国作家》《小说月报》《小说选刊》《中篇小说选刊》《萌芽》《文学港》《山花》《长江文艺选刊·好小说》《花城》《芙蓉》《江南》《作家》《天涯》《青年文学》《青年作家》《百花洲》《小说林》《小说界》等三十余种文学期刊进行统计整理,以此考察2015年文坛“80后”写作的大致走向。经统计,今年发表小说数量(包括去年发表,今年被刊物转载的篇目)排在前二十位的“80后”作家分别是:周李立(12)、甫跃辉(10)、于一爽(9)、孙频(9)、陈再见(9)、陈崇正(7)、小昌(7)、马金莲(6)、钱佳楠(6)、草白(5)、毕亮(5)、王威廉(5)、祁媛(5)、彭敏(5)、池上(5)、王哲珠(5)、大头马(5)、双雪涛(4)、文珍(4)、徐衎(4)、魏思孝(4)、寒郁(4)、叶临之(4)。此外,一些未进入榜单却得到刊物重点推荐的作家也值得关注,他们是手指、吴纯、王海雪、周嘉宁、向向、陈树泳、陆源等人。这些期刊之外,在那些青春文学辑刊,如郭敬明主编的《最小说》、笛安主编的《文艺风赏》、张悦然主编的《鲤》上也能看到一些“80后”作家的身影,其中,尤以科幻作家居多,陈楸帆、宝树等科幻作家均有专栏连载。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80后”作家已日益成为主流文坛的中坚力量,除不断有新人加入且人数甚众外,其他诸如甫跃辉、孙频、马金莲、王威廉、双雪涛、文珍等人,更是以稳健的步伐耕耘不辍,正日渐成长为“80后”写作的中流砥柱。
二
与去年相比,今年的“80后”写作整体上有更进一步的推进,除题材有继续的拓展、叙事技巧更为圆熟外,青年作家们的艺术个性亦日趋凸显,叙述上也更加讲究艺术的趣味及其氛围的营造。最显著的就是周李立的“艺术区”系列小说,今年她所发表的作品中近一半都是在讲述画家乔远的故事,关乎生存、压力、逃离、亲情、友情、爱情,乔远正经历着所有青年人都可能面临的人生困境:他可能在画完第五十幅画之后灵感枯竭,再也无法完成蒋爷所期待的“关键”第五十一幅,他渴望挣脱压力的枷锁,另存为一个崭新的生活片段,但这终将成为一场永远无法实现的旅行(《另存》);亲人的突然离世牵扯出一连串童年的创伤记忆,烧掉的十八子菩提手串彰显出都市文艺青年们微妙而略显随意的情感关系(《往返》);由借住所引发的心理危机,暗示着人总是勉为其难地在做一些不喜欢却又偏偏无法拒绝的事情(《冰释》《更迭》);面对失意的爱情和灰败的人生,只能以疯狂的偷树行为来掩饰,移栽的不只是一棵树,更是一种光明的期盼(《移栽》)。周李立通过艺术家乔远的际遇向我们展示了自己对于生活的“透视”——“其实人在很多事情上,都是没有选择的。”但所有的喜悦、痛苦也终将过去,宛如行车途中的一个个弯道,总会回到直路上的。这是一种崭新的尝试,却也成为一种局限。毕竟作者并不是绘画专业出身,在情感表达上总是隔了一层,乔远的艺术区画家身份显得可有可无,又或许这只是一种叙述策略,理性的表述背后是作者深刻的生命体察,只是以第三人称来表达更加稳妥些,是我也不是我,你们去猜吧!
毋庸置疑,如今的“80后”写作正越来越走向分化,媒体制造的印迹已愈来愈淡,地域差异、作家风格日益凸显,这是一种好现象,某种程度上标志着“80后”一代主体意识的凸显。文珍以北京为根据地的都市边缘书写,钱佳楠和张怡薇小说中上海弄堂的家长里短,甫跃辉笔端全球化大都市与僻远边地的“双重变奏”,毕亮和陈再见以深圳为背景的城市书写,以及马金莲小说里充满民族风情的“一抹晚霞”,都令时下的“80后”写作异彩纷呈。比如文珍,从她今年的三篇作品(《乌鸦》《觑红尘》《夜车》),不难看出作者的大胆尝试和不懈追求。《乌鸦》是个颇具魔幻色彩的小说,作者以一只乌鸦的视角讲述了一段悲伤的爱情故事,对比乌鸦先生对女孩的一片痴情,男孩的负心恰印证了鲁迅先生那句“首要是生活,爱情才有所附丽”。小说自如穿梭于浪漫与现实之间,通过视角的切换全方位记录着刚踏入社会的青年人们正在承受的巨大生存压力,逼仄的居住空间、遥远的上班路途、脆弱的情感维系已然成为他们这一代人的表征,全球化是机遇亦是挑战。因而文珍笔下的主人公们对远方总是怀有一种莫名的向往,他们或是出走别国他乡,寻求更好的发展(《觑红尘》),或是坐上一趟午夜的火车去到叫做加格达奇的远方(《夜车》),带着忏悔与期望,但这些地方终归不是可以停留的地方,他们也为此付出了代价,不但失去一段美好的姻缘,更加加速了预定死亡的降临。渺小的个体与宏大的时代激烈碰撞,在文珍的笔尖擦出细腻的情感火花,她准确地把握了“大”与“小”的尺度。
除此之外,双雪涛的《平原上的摩西》和常小琥的《收山》同样是今年值得关注的中篇佳作。作为备受瞩目的文坛新星,双雪涛近年来一直保持着喜人的创作态势,他的作品全无“80后”作家们惯常呈现的那种情绪过剩且叙述上不够节制的特点,而是坚持在“别人的故事”中述说时代、信念及历史,《平原上的摩西》就是一种全新的尝试。这个在侦探小说外壳包裹下颇具年代感的故事,拨开历史的重重迷雾走到我们面前,作者通过不断变更叙述视角,让小说中的关键人物自己发声,以此完成事件的来龙去脉,读者必须依靠自己的阅读经验和大胆的想象推理才能进入这个由各个故事拼凑完成的立体世界:这个世界中有幽暗的历史、美好的往昔、残酷的现实与不灭的信念。在略显漫长的时间跨度中,当代社会几十年的历史变迁毕然呈现,人物的命运却因一连串的意外事件而变得叵测难料,连环杀人案件的背后竟是一段单纯美好的暗恋往事,令人唏嘘的是李家父女阴差阳错的命运转折及随之而来苦难人生。平原上的摩西与其说是一个人,毋宁说是傅东心与李斐间一种信念的传承——“只要你心里的念是真的,只要你心里的念是诚的,高山大海都会给你让路,那些驱赶你的人,那些容不下你的人,都会受到惩罚。”这或许是同暴力与苦难和解的唯一方式。去年凭一曲《琴腔》广受业界好评的常小琥,今年带着他的全新中篇力作《收山》接连登上《上海文学》《小说选刊》《中篇小说选刊》三大主流期刊的舞台,足见其代表性。在“80后”作家中,常小琥算不上高产作家,但绝对是个值得期待的精品作家,其小说字里行间所浸润的文化继承感和厚重的历史感正是许多同龄作家所欠缺的,由此显得弥足珍贵。此外,李晁的《步履不停》同样值得品读,小说开放式的结尾令读者脑洞大开,读完深感意犹未尽,屋内越来越暗的灯光似乎早就预示了一场暴风雨的到来。
三
在我们欣喜地看到“80后”作家走向成熟的同时,亦必须正视其存在的问题。经验不足且想象力趋同仍旧是困扰他们的写作的主要问题。这使得他们整体上倾向于中短篇小说的创作,而不敢过多问津长篇,即使努力为之,诸如双雪涛的《聋哑时代》、张怡薇的《细民盛宴》、王若虚的《火锅杀》和杨则纬的《于是去旅行》,也仍旧还是在已有生活经验的基础上挖掘,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小说的气象和格局。这里尤以《于是去旅行》为代表。《于是去旅行》是杨则纬的第四部长篇。较之前几部,这部小说在叙述上虽显得更为悠如,但似乎并没有大的突破:仍旧是在男女两性的情感世界打转,仍旧是在成长的框架内展开故事情节。应该说,杨则纬及其小说在“80后”文学中是相当有症候性的,这一症候性表现在,生活在父母长辈之爱包裹中的青年主人公们,总是要在看似“无事”的日常生活中制造出“事件”和波澜来,他们的情感乃至情绪表达虽很真实,但总不免显得夸张而多变,因而也就往往停留在表面,并不能深入。她的小说,常常给人一种一览无余、了无遮拦的感觉,缺乏某种必要的(叙事上的)张力和(阅读上的)阻力。看来,情感表达上的缺乏节制和叙事上的随意漫漶仍旧是制约作者写作之路走得更远的主要障碍。
《细民盛宴》是张怡微的第三部长篇。这部小说延续了张怡薇以往擅写的世情小说风格,讲述了一个大家族里的少女袁佳乔在经历了父母离异、家族忽视、爱情破碎等一系列创伤往事后内心不为人知的隐秘伤痛,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为一部成长小说,但这显然与作者的初衷“家族盛宴”相违背,过于流露的情绪表达使小说不由自主地倾向于个人诉说,家族其他成员因此得不到充分延展,这也体现出作者在长篇掌控力上的局限。尽管视角有限,但聪明的张怡薇还是利用爷爷的病将形形色色的一大家子人凑到了一起,他们在麻将桌上说着无关痛痒的奉承话,私下却各怀鬼胎,觊觎着爷爷大自鸣钟的房子,上海人的精明世故跃然纸上。在一次次的饭局中,继父、继母、继母之子、公婆先后亮相,面对如此复杂而微妙的家族关系,袁佳乔以戒备的偏见抵御着人情冷暖的考验,顽强而固执地坚守着自己对于原生家庭的爱,但生父的冷漠一次次令她倍感失望,反而是继父及时弥补了部分空缺;为了与小茂的爱情,她忍受着公婆的轻视与挑剔。岁月过去,回首往事她蓦然发现,成长旅程中不期然的点滴才是生活最真实的本相,而时间让她理解并宽宥一切。
相比她的前两部长篇,这部小说虽显得更为成熟、老练而描摹入微,但仍不能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其题材、主题及其情绪的表达一仍其旧,延续的是她在家庭伦理层面的创伤情结及其内心情状的文学写作。对于张怡微而言,其症结与关键或许还在于如何挣脱或跳出已有的生活经验和内心世界的表象而后“向外转”。事实上,张怡微并非不能,而是不愿。在前一部小长篇《你所不知道的夜晚》中,张怡微把眼光转向上海的郊区田林,并尝试从时间上的纵深的背景以表现一个少女的成长。就这部小说而言,时空上的开阔带来的是新的气象和景象,如若沿着这一条道继续向前,定有新的斩获,但遗憾的是,张怡微并没有向着可能的新变迈进,而是向后,又回到了老路上来。对张怡微而言,她显示出来的是文学创作上的犹豫和一唱三叹。但这一部小说,还是显示出张怡微的努力来。这部小说把家庭伦理、人性的复杂置于一个家族的数十年的演变的过程中展现,不难看出张怡微的努力,这一家族小说的方向本可以使得小说显得厚重且凝重的,但因为作者有意把家族史从整个城市和社会变迁的背景剥离出来,其家族史的写作仍只能是家族成员人性之幽暗的展现,很难提供进一步的信息。
王若虚的《火锅杀》在题材上有一定的开拓,讲述的大学生校园内倒卖二手摩托车的故事。这是一批颇有经商头脑的校园商人,靠改装、倒卖二手车营生,普通学生都在拼命啃书、死记硬背应付考试的时候,他们在忙着做买卖挣钱,联系到如今校园里随处可见的物什摊位,你不得不说王若虚敏锐地扑捉到了21世纪正悄然变化着的校园生态,商品社会的利益化使得象牙塔也开始“朝野相通”,大学于这群人而言就是社会。这里的校园二手车倒卖团体,俨然社会上的“古惑仔”。步入校园的大一新生,要向大二的老生拜师,而后一步步做起,直至做到带头大哥的位置,层级之间等级森严。所不同的是,社会上的大哥是长期做下去,而这里的带头大哥到了大四,要找工作和实习,就会让位给大三的学生,以此类推。但这只是就理论而言,实际上,这里的权力更迭也和民间帮会一样充满“血腥”,团伙成员之间彼此勾心斗角,暗藏杀机。从这个角度看,这篇小说虽然写的是校园,其实是隐喻社会,至于里面的大学生形象也与我们通常理解中的大学生截然不同,他们的言行举止,行为处事完全就是社会上的成年人的派头,很难看出什么大学生的性格特征来。可见,题材在某种程度上只是一个虚设,一个噱头,但它通过时空上的错置,也能制造出某种戏剧效果来。应该说,这部小说,它最大的特色并不在题材,而在于它的结构及其起承转合上。它采用的回溯和前进并进的双线结构,两条线索之间的转换、联结,有点类似于电影镜头间的淡入、淡出,耦合得十分自然而了无痕迹,在在显示出了作者在结构上的用心经营和独有体会。
《聋哑时代》(连载于《鸭绿江》杂志,其中部分已于去年和去年之前公开发表过)是“80后”作家双雪涛继《翅鬼》之后的另一部(小)长篇。对于《聋哑时代》而言,其最明显的不同是它的结构。小说看似长篇,实则中篇小说的集锦。《序曲》之后,每一节皆以人名作为标题,一共有8节。小说的8个部分,分别讲述8个人的故事,但因为每个人的故事里都有第一人称主人公“我”的参与其中,因而被连缀成一个整体,它们彼此之间是一种互文性的关系。这是一种似断实连的串珠式的小说结构,其贯穿始终的线索(珠线)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时间和空间的转换,而是第一人称主人公“我”。这一结构特点,决定了小说虽然讲述的是与“我”有关的8个人的故事,但其实着重点在核心主人公“我”身上。换言之,这是以8个人的故事作为背景或铺垫来讲述“我”的故事。
就社会学的角度看,小说自有其思想史的认识价值(中学生成长主题的独特表现),但就“文学性”而言,小说的耐人寻味之处却在于叙述者与其所叙内容间的反讽的距离、叙述者对这一距离的把握及其独特的叙述语调上。这与小说中第一人称“我”的塑造有关。“我”是以叙述者兼小说主人公的身份介入到故事的讲述当中,因而某种程度上,对“我”的形象的塑造就决定了小说的整体叙述风格。虽然从小说中可以明显感觉出叙述者(甚至作者)对其主人公们的深深的忧虑、批判和反省之倾向,但作者却无意把“我”塑造成一个具有先知意识或弃绝于烟尘气之外的冷静的主体。他对自己(作为第一人称主人公“我”)是既不愿又不甘,因而总是无聊着,而对他的同学们,则是既认同又质疑,既批判又羡慕;可以说,他对小说的主人公们的态度,就像对自己的态度一样,摇摆不定犹豫不决。这使得小说在整体上充满一种反讽的精神气质和不彻底的风格。其中既有对现行教育制度的反思,但随之而来的又是对自己无力考上好的大学的无奈的感叹;有对自己和他人的调侃戏谑,但这背后又有对某种东西的近于固执的认真;有对世事洞察或感同身受的会心一笑,但又无积极进取或钻营的热情。正是这样一种无奈和情感与理性上的进退失据,构成了双雪涛小说的最为坚硬的内核,也最终把主人公“我”塑造成这样一个左右摇摆的复杂形象。他的小说中大量使用第一人称叙述,虽然很难说是作者“我”的意志(或意识)的表征,但其实表现出作者强烈的主体意识。这在“80后”作家中实属难得,其作品的独特之处也正在于此。
四
2015年的文坛,孙频、甫跃辉、于一爽等多位“80后”作家的表现十分抢眼,作品数量相当可观、个人风格特征比较明显。相对于通过“新概念作文”出来的“80后”作家们,他们的小说呈现出一种与众不同的质感。其中,孙频尤以中篇小说见长,独特的底层经验书写与扎实的写作功底令其作品质朴而深蕴,坚硬且沉着,显示出少有的成熟和老辣,即使置身于“70后”,甚至“60后”作家们的作品中,也毫不逊色。熟悉孙频的人都知道,笔锋犀利而冷静是她最为鲜明的特点之一,正是基于对现实残酷、尊严可贵的清晰体认,她笔下的人物才一次次被损害被侮辱:童年的创伤与暗疾使张子屏害怕独自面对彻骨的孤独,李觉越是侮辱她践踏她,她却愈发爱他,她爱这种侮辱,只因为这也是一种变种的审判,似乎只有这种真切的痛和抚摸才能让她感觉自己还活在世上,与这个世界有所联系(《抚摸》);单身女博士张月如在与院长李文涛发生一夜情后,对于后者对自己的不闻不问倍感受伤,为了证明自己的尊严与魅力,先后与酒吧小老板周小华、入室抢劫的水电工发生关系,终于亲手将尊严毁掉,一步步把自己逼到绝路(《丑闻》);推销员许峰本想利用老女人宋怀秀对女儿的爱趁机向她兜售保健品,怎料却被这对母女相中,宋怀秀以房子为条件诱使许峰娶自己的智障胖女儿,为了生存,许峰竟鬼使神差答应了这个要求(《圣婴》);1997年的下岗大潮和随之而来的暴力拆迁令张利生一家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面对邻居的蓄意栽赃,为证清白的张妻武兰用刀刺死了自己,张利生也意外进了监狱,这间接导致他们的女儿张荣荣不堪受辱而跳楼自杀(《我们的盐》)。仔细阅读,不难发现孙频很喜欢以狗来喻人,张利生“用一种狗一样的目光更用力更可怜地瞅着他们,怕他们真的就抛下他走了”;每当张子屏“看到自己落在地上一摇一摆的影子,她便觉得自己像条狗”;杨红蓉的房东从不喊她名字,只喊她租房的“像是在她脖子里挂了只狗牌,大黄,二黑,哪只狗都可以这么叫,她在这些有房的人眼里连个名字都不配有。”狗的倔强而卑微,某种程度上恰是孙频对小人物所做的精神写照。尊严对于这些人来说实在是奢侈且近于妄想,但他们却固执地持守着,正是这种矛盾心理,使得他们显示出某种不可化约的坚硬和力度来,这就是孙频的力量!
作为从“彩云之南”的边地来到国际化的大都市上海的青年作家,甫跃辉深知,没有广大农村作为他的创作的后花园,这样的文学之路并不能走远。以乡土为背景的小说在他的作品中一直占有很大比重。记忆中的乡村总是有一些亘古不变的永恒存在,是老一辈人世代坚守的松林,是山里的孩子险象环生的艰难上学路,是慈祥老奶奶园子中的月季,是河岸边永远矗立的坟。但这看似平静的乡村实则早已暗流涌动,金钱对人的异化正悄然上演,《乱雪》中的儿子因嫌家里穷而选择入赘,其母得知后一时无法接受,不久便得病死去。余国安“无论如何不能相信,无论儿子还是女儿,都只想要那片松林,没人想要他和妻子。”终于他擎起铁锹,照着儿子的脑袋拍了下去,结尾略为现代的处理方式与余国安崩溃的精神互为印证。《看黄河》结尾模糊的时间处理几乎让人以为整个故事只不过是主人公的一场春秋大梦,但那种对于河对岸的向往却是真切扎根在人们心中的,黄河南岸在某种意义上象征一种全新的生活,可以是县城、城市,是城镇化进程的某种表征,人们愿意出走、告别和追寻,并为此付出任何代价,彼岸有什么谁也不知道,也可能什么也没有。相对于《乱雪》与《看黄河》中对于苦难略显沉重的描写,《星垂》则因其充满童趣的少年视角而显得轻松许多,尽管山区的孩子上学依旧艰险,但这一切似乎都被孩子的天真快乐所消解,甫跃辉将两兄弟面对黑暗竹林、死人传说、断崖危险时的害怕与恐惧写得入木三分,又将孩子生气勃勃、对一切充满好奇的天性表现地淋漓尽致,竹林的大火在他们眼中就是“黑夜黑色的衣服被一块块卷下来扯下来撕下来,烧着了!”火焰迎着天上的流星实在是太美了,面对大自然,他们懵懂的心灵第一次产生了一种渺小感。
于一爽作为今年众多刊物的重点推荐对象,以率性的语言、真实而不矫饰的情感表达成为“80后”作家中独树一帜的一个。有评论家称其“爽利,如天上的云,淡然多姿,独有韵味”,她对爱情、生活和性都有着自己一套独特的理解,往往在偏个人化的叙事风格中倾向对人物意识流动展开细致描摹,毫无章法的自由叙说有时显得过于随意,难以把握,但又毫无例外地给人带去一种新鲜感,《云像没有犄角和尾巴瘸了腿的长颈鹿》的书名就颇为有趣。云淡风轻的戏谑态度、基于个体经验的陌生化修辞表达,诸如“很多问题塞进她狭小的锁骨里,让她根本没时间介意矫揉造作”“方糖融化在咖啡里就像一场雪崩”等都显示出其别样的语言美感。在对日常生活流的“如实”记录中,她真正关心的是人们内心深处无法言说的暗疾与伤痛,这种个性化的经验书写几乎成为辨认于一爽的重要标识,亦是她十分可贵的探索。
(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