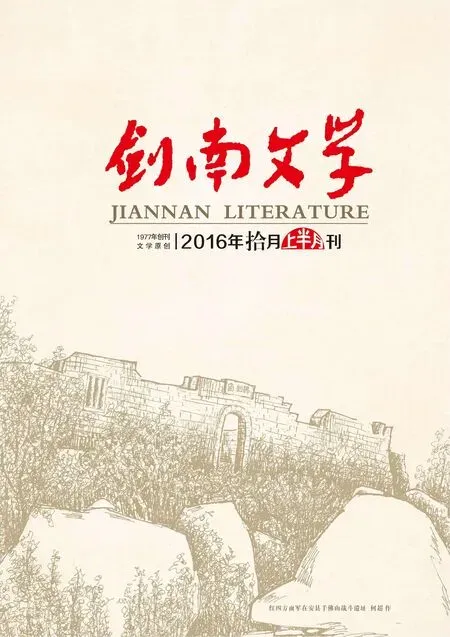门
□言 子
门
□言 子
第一扇
屋里无人,一把将军不下马铜锁,静悄悄挂在两扇门腰。
檐坎边沿的一溜檐脚石砌得整整齐齐,凿子的痕迹若隐若现;屋檐下的一排垫脚石,乌青、细腻、铮亮,屋檐水落在上面,如时钟走动,滴出了时间的印迹。进林家,先要从稻田边的一条黄泥路爬石梯、过敞坝、上檐坎、跨门槛,这是林家的大门,双扇扇开,我外婆我母亲以及我,在这里进进出出,那是从前的事。大瓦房坐北朝南,这扇双开门偏东,林家的这间大屋子,名耳房,像一只耳朵贴在青瓦房的右面。陶屋(堂屋)在这座房子的中间,两扇木门朝南,太阳天,人在陶屋,也可看见时光流逝——阳光慢悠悠向西而去,房顶阴了,檐坎阴了,敞坝阴了,竹林阴了,稻田阴了,山坡阴了。夏日时光,林家人的日子跟随太阳转动;冬日时光,灰云笼罩,太阳稀少,目睹光阴一寸寸流逝的日子不多,阴晦里,时光并未停滞,夜长昼短,三餐饭减成两餐,天亮天黑,我外公外婆舅舅舅母在看得见看不见的时光里消失得无影无踪。两兄弟之间,我外公是这座大瓦房的掌门人,一家老少的温饱靠他在外奔波获取。1950年,两兄弟分家,陶屋那边的屋子,归外公的兄弟——我叫二家公的那个高高大大、咳嗽气喘的鳏夫;陶屋这边的,归外公。从此,两家人各过各的日子,只在过年过节寿宴婚庆来往走动。
门槛粗朴,一尺来高。儿时,我们把门槛当板凳,骑在门槛上。近处是竹林,远处是山坡,再远处,黑苍苍的七星岩绵延天边。外婆看见我们骑门槛,又骂又赶,待她转身离去,我们又把屁股放在门槛上。外婆说门槛不是拿来坐的,她有她的讲究。我们顺便在门槛上歇息,外婆看见,都歇得差不多了,她从早到晚忙个不停,哪有功夫时时盯着。外婆不知道我会写她,会用文学记录林家这座已经消逝了的板壁瓦房。她离世那年,我还是个学生,舅舅舅母也未衰老,能吃能做,他们已经不在人世!我的表哥表弟表姐表妹也如我一样,被时光催老!外婆一生一世从这扇门进进出出,三十四年前的一天,她出了这扇门,再也没有回来。
出了这扇门未回来的,还有我的外公幺舅
舅舅舅母七表妹。
第一个未归的是外公,其次是幺舅,表妹林七,他们因病夭折,后来是外婆,舅舅,舅母。舅舅脑溢血,舅母胃癌。
站立檐坎下,目光穿过开启的两扇木门,看得见耳房中央的四方桌,四条高脚长凳,这些日常用品未上漆,被时光抹上一层包浆。板壁上方,一扇小木窗向西开启,大人的头够到窗口,看得见天空山坡,看得见大路上赶场的人。窗口下边,一条黄土路,蜿蜒通向对面的大路,槽坊这边和七星岩方向的人去赵场,要走这条路,窗口隔路高远,人在窗口,听得见过路人的脚步声,看不见人影,垫高的墙壁青石头垒砌,人在路上,擦着高高的石壁走动。儿时,我多次踮起脚尖,也看不见窗子外面的风景,借助凳子看过。窗子转角处,挨南墙,放了另一张方桌,放了洗脸架,放了甑架子。日日午饭,这壁木板墙烟雾氤氲,甑盖揭开,大米饭的香味随蒸汽弥漫。夜晚,耳房的角落会增加几件东西,椅子背篼箩篼锄头,外婆早上起来,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把这些东西拿出去,耳房又恢复了它的整洁、敞亮。
人影在耳房穿梭、晃动,那些我从前见过的或近或远的故人,他们从旧时光走来,让时光重现。
为外婆祝寿的客人。
记忆里,外婆每年都要做生,远远近近的亲戚赶来,有的住上一夜两夜,各自散去。过夜的都是住得远的,当天赶不回去;外婆留下的亲人,不易见面,住上两夜说说家常话。外婆德高望重,又是农闲,亲戚们年年跑来祝寿。粮食不宽裕的日子,外婆的生日酒是传统的九大碗,土地下户,有了余粮,外婆的寿宴讲究起来,饭前要吃茶。吃茶,也就是开饭前喝茶吃糕点吃粑粑。糕点是炒米糖,外婆亲手做的,红的白的都有,八九道工序,全靠一双手。外公在世,一家人的日子不算差,做炒米糖的一套工具,外婆保存着,没想到在她高龄后还能派上用场,还能把她的手艺传给母亲舅母表姐,炒阴米炒红苕丝的铁砂子,外婆也保存着,与炒米糖工具一起放在阁楼上,灰尘满面。黄粑也是自己做,蒸熟后煎成两面黄,同炒米糖一样,装进一只陶瓷盘,四只盘子摆上桌,白的白,黄的黄,红的红,诱人。耳房三桌摆不下,敞坝要摆两三桌,二家公家里的桌子板凳搬出来。年长的坐耳房,年轻的坐敞坝。舅舅老表陪客人喝酒,外婆舅母表姐在厨房忙碌,大家下桌子,她们才上桌。表姐负责添饭,拿把木勺屋里屋外到处转,看见谁碗里的饭不多了,便从侧面囥一勺饭进碗。有人推迟着说吃饱了,表姐不管,一边喊人家多吃点,一边将勺子里的饭囥进人家的饭碗。待客的热情和实诚,都表现在劝饭上。敞坝吃饭的,大多是带着孩子的妇人,不喝酒,比耳房的人下桌早,收拾完毕,大家坐在敞坝喝茶闲聊,我们这些小孩,便进竹林乱跑,跑够了,回到敞坝跳房。天色暗淡,耳房几个嗜酒的男人还不想下桌。
外婆走出这扇门,舅母表姐母亲接着做炒米糖,未学到家的缘故?还是我的口味发生了变化?再也吃不出从前的味道!
幺舅走出这扇门,我太小,二十多岁,肺上有毛病,多年医治无效。生产队分的口粮不多,家家户户艰难度日。门里的事情已模糊,门外的一些事还记得。外婆没想到幺舅会病逝,或是想到了,不愿意面对。母亲同大家一起奔走、忙碌,我在敞坝看两个木匠为幺舅打棺材,白煞煞的木头,刨花堆了一地,怎么出门怎么上山怎么下地的,已经走出记忆。那段时光对于年幼的我,几乎是空白,只留下模糊影像。外婆弥留之际,我在柏溪县二中上高中,县城的二爷爹来学校通知我,请假回去,外婆已经被家人从床上抬进耳房,衰竭瘦弱的外婆躺在地上——一张门板上——一双三寸金莲的小脚对着耳房的大门,气若游丝。我进门,俯下身唤她,唤她,气息奄奄的外婆毫无反应。外婆爱我痛我,她一定听到了
我的呼唤,她,已经没有力量睁开眼睛。她的生命在1981年的深秋,如一片落叶一样,凋谢、衰竭。七十三年的岁月,她,历经磨难,看尽人间沧桑,坚韧乐观地活着,像一片秋叶一样归入泥土。
后来是舅舅舅母,一个在九十年代,一个在2000年,他们走出这扇大门,我在异乡,没有回去为他们送行。
我们一生都在寻找一扇门,一生都在为一扇门奔波、劳累,最终,都将走出我们辛苦营建的门。
这扇门,既是人生的第一扇门,也是人生的最后一扇门。
生命的第一扇门,不是我们进进出出的大门,而是母亲的子宫,从封闭、温暖中落地,我们漂泊、挣扎、寻找、奋斗,富贵也好,清贫也好,功名利禄,最终,回归泥土。
林家耳房的这扇门,被时光关闭,门上悬挂的将军不下马,发出绿幽幽的青光,铜质钥匙,如一把耳勺,与廋长的铜锁一样漂亮,有质感。
第二扇
第二扇门只有门槛。
以前有门,舅舅把门卸了。
门槛内一截通道通向灶房、猪圈、连接左右房间,舅舅舅母老表的房间在通道的两边。
通道窄,无任何杂物。
第三扇
这扇门在通道的左边,舅舅舅母的房间,一间亮堂的屋子,板壁上的小木窗一年四季开启,我常站在墙下的一块地脚石上,踮起脚尖,双手抓牢窗沿,看外面的风景。外面的风景,随春夏秋冬而变化。春天,坡上是绿油油的麦苗油菜;夏天,是青幽幽的苞谷花生;秋天,是苍绿的红苕叶;冬天,翠嫩的麦秧又盖满山坡。半坡的梯田,稻子未收割,已成旱田,栽秧季节,一场大雨让久旱的梯田注满水,雨中犁过耙过,栽上秧苗,返青后,层层翠绿,向着山坡抬升;秋天,翠绿转青黄,再转金黄,随山坡层层抬升。坡脚的冲田,一年四季不缺水,浅梯状,从两坡间的坳绵延下来,迂回曲折到我们望不见的地方;夏天,山山弯弯的秧田丰茂;秋天,山山弯弯的稻田金黄。山山弯弯,绵延起伏到七星岩脚,到金沙江长江沿岸;谷粒归仓,山山弯弯的冲田一汪清亮的水,如大地的眼睛仰望天空,蓝天白云房舍竹林映入清亮的瞳仁,行人的身影也映入清亮的瞳仁。一块月牙形的冬水田,就是大地的一只眼睛,只只眼睛明亮清澈。没有舅舅这样热爱耕耘的人,站在窗口,我看不见田野风景。
床挨窗口摆放,隔着一张条桌。
架子床,纱布蚊帐。
舅母在这张床上生育了九个儿女,四个夭折。
条桌上,放过一本书——《春潮急》,作者克非。老表从什么地方弄来的,不清楚。出完工,老表躲进舅舅的房间,坐在窗下阅读。封面上简单的三个字我认识,书页内密密麻麻的文字大多不认识,无兴趣细看。老表读完,条桌上,不再出现书籍。老表这一生,也许只读过这本小说。这是我看到的第一本小说,想不到多年后,我会见到本书的作者,他居住在我工作的城市——涪江边的青义小镇,省专业作家。作为文学青年,我在一些会议上听过他讲话,去那座田野的小院拜访过他。我没有告诉他,我见到的第一本小说是《春潮急》,没有告诉他,70年代的乡村,有一个农村青年,夜晚在煤油灯下读他的小说。我也没有告诉老表,我见到了《春潮急》的作者,他居住在我工作的城市,在涪江边写作,四周是田野。不是不想说,短暂的见面,让我将这些埋藏在心底的记忆忘却,当时光在我笨拙的文字重现,当林家的第三扇门出现在我的记忆,当门内
的一切景象跟随文字再一次浮现脑海,我看到条桌上的那本小说,再一次想起了这些。已经是爷爷的老表,安了假牙的老表,脸色黑茬茬的老表,是否记得他在青年读过的那本书?那本不知他从何方找来,又归于何处的书!下次回家,如果他已经退出打工潮,同他说说《春潮急》,说说我见过的这本书的作者克非先生。
青年老表,不但看小说,还吹过笛子。
对于童年的我来说,老表吹奏出来的笛音还算悠扬,与读小说一样,老表的吹奏没有坚持下去,那节竹笛,不知去向。
一扇窗口,让舅舅的房间亮堂,我们这些不醒世的孩子喜欢进去玩耍。白天,舅舅舅母很少进屋,夜晚,忙完活他们才进屋睡觉。不但亮堂,踮起脚尖,可以眺望我前面描写的那些风景,可以看到离窗口不远的楠竹梢,可以看到窗下年年长高的一排桉树梢,可以听到赶赵场的人从窗下走过的脚步声话语声,这些,犹如节节春笋,犹如叶叶春芽,慢慢地,在我的小小心灵发枝吐叶,时光里,成为一棵古老的树,一棵我的生命里拥有的古树。
树叶凋谢,便是时光流失。
我的外婆,像一张风中的树叶,离凋谢的日子不远了。
外婆在为凋谢的日子作准备,将寿衣寿材早早准备好,以防不测。历经岁月磨难的外婆,深知生命的脆弱,也深知生命的不测,随着年龄的增长,她知道,自己随时都可能与家人分离,她为自己的凋谢做好了准备,一口黑黝黝的寿材,放进舅舅的屋子,前后用两根高脚长板凳支撑,占据着大半堵南墙。我不敢像先前那样自由进出了,外婆舅舅舅母无视寿材的存在,那口又大又长的黑漆漆的东西,对他们进出屋子无任何障碍,我看到它,就像看到了死亡,尽量避开。避不开,去外婆房间,去灶房茅私(茅厕)都要经过这间屋子,大白天,这扇木门都是开启的,重不上锁,进进出出,经过这扇门,有意无意,都会瞥见那口让我感到沉重与死亡有关的东西。那东西不是空的,外婆装了谷子进去,我从门口经过,有几次,瞥见外婆在舀谷子。装外婆的寿材,外婆先用它装了食粮。那口黑漆漆的东西,对于外婆,好像与死亡无关,倒是与生命不可分割。外婆凋谢后,躺进去,不是一个没有气息的老人,仿佛是无数的谷粒归仓。
是归仓的食粮。
这间生育过一代人九个儿女的房间,后来成为老表的新房,舅舅舅母让出来,搬进对门的屋子,老表在这间不算宽敞的房间里,生育着又一代人。
这间两代人生育过的房间,装过谷粒,与凋谢有关的房间,外婆走出林家,不再有粮食进来。
第四扇
这扇门在第三扇门的对面。
跨出第三扇门,一步可以跨进第四扇门。
门内除了一张床,几乎没有什么摆设,以前,这间屋子是老表和表兄的睡房,老表结婚,与舅舅舅母对换房间,搬进了第三扇门,表兄住进了耳房的阁楼。林家的这座大瓦房,唯有这间是土墙,与整座房子不协调,布局也不协调,突然从外婆的睡房和二家公的堂屋伸出来,像是树干上长出一个肿瘤。眼睛将这间屋子避开,林家的这座瓦房,是一座三合院,分家后,耳房成为外婆家的堂屋,请客吃饭、一日三餐,都在这间屋子进行。土墙屋子,分家后修的,利用敞坝的空间,利用现成的两面墙,立了起来。倒是简单,只需在北面在东面增加两堵墙,上梁盖瓦,便是一间屋子。这间不搭调的屋子,林家经济不景气时修的,三代人,不够住,多立一间栖身,不在乎是板壁还是土墙。南墙上的窗子,无门,几根木窗棂镶嵌进土墙。站立窗口,从窗棂缝隙处,望得见敞坝边的皂角枇杷梨子柑子竹林,竹
林在敞坝下边,连接田野,慈竹林,由近至远,是李子坡寨子山老糖房多耳田七星岩。竹林边的冲田,迂回盘旋、曲折起伏、随丘陵随山弯四处延伸。不知舅舅舅母站立窗口眺望过外面的风景没有?他们一生劳累,勤勤恳恳耕耘,田地是他们的生命。这些风景对于日日在土地上劳作的人,不稀奇,是他们,创造了一年四季的田野风光。没有舅舅舅母田间地头的劳作,冬天不会有清亮亮的水田,春天不会有绿茵茵的麦地,夏天也不会出现清幽的秧田,秋天也看不到黄灿灿的稻谷。是他们,创造了这片土地,耕耘了这片土地,美丽了这片土地。这片不算肥沃的土地,坡坡坎坎,曲里拐弯的土地,在他们的耕耘下,风光如画,四季牧歌。他们离去,不再有人在这片土地勤劳耕耘,田地里,长的不是庄稼,是野草,是花木;不再有清亮亮的冬水田。一生在土里劳作的舅舅舅母,随着他们生命的消逝,精耕细作的农耕消逝,四季的田野风光消逝。他们,将这片土地上的风景,带走!
舅母是个文盲,嫁到林家,生儿育女,家里家外的忙碌,从不停歇。她和外婆和母亲的关系,谈不上好坏,舅母不是那种能说会道的人,低头做人,低头干活。记忆里,没看见她和外婆和母亲发生过口角,也没看见她和舅舅发生过口角,三代人住在一个屋檐下,一口锅里吃饭,大家相安无事。最后见舅母的那个夏天,我回老家与母亲去看她,她躺在床上,熬着,明知是胃癌,不去住院不动手术,躺在床上,像一盏灯一样熬尽最后一滴油。回单位不久,接到老表的电话,说舅母已经上山了!她是不是在这间屋子,熬尽了生命的最后一滴油?还是像外婆一样,弥留之际,家人把她抬进耳房,躺在一张门板上,咽下最后一口气?
相对于舅母的煎熬,舅舅的离去比较轻松,无任何病痛,倒下时,他还在坡上的一块红苕地扯草。倒进旷野,把生命还给了田地。
这间屋子,舅舅不再进来,舅母独自进进出出。
几年后,舅母也不再这间屋子进出,让她煎熬的病床,空空荡荡。
舅舅一生嗜好烟酒,抽自己种的叶子烟,喝散装高粱酒。好客,喜交朋友。农闲,赶场天,有时看见舅舅带个陌生人回来吃饭喝酒,怎么认识的,我们不得而知。舅舅经常干这种事,他结交的人,都是赵场的过客,以雕虫小技在赵场混碗饭,混不下去,一走了之。老朋友走了,舅舅又结交新朋友,赶场天,又带着新朋友回来吃饭喝酒,两个人在酒桌上坐到天黑。这些修理钟表卖草药的过客离开赵场,不会再出现,我无法推测舅舅的内心,是否失落?
舅舅还有一个嗜好,读古书,线状的发黄的竖排古书,我见过的有《曾广贤文》,舅舅黄昏坐在敞坝读,有时听见他念出声来,一句也不明白。
第五扇
这扇门与第四扇成直角。
站在第四扇门,转身就能跨进第五扇门,我外婆的房间。
挨门,一把黑漆漆的太师椅如摆设,无人坐,外婆也从来不坐。椅子上,有时放一把铜壶,一钵土陶,一只针线竹篮,更多的时候空空荡荡,安静坐落于暗淡光线下。四表姐长大,椅子上方的板壁上,挂了个四四方方的相框,四表姐下城进照相馆照的照片,全部放进了相框,黑白,一寸两寸三寸的密密麻麻挤着。相框里的四表姐笑盈盈,满月似的脸,两根黑幽幽的辫子搭在胸前,碎花布衣是夏天照的,圆领毛衣是秋天照的,小格子呢子短衣是冬天照的。生活中的四表姐,也是笑盈盈的,难得看到她愁眉苦脸。林家的人,我母亲是最爱照相的,其次是四表姐,清早启程走三十里路下城,不为别的,只为进照相馆照一张相,那是青春期最大的乐趣。我母
亲,出嫁后与娘家隔得近,已经不算林家人,这座房子的人,四表姐是唯一一个下城照相,拥有相框的人。表哥表兄表妹们没有进过照相馆,更不会有自己的相框。四表姐在这座房子与众不同。椅子上无物,四表姐放了新照片进去,我就站在椅子上看,四表姐在我下边,眉开眼笑。长宽不足一尺的相框,里面陈列的,是四表姐的青春,简单而快乐,辛苦而勤劳,进城照相买相框的费用,是四表姐种菜卖菜积存的,舅舅没有闲钱拿给四表姐乱花,也不反对四表姐把自己劳动所得的钱花在自己身上。
椅子与床之间,摆放着一张黑漆漆的条桌,一盏煤油灯,放在靠床的条桌上,日日夜夜照耀着外婆上床起床。一张大木床,一年四季罩着蚊帐,与椅子条桌一样上了黑漆。这堵摆满物件的墙壁,从前面向敞坝,有了第四扇门,有了一间土墙屋子。外婆这间与整个林家堂屋相连的屋子曲折幽深,通向屋子的这扇门,以前面向敞坝,现在隔着一间屋子。结构上,这间挨着堂屋的房间仅次于耳房,长方形,应该是林家的第一扇门,有了土墙屋子,第一扇门退居为第五扇。如果不是临时多一间屋子出来,这扇面向敞坝竹林的门,可能也不会常常开启,毕竟不同于别的屋子,这间屋子是林家的主卧,我的表姐表妹都在这间屋子睡觉,外人不会轻易踏入,除非主人邀请。主卧隔壁,是二家公一家,从前一大家子共有的陶屋,现在属于二家公。这座三合院,大进深格局,进第一扇门,曲径通幽,最后一扇门到达后坡。这间主卧,进深到山墙,比别的屋子宽大,靠近山墙,屋顶低矮,成人站立墙边,头几乎挨着屋顶。屋子半空,梁柱之间,搭了楼板,楼板下一架梯子。阁楼是外婆的领地,家里人难得上去,外婆在梯子上爬上爬下,我跟着爬上爬下,外婆从来不禁止。楼板上的物件简单,放些不常用的贵重的,两口木箱子,放着外婆换季的衣裤,种菜卖菜积存的钱也放进箱子,缝制的寿衣寿鞋也放进箱底,几个银元也压进箱底,这些,外婆临终前告诉了舅舅。空中这方不算宽敞的阁楼,是外婆的隐秘之地,一个女人的私人空间。没有多大秘密,梯子成年累月搭在板楼上,谁都可以上去,谁都不想无故上去,舅舅舅母老表表兄很少进这间屋。
房间无窗,屋顶的亮瓦落满竹叶,阳光灿烂的日子,整间屋子从早到晚朦朦胧胧。
朦胧光线下,不知遮蔽了多少苦难和艰辛。
年幼时,把外婆家当着自己家,觉得一切都比我们家好,饭菜比我们家好吃,床比我们家睡着舒服,人也比我们家多,天黑不想回家,喜欢和外婆一起睡觉,第二天外婆见到母亲,说我睡觉不老实得很,蹬得她青痛!外婆瘦弱的身子,怎么经得起我整个晚上的跌打?我一夜无梦,一觉睡到天亮,不知道自己在夜里乱蹬乱跌,再和外婆睡觉,她依然乐意,早上醒来,问外婆:家婆,昨晚上我睡觉没乱蹬乱跌吧?外婆说:咋个没有?一夜都在乱跌乱蹬,长个子呢!
我长个子,外婆在一天天枯竭,矮小的身子似乎越来越矮小,尖尖脚走起路来似乎也不如以前稳当了,闲不住,天不亮起床,家里家外的忙碌。一个劳累了一辈子的人,要她突然停下来休息,过不惯的。外婆十几岁进了林家就开始劳累,哪能停下来不做事情。我妈说外婆是童养媳,进林家也就十一二岁,长大了同外公圆房,生儿育女,没分家时,林家两兄弟,一大家子过日子,拖儿带女的,外公三天两日的在外面奔波,作为一个主妇,管着十几口人的温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家里家外的风风雨雨,外婆哪件没有经历过!外公病死那一年,粮食关,一家人都在饿肚子,林二林三先后夭折,过了几年,林五夭折,林七长到十五岁,癫痫病发作,在我家解溲摔进茅坑淹死,孙儿孙女一个个离去,幺舅舅也不让外婆省心,成了病秧子,四处医治,还是没有把他留住,年少的老表病重,床上躺了两年捡回一条命。我看不见外婆的伤痛和焦虑,这间朦胧的屋子,将外婆的心事遮蔽,也许夜深人
静,睡眠不好的外婆,才将心事一件一件掏出来,独自在黑夜咀嚼、叹息。
四表姐出嫁,外婆还住在这间屋子,床上的一套绣花嫁妆,是外婆带着四表姐一起准备的。六表妹出嫁,外婆不能给她准备嫁妆了,这个年少得肺病的人,外婆多年体恤她,不让她做任何重活,身体养好,到了出嫁年龄,外婆不能目睹。老九出嫁,这间屋子空了,挨墙壁摆放的三张床铺也空了,八老表搬进这间屋子,成了他的新房。
外婆离开这间屋子,我很少进来,八老表住进来,我不再跨进这扇门,房间里的格局,有可能和以前大不同了,八老表的儿子伟倌,在这间屋子出生,林家的第四代。
这间抵达山墙的房间,后半截房顶,被楠竹林掩映,刮风下雨,瓦顶上,摇曳着风声雨声。
白天,光亮最后落进来,最先溜出去,幽幽时光里,看似沉寂,实质风风雨雨。
第六扇
这扇门与通道,与通往耳房和茅私的门成直线。靠在门枋,前面是黑洞洞的茅私,后面是狭窄的通道和耳房,视线向左移动,一方土石结构的灶头,结结实实,台子一样。台面上,放了两口大铁锅,一口烧柴,一口烧炭,人食猪食都在这两口锅里煮。柴火不够要上七星岩找,煤炭也要上七星岩挑。麦秸苞谷稻草所有能燃烧的植物,对于这片贫瘠土地上的居住者,都是珍贵的柴火,一根茅草都无浪费。柴灶铁锅边,靠近灶门,放了一口鼎锅。一口黑乌乌的铁鼎锅,被岁月的烟火熏得满锅烟尘,穗子一样的烟灰,比煤炭还黑。一年四季烟熏火燎,锅外污垢,锅内洁净。这是林家的老古董,与外婆房间的太师椅一样陈旧,别的人家,房子虽老,也不见这种锅。什么都缺的贫瘠土地,这口鼎锅,很实用,一顿饭还未煮熟,锅里的水滚开,可以泡茶洗脸洗手洗碗。饭前,外婆常常舀锅里的水给客人洗脸。我羡慕灶台上有这口鼎锅,灶里有火,就有热水开水,节省柴火,节省时间,日日少做一件烧水的事。
一日三餐,外婆舅母四表姐轮流上灶台,坐近灶门烧火的,也不确定,煮饭的人都烧过。天蒙蒙亮,外婆起床进灶房煮饭,春夏秋冬不变,多年养成的习惯。四表姐长到十三四岁,帮着外婆一起煮,再大点,一家人的饭菜都交给四表姐,请客摆酒席,过年过节,家里的三个女人都在灶房转,难得进灶房的表哥也不得空,帮着择菜洗菜。
勤劳俭朴,也体现在灶房。煮完饭,灶门下永远是干干净净,无杂乱柴草。烧火板凳后面的柴火,小把小把绾紧堆积地上。石灰灶面无尘埃,空寂的铁锅洗刷得干干净净,被烟火熏黄的木质锅盖上,放着锅铲刷把水瓢。吃豆花豆腐的日子,鼎锅周边,一圈豆渣包由白到黄,由软到硬,残渣应该喂猪喂鸡,舅母舍不得,放少许盐,每次将粗糙的豆渣捏成球放在鼎锅周边借灶火慢慢烤黄烤硬,没有人喜欢这种满口钻的食物,舅母外婆四表姐肯定也不喜欢,她们舍不得扔,顿顿拿一坨下饭,当粮食吃下去。我尝过一口,再也不吃,好在我妈没有这么勤俭,懒得做懒得烤,我家的豆渣都喂了猪。灶背后,靠墙摆放着一口长方形的石水缸,装得下五六挑水,挑水是舅舅老表的事,他俩天天黄昏负责将水缸挑满,外婆她们天天负责将缸里的水用尽。水缸隔些日子要淘洗,表姐的事。家里老老少少男男女女,时间长了,该干什么不用说,自己晓得摸着自己的事做。被井水打湿的水桶,为了耐用,挑完水翻转来,桶底向上,隔断潮湿的地面。从灶房旮旯角落的细节处,可以看出林家是怎么过日子,怎么持家的,一日三餐,好好歹歹,炊烟按时从灶房升起。
也有不按时的日子,吃大食堂的日子,缺粮少米以白泥巴树叶草叶充饥的日子,林家灶房
顶上的烟火并不准时。好多年,为节省粮食,农闲都是两顿饭,到晚上,无人进灶房,天黑上床睡觉,煤油按量供应,为了节省,晚上不敢多点灯,记得我家四口人,每月只有半斤煤油。1979年,生产队解散,家家户户在分配的土地上劳作,粮食吃不完,一日三餐,林家的烟火按时从灶房升起,外婆荒废了多年的手艺又派上了用场,夏天晒阴米苕丝,冬天做各式各样的糕点,黄粑叶儿粑,过年过节,寿宴婚宴,饭前是必吃的。
灶房不算宽敞,深处,却亮堂,西面板壁墙上有窗,有窗棂的一扇大窗占据半壁墙,一扇年深月久的窗门,从来没有关闭过,一截木棒将这扇窗门撑起,刮风下雨,雷鸣电闪,窗外风雨飘摇,窗内寂静安宁。
外婆没有看到林家安宁的日子被一个女人打乱。
老表结婚,喜庆之后,便是烦恼。
一家人磕磕绊绊过了一段时间,分成了两家人,老表两口子要分开过,灶房两家人共用,各煮各的,各吃各的。
两家人在一个屋檐下生活,房子是完整的,就像外公两兄弟分家,林家的这座大房子,一直保持着完整,到了第三代,房子与家庭一样,分崩离析,老表一家三口住了几年,拆掉分给他的老屋,去太阳坡修了一座水泥楼房,林家居住多年的三合院板壁瓦房,七零八落,外婆舅舅没有看到这种景象,看见,阻止得了吗?舅母看见了,少言寡语,像牲口一样劳作的她,阻止不了!
谁也阻止不了!
第七扇
这间屋子是茅房,谷草上,落满竹叶。
站在房子正面,看不见这间屋顶,也看不见茅草,它静悄悄隐藏在这座大瓦房的深处。隐秘、偏僻、阔大。看似不起眼,用途却大,林家的老老少少离不得这间屋子。这间幽暗的大草房,不仅仅是茅私,是一间大杂物,林家人从灶房踏进这扇门,在这间茅屋排泄,也在这间茅屋养猪养牛关鸡放农具堆柴火。靠西墙,茅坑,茅坑上面的猪圈,条形青石板镶嵌,青石边三方木棒栅栏,猪在栅栏内吃喝拉撒,哼哼唧唧,磨皮擦痒,游荡昏睡,人在栏外的两条石缝大小便。鸡罩摆放东墙,打成捆的柴火也顺东墙摆放,隔壁是外婆的房间。南墙抵拢后坡,屋檐低于山墙,一条排水沟将山墙隔断,我们叫它后阳沟。南墙下,大水牛的地盘,也是这间茅屋最幽暗之处。春耕,大水牛白天在野地劳作吃草歇息,夜晚进来睡觉;盛夏,大水牛无事情干,被舅舅牵进竹林下的一块牛滚凼乘凉,去赵场去林家去井边洗衣挑水,要经过这片竹林,经过这口牛滚凼。牛滚凼外边,是田埂是秧田,林家修了房子,坎下这块半月形的小水田,作了水牛的澡堂,大水牛年年在这里消夏。天寒地冻,大水牛不上坡不下水,白天黑夜躲进茅屋,以谷草度日,躺在南墙下咀嚼、反刍,幽暗里,难得见阳光。
离水牛不远处,有口幽深的地窖,窖口盖着木板,我见过舅舅老表下地窖取红苕。我家的红苕大冷天被风吹烂,林家地窖里的红苕个个完好,青黄不接的日子,解决一家人的燃眉之急,外婆做的红苕粑,是我吃过的最好吃的食物,外婆离去,无人会做。
这扇由灶房通往茅私的门常年开启,有人进去解溲,才将门关闭、拴牢。门腰的木质插销,被触摸得油亮。
茅私,我们川南人的土话,书面语是茅厕、厕所,在一篇小说里,编辑将我文字里的“茅私”改成“茅司”。厕所这个隐秘之处,属私人空间,我们的土话,说明了它的私密性,是“茅私”,不是“茅司。”
第八扇
啰嗦了这么多,有心的读者应该明白我的
用意,从第一扇门开始,读者跟着我跨过林家的一扇扇大门,一道道门槛,进入林家的一间间屋子,对林家的生活,对这座老宅多多少少有所了解。曲径通幽,耐心的读者,终于可以跟随我走进林家老宅的深处,抵达林家老宅的最后一扇门,至于那些缺少耐心的读者,有可能进入第一扇门,第二扇门,不耐烦地转身出去,他们的匆匆、浮躁,使其只见陈旧粗糙的木门不见幽林,只见黑洞洞的房间不见旷野,拉拉杂杂不厌其烦写了这么多,仿佛就是为了这最后一扇门。
好,现在我已经抵达门边,打开了林家老宅的最后一扇门。
这扇门同我前面叙述的门一样,简单、粗糙、陈旧,未涂抹任何东西,门腰上,仍然有一条活动的木头门栓,结实、厚重,形状似半块肥皂;门枋上,有木头插口,关闭,将门栓卡进插口,开启,将门栓往上抽;门开启,活动自如,门关闭,牢实稳当。林家的门,除了耳房双扇扇的大门挂了将军不下马铜锁,别的门都不上锁。白天,家里有人,大门难得关闭,晚上睡觉,最后一个上床的人,将大门拴好。门栓还是安插门腰,比单扇扇的门拴长两倍宽两倍,关闭时,对准插口推上门栓,谁也进不来。有的人家是双门栓,更保险。茅私深处这扇门,开启的时候不多,牛从这扇门进进出出,舅舅的事,他牵着牛,常从这扇门进出。挑猪粪牛粪,人从这扇门进出,不是舅舅一个人的事,能挑能背的都干过,外婆舅舅舅母老表表姐,后来长大的表兄表妹,他们,都干过,都从这扇门进出过。
我打开了林家的最后一扇门。
你跟随我从黑洞洞的茅屋跨出了门槛,我们站在门外,站在几棵楠竹下。细翠、飘逸的竹梢上空,蓝天白云,我们望见了一只小鸟飞鸣而去,不知它要栖息何处?门边,一条黄泥小路,斜缓着从竹林通向大路。大路外边,层层田野。这些半月形水田,从高处来,到低处去,到达另一弯口,另一山坳,又向高处去,向低处去,迂回着、盘旋着,坡坡弯弯,曲折着,或上或下,四处延伸。目光越过竹林下的这弯冲田,对面太阳坡大路旁,有两三座房子,其中一座,是我表哥的楼房。外婆活着的日子,太阳坡上没有房子,林家的另一房人,在大路下修了一座土墙瓦房,后来表哥和另一个刘姓人也把房子修在太阳坡,都是婚后分家重建。太阳坡遮挡了我们的视线,我们的目光只好偏离,望见了蜿蜒的冲田,望见了远处山窝里的一座大瓦房,望见了近处的石板路,望见了一片竹林,望见了刘家的瓦房,望见了半座山坡,山嘴上,是林家的老房子。我们的目光围着山野绕了半圈,又回到了我们站立的地方,回到了林家的这扇门外。现在,你跟随我离开了这扇门,我们走进了楠竹林,又走进了簧竹林,来到了幽林深处。刚才,我们在西侧,现在,我们在林家房子的背后,在竹林掩映,长满野草青苔的山墙上,林家的青瓦脊一目了然,静悄悄,青幽幽。离开山墙,我们踏入竹林的另一条黄泥小路,这条路,向下通往林家,向上通往另两房林姓,向西通往刘家,向东通往李家。向西向东,这条黄泥小路都可以通向大路,抵达赵场柏溪宜宾七星岩,抵达更远之地,抵达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我们下坡,从一片竹林进入另一片竹林,经过一口老井,一块水田,回到林家的敞坝,又望见了林家的两扇大门,望见了将军不下马铜锁。我们进入这扇大门,跨过一道道门槛,经过一扇扇开启的门,抵达了最后一扇门。黑暗里,我们开启了林家这扇通往幽林旷野,通往外面世界的门。门外的黄泥小路,可以通向任何一个地方,也可以回到原点。你可以反身进门,再次进入林家曲径通幽的老宅。反身进入的这扇门,现在成为你进入林家的第一扇门,耳房的两扇大门,是你踏进檐坎的最后一扇门。下了檐坎是敞坝,你看到了青翠的竹林,看到了茂密的皂角枇杷李子柑子树。敞坝半圆形,中间往外凸,走到凸处,你看到的风景,与在房后看到的差不多,竹林外,田野山坡高高低低,迂回曲折。
站在林家的第一扇门和最后一扇门外,你都可以望见幽林山丘。可以不断地走向旷野,走向丘陵深处。也可以越过丘陵,走向喧嚣,走向繁华。你,可以选择一扇通往纵深地的门,也可以选择一扇通往繁荣地带的门。
林家的最后一扇门还开着,我引领你穿过幽寂来到门边开启的,门内门外的景象你都看到了。当我打开这扇未作任何修饰的门时,时光从楠竹林进入黑洞洞的房间,我们站在门边,站在时光下。我们进入竹林回到大门,这扇门已经关闭,“吱呀”一声,时光被关在了门外;我领着你去敞坝边看田野山坡时,“吱呀”一声,林家的两扇大门也关闭,时光被关在了门外。那把简洁明亮,闪烁着时光的铜锁,那把挂在门上的将军不下马,不知去向,也许化为了灰烬,也许落尽了草野,也许埋进了泥土。
“吱吱嘎嘎”声里,林家所有的门都关闭了,不再开启。
你跟随我从第一扇门跨进林家,从最后一扇门出来,时光,已经在我们的身后关闭。
某个夏日的黄昏,我拾级进入八老表的二楼,伫立铝合金窗边眺望田野,残阳辉映,时光流淌丘陵,对于我对于林家,不再是从前的时光。
时光,被一扇扇粗朴、简陋的木门关闭。
我打开另一扇门,进入了尘嚣,越过纷乱、嘈杂,我将那扇门关闭,又回到寂静,回到旷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