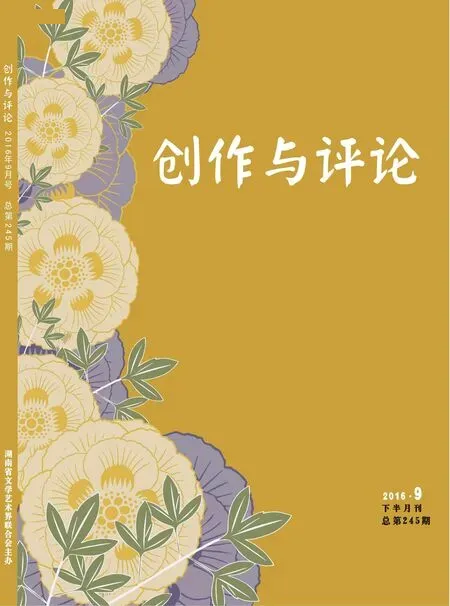无处安魂的漂泊与迷离
○ 聂茂
无处安魂的漂泊与迷离
○聂茂
一、浮华背后的苍凉与惆怅
2015年,对于赵燕飞而言,算得上是一个创作丰收年。敦煌文艺出版社推出她的两部中短篇小说集:《手心里的痣》《一声长啸》;发表了一部长篇小说《香奈儿》 (《芳草·小说月刊》2015年第12期);发表了三篇中篇小说,其中,《春晚》被《小说选刊》第5期和《中华文学选刊》第5期同时选载;《红月亮》和《河边的曼陀罗》则同时被《中华文学选刊》第10期选中:《红月亮》被全文选载,《河边的曼陀罗》在“佳作点评”栏目予以重点推介。作为一家影响广泛的重要选刊,《中华文学选刊》在同一期关注同一个作者的两部作品,实属难得。赵燕飞用自己的努力赢得了文坛的关注。评论家李一鸣在《生活意义的参与者》一文中指出:赵燕飞的小说,无论是《春晚》《阿里曼娜》,还是《赖皮柚》《地下通道》等,其最大的特点是“其现实主义的意义指向,对人生真相的直面,对当下人们生存境遇的叙事,都达到逼真的程度。”(《文艺报》2015年11月11日)
读了赵燕飞的作品,一个强烈的感觉是:她的叙事很平实,注重细节的力量,没有花里胡哨的东西,小说中的人物常常在平和的情调和琐碎的烦扰中裹挟着一丝不安、焦躁以及漂泊中的无助与无奈,在霓虹灯的闪耀下,这样一群拥有理想和激情、却徘徊于情感世界中的青年男女在都市生活的漩涡中苦苦挣扎,他们或为情所困,或失去了生活的方向,或对未来充满迷茫,他们像无根的浮萍,不知道将灵魂安放在何处。尽管如此,他们并没有放弃对梦想/诗意的追求,他们有自己的独立判断,愿意对自己的选择(事业或家庭)负责,甚至为了这一份责任,他们不得不选择妥协,不得不违心与社会达成一致。在此情况下,理解和体谅比同情或怜悯更能够引起他们情感的共鸣。
例如,在长篇小说《香奈儿》中,作者将故事背景置于文学杂志社,这显然与作者的真实生活和体验有关。作为一名文学编辑,主人公陶子经历了一场失败的婚姻,无法走出情感之痛,工作和生活处于一种迷糊或混沌状态。如果没有柳云的出现,陶子恐怕要一直这么麻木不仁地混下去。在作者笔下,柳云是一个理想化的人物,她既是陶子的启蒙者,又是陶子的引路人。她不仅拥有高学历,好职位,还蕴藏着一颗纯真美好的心灵。最有意思的是,她是陶子前妻的姑姑,在陶子与前妻分手后,她发现了陶子“闪光”的地方,不知不觉地爱上了陶子,并希望用真心和爱意拯救日益颓废的陶子。原本对“博士”“大龄剩女”和“前姑姑”三位一体的柳云毫无好感的陶子在一次次粗鲁、愤怒、不屑和对质中,一次次被她的单纯、善良、真情所打动。最终,陶子由对柳云的厌恶嫌弃到发自内心地爱上她,反映了单纯、善良、真情所彰显出来的传统文化的修复力。这部小说的价值在于,陶子虽然在感情上遭遇到失败,但并没有放弃对真正爱情的向往和憧憬。虽然他离过婚,年龄也老大不小了,但一直没有“长大”,需要有柳云这样的引路人伴随他成长。而柳云虽然是“博士”“大龄剩女”和“前姑姑”,却乐意成为陶子的引路人,在与他的交往中,发现自己的脆弱和幼稚,最终一起成长。小说取名“香奈儿”,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这原本是一种款香水,实则暗指柳云身上所特有的“女人香”,有了这样的“女儿香”,再狂野的男人也会闻香生变,循香而去。
赵燕飞生动地展示了一群为情所困和生活所累的青年男女,让我们感同身受,体验到现实生活中真实刺骨的痛感。在熙熙攘攘的人流中,总有一个狭小而隐秘的空间,在我们面前若隐若现。作者的笔端触及了都市青年潜藏在耀眼光影中不为人知的内心世界,这里的世界少了一份浮华与享乐,多了一份苍凉与惆怅。
二、逃离与渴望:“家”在爱的皱褶处
赵燕飞作品的发生地几乎都在城市,主人公既有出生在城市里的人,更有从农村进城打拼的人。小说《春晚》中的叶子就属于后者,她是一名只身前往城市拼搏的青年女性,她离开偏远的家乡,在都市的繁忙节奏中寻找属于自己的世界。安平的出现打破了叶子的宁静,原本陌生的男女在断断续续的交往中坠入了爱河。然而,叶子是一名独身主义者,“在叶子心里,安平到底算什么?叶子自己常常犯迷糊”。爱情在叶子和安平之间除了甜蜜和欢乐,似乎还多了一份神秘与若有若无。“他有时会突然失踪,其实也不是真的失踪,只是叶子很少主动找他,如果安平十天半月的不主动和叶子联系,于叶子而言,那就是失踪……一来二去,安平也懒得去考验叶子到底想不想他了。反正,叶子从没说过想嫁给他,他也从没主动说过要娶叶子。没有希望,自然也就没有失望。”就这样,叶子一次次从希望走向了失望,又从失望的边缘回到了与安平的爱情中。叶子的爱情如同自己的名字,在漂浮不定中寻找着一份安稳与依靠。然而,女人的内心终究是敏感而脆弱的,在交往了两年后,叶子实实在在地考验了一回安平。出其不意的考验最终让叶子获得了心中想要的结局,毕竟安平是爱自己的。然而,这场考验也让叶子在焦虑和不安中萌生了一层新的焦虑,毕竟安平是离过婚的人,一纸离婚证书能宣告他和前妻之间婚姻的终结,却无法斩断他与女儿之间血浓于水的亲情关系,而夹杂在其中的则是叶子对安平的爱。一场看似单纯的都市爱情在掺杂着婚姻的纠葛和世俗的欲望后,就多了一份顾虑和担忧,少了一份安逸与快乐。叶子的爱情该何去何从,那份渴盼已久的家又在何处?对“家”的逃离与渴望如影无形地纠缠着叶子。而这份纠缠同样适用于安平:在象征着一家人团圆和欢乐的春晚时刻,安平是该回到女儿身边,还是留在叶子身旁?这种选择看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叶子当然明白,却又不愿强求,任焦虑与不安滋生,任惊恐和担忧萦绕。万家团聚的时刻,形单影只的叶子在繁华的都市夜色中只留下无望的等待和孤独的呐喊。
小说用“春晚”作题,象征着团圆与欢庆。作者以“春晚”命名叶子的情感生活,似乎暗示了叶子在都市打拼的最后归宿就是拥有一个温馨的家。在叶子心中,“家”是一处可望而不可即的港湾,她渴盼着这里的温暖和安逸,却又时时警醒,没有安全感,生怕大风大浪打乱她生活的阵脚,进而迷失生活的方向。叶子陷入了对“家”的困境中:一方面幻想拥有,一方面又害怕因为拥有而失去。在当下都市生活的灯红酒绿中,赵燕飞笔下的“家”多了一份春节的文化寓意,被赋予了更多的人文情怀与情感魅力。“从小到大,叶子就渴望拥有一套自己的房子,最起码,也得有一间房只属于她一个人”。安平带给了叶子渴盼已久的家的感觉。然而,就在万家团聚的春晚时刻,安平对女儿的疼爱和不舍以及无法陪叶子看春晚的尴尬让叶子陷入了窘境中。“今年这么多人一起看,明年呢,后年呢,大后年呢……到时谁陪我看?”赵燕飞将情感集中爆发点选在了象征着合家团聚的春晚时刻,正如曹雪芹把林黛玉生命的终结选在了贾宝玉新婚的夜晚。在一悲一喜的强烈反差中,内心孤独的叶子在失去了安平的陪伴后,在欢乐的春晚气氛中更为形单影只和孤独无依。小说最后,叶子那一声“我要和你们一起看‘春晚’”的呐喊道尽了心中的荒凉与无奈。“家”在爱的皱褶处。有爱的地方未必有家,而家也未必就是爱的代名词。这是作者对都市在场的深刻悟。叶子与安平的爱究竟何去何从,她对婚姻的渴望能否继续下去,一年又一年的春晚时刻又该寄予何方,种种疑问最终浓缩在了赵燕飞笔下的省略号中。作者以不确定的开放式结局,把未知的答案交给了读者。
就这样,传统意义的“家”在叶子的窘困与无奈中最终成了一张无形的大网。在这张纠结着情感、欲望、矛盾和困惑的大网中,曾经满怀希望的叶子成了一名格格不入的追寻者和闯入者,她试图在“家”的生存空间中找着属于自己的一方天地。但现实是残酷的,叶子以有声的呐喊宣告着无言的痛苦和无奈。在这样一声强有力的呼喊中,赵燕飞将笔伸向了都市女性最敏感、也是最脆弱的部位。在这样一片隐秘而无人问询的陌生境地里,与都市生活外在的繁华和喧闹相比,生活在其中的都市女性的内心世界显得更为孤独和荒凉。
三、曼陀罗:浪漫的守望与诗意的追寻
如果说《春晚》中的叶子将自己推向了家的困惑中,那么《河边的曼陀罗》中的另一个叶子则把对爱情的渴望和对婚姻的追求寄托在了盛开的曼陀罗上。这一次,赵燕飞把描写的笔触伸向了更为真实而无奈的现实之痛。面对来自理想与生活的矛盾,在爱情和婚姻的抉择中,向往曼陀罗的叶子陷入了更深的漩涡中,进退两难。
在这个文本中,赵燕飞对叶子一类的都市女性寄寓了一丝无法捉摸的孤独感与漂泊感。青年女性在生活的路途中,正如一片随风飘荡的叶子,无居无所,无依无靠,甚至于无欲无求。当暴风骤雨的袭击来临时,一片叶子的脆弱也暴露无遗,虽使劲浑身解数也难敌外来的强压。新时期文学以来,我们曾见到了很多这样的“叶子”:卢新华《伤痕》中的王晓华暗示了如“小花”般青春而稚嫩的生命;张贤亮《绿化树》中的农家女孩马缨花既如马缨花般美丽动人,质朴纯洁,“马缨花”又是绿化树的别名,与小说名相照应;阎连科《受活》中的四名儒妮儿桐花、槐花、榆花和娥儿也在花名的烘托下愈显得娇小可人。赵燕飞《河边的曼陀罗》中不仅又一次出现了“叶子”的身影,与《春晚》中的都市女性叶子不谋而合,小说中极具象征意味的铅笔花也是曼陀罗的别名,这一称呼的转换与小说名相呼应。陌生化手法的运用让故事情节发展自然,而又寓意深刻。
小说《河边的曼陀罗》中,文本互涉般的叶子再次出现在了赵燕飞的小说世界中。与《春晚》相比,叶子对“家”的逃离和回归不再受阻于情感的纠葛和人性的捉摸不定。在新的社会压力和现实情形面前,一场势力悬殊的“三角恋”让叶子的情感生活受到了来自现实的挑衅。
叶子与童年玩伴羊远航从小青梅竹马,但成年后的羊远航家境贫寒,且没有一份稳定的工作,这与衣食无忧的叶子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叶子和羊远航的结合显得门不当户不对,他们之间的爱情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显得脆弱不堪。高干子弟出生的李由家境富裕,他对叶子心生爱慕,且李由父母身居要职,在叶子父母工作的煤矿区拥有权力和地位。李由对叶子的追求似乎更符合现实的婚姻观念,也更容易勾起读者对灰姑娘与王子喜结良缘的美好向往。然而,尽管李由的父母凭借手中的权利为叶子的家庭生活带来了明显的改善,叶子的父亲调离了危险的井下作业工作,担任地面工作组的组长,叶子的母亲也从家属工转为正式工,不仅工资与以前相比增长了不少,腰板儿也挺直了许多,叶子本人也在李由父母的帮助下进入煤矿子弟学校当上了老师,工作体面而轻松,让许多年轻女孩羡慕不已。但爱情毕竟太美好,面包有了之后,爱情的磁场尤其强大。静下心来的叶子慢慢感受到生活的压抑与苦痛。羊远航成了一道挥之不去的阴影,时刻萦绕在叶子的脑海中,无法让她释怀。
与其说叶子徘徊于羊远航和李由之间,毋宁说她纠结于单纯的爱情和复杂的人性中,进退维谷。“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爱情观念让人们坚信只有真爱才能修得婚姻正果的道理。但在残酷的现实面前,物欲的横流和权力的无所不能成了爱情的引领者,在婚姻的殿堂中成了唯一的主宰。有情人的真爱在权力和欲望面前不堪一击,最终让位于残酷的现实。尽管叶子与羊远航之间的爱情纯洁而不掺杂任何俗念,但世俗观念挑衅着爱情的至高无上。最终,叶子和羊远航不堪重负,选择远走高飞对抗残酷的一切。但两人计划的失败再次将他们拉回到现实生活中。与李由的结合让叶子在失去了感情基础的婚姻里,成了一个无依无靠的孤独者,行走于情感的边缘,而无力于追寻心中的浪漫。
叶子的孤独无助和李由的位高权重让两人之间的交往也处于一强一弱的态势。父母生活的需要和自己毕业后分配工作岗位的需求让叶子被动地置于弱者的地位,在无权无势的权力运作中俨然成了一名失败者,听凭别人的安排与操纵。李由作为高干子弟,他凭借父母的强势在权力主宰一切的时代背景下成了不折不扣的强者。而在权力操控的爱情面前,李由收获了叶子父母的好感和这场爱情的主动权,与叶子的结合自然也显得顺理成章。然而,叶子与李由之间的爱情只是建立在欲望和权力基础之上的海市蜃楼。当失去了为之依赖的权力和物质后,这场爱情也将随之倒坍,不复存在。叶子最终是回到了羊远航的怀抱,还是成了李由的妻子,小说结尾也同样没有明说,任由读者去猜测。
赵燕飞笔下的女性人物在小说结尾都没有一个具体的生活指向。《春晚》中的叶子最终选择和安平在一起,结束单身生活,还是选择离开安平,继续追求理想的幸福,小说结尾没有明说,叶子也只是在呼喊声中倾吐着内心的不快与无奈。《河边的曼陀罗》中的叶子则游离于理想与现实的边缘,在爱情的织网中寻寻觅觅,寻找着婚姻的殿堂和生活的归宿。赵燕飞将小说主人公的结局做了模糊化处理,这样的模糊似乎更增添了生活的变数,击中了纠结于女性内心世界中的情感之痛,也拓展了文本的想象空间。
在易卜生的剧作《玩偶之家》中,主人公娜拉最后的离家出走宣告了对夫权的挑战和一个女权主义者的自尊与独立。与《玩偶之家》的结尾相似的是,《河边的曼陀罗》中,叶子也以离家出走的方式离开了这个让自己无所适从的家。只不过这里的叶子抱起门口的铅笔花朝着远方奔去。这样一种奔跑的姿态更像逃脱,逃避感情世界的纠葛和现实世界的残酷。叶子的奔走少了娜拉的果敢和决绝,多了一丝犹疑和徘徊不定。叶子终究是敏感而脆弱的,无论是满足于现有的安稳生活,还是不顾现实的反对追求理想的幸福,只有那盛开在河边的曼陀罗才能拨开这迷乱的景象,为叶子的内心带来一丝快慰和抚恤。
四、何处安放漂泊的灵魂
赵燕飞笔下的女性代表——叶子的情感状态和生活经历做了细致入微的刻画和真实情感历程的还原。《春晚》中叶子的孤独与无助,《河边的曼陀罗》中叶子的迷茫与徘徊,在跌宕起伏的生活原态中,作者通过简单而饱含深情的描写,表达了自己的艺术立场。
与陷入窘境中的女性形象相比,赵燕飞笔下的男性形象也在情感的纠葛和漩涡中迷失了生活的方向。与之前模糊化的小说结局不同的是,在小说《红月亮》中,男主人公李伟杰在理性和良知的引导下突破了情感的迷雾和生活的困扰,最终以反抗的姿态对触目惊心的黑暗现实大胆地说出了“不”字。
《春晚》中的叶子徘徊于爱情的边缘,执着于心中的幸福却又无法对不如意的现实勇敢地放手;《河边的曼陀罗》中的叶子纠结于理想与现实的困惑却又无法坚守住心中的向往,只能在迷离的梦幻中守护心中的那束铅笔花;《红月亮》中的李伟杰却在离异后的自责与内疚中独自面对来自生活的艰辛与情感的波折,在压抑中寻求突破。如同一场阴郁、沉闷而亟待爆发的暴风雨,赵燕飞的作品在人性的揭示和情感的波澜起伏中由浅入深地探寻着,剖析情感道路中的波折与艰辛,窥探人性的脆弱与觉醒。
赵燕飞小说世界里的青年男女似乎都逃脱不了一张无形的情网,在爱与恨的交织中寻找感情的归宿与生活的安逸。李伟杰作为赵燕飞笔下少有的男性形象,他的情感路程在面临相同的困扰和焦虑的同时,多了一丝世俗的无奈和良知的叩问:李伟杰原本有一个幸福的家,但身患隐疾的他无法向妻子说明这不明不白而来的病痛的缘由。在妻子的怀疑下,李伟杰无奈地选择了离婚结束这段感情生涯,并放弃了城市优越的生活,自愿来到偏远的伏林镇当起了村支书。原本以为远离了情感的困惑和都市生活的烦恼后,李伟杰便不再经受精神的压抑与折磨,重新开始新的生活。但偏远乡村的愚昧与无知让李伟杰触目惊心:村民马凤英为了延续香火,在生了两个女儿后仍然违背计划生育政策怀起了第三胎;村主任段鹏远为了求子,公然与村妇女主任程习发生性关系;村会计老屈和妻子为了发财,不顾生命危险在即将倒坍的自家房檐下刨煤碳,并斥责前来制止的村干部和村民们,“这田地反正都废了,不挖煤我们吃什么去?这满山的煤,哪会那么容易被挖光!就算挖光了,再有啥吃啥也不迟”。面对村民的无知和愚昧,李伟杰困扰于良心的纠葛与世俗的执念中,二者的纷扰让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无可奈何,心中的不满和怨恨最终以咆哮的呼声宣告了对黑暗现实的挑战。
赵燕飞笔下的贪婪人性真实而让人心寒。如果说《春晚》和《河边的曼陀罗》中情感的纠葛来自于对爱情的掠夺和对欲望的占有的话,那么《红月亮》中的贪婪则来自于人性深处的欲念。令人心惊的是,都市生活的贪婪和欲望尚且纠葛于个体的思想深处,隐秘却不易构成外在威胁。而在这座偏远的伏林镇上,作为个体的村民却在蒙昧无知的状态中公然违背自然规律和法律约束,欲望的张扬与人性的愚昧充斥在李伟杰的世界里,物欲横流的欲念已经不再归属于都市社会。在贫穷落后的乡间,人性的贪婪与欲望以更极端的方式存在于不为人知的角落中,那些触目惊心的权利斗争和金钱交易在满足人们日益膨胀的虚荣心的同时,也在给时代的发展带来了更大的危害和潜在的威胁。在这样一座贫穷落后的小山村里,贪婪的欲望和自私自利的念头充斥在每一位最憨厚朴实又最愚昧无知的村民的心间,有人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有人执迷其中无法自拔,更有甚者明知故犯,最终难逃法律的谴责。
农村原本是一片净土。在这片广袤的乡间,千百年的男耕女织养育了生生不息的血脉与生命。作家笔下朴实的民风和淳朴的乡民曾为都市生活的繁忙和喧嚣开辟了一方悠闲自在的乐土:沈从文笔下的“边城”滋润着一代又一代湘西儿女;阿城笔下的棋王、树王和孩子王让厚重的黄土地多了一份惊奇与智慧;贾平凹笔下的秦腔回响在辽阔的陕北土地间,在嘹亮的强调中回响着一份来自历史的召唤。然而,随着历史的推移,一个破败不堪和愚昧无知的农村也震颤着时代的脉搏,滞缓的建设和愚钝的乡民在现代化的城市进程中显得脆弱无能,却又无法回避。
人性的欲望似乎是一个无底洞,在蚕食有限的资源和挑衅生存的信念。不断膨胀的欲望和无休无止的贪婪让这样一群走在毁灭的道路上的人们或者陷入了堕落的俗世中,或者放弃了自己的生命。但令人心痛的不仅在于他们生命的终结,更是根深蒂固的愚昧和不能自拔的欲求。面对丧失理性和良知的人们,不堪良心谴责的李伟杰最终说出了内心的“不”字,勇敢地面对人性中的黑暗与欲望。
小说结尾,“流着泪的红月亮”让李伟杰的悲伤与痛苦更为强烈而无奈。如果说张爱玲笔下的月亮泛着一丝沧桑而凄凉的色彩的话,那么赵燕飞笔下的红月亮则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诡异和无法言说的困顿。或许,只有红月亮的幽微光芒才能照亮人性的黑暗与丑恶。李伟杰在情感的波折和扭曲的内心中寻找着一份光明和希冀,反抗着世俗的贪念与欲望。这些都市青年受困于感情和良知双重拷问,在世俗的欲望和人性的欲求中艰难地挣扎着,在寻寻觅觅中探求着生活的动力。合家团圆时刻的春晚、独自盛开在河边的曼陀罗、还有静置在天边的红月亮,种种意象的生发都指向人性的孤独与困惑,迷茫与无助。对生活的还原与呈现让赵燕飞的小说世界多了一份理性和智慧。或许,只有重新回归生活的原点,执迷于其中的人们才能解开内心的疑惑,重拾生命的希望。
总之,赵燕飞的小说昭示着:在消费因子无处不在的今天,人是躁动不安的。爱是如此珍贵,却又如此脆弱;家是如此美好,却又如此难得。不管你出生在都市还是乡村,每个人都有一种难以逃离的漂泊感。这种漂泊,不仅仅是物质上的无助感,更是精神上的无根感。因为漂泊,所以难以找到可以令自己“安稳”的一隅。一个人,当灵魂无处安放的时候,无论多少财富,无论事业多么成功,内心的躁动和不安也必将一直存在。而唯有少一点物欲,少一点贪念,先让内心宁静,真正感受到张爱玲对胡兰成所谓“现世安稳”之重要,然后才有接近海德格尔所谓“诗意的栖居”之可能。唯其如此,灵魂才能得以安放。而这,也正是赵燕飞小说给予我们的启示。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中国新时期文学自信力”(项目编号:15FZW061)、湖南省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文学新湘军新批评”(项目编号:2016WTA07)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中南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佘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