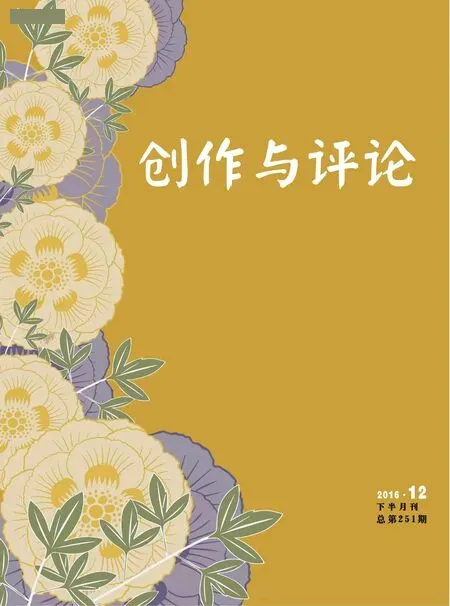詹姆逊后现代理论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发展
○张文
詹姆逊后现代理论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发展
○张文
二十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东欧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发生根本性改变,世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进入低潮,国际上掀起一股反马克思主义的狂潮。马克思主义的敌人纷纷认为马克思主义已寿终正寝,高呼社会主义终结了,历史终结了。他们坚信马克思主义只能生活在那个工厂林立、到处充满饥饿和工人暴动的不幸世界里,而在今天这个阶级意识日益淡化的后现代西方社会里,马克思主义早已无处安身。然而,正当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声浪甚嚣尘上之时,美国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和理论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挺身而出,声称自己是“剩下的少数马克思主义者之一”①。他清醒地看到了马克思主义危机背后的原因:“每当马克思的研究对象——资本主义——发生变化或经历出乎意料的变异时,马克思主义的范式就会产生危机。由于对论证问题的旧表述不与新的现实相适应,所以很容易得出结论说,这种范式本身被超越了或过时了。”②针对这种否定马克思主义时效性的结论,詹姆逊予以坚决否认,同时不无坚定地指出:“马克思主义是关于资本主义的唯一科学;其认识论方面的使命在于它具有描述资本主义历史起源的无限能力。”③在他看来,“庆贺马克思主义死亡正像庆贺资本主义取得最终胜利一样是不能自圆其说的。”④
那么,产生于资本主义工业化早期的马克思主义在进入20世纪后,特别是20世纪下半叶的后现代社会,如何在后现代的理论潮流中坚守自身的立场?后现代社会对马克思主义又提出了哪些新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究竟能否对话?这些都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必须研究的重大课题,也是关系到马克思主义存亡与发展的大事。针对这些问题,詹姆逊表现出了强烈的时代感和社会热忱,致力于推动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在当下的对话;同时在坚守马克思主义立场的基础上发展和升华马克思主义,以期开阔马克思主义的当代视域,激活马克思主义阐释当下的理论活力。
一、马克思主义遭遇后现代主义
在多数人的观念里,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因产生的社会背景有别、批判路径迥异,是两套截然不同的理论体系。对于二者在当下相遇的关系问题上,主要存在三种立场。一种观点认为,产生于资本主义早期阶段的马克思学说已经无法解释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发生根本改变的后工业时代或晚期资本主义时代,因此马克思学说是一种过时的学说,它已经丧失了阐释当下后现代社会的有效性。另一种观点认为,具有怀疑论解构倾向的后现代主义是一种虚无主义的颓废思潮,它不过是一种拒斥深度的语言游戏,无法与追求人类解放的马克思主义伟大理论相提并论。第三种观点主要来自以拉克劳与莫菲为代表的后马克思主义者,面对20世纪60年代之后西方科技革命的浪潮和20世纪末的全球化趋势,他们立志“革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前两种观点将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非此即彼的范畴对立起来,认为两者之间存在难以跨越的鸿沟,因此在当下无法进行对话与沟通。另一种后马克思主义观点虽然披着调和两者关系的外衣,实则彻底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立足点,在本质上无异于第一种观点。这种立场通常认为,以经济还原论和阶级还原论为实质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已经不再适合后工业社会,因为在后现代社会中经济已经不是“决定因素”了,从而阶级斗争也失去意义,革命更是无从谈起。因此,后马克思主义解构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理论,企图“重铸”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在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问题上,不可否认地是詹姆逊的确看到了两者在当下开展对话的困难。他曾坦言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给人的感觉是一种缺乏稳固基础的罕见的或悖论的组合,甚至还自我解嘲地构想一幅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在当下相遇的画面:“一个正在艰难经营的小旅馆,里面充满一种怀旧的氛围,墙上挂着老照片,一位苏维埃的服务员懒懒地端上一盘糟糕的俄罗斯饭菜——而这个小餐馆却处在闪烁着霓虹灯的繁华的建筑群中”⑤。在这幅不和谐的画面里,苏联服务员不可避免地让人想起列宁、苏联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繁华的建筑群则让人想起后现代主义。那么,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是否真的是一对冤家,两者之间是否真的存在无法调和的矛盾?詹姆逊的答案是否定的。
詹姆逊既不同意上述二元对立的价值判断,认为简单地赞美后现代主义或不承认后现代主义都是不可能的;也拒斥后马克思主义的身份,认为它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的背弃。作为富有历史责任感的马克思主义者,詹姆逊敏锐地洞察到了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在当下开展对话的可能性:马克思主义关注的是资本主义的问题,而后现代主义关注的俨然也是资本主义的问题,而资本主义的问题需要被纳入马克思主义的框架内加以考察。这正是詹姆逊后现代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在当下开展对话的前提。在詹姆逊看来,尽管与马克思所处的资本主义早期阶段相比,后现代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但是从本源上来看,“今日的资本主义并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⑥,它只是经历了一个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被詹姆逊历史化地加以考察。他认为现代主义时期的工业资本主义是不完全的,因为它仍然带有农业和封建习惯的残余;而后现代主义时期则彻底地抹除了前资本主义的农业,以前一切已被现代化和机械化的社会空间和经验基本均质化。因此后现代时期是资本主义发展得更纯粹和更发达的阶段。在辩证地思考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基础之上,詹姆逊巧妙地指出,资本主义阶段的表达——早期、成熟期、晚期或进步期,是一个应该被逆转的误称:“最早的几年应该被称为高龄的资本主义,因为这个时期仍然是一件关乎来自先前世界令人厌烦的传统主义论者的事情;成熟期的资本主义这个说法将维持不变,以便反映出伟大的强盗男爵和冒险家得到它们应得之物这件事情;我们的晚期资本主义可以被视为‘婴儿期的资本主义’,因为每一个人都生在这个时期里,将他视为理所当然,而且从不知道其他任何事物,先前的摩擦、反抗和努力已经屈服于自动化的自由运用和众多可以取代的消费大众和市场。”⑦由此可见,晚期资本主义并非资本主义走向了穷途末路,而是资本主义更为充分发展的“最近”阶段。面对后现代社会,詹姆逊仍然坚信马克思主义是对资本主义有效的时代诊断。正如他所言:“马克思主义是关于资本主义的科学,或为了给资本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这两个术语以更深刻的含义,我们还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是关于资本主义固有矛盾的科学。”⑧因此,作为关于资本主义固有矛盾的科学,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具有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不管你从何处着手,如果你步骤正确,你最终会谈及资本主义。因此,贯穿我著作的框架来自我们所处的时代本身。马克思主义的成分来自这个历史阶段的根本的经济动态。”⑨因此,对资本主义的时代关注是詹姆逊后现代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在当下开展对话的重要前提。
二、马克思主义是不可逾越的地平线
在后现代主义的洪流中,詹姆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推动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在当下实现对话。受萨特关于马克思主义“是我们时代不可超越的哲学”观点的深刻影响,詹姆逊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不可逾越的地平线”⑩。他认为马克思主义至今仍然是解释和分析资本主义的最佳模式。这是他与当代多数后现代理论家的不同之处。詹姆逊的后现代理论始终以马克思主义为不可超越的视域,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从生产方式变革的层面阐述后现代,使经济的结构形式在文化理论中拥有根本的重要性;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思想,寻求对文化的“总体化”理解;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历史观,从客观的、历史的角度出发,小心回应后现代主义带来的“进步与灾难”。
首先,詹姆逊从马克思主义生产方式变革的层面阐述后现代。他提出一个资本主义时期划分的假设——古典或市场资本主义、垄断或帝国资本主义、跨国或晚期资本主义。第一个阶段以资本主义国家市场的建立为标志,通过暴力进行资本的原始积累;第二阶段以帝国主义体系的形成为标志,通过打破国家市场的界限建立起世界规模的殖民主义体系;第三阶段是资本主义全球性发展史上的第三次大规模扩张。詹姆逊的时期划分假设受益于比利时经济学家欧内斯特·曼德尔的观点。他认为曼德尔的书《晚期资本主义》首次从一个有用的马克思的观点,将资本主义的三阶段理论化。詹姆逊赞同曼德尔以机器的发展为依据,来划分资本主义三阶段的观点。他引用了曼德尔的一段论述:“动力科技的基本革命——用机器制造动力机器的革命——似乎是整个科技革命的决定因素。1848年以后的蒸汽马达的机器生产,1890年代以后的电动机器化马达的生产、1940年代以后的电子及原子能装备的机器生产——这些是自18世纪后期‘原始’工业革命以后,由资本主义的生产模式引发的三个普遍的科技革命。”⑪因此,根据曼德尔的观点,资本主义的第一阶段是与蒸汽机对应的市场资本主义,第二阶段是与电力发动机和内燃机对应的垄断或帝国资本主义,第三阶段就是当下与电子和原子能相对应的晚期资本主义。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晚期”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进入“末期”,而指更彻底、更完全的发达资本主义阶段。正如詹姆逊指出:“这并不是要预告说资本主义即将终结,只是表明就资本主义而言,存在有早期阶段、马克思所说的民族资本主义阶段、以及这之后的帝国主义阶段,现在我们处于某种新的阶段——你可以将其称作全球化资本主义阶段。”⑫詹姆逊坦言曼德尔的时期划分的概念使得他的后现代主义思考成为可能。他认为这一时期划分极具马克思主义特色,因为它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无法跨越的部分——对经济结构的分析。他甚至说道:“对我而言,后现代时期的理论就是一种经济理论。”⑬在分析生产方式变革的基础上,詹姆逊阐述了资本主义各阶段的文化变迁,提出后现代主义是“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的重大命题。在他看来,资本主义三个阶段的文化的主导形式分别是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詹姆逊将后现代主义研究置于整个资本主义发展过程的框架中。他对后现代主义的思考是对第三个阶段资本主义文化生产的特殊逻辑进行理论化的尝试,而不是脱离实体的文化批判或时代精神的诊断。
其次,詹姆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思想,寻求对后现代文化的总体化理解。在吸收和借鉴黑格尔、马克思、卢卡奇、萨特和阿尔都塞等人的总体性思想的基础上,詹姆逊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总体性理论。詹姆逊最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地方在于他以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视角看待生产关系,将后现代文化置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加以分析和理解;他秉承卢卡奇对于总体性的高度重视,致力于唤醒资本主义社会的集体意识形态来抵制资本主义制度;他继承萨特的“总体化”概念,重视社会历史中的个人实践;他吸收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整体性,在坚持社会统一整体的同时,尽可能给予整体中不同层次以相对自律性和多元互动性。詹姆逊的总体性概念是一个既统一又存在差异的总体模式。他对总体性概念的坚守是区别于众多后现代理论家的重要标志。六十年代以来,“总体性”成为众多后结构主义者与后现代主义者发难和攻击的目标。他们认为启蒙以来的现代思想并没有兑现人类全体解放的允诺,反而导向了希特勒的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的红色恐怖,这主要是因为排斥差异、强求同一的极权主义总体性思想,因此他们拒绝总体化、一般化、普遍化的理论,拒绝将特殊性、差异性连成统一体和同一性的抽象原则,认为总体性是一种具有压抑性质的同一性理论。利奥塔甚至呼吁“向总体性开战”,认为后现代主义就是对总体性的元叙事的怀疑。
针对后现代主义“向总体性开战”的宣言,詹姆逊反对把总体性的哲学概念与极权主义的政治实践令人哀怜地等同起来,明确表示总体性是研究后现代不可跨越的理论视野。值得注意的是,詹姆逊的总体化思想是开放的,它以差异为前提,包含各种对抗的力量。他在把握系统和结构关系的基础上强调总体的认知,同时尊重差异、不连续性、不平衡发展和相对自律性。因此,同一性与差异性成为构成总体性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詹姆逊的总体性是一种积极的关系概念,“这种观念使差异观念重新获得适当的张力。这种经由差异造成的新关系模式,有时可能是一种已经获得的崭新且原创性的思考和感知方式;更常见的是,这个模式以一种不可能的命令的形式出现,以便在那个可能不再被称为意识的事物里获得新的变化组合。”⑭正是在这样的一种总体性的理论框架内,詹姆逊以一种总体化的方法对后现代主义展开深入分析。詹姆逊注意到了历史分期这一假设可能存在争议,正如他指出:“时期划分的假设经常引发的问题之一就是这些假设倾向于抹除差异,倾向于将历史时期视为一个巨大的同质体(两段的界限分别是一种不能解释的年代学的改变和分期记号)。然而对于我而言,这正是何以将后现代主义理解为一种文化支配物,而非一种风格的重要原因:这种观念使得各种迥异但从属的特征能够存在和并存。”⑮由此可见,詹姆逊将后现代主义视为一个力量场域,而非不能容纳差异的铁板一块。在这个场域中,各种文化的推动力——雷蒙·威廉斯曾称为文化生产的“残余”和“新兴”的东西,必须在此奋斗前进。詹姆逊以文化霸权来描述后现代主义,并不是暗示社会领域某种庞大而一致的文化同质性,而是在暗示后现代主义和其他反抗力量和异质力量的并存。他认为唯有按照某种支配性的文化逻辑或准则的观念,我们才能衡量并评估真正的差异。相反,“倘使我们没有获得一个文化支配者的某种概念,那么我们将视当前的历史为一种纯粹的杂物,一个任意的差异体、各种相异力量的共存体,其效力是不能判定的。”⑯詹姆逊认为只有将当下的历史时刻作为一个整体性来理解,才能理解社会差异,设想社会变革。他坚定地指出,“没有社会总体性这个概念(以及改造整个制度的可能性),就不可能有正当的社会主义政治。”⑰
再者,詹姆逊继承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辩证观,以一种历史的、辩证的观点分析目前的历史时刻。“后现代主义概念不是一种风格上的概念,而是一种历史概念。”⑱面对这一历史现象,他以马克思所教导的真正的辨证法来思考它的发展和改变。他以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思考为例,辩证地指出:“马克思有力地激励我们去做不可能的事情,即同时以肯定和否定的角度去思考这个发展;换句话说,去获得一种思考类型,这种类型能够在一次思考中同时把握住资本主义显然有害的特点和其不寻常的解放动力,但不会削弱任何一种判断的力量。我们将提高心智,直至能够了解资本主义是发生在人类当中的最好的也是最坏的事情。从这个严格的辨证命令堕落到采取道德立场这个舒服的行动是一个积习的、太人性化的过程。”⑲詹姆逊借鉴马克思将资本主义同时视为“灾难和进步”的辩证思维,历史地、辨证地思考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发展。他坦言后现代主义的一些方面是相对积极的,例如在现代主义常生产的诗歌小说后的叙事(storytelling)的回归;有些方面显然是消极的,例如历史感的消失。因此,詹姆逊既不认同前一代理论家,如依哈布·哈桑、福柯等人站在反现代主义的立场,欢迎后现代主义的到来,也不同意哈贝马斯等人对后现代主义所做的泛道德主义式的批判,不赞成他们在处理后现代问题时所表现出的“现代中心论”的倾向。他反对任何企图对后现代主义做出最后判断的道德化立场,因为它们既不是辩证的,也不是历史的。他认为后现代主义是一种历史现象,因此应该从历史的角度分析这一文化形态,进而对其在历史中的作用做出辩证的评价。詹姆逊诚恳地指出:“我们已置身于后现代主义文化之内,轻易斥责这个文化是不可能的,就像轻易赞扬这种文化是一种自满和堕落之举一样。”⑳詹姆逊没有因为后现代主义缺乏伟大的现代主义的乌托邦式的“高度严肃性”而谴责它,也没有给予它一种麦克卢汉式的对某种崭新的精彩乌托邦的庆祝。他始终把后现代主义当作历史状况来面对,而不是在道德上予以严厉的谴责或简单的庆贺。
三、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空间“联姻”
作为怀有历史责任感的马克思主义者,詹姆逊并没有止步于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间的对话,他以极大的热忱投入到后现代空间的理论中,尝试在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空间之间实现“联姻”,从而发展和升华马克思主义。众所周知,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组成部分。根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生产方式的变革是一切重要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它推动社会形态不断演进,由此产生不同社会阶级的斗争和消亡,阶级问题成为马克思主义关注的焦点,因而“时间”成为马恩社会理论体系中最为核心的概念,而“空间”则被长期埋没在历史唯物主义所强调的时间维度中。尽管经典马克思主义具有“时间优位”的倾向,没有建立起鲜明的、系统化的空间观点,但它仍然具有一定的空间意蕴。马克思与恩格斯曾敏锐地注意到了资本积累与地理扩张的内在关联,以此分析资本主义如何实现经济政治功能。正如哈维所言:“城市化、地理转型和‘全球化’等问题在他们的观点中占有重要的地位。”㉑尽管如此,“空间”始终不是马恩社会体系中的核心概念,并未得到系统研究,有关资本主义空间产生的原因、类型及影响的分析明显不足。
针对“空间”这一马克思主义未完成的因素,詹姆逊在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对话的基础之上,试图通过推进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空间化转向,实现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空间理论的“联姻”,来发展和升华马克思主义。詹姆逊的空间理论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补充与发展。美国批评家乔纳森·阿拉克曾指出:“詹姆逊对后现代的理解以及他的文化政治事业的关键之处,是从一种时间性的逻辑过渡到后现代的空间逻辑。”㉒詹姆逊认为空间是后现代文化的主宰,因此对资本主义的空间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一方面,他仍以马克思主义为绝对视域,将空间范畴引入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以“资本”的总体化逻辑对资本主义空间展开分析;另一方面,他视马克思主义为作用于各种理论之间的“更为巧妙的、灵活的转译机制”(translation mechanism)㉓。詹姆逊认为理论是一种个人言语或私人语言,而马克思主义“与其他大多数系统相比,是一种作用于这些语言之间的更为巧妙的、灵活的转译模式。”㉔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仍然是一种能够包罗万象的转译技巧或机制。它兼收并蓄、汲取各种理论话语,容纳互不相容甚至敌对的批评,在它自身内部为这些批评规定了部分合法性,既消解又同时保存它们。在詹姆逊的后现代空间理论中,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对詹姆逊后现代空间理论的贡献功不可没。詹姆逊曾坦言:“空间在后现代占优势这个观念归功于亨利·列斐伏尔。”㉕此外,曼德尔的分期理论、美国城市规划专家凯文·林奇的《城市意象》以及法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等也对他的后现代空间理论产生了较大影响。詹姆逊深入后现代空间,通过汲取和吸收各种理论话语,推动马克思主义的空间化转向,激活马克思主义阐释和言说当代问题的能力。詹姆逊对后现代空间的分析主要从两个方向着手:一方面,他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空间转变及其对主体生存经验的影响结合起来,探讨后现代空间产生的原因、特征及影响;另一方面,他在空间研究的基础上,致力于探索走出后现代“超空间”的文化策略和政治方略。
詹姆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方法,以“资本”的总体化逻辑对后现代空间展开分析。他认为列斐伏尔对“空间”的强调纠正了一个现代主义的不平衡,它帮助我们直面当下的生活经验。列斐伏尔认为自然空间已经无法挽回地消逝了。虽然它仍然是社会过程的起源,但是,“如果空间有一段历史,空间若具有依据时代、社会、生产模式与关系而定的特殊性,那么就会有一种资本主义的空间,亦即有布尔乔亚阶级所管理支配之社会的空间。”㉖受列斐伏尔这一观点的影响,詹姆逊认为空间与社会历史相关,是构成着的社会关系。他借鉴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和曼德尔的资本主义分期理论,将资本扩张与空间转变及其对主体生存经验的影响结合起来,提出了“资本的三个历史阶段各自生产它特有的一个空间”㉗的论断。詹姆逊将资本假定为一股统一的总体化力量,视其为资本主义空间转变的根本推动力。他明确指出:“这三个空间都是在资本扩张中,在资本向迄今未商品化的地区的渗透和殖民化的过程中,断续扩张或量子飞跃的结果。”㉘尽管资本主义三个特定阶段的空间比其他生产方式的空间更深刻地联系在一起,但由于资本扩张的手段和范围不同,这三种空间仍然有各自的特点。首先,就詹姆逊对古典或市场资本主义的空间的描述来看,这是一个欧几里德式的几何空间。这个空间“把一些旧的神圣和异质的空间重新组织成几何的和笛卡尔式的同质性空间,一个无线对等和延伸的空间”。㉙它与启蒙运动具有普遍联系,即对世界的非神圣化、对旧的神圣或超验形式的解码和世俗化,交换价值对使用价值的逐渐殖民化。鉴于此,主体的直接和有限经验能够包容支配那个经验的真正的经济和社会形式,并与之一致。换言之,主体能够感知空间的存在和位置。再看詹姆逊描述的垄断或帝国资本主义的空间,这是一个结构断裂的、矛盾激化的帝国殖民空间。它最大的特征是生活经验与结构之间的对立。这个空间已无法被主体的直接经验所触及,正如詹姆逊指出:“新的巨大的全球现实是任何个别主体或意识所接触不到的——甚至黑格尔,自不必说塞西尔·罗德兹或维多利亚女王了。”㉚因此,主体的经验只能被局限于社会世界的微小角落里,此时经验的真实性已不再与真实的空间一致了。为此詹姆逊举例,伦敦有限的日常经验的真实性不在伦敦,而在于印度、牙买加和香港。最后,詹姆逊将后现代空间命名为“超空间”。他认为这种空间是一种超越传统和现代的崭新空间,且这种空间性就历史而言可以宣称具有巨大的差异性和原创性。它指的不仅是某种新的超都市结构,也指愈来愈抽象化的全球化信息技术网状组织,其极端的形式就是跨国资本主义的权力网。因此,在这个巨大的全球性跨国的、非中心的交流空间中,民族国家不再扮演核心角色,先前两个阶段的古物被抛至身后。在詹姆逊看来,超空间具有如下特征:对距离的压制、无情的渗透(包括后现代身体)、无方位性等。而被浸透的空间独特的“无方位性”㉛是理解后现代空间最有力的指导线索。这些空间特征是历史困境的征候和表达:在实际生活经验中表现为“主体之死”,或曰主体的分裂和破碎,此时现代空间中主体的疏离已被主体的分裂取代,主体已无法获得对空间的认知性把握。超空间不同于由各种事物构成或组织的正常空间,因为主客体在此已被消解。
詹姆逊认为“空间”对于我们理解自己在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中的位置至关重要,因此在资本主义空间研究的基础上,他提出了一种“认知图绘”的文化策略,来积极寻求实现空间政治的可能性,以期走出后现代空间的历史困境,重建适合晚期资本主义的认知体系。詹姆逊的“认知图绘”的概念得益于美国城市规划专家凯文·林奇的《城市意象》。林奇将此时此地在城市中的直接感知,与把城市作为一个缺场的总体性的想象感知进行辩证分析。他认为城市的可识别性是城市构成的一个重要方面,对于市民心理具有重要影响,因为“一旦迷了路,焦虑甚至恐惧的心情使我们体会到这与我们的内心平衡和健康如此地有联系。”㉜詹姆逊将这种无法确定地理位置的“迷路”体验与后现代社会中“无方位性”的主体经验联系起来。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詹姆逊对林奇的《城市意象》只是作了象征性的利用,与其说林奇的《城市意象》启发了詹姆逊的“认知图绘”思想,不如说法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引发了他更为深入的思考。阿尔都塞认为,“意识形态表述了个人与其实在生存条件的想象关系”㉝,亦即人们以想象的形式对自己表述了他们的实在生存条件。根据阿尔都塞的观点,在意识形态中表述出来的东西不是主宰个人生存的实在关系,而是这些个人同自己身处其中的实在关系所建立的想象的关系。意识形态只有借助于主体的范畴和它所发挥的功能才能达到,所以意识形态传唤主体,主体被意识形态取代。“我自以为是我人格的主人,而实际上却是被意识形态隐性驱使的奴隶。”㉞这正是意识形态与科学的不同之处,意识形态的明确作用在于掩盖真实的矛盾。在阶级社会中,统治阶级以自身利益为出发点,通过意识形态来调整人们对其生存条件的关系,并把这些关系纳入到一种社会形态的全面统一中,意识形态由此成为一种阶级无意识。詹姆逊认为阿尔都塞将意识形态作为任何社会生活形式之必要功能的肯定观点具有一个极大的优点,即强调个别主体的局部位置与他或她所处的总体阶级结构之间的距离。在此视域下,詹姆逊将林奇构想城市经验的方式与阿尔都塞关于意识形态是对实在生存条件进行想象性置换的观点作了相似的空间类比。他将林奇探讨的城市空间的精神地图,外推倒以各种篡改了的形式存留在我们大脑里的关于社会和全球总体性的精神地图,即把林奇的空间分析外推倒全球规模的总体阶级关系上来。这种类比关系的结果在于,就像不能进行空间测绘会损害城市经验一样,如果无法进行认知图绘就会损害政治经验。因此,詹姆逊在面对后现代社会时间空间化所造成的主体实践毁灭、社会呈现出日益精神分裂的结果时,呼吁主体作为一个单一的个体为自己在跨国资本主义中进行定位。这种主体定位,不仅是从精神上或认知上将自身置于一个地理意义的系统中,最为关键的是置于一个社会系统中,从而再度获得我们因空间上的困惑而已丧失的行动和挣扎的能力。
事实上,“认知图绘”就是审美再现的问题。詹姆逊承认:“问题仍然是再现和再现的可能性的问题:我们知道我们被困在这些更复杂的全球性网络里,因为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处处明显地忍受共同空间的延伸。然而在想象中,我们无法去思考它们、塑造它们(不管是多么抽象地)。”㉟值得注意的是,在詹姆逊的语言中,他所呼吁的新的再现并不意味着回归巴尔扎克或布莱希特,亦不是把内容凌驾于形式之上。根据他的观点,“认知图绘”具有四个维度:“如何考虑它,如何想象它,如何从政治上意识到它,如何再现它——这些也许是任何认知图绘的四个方面——或者说一种概念,一种日常生活的意识形态的形象,一种正在提高或正变得明确的对现象的政治意识,并最后在可能存在或必须创造的情境中寻求再现的方式。”㊱由此可见,认知图绘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地图绘制,后者明确地再现地貌特征或各类路线,而前者所需要把握的认知对象则是难以想象的、去中心的、充满了矛盾和不确定性的庞大的全球性跨国空间。与其说詹姆逊的认知图绘是一种具体实践,不如说它是一种具有政治意义的乌托邦式思考。它体现了詹姆逊一贯以来的辩证思维——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深层同一性,我们既可以从否定的层面去批判意识形态的虚假性,也可以从肯定的层面理解隐藏于意识形态背后的乌托邦特质。这也是“认知图绘”对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的发展。在以充斥着解构、颠覆的后现代混沌中,詹姆逊苦苦探寻当下社会的出路,希冀“认知图绘美学”能够拨开后现代景观社会的重重迷雾,肩负起越来越重的文化任务。尽管他清醒地认识到文化无法摆脱经济的束缚发挥无限的作用,但他相信我们仍然可以在当下的社会现实中预想出一种积极的文化策略,因为“根据正常的马克思观点,未来的种子已经存在于现在之内,而且在概念上必须借由分析和政治应用将它从现在分离出来。”㊲詹姆逊一直在努力挖掘这些预示着未来希望的种子,展现了他独特的乌托邦守望精神。“即使我们不能想象这样一种美学的生产,但正如乌托邦思想本身的情况所示,继续想象这样一个事物的可能性,这种努力本身就具有某种肯定的因素。”㊳
詹姆逊之所以能够在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间游刃有余,是因为他没有固步自封地把马克思主义视为僵化的教条;而是选择在历史的洪流中,积极促成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间富有成效的对话。他将马克思主义视为一种兼容并包的“转译机制”,吸收和批判其他理论的内容。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比其他理论更易于介入和斡旋于各种理论符码之间,正如他所言:“如果你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是从内部去吸收别的语言体系,同时揭示这种语言的局限性,那么这也许的确是马克思主义的一种特征。”㊴从萨特到鲍德里亚,乃至又回归到阿多诺,并在这个过程中消解拉康、阿尔都塞、德里达、弗莱等理论家的观点,詹姆逊在后现代主义中不断提出“总体性”的立场,将后现代主义纳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内加以考察。他强调马克思主义“社会总体”概念的革命性质,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对每个社会的结构设想——由一种特殊因素衔接在一起的“层次”或“领域”,由此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在当下的跨时空对话。
更为重要的是,詹姆逊对社会结构的“总体性”的坚持,使他看到了马克思主义的空间隐喻。“把每个社会的结构说成为一座大厦,它有一个基础,在它上面竖立着两‘层’上层建筑,这是一个隐喻。具体地说,这是一个空间的隐喻,即表示位置(topique)的隐喻。像每个隐喻一样,这个隐喻也暗示着某种东西,使某种东西变得明显可见。”㊵这个东西便是经济基础,因此詹姆逊始终以“资本”这一总体化逻辑为起点,对资本主义各个阶段所产生的独特空间及其对主体生存经验造成的影响展开深入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一种“认知图绘”的文化策略,试图重建适合晚期资本主义的认知体系。詹姆逊对于马克思主义中“空间”这一未完成因素的重视,对于马克思主义中蕴含的巨大空间分析潜能的充分挖掘,对于从现代主义时间性逻辑到后现代空间逻辑过渡的有力推动,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补充和发展,正如他所言:“马克思主义框架对于理解新的历史内容仍然不可或缺,它需要的不是修正而是扩展。”㊶詹姆逊在坚守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构建后现代理论,发展和升华了马克思主义。他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能够为后现代主义提供观照,有助于我们理解错综复杂的后现代社会;同时他的后现代理论,尤其是空间理论,能够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有助于我们在当代语境中理解马克思主义,激活马克思主义阐释和言说当代问题的能力。
注释:
①㉗㉘㉙㉚㉛㊳弗雷德里克·詹姆逊:《认知的测绘》,见王逢振编:《詹姆逊文集第1卷:新马克思主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93页、第295页、第295页、第295页、第297页、第299页、第307页。
②③④⑥弗雷德里克·詹姆逊著,王则译:《论现实存在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7年第1期,第45-51页。
⑤弗雷德里克·詹姆逊:《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见王逢振编:《詹姆逊文集第4卷:现代性、后现代性和全球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02页。
⑦⑪⑭⑮⑯⑱⑲⑳㉕㉟㊲弗雷德里克·詹姆逊著,吴美真译:《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版,第429页、第57页、第53页、第22页、第24页、第68页、第70页、第91页、第426页、第161页、第91页。
⑧⑰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后马克思主义五条论纲》,见王逢振编:《詹姆逊文集第1卷:新马克思主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08页、第304页。
⑨⑬Fredric Jameson and Zhang,Xudong.“Marxism and the Historicity of Theory∶An interview with Fredric Jameson”,New Literary History,Vol.29,No.3,pp.353-383.
⑩弗雷德里克·詹姆逊著,王逢振、陈永国译:《政治无意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页。
⑫何卫华、朱国华:《图绘世界: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教授访谈录》,《文艺理论研究》2009年第6期。
㉑戴维·哈维著,郇建立译:《马克思的空间转移理论——〈共产党宣言〉的地理学》,《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5年第4期。
㉒乔纳森·阿拉克:《詹姆逊的后现代马克思主义》,见王逢振编:《詹姆逊文集第1卷:新马克思主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80页。
㉓㉔㊴Fredric Jameson and Zhang,Xudong.“Marxism and the Historicity of Theory∶An interview with Fredric Jameson”,NewLiteraryHistory,Vol.29,No.3,pp.353-383.
㉖亨利·列斐伏尔:《空间:社会产物与使用价值》,见包亚明编:《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47页。
㉜凯文·林奇著,项秉仁译:《城市的印象》,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0年版,第3-4页。
㉝阿尔都塞:《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见陈越编:《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53页。
㉞张一兵:《意识形态:永存的想象之境——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评析》,《学术研究》2002年第12期。
㊱王逢振、谢少波:《文化研究访谈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12页。
㊵路易·阿尔都塞:《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见杜章智、沈起予编:《列宁和哲学》,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版,第157页。
㊶Anders Stephanson and Fredric Jameson.“Regarding Postmodernism-A Conversation with Fredric Jameson”, Social Text,No.17,1987,pp.29-54.
(作者单位:上海大学电影学院)
责任编辑 佘 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