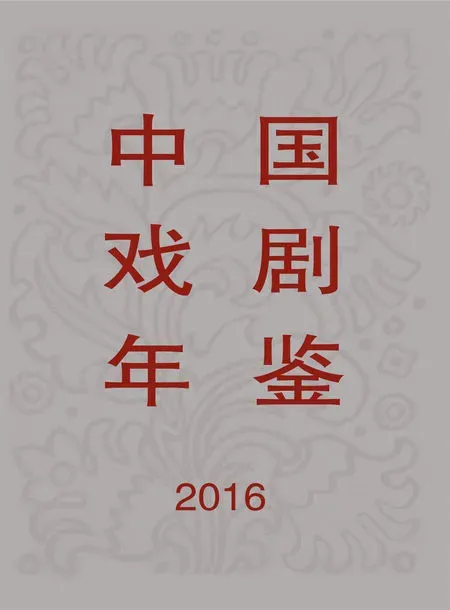剧本“荒”还是剧本“慌”
颜全毅
近几年来,戏剧界,特别是戏曲行业“剧本荒”的说法甚是流行,许多媒体甚至业界人士都再三发声强调:戏剧剧本数量稀少、作品参差不齐,编剧人员青黄不接。这些声音似乎表明剧本荒芜问题已经迫在眉睫,需要全社会重视作品创作,培养更多编剧人才。重视与培养自然十分紧要,但关于“剧本荒”的一些说法并未切中当下戏剧创作的肯綮所在,就笔者目力所及,眼下戏剧,特别是戏曲编剧人数与剧本创作相对数量并非太少,与当前戏曲舞台的实际需要相比也没有巨大差额,不断扩招的艺术院校相关专业还源源不断培养出编剧专业后备人才。所谓剧本荒,更多是剧本上演难、获奖难、出精品难、供需对应难等等,这其中,更值得注意的是排演剧目的功利性目标与戏曲创作艺术特性之间的协调难;创作主体对于剧本所承担的功能目标,时间、速度与剧本创作沉淀、过程的两难;对成名剧作家涸泽而渔、青年创作者渴望成长之间的人才使用与培养两难。可以说,剧本荒的实质是剧本“慌”,处在上述难题语境,戏剧创作因而呈现出来的一种慌乱和无措心态。
剧本慌首先慌在命题的急功近利上。剧本固然是为舞台表演而服务,但归根结底也是一种文学创作,文学创作是一种生命体验和情感积累,需要有灵感的促发;戏曲创作又有其特殊性,剧种声腔作为剧本的呈现方式,演员作为剧本的呈现主体,三者之间需要有至少的熟悉关联,能形成默契力量则是成功的基石,因而,戏曲创作选题和文本良性起因应是作者的文学灵感以及和剧种、演员的熟悉默契。回望以往,民国时期京剧创作大抵是这种路数,编剧、剧种、演员有深厚的渊源关系;显然,这样的创作关系在当前的戏剧创作环境中逐渐变得少见,更多是选题在前,“点将式”的作者遴选,剧目创作的主管方和院团以“押宝”心态选择编剧,剧本创作更多是技巧性而非感怀而作。实事求是,“命题作文”并非坏事,也向来是戏剧创作常见模式之一,气质不乏优秀作品的出现,但太过频繁和几乎成为绝对选择的命题写作样式,常使编剧更多激发了技巧对于剧本创作的能动,难免缺乏潜入生活和生命情感的深入与细致,带来创作意识上的“慌”,编剧频频流于技巧层面上的熟能生巧,却难能在深入采风考查中寻找到每一个题材的个性符号;更有甚者,过于自信的创作心态,对剧种特色风范、演员的阵容和个性都未做虚心细致的体味了解,也未对题材做深入开掘,全凭技巧和经验驾轻就熟,这就使得作品缺乏个性与特色,容易流于一般和粗糙。当然,在当前戏剧创作环境中,相比起来,一度创作还往往是投入精力时间最多,因为剧本立项总要经过层层论证、研讨、修改,编剧也需要有一定的题材熟悉度和材料掌握才能应付裕如,二度上,许多导演、音乐甚至连最基本的采风、交流都免去,全凭自己的感觉和经验任意挥洒,这样出来的剧目自然更为局促和重复,许多导演作品的相似度实在令人瞠目。
其次,剧目生产心态和过程之“慌”。许多作品不是顺时顺势的产物,更不是在市场中几经淘洗锤炼的作品,不少匆忙上马,一旦没有获得理想成绩与反响便急急收兵,导致打磨修改的机会很少,使得花了许多物力财力精力、原本有可能留下的剧目,仍旧以粗糙的面目黯然消失,这无疑是剧目生产的一个浪费。剧目创作和一般诗歌、文学等纯文本创作不同,更是一个集结导演、表演、音乐、美术各方面力量的综合艺术,一项短板很可能导致一出优秀作品在舞台呈现上功亏一篑,因而,许多编剧费尽心思、反复推敲的剧本,因为呈现的不够理想,丧失了进一步精致化的可能。而从历史来看,即使如京剧大师杨小楼、梅兰芳、程砚秋等人,也并非每一出新戏都遽尔成功,杨小楼整理的《灞桥挑袍》、《楚汉争》因剧本原因不甚理想,演出很少,《野猪林》、《霸王别姬》却是经过一次次反复打磨,才成为经典。梅兰芳、程砚秋的《宇宙锋》、《贵妃醉酒》和《锁麟囊》等,也有在舞台上不断修改完善的过程。当今新戏创作往往在前期编剧过程中反复修改,但这样的修改都是编剧一人之力,真正立到台上,才能看出不足,如果不给出“台上见”的时间和反复打磨的过程,能够成为保留剧目的作品自然少之又少。
当然,大多业界人士也知道,现在许多地方戏曲剧种离市场挺远,新剧目创作难与票房和观众口碑挂钩,说白了,更多是为“节”和“奖”而生而兴。良性的“节”和“奖”确实为创作的繁荣推波助澜、意义重大。问题在于,当许多原创剧目不是来源于院团有效的艺术积累,经过观众再三检阅,而只是现行体制下政绩的快速反映,在主管领导当政期内,常常要在很短的时间里快速成型、快速上台的作品。这样的剧目打造背景,注定剧目生产基础的“急切”心态,快速或者一次成型成为精品自然是最佳选择。于是乎顺理成章,为了保证(至少从主管领导和投资方来说)剧目能有一定的艺术水准,或是能有更大的获奖可能与美誉度,主管方或投资方通常会选择行业大腕与知名编剧,不敢也没时间去培育、打磨有一定风险性的年轻或本地编剧的作品。显然,更多并非经过长时思考蕴育和淘洗甄别、而是在短时指定创作的快餐剧本搬上了舞台,参加了难得的各种汇演机会,这种剧目生产时间上的“慌”,使得出精品更难。
由着以上两点,产生了剧目创作生态环境上的“慌”,主要表现两个方面,一个是本土编剧与全国性著名编剧选择的两难;一个是青年编剧的着慌和流失。前者的两难说难也不难,戏剧创作其实并无“金牌编剧”这一说法,优秀作品来自才华和积累,题材开掘和生活积累显然是其中重中之重,一个优秀编剧穷其一生或许只有几部作品蜚声剧坛,称得上精品,而一些本土编剧可能一辈子默默无闻,却能以一部植根个体生活经历的剧目绽放出极大光彩,例如湖北十堰的忽红叶,当年就以反映农村生活的《丑嫂》带给剧坛十分惊喜,剧中饱含的艺术浓度,是剧作家大半辈子人生感悟的体现。地方剧目生产应该依赖本土创作,但也确实存在一些本土编剧眼界不够开阔、创作思维老化的问题,引进奋战一线的知名编剧,其实也是开拓思路、有所借鉴的意味,是否会对本土编剧的培养产生负面影响,也是一个“度”的把握问题。
但年轻编剧的成长问题显然急迫焦虑许多,一个戏曲编剧的成长过程往往是漫长的,需要有“不慌不忙”的知识积淀与不断实验的丰富经验,在与舞台、剧种、演员的密切接触中,逐渐了解掌握创作要领。整个创作环境如此慌忙,年轻编剧的成长空间因而更为逼仄,机会如此渺茫,未来是否能提供年轻人可供期许的成长空间,只怕很难直面。而在剧团不断向企业改制的环境下,正式进入剧团从事创作或为创作蓄积的机会极少,连基本生存都成为问题,谈何坚守?如何坚守?作为中国戏曲学院戏文系教师,我们以培养戏曲编剧为己任,但面对现实,也不敢轻易鼓励年轻学生死守行业。现在能够继续守在戏曲编剧行业的年轻学生,都是有着强烈执着的爱好,不甘心放弃。我有一个年轻学生,坚决回到了家乡的剧团,一年多来帮着剧团年轻演员整理改编和创作小型剧本,为剧团排演的大戏充当编剧助手、在现场辅助导演工作,其才华和能力深得剧团上下肯定,但剧团极其有限的编制只能先给演员和乐队,这位学生迄今没能解决编制,一个月靠临时工一千八工资养活自己,他只能考虑,如果在剧团再看不到前景,只好和大多同学一样,回到北京,从事网站或影视编辑工作。确实,如果我们社会一直没有机会和机制去解决,年轻戏剧编剧没有成长发展空间,导致他们对未来真正的慌张绝望,剧本“慌”会变成真正的剧本“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