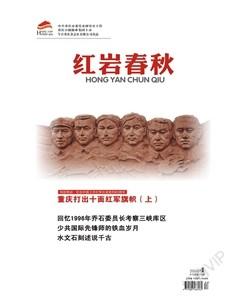难忘父母心和手足情
冯秋群
3岁时,我被送进香港的育婴堂,继而进入香港的粉岭保育院及元朗保育院。随着战火的蔓延,我跟随保育院辗转流离,经贵州来到四川。1946年的夏天,我又随重庆江北水土沱保育院合并到了重庆歌乐山第六育幼院(即歌乐山第一保育院)。
妈妈们视保育生为亲人
保育院的环境很好,对于之前长期居住庙宇的保育生来说,这里就好像是仙境。所有的建筑都是新盖的灰瓦黄墙平房,从大门拾级而上,进入一个开阔的大院,院子中央有一个精心培植的大花园,色彩斑斓的花朵在碧草绿树的陪衬下显得格外美丽。花园周围及道路两旁种植着整齐茂盛的冬青树,还有不少法国梧桐。每到夏天,梧桐树上知了齐鸣,令人心醉。保育院的大礼堂(兼食堂)正对着大花园,大礼堂的山墙上写有“霭龄堂”3个大字,由此可见宋氏三姐妹对战时儿童保育事业的关怀。
最令我难忘的不是保育院的优美环境,而是爱院如家并视保育生如亲人的保教人员。我们的院长徐篆,个子不高,皮肤白皙,端庄文雅,和蔼可亲,同学们都亲昵地称她为“徐妈妈”。徐妈妈热心儿童保育事业,她和两个孩子都投身其中,深得全院师生的敬重和爱戴。记得徐妈妈50寿辰时,恰逢元旦,全院还热闹地庆祝了一番,节日的盛况至今历历在目:会场内外灯火明亮,装饰五彩缤纷,喇叭里传出美妙的乐曲,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喜悦。当天的庆祝晚会上有一段自编自演的歌舞,歌曲中唱道:“今天是元旦日,又逢院长五十庆,又演戏又吃肉,多么高兴,嗯,多么高兴,嗯唉哟!”
我的班主任刘妈妈,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叫刘力生,其实他是男性,只因他非常诙谐,又和蔼可亲,所以同学们都称他为“刘妈妈”。他教过我们好几门课程,有国文、算术、常识等。他备课认真,讲课深入浅出。有一次上常识课,他讲到全国各省会时,同学们苦于记不住,为了帮助大家加深记忆,从来不唱歌的刘妈妈竟然自编了一个歌诀:“吉辽黑热察绥、晋陕甘冀鲁豫、苏浙闽赣鄂皖川湘、滇黔粤桂青宁新康……”使我至今还牢记不忘。刘妈妈平易近人,但上课时却严格要求,从不姑息迁就。一次,同学吴蕾香在课堂上躲着玩蚕宝宝被刘妈妈看到了,他严厉地没收了蚕盒并扔到教室外面。吴蕾香伤心极了,事后模仿诗人高兰的诗作《哭亡女苏菲》,为蚕宝宝写了一首祭文《你哪里去了呢,我的蚕宝宝?》。当我们把祭文念给刘妈妈听时,他会心地笑了。
刘妈妈个子比较高,经常穿着一件褪了色的蓝布长袍,走起路来步子迈得很大,长袍后摆也随之飘起来。一次,有两位同学走在他的后面,看到飘荡的长袍便顺势一人抓住一个衣角,嘴里调皮地喊着:“刘妈妈!给你牵纱。”刘妈妈回过头来风趣地说:“还等10年!”两位同学反应过来后连说:“刘妈妈好坏!刘妈妈好坏!”刘妈妈又报以会心一笑。那时候,刘妈妈大概30多岁,但一直独身。有一次上国文课,他朗读贺知章的诗作“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其语调充满激情,令人深受感染。课后同学们问刘妈妈“是不是想家了?”刘妈妈巧妙地转移话题,只字不提家里的事。
曾经,我们在刘妈妈的宿舍里看到一本从来没见过的《观察》杂志。有时候他会给我们讲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如王若飞、叶挺的事迹,对我们进行潜移默化的教育,使我们的思想豁然开朗,得到启迪。
大家庭的温暖永难忘
我们的音乐老师徐大哥,他实际姓赵,名叫赵宗信,他是院长徐妈妈的儿子,所以我们都称他为徐大哥。他是音乐学院毕业的高材生,年轻活跃,据说常到电台录音。这样一个大学生来教小学,真是大材小用,但徐大哥非常热爱所从事的工作。他教导我们说:“音乐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民族文化素质的标准。”他给我们介绍了不少世界名曲,如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田园交响曲》,舒伯特的《摇篮曲》《小夜曲》等。他教给我们的歌曲都是进步健康的,如《卖布谣》《新中国的儿童》等。尤其是《新中国的儿童》,里面的歌词令人振奋:“我们的身体强壮,我们的行动光明,真理,爱劳动,努力学习不放松,为民主,为和平,团结一致去斗争。我们是新中国的儿童,我们是新时代的主人。”
徐大哥经常组织保育院的文娱活动,如文娱晚会、歌咏比赛等。一次,全院举行独唱比赛,徐大哥让我也参赛。我说:“我既不识谱,也没有唱过一首完整的歌。”徐大哥说:“我听你说话就知道你一定能唱歌。”在他的鼓励和指导下,我参加了比赛并得了奖,奖品是一条红绸发带和一张有徐大哥落款的贺年卡。我参赛的歌曲是徐大哥挑选的,歌名是《追寻》,歌词是这样的:“你是晴空的流云,你是子夜的流星,一片深情紧紧地封锁着我的心,一线光明照耀着我的心。我哪能忍耐住啊,我哪能再等待哟!我要追寻,我要追寻,追寻那无尽的深情,追寻那永远的光明。”这支歌大概也道出了徐大哥对光明的憧憬,对未来的深情吧!
保育院还组织各种学习活动,如讲演比赛、作文比赛等。记得有一次的作文比赛题目是《暴风雨夕》,我也参加了比赛并得了奖,奖品是一副木质三角板。
保育院也组织一些义务劳动。譬如组织全院同学参加植树活动,我栽种了一棵苦楝树,种好后还在树枝上挂了一个小牌子,牌子上写着树的种类、栽种日期、栽树人的姓名。
当年,保育院办得有声有色,颇有名气,不时引来外宾的参观。有一次是英国的克列普斯夫人来了,客人频频点头,笑容可掬,对育幼院很是赞赏。
作为保育生,虽然我们失去了父母的抚爱和家庭的温暖,但老师的父母心和同学的手足情,一直滋润着一颗颗幼小的心灵。时至今日,每当我看到自己这双完好的脚,就情不自禁地想起他们。那是在一次荡秋千的活动中,当我荡得最欢快时,不慎失手从高空摔了下来,霎时不省人事,同学们争着把我背到了院医务室。苏醒后,看到脚肿得不像样子,且巨痛钻心,我难过极了,眼泪簌簌地流下来。我含泪问医生:“我的脚会好吗?”院医袁芝英老师亲切地望着我,肯定地点点头。在她的关怀和精心治疗下,我的脚伤终于痊愈了。
1947年夏,我们这个年级的同学面临毕业。通过测验,前十名同学被保送到国立荣昌师范学校。我们依依难舍地告别了敬爱的师长,告别了朝夕相处的兄弟姐妹,也告别了童年的家——重庆歌乐山第六育幼院。
(责任编辑:韩西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