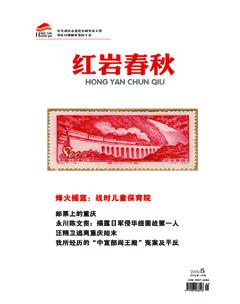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历时最久的保育院
邱月杭++芝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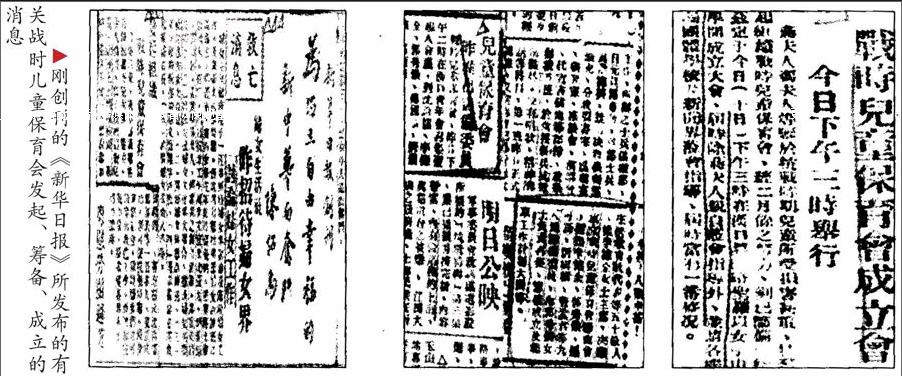


抢救、教养战区难童,起于1938年3月,止于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9月,历时8年又5个月。1946年9月后,全国几十所保育院除陕甘宁保育院在党中央直接领导下继续存在外,均被撤销。而重庆歌乐山保育院自1938年5月1日“汉口第一(临时)保育院”至1951年10月以“歌乐山保育院”院名结束,竟然历时13年又5个月。因此,可以说:重庆歌乐山保育院是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历时最久的保育院。
难童从武汉撤至重庆
1938年3月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成立时,正值日寇进抵黄河危及郑州、开封,总会理事会常务委员曹孟君、沈兹九亲赴前线,拉开了战区抢救难童的序幕,在郑州一带收容逃亡儿童300余名。4月,总会理事会常务委员唐国桢和候补常务委员徐镜平又率领冯云仙(西康保育分会理事)、于汝州(总会保育委员会委员)、汪树棠(后任汉口第一临时保育院副院长)等到陇海铁路沿线抢救儿童400余名。4月下旬,在日寇集结重兵进犯徐州的危急关头,曹孟君偕同冯光灌(总会秘书处秘书)等亲赴前线,在烈火硝烟中寻觅受难儿童,随军突围,经八昼夜,脱险带领100多名儿童回武汉。以上战区抢救的儿童就是汉口第一(临时)保育院5月1日建院的基础。汉口第一(临时)保育院也成为战时儿童保育事业在日寇侵华战争的炮火下建立起来的首个保育院。
5月中旬,由于武汉受到日机轰炸的威胁,且日军以海陆空优势进逼九江,危及难童安全,汉口第一(临时)保育院奉命撤离,开始向重庆转移。28日,由副院长汪树棠护送的首批100余名儿童抵达万县,不久,第二批、第三批也先后到达重庆,先是住在万寿宫临时保育院,后陆续进入战时儿童保育会四川分会第一保育院(简称“川一院”,因院址在歌乐山,亦称“歌乐山保育院”)。
值得一提的是,至1938年10月最后一批在院儿童撤离汉口的7个月中,汉口第一(临时)保育院共计接收转运儿童约8000名,分送香港、广东、湖南、贵州、四川和鄂西均县等各地保育院。战时儿童保育会发起人之一,著名剧作家、诗人安娥发表在《妇女生活》第六卷第四期的《孩子们到四川去了》一文提及:“战时儿童(汉口第一临时)保育院陆续有五百名儿童送到四川第一保育院去了。”
模范保育院
川一院坐落在歌乐山高店子镇左侧的山坡上。进大门,一条4米宽的石板大道,由低向高把大院分隔为西区(教学区)和东区(生活区)。西区有小花园、凉亭、6排大教室、办公室、实验室、标本室、图书馆和可容纳600多人的大餐厅;东区有澡堂、理发室、草顶方形大礼堂、8排学生宿舍(每排8间,每间4张双人床)、大操场、小农场、小工厂等。还有一个拥有10余床位的病房和医务室的小独院。
保育院接收的孩子有家的固不少,但流浪街头的数目更多。“无论谁大概都能想象到集一堂没有教养、没有拘束,终日为追求二餐而生活的孩子的情况吧?身上的污臭,几使人鼻为之塞;吵嘴、叫骂、哭号,几使人耳为之震聋;摔跤、打架,甚至头破血流,更使人夺目惊心……‘集体生活在他们脑中根本不会存在过……”从刊载于1938年5月16日《妇女生活》署名“永沂”的这篇文章可以看到,刚进院的孩子多么让人头疼。
进入歌乐山保育院后,通过文化测验,孩子们被分配到不同的年级。他们所学的文化课,大抵与外面的小学课本相似,除语文、数学外还有社会科学及自然科学常识,教学方法也很民主。除了文化学习,老师还对孩子们进行抗日救国教育,教唱《保育院院歌》、《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打回老家去》等歌曲,组织战时儿童团在周边地区宣传抗日。经过保育工作者耐心的说服、恳切的教导,孩子们逐渐改掉了相互打骂、自私的恶习,在学习互助中进步着。他们变得团结而自律,爱国家、爱民族,会劳动、有技能,讲卫生、锻炼身体,艰苦朴素、吃苦耐劳。
1939年1月,《新华日报》记者田禾实地走访后发表了《歌乐山保育院印象记》,称这里是“三千尺上的自由天地”——这里没有一点猫鼠式的学校管理,几百个小孩的脸上一天到晚都是挂着笑脸的。文中提到,孩子们自己办了壁报、图书馆;最有趣的是会客室旁边的小公园(即巴山公园),它完全是由孩子们开辟出来的,铺路、筑鱼池、砌草坪、建亭子,连监工员都是孩子;“引人注意的是每个假山上都装设了大炮,他们还要建设防空壕,飞机场,江防要塞……这是他们创造新中国的试金石”;小公园后面的小牧场养了兔子、小羊、鸭子、鸽子,每天轮流两个同学来管理。
安娥在《歌乐山上的保育院》一文中还提到,每天睡觉之前,孩子们在自己寝室里开半个钟头的晚会,主要任务为每日生活的自我检讨。“有一次扩大晚会上,曾解决过这样一个有意义的问题。当孩子们初上山的时候,省份之见非常浓厚……‘打群架的表演每天都有。后来他们在这次扩大晚会上,决议说:‘大家都是中华民族的儿童,大家都是被日本军阀炮火压迫下的流浪者。大家的遭遇一样,大家的境遇一样,大家的生活一样,大家的目的是一个,大家的敌人是一个,大家的工作是一个。因此彼此都不要分省份,不要打架。中国人的拳头,中国的武器,只是打击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走狗们的!”安娥认为,“保育会……事实上给中国儿童教育开辟了新的路”,“由保育会儿童做起,将形成全国集体生活的儿童的营垒,建立起儿童抗建工作的核心作用”。
从保育会的文件、工作计划、报告,报刊消息以及某些当事人的回忆中,我们还可以看到,歌乐山保育院的儿童曾组织小分队参加“五三”、“五四”大轰炸的抢救工作;为前方将士节食义卖,募寒衣、防毒面具,缝制棉背心;到学校、军营、街头、伤兵医院宣传抗日救亡及慰问;到广播电台演唱;给前方将士及华北游击队写慰问信;办群众夜校,教大众识字读书;调查烈军属家庭状况;自己种菜;缝衣、打草鞋;下山背米运物;办小工厂制肥皂;以工代赈修路;挖建防空洞……可以说,保育工作者所选择的陶行知倡导的抗战教育(儿童必须过战时的生活,必须为抗战服务,必须在抗战的洪炉中锻炼)及启发创造性教育方法取得了初步成效。
歌乐山保育院取得的一系列开创性成绩、经验,被保育总会理事长宋美龄誉为:“堪称模范保育院!”不仅通过总会及时推向各地保育院,还吸引了热心捐助或关心战时儿童保育的美、英、法、苏、印、缅等国际友人来院参观访问。如1939年8月,蒋介石、宋美龄、宋霭龄、孔祥熙等陪同印度总理尼赫鲁来歌乐山保育院参观。国内的社会名流、专家学者经常到歌乐山保育院,如周恩来、邓颖超常来此与师生相见谈心;发起、推动儿童保教工作的冯玉祥、李德全夫妇住处与保育院一墙之隔,更是常客;邓颖超、李德全、安娥、王昆仑等常来保育院做时事、抗战演讲……由此,歌乐山保育院成为保育总会的保教工作实验及示范场所和对外宣传展示保育事业的窗口。
保育院里的妈妈们
孩子们常会在早晚唱《战时儿童保育院院歌》:“我们离开了爸爸,我们离开了妈妈,我们失去了土地,我们失去了老家……”能够关怀和照顾孩子们的,是战时儿童保育总会和战时儿童保育院的妈妈们!
然而,当时保育工作者面临的困难很多。院长曹孟君在《克服困难,迈步向前》(见于1940年8月《妇女新运》第二卷第八期)一文中写道:“经费困难:米价暴涨时,孩子们连饭也吃不饱……固定的预算应付不来日在高涨中的物价;孩子们难于管教,来源复杂……语言都不易一致,教育程度不齐……工作人才难于寻找,而且流动性太大……”其中,最让人震撼的一句话是:“多少个负实际工作责任的人在工作过分重负下,损失了健康,多少人在叫苦、灰心,有些甚至因辞职不准,而困难又无法克服,竟想以自杀来解决问题……”就是在这样艰难的情况下,妈妈们不求回报地付出着。
早年投笔从戎参加青年远征军、后又参加解放战争的原增鑫在《一碗阳春面》里深情回忆了他在歌乐山保育院的一件往事。当年,他因一个恶作剧没能及时承认错误以得原谅,赌气以一天不吃饭来赔偿盘子摔坏的损失。晚上,曹孟君院长知道后,把他叫到了宿舍,心疼地拉着他的手说:“你才12岁吧?在家时有爸爸妈妈疼你吗?……要是你妈妈一天见你不吃饭,该怎么想啊?……现在我就是你的妈妈……”当原增鑫抬头看见曹妈妈面颊上挂着泪珠,并双手把桌上一碗热气腾腾的阳春面捧到他面前时,这个在保育院生活了1年成为“硬汉子”的孩子,强忍的泪水禁不住簌簌长流!
曹孟君是1929年在北大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老党员,是战时儿童保育会的常务理事,1938年9月担任歌乐山保育院院长,孩子们亲切地称她“曹姑姑”。她于1939年7月在反共高潮中被迫离院。后来成为散文作家的院童魏福茂在纪实文学作品《风雨故人情》中这样描述当时离别的场景:
同学们可怜兮兮眼巴巴地痴望着即将离去的曹院长……在曹院长即将走近站在队列一侧的李梅时,突然,李梅同学从队列里冲出,扑向了曹院长的怀抱,她大声地嚎啕着:“好妈妈呀!是您把我从敌人狂轰滥炸的瓦砾堆里救出,没有你们亲自到徐州前线抢救我们,哪有我们的小命啊,哪有我们今天的一切啊!?”……引发队列里的孩子都大声痛哭起来……李梅边哭边哀求着,“曹姑姑!你再抱我一次吧!”……曹姑姑弯下腰,展开双臂,将李梅紧紧地抱在怀里……就在曹院长一只脚踏上汽车之时,只见马健德(在曹院长的启发下以后上战场参加远征军,成为美术家、散文作家——作者注)举起了手臂,手里拿着一个小本子挤进车门,大声的叫喊:“曹姑姑,请您给我写下几句话吧!”……(曹姑姑)郑重地在小本子上写下了“马健德,在你的图画中有祖国完整的地图吗?!曹孟君1939.7.”
曹院长的离院欢送会是由新到任的刘尊一院长主持的。刘尊一也是早期共产党人,曾担任北大救国会宣传部长,1927年春被捕入狱,在刑场上获救,后赴英国留学。抗日战争爆发后,刘尊一回国积极投身救护训练等抗日救亡工作。当曹孟君院长迫于在歌乐山保育院使用《抗战建国读本》(由“生活教育社”地下党员孙铭勋、戴伯韬、陆维特为保育会编写,1939年蒋介石来院视察后,禁止使用该读本——作者注)的压力不得不撤离时,保育总会常务理事邓颖超推荐刘尊一继任歌乐山保育院院长。她在歌乐山保育院积极推行“抗战教育”,将全部薪俸捐给了保育院。同时,1938年底由党派到院里任教导主任的地下党员酆道淳继续留任。酆身任歌乐山地下党支部书记和歌乐山保育院地下党小组长,继续推行“抗战教育”,直到1940年10月刘尊一、酆道淳均以“异党嫌疑”再次被迫离院。
此后,非党的原总务主任姜榆之暂代歌乐山保育院院长,保育总会派遣教育界民主人士徐篆充任总务主任遗缺。徐篆带上她在川七院共事的密友搭档、地下党员傅淑华到歌乐山保育院就任,虽因异党嫌疑受监视,不久即趁病离院,但对保育院的情况有了了解。1942年1月歌乐山保育院由“川一院”改为保育总会直属的“直一院”后,面临办院的艰难时期。1944年11月,由保育总会邓颖超、李德全推荐,再次任命徐篆接任歌乐山保育院院长,南方局妇委派地下党员傅淑华继续辅佐徐篆,出任总务主任。徐同时带去了直三院共事的一批地下党员和进步教职员工。中共在歌乐山保育院新建了地下党支部,扎下了深根,直至解放。
当年的院童吴珊1968年去看望徐篆院长,以谢养育之恩。1945年只有两岁的她从贵阳托儿所转到歌乐山保育院,当时她患了火巴眼,眼睛又红又肿,耳朵也聋,还不会说话,可怜兮兮的样子让徐篆非常心疼,便将她放到自己身边亲自料理饮食起居。后来吴珊健康长大,参加了工作。在再见徐篆的一瞬间,“我控制不了自己的情感,立即投入到徐妈妈的怀抱里,不停地喊着徐妈妈,徐妈妈,泪水也不住的流淌。徐妈妈不停地抚摸着我的头说:孩子别哭了,别哭了”。尽管那时她已是二十几岁的大姑娘,但住在徐篆家,“半夜里徐妈妈还要起来给我掖被子,一股暖流,使我感到好像又回到童年时在她身边的日子,禁不住热泪夺眶而出湿透了枕巾……”
在歌乐山保育院还有一位“男妈妈”叫刘力生,孩子们叫他“刘妈妈”。刘妈妈严格而又和蔼可亲,他知识渊博,说话诙谐风趣。当年的院童冯秋群回忆说:“刘妈妈个子比较高,经常穿着一件褪了色的蓝布长袍,走起路来步子迈得很大,长袍后摆会飘起来。有一次两位女同学走在他的后面,看到飘起来的长袍后摆便顺势一人抓住一个衣角,嘴里调皮地喊着:‘刘妈妈!给你牵纱。刘妈妈回过头来幽默地说:‘还等10年!”冯秋群还提到,刘妈妈教过国文、算术、常识等等,他备课认真、教课深入浅出,为了帮助同学们记忆28个省名,自编歌诀:“吉辽黑热察绥,晋陕甘冀鲁豫,苏浙闽赣鄂皖川湘,滇黔粤桂青宁新康。”直到解放之后,孩子们才知道他们敬爱的“刘妈妈”是歌乐山保育院地下党组成员之一,也是歌乐山保育院最后一任院长。他参加过顺泸起义,曾担任中共泸县、内江、乐山县委书记。1939年进入战时儿童保育战线,先后在川七院、直三院、歌乐山直一院、社会部第六育幼院(1946年秋,战时儿童保育会结束,直一院移交社会部)任教。重庆解放后,他参加了人民政府对第六育幼院的接管,并于1949年12月1日接任院长。1950年5月1日,保育院正式挂牌恢复“歌乐山保育院”院名。1951年10月,由于院址用作抗美援朝负伤归国志愿军的疗养院,在院幼童移交重庆市儿童教养院,刘力生调任重庆市政府机关文化学校副校长、南开中学政治教员兼教职工支部书记。
在歌乐山,还有一位不是院长却胜似院长的傅(淑华)妈妈。在红岩村,周恩来、邓颖超亲自交代给她的任务:一是以总务主任身份全力辅佐进步儿童教育家徐篆任院长;二是一旦独山失守将全部儿童转移大巴山。傅妈妈对孩子的爱,试举一例:歌乐山保育院后期改为“社会部第六育幼院”,在孩子们升学路绝时,她开办“初中班”教育未能升学儿童,压下了教育部“不照保育生办理”和社会部“让毕业学生回家”的文件,当不能升学儿童怪罪于她、之后又得知真相时,个个抱头痛哭!
保育院走出的人才
大约是1939年六七月间,歌乐山保育院来了4位客人:帅昌书、魏东明、常学镛、皮晓芳。原来,他们是受陶行知所托,为创办育才学校选拔具有特殊才能的儿童。1939年7月20日,36名从重庆歌乐山保育院个挑个选出来的儿童在北碚北温泉参加了育才的开学典礼。不久,陆维特、孙铭勋、张望、章泯等人在四川境内的直一院、川二院、川五院、川七院、直三院等多所保育院、教养院、慈幼院选拔的特长儿童已达168名,于8月初转移到育才新校址——合川草街子古圣寺。
歌乐山保育院选拔进育才学校的儿童前前后后有40多名,他们被分进文学组、音乐组、戏剧组、绘画组、自然组、社会组、舞蹈组等。翦伯赞、贺绿汀、郭沫若、夏衍、田汉、阳翰笙、刘白羽、沙汀、任光、艾青、安娥、范继森、丰子恺、陈烟桥、章泯等名家都曾到校无偿授课或作专题讲座。
在老师的精心培育和自己不断努力下,歌乐山保育院走出了不少在各行各业有突出建树的孩子,如:中国电影剪辑“第一把剪刀”傅正义,上海音乐学院声乐系教育家王为,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教授伍必端,中央乐团副团长、首席小提琴演奏家杨秉孙,地貌专家龚国元,核工业动力专家黄利富,冶金高级工程师张楚骧,等等。
(作者邱月杭系四川省棉麻集团公司退休人员,1940-1945年曾在北泉慈幼院接受过战时抚育。相关资料及图片来源:《战时儿童保育会歌乐山保育院纪念·研究专集》)
(责任编辑:杨山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