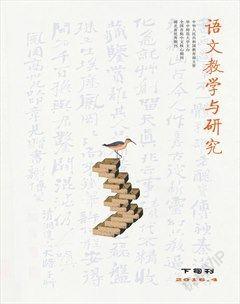远逝的弹硌路
叶永烈
又去欧洲。漫步在旧城区,我的双脚踏在用方形花岗石铺成的路上,有着时光穿越到中世纪的感觉。在一个个矗立着横刀立马的铜雕的古老广场,那些方石则铺成鱼鳞状图案,像粼粼水波般漾开来。方石仿佛打开我的记忆闸门,哦,记起上海那远逝了的弹硌路。
弹硌路是上海话。硌路,就是街道,点睛之笔是那个“弹”字。弹硌路是用花岗石块铺成的,只是那花岗石块不像欧洲那样打磨成平平整整的方形,而是大体上加工成上大下小的方锥形石块,不仅石块表面不平,而且石块之间有很大的缝隙,所以车子从上面驶过的时候,车轮不由得蹦蹦跳跳,于是得了“弹硌”路之名。也有人“音譯”为“台阶路”,显然不妥,会被人误以为是铺了台阶的路。
对于上海的90后、00后来说,已经不知弹硌路为何物。然而对于我来说,弹硌路显得那样的亲切,是一种强烈的记忆符号。那时候,我家住的弄堂,就是一条五、六米宽的弹硌路。我家门口是两米宽的用红砖铺成的“上街沿”,而与“上街沿”相连的就是弹硌路。我天天走在弹硌路上。
不光弄堂里是弹硌路,我的工作单位——电影厂所在的斜土路,也是弹硌路。我骑自行车上班,行进在弹硌路上,充分领教弹硌路的“弹”,所以我不敢给车胎打足气,也不敢在弹硌路疾驶,以免“弹”得太厉害。那时候的斜土路不全是弹硌路,有的地段没有铺石块,成了烂泥路,所以同事们笑称斜土路“又斜又土”——其实斜土路是从斜桥到土山湾而得名的。在下雨的时候,我充分体会弹硌路的优点,因为弹硌路泄水快,不积水,而骑车进入烂泥路,泥水飞溅,又脏又滑,一不小心就会摔跤。
那个年月,上海人的晨曲——伴随着一声声高亢的“马桶拎出来”的呼喊,是粪车推过弹硌路而发出的低沉的辚辚之声。夜幕下的上海人,饭后茶余走出逼仄的弄堂小屋,他与她开始那充满小资情调的荡马路,荡的是弹硌路。当然,对于穿高跟鞋的小姐而言,荡在弹硌路上那清脆的橐橐声固然赏心悦耳,可是在黄晕的路灯下却时不时要留心足下,以防偶尔有三两块异军突起的路石崴了脚,好在那个年月穿高跟鞋者毕竟属于“稀有元素”。
有一回,家门口的弹硌路翻修,正值星期日,我端了张小竹椅和儿子并排坐在“上街沿”,细细观察弹硌路的铺建过程:在清理路基之后,先是用小车倒上黄沙,铺平,然后工人把那些上大下小的方锥形石块,整齐地“插”在黄沙上。路面上方拉着一根细细的尼龙线作为水平线,工人用小铁锤敲打着石块,使石块紧紧进入沙层。有时候觉得这石块太大或者太高,就挑选着换上另一块,直到路面平展展为止。一边铺,一边往后倒退,没有多久,新的弹硌路铺好了。刚铺好的弹硌路踩上去有点松软,日久天长,人走车行,越压越紧。
1922年11月,爱因斯坦到上海城隍庙游览,走在那里高高低低的弹硌路上。陪同者向他表示歉意,不料爱因斯坦却说:“不要紧,意大利的街道上也铺着这样的石头呢。”我原以为,上海的弹硌路大约是从欧洲传入。后来得知,早在上海开埠前的明、清时期就已经有弹硌路。上海本地不出花岗石,弹硌路在上海如何起源,尚待考证。到了20世纪50年代末,上海处处弹硌路,可谓进入弹硌路的全盛时期。据统计,当时上海约有4000条弹街路,全长达800多公里。不过,上海的大道通衢,不是弹硌路。早年的南京路,曾经铺过原产澳大利亚的铁藜木。后来,上海的大马路铺柏油、水泥,小马路以及弄堂建弹硌路。
弹硌路的优点是成本低,施工简单,尤其是遇上修理马路下的管道的时候,不论是扒开或者修复弹街路,都很方便。不过弹硌路毕竟路面粗糙,“光洁度”差,行车颠簸,轮胎磨损度大。柏油马路逐渐取代弹硌路。当下,弹硌路在上海几近绝迹,据称只剩下几条小弹硌路,总长不足600米。只有在新天地,为了与那里的石库门房子一起“彰显”老上海特色,特意新铺了一小段弹硌路。
曾经遍布上海的弹硌路消失了。弹硌路只存在于老上海的记忆中,只存在于浓浓的怀旧思绪中。
(选自《新民晚报》)
【推荐语】 作者由异国他乡的鱼鳞纹方石触发了老上海弹硌路的记忆,层次清晰、有条不紊地介绍了老上海弹硌路名称的由来和特点,在质朴的叙述和说明中融入了淡淡的怀旧情绪。这种融叙述、说明、描写、抒情于一炉的写法、不急不缓的写作风格需要读者细细品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