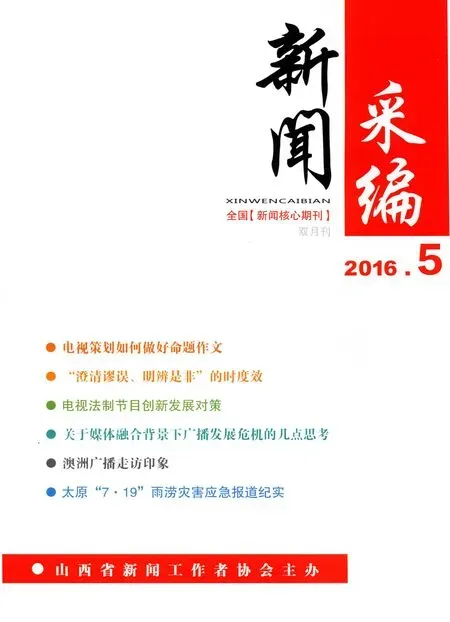任质斌:走过长征的红色报人
任质斌:走过长征的红色报人
深秋的北京,空气中飘来阵阵凉意,任全胜讲述其父任质斌“书生长征记”的经历与故事。
从私塾教育到平民大学
1915年7月17日,任质斌出生在即墨县县城南关一个贫苦家庭里。父亲任玖湘在其两岁时前往法国做劳工,补贴家用。1921年,任玖湘回国,儿子任质斌已经6岁了。从法国归来的父亲,用劳工费购置了几间房子和六七亩地。第二年,任质斌被送到私塾读书,开始启蒙教育。接受3年私塾教育后,任质斌进入中学附属高级小学学习,并在一年后升入本校初中。
胶东中学的前身是教会学校明德中学,不同于传统私塾,胶东中学重外文、轻中文。在胶东中学,任质斌思想发生蜕变,开始阅读政治类书籍,将目光投向校园外的世界。积贫积弱、落后挨打的中国,兴盛强大、霸道贪婪的列强,这让11岁的任质斌愤怒焦急又不知所措。
1927年7月,报纸上登出青岛大学附属中学招生启事。任质斌决定离开胶东中学,报考青岛大学附中。经过考试选拔,任质斌如愿以偿,这个决定也成为其人生至关重要的转折点。
青岛大学校址原为俾斯麦兵营,是德国海军当局在青岛建设的大型军营之一。校园依山而建,一派欧式古典兵营建筑,景色壮丽。在这里,任质斌开始思考人生,寻找方向。据其晚年回忆附中的生活时说,“给我印象很深的是,文学研究会作家王统照的一部长篇小说《一叶》。那本书描写旧中国青年的苦闷、没出路,像树叶一样在大海里漂泊,无法掌握自己命运的状态。这本书对我影响很大,那时候我就开始想,人活着究竟有什么价值?”
正读初三的任质斌,开始接触到创造社作家郭沫若、太阳社作家蒋光慈等人的文学作品。受作品中反帝反封建的激进思想影响,加之五三惨案的发生、青岛大学被裁撤,七月份毕业后,任质斌决定继续求学。恰逢北平平民大学来青岛招生,任质斌通过考试,成为该校预科班的一名学生。从未离开过家乡的任质斌告别父母,踏上北上的列车,越过黄河,开始了人生新的阶段。那一年,他只有14岁。从海滨青岛来到古都北平,威严雄伟的故宫,熙攘热闹的街市,在任质斌眼中,一切都是那么新奇。平民大学位于德胜门内大街大石虎胡同内,国槐夹道,花香馥郁,浓荫如盖。起初报考平民大学,是因为任质斌对该校新闻学系心仪已久,该系创办人之一、著名记者邵飘萍是其心中的偶像。也是因为最初的新闻理想,任质斌后来创办刊物,并成为红色报人。1927年大革命失败,北方革命力量受挫,平民大学中的革命力量也遭到严重破坏,一心追求进步的任质斌入学后没有找到“组织”。此时的平民大学也不复往日风采,学风不正,。对学校不满许久的任质斌毫无留恋地离开了平民大学。

青年时期的任质斌
《少年之友》与共青团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第二年,任质斌再次踏上北上的列车,只是他不知道,此次与父母分别,下次再见已是18年后。回到北平,任质斌发现书摊上出现了许多进步书刊,据其晚年回忆:“书摊上有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还有瞿秋白的《中国革命向何处去》。”任质斌一边阅读学习先进的革命理论,一边自己学写文章,以期日后投给各个刊物。1932年7月,任质斌成为中国大学商学系的一名学生。之后,任质斌成为一名共青团员。过了不久,10月中旬,严类若通知任质斌:中共河北省委派其去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参观学习,学成回来指导北方地区开展武装斗争,创建新苏区。接到任务的任质斌,匆忙将书籍和衣物托付给即墨同乡徐守伟,便前往天津,与其他同志会合共同南下。那时,任质斌未满18岁,满腔热血,决心为国家、为民族作出一番贡献。
中央苏区与《红色中华》报
“父亲的一生,可以用三个‘唯一’来概括。”任全胜说,“首先,他是唯一的一位由北方局抵达中央苏区学习武装暴动经验的青年学生。”在天津,任质斌见到了一起前往南方学习的同志:一位唐山的工人和一男两女三位学生。一行五人乘轮船前往上海,再转赴中央革命根据地。1932年10月中旬,他们抵达上海,并与中共地下党组织接上关系。根据设在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决定,河北省委赴苏区参观团只任质斌一人前往中央革命根据地,其他四人另作安排。当时,蒋介石正纠集四十万大军,准备发动第四次“围剿”行动,国民党军队已将中央革命根据地团团围住。任质斌的任务就是突破重围,进入苏区,学习掌握革命经验和实践方法后,从苏区返回北方。为了能顺利将其送进被层层围住的苏区,上海地下党选择了一条隐秘中央交通线:不经香港、直放汕头,经潮州、大浦、清溪、永定潜赴中央苏区。在中共地下党的护送下,任质斌安全到达瑞金城东北方向的叶坪村。白天参观学习,夜晚记录整理,任质斌常常忙到天亮,他还在临时中央机关报《红色中华》报上发表《参观兴国以后的感想》一文。一个月的参观结束后,任质斌积累了丰厚的参观感悟和资料,准备带回北平,用于实践斗争。因局势动乱,中共临时中央从上海撤离,秘密交通线终止。加之在苏区的一个月,任质斌因其认真的工作态度,崭露头角,得到组织认可。1933年2月,中共苏区中央局组织部部长任弼时找来任质斌,宣布组织决定:留任质斌在中央工作,担任中央苏区反帝拥苏总同盟代理主席。任质斌上任不到半年,被调任到《红色中华》报任专职编辑。承担《红色中华》报的编辑出版、“参考消息”的编印、为红色中华通讯社提供播发新闻、《工农通讯员》的编印等工作。1934年1月,瞿秋白来到中央苏区,担任《红色中华》报社社长兼主编,任质斌任秘书长,实际工作由任质斌主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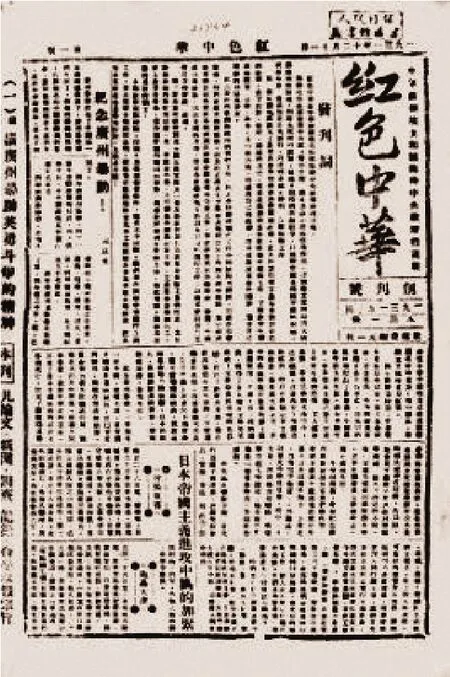
红色中华报创刊号
书生长征记
“父亲的第二个‘唯一’,是唯一一位跟随红军长征的《红色中华》报人。”任全胜说。随着国民党军队的大举进攻,中央苏区的情况日渐危急。长征,成为中国共产党寻求生机的唯一出路。1934年10月3日,《红色中华》出版第240期,这是长征前最后一期。党政工团和后勤部队、卫生部门及担架队组成第二纵队,近一万人,由李维汉任司令员兼政委。本应属于该纵队的任质斌却不在行军名单中。李维汉亲自安排任质斌跟随红九军团走,并写了介绍信,让其到会昌县城等候部队,一起长征。11日夜晚,红九军团抵达会昌,任质斌连夜前去报到。这是任质斌第一次在部队中生活,以前虽有下部队采访的经历,但时间较短,并不算真正的军旅生活。初入部队的任质斌,生活处处不适应,半生不熟的行军饭,和衣而睡的宿营觉。但很快,任质斌学会了打背包,习惯了半夜启程的生活。10月21日,红军在古陂、新田突破第一道封锁线,红九军团在大庾黄龙阻敌,付出惨重伤亡,紧接着,红军突破了第二道、第三道、第四道封锁线。任质斌第一次直面激烈的战争,战争的冷酷与残忍,震撼着内心深处,对战争有了深刻的认识。他积极投身于宣传工作,编写战报,帮助护理伤员。任质斌一边跟随队伍行军,一边采访、编写新闻稿件,为部队编印传单式报纸,刻蜡纸、油印,鼓舞士气,并向沿途群众进行动员、宣传。任质斌的出色工作,受到上级认可,中央纵队来电,派任质斌去中革军委机关报《红星报》工作。1935年1月,任质斌开始在《红星报》工作,他与陆定一和其他三位工作人员在“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的恶劣环境下,坚持办报,十天或半个月一期,每期油印七八百份,分发各个连队。随军委纵队,任质斌来到金沙江畔,据其晚年回忆:“渡江的场面是很壮观的!人在船上牵着缰绳,马和骡子浮水过。我不会浮水,就拉着马尾巴浮在水上,昂着头过了江。”过江后,任质斌被调到渡江指挥部工作,而此时渡江指挥部正因征集的船只太少而头疼不已。在指挥部统一协调与安排下,任质斌和其他同志开始张贴布告、动员船户支持、宣传渡江纪律的准备工作。通过积极有效的宣传与动员,由最初十八人船工增加到35人。在船户的支持配合下,红军胜利渡江,没有留下一人一马。5月12日,军委纵队抵达会理城郊的铁厂,并举行扩大会议,史称会理会议,进一步巩固了遵义会议的成果。会议结束后,任质斌被分配到红三军团,负责编辑《战士报》。《战士报》归军团政治部主管,是八开油印小报,共出版二百多期,现存世只有三期,其中1935年9月27日出版的第194期和9月30日出版的第195期是任质斌在长征途中进入甘肃后所办。任质斌跟随红三军团爬雪山,过草地,他晚年回忆说:“部队在爬雪山中途站着休息时,有一个同志离开队伍去解手。部队休整后要继续前进,我就跑过去喊他快走,那个同志蹲在那里不说话,只是表情僵硬地冲着我笑。我就把他搀起来,刚一松手,他就倒在雪地上死了。我不知道他叫什么,但是永远记着他临死前被冻僵的有点古怪的笑容。过草地更艰苦,一望无际的草原,树很少很少,草长得近一米高。我们八九月从那里过,差不多每天晚上都下雨,草地都是湿的。有很多暗沟被草遮了起来,人一旦踏上去就很危险。沟里都是泥沼,要是和队伍在一起,如果踩下去,其他同志可以帮忙拉出来;如果自己一个人踩下去,就很危险,越挣扎陷得越深,直到灭顶。草地没有粮食,带的干粮吃完了,就吃草地上一种野蒜。雪山六十里路以内没有人烟,以外有很少的人家,草地呢,根本就没有人烟。”“我父亲是唯一一位在中央纵队、红三军团、红五军团、红九军团工作过的新闻工作者。这是他的第三个‘唯一’。”任全胜说。

1986年任质斌夫妇重返红色中华通讯社
选摘自《大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