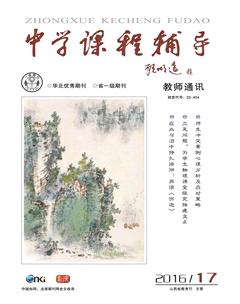在血与泪中挣扎徘徊:再读《伤逝》
陈志宏
五四时期,具有反封建思想的启蒙者高举“科学”“民主”的大旗,提倡人的解放,倡导自由恋爱,婚姻自主,出现了许多反映青年男女爱情题材的作品,鼓舞了众多男女青年挣脱封建伦理道德的束缚,追求自主性和自我价值的实现。鲁迅的《伤逝》即成为这一时期青年追求自由恋爱反抗包办婚姻的真实写照,成为现代小说中的经典之作。再读这部作品,不禁深深地为主人公子君的精神所感染,在钦佩她的反抗精神的同时,又不得不为其悲剧命运结局而扼腕叹息。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原本美丽的爱情之花瞬间凋谢呢?曾经至爱的人又为何会被轻易地抛弃呢?
首先,子君的悲剧源于其对传统文化的奴性服从与皈依。
在漫长的历史中,女性在生产生活中,丢失了自我,迷失了方向却浑然不知,她们是以男权为中心的社会的牺牲者和受害者,却又是男权文化的自觉实践者和维护者,在她们看来,“夫为妻纲”是天经地义的。作为被新文化洗礼的现代女性,子君大胆喊出了“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的时代强音,其自觉意识展现无遗,我们不禁为之欢呼。然而事实上子君的人生终极目标是而且仅仅是获得婚姻自主,这是他作为新女性唯一之所在,除此外,她和传统中国女性并无两样。果然,当她达到目的而与涓生同居后,她就遁入了“夫为妻纲”、“贤妻良母”、“相夫教子”的旧轨道,平庸、委顿、琐屑、不思进取,心安理得地做丈夫的附庸,整日的忙碌于“川流不息”的吃饭,使新生的爱情变得没有活力,显得苍白。这是涓生所不能忍受的,他想要的是“时时更新,生长,创造”的爱情,但同居后的子君没能达到他的要求,不能陪他散步、读书,以至于他觉得子君已经“没有先前那么幽静,善于体贴了。”虽然涓生和子君婚姻的解体和子君的死亡不能完全归因于子君本身,但她观念的陈旧和人生追求的狭隘是她悲剧的基础和前提。
其次,子君性格上的缺陷是导致其悲剧的重要原因。
同居前的子君在精神上和人格上都是是独立的,她说过:“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但同居后,这种独立和自主消失了。她将自己的身体和精神完全依附于涓生,以涓生为中心,似乎涓生就是她生活的全部,并把自己的一切交给涓生去经营。张爱玲也说过,女性的奴役地位很大一部分是由女性自身的弱点造成的。
在生活上子君对涓生的照料无微不至,宁愿不去谋求独立的工作,而是甘心当家庭主妇,为家务而操劳。涓生自己也感到他的食品“却比在会馆里时好得多了。”但是子君在生活上对涓生的依附进而造成他们在精神上的不平等,当子君因个人爱好而养油鸡和阿随却没有给涓生买的花浇水时,这引起了涓生的不满。在涓生的一再催逼之下,子君忍痛割爱,顺从了涓生而没有丝毫反对。唐毅说得好:“女性和男性的所谓平等,只能是真正的,最后的,精神上的完全平等。这是一个前提,也是一个底线。”只有两性关系的平等才能带来两性的和谐,当这种和谐被打破时,脆弱的一方必将受到伤害。而子君恰是依靠爱情和感情来维持生活的女人,当这种爱和感情不牢固而崩溃时,带来的后果就是子君精神的崩溃。一个没有精神信仰支撑的人无异于一具行尸走肉,他们只有两种结局:要么他们毁灭生活;要么被生活所毁灭,而子君即属后者。
最后,独立的经济权利的丧失导致子君成为男权的附庸的牺牲品。
鲁迅在《关于妇女解放》一文中说:“自然在生理和心理上,男女是有差别的;即在同性中,彼此也都不免有些差异,然而地位却应该同等,必须地位同等之后,才会有真的男人和女人,才会有消失了叹息与苦痛。”
这地位主要是指社会地位,而经济权利是其基础。唯物辩证法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阶级社会里,人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是由他们所处的经济地位决定的。因此鲁迅说,一切女子,倘不得到和男子同等的经济权……所有好名词,就都是空话。在《伤逝》中,子君并非没有争取平等的经济地位,为了买家具,她坚决卖掉了唯一的金戒指和耳环,因为“不给她加入一点股份去,她是住不舒服的。”但是同居后,她主动放弃了独立的经济权。她要的只是爱,得爱可以“坚决地毅然前行”,当爱成了“虚空”,便立刻失去“勇敢与无畏”。因此她会有父“养”仍然忧郁;会有因勇气全无,过去并不畏惧的“冷眼”转而成为可畏。在很不健全的土壤里,即使是新女性也是相当脆弱的,他们没有能力以自己的弱小身躯去抗衡整个社会,最终必将被黑暗势力所侵吞或自行凋零。
《伤逝》以类似于忏悔录式的手记形式叙写这个爱情悲剧故事,但是这种懊悔与悲哀却难以得到我们的宽恕,在忏悔中仍然表白对子君的爱情显得十分虚伪。为了自己的生路,他将同一战壕的战友推向敌人,不顾其死活,任其面对“烈日一般的严威和旁人的赛过冰霜的冷眼”。依依不舍离开家的子君却仍然深爱着涓生,把所以的生活资料都留给了他。在涓生和子君对待对方不同的态度中,我们看见自私与宽容,卑怯与勇敢,渺小与崇高的不同境界。涓生最后想在风中寻觅子君,当面说出自己的悔恨和悲哀,这还有意义吗?在我们看来,这未尝不是一种病态的忏悔,亦或许仅仅是另一种遗忘和说谎吧!
(作者单位:安徽省合肥市第八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