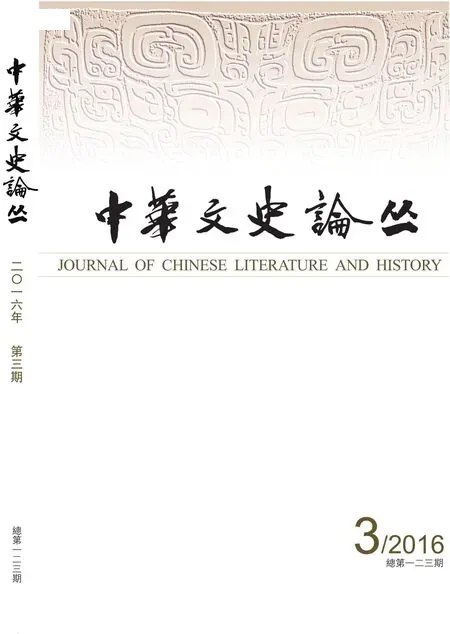《秦王破陣樂》的誕生及其歷史語境
李丹婕
《秦王破陣樂》的誕生及其歷史語境
李丹婕
《秦王破陣樂》是秦王李世民擊敗劉武周後河東地區流行起來的民間俗曲,後在太宗主導下,改編、制詞,並編配舞蹈,於元日朝會正式隆重演奏。前人的研究多集中於樂舞史的範疇,梳理其形式與流變。本文圍繞樂舞的誕生,考察制作者的意圖和期待,揭示其誕生的時代背景和政治語境。《秦王破陣樂》曲風鏗勁有力,配舞高度寫實,具有鮮明的戰陣特色,既非儒家傳統雅樂風格,也非中古宮廷樂舞慣例,顯然,脱胎於初唐特定的政治文化,具有相應的政治功能。《秦王破陣樂》與貞觀朝的意識形態建設高度一致,通過對暴力與征伐的演繹和闡釋,形成一套撥亂反正、抵達正義的敍事邏輯,宣揚貞觀政權的合法性。只有結合政治史的脈絡,纔能理解此中的複雜性。
關鍵詞: 秦王破陣樂初唐權力合法性政治文化
《秦王破陣樂》最初是李世民擊敗劉武周後於河東地區流行起來的民間俗曲。登基爲太宗後,李世民命人將之改編、制詞、配舞,於貞觀元年(627)首次元日朝會正式隆重演奏。前人對這支樂舞的研究主要圍繞其形式和流變,*就名稱而論,《破陣樂》最早大致出現於高祖武德三年(620),到晚唐懿宗咸通年間(860—869)仍有記錄,前後綿延兩百餘年。相關歷時性研究,參歐陽予倩《唐代舞蹈》,上海文藝出版社,1980年,頁88—93;王克芬《中國舞蹈史·隋唐五代部分》,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87年,頁136—144;沈冬《咸歌破陣樂,共賞太平人——〈破陣樂〉考》,《唐代樂舞新論》,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頁51—91;王頲《破陣玄野——唐代舞蹈〈秦王破陣樂〉及其演變》,《內陸亞洲史地求索》,蘭州大學出版社,2011年,頁16—29。本文視角稍有不同,試圖探討這支樂舞誕生和演繹的時代背景和政治語境。不同於一般宮廷樂舞,《秦王破陣樂》鏗勁有力,配舞高度寫實,具有鮮明的戰陣特色,既非儒家傳統雅樂風格,也未形成中古宮廷樂舞慣例,顯然,這支别具一格的樂舞,脱胎於初唐特定的政治文化。*《秦王破陣樂》的配舞名作《七德舞》,但史籍提及《秦王破陣樂》之名往往也包括樂舞,本文提及此名,一般兼指樂舞。本文結合《秦王破陣樂》由來、特色與功能,考察其誕生的歷史背景與文化環境。
一 《秦王破陣樂》與秦王
關於《秦王破陣樂》源起,最早記錄見於《隋唐嘉話》,言“太宗之平劉武周,河東士庶歌舞於道,軍人相與爲秦王破陣樂之曲,後編樂府云”。*劉餗《隋唐嘉話》中,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頁18。劉武周是隋末河東地區武裝勢力代表,和突厥往來甚密,被突厥可汗授予“定楊可汗”之號,並以突厥旗幟“狼頭纛”爲號召,*《舊唐書》卷五五《劉武周傳》,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頁2253。可見突厥的政治權威和文化符號在河東地區並不陌生。就地理位置而言,并州北經代州、雲州而通漠北,*參嚴耕望《太原北塞交通諸道》,《唐代交通圖考》第5卷《河東河北區》,中研院史語所專刊之83,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2007年,頁1335—1396。魏晉北朝以來一直是北方民族南下的重要通道,匈奴、鮮卑和羯都由這裏發迹或進入中原,也有氐、羌等部衆遷徙至此,隋至唐初還存在着粟特人聚落,*榮新江《隋及唐初并州的薩寶府與粟特聚落》,《中古中國與外來文明》,北京,三聯書店,2001年,頁169—179。社會風俗和文化面貌有其地區特色。河清三年(564),并州刺史蘭陵王高長恭取得邙山大捷時,士兵間曾流行《蘭陵王入陣曲》,*《北齊書》卷一一《文襄六王傳·蘭陵武王長恭》,北京,中華書局,1972年,頁147;參傅芸子《舞樂〈蘭陵王〉考》,《白川集》,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0年,頁75—90。後又編成舞蹈,*《通典》卷一四六《樂六》,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1988年,頁3729;《舊唐書》卷二九《音樂志二》,頁1074。當與其地方文化不無關係。武德三年(620),秦王李世民大破宋金剛於介州,宋金剛與并州劉武周北奔突厥,李世民隨即拿下并州,《秦王破陣樂》當流行於此時。與《蘭陵王入陣曲》類似,《秦王破陣樂》一曲在最初,不過是一首坊間相傳的俗曲歌謠。
就是這首名不見經傳的樂曲,在貞觀元年李世民首次以皇帝身份大宴羣臣的正月朝會中,被當庭演奏,成爲元會重要曲目。太宗對此的解釋是:“朕昔在藩,屢有征討,世間遂有此樂,豈意今日登於雅樂。然其發揚蹈厲,雖異文容,功業由之,致有今日,所以被於樂章,示不忘於本也。”*《舊唐書》卷二八《音樂志一》,頁1045。足見這首樂曲的特别之處,正在於其對秦王征伐功業的記錄。此後,《秦王破陣樂》幾經完善,其中關鍵性一步發生在貞觀六年九月。羣臣隨行太宗幸其出生地慶善宮,在他看來,此處宮殿意義“有同漢之宛、沛焉”,*《舊唐書·音樂志一》,頁1046。即好比宛縣之於光武帝,沛縣之於漢高祖。太宗於渭水之濱設宴,與從臣同飲,並賦詩十韻,即《幸武功慶善宮》:

壽丘位於山東曲阜,傳爲黄帝出生地,酆邑則是漢高祖劉邦故里,借用這些典故太宗便巧妙地將自己嵌入歷代偉大帝王的“神聖序列”之中。以“共樂還鄉宴,歡比大風詩”作爲結束,意在將眼前慶善宮之宴,比擬爲漢高祖在沛宮款待故人父老的宴會。就在那次宴會上,高祖寫下著名的《大風歌》:
發沛中兒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上擊筑自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兒皆和習之。*《漢書》卷一下《高帝紀下》,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頁74。關於《大風歌》概述,參吉川幸次郎著,章培恒、駱玉明等譯《漢高祖的大風歌》,《中國詩史》,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頁43—57。
與《大風歌》命運一樣,太宗《幸武功慶善宮》隨即以起居郎呂才配以管弦,名《功成慶善樂》,並相應以“使童子八佾爲《九功》之舞”。*《資治通鑑》卷一九四,北京,古籍出版社,1956年,頁6098。太宗又借機改編《秦王破陣樂》,令呂才重新編曲,由魏徵、虞世南、褚亮、李百藥等人改寫歌辭,增舞者爲一百二十人,名爲《七德》之舞。至此,冬至享宴及國有大慶的場合,演奏樂曲便是《秦王破陣樂》與《功成慶善樂》,相應舞蹈即《七德舞》與《九功舞》。
樂舞設計者呂才不僅精通音律,諳熟陰陽五行之學,還善於製圖,曾受太宗之命,繪製《方域圖》及《教飛騎戰陣圖》。*《舊唐書》卷七九《呂才傳》,頁2726。重新編排《秦王破陣樂》後,在太宗親自督作下,呂才又製成《破陣舞圖》。畫面上,“左圓右方,先偏後伍,魚麗鵝鸛,箕張翼舒,交錯屈伸,首尾回互,以象戰陳之形”。太宗令呂才用這幅圖來排練舞蹈,一百二十舞者,皆披甲執戟,過程中陣形凡爲三變,每變爲四陣,配合樂曲節拍,披甲執戟的舞者疾徐奔跑,互爲擊刺。整個舞蹈場面,聲韻慷慨,氣氛昂揚,*《通典》卷一四六《樂六》,頁3718—3719。意在以寫實手法演繹戰事。這其實反映了太宗本人的意志,對照貞觀末年太宗親撰的《帝範》序文便非常清晰:“朕以弱冠之年,懷慷慨之志,思靖大難,以濟蒼生。躬擐甲胄,親當矢石,夕對魚鱗之陣,朝臨鶴翼之圍,敵無大而不摧,兵何堅而不碎。”*《全唐文》卷一〇《帝範·序》,北京,中華書局影印,1983年,頁120下。由是觀之,《秦王破陣樂》以高度寫實的手法描述了秦王的戰功,其舞者都是披甲執戟的武士。*可資旁證的是目前藏於日本正倉院的《秦王破陣樂》甲士舞所佩腰刀,參傅芸子《正倉院考古記》,上海書畫出版社,2013年,頁106;圖片參《第66回正倉院展目錄》,奈良,天理時報社,2014年,圖8。整支樂舞致力於再現戰爭場景,更具體而言,便是秦王“百戰百勝之形容”,對應武德年間秦王的歷次征伐。這一內容與貞觀年間的意識形態論調可説是高度統一。
唐朝開國皇帝李淵自稱得天下乃源於天命,受隋帝“禪讓”,加之開國初年割據政權尚四方林立,因此武德朝施政原則基本是“用隋舊文,承隋舊制”。然而,與李淵不同,李世民繼承帝位,是通過血腥的家族暴力政變。貞觀初年,“玄武門事件”爲朝野上下所“諱言隱筆”、“避而不談”,本身就説明時人對此事原委的敏感與態度。對於皇位繼承而言,李建成擁有血統的正當性和優先權,李世民在這方面無競爭力可言,他的策略是基於戰功和德性而主張擁有權力合理性的渲染。在出身(血統)和賢能(功業)之間,李世民只能選擇後者。他起誓所憑藉的權杖便是武德年間的戰功。一再突顯這段歷史,太宗還把自己和衆多開國功臣以及國家命運緊緊捆綁在一起,因此,武功與勳德成爲貞觀朝公文書頻繁出現的關鍵詞。武德九年,高祖禪位詔書對此已有體現:
皇太子世民,……英圖冠世,妙算窮神,伐暴除凶,無思不服。薛舉負西戎之衆,武周引北狄之兵,蝟起蜂飛,假名竊號,元戎所指,折首傾巢。王世充藉府庫之資,憑山河之固,信臣精卒,承閑守險;建德因之,同惡相濟,金鼓纔震,一縱兩擒。師不逾時,戎衣大定,夷劉闥於趙魏,覆徐朗於譙兗。功格穹蒼,德孚宇宙,雄才宏略,振古莫儔,造我大唐,繄其是賴。*《禪位皇太子詔》,《全唐文》卷三,頁39下—40上;《徙居大安宮誥》再次重申,頁40下—41上。
貞觀五年太宗在回覆朝集使王孝恭等人請封禪奏疏的手詔中再次重申:“自有隋失道,四海橫流,百王之弊,於斯爲甚。朕提劍鞠旅,首啓戎行,扶翼興運,克成鴻業,遂荷慈卷,恭承大寶。”*王欽若等編纂,周勛初等點校《册府元龜》卷三五《帝王部·封禪一》,南京,鳳凰出版社,2006年,頁365,《唐大詔令集》卷六六《答請封禪詔》,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頁367。這番關於以戰功安天下的歷史敍事,成爲話語格套,被太宗反覆提及。如《經破薛舉戰地》一詩:
昔年懷壯氣,提戈初仗節。心隨朗日高,志與秋霜潔。移鋒驚電起,轉戰長河決。營碎落星沈,陣卷橫雲裂。一揮氛沴靜,再舉鯨鯢滅。於兹俯舊原,屬目駐華軒。沈沙無故迹,減竈有殘痕。浪霞穿水淨,峯霧抱蓮昏。世途亟流易,人事殊今昔。長想眺前蹤,撫躬聊自適。*《唐太宗全集校注》,頁25。
此詩得到長孫無忌、楊師道、褚遂良、許敬宗、上官儀等人的奉旨應和,*《翰林學士集》,傅璇琮編《唐人選唐詩新編》,西安,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頁21—23。衆人寫景、用典各異,但在追摩太宗戰爭功業這一立場上,完全一致。再如《還陝述懷》一詩:
慨然撫長劍,濟世豈邀名。星旂紛電舉,日羽肅天行。遍野屯萬騎,臨原駐五營。登山麾武節,背水縱神兵。在昔戎戈動,今來宇宙平。*《唐太宗全集校注》,頁29。

隋末喪亂,百姓凋殘,酷法淫刑,役煩賦重,農夫釋耒,工女下機,徵召百端,寇盜蜂起,人懷怨憤,各不聊生,水火之切,未足爲喻。先朝不忍塗炭,思濟黎元,朕稟承神算,奮劍南起,與彼境英雄,同心協力,不顧軀命,以救蒼生。爰自晉陽興兵立義,雄鋒接刃,櫛風沐雨,除凶去暴,布德行仁,天下乂安,戎車止息,九夷八狄,莫不來庭,以至於今二十餘載。*《册府元龜》卷一七二《帝王部·求舊二》,頁1913。
此處“二十餘載”便將武德年間秦王征伐歲月與貞觀時代順理成章無縫銜接,構成太宗繼承皇位的正當基礎。貞觀十八年太宗《親征高麗手詔》依然强調,“隋室淪亡,其源可睹,……(朕)昔受鉞專征,提戈撥亂,師有經年之舉,食無盈月之儲,……蕩氛霧於五嶽,翦虎狼於九野,定海內,拯蒼生”;*《册府元龜》卷一一七《帝王部·親征二》,頁1278。出征行經洛陽時,太宗寫下《感舊賦》,內容大體一致。*“屬隋季之分崩,遇中原之喪亂。……遂收袂而電舉,乃奮衣而雲翔。據三秦兮鳳跱,出九谷兮龍驤。揮寶劍之虹彩,回雕戈於日光。掃欃槍兮定六合,廓氛沴兮靜八荒”,參《唐太宗全集校注》,頁112。這些文獻共同反映出,“秦王破陣、奠基李唐”的歷史敍事是李世民親自主導下形成的,成爲貞觀年間,特别是貞觀前期最爲核心的輿論基調,也是《秦王破陣樂》得以被選中、改編並最終於元會典禮鄭重演奏的直接背景。
與改編、演奏《秦王破陣樂》並行的,是太宗貞觀十四年下詔編修皇帝實錄。房玄齡等人遂受命撰成《高祖實錄》《太宗實錄》各二十卷。太宗看到其中關於玄武門之變的記錄頗爲曖昧,於是回覆房玄齡等人,將此舉比附爲周公誅管蔡,乃“安社稷、利萬人”的義舉,無需隱晦,這一態度爲魏徵大加贊賞,稱“陛下今遣史官正其辭,雅合至公之道”。*《貞觀政要集校》卷七《文史》,頁391—392。此事提醒我們,太宗並沒有篡改歷史,但他利用更隱秘的方式左右了歷史敍事,通過官修史書渲染自己的戰功“篡奪”了乃父李淵晉陽起兵之初的主導權,因此《高祖實錄》從唐起兵反隋,延續到太宗貞觀九年,所載核心人物其實也是李世民。
太宗此舉確實起到了“以史資治”的效果,憲宗元和四年(809)前後,白居易《新樂府》組詩之一《七德舞》寫道:
觀舞聽歌知樂意,樂終稽首陳其事。太宗十八舉義兵,白旄黄鉞定兩京。擒充戮竇四海清,二十有四功業成。二十有九即帝位,三十有五致太平。*朱金城《白居易集箋校》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頁140。陳寅恪先生指出,白居易《新樂府》組詩整體構思頗受《貞觀政要》的影響,不僅如此,白居易還大量參考了《太宗實錄》。*《元白詩箋證稿》,北京,三聯書店,2009年,頁136。此詩的確出自太宗自述:“朕年十八便爲經綸王業,北剪劉武周,西平薛舉,東擒竇建德、王世充,二十四而天下定,二十九而居大位,四夷降伏,海內乂安。”*《貞觀政要集校》卷一〇《災祥》,頁524—525。兩篇文字相隔近兩百年,表述卻幾近一致,不僅反映了《秦王破陣樂》的具體內容,也表明太宗通過歷史敍事成功塑造甚至再造了自己的形象。《秦王破陣樂》便是這一形象塑造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這支樂舞是對秦王戰功的敍事,具有鮮明的寫實性。但必須强調的是,這種寫實性並不在於傳遞純粹的事實,而是經過選擇、拼綴、提煉和濃縮,被有意編排、觀念主導的“事實”,並在廣泛宣揚傳播過程中,成爲秦王和唐朝的開國“故事”,甚至是“史實”。
二 戎音與正聲之辨
渲染秦王勳功是《秦王破陣樂》成爲貞觀朝“主旋律”的直接原因,但記述戰爭功德以爲宮廷曲樂的手法還有其深層的歷史背景。《秦王破陣樂》有三點重要屬性值得措意,其一是伴隨征伐凱旋而生;其二最初屬於軍樂範疇;其三配舞在於寫照征伐。
武德四年(621)李世民打敗王世充,攻克洛陽城,對於建基不久的唐朝而言是件提振國威的大事。這年六月,李世民率兵凱旋,回到長安。《舊唐書·太宗紀上》記下了這一幕:
六月,凱旋。太宗親披黄金甲,陳鐵馬一萬騎,甲士三萬人,前後部鼓吹,俘二僞主及隋氏器物輦輅獻於太廟。高祖大悦,行飲至禮以享焉。*《舊唐書》卷二,頁28。
《册府元龜》卷一二《帝王部·告功》收錄此條,*《册府元龜》卷一二《帝王部·告功》,頁122。文字略有出入,但文本幾乎一致,也就是説,其史源當是《高祖實錄》或《太宗實錄》。杜佑《通典》也錄此事,但歸於武德四年七月:
秦王平東都,被黄金甲,陳鐵馬一萬,甲士三萬,以王世充、竇建德及隋文物輦輅,獻捷於太廟。*杜佑《通典》卷七六《禮三六》,頁2085。《唐會要》卷一四《獻俘》所記則略同於此條,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頁371。
《通典》此條,除了時間出入外,最大的不同,在於“聲音的消失”,也就是“前後部鼓吹”一句不見了。這裏的“前後部鼓吹”,究竟是什麼呢?
《舊唐書》卷二八《音樂志一》保留一則大和三年(829)太常禮院奏疏,其中寫道:
謹按凱樂,鼓吹之歌曲也。《周官·大司樂》:“王師大獻,則奏凱樂。”注云:“獻功之樂也。”又《大司馬》之職,“師有功,則凱樂獻於社。”注云:“兵樂曰凱。”《司馬法》曰:“得意則凱樂,所以示喜也。”《左氏傳》載晉文公勝楚,振旅凱入。魏晉已來鼓吹曲章,多述當時戰功,是則歷代獻捷,必有凱歌。太宗平東都,破宋金剛,其後蘇定方執賀魯,李勣平高麗,皆備軍容凱歌入京師。謹檢《貞觀》、《顯慶》、《開元》禮書,並無儀注。今參酌今古,備其陳設及奏歌曲之儀如後。*《舊唐書·音樂志一》,頁1053;《新唐書》卷二三《儀衛志》簡化爲:“歷代獻捷必有凱歌,太宗平東都,破宋金剛,執賀魯,克高麗,皆備軍容,凱歌入京都,然其禮儀不傳。”(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頁510)《唐會要》卷三三《凱樂》與此略同,《册府元龜》卷五六九《掌禮部·作樂》(頁6548)有若干抄寫錯誤,但史源明顯一致。
照這位太常寺禮官之説,太宗武德四年凱旋時的“前後部鼓吹”,其具體形式就是“軍容凱歌”,爲説明“凱歌”的重要性,他追溯或重塑了其悠久淵源,並將魏晉以來的鼓吹曲章述於上古凱樂脈絡之中,由此形成一個源遠流長的凱樂“傳統”。在他看來,直到唐初,太宗依然是在延續這個“傳統”。然而,他也不無遺憾地發現,遍檢《貞觀禮》、《顯慶禮》、《開元禮》,並沒有發現有關於此的任何儀注。*《大唐開元禮》卷八三“軍禮”下僅有“凱旋獻俘”條,內容極爲簡單。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年,頁402。若果然如這位禮官所言,凱樂傳統源遠流長,那麼它爲唐前期國家禮官一致忽略,不能不説相當意外。最有可能的情況是,此處凱樂“傳統”源流,是這位禮官爲了論證太和年間設置凱樂的合理性而編織出來的。不過,如果沒有這條發展脈絡,太宗的“凱旋軍樂”從何而來呢?我們可以試作追溯。
沈約編撰《宋書·樂志》將音樂從《禮樂志》單列出來,對前代音樂文獻進行了充分整理彙編,顯然是梁武帝繼位後“思弘古樂”的產物。*《隋書·音樂志上》,北京,中華書局,1973年,頁287。此後,魏收《魏書》也單立《樂志》,這一做法爲初唐官修《晉書》《隋書》等沿襲。然沈約《宋書》、魏收《魏書》中都沒有關於“凱歌”、“凱樂”的記錄。沈約筆下的“鼓吹”,與唐大和年間那位太常禮官所言大體一致,*“《周官》曰:‘師有功則愷樂。’《左傳》曰,晉文公勝楚,‘振旅,凱而入’。《司馬法》曰:‘得意則愷樂愷哥。’”《宋書》卷一九《樂志一》,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頁558。但緊接着轉而爬梳軍樂鼓吹流變,隻字未提“凱樂”。沈約《樂志》以詳盡甚至是繁瑣著稱,這顯然不是刻意或無心的遺漏,再次證明,上述太常禮官梳理出來的凱樂“傳統”是個人建構的產物,並不存在一個連續的凱樂“傳統”。考慮到北周力圖借復興《周禮》之名以强化正統的背景,對於“凱樂”在北周的“橫空出世”,或許就不會顯得那麼突兀。《周書·武帝紀》記建德六年(577):
夏四月乙巳,至自東伐。列齊主於前,其王公等並從,車轝旗幟及器物以次陳於其後。大駕布六軍,備凱樂,獻俘於太廟。京邑觀者皆稱萬歲。*《周書》卷六,北京,中華書局,1971年,頁102。
《周書》由令狐德棻領銜編撰,修成於貞觀十年。這條記載描述了建德六年周武帝親征北齊凱旋的情景,與武德四年秦王凱旋的場面高度相似。也就是説,秦王所備的“前後部鼓吹”,其性質就是周武帝的“凱樂”,而北周“凱樂”之名很可能借自《周禮》,即“王師大獻,則令奏愷樂”。*《周禮注疏》卷二二《大司樂》,十三經注疏整理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頁697上。北周“凱樂”詳情,我們不得而知,但風格很可能是民間俗樂。沈括《夢溪筆談》曾提到:“邊兵每得勝回,則連隊抗聲‘凱歌’,乃古之遺音也。‘凱歌’詞甚多,皆市井鄙俚之語,予在鄜延時製數十曲。”*胡道靜《夢溪筆談校證》卷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224。恐怕正在於“市井鄙俚”等因素,導致其未能進入唐前期官修禮典之中。
太宗奏凱樂、行凱旋禮直接源自北周而間接呼應《周禮》,其以凱樂敍功德的做法則還與唐之前“鼓吹曲章”的發展有關。上述唐大和年間太常禮官追溯“凱歌”歷史時提及一個細節,“魏晉已來鼓吹曲章,多述當時戰功”。關於鼓吹,沈約《宋書·樂志一》稱:“鼓吹,蓋短簫鐃歌。蔡邕曰:‘軍樂也,黄帝岐伯所作,以揚德建武,勸士諷敵也。’”*《宋書》卷一九,頁558。參吉川幸次郎《關於短簫鐃歌》,《中國詩史》,頁88—97。其中短簫鐃歌,實際上是一組鼓吹曲辭,總題爲《漢鼓吹鐃歌十八曲》。*《樂府詩集》卷一六,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頁223;另參《晉書》卷二三《樂志下》,頁701。這十八篇曲辭是在先秦鼓樂、吹樂以及軍中凱樂的基礎上,融合北方少數民族的橫吹、鼓吹而形成的音樂,最初並非僅用於軍事禮儀,其內容也不僅關於戰爭。*趙敏俐《漢鼓吹鐃歌十八曲研究》,《文史》2002年第4輯,頁38—76;另參戶倉英美《漢鐃歌“戰城南”考——並論漢鐃歌與後代鼓吹曲的關係》,吴相洲主編《樂府學》第2輯,北京,學苑出版社,2007年,頁1—18。
鼓吹曲辭的重大變革始於曹丕稱帝。*渡邊信一郎著,牟發松譯《曹魏俗樂的政治意識形態化——從鼓吹樂所見》,《襄樊學院學報》2010年第10期,頁19—22。正是在“漢末大亂,衆樂淪喪”的時代背景下,精於文章之學又擅長騎射擊劍的曹丕對漢代民間流傳起來的鼓吹曲進行了創造性更張,將其改變成一組壯觀的征伐敍事歌詩,具體內容詳見《晉書·樂志下》。*《晉書》卷二三,頁701;《樂府詩集》卷一八,頁264—274。這組鼓吹歌辭並非上古通行的四言,而是據原本謳謠格式,長短不一,內容則以始自曹操的曹魏戰功歷程爲核心。“不以喪廢樂”的魏文帝這樣做,*《晉書》卷二〇《禮志中》,頁618。顯然是爲自己繼位進行輿論宣傳,這首敍述王朝功業的“政治史詩”也就成爲黄初元年(220)魏文帝稱帝的重要道具。很可能受此啓發,東吴後來也由韋昭於吴景帝孫休朝製成《鼓吹鐃歌》十二曲,記述吴國的功德與天命。*《晉書·樂志下》,頁701—702。蕭滌非認爲,吴鼓吹曲,名雖代漢,實本於魏,參《漢魏六朝樂府文學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1年,頁157。西晉武帝登基後,命傅玄重新編製鼓吹鐃歌二十二首。*《晉書·樂志下》,頁702—703;《樂府詩集》卷一八,頁275—284。此後,東晉不見類似創作,南朝宋、齊則並用漢曲。*《樂府詩集》卷一六,頁224。值得注意的是,永明八年(490),謝朓曾奉鎮西隨王命製作過鼓吹曲辭十首,以歌帝功、頌君德爲核心內容,其辭皆爲五言,參《樂府詩集》卷二〇,頁293—295。梁武帝蕭衍在位時,沈約對前朝鼓吹鐃歌進行重新填詞,形成敍述梁朝功德的鼓吹十二曲,*《隋書·音樂志上》,頁304—305;《藝文類聚》卷四二《樂部二》載《梁沈約鼓吹曲》十二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頁759—760;另參《樂府詩集》卷二〇,頁297—300。以爲梁朝政權合法性的輿論宣傳。北齊也有鼓吹曲辭。郭茂倩《樂府詩集》鼓吹曲辭解題中稱:“北齊二十曲,皆改古名。……後周宣帝革前代鼓吹,制爲十五曲,並述功德受命以相代,大抵多言戰陣之事。”*《樂府詩集》卷一六,頁224。
開皇二年(582),顏之推上奏稱,“禮崩樂壞,其來自久。今太常雅樂,並用胡聲”,建議暫行梁朝舊樂,被隋文帝否決。文帝以爲:“梁樂亡國之音,奈何遣我用邪?”於是命鄭譯主持設計正樂。改革方案遲遲不能落定,文帝非常憤怒,斥責臣僚道:“我受天命七年,樂府猶歌前代功德邪?”*《隋書·音樂志中》,頁345。值得注意的是,文帝計較的重點,不在於是否符合儒家經典傳統,而是這套音樂並非對自己功德的寫照。隋樂官後來製成一套樂舞,次序大致是,“始而受命,再成而定山東,三成而平蜀道,四成而北狄是通,五成而江南是拓,六成復綴,以闡太平”。文帝觀後,稱“不須象功德,直象事可也”,*《隋書·音樂志下》,頁358。並准予表演。這套演繹隋文帝戰功的樂舞,和此前歷代鼓吹曲辭不同,乃是以舞蹈演繹征伐,形式近乎周公《大武》。*以樂舞演繹武王伐紂,共分六場,每場配以《詩經·周頌》的一篇。相關研究參陰法魯《〈詩經〉中的舞蹈形象》,《陰法魯學術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頁423—428,原載《舞蹈論叢》1982年第4期;馬銀琴《西周早期的儀式樂歌與周康王時代詩文本的第一次結集》,《詩經研究叢刊》第2輯,北京,學苑出版社,2002年,頁23—30;柯馬丁《早期中國文學: 開端到西漢》,孫康宜、宇文所安主編,劉倩等譯《劍橋中國文學史》上卷,北京,三聯書店,2013年,頁50—51;傅道彬《象樂的戲禮形態與演唱式史詩形式》,《中國文化研究》夏之卷,2013年,頁23—37。據《通典·樂六》“前代雜樂”稱:“齊梁至陳則甚重(鼓吹)矣,各製曲辭以頌功德焉。至隋,亡。”*《通典》卷一四六,頁3731。《隋書·音樂志》暗示了此舉的原因,即“舊三朝設樂有登歌,以其頌祖宗之功烈,非君臣之所獻也,於是去之”,這裏的登歌即曹魏以來歷代鼓吹製作。頁302。也就是説,曹魏以來重編鼓吹鐃歌的做法至隋代而終結。*渡邊信一郎認爲,隋文帝改革曹魏六朝以來歌頌王朝文德武功的鼓吹樂,以源於北魏鮮卑系的北狄樂爲核心,結合漢魏以來傳統清商樂,開創了新的形式,顯示了隋文帝的一統,既不是復古性地回歸漢代以來的傳統王朝權力,也不是單純的胡漢融合的政權。對以北狄樂爲核心的鼓吹樂予以再編,有强調繼承西魏、北周的權力基礎的意圖,並將其政治文化置於權力中樞。參氏著,周東平譯《隋文帝的樂制改革——以鼓吹樂的再編爲中心》,《日本學者中國法論著選譯》,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2年,頁237—255。
而《秦王破陣樂》可説復興了“製曲辭以頌功德”的做法。不僅如此,唐朝也繼承了隋代以樂舞演繹功德的做法,貞觀年間曾製作《凱安舞》,用於郊廟祭享,其內容“凡有六變: 一變象龍興參野,二變象克靖關中,三變象東夏賓服,四變象江淮寧謐,五變象獫狁讋伏,六變復位以崇,象兵還振旅”,*《舊唐書·音樂志一》,頁1048。與《秦王破陣樂》有異曲同工之處。
隋唐以來以樂舞演繹征伐的做法看似可以追遠溯古,卻很可能當時還受到北族文化的啓發。以視覺形式寫實地記錄戰陣實係北族傳統,突厥可汗去世後,“表木爲塋,立屋其中,圖畫死者形儀及其生時所經戰陣之狀”。*《隋書》卷八四《北狄傳·突厥》,頁1864。隋朝、唐初正是與突厥汗國交織互動最爲頻密的時期,以樂舞演繹戰陣出現在此時當有其具體的時代語境。此或又可旁證《秦王破陣樂》何以源出與突厥關係密切的河東地區。*甚至有學者推測《秦王破陣樂》最初當是《破陣樂》,而後者則是通過突厥傳自羅馬的軍事樂舞,參楊憲益《秦王〈破陣樂〉的來源》,氏著《譯餘偶拾》,北京,三聯書店,1983年,頁57—60。
《舊唐書·音樂志二》“北狄樂”條記有一則,“後魏樂府始有北歌,即《魏史》所謂《真人代歌》是也。代都時,命掖庭宮女晨夕歌之”。*《舊唐書》卷二九,頁1071—1072。據魏收《魏書·樂志》載,《真人代歌》“上敍祖宗開基所由,下及君臣廢興之迹,凡一百五十章,昏晨歌之,時與絲竹合奏。郊廟宴饗亦用之”。*《魏書》卷一〇九《樂志》,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頁2828。田餘慶先生認爲這些樂辭采集於道武帝皇始元年(396)建天子旌旗、取并州、奪中山,至天興元年(398)克鄴、滅後燕、定都平城之間,還强調“代歌是經過拓跋君主有意篩選甚或部分改造的燕魏之際鮮卑歌。篩選是按照道武帝個人意志進行的,目的是用口碑資料中拓跋傳説,編成歌頌先人功烈的歌謠,於代人中廣爲傳播,爲道武帝的帝業製造輿論”。*田餘慶《〈代歌〉、〈代記〉和北魏國史——國史之獄的史學史考察》,《拓跋史探》,北京,三聯書店,2003年,頁218—220。羅新先生結合嘎仙洞祭祀題記出現的時代背景,提出《真人代歌》的編定是太武帝進一步擡升鮮卑這一族羣標籤政治地位、建構拓跋集團歷史的組成部分之一,而整飭鮮卑語《真人代歌》與漢文書寫《代記》都是這一時期政治舉措的關鍵步驟。*羅新《民族起源的想象與再想象——以嘎仙洞的兩次發現爲中心》,《文史》2013年第2期,頁20—21。兩人都注意到《真人代歌》背後特定的意識形態訴求。以歌謠傳唱功烈實現具有政治意圖的正統敍事發生在拓跋王朝國家建構的關鍵時期,此舉是否受到曹魏鼓吹曲辭的啓發不得而知,但兩者就其做法和意圖確有相通之處。北魏時期不僅有《代歌》這樣的音樂作品,還有相應的視覺創作。道武帝在位時,命禮官製作鹵簿禮制,天興二年(399)製成的三駕鹵簿之大駕規模如下:
設五輅,建太常,屬車八十一乘。平城令、代尹、司隸校尉、丞相奉引,太尉陪乘,太僕御從。輕車介士,千乘萬騎,魚麗雁行。前駕,皮軒、闒戟、芝蓋、雲罕、指南;後殿,豹尾。鳴葭唱,上下作鼓吹。軍戎、大祠則設之。*《魏書》卷一〇八《禮志四》,頁2813。
天賜二年(405)初,又“改大駕魚麗雁行,更爲方陳鹵簿。列步騎,內外爲四重,列標建旌,通門四達,五色車旗各處其方。諸王導從在鉀騎內,公在幢內,侯在步矟內,子在刀盾內,五品朝臣使列乘輿前兩廂,官卑者先引”。*《魏書》卷一〇八《禮志四》,頁2813—2814。無論“魚麗雁行”,還是“方陳鹵簿”,都是以甲騎或步兵爲主體構成的作戰方陣。目前發現於山西大同沙嶺、修於太武帝太延元年(435)的北魏壁畫墓中,有幅别具特色的出行圖,是方陣與百戲相結合的形式。學者整體分析後,認爲這一出行圖像正是道武帝禮儀製作“胡風國俗”相雜糅的結果。*林聖智《北魏沙嶺壁畫墓研究》,《中研院歷史語言所研究集刊》83.1,2012年,頁11—17。文成帝和平三年(460)還有盛大的戰陣演習,“十有二月乙卯,制戰陳之法十有餘條。因大儺耀兵,有飛龍、騰蛇、魚麗之變,以示威武”。*《魏書》卷五《高宗紀》,頁120。可以看出,軍陣、鼓吹、百戲相結合的禮儀成爲北魏演繹軍威的重要形式。
隨着北魏文化轉向進程的加速,《真人代歌》也發生變化,《魏書·樂志》載,太和七年(483)秋,“中書監高允奏樂府歌詞,陳國家王業符瑞及祖宗德美,又隨時歌謠,不準古舊,辨雅鄭也”。*《魏書》卷一〇九《樂志》,頁2829。永平三年(501)冬,太常卿劉芳又上奏:“觀古帝王,罔不據功象德而制舞名及諸樂章,今欲教文武二舞,施之郊廟,請參制二舞之名。竊觀漢魏已來,鼓吹之曲亦不相緣,今亦須制新曲,以揚皇家之德美。”*《魏書》卷一〇九《樂志》,頁2832。這一建言似乎是吸取曹魏以來鼓吹曲辭的經驗來重製北魏功德樂章。此前幾年,孝文皇帝太和十九年(495)下詔,“不得以北俗之語言於朝廷,若有違者,免所居官”,*《魏書》卷七下《高祖紀下》,頁177。這一禁令對於以鮮卑語《代歌》想必也同樣適用,鮮卑史詩遂逐漸過渡爲漢文曲辭。
北周初年,政治立場“多依古禮(《周禮》),革漢魏之法”,因此,北周太祖、武帝沒有延續曹丕以來改造漢鼓吹鐃歌的做法,卻創造性借用了“凱樂”之名。北周凱樂不止有音樂,還配以舞蹈,舞名《安樂》。據《舊唐書·音樂志二》:“《安樂》者,後周武帝平齊所作也。行列方正,象城郭,周世謂之城舞。舞者八十人。刻木爲面,狗喙獸耳,以金飾之,垂線爲髮,畫猰皮帽。舞蹈姿制,猶作羌胡狀。”*《舊唐書》卷二九,頁1059。《通典》卷一四六《樂六》,頁3718。羌衆的音樂特色,參《隋書》卷八三《党項傳》:“有琵琶、橫吹、擊缶爲節。魏周之際,數來擾邊。”頁1845—1846。這支《安樂》舞和《凱樂》同時出現在武帝平齊之際,他們擁有典雅樸素的漢文名字,但就上述舞蹈場面的描述來看,其不僅表現征伐場面,而且還與遊牧民族的風俗大有關係。*《隋書·音樂志中》,頁344。
以樂舞表現殺伐似乎在北族中有其淵源。如《北史·奚康生傳》記: 正光二年(521)二月,“明帝朝靈太后於西林園。文武侍坐,酒酣迭舞。次至康生,乃爲力士舞,及於折旋。每顧視太后,舉手蹈足,嗔目頷首,爲殺縛之勢”。*《北史》卷三七,頁1361。又如《北史·勿吉傳》:“(隋)文帝因厚勞之,令宴飲於前,使者與其徒皆起舞,曲折多戰鬥容。上顧謂侍臣曰:‘天地間乃有此物,常作用兵意。’”*《北史》卷九四,頁3125。《秦王破陣樂》與這些樂舞類似而規模升級,意在摹寫軍事戰陣,舞者“首尾迴互,以象戰陣之形”。*《舊唐書·音樂志一》,頁1046。初唐名將李靖觀摩此舞後對太宗説:
臣竊觀陛下所製《破陣樂舞》,前出四表,後綴八旛,左右折旋,趨步金鼓,各有其節,此即《八陣圖》,四頭八尾之制也。人間但見樂舞之盛,豈有知軍容如斯焉!
太宗聽到此語,頗有得知己之悦,回應道:“朕爲《破陣樂舞》,惟卿已曉其表矣,後世其知我不苟作也。”*《李衛公問對》卷中,文淵閣四庫全書本,726册,頁153上。足見《秦王破陣樂》表現了現實中的作戰陣勢,如史所言:“太宗在藩,樂工爲《秦王破陣樂》,以歌用兵之妙。”*《册府元龜》卷二七《帝王部·孝德》,頁275。
以樂舞演繹征伐,在儒家士人看來並非中原文化的傳統。神龍二年(706)并州清源尉呂元泰建議禁演潑寒胡戲,説道:“旗鼓相當,軍陣勢也;騰逐喧噪,戰爭象也;……安可以禮義之朝,法胡虜之俗?”*《新唐書》卷一一八《呂元泰傳》,頁4277;《陳時政疏》全文見《全唐文》卷二七〇,頁2741下—2743上。由此我們可以回味一個細節,魏徵每聽見演奏《破陣樂》,便低頭不看;若是《慶善樂》,則欣賞不已。*《隋唐嘉話》中,頁18。魏徵的表現可有兩種解釋,其一,這一樂舞並非儒家傳統宮廷雅樂;其二,這支樂舞高度寫實,記錄秦王歷次征伐,而魏徵則出身於落敗方。關於後者,我們還可舉出另一證據。貞觀七年,蕭瑀觀《秦王破陣樂》後對太宗言:“今《破陣樂舞》,天下之所共傳。然美盛德之形容,尚有所未盡。前後之所破劉武周、薛舉、竇建德、王世充等,臣願圖其形狀,以寫戰勝攻取之容。”*《貞觀政要集校》卷七《禮樂》,頁419。從中可以看出,《破陣樂》舞即便是“陳其梗概,委曲寫之”,*《新唐書》卷二一《禮樂志十一》,頁468。也依然清楚寫照了秦王的歷次征伐。
李唐統治者對北族文化並不陌生。高祖李淵早年在東都城內頗有一幫“積小故舊,編髮友朋”,*《舊唐書》卷七五《孫伏伽傳》,頁2637。立朝初年,又以突厥騎兵兵法對抗北族,使得“突厥每見帝兵,咸謂似其所爲,疑其部落”,*《大唐創業起居注》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頁2。這些都反映出李淵的成長環境與突厥文化密切相關。太宗長子李承乾極熱愛突厥文化,嗜好在宮中烹煮牛馬,與身邊侍衛分而食之。不僅如此,李承乾還喜歡説突厥語,穿突厥衣,並專門選拔突厥侍衛,以草原部落爲單位,辮髮、披裘、騎馬、牧羊,甚至在東宮設置穹廬帳篷,張挂突厥戰旗狼頭纛。*《資治通鑑》卷一九六,頁6189—6190;另參汪籛《唐初之騎兵——唐室之掃蕩北方羣雄與精騎之運用》,《汪籛隋唐史論稿》,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頁226—260。李承乾深染突厥習俗,既來自家族風氣,也與太宗本人的態度大有關係,*陳寅恪《讀書劄記一集》,北京,三聯書店,2001年,頁436。反映出突厥文化在初唐宮廷最上層相當盛行。杜佑《通典》稱“胡舞鏗鏘鏜鎝,洪心駭耳,……雖此胡聲,足敗華俗”,*《通典》卷一四二,頁3614—3615。並不是空來的感嘆。據《舊唐書·音樂志二》載:“自周隋已來……鼓舞曲多用龜兹樂,其曲度皆時俗所知也。惟彈琴家猶傳楚、漢舊聲。”*《舊唐書》卷二九,頁1068。段安節《樂府雜錄》則徑將《破陣樂曲》歸入“龜兹部”,稱“《破陣樂曲》亦屬此部,秦王所製。舞人皆衣畫甲,執旗旆”。*丌娟莉《樂府雜錄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頁40。如果站在傳統儒家士人的立場,此際的宮廷音樂已完全背離雅樂傳統,玄宗《定大唐樂制》指出“但紀鏗鏘之節”已非王者“正聲”,*《全唐文》卷二四《定大唐樂制》,頁279上。直到明代,胡震亨仍有“西北胡戎之音,揉亂中華正聲”之嘆。*胡震亨《唐音癸籤》卷一四,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7年,頁133。
三 傳播、觀衆與意義變換
上文分析顯示出,《秦王破陣樂》與太宗特定的政治動機有關,意在以宣揚功德鼓吹政權合法性,這一做法並非憑空而來,有其歷史淵源和文化依據。其中重要一點,在於對內亞文化因素的吸收,而這一點還與此曲同時承載的對外宣威政治功能密不可分。我們可以透過這一樂舞的傳播和觀衆來討論這一問題。
音樂在用來欣賞和娱樂之外,還有强大的激勵和感染效能,這在中古政治傳統中並不鮮見。《晉書·劉疇傳》曾記下劉疇“以樂退敵”的故事:
少有美譽,善談名理。曾避亂塢壁,賈胡百數欲害之,疇無懼色,援笳而吹之,爲《出塞》、《入塞》之聲,以動其遊客之思。於是羣胡皆垂泣而去之。*《晉書》卷六九,頁1841。
《洛陽伽藍記·法雲寺》一則記載更典型。正光末年,征西將軍崔延伯出征高平之際,樂手田僧超在軍隊後方吹送《壯士笛曲》以助威,於是“聞之者懦夫成勇,劍客思奮。延伯膽略不羣,威名早著,爲國展力,二十餘年,攻無全城,戰無橫陣,是以朝廷傾心送之。延伯每臨陣,常令僧超爲《壯士聲》,甲胄之士踴躍”。*周祖謨《洛陽伽藍記校釋》卷四,北京,中華書局,1963年,頁158。隋朝裴矩在河西走廊以“焚香奏樂,歌舞喧噪”的方式震懾並招徠西域諸國的事件也爲後人熟知。*《册府元龜》卷六五六《奉使部·招撫》,頁7573。隋大業二年(606)突厥可汗來朝,煬帝特舉行大型樂舞表演,“盡通漢、晉、周、齊之術,胡人大駭”,煬帝深知音樂的宣威功能,於是“命樂署肄習,常以歲首,縱觀端門內”。*《舊唐書》卷二九《音樂志二》,頁1073。這些爲煬帝所重視的樂舞,正是針對“蠻夷三十餘國”所特有的震懾之術。*《册府元龜》卷九七四《外臣部·褒異一》,頁11274。到大業三年,隋煬帝“欲誇示突厥,令宇文愷爲大帳,其下可坐數千人;甲寅,帝於城東御大帳,備儀衛,宴啓民及其部落,作散樂。諸胡駭悦,爭獻牛羊駝馬數千萬頭”。*《資治通鑑》卷一八〇煬帝大業三年八月條,頁5632。同年隋煬帝還巡幸河西,令宇文愷製觀風行殿,宣威諸部,使得“胡人驚以爲神,每望御營,十里之外,屈膝稽顙,無敢乘馬”;*《資治通鑑》卷一八〇大業三年八月條,頁5633—5634。此後由於數量龐大的外族朝貢者前往東都,裴矩便“諷帝令都下大戲”,*《册府元龜》卷一七〇《帝王部·來遠》,頁1890。顯然是針對北族的專門安排。
太宗對於這一點自然也相當熟知,因此我們看到這樣的場景: 貞觀七年正月,太宗於玄武門設宴款待朝廷三品以上官員、地方州牧、蠻夷酋長,特命表演《七德舞》和《九功舞》,在場觀者“見其抑揚蹈厲,莫不扼腕踴躍,凜然震竦”,一起向太宗上壽稱,“此舞皆是陛下百戰百勝之形容”,隨後,羣臣一起高呼萬歲,四方蠻夷則在得到太宗准允後,親身參與到了舞蹈當中。*《舊唐書》卷二八《音樂志一》,頁1046。這種羣臣與藩使同歌共舞的場面,也與內亞文化傳統有關,曾見於北魏孝文帝朝:“太后曾與高祖幸靈泉池,燕羣臣及藩國使人、諸方渠帥,各令爲其方舞。高祖帥羣臣上壽,太后忻然作歌,帝亦和歌。遂命羣臣各言其志,於是和歌者九十人。”*《魏書》卷一三《皇后傳·文成文明皇后馮氏》,頁329。這一羣臣共舞的形式並未成爲唐朝慣例,杜佑《通典》描述唐朝正月大典樂舞寫道,“太樂令帥九部伎立於左、右延明門外,羣官初唱萬歲,太樂令即引九部伎聲作而入,各就座,以次作如是”,*《通典》卷一二三《開元禮纂類十八·嘉禮二》,頁3158。這時井然有致的秩序和景象,已與貞觀初年嘉年華式的狂歡場面大爲不同。*石見清裕曾大致介紹過唐代外國使節宴會禮儀上的音樂,但直接材料反映的情況基本上是開元以後的面貌,參《唐の北方问题と国际秩序》,汲古書院,1998年,頁488—490。顯然與唐初存在很大差異。
太宗顯然非常了解音樂之於北族的特殊意義,也以此爲籠絡、收編甚至統治對方的重要手段。《朝野僉載》就爲我們保留了這樣一個故事。西域某國進貢一位擅彈琵琶的胡人,太宗不願國人技輸一籌,便讓宮中一位樂人羅黑黑在帷幕後偷偷觀摩,待西域胡人演奏完畢,太宗隨即讓守在幕後的羅黑黑即興彈奏一曲,胡人以爲對方只是一名普通宮女,大爲驚嘆,含羞而去。這則故事的重點在於其結果: 西域各國聞此事後,“降者數十國”。*《朝野僉載》卷五,頁113;《隋書·音樂志下》:“六年,高昌獻《聖明樂》曲,帝令知音者於館所聽之,歸而肄習。及客方獻,先於前奏之,胡夷皆驚焉。”頁379。與此略同。針對貞觀年間炙手可熱的漠北悍部薛延陀,太宗采取了類似手段。他將新興公主嫁與薛延陀突利失可汗,在這次宴會中,羣臣陪坐,列陳寶器,並“奏《慶善》、《破陣》盛樂及十部伎,突利失頓首上千萬歲壽”。*《新唐書》卷二一七下《回鶻傳下·薛延陀》,頁6137。音樂在這裏仿若武器,誇示權威、彰顯國力的同時,還營造了一種强烈的震懾效果。
太宗不僅深曉音樂的政治功能,他還相當看重圖像宣威與震懾的作用,*Edward Schafer, “The Tang Imperial Icon”, Sinologica, 7.3, 1963,pp.156-160;皇帝畫像與國家祭祀之間的關係,參雷聞《論唐代皇帝的圖像與祭祀》,榮新江主編《唐研究》第9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頁261—282。因此“以圖記功宣威”也成爲貞觀朝的重要政治舉措。太宗曾在擒獲王世充、竇建德的汜水武牢關修建昭武廟,並立像。*《册府元龜》卷三一《帝王部·奉先》,頁313。長安崇業坊玄都觀也張挂太宗畫像,此像原爲閻立本奉詔繪製,“後有佳手傳寫於玄都觀東殿間,以鎮九崗之氣,猶可仰神武之英威也”,*朱景玄撰,溫肇桐注《唐朝名畫錄》“神品下”,成都,四川美術出版社,1985年,頁8。可見太宗畫像廣爲傳播,且受到民間祭祀和崇拜。貞觀十二年在長安建立景教寺院時,太宗“令有司將帝寫真,轉摸寺壁”。*《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據朱謙之《中國景教》附錄一,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頁224。太宗借畫像以爲塑造君王形象的重要手段,將自己轉化爲淩駕於一切的權威。這些圖像一經傳播,就具有政治宣傳的功能,用於宣示太宗的權威。正是如此,太宗纔命宮中專家,對一首原來只是流傳於坊間的俗謠,進行重新譜曲填詞,親自監督設計《破陣樂舞圖》,將其偉業以圖像、樂舞的視覺形式表現出來。這一太宗並未現身的樂舞,卻是以他本人爲絕對主角的。這些舉動背後有着類似的政治考量,即所謂“刊石紀功,圖像存形”。*《魏書》卷二三《衛操傳》,頁601。這些受命於太宗的製作,無疑承載着呈現帝王聲威、塑造太宗形象,並將之宣而廣之,最終教化大衆、收束人心的任務。
在識字率尚低、普通民衆主要以觀看而非閱讀、口耳相傳而非獨自欣賞的方式獲得資訊和知識的中古時代,圖像與樂舞展現國家權威和帝王形象的功能尤其值得關注。《秦王破陣樂》演奏於正月元會這一特殊場合也大有深意。《册府元龜》卷一九《帝王部·功業一》載,“貞觀一十三年二月辛酉,太宗克平沙漠,以爲州府,其都督、刺史、候(俟)利發等競遣使來詣,每元正朝賀,則數百千人,尋常馳使,道路不絕,老幼不憚遐遠,悉手持方貢”。*《册府元龜》卷一九,頁196。以圖像或樂舞宣揚個人威望和意識形態,並以入朝酋長蕃客爲媒介遠播域外。高僧玄奘貞觀十六年返回大唐、途經羯若鞠闍國時受邀見到戒日王。戒日王得知玄奘來自大唐國(當地人所謂“摩訶至那國”)後,便問:
嘗聞摩訶至那國有秦王天子,少而靈鑑,長而神武。昔先代喪亂,率土分崩,兵戈競起,羣生荼毒,而秦王天子早懷遠略,興大慈悲,拯濟含識,平定海內,風教遐被,德澤遠洽,殊方異域,慕化稱臣。氓庶荷其亭育,咸歌《秦王破陣樂》。聞其雅頌,於兹久矣。盛德之譽,誠有之乎?大唐國者,豈此是耶?*季羨林等《大唐西域記校注》卷五,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頁436。
此番發問透露出,秦王征伐戰績已遠傳西土,而戒日王所聞與唐朝對於太宗形象的官方論調全然一致,其中《秦王破陣樂》是最關鍵的載體。值得注意的是,這次會見是出於戒日王的特别邀請,其動機無疑和他耳聞唐太宗的各種事迹有關。
《秦王破陣樂》遠播印度,還可以通過《大唐西域記》另一記載得到印證。受到戒日王的委托,迦摩縷波國國王拘摩羅邀請玄奘返程途中前往該國。見到玄奘後,拘摩羅向其求證,“今印度諸國多有歌頌摩訶至那國《秦王破陣樂》者,聞之久矣,豈大德之鄉國耶?”*《大唐西域記校注》卷一〇,頁797—798。玄奘回答此曲正在於贊美唐朝君主的德行,拘摩羅王則進一步表達了親自東遊、稱臣朝拜的願望,足見樂舞作爲政治宣威手段所起的巨大作用。有學者質疑這兩處記載出於玄奘虛構,但無直接證明。認可其真實性的學者强調,《秦王破陣樂》本質上頗似吟游詩人傳唱英雄事迹,“這種形式正是印度人習慣的口口相傳的唱誦的表現方式,其內容又是與戰爭勝利(破陣)相關(追求勝利、贊頌勝利,這正是傳統印度教,尤其是濕婆派和毗濕奴派最爲推崇的品質和行爲),非常符合印度人的審美取向”。*陳遠《〈秦王破陣樂〉是否傳入印度及其他——兼與寧梵夫教授商榷》,《南亞研究》2013年第2期,頁147。與印度人審美取向有所契合只是一方面,更重要者在於《秦王破陣樂》這一作品所反映的太宗及其帝國强勢崛起的現實。無獨有偶,與戒日王口吻相似,高句麗一位年邁老臣,勸説其國君不宜與唐朝對抗,理由就是“吾聞中國大亂,英雄並起,秦王聖武,所向無敵,遂平天下,南面爲帝,北夷請服,西戎獻款。今者傾國而至,唐兵之壯健者悉來,其鋒不可當也”,*《册府元龜》卷一一七《帝王部·親征二》,頁1282。反映了“秦王破陣”之名所形成的威勢。
《秦王破陣樂》也成爲唐朝與吐蕃交往的重要媒介。貞觀十五年(641),文成公主入藏時,其服飾禮儀之美令松贊干布大爲贊賞,隨後派大臣子嗣前往唐朝國子監修習詩書。*《通典》卷一九〇《邊防六》,頁5172。數十年後,金城公主入藏聯姻,中宗念及公主年幼,更是特别賜予“錦繒别數萬,雜伎諸工悉從,給龜兹樂”。*《新唐書》卷二一六上《吐蕃傳上》,頁6081。長慶初年唐朝使者劉元鼎前往吐蕃會盟時,在吐蕃贊普正式招待宴席上看到這一場景,“飯舉酒行,與華制略等。樂奏《秦王破陣曲》,又奏《涼州》《胡渭》《録要》雜曲、百伎皆中國人”。*《全唐文》卷七一六《使吐蕃經見紀略》,頁7360下。《秦王破陣樂》此時已成爲吐蕃正式宴席中的演奏曲目,而樂手、百伎則來自中國。這一局面的出現,未嘗不是唐蕃長期以來文化、政治互動的結果,這支舞樂在其中的政治意涵和功用可見一斑。
貞觀後期,“四夷大小君長爭遣使入獻見,道路不絕。每元正朝賀,常數百千人”,*《資治通鑑》卷一九八唐太宗貞觀二十二年二月條,頁6253。《秦王破陣樂》成爲元會朝賀禮儀當中的重頭戲,其傳播速度和範圍可想而知。貞觀二十二年,太子李治爲其母長孫皇后追福,修造大慈恩寺,命玄奘爲上座,當年十二月戊辰,皇室特别舉行了盛大莊嚴的迎像入寺儀式,“衢路觀者數億萬人”,這次儀式最後的高潮,是在大慈恩寺殿中,“奏九部樂、破陣舞及諸戲”,*慧立、彥悰著《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七,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頁156。反映了這支具有鮮明政治功能的樂舞在貞觀時代至高無上的地位。
《秦王破陣樂》在太宗去世之後得以延續,名稱有所改變。高宗朝更名爲《神功破陣樂》,至玄宗朝則作《小破陣樂》。規模大爲縮減,形式也有所不同。《小破陣樂》演奏的場合是玄宗生日千秋節,史載每千秋節有“宮人數百,衣錦繡衣,出帷中,擊雷鼓,奏《小破陣樂》,歲以爲常”。*《新唐書》卷二二《禮樂志十二》,頁477。這時所奏《小破陣樂》只是助興添彩之用,已喪失《秦王破陣樂》特有的政治內涵和寫實功能。
“秦王”離世後的《破陣樂》顯然隨之喪失了其本來內涵和價值,這恰恰説明這支樂舞與其創制者之間密不可分的關係。於是時至中唐,元稹《法曲》一詩中仍然這樣寫道:“漢祖過沛亦有歌,秦王破陣非無作。作之宗廟見艱難,作之軍旅傳糟粕。”*《全唐詩》卷四一九,頁4617。元稹此詩或與白居易《七德舞》一樣,和閱讀《貞觀政要》、《太宗實錄》密不可分。*吴兢在《貞觀政要》之外還撰有《太宗勳史》(《新唐書》卷五八《藝文志二》,頁1467)一書,很可能也爲元白所參考。因此,即便《破陣樂》當時已不過是太常立部伎所奏諸曲之一,*關於坐、立部伎的性質和特色,參左漢林《論唐代二部伎的性質及其與多部伎的關係》,《湖南大學學報》2007年第2期,頁131—134。元稹依然强調其與太宗破陣之間的對應關係,所謂“太宗廟樂傳子孫,取類羣凶陣初破”,並極力批判後世的改編,即“宋沇嘗傳天寶季,法曲胡音忽相和”。《立部伎》詩夾注稱:“太常丞宋沇傳漢中王舊説云: 明皇雖雅好度曲,然而未嘗使蕃漢雜奏。天寶十三載(754),始詔道調法曲與胡部新聲合作,識者異之。明年祿山叛。”*《全唐詩》卷四一九,頁4617—4618。這裏直接在胡曲和安祿山反叛之間建立起了因果關係。白居易《立部伎》與元稹論調一樣。*《白居易集箋校》卷三,頁150—152。對於這些中唐士人而言,太宗作爲大唐明君正主的地位已然無可置疑,《秦王破陣樂》也就隨之成爲雅樂正聲,擊鼓、吹笙、鳴笛、舞劍等都成爲天寶以後的篡改,終使得雅樂淪喪、胡音橫行,這顯然反映了中唐士人對《秦王破陣樂》及其歷史的記憶、想象與曲解。

結 論
此前已有學者提及《破陣樂》作爲權力象徵的意義,*沈冬《咸歌破陣樂,共賞太平人——〈破陣樂〉考》,頁83—89。卻未對其得以成立的背景進行具體分析。本文以爲,《秦王破陣樂》從其樂器舞蹈到演奏形式,皆非中土儒家傳統而言的雅樂。*如顏之推所言:“禮崩樂壞,其來自久,今太常雅樂,並用胡聲。”《隋書·音樂志中》,頁345。其最初功能是北周武帝以來的凱樂,屬性則是曹魏以來的鼓吹鐃歌系統,樂舞形式當與北魏以來的內亞文化絲縷相連。就歷史發展脈絡而言,它既不算“正統”,也不是“異物”,而作爲宮廷盛典,它又是初唐的“發明”,是受時代風尚和個人趣味左右之下對既有資源的重新利用和再造,成爲一套被廣爲接受、受到特定規則約束的禮儀實踐和政治戲劇,以反覆演繹太宗的戰功榮耀,展現貞觀王朝的權威和正統。曹魏以來的鼓吹鐃歌製作後來又延續至五代,到宋徽宗崇寧年間議定大晟樂時,則以“所奏皆夷樂也,豈容淆雜大樂”爲由,*《宋史》卷一四二《樂志十七》,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頁3362。關於大晟樂,參Joseph S. C. Lam, Huizong’s Dashengyue, a Musical Performance of Emperorship and Officialdom, Patricia Buckley Ebray and Maggie Bickfor eds., Emperor Huizong and Late Northern Song China, The Politics of Culture and the Culture of Politics,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6, pp.395-452。徹底將其罷黜,可見透過宋代文化重建之後儒家禮官的眼睛,這套樂曲全然不符禮樂傳統。這一點再次提醒我們應該謹記初唐的時代背景。當時的政治並未完全陷入經典和禮儀枷鎖之中,君主尚可以向多元的歷史遺產尋求治國之道。作爲“創世”英雄的敍事史詩,《秦王破陣樂》無疑與《真人代歌》、《闕特勤碑》、《毗伽可汗碑》等作品在創作意圖上更爲親近,*耿世民指出,《闕特勤碑》、《毗伽可汗碑》的突厥文部分出自其侄藥利特勤之手,在一定程度上可説是兩篇英雄敍事詩。參《古代突厥文碑銘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05年,頁47。這類作品對觀者的要求,並非與主人公發生共鳴,而是要對主人公的活動表示驚愕,*本雅明《什麼是史詩劇》,漢娜·阿倫特編,張旭東、王斑譯《啓迪: 本雅明文選》,北京,三聯書店,2008年,頁161。成爲徵集服從與忠誠的重要手段。*這與清末民初充當意識形態重要展演形式的“國樂”與“國歌”異曲同工。參小野寺史郎著、周俊宇譯《國旗、國歌、國慶——近代中國的國族主義與國家象徵》,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年,頁104—133。
儘管後人看來,這支樂曲似乎只是王朝宮廷樂曲之一,但對於那些目擊者而言,這支樂曲則使太宗本人、貞觀朝廷及其權力成爲清晰而合理的存在。《秦王破陣樂》演繹着勝利者的姿態和雄心,君王的威信和權力,同時也引發觀者內心交織着愛戴、感激、服從和尊敬等的複雜情緒。因此,貞觀元年元會典禮中,這支樂曲既是對新君主即位的宣告,也是對羣臣諸酋集結的命令,表達舉國歡騰的同時,更是對漠北敵國的警告。它的意義是多元的。這一樂舞儀式無形中導致在場者身份意識的轉變,使他們得以心照不宣地明確彼此間嶄新的身份等級和政治關係,並一定程度上形成了某種集體情感。即便暴力、征伐與屠殺本身充滿了血腥與不義,但這支樂舞卻通過對暴力、征伐與屠殺的演繹和闡釋,即新君終結了混亂與無序,剪除了割據軍閥的威脅,形成一套撥亂反正、抵達正義的敍事邏輯。
初唐大型宴會某種意義上可被視爲或大或小的儀式複合體,其中《秦王破陣樂》便是一場描繪勝利、革命、權威、攀附與服從的典範戲劇,具有“揚德建威、勸士諷敵”的功能,在文武百僚和四夷酋長面前多次上演。關於這支樂舞的內涵,需要從其發明人、設計者、演奏場合以及在場觀衆的不同立場去探求,而其中最爲核心的人物,無疑是秦王本人。也就是説,從誕生那一刻起,這支樂舞便深深滲透着李世民本人的意志和欲望: 透過展演國家的政治威望和意識形態,灌輸官方價值標準,塑造並維繫秩序,成爲傳播貞觀王朝形象最有力且有效的媒介。也正因此,太宗之後,這一曲目和“天可汗”之名一樣延續了下來,其形式、性質與功能隨着君主更迭、時代演進各有不同,成爲後世皇帝模仿、改造、挪用的資源,但無論如何已不能承載其誕生之初的政治職能。究其原因就在於,隨着實物的消逝,一個象徵符號或許還能延續下去,但由於語境、組合以及觀衆的嬗變終將成爲“再造”的歷史產物,其原本意義則隨之衰減、逐漸蛻變、徹底改變甚或完全消失。
(本文作者係中山大學歷史學系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