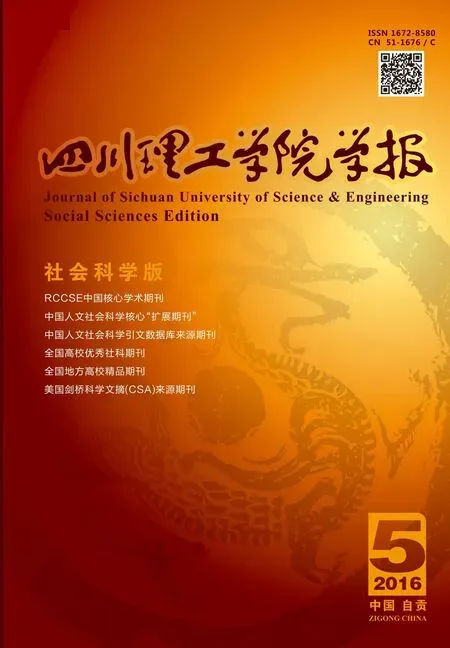违法信息披露:一种全新的行政实效性确保手段
马有芳
(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重庆401120)
违法信息披露:一种全新的行政实效性确保手段
马有芳
(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重庆401120)
市场经济中信息本身是不对称的,在这种市场失灵的情况下如何进行政府规制成为长期以来的研究重心。传统做法是对扰乱市场经济秩序及破坏安全、环境的行为进行经济性规制或社会性规制,但随着实践中行政不法现象越来越复杂,传统做法的高成本缺陷逐渐暴露。在此夹缝及信息公开的大背景中,违法信息披露作为一种全新的规制手段找到了一席之地,并被广泛运用于道路交通、产品质量、食品安全、环境保护等领域,发挥传统规制手段无法企及的优势。但目前对该手段的认识与应用呈现出杂乱无章的局面,尤其是有关违法信息披露的性质问题,既有事实行为说,又存在各种不同形态的法律行为说,这些观点并未从该规制手段的内部法律关系角度进行认定,导致了认识的片面化。关于违法信息披露的粗线条、点状式规定与研究路径很可能为行政主体权力滥用提供新的契机。为高效挖掘此规制手段之作用,有必要从大处着眼,改分散性研究为整体框架式研究,从性质、合法性、正当性、具体应用与法律限制的角度规范性地把握此问题,使其在现有行政法中找准自己的位置,以更好地与行政法框架下其他理论和制度相衔接,真正为行政规制目标之实现而发挥强力。
违法信息披露;规制手段;事实行为;法律行为;行政强制执行;实效性确保
一、问题提出
近年来,酒驾事件在我国频繁发生,酒驾违法人员上至一线明星,下达普通大众,实令人痛心疾首。据交通部统计数据显示,因驾驶员酒后驾车所导致的交通事故平均每年有25万余起,造成约5万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近13亿[1]。酒驾案发率一直居高不下,引来社会各界的关注热潮。为严厉打击、防范酒驾违法行为,各地公安局交警部门纷纷采取措施,坚持落实抄告、通报制度,实名曝光酒驾违法者,部分地区还设立了交通违法曝光台,提醒广大驾驶人员自觉告别酒后驾驶[2]。在行政领域,曝光作为一种执法手段,已被越来越广泛地使用。例如产品质量不合格企业名单的曝光、食品安全风险警示、违章驾驶拍照曝光等。从行政法角度分析,“曝光”并非专业词汇,学界对其称呼也各不相同,但是本质内涵并无太大差异,本文将曝光称作违法信息披露。随着实践中行政不法现象越来越复杂,传统做法的高成本缺陷逐渐暴露,在此夹缝及信息公开的大背景中,信息披露逐步崭露头角成为一种重要的规制手段,发挥传统规制手段所无法企及的优势。那么何为信息披露,这种信息披露的性质到底是什么?与行政处罚的界限何在?正当性在哪里?披露过度如何救济?此种规制手段正面能量的发挥必须建立在消弭上述分歧之基础上。因此,本文就期厘清信息披露的相关问题进行探讨。
二、国内外研究状况
国内关于违法信息披露的研究总体偏少,但也有部分学者尝试对这一问题进行系统化阐释。杨建顺《行政法总论》一书中重点介绍了违法信息披露的含义、性质、原则及效力,并区分作为事实行为的政府信息公开与作为制裁行为的公布违法事实;章志远主张对违法信息披露进行类型化研究,根据法律形式理论对违法信息披露的性质作声誉罚、行政处罚结果公开、公共警告、行政强制执行的区分,并建议从行使条件设置、程序遵守和救济机制三个角度对其进行有效控制;王周户则反对这种类型化研究,认为违法信息披露是一种法律行为,是行政主体为督促行政相对人履行义务而采取的一种以公告违法事实方式实施的行政强制执行。
国外对这一问题也有一定研究。德国学界倾向于将违法信息披露认定为事实行为,哈特穆特·毛雷尔在《行政法学总论》一书中将与违法信息披露同质的“公共警告”视为事实行为的一种特殊形式;日本学者远藤博也与阿部泰隆在《行政法(总论)》中将违法信息披露认可为新的强制手段;盐野宏在《行政法总论》中将违法信息披露划归行政上确保义务履行的制度。美国将违法信息披露称为“作为制裁的信息披露”,欧内斯特·盖尔霍恩把行政主体的不利信息公开举措作为信息工具,并就其功能、限制与条件等进行深入研究。与其他国家相比,美国更侧重违法信息披露在权限、内容、程序等方面的法律控制研究。
概观国内外研究状况,学术界对这些问题依旧歧见纷纭。国外研究的发展趋势是在信息行政的背景下逐步承认违法信息披露的法律性,并在认可这种新型规制手段正当性的基础上深入探讨违法信息披露的法律控制。我国关于违法信息披露的研究较为粗糙。在属性认定方面,缺乏一个结合时代背景与相关制度功能价值的综合性把握;合法性依据层面,局限于简略的法条罗列,规范性分析匮乏;法律控制层面,过于笼统,没有结合违法信息披露的不同种类及当事人违法的不同情状分类型讨论。粗线条、点状式规定与研究路径为实践运用带来了困境,为改变这种滞涩难行的局面,有必要深化相关研究。
三、违法信息披露的定性分析
违法信息披露是指行政机关出于公益考虑,将执法中获得的行政相对人违法或不履行行政法义务的行为或事件通过一定的媒介向社会公开,并根据由此产生的社会批评这一心理强制来实现特定的行政管理目标[3]。作为一种全新的政府规制手段,信息披露被越来越多地应用到行政法诸领域,对其合法性、实效性及法律规制的研究也如火如荼地展开,其中合理定性是一项前置性与基础性工作,其奠基作用不容忽视。
(一)事实行为与法律行为之争
1.传统事实行为说
持传统见解的学者热衷于将违法信息披露定性为行政事实行为。毛雷尔在《行政法学总论》一书中将与违法信息披露同质的“公共警告”视为事实行为的一种特殊形式,他认为至少从当时来看,将行政警告确定为一种新管理方式的条件还不成熟[4]。韩国学者金东熙也在其撰写的《行政法I》一书中提到违法事实的公布本身是不发生任何法效果的事实行为[5]336。我国台湾地区由于受德国法影响缘故,倾向于将其认定为事实行为。
近年来,随着政府不断利用调查所获违法信息作为制止不法活动产生、继续的手段,学者们逐步认识到违法信息披露可作为传统规制方法的一种替代或补充方案,对事实行为说开始反思,传统观点无论是在理论层面还是实务层面都受到了挑战。章志远基于类型化研究将违法事实公布区分为:作为声誉罚的公布违法事实、作为公共警告的公布违法事实、作为行政处罚结果公开形式的公布违法、作为行政强制执行手段的公布违法事实[6]。事实行为说日渐式微,但目前持此说者大有人在。针对传统与新近学说之间的激烈角逐,有必要对违法信息披露的性质进行深入探究。
2.违法信息披露的层次性
判断一个行为是否属于法律行为主要看两个要件:一是意思表示;二是法律效果[7]。即该行为首先应根据行政主体的意思表示作出,其次以产生、变更、消灭公法权利义务为目的。事实行为系行政主体所为的不以产生特定法效果,而是以事实效果为目的的行政行为形式[8]。就作为规制工具的违法信息披露而言,之所以性质难判断,主因是与传统行政行为只涉两方主体、一种法律关系不同,它囊括三方主体:行政主体、相对人、社会公众,涉及多种法律关系,法律效果的发生需借助第三方力量之发挥。一方面,从行政主体与相对人间的关系(主关系)分析,违法信息披露属于法律行为。捕捉时代脉搏,违法信息披露不再仅仅是单纯的提醒式或预防式公布,而变为一种实实在在确保行政法义务得以履行、行政合法状态得以恢复的信息规制行为。行政主体采取这种规制工具,目的就是为影响相对方的公法行为,激励他采取合法行为,回归适法状态。对此有学者指出此种规制仅产生间接法律效果,与法律行为追求的直接法律效果不一致。笔者认为这种看法割裂了信息规制的整体性,违法信息披露是一项系统性手段,由多阶段行为组合起来共生影响力,在多方配合下最终产生法律效果,这与传统单靠行政主体强制性权力的法律效果实现方式截然不同。因此,这一层次的违法信息披露是以实现某种法律效果为目的,具有处分性,可以划归法律行为。另一方面,在行政主体与社会公众之间关系(次关系)层面,违法信息披露属于事实行为。行政主体只是为公众提供相关信息或是作出某种风险警示,并没有产生、变更、消灭公法权利义务关系的意思表示。虽然违法信息披露法律效果的产生要借助社会公众的力量,但就这一阶段的信息提供本身来说应将其定性为事实行为。有学者提出传统学者主要看重行政主体与社会公众之间的关系,自然倾向于将其认定为事实行为,当然这也与当时信息规制作用的发挥相当薄弱而密切关联。但相比行政主体与社会公众之次关系,行政主体与相对人之主关系更值得我们去把握,下文重点探讨作为法律行为的违法信息披露。
(二)行政处罚与行政强制执行之争
从行政主体与相对人关系角度,违法信息披露是一种法律行为,那么究竟这种法律行为的具体表现是什么?众学者歧见纷纭,有行政处罚说、行政强制说,还有学者主张类型化处理,笔者认为它是一种全新的行政实效性确保手段。
1.违法信息披露不属于行政处罚
首先,从行政处罚的形式要件分析,依《行政处罚法》第39条、第40条规定,行政机关给予行政处罚,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并在法定期间送达当事人。而违法信息披露则没有这种严格要求。其次,从实质要件分析,行政处罚以制裁性为本质特征,属于行政制裁范畴。翁岳生曾指出,行政罚系对违反行政义务者所施加之不利益,藉由此不利益,以非难违法,并发挥吓阻作用,故具制裁性质,若施加不利益之目的,在于督促履行应尽义务或实现其他行政目的时,则非行政罚[9]。很明显,处罚是对相对人施加额外的不利益,使其承担新的义务,制裁是其本质特征。违法信息披露是通过不利信息公布而迫使相对人履行原来的义务、停止原本违法的行为,或者制止业已泛滥的同类违法行为、对未来风险进行控制。披露作为一种规制方式,虽通过社会批评对相对方有一定的惩戒作用,但其目的并非惩戒,而是实现特定行政管理目的。再次,二者实现法律效果的机理不同。处罚是由公权力一方单独完成,而违法信息披露是公私协力实现行政法目的,法律效果是靠市场效应、舆论监督的作用完成。
有学者认为违法信息披露与行政处罚中的警告、通报批评有异曲同工之效,均属于申诫罚。笔者不这么认为,警告、通报批评(处罚而非处分意义上之通报批评)本质是一种制裁,是行政主体直接施加的声誉方面的不利益,这种不利益的施加本身就是立法追求之目的,违法信息披露的目的并非制裁,而是原义务的履行、特定管理目标的实现,公布违法信息仅作为手段存在。而且,警告、通报批评一般针对的是轻微的行政违法行为,违法信息披露针对的是严重的违法行为,是经处罚后,行政机关责令改正仍不改正,继续实施违法行为或者这种违法现象已泛滥,需以披露方式解决。
2.违法信息披露是一种全新的行政实效性确保手段,可能属于实效确保手段中的间接强制执行手段,也可能属于其中的其他新型手段
行政实效性确保手段是行政法律法规赋予公民一定的义务或禁止其从事某些行为,对违反这些义务或禁止性规定的行为,出于公益目的,设计了确保义务履行或纠正违法状态的各种手段;而且即使不是以向相对人赋予义务或以不履行义务为前提的行政违法状态,由于有必要消除上述状态,确保适当的行政状态,因此规定了相应的手段[5]317。违法信息披露发挥作用的机理便是通过公布违法事实的手段确保义务履行、制止或预防类似违法现象的泛滥,回归适法状态,与实效性确保手段的设计初衷不谋而合。在传统实效性确保手段中,有相对直接的行政强制,也有作为间接手段的行政处罚。最近几十年,日韩学者在传统手段之外发现了很多新手段,比如:违法事实公布、授益行政行为的撤回、官许事业限制等。余凌云在《行政法讲义》中将实效性确保手段分为三类:处罚、强制、其他新型手段,并将违法事实披露列入其他新型手段中[10]。对此笔者不是完全同意,违法事实披露其实可以分为两类:一是行政主体已对违法行为作出处罚决定,相对方不履行该决定,或者限期不改正,继续实施违法行为,行政机关采取违法信息披露的方式迫使相对方合法行为,此即间接强制执行手段;二是相对人已履行处罚决定所规定的义务,不存在可供执行的法律文书,但由于现实生活中该违法现象泛滥成灾,又与民众生命、健康安全休戚相关,必须严厉打击,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在这种情况下,为消弭现实违法状态的继续发生,有必要采取手段予以遏制,以实现行政管理目的。此类之信息披露可归入其他新型手段中,目的在于对特定违法现象进行规制或风险预防。因此,笔者不赞成一刀切全部归入其他新型手段。
总之,对违法信息披露的定性应当分情况处理,在行政主体与公众关系层面将其视为事实行为,在行政主体与相对方关系层面,宜将其归入法律行为的范畴,这种法律行为是一种全新的行政上实效性确保手段,可能属于间接强制执行手段,但并非行政处罚。具体见下图1。

图1 违法信息披露的法律行为关系图
四、违法信息披露的合法性寻找与正当性论证
(一)合法性寻找
“无法律,无行政”是贯穿公法领域的一条重要格言[11]。行政主体实施行政活动必须具有法定依据,没有法律、法规、规章规定,不得作出影响相对人权益或增加相对人义务的决定,否则须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因此违法信息披露须具规范依据才可做出,这是依法行政的基本要求。与违法信息披露联系最紧密的规范是《信息公开条例》,本条例虽未直涉违法信息披露,但可通过规范分析解读出来。政府信息可以分为两种:一是公信息,即政府自己形成的可反复适应之信息;二是私信息,是行政主体在执法调查活动中获取的有关特定相对人之信息。私信息以不公开为原则,公开为例外。那么作为私信息的违法信息到底有无公开必要,需结合规范进一步分析。根据该条例第九条,政府信息主动公开情形中第二项是需要社会公众广泛知晓或参与,该项是当下合作行政在立法上的有力反射。需要公众知晓或参与意味着相关事项涉及公众切身利益,抑或传统执法手段滞涩难行,否则即无需公众参与,因为附加公众参与随之而来的是成本增加。由于该条第一项已单独列出“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切身利益”,此处“需社会公众广泛知晓或参与”意指后种情形。主动公开的信息如果是行政主体自制公信息,一般均可以,如果要公开相对人之私信息,则须判断有无特别需求,传统执法手段是否捉襟见肘,是否需公开私信息以借助公众支持。就酒驾问题来说,之所以曝光是因为现实生活中酒驾问题相当严重,传统手段已显力不从心,否则醉驾也不至于入刑。通过公布信息方式,实际是引起公众对此现象的关注,公私协作解决这一问题。另外,本条例第十条在主动公开的范围内罗列了十一项应重点公开的信息,第十一项涉及环境保护、公共卫生、安全生产、食品药品、产品质量的监督检查情况,那么酒驾是否属于安全生产范畴?依据《安全生产法》第二条规定,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及监督管理,适用本法。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对道路交通安全另有规定的,适用其规定。也就是说广义上可将酒驾列入其中,只是出于道路交通安全的特殊性与重要性,另行立法。再者从立法目的考量,不论食品药品还是安全生产,重点公开更多是要规制尚未发生之风险,非个案解决这些领域的问题,这与公开酒驾的初衷不谋而合。另外,酒驾是否可列入安全生产也是个政策选择问题,需要行政主体把握。因此违法信息披露在信息公开条例中可挖掘出合法性。当然除了信息条例,其他部门法规范也有关涉违法信息披露,比如食品安全法、环保法等,在此不一一赘述。
(二)正当性论证
行政活动不仅要求具备合法性,而且追求合理性、正当性,以实现适度行政。当前违法信息披露风靡于众多行政法领域,那么这一规制手段为何会出现?行政主体又为何青睐使用这种手段?回答这些问题有必要回归其正当性论证。
1.违法信息披露的运用有其现实原因——传统政府规制手段失灵,无法有效解决日益复杂的现实难题
经济快速发展的当下,重大事故频繁发生,不断侵及公众生命、健康安全。这些事件背后折射出企业和个人的反社会倾向,为追求自我满足或自我利益最大化,不惜牺牲社会利益,同时也可管窥出政府监管失语。在食品药品、安全生产、道路交通等频发事故领域,单靠传统监管手段已无力实现行政管理目标,无论个人还是企业都认为,发生事故无非只是钱财遭殃,处罚完后依旧肆无忌惮。针对这种情况,行政主体开始积极探索全新方式以弥补传统规制手段的不足,违法信息披露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逐步脱颖而出。此规制手段虽然也有信息公开所具有的知情权保障功能,但它超越了知情权,是政府下意识地将其作为一种纠正违法或风险预防的规制手段。该手段在原处罚基础上进一步提高违法成本,对潜在的违法行为进行抑制,不仅解决了传统手段无法解决之难题,而且缓解了行政任务多元化与行政规制资源有限性之间的矛盾[12]。另外,违法信息披露与传统规制手段相比,成本低廉,通过舆论监督来实现对实在违法者和潜在违法者的自我约束,效果波及范围更广。因此,在当前信息公开的大背景下,信息规制无疑可以发挥更有力的作用。
2.违法信息披露符合合理性权衡要求
所谓合理性权衡是指被采取的措施是否符合法律目的,手段与目的之间是否相称,采取该项措施时是否有对公私利益进行衡量。毛雷尔曾指出,无论是在基本权利审查中,还是作为行政法一般原则,比例原则都具有重要作用,它既适用于是否发布公共警告,又适用于如何发布公共警告。行政主体采取违法信息披露的目的是促使相对人履行行政义务、消除违法状态,并对潜在的违法行为进行预防,从而实现行政管理目标。这一目的,毋庸置疑,符合法律规定。至于手段与目的之间是否相称涉及公私利益权衡。依据均衡性原则,行政主体实施行政活动,对相对人个人利益的干预不得超过实现行政目的所追求的公共利益。个人虽不因其隐私成为公共记录的一部分而丧失该隐私权[13],但是为实现对重大公益的倾斜性保护,相对人的隐私权有必要作出让步。当然此让步必须建立在对私益与公益权衡的基础上,权衡的标准可采取成本效益分析,如果对一人权益的干涉可以实现对社会中该类违法现象的控制或预防,那么该手段就是值得采取的。违法信息披露是为了实现重大公益而干涉个人权益,在具体运用过程中要进行严格的衡量才可适用。在酒驾问题上,目前酒驾事故泛滥,因酒驾导致的死亡人数平均每年以7.3%的速度增长,重视交通安全公益顺应了公众诉求,此时保护公众生命、健康的价值远大于个人权益保护,维护交通公益也自然是大势所趋。
3.违法信息披露能够发挥具体作用,具备实效性
首先,这种规制手段可以确保行政法上义务的履行或违法状态的纠正,并对相对人再犯有阻却功能。违法信息公布发挥作用的机理是借助舆论力量,引发社会谴责,对相对方形成精神压力或商誉影响,迫使其痛改前非,并以此为戒不再触犯法律。这种精神抑制作用的产生源于中国人的耻辱观[14]。当社会集体对一个人进行非难时,他内心会产生浓烈的羞耻感,这种内心压力会促使他以后采取适法行为,但这种精神力量的发挥并非像学者所言源于“熟人社会观”[15]。其次,违法信息披露对潜在的违法者有教育与警示作用。披露的原因之一就是相关违法行为屡禁不止,为预防该类不法行为继续泛滥,防止有违法倾向的民众径直走上违法之途,行政主体创造性选取了这一规制方式。再次,从实证分析的角度,违法信息披露也确实具有实效性。实践中,不论是酒驾曝光台的设置,还是食品中毒信息的披露都有所成效。但仍需注意的是若被披露者充耳不闻,违法信息公布很难发挥效果,此时可以将其与其他行政实效性确保手段相衔接,以督促相对人履行行政义务。
五、违法信息披露的限制之探索
盐野宏有言:关于个人信息的处理如果欠缺适切性的话,就会发生不当的侵害个人权益的事情[16]。作为一种全新的实效性确保手段,违法信息披露的确能发挥一定的规制效果,但一种常态化存续的制度设计总会有其条件约束,否则过犹不及,不仅会对相对方的名誉、商誉及其他利益造成巨大的持久性损伤,而且还会折损政府公信力。因此有必要对其使用严格把关。
(一)披露内容
违法信息披露固然可发挥一定的规制效果,但是否任何领域的违法信息均可公布?如果不是,允许披露的信息类型到底是什么?其实违法信息披露并不是在所有的行政法领域都可收获良效,运用不当会侵害当事人基本权利。虽然法律对信息披露的相关内容并不是都有明确规定,法律也没办法规定那么细,而更多是赋予行政主体裁量权来解决。但笔者认为就哪些领域的违法信息应披露这一问题必须要有规范依据,法律法规必须限制违法信息披露的适用领域,否则会出现乱象丛生的局面,不仅起不到规制违法现象的效果,反而会发生一连串负面效应。
目前涉及到违法信息披露的法律主要有:《环境保护法》、《水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食品安全法》、《产品质量法》、《安全生产法》、《证券法》、《招标投标法》、《标准法》、《对外贸易法》。除了法律外,规定违法信息披露的还有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法规层面主要是《政府信息公开条例》、《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禁止传销条例》等,部门规章层面有《注册税务师管理暂行办法》,规范性文件有《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促进城市园林绿化事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观察分析这些法律规范,不难发现这些领域不是与国家利益休戚相关就是与公共利益紧密联系,其中涉及公共利益者居多。将这些领域的违法行为予以公开是个人利益与国家、公共利益权衡的结果。但是值得思考的是,目前违法信息披露的合法性依据过于分散,法律中有法规中未涉及之领域,法规中亦有法律中所没有之领域,毋宁说规章及规范性文件了。鉴于这种凌乱现状,笔者认为应当在作为违法信息披露总括性依据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比较全面的总结违法信息公布的适用领域。目前《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明确规定的私信息公开领域集中在封闭式的环境保护、公共卫生、安全生产、食品药品、产品质量领域,我们可以在此基础上添加:道路安全、价格标准、招标投标、对外贸易等,使得违法信息披露领域更加明朗化[17]。
(二)披露的原则和程序
知晓披露对象仅仅解决了初期阶段问题,怎么披露无疑是重中之重。违法信息应当在一个多大的地域内公开?受众范围如何?披露应依据怎样的程序展开?披露时间是否有限制?这些问题都须透彻参悟,可事先规定的尽量予以制式化,需结合具体情况分析的,尽量确定分析要点,以防行政主体如无头苍蝇随意适用该手段,乘兴而去,败兴而归。
首先,分情况、分类型地尽可能缩小违法信息披露的地域范围及受众范围。信息披露的方式无外乎三种:(1)向特定的人群披露,比如家人、小区居民;(2)向当事人所在单位以及保险公司、社会性组织披露,形成联动作用;(3)向不特定社会公众披露。怎么分对象、轻重缓急地适用不同的披露方式是摆在现实面前的一大难题。笔者认为对违法行为通过其他方式可解决的,则无需借助公开方式。即使有必要使用信息披露手段的,也不一定非要面向不特定社会公众公开,可以视情况并结合社会效果,选择公开的地域、人群。如果当事人首次违法,情节轻微,那么将其违法信息公开就变得不合时宜;但如果相对人屡教不改,且该违法现象还未发展为社会事件,此种情况下只适合在特定人群中披露,尤其是在当事人家人面前。有些违法行为当事人虽首次实行,但鉴于此类违法现象发案率过高,已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则需向一定地域的不特定社会公众公开,比如食品中毒问题、酒驾现象、药品安全等。当然这也不可绝对化,比如卖淫嫖娼问题,将这些违法者信息直接向单位甚至社会公布就欠缺适当性,因为卖淫嫖娼很敏感地涉及个人隐私。在公私泾渭二分关系已被打破的现代社会,公共领域的隐私权保护日益获得合法性,但公显私隐观念下显与隐的尺度如何把握,社会中隐私权的界限何在实难抽象确定[18],在此背景下宜采取保守方式,不予公开,待公私合作可详细予以分辨后再考虑是否披露。
其次,对违法信息披露应设置严格的程序壁垒。程序是实体的最好保障,防止信息披露滥用除了对披露的内容、范围进行限制,还可从程序角度入手,拉张该规制手段的合理性宽度。第一,建立严格的事前审查机制,以防不当披露损害当事人权益。对作为间接强制执行的违法信息披露,应着重分析该法定职责的履行是否与公民的切身利益休戚相关,是否必须借助公众力量相对方才有可能履行。此处可规定优先选择其他间接强制执行方式,其他方式没有效果时才可启动违法信息披露方式。如果违法信息披露是为了缓解业已泛滥的违法现象或风险预防,则需重点审查现实生活中该类违法行为是否频繁发生,是否严重危及公众利益。这就需进行细致的实证评估,锁定几个时间、地点,计算违法行为发生的频率,预估复发的可能性。当然任何调查研究都会有误差,这就需相关专业人士尽可能科学地考虑相关因素,多次采样,综合分析。如果违法信息披露的目的是双重的,即履行法定义务与制止、预防泛滥的违法现象两个目的之间发生竞合,则可采便宜原则,只需重点审查一种目的即可。经过审查,确需运用违法信息披露方式的才可使用。如果当事人已履行法定文书规定义务,且该类违法现象尚未发展为社会事件,不足通过公布方式预防,此时如再使用违法信息披露,就是滥用裁量权。第二,经审查需公开的应当在公开前将披露原因、方式告知当事人,当事人有异议的,应当允许其陈述、申辩,必要时举行听证。当事人作为弱势一方,有必要为其提供程序性权利,以监督行政主体采取最低限度的执法手段实现行政管理目标,同时也使行政主体再次认真对待披露手段的合理性,斟酌披露手段与执法效果之间的比例性,并确保所披露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减少不当考虑之误差。第三,对披露时间进行合理限制,这一要求主要针对向特定人群披露情形。为防止违法信息向更广泛的人群扩散,有必要在披露时间上给予限制,否则该特定人群之“特定”将会变成河汉空言。至于披露的具体时间可结合违法行为的性质、严重情况、公众知晓情况设定,尽量控制在一周左右,不宜过长。
(三)救济机制
虽然违法信息披露有覆水难收之效,但为减少当事人损失,必要的救济措施仍不可缺。第一,行政主体若发现披露的违法信息错误或超过了必要限度,必须通过新闻媒体或政府网站等可为公众知晓的途径对所公布信息进行及时撤销、更正,缩小不当信息的影响范围。此外,对作出不当披露的行政机关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应追责,可以由上级行政机关给予处分,也可根据严重程度采取罚款、拘留措施。第二,在行政主体与相对人关系面向,违法信息披露具有法律行为性质,因此允许当事人通过事后复议或诉讼途径救济。即使相对人损失难以通过事后救济弥补,但对纠正行政主体滥用违法信息披露手段有积极作用。第三,探索建立预防诉讼机制。分析外国行政诉讼立法,可以管窥出对当事人权利保护主要有三种类型:事后救济、预防救济、暂时救济(诉讼停止执行),这三种类型组成一个严密的权利保护体系,缺少其一均不利于实现“有效且无漏洞的权利保护”标准[19]。我国行政诉讼法只建立了事后救济,近年来在很多案件中该类救济的局限性逐渐暴露。在违法信息披露中,如果只规定事后诉讼,当事人的名誉、商誉及隐私必定被无情牺牲,换来的仅仅是经济赔偿,而这完全不是当事人期望的结果。为响应新行政诉讼法优先保护公民合法权益的理念,发挥司法能动性,我国应借鉴国际经验,弥补权利保护漏洞,不断摸索建立预防诉讼制度。最后,行政主体披露违法信息后,应当根据当事人履行义务的表现情况而允许其申请停止披露违法信息,是否停止披露由行政主体弹性决定。
六、结 语
作为一种全新的行政实效性确保手段,违法信息披露成为备受行政机关青睐的一种规制工具。但理论研究的浅显与不完善为实务层面的运用带来了诸多困扰,为破解这种脱节局势,本文从整体性视角对违法信息披露的关键性问题进行了详细剖析。
第一,理性看待违法信息披露的性质[20]。从内部结构看,违法信息披露的性质包含两个面向。在行政主体与社会公众层面,违法信息披露的主要功能是信息提供、风险警示,消除公众信息匮乏的局面,使公众自我防范危险,审慎作出选择,属于典型的事实行为;在行政主体与相对人关系层面,行政主体之所以将相对人的违法信息予以披露,就是想借助这种规制工具,对相关违法现象进行规制,通过影响相对方的公法行为,督促他回归适法状态,应归属法律行为范畴。在法律行为类型问题上,则可以创造性地结合实效性确保手段制度分情况而作出判断。
第二,全面认识违法信息披露的合法性与正当性。该规制手段之所以能有效的发挥其功效,不仅是因为传统规制手段的失灵为其提供契机,而且是因为其自身发挥作用的机理符合了文明社会中公众的社会意识感以及行政法基本理念。虽然违法信息披露在《信息公开条例》中找不到直接依据,但可通过规范性分析方法解读出来,也可在其他分散性规范性文件中寻得踪影。
第三,多策略探索违法信息披露的限制方法。违法信息披露能够弥补传统规制手段的不足,取得良好的执法效果与社会效益,创新之举值得肯定。但违法信息披露又是一把双刃剑,使用不当,杀伤力极大,因此有必要对其严格把关,从内容、程序、救济的多角度改变该手段的失范状态,使其确能发挥正面执法效力。
总之,违法信息披露手段的运用是执法与政策考量的结果,并非行政机关随心所欲获取部门利益的工具。期望在未来的执法实践中,行政主体能轻重缓急地审慎用好违法信息披露这把利器,真正地发挥好它的实效性。
[1]高峰.酒后驾车 科学家来管[EB/OL].(2015-01-14)[2016-06-06].http://xw.sinoins.com/2015-01/14/ content_141694.htm.
[2]东营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直属二大队.东营酒驾曝光台看看有你么[EB/OL].(2015-03-03)[2016-06-06].http://sd.sina.com.cn/dongying/new s/z/2015-03-03/0943-6219.htm l.
[3]张新宇.论行政信息披露的法律性质[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2):93-97.
[4]哈特穆特·毛雷尔.行政法学总论[M].高家伟,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393-397.
[5]金东熙.行政法I[M].赵峰,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6]章志远,鲍燕娇.公布违法事实的法律属性分析[J].山东警察学院学报,2011(6):47-54.
[7]莫于川.建设法治政府需要司法更给力[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23.
[8]翁岳生.行政法(下册)[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885.
[9]翁岳生.行政法(上册)[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796.
[10]余凌云.行政法讲义[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281-323.
[11]梁亮.行政机关公布违法事实行为的法律问题分析[J].河北法学,2013(4):170-175.
[12]鲍燕娇.公布行政违法事实的法律属性分析[D].苏州大学,2013.
[13]汪厚冬.论公布违法信息——以工商行政管理为例[J].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13(2):92-100.
[14]章志远.作为行政强制执行手段的违法事实公布[J].法学家,2012(1):52-62.
[15]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16]盐野宏.行政法总论[M].杨建顺,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17]黄全.论政府信息公开的原则体系[J].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79-85.
[18]刘泽刚.公共场所隐私权的悖论[J].现代法学,2008(3):168-174.
[19]黄雪娇.论我国预防性行政诉讼之确立[J].理论月刊,2015(4):96-101.
[20]李海良,刘文祥.论违法性认识之必要[J].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15(8):72-77.
责任编校:陈于后
Illegal Information Disclosure:A New Means of Ensuring Administrative Effectiveness
MA Youfang
(Administrative Law School,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Chongqing 401120,China)
The market economy itself is asymmetric information.Under the situation of market,how governmentmakes regulation becomes the focus of research.Traditional practice is to carry out economic regulation or social regulation to the behavior of disrupting the market economic order and undermining the security and environmental.Butwith the increasing complex of administrative practice lawlessness,the high cost shortcoming of traditional practices gradually is exposed.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nformation disclosure, as a new regulation means,illegal information disclosure gets its position and is widely used in the field of road transport,product quality,food safety,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The role of traditional regulatory instruments cannotmatch its advantages.But the understanding and application of themeans show a chaotic situation.In particular,as for the nature of illegal information disclosure,there are both factual action argumentand legalacts argumentof variety of different forms.These views do notaffirm from the viewpointof internal legal relations of the regulation means and thus lead to the unilateralness of cognition.The slapdashness,dot-type regulations and research way of illegal information disclosure may provide a new chance for right abuse of administrative body.To fully play the function of this regulation means,it is necessary to change the dispersed research into entire frame type research and grasp the issue from the viewpoint of nature,legality,validity,specific application and legal restrictions.In this way,it can find its proper position,better coordinate with other theories and systems under the administrative framework and really play its function for achieving administrative regulation.
illegal information disclosure;regulation means;factual action;legal acts;administrative enforcement;ensuringeffectiveness
DF312
A
1672-8580(2016)05-0018-12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5AFX009);西南政法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项目(XZYJS2015156)
马有芳(Email:1258687343@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