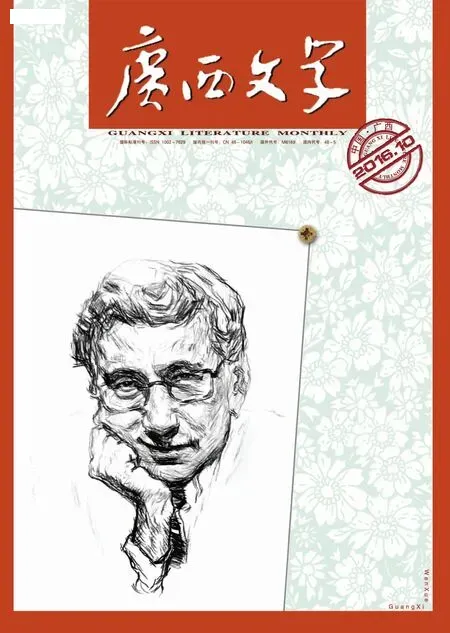龙建芬小小说二题
龙建芬/著
陈年老抽
恭诚在床上辗转,终于还是忍不住摇醒了他的妻子。
“告诉你,我就快要从乡镇调动上来跟你们团聚了。”恭诚伸手从背后揽住了妻子的肩膀。
“你在做梦吧?你都借调上来多少次了?行了,睡吧,别胡思乱想了!”妻子说着又发出了均匀的呼吸声。
“我说的是真的,我发誓这次一定正式调动上来,不是借调!”恭诚就差没伸出三个手指对天发誓了。
“行了,你知道外面人都叫你什么吗?‘陈年老抽’!你要是能调动上来,早就上来了,别再痴人说梦了,睡吧!”
第二天刚好是双休日,清晨,恭诚跟妻子刚好把瘫痪的母亲推出家门去晒晒太阳。这时,恭诚的手机响了。
“罗主任,您好,有什么指示吗?”恭诚尽量使电话里的声音能够听得出诚挚的恭敬和愉悦。
其实,老婆一听到电话那头是罗主任,她就早已知道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了,无非是要老公去打打麻将喝喝酒送送礼,再缴纳由“借调”去往“调动”的 “买路钱”之类!
前两个星期恭诚刚办好借调手续,踏进县委办,第二天罗主任就安排他和一个老行政股股长去送材料。仍旧是老套路,这个股长依旧像从前一样,以一种指点迷津的姿态,语重心长地跟恭诚聊着每位领导的喜好,譬如这个领导好一口烟,那个领导喜一口酒,另一位领导喜欢你陪他打打小牌……如此这般,这个股长其实就是一只“牧羊犬”的角色, 而恭诚则是他们要放牧的“绵羊”了。吃得香的“牧羊犬”无非就是善于帮那些中层领导将“绵羊”们供奉的“红利”撵进他们的腰包。
作为“陈年老抽”的恭诚,假如还对“雁过拔毛”和“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耿耿于怀,那就只能成为“古董级老抽”了。
恭城对于这些“游戏规则”早已了然于胸,他心里敞亮得像点着上千瓦的白炽灯一样。其实从前他也不是不懂这个道理,但那时候年轻气盛,心里撑着一口硬气,觉得自己可以凭能力吃饭,不必去走这些歪门邪道。因此他一般对这些“善意的点拨”都充耳不闻,假装是闲聊,过后并不在意,更不钻营,谁要邀他参与任何需要占有他合法收入的活动,企图“潜规则”他,他都置之不理。但是眼下他怎么能置之不理呢?他可以讲骨气,但一个家庭的担子都扔给孱弱的女人,他又于心何忍呢?想到这里,恭诚应了罗主任的邀请,买了两条蓝真龙香烟,两瓶天之蓝名酒,陪着罗主任打了大半夜的麻将,输了将近两个月的工资……
罗主任一高兴,当着其他还未开窍的借调人员说:“哎呀,小恭啊,记得你第一次到这里跟班学习已经是两三年前了吧?”恭诚娓娓道是,“你比从前进步了很多啊,无论是写材料还是工作的沟通上,那真是有了令人刮目相看的进步啊!难得啊难得!”
另外两名从其他乡镇借调上来的年轻人顿时面面相觑,带着羞赧的颜色低下头来。罗主任扔下一张牌,恭诚胡了,差点将牌推了下去,好在醒悟得快,收住了,吓得冒出一身冷汗。罗主任并没有注意到恭诚神情的波澜,边整理牌边接着说:“你们两个以后要向小恭好好学习学习,不是我说你们,你们在经验上面确实要继续加强……”
恭诚抛出一张牌,罗主任以上的话没说完,却打住了,他双手一推牌,马上笑逐颜开地轻喊一声:“哎呀,我又胡啦!”
“哎呀,愿赌服输,罗主任真是吉人天相,好手气,神仙都挡不住呀!”恭诚很违心地大肆赞美着罗主任,他对自己也会拍这种小清新的马屁感到惊讶。
一个借调的小年轻趁机看了一下手机,借口说太晚了,有点事要先回去,就离开了。恭诚却一直陪到罗主任在凳子上坐不下去为止,最后还恭恭敬敬地为罗主任点燃了一支烟,才一边点头哈腰,一边斜欠着身子倒退着离开了罗主任的家,那股殷勤简直点得燃烈火、浇得开枯木。
经过几次三番的应邀,恭诚总结出了规律,罗主任若是跟别人搓麻输了,或是烟抽得差不多了,或是一个月下来,开支大了,就会电话告知他三缺一,听到这个召唤,恭诚都会随叫随到。
两个月就要过去了,恭诚心里琢磨着三个月借调周期满之后的结果,同时走过一个服装店的橱窗。妻子经常在这个橱窗外对着一条粉色的长裙眼放异彩,是啊,已经很久没有给妻子购置新的衣物首饰了,恭诚的心似乎被撕咬了一下,生生地疼痛起来。想到下个星期就是妻子的生日,他折回头,走进了那家服装店。
“老板,帮我把这款裙子的M码装起来。”恭诚不假思索地说。老板十分利索地为他装好裙子,很干脆地说:“原价一千五,给你一千三吧,刷卡还是现金?”
说时迟那时快,恭诚的电话又响了,罗主任说让他到家里喝喝茶,他只得收起了为妻子买裙子的念头,因为手头上的钱只勉强够买到罗主任家喝茶的见面礼了。恭诚三番五次跟老板道歉,退了裙子,买了两条烟两瓶酒直奔罗主任的家。
恭诚发现,上次提前退场的借调人员此后很少再应罗主任的邀请参加活动了,很快,三个月过去,这个跟年轻时候的恭诚一样不开窍的借调人员卷包袱回了乡镇,而恭诚终于能够如愿留了下来。
不久,行政股长高升,恭诚取而代之。当有新的借调人员加入到这个队伍当中,恭诚每每看到跟他当初一样硬气的借调人员,就不免有些于心不忍,但他又能有什么办法呢?仅凭他一己之力不可能扭转乾坤,点拨一下那些年轻人,或许并不算得上是坏事,反而是为他们尽早实现抱负推波助澜。
办公室新来了一个年轻小伙子,恭诚看他材料写得很不错,不免有点恻隐之心,于是早早就找了个机会对他谆谆教导:“这一个喜欢抽抽烟,那一个喜欢喝喝酒,另一个人喜欢打打牌……”说完,恭诚吸了一口烟,再像叹息一般,将烟雾缓缓从口腔中释放出来……
上 任
闫正三的手机一直响着,可他却烂醉如泥地倒在沙发上不省人事。
“你起来,办公室打了你好几次电话,你说这几天值班,是不是假期有突发事件?”闫正三妻子摇了摇他的手臂,刚开始没反应,而后竟然一个翻身,手臂无意识地重重砸在妻子白皙的脸庞上,顿时一片红云浮了上来。这突如其来的一击,也将妻子手中要递给他的手机摔到了地板上,一声闷响 ,顿时摔出了电池板。沉闷的顿音点燃了妻子内心积蓄已久的幽怨。
“你个死货,昨天说去陪领导搓麻,润滑润滑关系,输了打算购置空调的钱;前天输掉了要偿还房贷的钱;今天又喝得像条死狗,说像你这种身份的人,不应酬没前途。你像条死狗一样被人抬回来,你的前途又在哪?我怎么就瞎了眼嫁给你个死赌烂喝的死货!”压抑了很久的妻子一巴掌打在闫正三喝成猪肝色又有些浮肿的脸上,过往的温柔都被这往复的折磨和煎熬浇铸成了委屈。
闫正三居然在这样的一记掌掴之下睡得更沉了,震撼的呼噜声在妻子的怒火之上撩拨,击碎了一串串滴落的眼泪。正在妻子伤心之时,闫正三更是一个沉重的翻身,将毫无戒备的她挤得一屁股跌坐到床下。这下妻子彻底恼了,盛一盆凉水全都浇到了闫正三身上,他居然还是打着响亮且节奏明快的鼾声。
“你这人模狗样的王八蛋,我看你还喝不喝还赌不赌!”妻子绝望地将盆子一起扔到了闫正三的身上,“砰”的一声,转身关掉房间的门 ,到书房睡觉去了。
闫正三妻子此时只有一个想法,那就是像他这种喝酒误事又嗜赌的角色,就算明天单位开除他,也不算冤枉,也难怪亲姐夫都不敢帮他。
跟闫正三一起值班的同事正提着手机直跺脚,他已经拨打闫正三的电话无数次了,忍不住心里直咒骂:“闫正三,你个狗日的,一到值班,手机就出故障,一定又是马尿喝多了,他妈的,老子真是倒了八辈子血霉了,总是跟你一起值班!”同事一肚子要掘闫正三祖宗坟的火气。
同事无奈之下只得拨打了镇长的电话:“韦镇长,刚刚有村民报在牛头岭有火灾,村里的经济林被点燃啦!今天的值班领导是闫正三,打了他几次电话,关机了。我调动不开灭火队,想请您指示,该怎么处置?”
“这个闫正三已经不是第一次给老子扣屎盆子了!”韦镇长把一副牙齿咬得咔咔作响,想把话活生生咽下去,最终还是没忍住,话如脱缰之马奔了出来。
韦镇长想起上次区检清洁卫生工作,因为这小子的玩忽职守,喝醉了,他挂的村卫生纹丝未动,恰巧又被检查组给逮住了,结果害得全镇乃至全县在全区被通报批评,坏了他马上就可以提拔任用的好事,韦镇长想起这件心头恨,耳际的两块咬肌就恨恨地凸显出咬牙切齿的僵硬线条。今夜,韦镇长再次为闫正三酗酒玩忽职守擦了一次屁股,心里的不痛快又增了一分。
这厢扑火如火如荼,那厢鼾声雷作。闫正三有今天,都是他的姐夫在组织部帮的忙。
那天,闫正三酒醒后知道自己误了大事,亲自跑到姐姐家,想寻求姐夫说情。哪知道,正三刚到门口,就听到姐姐跟姐夫的对话。
“老公呀,刚才来咱家送礼的小李提了乡镇的副职?”正三姐问。
“那你说呢?谁无事会登三宝殿?”正三姐夫反问一句,脸上带着一种男人在女人面前的尊严之色。
“你敢情就是个活雷锋,一个组织部长只帮外人,那咱弟正三的事呢?你有没有放心上?”
“我听说这小子挺浑的,经常出事!”姐夫说。
正三姐一听这话,心里不乐意,玉容一沉,用手挪开正三姐夫幽幽探上来的手, 娇嗔地说:“如果他争气,哪还需要动用你这个大组织部长!”
“好好好,夫人消消气,我明天就去过问过问这个事情,听说他们乡镇正准备增加一个副职,就在本地产生!” 他最害怕身上燃起三丈火又遇上夫人的一寸冰,赶紧巴巴地说道。
正三姐一听,喜上眉梢,转而换上了令人神魂颠倒的笑靥,娇俏的玉指轻轻从他的短发间梳理过去,正三姐夫一记轻轻的拥抱,正三姐就消融了进去。
正三听到姐姐与姐夫的对话,就像吃了定心丸,悄悄地离开了。
几天后,恰逢组织乡镇长赴他县调研,韦镇长瞅了个时机,凑上前去跟组织部长,也就是正三姐夫单独攀谈。正三姐夫脸上带着随和的笑意,他不敢忘记娇妻的要求,于是将目光调整得非常柔和,当他的视线与韦镇长相逢之时,他刻意没有马上挪开,而是多停留了几秒,韦镇长也就顺水推舟地跟着他行走,正三姐夫似乎是无意却认真地问了一句韦镇长:“闫正三工作如何?”
韦镇长怔了短短的几秒,那几秒,他跟从前对闫正三的判断和看法闪电般短兵相接,他的思绪在翻滚,却面无异色,丝毫没有蛛丝马迹让人可以追寻到他已如狂澜席卷般翻滚的内心,他很快调整了状态,即刻回答说:“安监办的主任,工作蛮积极的。”
“既然如此,你们不是缺一个副乡长人选吗,我看应该可以考虑。”正三姐夫说。
韦镇长立刻醍醐灌顶般,眼放微芒,心里正巴不得送给组织部长一个人情,于是说:“这个小伙子大家评价不错,工作积极肯干,有冲劲,肯负责,是我们乡镇的后备干部。”说时,用真诚的目光对视着正三姐夫,默默传递着情感,仿若热恋中的人,恨不得信誓旦旦地承诺:“部长,我办事,你放心。”韦镇长太需要这样一个有实力的同盟了,这个同盟的交换条件,正三姐夫满意地点了点头。
韦镇长踏着轻快的步伐,似乎捡到了意外的财富,心里却在暗暗思忖这个越来越难以捉摸的乡政府大门,最高境界是看得穿人心,这哪一层意思要是理解有了差池,都会是障碍,想到这些看似细微却不可小觑的细节,他的步伐更加小心翼翼了。
过了半个月,闫正三莫名其妙地在公推乡镇副职的会上当选为副镇长,连他自己都感到意外得摸不着头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