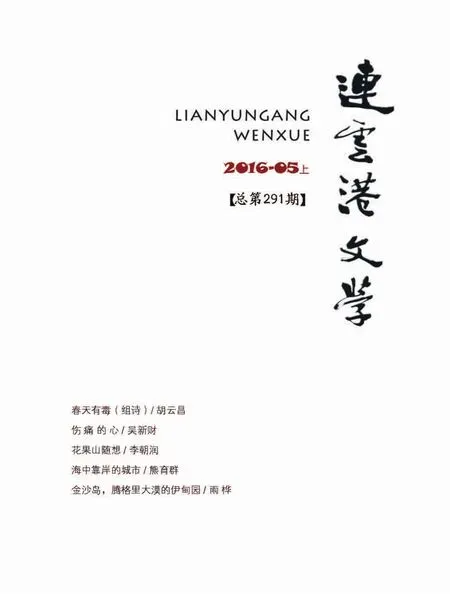蚁民三题
马浩/江苏
蚁民三题
马浩/江苏
闽
闽,人名。他原名不叫闽。叫什么呢?卖个关子。
有个同学叫广林,大约是他父亲想多养几个儿子吧,独木不成林嘛,不知结果怎样。不过,同学们由此为他衍生出了个有趣的绰号——麻子。这恐怕是他父亲始料未及的。我想闽或许受此启发而更名,亦未可知。
写此,关子似乎有些豁然了。闽,福建的简称。
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固然好,可通常会适得其反,就像修剪的树,剪去一枝,定会分出多头。就比如这省份的简称,本让人易记,可想把省份与其简称捻熟地对应统一起来,非要下点功夫不可。这让我莫名地想到孔乙己的卖弄:茴香豆的茴字有四种想法。我觉得有些知识就这么被泡沫化了。扯远了,回正题。
闽姓程,原名程福建。高中时,我们可以说是真正意义上的同窗。那时,我们共用的课桌就置在一扇窗下,他坐在靠窗的一边,常见他无端地对着窗外发呆,不知他脑袋里想些什么。
他学习很刻苦,三更灯火五更鸡的,效果似乎不佳,不像他吃饭长肉那般明显。从他体格上看,好像更宜练体育,不错,他喜欢运动,可在篮球场上,大虾似的,找不着北,他似乎不知道自己在干嘛,追着球,横冲直撞,常遭队友大声呵斥,他却一脸茫然,很无辜。看他打乒乓球很是一种享受,就像看“憨豆”先生的滑稽表演,他动作夸张,如跳大神,每接发球,嘴都会张成螃窟,也不怕飞虫误入,让人忍俊不禁。
课余,几人一起玩时,比腹肌、比胸肌、比腕力……他很热衷。一次,我撩起上衣,显示我的腹肌,他看着不过瘾,用手摸,果然一棱一棱的,他边摸边说,能让我打一拳吗?我不加思索地说,可以。说着,他就一拳打了过来,我能感觉到,他似乎连吃奶的劲都使出来了。就这一拳,让我的腹部难受了一个多星期。
三年的高中时光,一晃而过,大家各奔东西。不过,他为了爬过高考那堵围墙,依旧在学校里苦练本领。那年,也就是他参加第三次高考之后,暑期,他到家里找我,那晚,我们喝了很多酒,说了很多话,他的酒喝高了,在我家哭了大半夜,招来四邻的探视。
同年秋,我收到一封信,确切地说是一封挂号信,山东某中学程闽缄。程闽,何许人也?大脑快速检索,无所获,搞错了吧,想着撕开信的缄口,原来是程福建的信,他改名以示其志,类如削发明志,他要在山东参考,这是最后一搏,如愿则罢,不如意也就死心了。他的名字改得很巧妙,闽,也就是福建,轻装简从,与没改的一样,我很喜欢。
虽则轻装简从,那年,他还是没有跃过高考这道横杆。这是秋后我去看他,知道的。这次,不知是苦痛得麻木了呢,还是真的看透了什么。他的变化特大,我尽量不提及高考的事,他却能坦然面对,似乎把这档子事看得很平淡了,就像秋风之中飘浮的落叶,轻轻地触地,没有任何的反响。我很为他捏把汗,就他而言,不应如此反应的,那他该怎么反应呢?心存疑惑,说不出。他说他结识了一个女孩子,漂亮、温柔。这么多年,我第一次见他如此丰富的表情,原来,他也会眉飞色舞;原来,他的眼睛是这么的明亮;原来,他的嘴角也能弯出动人的微笑……他激动地跟我说,他第一次约会,就强行拥抱了她,亲吻了她,尽管她作了徒劳的挣扎,可她还是被他征服了。一脸的得意。一阵无忌的狂笑,我释然了。
我们坐在河边的柳荫下,毫无边际地闲扯着,特开心。他告诉我,他要子承父业,做一名乡村牙医——一名出色的牙医。我看着他平静地望着潺缓流淌的河水,莫名地感动,不知因何,我相信他一定能做名好牙医。不过,有一件事,我忘记了问,他改名可否受了广林,即麻子的启发而动的灵机呢?
这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我的一些想法,或者说疑问,一直没有机会得到证实。
小丁
小丁,我同窗,善金石,写手好字,人言其怪,我却没有看出来怪在何处,大约与他走得太近,近而不察,熟视无睹吧。
小丁而今不小了,已是不惑之年的人了,却不能称老丁,老丁这顶帽子还由其父带着,老丁为人师表一辈子,今赋闲在家,习字养生,大约是从小受老丁的影响(我总觉得另有原因),小丁亦酷爱书法。书法讲究气定神闲,可修身养性,小丁学生时代,却有“愣”名,与人打架,家常便饭,打起架来,动刀子的事也常有,因而,老丁的工作常调动,就这么,老丁带着小丁到了我们学校。
我认识小丁时,并没有江湖传闻的那样悍,白白净净,文文弱弱的样子,随意的如一片浮荡的白云,说话慢条斯理,声音不大,人一笑,眼睛也跟着笑。不知因何,我们很快就成了无话不谈的死党。
他会刻章,给我刻了不少印章,我那时正迷恋文学,喜欢给自己起笔名,好像没有笔名就不文学了,晓峰、疏雨、东篱……一连串,每起一个自以为意的笔名,就让他刻一枚印章,篆书、隶书、楷书皆有,大约是得来不用费功夫,不珍惜,而今一枚都寻不到了。有时,打趣他,他的金石有今天的成就,多亏了我。他总是报以不屑一笑。
就这个文质彬彬的人,还是让我见识了,他的狂野来。一日,校外几个小混混来学校滋事,围观者众,上前制止者少,他正给我刻章,听说后,拉我前去,他扒开人群,笑眯眯地拽过一大个,手中摆弄着那把刻章的小刀……也许他的名声在外吧,几个小混混竟然灰溜溜地走了。事后,他跟我讲,打群架的那些家伙,最是胆小鬼,择其一人,单挑,其他人立马就熊了。
这是很早以前的事了。要想让一个人平庸,就让他失去个性。漫长的学校生涯,不断打磨着他的个性,中学、大学、机关,继而结婚,一路走来,似乎风平浪静。人生于此,说不上什么好,也说不上什么不好。书法,还是他的最爱,练字还是他每日坚持的必修课。
那年,我去政府找他,听说他已离婚了,听说而已,进他的宿舍,方觉是事实。那时,他吃在公家食堂,住在单身宿舍,进门,一张床,一架书而外,就是屋中间的一张大案子,案上,习字的纸张,乱七八糟,相互枕压,零落一地,四壁,乃至门后,贴满了他的书法作品。据他说王羲之的《兰亭序》贴,让他临摹不知几千遍了。书法于我是外行,不过,感觉他的字,有韵味,有某种言不出的东西,字里行间感觉有他的影子晃动,印象最深的是贴在门后的那幅: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晚上,顶足而眠,闲扯,怎么竟走到离婚这步了呢?老婆是他同学,高中美术老师,幸福一对。他说一言难尽,婚姻就是双鞋子,这话真他妈的对,不合脚,无论多么华美的鞋子,都他奶奶的敝履,最不能与搞美术的女人结婚,他说前妻什么都不会,甚至生孩子,这也就罢了,家务一切全包,不能生孩子,将来可领养一个,可他嫌弃他不求上进,说到底,嫌他挣钱少,不能满足他的物质生活所求。他净身出户。
我不知说什么好,婚都离过了。找了没有?
自由一段时间再说吧。我说也好,至少,我们还能同榻而眠,扯淡。都笑。说话之间,十年了。那时,他三十多岁,时间如同床下那摞宣纸,随他挥写,前路如他笔下的字,留白,令人向往。其间,聚合离散,席前宴后,吹牛闲扯,当然,总忘不了关心一下他的个人问题。那事,别提。不提,怕你忘了,误了你儿子不说,别耽误丁老师的孙子。一笑而过。
他至今依旧孑然一身。今年见他时,他已调至治理河道办公室了,工作地点在大铁船上,如航母般的大船,抬眼碧波荡漾,风景宜人,他手下都是清一色的愣头青,河道治沙不力,河床坍塌严重,不知因何,领导点了他的将。我在船上闲逛时,他正点名,声音洪亮有力,然后,到他办公室领大锤,每人一把,他也亲自拎一把,执法去了。
这是昨夜与我谈论文字、书法的那个小丁吗?我突然想起,在学校,他与人动刀子的事来,在他的身上,有些东西没怎么变。我似乎明白了,他因何这么酷爱书法了,我想他意欲以书法的形式去改变些什么吧,看来是未能如愿,他的书法路,还很漫长。
阿丘
阿丘死了。
我以为听错了。怎么可能呢?不过,来者说得有鼻有眼的。阿丘从脚手架上,不小心摔了下来。他这一失足,便千古了。
没事爬什么脚手架呢?心生暗怨。这下可好,命休矣。
阿丘,我拜把子的兄弟,为人有豪气,尊为老大。前些年,他拉起一支建筑队伍,俗称包工头,这年头,包工头似乎不是什么好头衔,几乎是暴发户、骗子的代名词了。在县城,他带领着一帮手下,在那儿拔“城”助长。他是从拎灰桶起家的,深知建筑民工的艰辛,工钱从来分文不少,干活向来都是身先士卒。
阿丘什么都好,就是有一样不好:贪杯好客。不知是因为好客而染上酒瘾,还是因贪杯中之物而习成的好客?酒场上,义字当头,感情浅舔一舔,感情深一口闷。据说他上脚手架时,便带着满身的酒气。
如此,阿丘果真……简直不敢去想,前不久的那次相聚,似乎就在眼目之前。这话该怎么说呢?
我在外漂泊,一年也就是春节回家一次,因而,好友节后聚会,必不可少,几乎年年如此,几成定例。
民主路的拐角处,一家酒店,同学开的。在哪儿消费不花钱?同学的场,一定是要去捧的。在场的有:阿丘、小石、小邹、小丁、小沈、我还有小楠,小楠,难得一见。那晚的酒喝得真叫畅快淋漓,尽兴而开心。白酒开了多少瓶,记不清楚了;啤酒开了几箱,不知道,但可以肯定,没有一人钻到桌子底下,尽管站起来时,大家都东摇西摆,走起路来,踉踉跄跄,给人感觉头重脚轻,脚下无根似的。
席间,胡言乱语,陈芝麻、烂谷子的,都往外翻腾,都是些糗事,时过境迁,当年的短处,现在揭开来瞧,格外的有趣味。
阿丘暗恋班上某女生,让小丁传情,传来递去,结果该女生就成了小丁的现任老婆。我揭这事时,邻座的小石,不时用肘击我,用脚踹我,还给我递眼色,意思是嫌我哪壶不开提哪壶,可我在酒精的作用下,满嘴跑火车,刹不住。招来阿丘、小丁联合起来,用酒来讨伐我,弄得我只有招架之功,无还手之力。
从酒店出来,便一脚踏进了隔壁的歌厅。小楠为我点了一首陈星的歌《离家的孩子》,音乐声起,我刚开个头,便被阿丘大声喝断了,叫嚷着换歌,点的啥玩意歌,凄凄凉凉的,唱个豪放的,《好汉歌》,于是,歌厅里回荡着:“大河向东流啊,天上的星星参北斗……”不觉已是凌晨一点多了。酒劲散了不少,肚子也有点饿。
“去夜市。”阿丘说。
走出歌厅,冷冷的夜风一吹,不禁打个寒战,抬头见几粒寒星挂在夜空,眨着冷眼,此情此景,久违了。一行几人散行在空荡的马路上,有人歌兴未尽,还在哼唱着,偶有小车疾驶而过,出租车更是少得可怜,好不容易碰到一辆,招手停车,司机见是一群酒鬼,一踏油门,溜之大吉。急得我们顿足骂娘。没办法,只得麻烦自己开动11号了。
万兴市场东边的夜市。大排档。几人坐定。添酒回灯重开宴。一直闹腾到凌晨4点多方休。阿丘带着我们去找旅馆,不知砸了多少家旅馆的门,终于寻到歇脚之处,也算是苦心人天不负吧。
想此,不由心楚鼻酸。于是,摸出手机给小石打电话,问问阿丘的具体情况。
“没影子的事,要不就是那让人搞错了。不过,阿丘最近资金周转不灵,昨天,他在我这儿借了些钱,给工人发工资呢。”
挂了手机,一时无语,大脑一片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