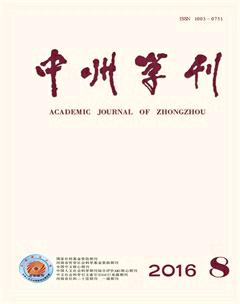李佩甫与中原文化的叙述方式
摘要:李佩甫是地地道道中原说书人的角色。他完全用中原人的思维方式和说话方式,讲述着中原地区的一草一木、一村一店、一人一事,呈现着中原人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原貌,以及中原文化的存在状态,从而形成了一种叙事学意义上的阐释,这也许就是李佩甫中原文化的叙述方式。简要言之,他的叙述脉络一般先从草的本性入手,继而叙讲人的故事,从人的故事中展现村庄的历史,进而再现多彩的中原民间风情,可谓环环相扣,步步深入。
关键词:李佩甫;中原文化;叙述方式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6)08-0154-05
李佩甫是地地道道中原说书人的角色。他完全用中原人的思维方式和说话方式,讲述着中原地区的一草一木、一村一店、一人一事,呈现着中原人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原貌以及中原文化的存在状态,从而形成了一种叙事学意义上的阐释。这也许就是李佩甫的中原文化叙述方式。
一、草的本性
“我是一粒种子。我把自己移栽进了城市。”(《生命册》)“桐花的气味一直索绕在童年的记忆里。”“桐花很淡的,淡出紫,那紫茵茵的,一水一水的往喇叭口上润,润些紫意来,而茎根处却白牙牙的,奶白,那一点点的甜意就在奶嫩处沁着。”(《城的灯》)李佩甫的叙事往往从野草植物开始,这与他观察社会和事物的视角有关。李佩甫的生活从来没有离开过河南,甚至没有离开过豫中平原的那方水土。他虽然生在小城市,但自幼在乡下姥姥家厮混,后来又作为知青下乡,当过农村大集体的生产队长。所以,他的生命、他的人生经历是与那片土地以及土地上的标记一草一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定程度上,他是农业文明的产物,他的生命底色是那片土地。土地是生命的原乡,无论是草木、牛羊猪马,还是昂首直立的人。实际上,在李佩甫的意识中,草木稼禾是真正的生命之源,因为土地孕育了草木稼禾,草木稼禾供养了生命,泥土并不能直接成为人和其他动物的食粮。
但是,草木从来没有享有过高贵,往往被人小觑、蔑视。草木稼禾特别是野草,是土地上随处生长的植物,而且一岁一枯荣,极其普通,人们从来不珍视,践踏随意。“在平原,有一种最为低贱的植物,那就是草了。”(《羊的门》)然而,草木虽然低贱,生命却十分顽强,无论人们如何践踏,无论土地怎样贫瘠,只要有一点水土,它都要生长,甚至人们把它踩在脚底,割了一茬又一茬,烧了一遍又一遍,仍然不放弃生的希望。正是这极普通的草本植物,滋养了无数有生命的动物,特别是人。在李佩甫这里,人是与植物直接关联的,或者说,人和植物是分不开的。“我说过,我是把人当作‘植物来写的。就此,《羊的门》《城的灯》和最新出版的《生命册》这三部长篇组成一个‘平原生态小说系列,或者叫做平原上的‘植物说。”①为什么把人作植物来写?是因为李佩甫从低贱的野草身上看到了生命的高贵,精神的高贵。在芸芸众生,在中原,人犹如普通的草木一样,平淡地生存着,或百年或数十年,有枯有荣。人并非天生之高贵,也不是以寿命长短论高贵,而是以生命历程中所体现的精神和价值判断是否高贵。在李佩甫的笔下,有树、庄稼,更多的是野草。《羊的门》的第一章,李佩甫不厌其烦地介绍了二十多种平原上的野草,而且入木三分地揭示了草的本性,“平原上的草是在‘败中求生,在‘小中求活的。”这二十多种甚至叫不出名字的草,其实就是平原上生活着的各色各样的人,很多人虽然卑微,甚至被人欺辱,但他们仍然昂首活着,并且用自己的生命样态和底气续写着历史,汇集成洋洋大观的中原文化。
进一步说,历史与人的关系犹如人与草的关系。中原地区是中华民族的核心地带,几千年的重要历史事件都曾经在这里发生,战争、灾祸,历史的车轮在这里反复碾压,人的生命有时就像野草一样遭到不断的践踏,一茬一茬刈戮,但生命的根系仍然顽强地存在,人们并没有舍弃历史,而是像低贱的野草那样无声而顺从地排列在历史的路途之上,支撑着历史的延续。一般意义上,人都是普通的,身份的高低贵贱并不能消除人的一般规定性,所以,毛泽东认为,人民是创造历史的动力。②历史并非仅是神仙皇帝的历史,同时也是普通人生活的历史。民族的文化、中原的文化就是这样的文化,它是几千年普通人生活方式、精神生态的凝聚,普通、俗成、平易、精炼、持久,持续生长、蔓延,它的高贵、深邃不在于其身份,而在于其坚韧和生生不息的品质。
二、人的故事
无论是植物说还是野草叙述,李佩甫的目的还是讲述人的故事。作者以草喻人,切入历史车轮之下的社会底层,讲述底层普通人的故事。
李佩甫的叙事都是通过讲述人的故事完成的。而讲故事,讲述身边人物的故事恰恰是李佩甫擅长的招数。自幼融入乡村生活,耳濡目染,农村的生活方式、生活状态、精神图式原版地刻印在他的心中,特别是那一个个形象丰满、性格鲜明、记忆深刻的人物,排列在他的脑海之中,总是跃跃欲试,呼之欲出。在李佩甫的作品中,几乎都是普通的小人物,这与作者的生活圈子密切相关。这些人物皆与中原这块土地纠缠不清。他们都是地地道道的中原人,或者是一辈子厮守着这片土地,或者是在这片土地上出落成人,总之,都是由这方水土养育,跟这方水土有斩不断的血脉关系,中原大地及其历史是他们共同的底色和背景。这些人物曾经是李佩甫的乡亲、邻居、亲戚,他们或生活在一个村庄,或者生活在固定的生活圈,朝夕相处,喜怒相知。他们在一起生产、生活、奋斗、创业,有庇护、扶助、合作,也有矛盾、冲突、仇恨,爱恨交织,构成了五味杂陈的厚重浓烈的生活。李佩甫目睹他们的衣食住行,洞悉他们的精神世界,了解他们的喜乐,也感同身受他们的痛苦,甚至熟知“乡土中国”的困惑和人际关系中矛盾纠葛的症结,因而设身处地地以“当事人”的身份,讲述他们感性、原汁原味、原生态的故事,呈现出一系列带有浓厚泥土味或显著中原印记的人物形象。“描写在某种文化土壤中人物的生长,一直是李佩甫创作的一个重要着力点。”③
《羊的门》中的呼天成,是李佩甫笔下有代表意义的乡土人物。这个受教育背景不详,一辈子没有离开过家乡土地的村支书,在作品中显然是有丰富故事的人。尽管作者在叙述这个人物时有所保留,或者说,作者故意采取一种欲言又止、欲说还藏的手法,神化玄化这个人物,但作品让我们深深地感受到了这个乡土人物的能量,看到了一个乡土世界的“巨人”。呼天成二十多岁就成了呼家堡的掌门人。几十年中,他以自己的胆量、执着、能力、智慧,把一个贫穷的乡村改变成富裕、小康的样板村,建立了自己的“乡村王国”,同时也建立了自己在呼家堡的绝对权威和不倒神话。他琢磨乡土,琢磨土地上的一草一木,琢磨他管辖的每一个人;他研究平原的沟坎和胸怀,甚至研究社会和政治,他从平原、乡土社会以及人情世故中学习和积累了经验与智慧,使他管理操纵起呼家堡来游刃有余。在呼家堡,他就是圆心,人人都要与他发生关联,他的行为影响着呼家堡,影响着每一个人。不仅如此,呼天成还是一个通天的人物。他不仅在呼家堡建立了自己牢固的关系网,在呼家堡之外也有一个巨大的人情圈。所以,他足不出户能够影响县里、市里的事情,当呼国庆职位岌岌可危,甚至身陷囹圄之时,他一句话或活动一下便转危为安。呼天成是中原乡土文化的产物,也有当代中国社会政治的鲜明印记。
钢弹(冯家昌)和丢(吴志鹏)是从平原土地中走出来的人物,但他们生于平原,在乡土的滋养和塑造中成人,因此,血液中混合着平原泥土的原汁。冯家昌的父亲是上门女婿,孤家小姓在村里没有地位。母亲早早去世,难以撑起门户的父亲把当家的重担交给了年幼的他。他别无选择,无论多么艰苦、困难,他都得面对。他从小没鞋穿,成了赤脚大仙,为了磨练出铁板一样的脚板,他把蒺藜蛋扎在脚底蹦跳。困苦生活,磨砺出他坚强、坚韧的性格和意志。他忍耐着,积蓄着,一种信念在心中成长。他要帮助父亲把四个弟弟带大,他要挣脱这苦难的土地,走向希望和向往的城市。他在困苦中养成的勤奋、忍耐、坚韧帮助他实现了愿望,在城里成家立业,并且把弟弟们也带进了城市。但当他们真正成为城里人后,那刻在骨髓里的乡土情结不由自主地浮上心头。吴志鹏是“嵌进城市里的一只柳木楔子”(《生命册》)。他是上了大学,读了研究生,具备了嵌入城市的条件之后落户到城市的。但吴志鹏成了城里人却改变不了乡土背景和血缘关系,还必须承载乡土文化赋予他的人情重负。所以,村里所有的人都是他的亲人,每一个人的电话都是承载着亲情的重托,他必须去办。然而,一粒乡村的种子撒在城市,并不意味着拥有城市,更不意味着有能力解决乡亲们所有的问题。于是,乡土文化成了他卸载不了的负担,他害怕电话,他像躲瘟疫一样躲避电话。无奈,他选择了逃离,逃离到更远的地方。
孙布袋、梁五方、虫嫂们是生于乡土,生活于乡土,堙没于乡土的底层人物,他们就像野草一样顽强地生活在平原的土地上,无论土地多么贫瘠,无论生活怎样挤压他们,他们贱微但不自暴自弃,仍然在平原上扎下根;他们有自己的生存手段,他们隐忍,他们打掉牙齿咽肚里,甚至屈辱地活着,延续着生命的故事和历程,展示着人的价值和平原文化的精神。刘汉香是巧珍式的女性,她美丽、善良、忠贞,但她又有自己的主见,自强不息。冯家昌的刻苦、自强、坚韧让她倾慕,她愿意为他牺牲、奉献,帮助他度过困难。当冯家昌在城市有了地位、有了新欢之后,她虽然内心保存着那份执着的爱,但毅然决定与他彻底割舍,坚决地回到生养自己的那片土地,“她要把这爱意播撒在这块土地上!”继承父亲的事业,担任了村长,把爱的故事转化为一个乡村神话。这是中原人的“故事新编”,是乡土文化的新的阐释。
三、村庄的历史
村庄是我国乡土社会的基本空间。李佩甫讲述的人的故事,皆纳入了村庄的单元,因此,他的乡土叙事就是村庄叙事。他为我们设置了大李庄、呼家堡、上梁村、无梁村等众多村庄,它们构成了中原地区的乡土社会。在农业社会,乡村与其生产方式密切联系,具有相对的稳定性。村庄既是农业社会人们安居的“村舍”,也是社会交往、流通的枢纽。在李佩甫的作品中,村庄既不是点,也不是一个平面,而是一个延伸的长廊。时间在长廊中流淌,生活在长廊中交替,人们在长廊中千转百回。可以说,村庄具有巨大的容量,村庄的生活也具有无限的丰富性,它涵盖了乡土社会的所有内容,从人的生老病死、生产生活、经济活动、文化活动、社会治理,甚至于民族、国家、政治等等,都成为村庄实体的重要构成。以“平原三部曲”为代表,李佩甫用了大量的篇幅,通过人物的成长、奋斗甚或挣扎、沧桑经历等展示若干村庄变迁、发展的历史,其历程可能是迟缓、滞后的,也可能是跌宕、剧烈的,让读者从中窥视乡土社会历史的浑浊与厚重,感受深植平原沃土的中原文化的丰富与多彩。
呼家堡是中州大地上的一个普通村庄,但同时它又是一个独特的村庄。它的特殊性不是因为它具有某些优越的区位,也不是因为它的构成具有某种独特性,完全是因为它出了一位独特的人物,一个人改变了一个村庄,一个人改写了村庄的历史。呼家堡曾经和其他平原的村庄一样,贫穷、饥饿、涣散,以至于几乎人人都去偷。这成为摆在年轻村支书呼天成面前回避不了的问题。于是,治村从治人开始,因为村庄是由人组成的,有什么品质的人就有什么品质的村庄。呼天成首先组织抓“贼”,让“贼”在大庭广众面前把“赃物”亮出来,刹住习以为常的顺手牵羊、小偷小摸的坏毛病。其次是让村民们集中揭查私心,公开亮丑,暴晒灵魂,清理思想上的污垢,剥离身上的不良行为。虽然在“斗私”活动中,“窄过道儿”于凤琴为此付出了生命,但却由此真正触及了人们的灵魂,达到了呼天成期望的效果。再就是树立典型,制订村规民约,倡导新风尚,培养新的村民精神。呼家堡在新村建设中设立展览台,把麦升和徐三妮断残的指头放进去展览,弘扬他们的牺牲精神,激励村民为新村建设奉献;为在纸厂生产中殒命的老曹设立“英雄榜”,举行追悼会,把老曹奉为“英雄”,尊为“烈士”,坚定人们对呼家堡事业的信念;呼天成驱神祛鬼,在众目睽睽之下破除“打捞灵魂”的迷信,果断将承载迷信陋俗的十亩水塘填平;他敢于忤逆母亲的宗教条规,坚决按照村里规矩安葬母亲;制定“呼家堡法则”,规定“村歌”“村操”“村规”“评议法”“干部法”“学习法”“奖惩法”等,使呼家堡完全按照自己的规则运行。正是在呼天成的主宰下,呼家堡由过去贫穷落后涣散的乡村,变成了一个靠集体经济发展、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新村庄。呼家堡的发展轨迹和历史变迁中,承载的是传统历史文化中均贫富的思想和新时代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精神,其中都蕴含着民族文化中绵延不断的内核。
无梁村和呼家堡相比,是中原大地更为普通的村庄。它的村情、民情、生产、生活、交往等等都与中原乡村保持着更广泛的一致性。吴志鹏是一个孤儿,但他的生命、生活却得到乡亲们热情的呵护和帮助。他是喝着全村女人的奶,吃着百家饭长大的。老姑父作为村支书就是他最大的家长,村民都是爱护他的家庭成员。这体现着民族文化中扶贫济困的传统美德,也反映着乡土生活中人与人的血脉关系。正是在乡亲们的呵护和帮助下,吴志鹏成了一个研究生和大学老师。但是,也正是因为他生命中的这种图景,无论是他走多远,他都与这里存在着一种扯不断的关系。这种关系既是现实结下的,也是历史结下的,是流在血管里的,是刻在心里深处的,是乡村人与人之间广泛存在的。所以,吴志鹏是他们的骄傲,他们也寄予吴志鹏更多的期望和重托。无论吴志鹏是否承载得起,那是一种绵延的文化,一种殷殷的亲情、乡情。吴志鹏的逃离,是因为他意识到了这种乡土关系和重托的问题,一种文化和乡情的严重超载。但吴志鹏并非乡土文化彻头彻尾的反叛者,事实上,他就是中原乡土文化的成果,他在精神上仍然与乡土保持着多重的藕连。当然,无梁是普通的,更多的无梁人顽强地生活着、拼搏着,生命也是普通的。老姑父是一位英雄的军人,为了喜欢的女人入赘无梁村,一边是为村里奉献,一边是在与妻子打打闹闹中消耗生命,结局却颇为凄凉。虫嫂无论生活多么无奈、艰难甚至屈辱,以一个女人的坚韧、忍耐、无畏地把几个孩子养大、出息起来,但孩子们对她并没有施与应有的回报,存在着与文化和道德的悖离。蔡苇香是新一代乡土女性,自幼反叛家庭。她要挣脱乡土,挣脱家庭。她要到城市淘金,出人头地。尽管她淘金的手段不是那么体面和光彩,但她那种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决绝精神,不能不说体现着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们的一种不懈追求。蔡苇香成了蔡总,她成功了,她改变了人们对她的认识,她也在按照自己的意志改变无梁。人物的变化对应着乡村的变迁,人物的发展史也是村庄的发展史。乡土生活常常是波澜不惊的,历史和文化就深深地潜藏于其后。无梁的平淡和深沉正是深沉厚重的中原文化的展现。
四、民间的风情
可以这样认为,李佩甫的作品主要是一种民间叙事。这不仅是因为作者叙事的切入点大多基于乡村和底层身份,譬如草的线索,第一人称(亲历者)的身份,其效果是民间观察家的故事记录或陈列。更重要的是,作者讲述和描写的是底层民间社会的生活、故事、人物、风情、世态、苦乐。底层社会生活一般都是平凡的生活,这是社会生活的主体。恰恰是这种平淡的生活犹如浩瀚的江海,具有无限的丰富性,也更能显露出生活的真谛。
中原地区是中华文化的发祥地,具有深厚的文化土壤。中原文化与中华民族文化的核心部分保持着极大的一致性。中原文化主要由上层主导的主流文化和底层大众生活方式为主体的民间文化构成。虽然中原地区相当历史时期都是封建帝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但由于中原腹地辽阔,人口众多,因此存在着广泛的民间社会,民间文化在中原文化中占据重要的分量。毫无疑问,描述民间生活,表达民间文化,就是表现和反映中原文化。
李佩甫最擅长的就是进入民间社会。这里的土地、人、风物他都十分熟悉和亲切,都与他保持着心理上的相通性。进入乡土民间,就进入了他纵横恣肆的叙事场域。他的灵感,创作的爆发点,鲜活的人物,精彩的故事,乡土风情,就会接踵而来。《羊的门》是从“土壤的气息”开始叙事,“踏上平原,你就会闻到一股干干腥腥的气息”,“生的气息和死的气息杂合在一起,糅勾成了令人昏昏欲睡的老酒气息”。“这就是平原的气息。”接着,陈述许国三千年颠簸流离的历史,“一页黄纸一页泪。连年的战乱,天灾又是那样的频繁,人是怎么活过来的呢?”“人活着,树也活着。三千年啊,漫长的三千年也仅仅传下来这么一句话,说这是一块‘绵羊地。”之后,似乎该说到人,讲故事了,但作者却耐心地、不厌其烦地介绍各种野草。这样的叙事安排,作者是有深意的,那就是彻底把读者带入乡土民间社会,让你完全进入民间感受这里的人、物、故事。因为这就是中原这一方水土,人为什么能够在几千年灾害和战乱中生存下来,就是学到了野草的生存精神,像草一样紧紧扎根土地,不离不弃,吸收这片水土的养分和气息,以延续生命,延续历史,延续文化。《城的灯》是从桐花的气息开始的。桐树是中原地区常见的一种树,桐花的“娘娘香”是一种美好的记忆。但这种美好中常夹杂着苦涩和无奈。父亲一早发现“会跑”的桐树后,见人就“这得说说”。他找村支书国豆和村干部“说说”,找老德“说说”,找穗儿奶奶“说说”,找全村人“说说”,可是谁也不跟他认真“说说”,谁也给他说不出一个所以然。人们似乎很冷漠,父亲很无奈、无助,作品一开始就透出几分凄凉。这就是乡土民间的现状,就是乡村人情、关系、地位、势力的真实写照,门头硬和门头弱带来的利益的不均衡。同时,乡村中好事跑前头,赖事躲千里,也是人们常有的心态,家长里短,邻里纠葛,谁都不愿意掺和惹一身骚。所以,没人给父亲主持公道。《生命册》中吴志鹏所拥有的血缘和人情关系图谱,也是乡土民间社会结构和人际关系的典型反映。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而乡土民间更是如此,费孝通先生认为乡土中国是一种“差序格局”构成。④在农村,人们世代居住在一个村庄,长期通婚和毗邻,人与人大多沾亲带故,人们都不见外,在家互助,出外互帮,几乎就是乡村人们的一种思维。所以,当吴志鹏走出无梁,在城市有了“地位”以后,理所当然地成为他们的代言人和依靠,所有的关系线条都连接到他的身上。
另一种文化也是中原乡土社会风情的重要展示。一是呼家堡的“十法则”,几乎是乡村生活无所不包的村规民约,是呼家堡及其掌舵人呼天成的创造。这种创造不是完全的创新,是一种实用主义的活学活用,也有几分庸俗社会学的成分。例如村歌分为晨曲和晚曲,晨曲《东方红》,晚曲《大海航行靠舵手》,这是政治世俗化的产物。“村规(一):钟声就是命令。注释:单声是上工,音为‘当、当、当……;双声是下工,音为‘当当、当当、当当……;三声是开会或紧急集合,音为‘当当当,当当当……。”“村规(二):安装在各家各户屋门上方的‘广播匣子不能关,更不能私自拆除。呼天成说,要注意听‘精神。”是大集体的操作方式,带有军事化的印记。评议法细则(三)脱裤子,“注释:‘脱裤子即为一种自我检查的方法。如果在当月评议中,分被降下来了,那就要当众‘脱裤子,面对众人深挖自己的思想根源。”这是一种乡土权力的蔓延,是一种乡土政治学。凡此种种,其中体现着民间智慧,也体现着农民的机智、狡猾、顽劣。二是冯家和的《上梁方言》及其注释。作者整理了乡土民间“上梁”近30个常用的字词,并做了民间意义上的解释。这些字词是一种地方语言,但在使用中所体现出的含义,又是一种丰富多样的乡土生活,更是一种原生态的中原乡土文化。《城的灯》之所以把它以上梁方言的形式集中展示出来,是因为在人物和故事叙述中有所不及。作者要把民间风情充分表现出来,并实现对乡土文化的坚守。冯家和的形象及其《上梁方言》作为一种符号,完成了这一文化使命。
注释:
①李佩甫:《我的“植物说”》,程光炜、吴圣刚主编:《中原作家群研究资料丛刊·李佩甫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5页。②毛泽东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1031页。③何弘:《坚韧的探索者和深刻的思想者》,程光炜、吴圣刚主编:《中原作家群研究资料丛刊·李佩甫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52页。④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出版社,2005年。
责任编辑:行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