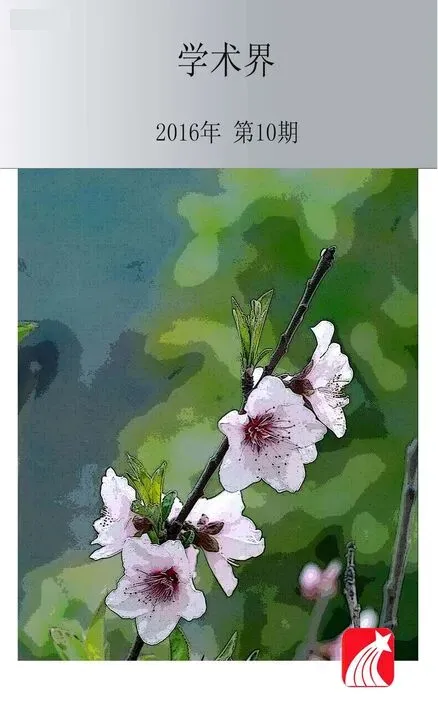政体、国体与国家类型学发轫
○张绍欣
(上海交通大学 凯原法学院, 上海 200240)
政体、国体与国家类型学发轫
○张绍欣
(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 上海200240)
政体和国体的分类及构造问题,是现代国家类型学的主要谱系。国体指的是国家的性质和统治的实质,政体指的是政府形式和统治的实现方式。西方政体学说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政体分类法开始,到20世纪的凯尔森的民主与独裁二分的理想型为止,经历了一系列损益变迁,却有着内在的谱系学逻辑。在现代主权理论和国家理论诞生之前,只有政体概念而没有国体概念。在现代主权理论和国家理论诞生之后,国体概念与政体概念发生了分离,并且国体问题相对于政体问题而具有更加关键、更为要害的地位。现代国体类型的谱系涉及到不同的分类标准,有主权结构的国体类型、历史哲学的国体类型、主权领导权威的国体类型等。卢梭的人民主权原理,精英统治论的“政治阶级原理”和“寡头统治铁律”,以及葛兰西在马基雅维利学说基础上发展出的“现代元首制”,构成统治原理型的国体理论。
政体;国体;国家类型;国家类型学
一、国家类型学语境中的政体与国体
“政治理论的中心问题是政府的分类。从法学角度来说,这是宪法的不同模式之间的差别。因而,这一问题也可以作为不同国家形式之间的差别提出来。”〔1〕国家类型学横跨宪法学和政治理论两个学科。国家类型学涉及到国家的分类、政府的分类和宪法的分类。虽然对凯尔森而言,国家的分类、政府的分类和宪法的分类发生重合而成为一回事,但我们却有必要来分别考察其谱系。本文作为国家类型学的刍论,限于讨论政体学说和基本的国体学说。
政体理论是一种以政府形式的分类为内容和功能的概念系统。政体问题的本质是政府形式如何分类,以及由相关分类所引发的政体的分类标准的问题。对政体的不同分类以及不同的分类所依据的不同标准的思考,形成了不同的政体学说。
当前语境下,国体通常指国家性质,也就是国家的阶级统治性质。作为政府形式的政体概念指的是统治的实现方式,而国体概念指的是统治的实质。西方古代政治只有政体问题而没有国体问题。在现代主权理论和国家理论诞生之前,只有政体概念而没有国体概念。在现代主权理论和国家理论诞生之后,国体概念与政体概念发生了分离,并且国体问题相对于政体问题处于更加关键、更为要害的地位。可以说,作为统治的实现方式的政体概念,属于一阶的统治范畴;而作为统治的抽象实质的国体概念,是对一阶政体概念进一步抽象化和理论化而得到的二阶的统治范畴。如果说政体概念在古希腊的出现是西方政治学说史在开端上的一次理论化突破的话,那么现代国家(state)概念、主权理论和国体理论的诞生,是西方政治学说史在现代语境中的又一次和进一步理论化跃升。
国家类型学本质上是一种谱系学的系统,其研究路径有三个:描述性路径,评价性路径和历史性路径。〔2〕描述性路径是一种类似生物学上的谱系分类系统的研究路径,而评价性路径是一种从伦理学视角对政体进行道德谱系学考察的研究路径,这两种路径构成了古往今来的国家类型学的最基本的方法论视域和方法论张力。如果说描述性路径是一种政治现象学的方法论的话,那么评价性路径就是一种价值规范主义的方法论。历史性路径不仅仅对国家类型进行分类和道德评价,还要描述国家类型从一种形态向另一种形态演化的历史谱系过程。虽然西方古典时代已经有各种政体间的演变和循环理论,但历史性路径真正发扬光大而成为一种有关政体的历史谱系学,还是自意大利哲学家维柯创立作为“新科学”的历史哲学以后。在中国语境中,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耳熟能详的有关国家类型的历史谱系。总之,生物谱系学、道德谱系学和历史谱系学,构成了国家类型学的方法论的三种理想型主干。下面就综合三种谱系学方法,对西方政体学说和国体学说分别进行考察。
二、西方政体学说的演变
(一)古典政体分类法
对古往今来的不同的政体学说的科学考察,形成了谱系学意义上的政体学说史。传统政体分类学说的鼻祖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的政治哲学存在盛年期到晚年的变化,其晚年著作趋向于实践审慎和务实。我们追寻柏拉图在政治哲学上的定论,应该更加着重于其晚年思想。柏拉图的晚期著作《政治家篇》区分了一人统治、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统治。这一基于统治者个数所做的政体分类法,构成了古往今来所有政体理论的思维原点。柏拉图的另一部晚期著作《法篇》谈到,君主制(monarchy)和民主制(democracy)是两种最基本的政体,其他所有政体都是这两种政体不同程度进行结合的产物。〔3〕后来马基雅维利的元首制和共和制的国家类型二分法,和凯尔森的民主与独裁的国家类型二分法,都可以在柏拉图这里找到端倪。
柏拉图之后,亚里士多德提出了最为经典的古典政体理论。我们都熟悉亚里士多德对城邦政体的六分法:君主制、贵族制、城邦制、僭主制、寡头制、民主制。在这个六分法中,亚里士多德同时使用了两种分类标准:一是统治者个数,二是好坏政体的区别——统治者个数是一个对事实的描述问题,而好坏的区别是一个价值评价。〔4〕政体好坏的标准是,每种政体的目的因是追求整个城邦的利益,还是追求统治者的私人利益。亚里士多德首先按照统治者个数,城邦政体区分为一人统治(autocracy或作monocracy)、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统治。进而,这三种统治方式都有好坏两种区分,这样就产生了六种政体:好形式的一人统治为君主制(monarchy),坏形式的一人统治为僭主制(tyranny);好形式的少数人统治为贵族制(aristocracy),坏形式的少数人统治为寡头制(oligarchy);好形式的多数人统治为城邦制(polity,现在通常翻译为共和制republic),〔5〕坏形式的多数人统治为民主制(democracy)。亚里士多德用于指称好形式的多数人统治的术语与“政体”是同一个词汇politeia。考虑到亚里士多德的美德伦理学和古典政治学对“善好”(good)事物的追求,这说明在他的实践思维中,最好的城邦政体就是好形式的多数人统治,即多数人统治并且追求城邦的整体利益的政体——城邦制。亚里士多德把城邦制描述为贵族制与民主制相混合而形成的以中庸为原则的政体,也就是用好形式的少数人统治来调和坏形式的多数人统治。〔6〕亚里士多德的这一政体分类系统,与古希腊城邦世界的任何具体城邦都没有直接关系,它并不是在经验主义层面上对已知城邦进行的分类,而是一种理想型的逻辑系统,六种类型中没有任何一种能在任何地方找到一模一样的。〔7〕我们要确知这一点,是因为现代政体学说的鼻祖马基雅维利正是以相反的思维提出自己的政体分类法——根据现实世界中的权力现象进行分类而不是采用逻辑上的理想型。
表一古典政体分类法对比

出身于希腊世界的罗马史家波利比乌仍然坚持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对统治者个数的描述和好坏评价,但他把好坏评价的标准,从亚里士多德的城邦目的因——追求何种利益,改换为统治者的正当性基础。城邦统治者的正当性基础有两种,依据血缘世袭,还是获得被统治者的同意——获得被统治者的同意的是好政体,仅仅依据世袭的是坏政体。〔8〕除此之外,波利比乌还改动了两处政体名称的用法。他将君主制(monarchy)几乎等同于僭主制(tyranny),而用王制(basileia, kingship)来指代好形式的一人统治。亚里士多德的君主制与僭主制之间的好坏对应,在波利比乌那里变成了王制(basileia, kingship)与僭主制(tyranny)之间的好坏对应。波利比乌还将民主制的败坏形式——也就是亚里士多德政体分类中的坏形式的多数人统治——称为暴民制(mobocracy或ochlocracy)。这样,波利比乌就为民主一词做了翻案,民主制成为一个中性且兼有褒义的术语。这样,亚里士多德的城邦制(polity)与民主制(democracy)的好坏区别,就转变成了民主制(democracy)与暴民制(mobocracy或ochlocracy)的好坏区别。〔9〕
(二)现代政体分类法
当今常见的君主制与共和制二分法,最早来自马基雅维利的元首制与共和制二分法。马基雅维利的政体分类法,见其《君主论》的第一章。严格说来,《君主论》论的并不是“君主”(monarch),而是“元首”(prince, principatus, principato),其古代渊源是古罗马的屋大维所建立的以“第一公民”(princeps)和“首席元老”(princeps senatus)为标志的奥古斯都元首制(principality)。在这里,传统君主制仅仅是马基雅维利所说的元首制政体中的一类现象。我们应该充分意识到马基雅维利的“元首” (prince, principate)概念和“元首制”(principality)概念的创新性。“元首制”作为一种政体理论的提出,固然有其罗马公法的渊源,但更多的,还是与马基雅维利创新性的“国家”(stato, state)概念关联在一起。“国家”理论的出现颠覆了传统的城邦概念和城邦思想,而“元首制”政体学说颠覆了古典的城邦政体的认知路径和君主制(monarchy)范畴——“元首制”概念超越了古代的“君主制”概念。认识到这一点之后,我们可以把《君主论》第一章的那短短一段话概括为下表:〔10〕
表二马基雅维利的政体分类

从古今断裂的思维来看,马基雅维利的政体学说是一种颠覆和创新。马基雅维利政体分类法的出发点是,考察实际政治现象中的差别而非用理念来指导分类,这是在方法论和思维上颠倒了古典的政体分类法路径。我们今天进行历史谱系学的回溯,会发现不单“元首制”概念是一种超越和创新,“共和制”概念也是一种超越和创新——马基雅维利决定性地塑造了现代人的“共和制”观念。但从古今延续的思维来看,自马基雅维利以来的现代政体分类法,始终是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波利比乌的古典政体分类法的思维中进行合并和整合。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以统治者个数为分类标准的视角来看,马基雅维利的元首制(principality)与共和制(republic)的二分法,实质是一人统治(autocracy或作monocracy)与复数人统治(polyarchy或作polycracy)的二分。
马基雅维利的国家类型学与古典政体学说的区别,造成了元首制与君主制之间的张力和共和制与民主制之间的张力。在国家类型谱系学上,解决了共和制与民主制之间张力的,是卢梭的人民主权理论。卢梭人民主权理论的核心,是其《社会契约论》中的连比例公式:主权者/政府=政府/臣民。卢梭的这一连比例模型的奇异之处在于,它能够实现一人统治(autocracy或作monocracy)与全部人统治的同一,其做法是让主权者=臣民=人民。卢梭的人民主权原理,饱含着他自己的直接民主观和共和理想,这样,他就取消了共和(republic)与民主(democracy)的区别,取消了马基雅维利学说中的张力。〔11〕
继马基雅维利之后对现代的政体分类法做出重要贡献的,是孟德斯鸠。孟德斯鸠的政体学说见于其《论法的精神》的第一卷,其政体分类法是在波利比乌分类法和马基雅维利分类法的基础上做了部分改进。初看起来,孟德斯鸠的政体分类原则同时使用了统治者个数和好坏评价两个标准,但是两个标准的使用都不彻底。按照统治者个数,孟德斯鸠首先区分了一人统治和复数人统治,并且把复数人统治称为“共和制”,而且没有在“共和制”内部区分好坏形式——到此为止的处理方法是马基雅维利式的。但是,接下来孟德斯鸠说共和制包括贵族制和民主制两种子形式,这就又回到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波利比乌分类法的思路,而没有采取马基雅维利所赋予“共和制”概念的创新性。奇怪的是,孟德斯鸠在复数人统治内部不强调好坏区分,而在一人统治方面特别强调好坏形式的区分——好形式是(立宪)君主制,坏形式是(君主)专制。孟德斯鸠的政体分类法纳入了古希腊政治思想所不列入文明形式的政体——东方的君主专制(despotism)。——不过在罗马宪制演变过程中,在戴克里先皇帝之后,罗马政体最终走向了君主专制。因而,孟德斯鸠的“(君主)专制”概念,实际上既包括古典政体理论的文明外形式——东方的君主专制,又包括古典政体理论中的僭主制。
表三古今政体分类法对比

孟德斯鸠的上述分类法十分混杂,为了清晰起见,他在统治者个数和好坏评价两个标准之外,又加入了分类的第三个标准——政体所应该有的动力原则。孟德斯鸠所说的政体的原则,是“使政体运动的人类的感情”。〔12〕共和制的原则是美德(品德),而且民主制需要总括的美德,贵族制需要美德中的节制;(立宪)君主制的原则是荣誉;(君主)专制的原则是恐怖。〔13〕到了动力原则这个分类标准这里,孟德斯鸠的政体分类法总算比较清晰一些了。孟德斯鸠政体分类法要获得完全清晰的理解,还是要放在历史谱系学语境中。孟德斯鸠的基本看法跟马基雅维利相同,就是认为共和制适合于古代的城邦世界,而君主制(或元首制)适合于现代世界。孟德斯鸠进而认为,立宪君主制适合于现代欧洲的大型领土国家,而君主专制适合于古往今来的东方种族。〔14〕
当今习以为常的君主制与共和制二分法,虽然已经不能反映当今的国家类型的实质,也还值得一提。德国公法学家耶利内克对君主制和共和制有很详细的进一步划分,他根据君主是否受到限制和受何种限制而将君主制分为无限制君主国、等族君主国和立宪君主国;他根据权力支配的主体而将共和制区分为社团共和国、寡头共和国、民主共和国和阶级共和国。〔15〕
我们所要考察的最后一种政体分类法,也是20世纪影响很大的一种政体分类法,是奥地利公法学家、法哲学家凯尔森的民主与独裁(autocracy)的二分法。凯尔森明确说民主与独裁的二分法是为了取代古典政体理论的三分法和马基雅维利的二分法,但他也同时指明民主与独裁是韦伯意义上的理想型,而不是政治现实中的特定政体。凯尔森的政体分类标准是政治自由和宪法创造法律秩序的方式。〔16〕民主与独裁的对立性区隔,实质是积极自治(服从自我的立法)和消极被治(服从他人的立法)这样两种宪法创造法律秩序的方式的区别。民主模型指立法者和法的实施对象为同一群人的情况,独裁模型指立法者与法的实施对象完全不同的情况。〔17〕凯尔森将政治自由定义为卢梭意义上的积极自由——自决(self-determination)和自我立法(autonomy)。〔18〕当立法者和法的实施对象为同一群人的时候,人的自我立法得到了完全的实现,所以凯尔森的民主模型是完全政治自由的模型;当立法者与法的实施对象是完全不同的两群人的时候,人的自我立法的程度打了各种程度的折扣,所以凯尔森的独裁模型是政治自由受到完全压抑的模型。在将民主与政治自由相等同这一点上,凯尔森与卢梭是完全一致的。民主与独裁的区别,我们按照亚里士多德的理解方式,就是全体统治(人民主权)与少数人统治(包括了一人统治)的区别。上文提到,柏拉图晚期著作《法篇》说君主制和民主制是构成其他所有政体的两种基本政体,如果我们从君主制中抽象出独裁要素的话,那就有了民主与独裁的二分。西方政体学说的发展,从柏拉图到凯尔森,又回到了原点。
民主与独裁的二分法,在大众传播领域常常被宣传成民主与专制(despotism)的二分。实际上,民主与专制的二分是一种不科学的宣传,在理论上这一二分法并不成立,因为民主制的坏形式——暴民制——在托克维尔的政治理论中也是一种专制。科学的分类,在法理上要回归凯尔森的民主与独裁(autocracy)的二分法,或者回归意大利政治哲学家、法哲学家诺伯特·博比奥的民主与专政(dictatorship)的二分法。〔19〕博比奥正是在凯尔森二分法的基础上,演绎出了民主与专政的二分法,这一演绎是为了描述20世纪的现实政体分类——作为意大利人,博比奥继承了马基雅维利的国家类型学的现实主义出发点。这里要指出一点,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与人民民主专政之间的区别是国体问题,而民主与专政之间的区分是政体问题。
三、从政体到国体
现代主权(sovereignty)学说和现代国家(state)学说构成了国体概念的理论基础和理论背景。意大利政治理论家马基雅维利创立了stato(state)意义上的现代国家概念,法国公法学家博丹创立了现代主权(sovereignty)概念并在法理上区分了立法权与执行权;而主权概念与国家概念一起构成成熟的现代国家学说——契约论国家学说,是在英国政治哲学家和法哲学家霍布斯的“利维坦国家”那里;主权概念、契约论与民主概念相结合,发展出成熟的现代人民主权学说,是在法国政治哲学家卢梭那里。在现代主权理论和国家理论诞生之后,国体概念与政体概念发生了分离,并且国体问题相对于政体问题处于更加关键、更为要害的地位。
现代主权理论首先是在其内部进行权力的分类和区分——立法权与执行权相区分,这一区分意味着,立法权指称主权的归属,而执行权指称主权的使用和运作。现代主权理论的诞生,在公法学上意味着立法权概念与执行权概念的分离,在国家类型学上意味着国体概念与政体概念的分离,在政治意识中意味着国家与政府的分离,在政治学上意味着国家理论与政府理论的分离。只是在立法权概念与执行权概念、政体概念与国体概念发生分离之后,国家理论与政府理论才发生了分离。立法权概念与执行权概念的分离,在国家理论中进一步意味着基础规范(国家理由)之预设与合法性(国家规范体系)之演绎的分离。立法权概念与执行权概念的分离,意味着同意(consent)构成立法权的一般原则,而独裁构成执行权的一般原则。在民主制情况下,人民主权构成了同意原则的最广泛形式。
表四国体概念诞生的理论背景

在国家类型学说史上,博丹以来的政治哲学家和法哲学家致力于区分统治的实质和实现统治的方式,区分主权的运作与主权的归属。虽然博丹的国家、政府和主权等概念还有逻辑含混的地方,〔20〕但还是有对统治的实质和实现统治的方式的初步区分。他的《国家六书》(Six Livres de la République)用于指称现代“国家”的法律术语是la république,进而谈到“国家诸形式”(formes de la république)包括君主制、贵族制、民主制。表面看来,这与他推崇君主制的主张有冲突,实际不然,博丹认为“国家”(république)的本质标志是法律上的统一元首——主权者,不同的“国家形式”仅仅是主权的归属不同,但主权的运作是相同的。〔21〕所以,主权—共和的有效运作构成了博丹思想中的国家本质和统治的实质,而具体的君主制、贵族制、民主制只是实现统治的方式。霍布斯区分了利维坦作为“契约论国家”的代表—授权—位格之三相构造和具体的君主制、贵族制、民主制政府形式。〔22〕卢梭区分了人民主权的法理构造和具体的君主制、贵族制、民主制政府形式。康德区分了共和(republic)和具体的君主制政府形式,因而他的共和概念能够跟君主制相兼容〔23〕。——我们今天说英国的立宪君主制也符合共和范畴,正是在康德的意义上说的。康德的republic并非孟德斯鸠的共和政体,而是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的三权分立之法理逻辑——真正的三权分立的法理逻辑缔造者是康德,而非孟德斯鸠。康德的三权分立逻辑在根本上奠基于博丹所确立的主权—共和的运作结构,只不过康德在主权归属方面接受了卢梭的人民主权——但不接受卢梭用来表示主权运作原理的连比例公式。
19世纪下半叶以来,两种新的政治思想颠覆了近代国家理论中的同意型法理和人民主权范式,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专政学说,和以意大利学者莫斯卡、帕累托和米歇尔斯为代表的精英统治(meritocracy)理论。阶级专政学说否定了契约论思想的根本原则——同意原则,而认为所有统治的实质都是不曾也不必征得被统治者同意的专政(dictatorship),因而现代统治的实质不是资产阶级专政就是无产阶级专政。这样,马克思列宁主义就区分了政权的阶级专政本质和具体的元首制、共和制、苏维埃制等形式。
精英统治理论则以马基雅维利式的直面现实世界的态度,取消了卢梭的“人民主权”之政治神话。精英统治理论认为,古往今来的所有人类集团都是少数政治精英统治绝大多数群众,无论何时何地,统治的原理都是少数人统治、多数人被统治——意大利宪法学家、政治学家莫斯卡所发现的这样一条基本政治原理就叫做“政治阶级原理”(统治阶级原理)。政治权力从来就集中于一小撮统治精英之手,具体的政权采用君主制、贵族制、民主制等政体形式,都不能撼动少数人统治的实质。这意味着,以往按照统治者人数区分出的君主制、贵族制、民主制等政体形式,还有贵族制与寡头制之间的好坏区别,在考察政治现象时并不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米歇尔斯进而将莫斯卡的“政治阶级原理”应用于政党社会学而得出“寡头统治铁律”:在现代民主社会中,代议制下当选的执政者对选民、被委托者对委托者、代表对被代表者,获得了统治地位。代议制和政党现象意味着,民主社会中的组织因素和自由社会中的组织化,导致任何政治组织都在不同程度上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寡头化倾向,即政治组织最终由一个有限且相对封闭的少数派集团所控制。〔24〕“政治阶级原理”和“寡头统治铁律”意味着,民主只是个神话,卢梭的人民主权原理只是一种超出现实世界的政治神学构想,而非政治科学原理。莫斯卡等精英统治论者,虽然揭露了人民主权的宏大叙事的神话性和空虚性,但绝不反对现代社会中的各种民主制度的实践和发展。
博丹将所有的现代政体,都归结为主权—共和构造;霍布斯将所有的现代政体,都归结为利维坦国家的代表—授权—位格之三相构造;〔25〕卢梭将所有的现代政体,都归结为人民主权原理和连比例公式之模型;康德将所有具有正当性的现代政体,都归结为三权分立逻辑意义上的共和实质。马克思和恩格斯将所有的现代政体,归结为阶级专政;精英统治理论则将所有的现代政体,归结为“政治阶级原理”和“寡头统治铁律”。在这里,无论是博丹的主权—共和构造,还是利维坦国家的代表—权威—位格构造,无论是卢梭的人民主权的法理,还是康德的三权分立的共和法理,无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阶级专政,还是精英统治理论中的“寡头统治铁律”,都是主权理论和国家理论意义上的国体问题。而具体的君主制、贵族制、民主制政府形式,是现代的政体问题。
在上文的政体分类法对比表中,马基雅维利和凯尔森的政体分类法都不仅超出古典的政体分类法,而且超出了孟德斯鸠的政体分类法。这是因为马基雅维利和凯尔森的政体分类法都有达到国体学说的理论空间。凯尔森的民主与独裁两种理想型所组成的二分法,既是一种政体学说,又是一种符号学意义上的国体学说——因为凯尔森的“国家与法秩序自同说”把国家等同于一个从宪法之基础规范演绎出的规范体系之秩序,把主权—制宪权概念弱化和虚化为“基础规范”这样一个预设性符号,所以这样的国体学说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国体学说,而是符号学的国体学说。主权—制宪权是国家概念和国体学说的根本,只要凯尔森尚且没有主张国家的彻底消亡,他就终究要有一个从制宪权概念虚化而来的“基础规范”符号。凯尔森的规范科学的国家符号学终究不能摆脱主权现象,民主与独裁模型之两端,都与主权概念脱不开干系——民主是一种来自人民主权的个体化映射的自决模型,而独裁原本就是主权的现象学要素。所以,凯尔森的国家类型学,作为一种符号学意义上的国体学说,也无法摆脱主权—制宪权学说的梦魇——只有国家(state)现象的消亡,才能实现主权—制宪权概念的消亡。
表五主要思想家的国体问题焦点

马基雅维利所处的时代没有主权概念,因而他并没有直接提出作为国家本质或者国家性质的国体问题。但是马基雅维利的元首制概念有导向国体理论的可能性,这个可能性是在20世纪的意大利政治哲学家葛兰西那里得以实现的。葛兰西用天主教政治神学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来重新解读马基雅维利,将马基雅维利的“新元首”形象凸显为作为现代一般国体的“现代元首制”问题。葛兰西的创新之处,是将马基雅维利国家类型学中的元首制,与大公教会的一元化精神领导秩序和马列主义的专政概念结合,发展出作为国体的“现代元首制”。葛兰西将所有的现代政体——无论是资产阶级共和国还是无产阶级共和国——全部归结为现代元首制,现代元首制的核心是以精神领导统合了国家统治和经济支配的霸权(hegemony)性支配,是具备独裁要素的一元化领导权。在霸权范畴中,葛兰西尤为强调精神权力(领导要素,即市民社会的意识形态权力)、政治权力(统治要素,即国家)、经济权力(经济基础)三元结构中的精神权力(领导要素)的绝对支配力。葛兰西对意识形态和精神权力的着迷,缘起于对大公教会精神领导秩序的政治神学考察,因为他的现实意识出发点跟马基雅维利是同感的——古老而又垂死的意大利因为受到大公教会精神权力的宰制而不能形成成熟的现代国家(state)。霸权概念意义上的一元化领导权,乃是“统治的统治”,是“国体的国体”,葛兰西称之为“现代元首制”。
四、诸种国体分类法
(一)统治原理型的国体分类法——直接民主制、精英统治与现代元首制
葛兰西通过解读马基雅维利而得出的以一元化领导权为本质特征的现代元首制,是葛兰西视野内所有现代政体背后的国体,是各种专政国体类型背后的“国体的国体”,在其自身层面上只有一种类型,本身不涉及分类。卢梭的人民主权模型的统治原理,只有一种类型——直接民主制,本身不涉及国体分类法。莫斯卡的“政治阶级原理”和米歇尔斯的“寡头统治铁律”意义上的国体,也只有一种类型——寡头制(精英统治),本身也不涉及国体分类法。但是现代元首制、直接民主的人民主权模型、寡头制精英统治这三种统治原理却构成一组对照,可以合组为一种国体分类法。
(二)主权结构意义上的国体类型〔26〕
1.单一制与联邦制、邦联制
单一制为一元化主权,联邦制为二元复合主权——联邦和组成邦分割主权。邦联制实际是法人地位平等的主权国家间根据条约而承担的国际性义务。邦联可以是国际公法的权利主体,拥有公法权力,却不具有公法上的法人资格。〔27〕在历史上,邦联一般被视为一种过渡性国体现象,最终或者走向联邦制国体,或者分解为各自彻底独立的主权国家。
2.宗主国与附庸国(附属国)
这是20世纪去殖民化浪潮之前常见的国体现象,反映的是弱国依附于强国或新生民族国家在传统多种族国家卵翼下逐渐成长的法律关系。附庸国丧失一部分主权或名义主权,而在法律上依附于受让这些主权或名义主权的宗主国。
(三)历史哲学的国体类型
历史哲学的国体类型学说以国家体制的历史演化类型为分类标准。常见的国家类型的历史演化标准有两个:一是政治社会学所关注的国家(state)扩张到社会(society)的历史进程,二是马克思主义所关注的经济生产方式的进步所导致的国家演化进程。
根据国家(state)扩张到社会(society)的历史进程,西方制度史学界最广为接受的国体演化过程是:封建国家→阶层国家(社团国家)→绝对国家→代议制国家→政党国家(党国)。〔28〕
马克思根据历史唯物主义意义上的经济生产方式的进步,从政治经济学和历史社会学角度关注了以下的国体演化进程:封建国家(地产制国家)→资产阶级国家→无产阶级国家→国家消亡。资产阶级国家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无产阶级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过渡型国家,这样,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国体演化类型,就与下面的主权领导权威的国体类型对应了起来。
(四)主权领导权威的国体类型
此处的“领导”指的是葛兰西意义上的以精神权力为主导的总括性支配,它通过主权的排他性的神圣权威而表现出来,因而主权领导意义上的国体类型特别注重意识形态(苏俄的阶级专政)和政治神学(日本明治宪法下的天皇制国体)。
马列主义的阶级专政类型区分的是何种阶级专政,是资产阶级专政还是无产阶级专政,是资产阶级国家还是无产阶级国家;至于西方学界所做的专政与民主之间的对比,则是一个政体问题。阶级专政意义上的国体,按照毛泽东的定义,就是“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29〕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体类型,是毛泽东折中“资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而提出的“第三种形式的共和国”,〔30〕是在专政国体中融入民主政体因素而得出的“人民民主专政”。
二战前日本的“天皇国体论”,来自日本国家法学的开创者、神权学派宪法学家穗积八束(1860-1912)的国体宪法学说。穗积八束的国体宪法学认为,明治日本的国体是天皇制,而政体是立宪制,所以明治宪法下的日本是立宪君主制。穗积八束的国体理论澄清了孟德斯鸠政体理论的含混之处:国体类型用于区分“国家之基轴”、主权之所在——是天皇主权还是人民主权,而政体用于区分统治权行使之形式,即政体类型沿用孟德斯鸠对专制与立宪的区分。〔31〕不过穗积八束的国体理论也有表述不确的地方,他所说的用国体来区分的“主权”之所在,实际是葛兰西所指的政治神学意义上的精神领导权之所在——是天皇制的神圣权威还是人民的神圣权威(人民主权)。天皇制国体的神圣权威来自二战前日本的国家神学——神道教政治神学中的“祭政一体论”和“神国思想、皇国史观”,将天皇视为“现人神”“皇国神”。
神的权威与人民的权威,在本质上都是政治神学意义上的对精神权力的排他性领导与支配。罗马公法上有谚语“人民的声音就是神的声音”,这句谚语可以看作是现代国体学说之人民主权原理的政治神学公式。英国社会学家斯宾塞曾说,君权神授论是前现代的政治迷信,而民选集团的权力神圣则是现代的政治迷信。〔32〕莫斯卡等人的精英统治论,正好揭示出人民主权原理的神圣权威跟传统的神权论一样,只是个政治神话。
注释:
〔1〕〔16〕〔18〕〔奥地利〕凯尔森:《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沈宗灵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第314、314-315、316-318页。
〔2〕〔9〕〔14〕〔17〕〔23〕〔28〕〔意〕诺伯特·博比奥:《民主与独裁——国家权力的性质和限度》,梁晓君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16-127、118、126、119、94、98-99页。
〔3〕〔32〕〔意〕加埃塔诺·莫斯卡:《政治科学要义》,任军锋、宋国友、包军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416、138页。
〔4〕〔意〕诺伯特·博比奥:《民主与独裁》,梁晓君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92、116-118页。〔英〕迈克尔·奥克肖特:《政治思想史》,秦传安译,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69-70页。
〔5〕亚里士多德赋予好形式的多数人统治的术语,希腊文为politeia,字面意思就是政体,拉丁文直接对应词是civitas,英文的直接对应词是polity。英文通常转译为republic而不是直译为polity,所以中文通常的翻译是共和制。但按照严格的对应关系,亚里士多德的好形式的多数人统治还是应该称为“城邦制”。
〔6〕〔7〕〔英〕迈克尔·奥克肖特:《政治思想史》,秦传安译,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84-85、70-71页。
〔8〕萧高彦:《西方共和主义思想史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75-76页。
〔10〕〔意〕马基雅维利:《君主论》,潘汉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3页。
〔11〕因为卢梭的人民主权理论实际构成了国家类型谱系学上的一种国体理论,此处不再赘言。至于卢梭人民主权模型的详情,尤其是连比例公式的意义,可以参见陈端洪:《人民主权的观念结构——重读卢梭〈社会契约论〉》,载《中外法学》2007年第3期,第280-296页;《政治法的平衡结构——卢梭〈社会契约论〉中人民主权的建构原理》,《政法论坛》2006年第5期,第145-164页。
〔12〕〔13〕〔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19、19-27页。
〔15〕〔31〕林来梵:《宪法学讲义》(第二版),北京:法律出版社,2015年,第205-206、191-193页。
〔19〕〔意〕诺伯特·博比奥:《民主与独裁》,梁晓君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四章“民主与专政”。
〔20〕对博丹的主权理论的基本阐述,见陈端洪:《博丹的立法主权理论》,载陈端洪:《宪治与主权》,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年。
〔21〕〔美〕乔治·萨拜因:《政治学说史》(第四版),托马斯·索尔森修订,邓正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下卷,第81-83页。
〔22〕〔25〕张绍欣:《霍布斯政治哲学中的代表概念》,载《思想与社会》丛刊第九辑《奥古斯丁的新世界》,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6年,第163-216、163-216页。
〔24〕〔意〕莫里斯·费诺切罗:《莫斯卡的政治科学:民主精英主义与平衡的多元主义》,载〔意〕加埃塔诺·莫斯卡:《政治科学要义》,任军锋、宋国友、包军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6-7页。
〔26〕〔27〕本部分曾参照〔俄〕M.H.马尔琴科:《国家与法的理论》(经修改和增补后的第二版),徐晓晴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23-224、229-231,229页。
〔29〕〔30〕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载《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62-711、662-711页。
〔责任编辑:马立钊〕
张绍欣,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博士后研究人员。
——《君主论》献词隐义的分析
- 学术界的其它文章
- 制度多样性的政治经济学〔*〕——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的制度理论研究
- A Corpus-based Study of Discusive Strategies inChinese Housing News Texts〔*〕
- An Analysis of Li’s Prose The Great Goal with Gee’s “the Seven Building Tasks”〔*〕
- 以“克己”代“敬”〔*〕——钱穆论朱子晚年工夫转向
- Mediational Effect of Multimodal PPT Presentation on Students’ Learning Achievements〔*〕
- 幸福社区理论、测量与实践探索〔*〕——基于两个中产社区的实证调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