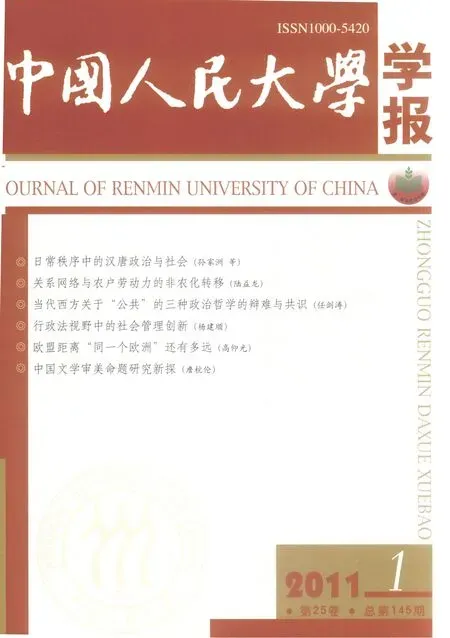对马基雅维利的重释:基于《曼陀罗》的文本分析
陈华文
对马基雅维利的重释:基于《曼陀罗》的文本分析
陈华文
马基雅维利形象在无数学者的诠释下颇为分裂对立,而致力于做出统一解释的努力总显得理据不足。这都与解释者局限于马氏的政治著作文本有关。《曼陀罗》作为一个形式上直接处理现实生活的戏剧文本,倾向于表达普遍性的问题,这就提供了一个避开文本分歧的可能性。借助于戏剧行动,马基雅维利充分阐发了一个人应该如何审慎行事的见解。在政治与戏剧这种并行结构中,人们会发现马基雅维利学说的核心并不是共和主义,也不是爱国主义,而是关于一个人应该如何生活的普遍性教诲。他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与古代伦理和现代道德的进路都有所不同。我们需要从这里出发,重新理解马基雅维利的思想及其与现代政治、现代伦理的关系。
马基雅维利;《曼陀罗》;审慎;现代政治
一、马基雅维利的问题
马基雅维利不仅在历史上备受訾议,而且近些年来在无数学者的诠释下,其形象更具分裂性。这可以从一篇对1969年以来西方学界对马基雅维利的研究综述中略窥一斑:“对于近期的研究而言,马基雅维利是现代政治科学、形而上政治学与国家理性之父……他是共和自由的爱国者导师,同样也是专制君主制、恐怖主义以及绝对主义的导师……”[1]。导致马基雅维利形象出现分裂的部分原因与其作品在对于邪恶毫不讳言的同时也提出了一些略显崇高的政治价值 (例如国家统一与公共福祉等)有关。马基雅维利在其政治著述,尤其是《君主论》中,直截了当地提出了一些“邪恶”主张:君主必须懂得如何善用野兽之道,当遵守信义反而对自己不利的时候,英明的统治者绝不能够、也不应遵守信义;施恩应细水长流,而伤害则应干脆利落……对于这些在他之前的古典思想家假他人之口隐秘表达的信条,马基雅维利不仅以自己的名义公开宣示,甚至欣然自得。①施特劳斯指出,马基雅维利并不是第一个表达类似观点的人,这种观点由来已久。柏拉图也曾借用其笔下人物卡里克勒斯和特拉西马库斯,阐发这些邪恶的政治信条;修昔底德则是借古代雅典的战争使节来宣扬同样的主张。施特劳斯特别指出,只有马基雅维利敢于在他名下无所忌惮地阐发这种信条。见Strauss.Thoughts on Machiavelli.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69,p.10。哪怕是在今天,马基雅维利的这些说辞,还会使得读者震惊。
对于马基雅维利的研究者来说,如果不打算仅仅停留在道德高度一味盲目责骂的话,那么就必须认真面对马基雅维利的“邪恶”学说,直接深入其最令人震惊的地方,如此方能做出切中肯綮的解读。对此,人们需要知晓关于马基雅维利的突兀评价。一方面,有研究者为其“邪恶”学说予以辩护。《君主论》最后一章,以及贯穿《李维史论》始终的、对于意大利统一的激情呼告,使得一些辩护者以为找到了马基雅维利作为一名抱有共和理想的爱国者形象。黑格尔指出:“一个人在读《君主论》的时候,必须既要考虑马基雅维利以前的若干世纪的历史,也要考虑他所处时代的意大利历史。”[2](P151-152)循此脉络,《李维史论》后来才成为剑桥学派探寻共和主义德性概念与自由概念的思想源泉。而另一些辩护者在其政治著述里找到了作为一名保持价值中立的政治科学家形象。尽管马基雅维利本人没有使用过“政治科学”这样的词汇,但由于他似乎强调审慎 (prudence)与技艺 (art)在夺取政治权力或者治理国家 (无论是君主国,还是共和国)时的重要性,因此被辩护者们视为政治科学之父。总的说来,辩护者或力图揭示出一个为国家统一或共和福祉而冷峻思考的马基雅维利,或将他塑造成在不同价值间保持中立的形象。另一方面,有论者仍然坚持抨击马基雅维利的立场。施特劳斯就重申马基雅维利作为邪恶导师的说法,认为不管是将马基雅维利视为爱国者抑或政治科学家,都是一种混淆视听的误解。[3](P10-11、80)
可见,马基雅维利形象在学者们的诠释下愈加分裂对立,但也有不少研究者致力于给出一个统一的马基雅维利形象。例如斯金纳认为《君主论》与《李维史论》的政治教训如出一辙,两书可统一为马基雅维利的一个基本论点:“任何人‘无论采取何种异乎寻常的行动,只要对于组成一个王国或缔造一个共和国有帮助’,都不能加以谴责,否则就是不近情理。”①斯金纳:《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上卷,284-28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斯金纳在《李维史论》最后一卷结尾处发现了马基雅维利将国家的生存与自由置于首位,而一切其他的考虑则应束之高阁。具体论述详见斯金纳:《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上卷,第六章。另外,曼斯菲尔德认为:“较之《君主论》给人的第一印象,以及在那些认为两书相互对立的普通看法下它所享有名声而言,它有着更多的共和主义因素;同样,与《李维史论》给人的第一印象及其据此所得的名声相比,它也有着更多的君主制甚或专制政体的因素。”[4](Pxxii)然而,斯金纳和曼斯菲尔德的两种解释并不足以提供一个完整的马基雅维利形象。前者仍然是以爱国主义为圭臬,并力图将马基雅维利的德性 (virtù)诠释成共和德性,从而建立起一个正大光明的马基雅维利形象。剑桥学派的这种做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马基雅维利的邪恶主张给人带来的道德张力,但实际上有论者认为这是对马基雅维利的误读,因为马基雅维利从来就没有提过什么共和德性。②曼斯菲尔德对共和主义的解读进路予以了强烈的反对,他认为马基雅维利并非如常人所言是共和德性的信徒,哪怕他的确认为共和国要优于君主国。见Harvey C.Mansfield.Machiavelli's Virtue.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6,p.23.不过,至于曼斯菲尔德的“其A中有B,B中有A”的解释进路,有可能忽视了A和B所共有的东西。实际上,为什么会有分裂的马基雅维利形象?斯金纳或曼斯菲尔德为统一的马基雅维利形象所作的解释为何不够?这两个问题都与文本选择仅局限于政治著作有关。目前关于马基雅维利思想的研究过多集中在其政治著述当中,尤其是《君主论》与《李维史论》的关系当中。实际上,马基雅维利除了在思想史上留下厚重的政治著述,还创作和翻译了几部充满嬉笑怒骂的诙谐戏剧,《曼陀罗》是其中最具原创性的一部。
那么,这些戏剧能否为我们提供理解马基雅维利政治思想的新资源?我们注意到,马基雅维利在给圭恰迪尼的一封信里,署名为“马基雅维利,历史学家,喜剧家与悲剧家”[5](P371)。戏剧和历史是马基雅维利表达的两个主要方式。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论述,较之历史,戏剧所表达的内涵更具有普遍性——“诗是一种比历史更富哲学性、更严肃的艺术,因为诗倾向于表现带普遍性的事,而历史却倾向于记载具体事件。”[6](P81)从这个意义上看,马基雅维利在戏剧里所表达的意涵较之其历史作品和政治著述 (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理解成由古代典范及其所处时代佛罗伦萨的事例构成)更具有普遍性。因此,施特劳斯强调马基雅维利学说的普遍适用性的解释方向[7]有其合理性,辩护者的说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舒缓其学说给人们带来的紧张,但它们毕竟没有直接面对马基雅维利对于邪恶的处理,因此反而有可能丢失其学说中真正重要的东西。相反,马基雅维利的戏剧《曼陀罗》作为反映现实生活的文本,其对普遍问题的揭露,有可能向我们展示出一个完整的马基雅维利形象,从而为我们提供重释其“邪恶”学说的新视角。
二、戏剧与政治:马基雅维利的两个舞台
从戏剧作品出发,理解马基雅维利的政治思想,首先会遇到这样的质疑:马基雅维利的政治思想在其政治著述里已得到完全的展现,并不需要诉诸其他作品,尤其是文学作品。《蠢驴》和《曼陀罗》“这两部作品对于理解马基雅维利的思想并没有提供什么新的东西。它们不过是通过诗歌和戏剧技巧,对那些在其政治著述中已得到完好发展的理念予以强调”[8](P6)。这类意见认为马基雅维利的所有思想都可以在其两部政治著述当中找到。
但这种诠释进路因没能注意到马基雅维利的世界的双重性,而把握不到马基雅维利学说的核心。马基雅维利在给维托里的一封信里写道:“不管是谁,看到我们的信,那些相对体面的,还有其他的,可能都会感到惊讶,因为我们乍一看都像是那么正经的人,讨论重大事件,那些不够正直和崇高的想法从来都不会在我们的头脑里出现。但几页过后,他们马上会发现,我们,同样的一个我们,竟是如此卑劣、薄情、放荡,总是如此不带遮拦地谈论荒诞不经之事。”[9](P312)而马基雅维利认为,他和维托里不应该因此遭受谴责,反而应该受到赞扬,因为他们如实地模仿了本性 (nature)本身的方方面面。马基雅维利文学作品及通信集里所显现出的轻与重,乃是对本性的模仿。[10](Px-xi)若仅仅阅读其政治著述,只能看到马基雅维利世界的一部分。
马基雅维利投入文学创作与他在政治生活中的跌宕经历密切相关。关于马基雅维利具体什么时候开始写作 (包括其政治著述和文学作品),研究者们并没有取得一致的看法。他们也很少怀疑,如果马基雅维利仍维持着他以前的那份工作,他就不可能创作影响如此深远的文学作品。[11](P135)美第奇家族复辟后,曾作为佛罗伦萨共和国外交秘书的马基雅维利遭受放逐。他向维托里描述了自己在这些日子里是如何生活的。他不仅谈到夜里与古代政治家纵横捭阖,还提到早晨有爱情诗歌相伴。[12](P262)事实上,马基雅维利献书洛伦佐以求重返政治舞台的希望落空后,他日益将自己视为一名文人。[13](P98-99)1517年他在给朋友的一封信里,表达了对于同时代著名诗人阿里奥斯托 (Ariosto)在其作品《愤怒的奥兰多》(Orlando Furioso)中没有将自己归为诗人行列的耿耿于怀。“我最近读了阿里奥斯托的《愤怒的奥兰多》,这部诗歌总体可谓精美,不少段落奇妙无比引人入胜。如果他和你在一起,那么代我问候并转告他,我唯一的抱怨是他提到了如此之多的诗人,却单独撇下了我。不过,在我的《蠢驴》中,我是不会落下他的。”[14](P318)在这段尖酸刻薄的评论里,马基雅维利将自己当做一名诗人予以自嘲,同时也暗讽阿里奥斯托像驴子一样愚笨。这充分表明马基雅维利有能力且迫不及待地想加入文学的圈子当中。
戏剧对于马基雅维利来说,是他离开政治舞台后唯一的出路,在这里他能扛住命运,使得他惨淡的生活稍有乐趣。[15](P10)但是,马基雅维利创作文学作品并不只是为了消遣时日或满足时下堕落的品味,而是需要通过抒情诗、叙事文与戏剧来体现理解现实生活的不同表达方式。关于喜剧与现实生活的关系,有两种主要的观点:一种是古典的,认为喜剧是现实的模仿,是自然、习俗和家庭私人生活 (domestic affairs)的一面镜子①代表人物莫过于亚里士多德,他指出喜剧和悲剧都是对生活的模仿,“二者 (指索福克勒斯与阿里斯多芬)都模仿行动中的和正在做着某件事情的人们”。见亚里士多德:《诗学》,4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这也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喜剧学家所支持的观点;另外一种则出自当代喜剧理论家,他们认为古典喜剧源自狂欢节,舞台上的这一天所呈现的是对现实的颠覆。②Marvin Herrick.Comic Theory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Urbana: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64;同样参见Douglas Radcliff-Umastead.The Birth of Modern Comedy in Renaissance Italy.Chicago&London: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9,introduction.马基雅维利并没有将喜剧视为现实生活的反面,而是私人生活的一面镜子。尽管喜剧兼具文雅与逗人发笑的语词,但是那些带着享乐的迫切心情来欣赏喜剧的人们只有
在回到私人生活之后、在当下现实之中才能慢慢咀嚼出当中的有用鉴戒。[16](P188)戏剧是对现实生活的模仿,行动作为戏剧的主要对象,是对人性以及人的思想、人的目的最清晰、最有表现力的揭露。黑格尔认为戏剧的创作主体首先要彻底洞察到人的目的、斗争及其终局是以内在普遍的力量为根据的。推动人动作的情欲和个性,在诗人那里应是了然于胸的。普通眼光所视为黑暗、偶然和混乱统治着的东西对于诗人却显示着绝对理性在实在界的自我实现。[17](P247-248)因而,唯有借助其戏剧里所描述的世界,我们才能懂得马基雅维利的学说是关于人类普遍事务的,而不是局限于某个时代某个国度甚或某个群体。尽管戏剧并不是一个强大的庇护所,但可以给他机会表达自己的想法。[18](P173)诉诸戏剧舞台,马基雅维利表达了自己对于那些影响人类行动的情感与野心的关注。因此,我们完全可以接受这样一个观点:“对话体给予柏拉图的机会,犹如戏剧之于马基雅维利。”[19](P338)
三、《曼陀罗》的隐喻式解读及其批评
《曼陀罗》是马基雅维利最具原创性的一部戏剧。与《君主论》和《李维史论》比较而言,这部戏剧在马基雅维利还活着的时候就为他赢得了名声。根据乔万尼 (Giovanni Manetti)1526年初写给马基雅维利的一封信,《曼陀罗》与普劳图斯的《孪生兄弟》同一个晚上在威尼斯上演,罗马喜剧虽然得到优美的吟诵,但与《曼陀罗》相比,却仍然被认为“毫无生机”[20](P379)。马基雅维利本人在与圭恰迪尼的通信里,也多次提起这部戏剧,并为好友能从中得到愉悦而甚觉快乐。[21](P164)可见,《曼陀罗》不仅获得别人的赞誉,马基雅维利本人对《曼陀罗》也甚为满意。
不少评论家给予《曼陀罗》一种重要的地位,认为它与马基雅维利的思想尤其是政治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从而对之进行直接的政治解读。解读的方式基本上是将戏剧情节与政治进行隐喻式的对照与比附,主要有以下两种具体进路:
第一,现实政治的隐喻:阴谋政治。这种思路强调从戏剧的形式出发来进行理解,认为戏剧是欢迎解释的,因而致力于探幽索隐、力图发现潜藏在文学作品当中的隐喻,并且相信马基雅维利对于文学作品里的隐喻传统是非常熟悉的。“马基雅维利肯定认为他的观众或多或少熟悉中世纪的隐喻写作传统,以及诸如但丁和薄伽丘等人在文学写作中使用隐喻所表达的主张。马基雅维利本人就写过《蠢驴》这样一首隐喻味道非常浓烈的诗歌。”[22](P807)持有这种解释进路的学者如阿兰桑多·巴隆基 (Alessandro Parronchi)、桑伯格 (Sumberg)和卡勒斯 ·罗德 (Carnes Lord)。他们受到马基雅维利是一名政治家的身份影响,利用剧本人物关系与历史背景的分析,认为《曼陀罗》里存在着关于现实政治的隐喻。巴隆基把《曼陀罗》看做美第奇家族回归的寓言。①Alessandro Parronchi.“La prima rappresentazione della‘Mandragola’”.L a Bibliof ilia.64(1962),37-86。原文“allegoria del ritorno dei Medici in Firenze”,也即“关于佛罗伦萨美第奇家族回归的寓言”。桑伯格认为这部戏剧表面上的缺陷以及庸俗景象下的隐性情节 (hidden plot)隐藏着一些马基雅维利政治教诲的危险因素。他指出,马基雅维利演绎了密谋推翻腐化国家的新科学,并预示着一场针对腐化的佛罗伦萨的阴谋。[23](P320-340)卡勒斯同样认为,《曼陀罗》当中包含着精心编制的隐喻,这种隐喻为马基雅维利在佛罗伦萨参与的政治活动,他在文章里详尽细腻地分析了剧中人物与1504年左右佛罗伦萨政治人物的对应关系。[24]强调《曼陀罗》是阴谋政治的隐喻,这种思路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到马基雅维利政治著述当中对阴谋的精心讨论的影响。马基雅维利在《李维史论》篇幅最长的一章里详细讨论了阴谋[25](P218-235),包括阴谋的重要性、君主防范阴谋的举措以及参与阴谋的私人公民应如何行动,等等,而这些近似于《曼陀罗》中的过程。这些认为剧中隐喻着阴谋政治的解读钩沉索隐,想象力丰富且极富创造性,但是除了挖掘出马基雅维利在写作上所展现出的审慎技艺外,它们对于理解马基雅维利的思想并没有实质性的意义。
第二,政治理念的比附:新君主典范与马基雅维利式人物的寻找。在这种进路中,阐释者将《曼陀罗》剧中人物与马基雅维利政治理念世界当中的新君主典范进行关联分析。另外,这种进路往往也会寻找剧中的马基雅维利。这类文献比较丰富。总体而言,研究者普遍认为,李古僚像是马基雅维利,而卡利马科则是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所设想的领导者。[26](P272)不过,也有文章认为,恰好就是看起来很愚蠢的尼恰,充分展现了马基雅维利作为一名愚人大师的德性。[27](P99-115)也有评论家指出,剧中的每个男性角色都被理解成为马基雅维利本人的自我表现。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合理的,因为我们对人物的刻画本身就蕴含着自我表露的因素。在一个对自我做出最有效介绍才有利于获得成功的社会里,这种可能性就更有依据。对于马基雅维利来说,在离开政治舞台的那些年月里,一直带有重返政治舞台的想法,那么,追求刻画一个全新的自己就显得理所当然。不管是就政治和外交方面进行著书立言,还是对自己所可能的样子予以戏剧或诗歌形式的嘲讽,这些都有可能为他回归政治舞台或者重建人脉提供帮助。[28](P153)借助于剧本里的人物角色与政治著述中的历史典范的比附,可以在马基雅维利的戏剧作品与政治著述之间建立起更为紧密的关系,但这样的结果是导致其戏剧作品淹没在政治著述业已构建起的理论框架当中,而看不到戏剧形式本身对于马基雅维利思想的重要性。
总而言之,把《曼陀罗》与政治直接联系起来,这种解读进路有其合理之处。“当政治行动对于马氏而言没什么可能时,他转向文学作品,因而其诗歌、书信以及戏剧里重复着他作为一名政治行动者被压抑的关怀,这并不是一件令人很惊讶的事。”[29](P265)这种进路注意到了马基雅维利在戏剧当中或针砭时弊、或冷嘲热讽。这既符合马基雅维利的能力和个性——他本人在《曼陀罗》的开场白当中毫不讳言,尖酸刻薄也是他最为擅长的技艺[30](P11),也与其时代的作风基本保持一致——“‘目光锐利、口舌刻薄’是对于这个城市 (指佛罗伦萨——笔者注)的居民的描写。对每件事和每个人都随便加以蔑视大概是当时社会上流行的风气。”[31](P175)然而,尽管这种进路注意到《曼陀罗》与马基雅维利政治著述中的一致性,却得出了一个夸张而草率的结论:“《曼陀罗》并不是一部普通的喜剧,它所呈现出的事件归根到底不是关于‘私人生活’的,而是对‘政治领域’的分析。”[32](P810)于是,这种进路使得戏剧仅仅成为马基雅维利表达政治思想的一个载体,却忽视了戏剧本身作为一部独立作品所具有的思想深度。因而,有研究者反对把《曼陀罗》视为挖掘政治寓意的素材。黑尔抱怨说,人们过度解释马基雅维利的文学作品,总是要用这些文学作品来撑起马基雅维利作为政治、军事或者历史作家的名誉,或者用来说明马氏某些不为人知的人格特征,而很少把他们视为艺术作品,亦即源自丰富的文学灵感、语言激情以及写作过程的作品。他恳求人们应该把马基雅维利的文学作品看做独立的艺术作品,而不是视为挖掘政治意涵的材料。他认为勉强从《曼陀罗》中挖掘政治意涵,是对马基雅维利的一种掠夺。[33](Pxi)
综上所述,文学作品固然欢迎隐喻式解读,而马基雅维利既是政治家又是戏剧家的身份也鼓励人们对其作品探幽索隐。但是,将马基雅维利的戏剧与其政治著述或现实政治进行简单的比附,然后得出结论认为马基雅维利的戏剧是政治的,这种观点与认为马基雅维利的思想在其政治著述中已完全展现的说法一样,都是对马基雅维利文学作品的轻视,从而一起陷入了马基雅维利为其观众所设下的局。[34](P10)政治领域与戏剧世界对于他来说,都是同等重要的,也只有在这种并行结构下,真正的马基雅维利才能得以彰显。
四、一个人应当如何生活:马基雅维利的审慎
《曼陀罗》里的戏剧行动围绕着这样一个具体问题展开:为了达成一个既定目标,应该如何去容忍恶与利用善。在《曼陀罗》所描述的私人生活里,这个目标是卡利马科势不可挡的情欲,以及卢克莱西亚与其丈夫尼恰想要一个孩子的欲望。卡利马科生于佛罗伦萨,后被送往巴黎,在那儿寄居多年。某日,他偶闻家乡有一位当今世上最美丽的女人,便不顾意大利战火缭绕,毅然返乡。驱使他置生死于度外的,是对于卢克莱西亚的占有欲望。与国家统一或者共和福祉这样的目标比较而言,情欲的实现既不高尚、也不诗意。但在马基雅维利看来,它是符合人性的。在马基雅维利的世界里,既有着沉重的政治问题、军事事务,也有着轻飘的感情与欲望。在他的生活与著述中,人们会看到他处理严肃的外交问题,会知晓他对于共和政治的偏好,也会读到他与友人讨论些不那么正经的事情。马基雅维利接受包括情欲在内的各种欲望所指向的任何目标,而不仅仅是为了国家或者公共福祉这些高尚的目的。然而,这位让卡利马科销魂夺魄的女人已为人妇,而且看起来端庄、虔诚。她的身份和表面上所呈现出的传统德性将戏剧行动置于冲突之中,自然欲求的实现遭遇到了道德对行动的限制。卡利马科在挣扎之后,情欲支配他势必“要筹划干点儿事情,哪怕像畜生一样残忍、冷酷、可耻”[35](P17)。
在这里,我们所遇到的就是在本文开篇所提到的那个马基雅维利,即传授邪恶教诲的马基雅维利。借用卡利马科的忧虑和行动,马基雅维利揭露出自然欲望的要求与道德的要求之间的紧张态势。为了达成个人所觊觎的目标,完全可以采取邪恶的行动,如同剧中为情欲所控的卡利马科一样。他在食客李古潦的主导下,诉诸一连串的欺骗,利用卢克莱西亚丈夫尼恰的轻信以及他们想要得到一个孩子的欲望,成功实现了目标。可见,马基雅维利的戏剧告诉我们,国家统一或共同福祉不能为他的邪恶教诲开脱,他的邪恶教诲同样为自然欲求服务。[36](P284-286)在后来,马基雅维利应圭恰迪尼的邀约为《曼陀罗》上演所添加的献歌部分里,开篇就指出,那些生活在忧虑和苦楚当中的人们,不懂得这世间的骗局。言下之意,马基雅维利旨在通过这部戏剧,向人们揭橥这世间的骗局。这个意图与其《君主论》当中最具影响力且备受争议的一章所揭示的甚为一致。“人们实际上怎样生活同人们应当怎样生活,其距离是如此之大,以至一个人要是为了应该怎样办而把实际上是怎么回事置诸脑后,那么他不但不能保存自己,反而会导致自我毁灭。”[37](P73)在这里,马基雅维利认为其写作的目的在于论述事物的真实情况,而不是想象的方面。但是,如果据此认为马基雅维利的作品仅仅是对人们实际上如何行事的观察与描述,那么必将难以发现马基雅维利的深刻,而且与其作品里所蕴涵的思想也不相符。事实上,马基雅维利的著述自始至终都在向人们传达“应当”如何生活的主张。
借助于反映现实生活的戏剧行动,马基雅维利充分阐发了对于一个人应该如何审慎行事的见解。在他的世界里,支配世事的并不是道德、上帝或者传统,而是必需 (necessity)。卡利马科为了实现其自然欲求,必须诉诸适宜的手段。一开始,卡利马科希望能通过改变卢克莱西亚的本性 (nature),在她面前展现自己的慷慨以吸引她。不过,李古潦认为这个计策不一定能达到目的,从而提出另一个主张。这个计谋主要依赖于欺骗,这是一个按照古典德性生活的人所不会采取的却是有保障的妙计。在他看来,道德、宗教给人们所营造出的是一种幻象。在生活中,芸芸众生 (people)宁愿“相信”这些“谎言”,而甚少能够凭借理智去“判断”,去看清这世间的真实 (effectual truth)。如同戏剧所指出的,只有祛除此种幻象的人,其行动的可能性才不会受到道德的限制,才能获取其所欲求的东西。但是,在戏剧里,李古潦洞察到卡利马科的澡堂计划不能保障目标的实现,从而提出以曼陀罗为药方。这说明在马基雅维利的世界里,并不是每个人都具有判断力和据以审慎行事的德性。又或者说,马基雅维利是在向人们建议,人应该审慎行事,他们需要充分洞察这种必需,而不被道德幻象所迷惑。也就是要能够洞察世事、深谙人性,以冷峻的意志扛住命运,做到顺势而为,包括容忍恶与利用善,而且能够“表现出”具有传统或习俗所尊崇的美德,从而达成既定目标。对于目标本身道德与否,马基雅维利不予置评——在他的作品中,我们所看到的目标,既包括国家统一,也包括共和国的创建,同样还有本能的情欲。可见,马基雅维利在洞察世事的基础上,提出关于人应当如何生活的训谕。他悉心教诲人们的是,为了达成既定目标,应该采取怎样的行动。他在《李维史论》中对此毫不讳言:“我以为或能多有所成,俾可给他人达到既定目标提供一条捷径。”[38](P6)不过,戏剧形式更能彰显出其学说的普遍性。《曼陀罗》作为一部戏剧,其主要注重的是行动,马基雅维利能够将其对审慎行事的理解,巧妙地与戏剧形式结合起来,表明应该如何生活;而马基雅维利的政治著述所讨论的只是其中一些具体的情势。一旦我们发现,在政治或军事上的真理可以转化成反映私人生活的戏剧,或者说在政治与戏剧的并行结构之中,我们会发现马基雅维利学说的核心并不是共和主义,也不是爱国主义,而是关于一个人应该如何生活的普遍性教诲。
关于这个问题,马基雅维利的回答与古代伦理和现代道德的进路都有所不同。前者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从行动者的美德出发,关注人的完善以及道德德性的实现;而后者则是从行动的普遍规则出发,围绕各种义务展开,例如霍布斯对确定政治义务的不懈努力,康德主义将道德责任视为道德哲学的根本问题,功利主义旨在捍卫普遍福利最大化的原则。至于马基雅维利,一方面,他关注德性,强调审慎行动的能力,尤其是具有洞察情势的判断力和扛住命运的男子汉气概。但他并没有像亚里士多德那样具体讨论行动者应该具有哪些美德。他不把道德德性作为行动的目的,反而认为审慎行事不仅要有作恶的能力,也需要伪善的本事。另一方面,他并没有对究竟应该如何行动提出具体规则,也不像现代道德理论那样对行动规则进行理论化。可见,他对一个人应该如何生活的回答,既不同于古代伦理又不同于现代道德。
我们正需要从这种区别当中去重新理解马基雅维利与现代政治乃至现代伦理的关系。伯林认为,马基雅维利所处理的乃是对两种不可调和的生活理想的区分,因此也是对两种道德的区分,一方面是基督教的道德,另一方面是异教徒的道德。人们必须在这两种生活方式中做出抉择,选择一种,放弃另外一种。伯林力图阐明,马基雅维利选择了一种相悖于基督教道德观的目的王国。分析起来,马基雅维利的学说的确具有规范意义,不是简单地玩弄技巧。但这种规范意义并不像伯林所说的那样,属于一种以共同目标为最高价值的希腊城邦伦理。马基雅维利的审慎概念,拒绝将道德德性视为行动的终极目的。[39](P43-58)论者认为马基雅维利是在两种道德之间选择了其中一种,这种说法同样也是浅薄的。它没有注意到马基雅维利的戏剧里对于这两种道德 (古典的道德德性与基督教的道德)的利用。马基雅维利并不是在两种道德之间进行选择,而是提出了一个超越两种道德的新范式。
《曼陀罗》还有可能让我们审视马基雅维利涉及的古今问题。施特劳斯注意到了马基雅维利利用爱国主义情结来服务于一个更隐秘不宣、讳莫如深的目的。他认为,马基雅维利实际上是在提出新的启示,一个新的法规准则的启示,一个新的基督教十诫的启示。[40](P83)但是,他将马基雅维利简单地置于古今之争当中并认为他属于“今人”或现代性的开创者也是有问题的。他的确洞察到马基雅维利与前人的断裂。但是,马基雅维利的审慎概念与现代伦理并不相同,同时他也没有开创出一种现代政治理性概念。不同于霍布斯的是,马基雅维利的审慎概念缺乏一种现代政治理性所具有的普遍性。他的审慎德行只为部分人所拥有,芸芸众生更多是“相信”而非“判断”。至少,从这个意义上看,我们很难认为马基雅维利是现代政治的开创者。因而,马基雅维利在戏剧行动里对审慎的理解,为我们重新审视其在思想史上的地位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1] John H.Geerken. “Machiavelli Studies Since 1969”.J 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1976,37.
[2] 黑格尔:《新的历史中的国家理性的理念》,1925。转引自卡西尔:《国家的神话》,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
[3][7][36][40] Strauss.Thoughts on Machiavelli.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69.
[4][25][38] Machiavelli.Discourses on Livy.translated by Harvey C.Mansfield and Nathan Tarcov.Chicago&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6.
[5][9][12][14][20] James B.Atkinson and David Sices.Machiavelli and His Friends:Their Personal Cor-respondence.Dekalb:Nor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1996.
[6] 亚里士多德:《诗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8] Joseph V.Femia.Machiavelli Revisited.University of Wales Press,2002.
[10] Vickie B.Sullivan.The Comedy and Tragedy of Machiavelli.Yale University Press,2000.
[11] 迈克尔·怀特:《马基雅维利:一个被误解的人》,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13] 斯金纳:《马基雅维利》,北京,工人出版社,1986。
[15][30][34][35] Machiavelli.Mandragola.Translation,Introduction and Notes by Mera J.Flaumenhaft.Illinois:Waveland Press,Inc.,1981.
[16][21][33] J.R.Hale.The Literary Works of Machiavelli.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1.
[17] 黑格尔:《美学》第三卷 (下),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18] Salvatore Di Maria.“Machiavelli on stage:MandragolaandClizia”.inSeeking Real Truths,ed.by Vilches Patricia and Seaman Gerald,Brill Academic Pub,2007.
[19][23] Theodore A.Sumberg.“L a Mandragola:An Interpretation”.The Journal of Politics.Vol.23,No.2,1961.
[22][24][32] Carnes Lord.“On Machiavelli's Mandragola”.The J ournal ofPolitics.Vol.41,No.3,1979.
[26][29] Susan Behuniak-Long.“The Signification of Lucrezia in Machiavelli's‘L a Mandragola’”. The Review ofPolitics.Vol.51,No.2,1989.
[27] Michael Palmer. “The Master Fool:The Conspiracy of Machiavelli's Mandragola”.inMasters and Slaves.Lanham,Lexington Books,2001.
[28] Ruggiero Guido.Machiavelli in Love.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07.
[31] 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37] 马基雅维利:《君主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39] Isaiah Berlin.“The originality of Machiavelli”.Nigel Warburton,Jon Pike,Derek Matravers(ed.).Reading Political Philosophy:Machiavelli to Mill.London:Routledge,2000.
(责任编辑 林 间)
Rethinking of Machiavelli:Based on the Reading ofMandragola
CHEN Hua-wen
(School of Government,Sun Yat-sen University,Guangzhou,Guangdong 510275)
There are many faces of Machiavelli hidden in the literature,some of which are even contrary to one another.However,the approaches that try to fix the gap are not convincible enough.The reason is that they are limited simply in Machiavelli's political writings.Mandragolatends to deal with a problem of the universal.In the light of the drama action,Machiavelli presents his understanding of how one should live,which constructs the core of his teaching.The answers he provides are different from the approaches of ancient ethics and modern morality.Thus,we can rethink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chiavelli and modern politics or modern ethic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Mandragola.
Machiavelli;Mandragola;prudence;modern politics
陈华文: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广东广州5102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