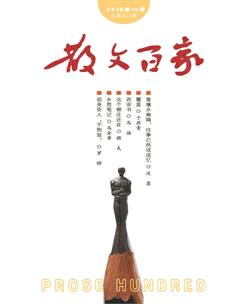银杏树下
曹丽琴
一
冬季,印象里总是一派萧瑟。但草木有心通灵,会真切地与我对话,诉之真谛。
那几株银杏始终巍然而立,静如止水。
我忍不住下楼去走走了。绵绵细雨,柔若无骨,飘在脸上还是冷意沁人。这几株银杏就这样静默在冬日的雨雾里。及至树下,抬头凝望着满目盛装的银杏树,心头蓦得划过一丝浅浅的黯然。
就在我凝神之时,一枚银杏叶从高高的枝头飘落下来,缓缓的,宛若一只小小的船儿飘荡在空气中,飞舞在我的视线里,最后飘落在了衰败的草坪上,好像极其微弱的游丝一般的一声叹息,与那些早已飘零而下的万千黄蝶融为一体。
落叶的过程原是这般稍纵即逝、悄然无声。
端详着这枚小小的银杏叶,我又抬头仰望气势如虹的树冠,恍然而悟,这是所有叶子熬尽生命的芳华最后的燃烧,它们汹涌澎湃、痛快淋漓、波澜壮阔,是给滋养它们的大地和阳光雨露以生命最后的馈赠。
二
春逝了,秋远了,冬至了,又一次滞留在银杏树下,昔日那个天真烂漫的水乡小姑娘,已是一位少年的母亲,已是众多孩子的老师。
迄今,我依然清楚地记得第一次看到银杏树时的情景。那时正是初夏时分,一片片银杏叶宛若一只只绿手掌微风里摇曳着,恰似与我们招手。在昔日苏州水乡,遍地红桃绿杨,银杏是极罕见的。几个十来岁如鸟儿般叽叽喳喳的小姑娘发现了新大陆似的,瞬间停下跳跃的步伐,聚集在银杏树下,仰起小脸新奇地观察起来。显然,我们被它特有的叶形紧紧地锁住了目光,才知自然界原来还有这样一种叶子有形的树。
英说,这树叶是一把把小扇子;花说,是婴儿脖颈上戴的百锁;我说,是一块块玲珑璧……我们争论不休,各持一词,尽情地遐想着。那一只只小手掌,一把把百锁,一块块玲珑璧,一团团绿云,无意间落在了我的心坎里。
当二十多年过去,机缘适时,我再次如儿时般驻足在银杏树下时,那抹画意突然在我记忆深处复苏,似昨日所遇,鲜活在我的眼前了。
也许,一切有形和个性的事物自然而然会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在我们的内心深处,骨子里其实是喜欢和向往有形和个性的。只是,由于现实中的诸种因素,成人之后,身心里倍添的更多的是人的俗性,而个性渐渐被抹杀。有时候,我们人类在某些方面真的是不及一棵树的。
今天这几株银杏呈现于我的,完全有别于儿时印象中的:一个是初夏的生机盎然、蓬蓬勃勃,一个是深冬的绿意褪变、辉辉煌煌;一个是生长,一个是落幕;一个是入世,一个是出世……但是都给予了我心灵的震颤和悸动。
不同的季节,不一的美。美从来都是丰富多姿的。可叹的是光阴,任凭我们怎样地努力,终是赛不过时间的步伐,就像银杏的纷飞、飘落一般,匆匆又匆匆。
记忆里,我们总是从水乡的这个村庄穿梭到那个村庄,几乎周遭的每个村庄都留有我们年少的身影,但我们只发现过那一株银杏。每每走过它身旁,便要情不自禁地去观望它几眼。后来,我们一群小姑娘,辍学的辍学,求学的求学,工作的工作,那株银杏也渐渐被我们淡忘。最后我们都出嫁,宛似村庄上的蒲公英飞散到城里或者其它村落,从此便在各地落地生根,组建了自己的家庭。那株曾经被我们关注过的银杏,也早已不知去向。就像我们曾经一度长大起来的玩伴,在时光的流逝中,渐渐失去了联系。
她们都不记得那株银杏了吧。抑或也会有一位如我般,在冬日里看到这般灿烂的银杏,忽然想起我们儿时仰望银杏的情景?
我无从得知。只晓得曾经那样熟稔和亲密的关系,最后还不是经不起光阴的冲刷。我们长大了,走向了各自的天地,最后却在人海中失散了。我的心里瞬间被笼罩上几朵怅然的阴云。
三
最让人痛楚的是英已经永远地离我们而去了。
2011年暑假,我回到我的村庄钱家簖。母亲对我说,英身患白血病七月初去世了,治愈了大半年,耗费了很多钱财,最终还是躲不过呀。
我惊愕得半晌无语,似晴天霹雳。眼前浮现出英小时候那永远红润、娇嫩的笑脸,那清秀、活泼的身影。可是,岁月是多么无情,怎么可以夺走这样一个善良、贤淑的女子呢?我忽然第一次意识到死亡原来与我们的距离是如此之近,它有可能随时会夺走一个人的生命。
英是我儿时形影不离的伙伴,每天清晨我都会去她家等她一起上学。放学后,一起做作业、跳牛皮筋,假日,约上几个伙伴,一起去田野上采青豆、油菜田里躲猫猫、北河泾清冽的河流中快乐地嬉戏玩耍,小学六年级儿童节庆祝会上,我和英、花羞涩地歌唱、合影留念……后来,我去江苏省吴江师范求学,她家搬到了苏州市区,我们的联系就少了。
最后一次见到她,已是我参加工作后。记得那是一个艳阳高照的早秋,她回到从小生养她的南河头村庄看望她的祖母。她刚从公交车上下来。我回家吃好午饭,骑着单车正急着赶往学校去教书。
“英回来了。”我微笑着和她打招呼,两人相视一笑,各种亲切和欢喜瞬间荡漾在我们的心间。她出落得更为标致、苗条了,已经不是儿时稚气的小姑娘,而是芙蓉花一样娇羞、迷人,阳光里亭亭玉立、顾盼生辉。
我回首望着她那秀气的身影,两人就此擦肩而过。没想,这成为永别。那时,我总觉得属于我们的时间还太多太多,我们的相聚还会像长江水一样滔滔不绝。如果世事可以预测,那次邂逅,我一定会和英像儿时那般促膝谈心、喜悦无尽。
可是谁又能预测我们的命运呢?谁又会知晓时间有一天会这么快地在一个人的身上终止呢?她迁往市区与我们别离的那些年,我先后陆陆续续知道一点有关她的音讯。她的母亲后来患癌去世了。之后几年,她的父亲也出车祸客死异地。而她的哥哥交友不慎、好赌成性。她于离世的前三年,跟随在上海机场当官的丈夫落户上海定居,做起了全职太太。原想从此生活可以安定些了,可最后却遭受如此劫难。
在英身心交瘁的那些年,我了解得并不多,偶尔零星知道些,也没有想办法去取得她的联系方式。其实并不难的。但是,我却什么也没做。也许是大家别离这些年,彼此都有了自己的经历和生活,淡忘了儿时情意;也许是世事的磨练,让人际变得生疏、冷漠了;更也许是愧疚吧。师范毕业,我回小镇村小教书那年,英父母托媒人说起过我,英的哥哥。她哥哥亦是我小学同学,但是初中毕业后辍学了。我就没有应允。于此,我总是觉得有点愧见英一家人。小时候,英父母,他们一家人是那么喜欢我,但是爱情、婚姻和友谊、乡情是两回事。
现在人至中年,想来英那时就应该能理解我的。我相信她也不会怨恨我的。我们是应该早取得联系的。但是,世事没有如果,错过了就错过了。一些逝去了就永远逝去了。我良心的反省和审问于英而言已经没有什么实质意义了。一切无法弥补。
英,她的父母亲最初为她取名的时候,即是希望她如春天的花儿一样永远芬芳。但是那年落英缤纷的晚春里,她的病情就已经非常严重了。她终没有熬过夏天。在草木最为兴盛的时候,她一个人在异地在繁华的上海,抛下了她的爱人和年幼的女儿,仿佛儿时,我们所关注过的一枚银杏叶过早地枯萎,失去了生命的绿意,独自凋零了。那年,她才三十三岁。
这些,我都是后来才知晓的。可是斯人已逝,一切都只待成追忆。一棵树的肃穆与沉静是否能表达对一个人的怀念和哀思?银杏不语,天空默然。只有我在银杏树下黯然神伤。
四
英走了,花呢,变得让我十分陌生。
去年隆冬,钱家簖拆迁的前几天,乡亲们都选择了一日,在这个村庄上对先人们进行最后一次的祭祀。我回去,像小时候从村西第一家自家出来,挨家挨户地走过。走至中村,看到曾经横跨村前北河泾的拱桥,现在只剩下两个桥墩,且早已颓废,不免有点伤怀。后至东村再折回。见见乡人,聊聊乡情,以让村庄在我心灵的版图上留下最后一遍印记。
花也正恰回娘家,我在村庄上遇到她时,竟没有认出。她穿着一袭皮袄,华丽的狐狸领衬托着她脸上厚厚的脂粉,鲜黄的头发,深黑的眼影,妖冶而媚俗,眼神里已然没有了儿时的那般纯净。
花和我同村,两家关系又甚好。念初中的时候我们还是同桌,只是念完初二她就辍学了。那年初二暑假,我曾去她家劝过她,但是她已厌倦读书。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苏州农村掀起了做缂丝之风,一条缂丝带销往日本能赚到五六千。很多和花一样的乡村姑娘都早早退学,跟随村上妇女融入了这大潮中。花也抵挡不了诱惑。可是,四年后,缂丝行业渐渐衰退。花因没有固定职业,成天混迹在麻将堆里。两年后,她嫁给了别村一个小她一岁的木匠,过了几年平静生活。再后来,我又听人说,花做起了安利产品的推销,认识了很多我们这儿家具城的老板,就嫌她男人没本事,买了车后经常几宿不归。偶尔回家,也和男人分床而眠。花的婚姻犹如一块布满了无数裂缝却始终没有彻底碎裂的钢化玻璃。再次邂逅,我们已然没有了共同的话题,彼此不知言何,我也不知怎么劝诫。
往事成空。花已不是过去那个单纯的花了。她已然不记得我们的欢声笑语,童真的质朴无邪。时光一去不复返,没有谁能踏入往昔的流年岁月,也没有谁有这个力量能阻挡住时间给予我们的变化,尤其是人的志趣。
落叶纷飞,斯人已远。
五
良久,我从沉浸的思绪里醒来。
转身准备回去,忽又见得离我六七步远,竟有一抹新绿。虽只是浅浅嫩嫩、星星点点的一小片,个头还不及一指甲高,但冬雨里尤显得可贵,让人为之眼前一亮。
我轻轻走过去,小心翼翼地移步,生怕一不小心会踩到它们。至近前,才缓缓弯腰、蹲下。相形这片小草,我就是一个巨人了。这是一片刚刚钻出泥土探出头来的小草,宛如新生儿一般,张开了对这个世界充满好奇的眼睛,极尽可能地冒出来,把头昂起,把身子挺直,欢欣鼓舞的,仿佛每一根筋络每一个细胞里都有着不断生长和舒展的活力。尽管微弱得不足一道,但却足以愉快地支撑它们在这个季节里尽情尽兴。就像儿时的我们。
它们是四叶生的,圆圆的叶芽儿好像四滴春水般闪烁着晶莹的光泽。任凭厚实的泥土硬如坚壳,任凭冬日的酷寒肆意侵袭,这么一小片不起眼的小草,却在四围无尽的衰竭中,彰显着生命的一种本能、一份力量,向大地向天空点亮起了这抹娇嫩的但又坚强无比的绿意。
冬日已深,它们却是生机无限的。高大的银杏树下,这抹小小的绿意与满地的落叶形成了色彩上的鲜明对比,或者更多的一些。我不禁对它们肃然起敬了。草木是多么的谦卑,但又让人动容呀。
花开有期,叶落无语。银杏也好,绿草也罢。枯荣有时,春秋无垠。生命轮回,自然永远是这般生生不息,每个季节都有它的特点。即使在冰冷的季节里,也不缺少美的丰盈,不缺少斑斓和生趣。再望不远处,香樟、桂花、广玉兰依然郁郁葱葱。
人生犹如四季,灿烂与落寞、欢喜与悲伤、纯洁和艳俗并存,谁也不能保证每个季节都浸染在同一个色调里。生活,充满五味杂陈,只是世相百态、诱惑纷繁、生命脆弱、性情易变,怎样才能最大限度地经营好自己、把握人生、从容安详,真是一门要认真研修的学问。
我和英、花都是千千万万水乡人家里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孩子,都是饮着北河泾的水长大,演绎的人生轨迹却迥然不同,然之何故?面对如此宏大、深邃的问题,我是如此弱小和无助。银杏树下,绿草边上,唯有默默地独思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