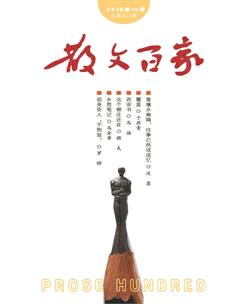长江与黄河
石厉
一
长江,是我心仪已久的地方。只因时运不佳,每次将临时也只是匆匆过客,每次都是从横跨长江的大桥上随火车一晃而过,只留下了许多散逸的思绪及想像。
少年时代,读过许多历代文人墨客写长江的诗词,当时潜入我心灵深处的恐怕是宋时李之仪的《卜算子·我住长江头》:
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此水几时休,此恨何时已。只愿君心似我心,定不负相思意。
在古乐府中有一首民歌《上邪》大致也有同类的情思:
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
看来长江上男女相悦之情中定有许多惊天动地的细节,在无穷无尽的时空中,一条汹涌绵长的河流,不知流过了多少儿女故事。其中这位宋时的进士、曾做过枢密院编修、后因写文章出事而被贬至安徽当涂一带的李之仪,在江边终以写词咏情了此一生。那么他的《卜算子》一词所描述的当是一种什么样的曲折悲欢呢?
个中的细节让人思想不已,个中的情由让人不得而知。时间抹平了许多情节,却不能抹去文字。这首词中的悠悠千古之情代表长江占据了我多愁善感的少年时代,甚至到了中年。这首词中的浓情也似乎化作了我意识深处最具体的江水,浪漫而透彻。
因为在每个人的身上都演绎过不知何种程度的爱情,尤其是在这样一个多情的时代。我也有过爱情,让人痛不欲生的时候,让人情不自禁的时候,甚至山盟海誓的时候,我都不想用与我长相厮守的黄河做比喻,我都愿意用幻想中的长江来抒发情怀。看来遥远与看不见的东西永远成了我们理想的标志。
二
长江无疑是我心灵朝拜的圣地。
中国文化除了以黄河流域为代表的中原儒家正统文化之外,再就是以长江流域为代表的楚文化了。中国两大诗歌源流《诗经》与《楚辞》,完全可以用这两大水系作为象征。尤其是春秋以降,中国最优秀的诗歌竟都产生于这一带。最明显的原因恐怕还是楚与周王朝的疏远。当时,楚并不隶属于周天子,不是周的诸侯国,而是一个可与周朝分庭抗礼的国家。在这样一个国家,人们在文化上没有过多的约束,精神上的殊异与自由无异是创造新文化艺术的阆苑。据《史记·楚世家》载,到周夷王时,楚主熊渠甚得民心,便说:“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东周初年,熊通伐随,命随人请周尊楚,周不许,熊通大怒说:“吾先鬻熊,文王之师也……蛮夷皆率服,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自此,楚的版图渐渐扩大几乎包括了整个长江流域。
楚国狂妄自大无疑带有野蛮的气息。
这也是长江与黄河的对抗!
除了文化上的长江之外,除了纸上谈兵之外,实际上我对长江一无所知。我是黄河上游长大的孩子,真正是黄河的儿子。后来又在黄河边读书、生活、工作一直到而立之年。命运使我被迫辗转别地。
这一次,第二届长江笔会在江上举行,全体与会者将乘船逆流而上,使我昏睡的内心似乎又要苏醒。
我愿“逆流”而上。
我不喜欢顺流而下。随着人生的沉浮与世事的变化,我越来越厌烦李白诗歌的轻狂,当得到一点点的苟且偷生时,便“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了。大概那种轻浮的顺利与快乐只是短暂的、肤浅的。人生的艰难,恐怕是自古不变的情境。“逆流而上”不言而喻成了我的向往。
屈原写于晚年的《涉江》一诗便是这种心境的写照:
乘鄂渚而反顾兮,唉秋冬之绪风。……乘龄船余上沅兮,齐吴榜以击汰。船容与而不进兮,淹回水而疑滞。……吾不能变心而从俗兮,固将愁苦而终穷!
屈子是从武昌过江而又沿湘水逆流而上的。在心志上与我殊途同归。正因为他不能随从流俗便“将愁苦而终穷”。是教训与告诫还是内心的写实?这只能是仁智两择了。但是对于诸多的传统文人大概只能是心境的写实了。因为除此而外,再就是无所适从了。
还有一种情绪大概也是颇为典型的,那就是人们对于顺流的感慨。
孔子将河水比喻成时间: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
这已是千古绝唱。那种对于已流逝的哀伤和悲叹几千年来让人吟诵不已。虽然这是孔子面对黄河时的喟叹,但如果他生长在长江边,会不会有同样的思绪呢?
大概又是因为我确实不忍看到时间如河水一样流逝,更不忍看到生命亦如河水一样流逝,我则愿意逆水而上,去探究和体验生命的源流。
这也确实是人生的又一理想。
三
背负着黄河赋与我的希望,来与长江会面。
当躺在包间的床上,眼看同室的朋友闭目睡去后,我却不能入睡,因为这一会儿我的心情不能平静。首先最大的遗憾是白天去“黄鹤楼”的想法最终落空了。笔会的活动时间被安排得井然有序,几乎没有时间去参观此楼。因为与会者很少有人对黄鹤楼感兴趣,与别人聊起来,他们以为仅是一座破楼而已,并且告知我此楼已卖给了商人,做了赚钱的道具。这怎能不使我怅然若失?
崔颢题诗《黄鹤楼》,感怀历史而生茫然之情。后来李白自以为崔颢诗已到绝妙境地,不免有压抑之感,除了他送孟浩然时写下的那首有关离别之情的诗外,便无奈地写下“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从此以后,直奔黄鹤楼而来的文人,可能是慑于李白的告诫,谁还敢到黄鹤楼上正儿八经地写诗呢?黄鹤楼上已经有诗为证,不在这里写诗也罢。
历代被放逐或沉沦的文人到了长江边便留下绝妙的诗句,黄河两岸与之相比反倒黯然失色了。长江远离中原正统的政治文化中心,以前到了这里的文人,失魂落魄者居多,难免生出欲驾鹤西去求生不能求死亦不能的痛苦心情,越是这样,也越能产生极为优秀的诗歌。看来不幸也拯救了文学。
庞大的游轮微微颠簸晃动起来,开始在江面逆水而行。江面狭窄,两岸都是耸立的青山,江水混浊得发黄,有点像黄河,一瞬间我还真以为自己是在黄河上呢。很快就觉得这绝对不是黄河。人们的皮肤都是湿漉漉的,潮气在阴郁的天空下随着游轮行进而掀起的微风包裹了我们。熟知长江的朋友告诉我,长江上一年四季都是这样的天气。
我真希望大风吹来,波浪翻滚,看来已是虚幻了。江面平静而沉郁,杜甫说的“江间波浪兼天涌”,似乎已是不实之辞。
闷热真正“使我不得开心颜”。我试图极目远眺,在东张西望中眼光却无法逾越江岸的曲折与两岸雾蒙蒙险峻的高山。
这就是长江三峡。是长江中最为经典的一段。
我的心情却随着身体的不适而郁闷起来。我终于在疑惑中断定这长江根本无法与黄河相比。黄河非常宽阔,两岸平缓、大多是一望无际的平原,爽朗的天空下,它像一条黄色的长带束在祖国的半腰。那里是古代文化政治的中心或发祥地。两岸有着碧绿而一望无际的草地,蓝天白云下,到处都是帐篷、牛羊、房舍与农庄。
我上了甲板,眼望着缓缓流过的发黄的江水,两岸的山中,隐隐约约有古栈道穿过,偶有炊烟飘荡,但总是看不见人迹。我觉得长江仿佛只是黄河走失的一个孤独而可怜的孩子。江面只因巨轮划过时,才有混浊的波浪翻起,然后又轻轻地落下。黄河则是奔腾和呼啸着的。你可以畅游长江,但却不能畅游黄河,因为黄河的水下还有许多可怕而不明的漩涡。
进入巫峡地段,已是第二日的凌晨了。用过早餐,我陪同著名评论家阎纲先生刘锡诚先生、著名散文家柳萌夫妇一同上了甲板,水气还是很重,不过已经比前一天适应多了,心情也畅快了一些。
北岸的神女峰开始若隐若现了。这神女峰,俨然一位古代女子的打扮。她的存在,不知又引出了多少故事。据宋玉《高唐赋序》:“妾在巫山之阳,高丘之阻,旦为朝云,暮为行雨,朝朝暮暮,阳台之下。”这神女自以为是长江之妾了。高山将她与长江阻隔,但却无法阻止她与长江的行云施雨。这种描写直接而形象。问题是这巫山之云后来却因唐代元稹的《离思》一诗显得更加广为人知:
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
取次花丛懒回顾,半缘修道半缘君。
这首诗前两句表述了元稹对某位女子的无尽思念,以及显示了这位女子在他心中至高无上的位置。后两句大意是,无论是什么样的花丛(指美人)我也懒得回头了,一半的原因是因为修道一半的原因是因为君。
这首诗是元稹为《会真记》中的崔莺莺所作。“君”无疑是指崔莺莺了。据国学大师陈寅恪在《读<莺莺传>》一文中考辨,唐代元稹所写的《莺莺传》又叫《会真记》,实为一自传体小说。元稹将自己化名张生,将自己曾喜欢过的一位绝妙的民间美女假托为相府少女崔莺莺。而后来这位元稹(字微之)为了巧取功名,便抛弃“莺莺”娶了高门韦夏卿女韦丛为妻;韦丛去世又娶高门女裴淑,裴淑未娶之前,还纳妾安氏。由此看来,整个一位花花文人也。而元稹对“莺莺”完全是始乱终弃。所以陈先生就这首《离思》指斥:“微之自言眷念双文(双文指莺莺)之意形之于诗者,如‘取次花丛懒回顾,半缘修道半缘君,是其自夸守礼多情之语,亦不可信也。”(见《元白诗笺证稿》)
《离思》这首因沧海水、巫山云而臻于化境的诗,其虚伪之情已被陈先生一语道破。也许在个体的意义上元稹是个说谎者,但是他的作品却带来了一种普遍的情感与真理。这也是陈先生失察的地方。元稹的《会真记》又被后世文人篡改成为《西厢记》,真相早已面目全非。而脱胎于宋玉巫山神女说的“云雨”一词,在明清小说中已成为最为淫荡的词汇了。
说来也奇怪,当抵达距离神女峰最近处时,刚才的一缕缕烟云突然化作温润的小雨下了起来。
甲板上的游客所剩寥寥。我没有离去,任凭来自神女峰的可人小雨弄湿,真正享受了一次“云雨”的快乐。这也是我从未在人间得到过的一种快乐。
等到雨停的时候,我也意兴阑珊,回包间休息去了。
四
将近10点钟,船到了白帝城。
这座古城并没有多大,说起来也没有什么好看的。我只是怀着文化历史的情感想见识一下这个地方。之所以叫白帝城,与后汉一个叫公孙胜的人在此筑城称帝有关。这里扼江据要,是古代军事重地。占山为王的人,在时间的长河里只是一些笑柄而已。这座山城以后变得几乎家喻户晓,完全是沾了李白和杜甫二位诗人的光。但是就这里的民风而言,诗礼的传承究竟有多少,这是让我这次旅行的不解之处。不过早在唐代,李益的《江南曲》曾描述:
嫁得瞿唐贾,朝朝误妾期。
早知潮有信,嫁与弄潮儿。
连妻子都怨自己的丈夫只认钱不认情,这一点让我颇有感触。
在码头上抬滑竿,这大概是白帝城人比较古老的职业了。我们一上岸,与我们同行的几位残疾人作家就开始让他们眼睛里放光。他们中一个自称是头儿的人向我们报价,每抬一个人100元。这时来接我们的当地导游小姐说,不是说好了每人50元吗?那人挤了挤眼睛说,不行,他们不是中国人,是外国人,外国人一律100元。我们有人上去给他们耐心解释说,我们是中国人,你们看我们都是从北京来的,都说普通话,长的也与你们差不多,都是黑头发、黑眼睛、黄皮肤。这头儿拖着四川腔说,差得远,你们哪里是中国人嘛,你们分明是外国人,是新加坡人。看来再讲下去也没有用,我们只好依了他们。除了残疾人之外,我们是步行登上这座山城的。
沿途的山路旁都被卖各种旅游小商品的小商小贩占据着,与别的旅游地大同小异。不过三峡从古至今都是商业繁华地带。李白著名的《长干行》、《江夏行》等诗歌都是反映三峡的商贾生活的,里面充斥着诸多怨气。杜甫的《最能行》也说:
峡中丈夫绝轻死,少在公门多在水。
为了赚钱,连死都不怕,还讲什么亲情与人情。我想李、杜二位当年在这里也不知吃了多少三峡商人的苦头。
在我眼中,这白帝城的走运,恰恰是因为这两位诗人的不走运造成的。
安史之乱期间,李白跟随永王李磷转战大江南北,稍后永王被指控谋反遭到肃宗王朝的剿灭,李白因此获罪被擒。此时幸遇喜欢李白文采的宋若思管理他的案子,宋若思释放了李白,并将李白安置在自己的幕府,同时还极力向肃宗皇帝推荐李白。李白在唐玄宗时就因让高力士为他脱靴而惹得朝野上下觉得他过于自负与傲慢。现在因在宋若思府中受到抬举一时又忘乎所以,写了许多诗文纵论时局,且自吹自擂,终于又一次被清算——长流夜郎(今贵州遵义附近)。统治者是否是有意将这个夜郎自大者长流夜郎,惩处之外又有讽刺意味呢?他沿江西上,在《流夜郎赠辛判官》一诗中写道:
我愁远谪夜郎去,何日金鸡放赦还。
他在无比苦闷的心情中舟行了一年多,此时因关内大旱,肃宗颁布大赦令。当到了巫峡白帝城时,李白欣闻自己已被放免,便乘飞舟回到江陵,兴奋之中写下那首著名的《早发白帝城》,狂喜之情显而易见。后来在漫长的岁月中,白帝城因这首诗而愈加著名。
大概之后不久,曾在十多年以前与李白结交过的好朋友杜甫因成都战乱频仍,便一直思谋沿江东下。但在中途病魔缠身,只好流落白帝城。杜甫在夔州时,由于朝廷有人羡慕他的诗名,向夔州都督过问杜甫的境况,杜甫便因此获得了主管一百顷公田的职务。在《晚》这首诗中:
朝廷问府主,耕稼学山村。
在这里,有公田,有奴仆,他带着家人,生活过得还算闲适。但是他并不喜欢巴山蜀水,时间久了甚至开始讨厌这块地方。有好几首诗都是表达这种心情的,比如《春日梓州登楼》、《奉汉中王手札》等。他在《闷》这首诗中写道:
瘴疠浮三蜀,风云暗百蛮;卷帘唯白水,隐几亦青山。
在这样一个自己并不喜欢的山城,朋友稀少,再加上他老弱病残,这种孤独苦闷的心态反而使他的创作欲望非常高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他写下了近五百首诗歌。其中艺术上具有代表性的诗歌,我认为是《秋兴八首》。在这组诗歌中他表现出来的思乡的痛苦不知又抚慰过历代多少游子的痛苦:
丛菊两开他日泪,孤舟一系故园心。
他思念黄河、思念北方的心情溢于言表。
三年以后,他沿江东下,顺着好友李白的足迹去了江陵。从此新的飘泊、茫然的命运又一次开始。
可惜的是,遍寻白帝城的碑林,也没有见到李、杜有任何的墨迹。尤其是诗圣杜甫,在这里住了那样长的时间,竟没有保存下一点他书写的痕迹,这使我在下山时禁不住寻思良久,神牵不已。
五
三峡一段,大概有一百多里长,游轮却航行了三天。我们是边走边停,夜里游轮停泊在某个码头,白天遇到两岸名胜,游轮偶尔也要停下来。第三天的上午,游轮停在了重庆市丰都县城。
丰都是长江北岸一个景色秀丽的小县城,据说世上的人死了都要到这里来报到,有“鬼国京都”之称,因此也名闻世界。这样一个都城,撩拨了我的好奇心。我观察阎纲先生对游览鬼都似有心动,我们自然就结伴而行。他执意不乘滑车,而要步行攀登这鬼城阎王殿所处的平都山。平都山也叫名山,东汉时,山上有高道阴长生、王方平二人潜心修炼,传说他们后来都得道成仙。阴、王二字连读便为阴王,阴王者,统管阴间之王也。东汉以后佛教传入中国,佛教中恰有“阎魔罗”(梵文音译)为统治地狱之神,中土百姓便简称“阎王”,阴、阎一声之转,“阴王”又可称为“阎王”也。
这是我迂腐的揣测。
对于北方人来说,这里阴湿之气太重,此时恰是正午时分,没有一丝的风,闷热使人无可奈何。我和阎先生沿着石阶而上,气喘嘘嘘,汗如雨下,有感而发时也只是轻声慢语。幸好阎先生带着一块毛巾,互相间递来递去,一会儿就能拧下许多水来。此时,我大有与阎先生共患难、同沦落的感受。
阎先生是文坛名家,鸿儒也,在修养和人品方面,都让我辈敬仰。只可叹,晚年丧失爱女,悲怆浸透了他的整个身心。
但在向阎罗殿的攀登中,他似乎比我还要坚韧。我好像能隐隐感觉到,在他清瘦的身体中闪现着一些沉重的希望。这希望让他显得越来越有一种飘逸之感。他一直走在前边,而我这个年轻后生只能紧随其后了。
阎先生的女儿阎荷,人如其名,漂亮优雅,是京城新闻界的才女,在1998年查出恶性肿瘤时仅三十多岁,从此一病不起,于2000年夏天不幸去世。
对于像阎先生这样一位有着多情而丰富内心的文学家,又是白发人送黑发人,让他如何承受得了!
但是他却承受着。
想到此种情景,我们都无意去观览周围的景色了。
一会儿就到了名山半山腰著名的奈何桥旁。此桥在一座大雄宝殿之前,一共有并列相连的三座石拱桥,创建于明代永乐年间。传说奈何桥为亡魂去地府时必经之桥,桥分金路、银路、奈何路,善人亡魂会平安地从金银路上过去,而恶人亡魂过奈何路时常被打下血河受苦受难。
这鬼文化说到底也是道教与佛教还有一些民间原始教的杂糅,中心意思是劝人为善。
我们也从奈何桥上走了过去。回想李白题诗“下笑世上士,沉魂此丰都”,这句话似有些玩世不恭的味道,能写下这种话的人,都是自认为能超越生死的人。不然,他怎么能口出狂言“下笑”世上所有人呢?
山上游客稀稀疏疏,石阶由刚才的蜿蜒曲折,变得直上直下,宽阔得多了。如果是一个人登山,难免有些阴森森的感觉。当到了一个有大理石栏杆的山崖旁,我和阎先生站在那里,凭栏而望长江,长江显得很遥远,好似一条明亮的带子,飘落在山谷之中。突然凉风飕飕,顿觉心旷神怡。从此,越往上走,越觉得天地开阔,心神俱爽,并且那个可以俯视江水的栏杆处好像就是人间与仙境的界限。大文豪苏轼有诗:
平都天下古名山,自信山中岁月闲。
午梦任随鸠唤觉,早朝又听鹿催班。
住在这样的地方,又怎能不有成仙得道的感觉。阎先生们开始兴致沓来,边走边指点许多书法碑刻。我也是祖国书法的酷好者,有阎先生这样的良师,又是乡党,操同样的口音,此时此刻我已经非常知足了。不知不觉中,已到了阎罗殿。这也是名山的绝顶之处。
阎罗大殿的正南面,是凌虚阁,又名二仙阁,这二仙肯定是指王方平、阴长生二位了。这里也一定是这二位仙人下棋的地方了。据载此楼修建于明正德十三年,为名山绝顶最高也最为壮丽的建筑。阁的顶层有人书写三个大字“凌虚阁”,书法朴茂厚重,题款看不清,不知出于何人之手。
只见上面宝座上塑着一位帝王,头戴五彩鎏金的盘龙冕旒,身着九龙戏珠的金丝衮袍,面慈神严,五柳胡须飘胸,两边分立文臣武将。这一定是阎王爷了。在这样一个朝堂之上,有很多礼仪,也颇能看出许多传统的演变。
当我们退出大殿时,阎先生说:“这阎王爷是我的本家了,我将女儿拜托给他,有他照顾,我就放心了。”唉,有阎先生这句话,我们不枉来此一趟。此时此刻,我也为阎先生感到一些欣慰,人在许多事情上的顾虑不就是一念之差吗,一个念头可以使人解脱,一个念头也可以使人沉沦。又沿着大殿,我和阎先生盘桓了好久好久。
我们返身下山,走下奈何桥时,阎先生和我都感到非常的轻松和畅快。在阴间世界走了一场,使我们在阳间的生命得到了丰富与充实,使我切实感觉到活着的虚无与真实。这样一个都城,又是有着悠久历史的都城,在现实世界是绝无仅有、独一无二的。
几千年来的中国,极盛时期的首都几乎都是建立在黄河流域。黄河成了封建统治的象征。不知是从什么时候起,长江上却出现了一个这样的都城——阴间世界的首都。
这是长江与黄河的又一种对话。
六
三峡这段长江,也是历代文人活动颇为频繁的地方。屈子毋庸多言,唐以后诗歌历史上两位巨星杜甫和李白,都曾奔波于这一带。还有流落在三峡乃至整个长江流域的文人之多更是数不胜数。那长江中的每一滴水、每一个浪花怎能说不是文人笔下的每一个文字、每一句诗呢?长江是那样的阴郁而多情,长江又是那样的绵长与宽广。长江两岸的每一寸土地上,都遗留下被黄河所放逐的才子们发出的哀怨与倾诉。是长江,使他们的心情得以宽慰。是长江,让他们的生命得以延续。也是长江,使中国的文化与精神得以繁荣与升扬。长江哺育着多少生命,长江又传下了多少文化。甚至在现代中国,长江终于走在了黄河的前列,其流域成了富甲天下的鱼米之乡。黄河——我们的母亲,已显得古老、沉重、贫瘠,长江方显得年轻、秀丽、丰腴。
从重庆朝天门的码头上岸,整个三峡的观光已算结束,虽然我越来越思念那苍老而浑浊的黄河,同时也开始恋恋不舍这滚滚不尽的长江。
长江是一本读不完的天书,是一卷漫长的诗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