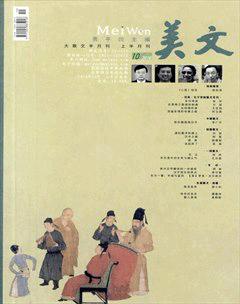摇到外婆桥
陈沭彤
快到七月了。
七月初一,是外婆的祭日。
一
我一直把外婆叫作“奶奶”,奶奶也叫作“奶奶”。两个老奶奶,都很老很老了。
我想起去年春夏的事情。清明,外婆的病犯了,家人急急忙忙把她送到老家。从三月份的桃花初绽,到五月份院子里的李子树挂果,再到六月份屋前的鸭梨沉甸甸地随风摇晃,我每周回去一次看她。星期六下午四点钟放学,五点钟出发,六点钟到,九点钟走,十点钟回家。只有在暑假里,我才陪了外婆一个星期。
只有一个星期。也幸好有一个星期。
二
六月份的时候,乡下的早晨依然很冷。早上十点之后,气温就开始升高。我搬个小板凳到上屋门前的台阶上,给奶奶放把小椅子,两个人晒太阳。早上奶奶给我添的棉褂这时候也不得不解开扣子。太阳光照在身上,痒酥酥的,像一片轻飘飘的羽毛在挠痒痒,是一种充满生机和希望的感觉。而这时候,奶奶却不像盛夏的世界一样生命力旺盛,她瘦极了,但精神意外地好。我不知道,也不敢想到那个词语,我只希望她的身体真的一天天在好转,还能回到县城的楼上去,还能等我放学后来看她,还能和我开玩笑,聊天,和我一起看电视,吃东西。
奶奶给我讲她年轻时候的故事。她是年轻的母亲,她养育着小儿,侍奉着丈夫,她有朋友,有姊妹,有妈妈。她年轻力壮,不知疲倦,她纺线、下田、做饭、缝衣,她就像宇宙中的太阳,源源不断地贡献着光和热。
我喜欢这个时候。外婆的话总是叫我想起青春。听一位白发绮丽的老婆婆讲青春的故事,叫人又伤感又欢喜,五味杂陈。
三
更多的时候,外婆会沉沉地睡去。我为她拉好被子,一个人悄悄地坐在台阶上。
这儿的天特别蓝。由于老屋建在半山腰上,我坐在院子里,一抬头就能看见土坡。屋后面坡上的那棵老树几乎就是从屋顶的高度开始长,盘虬的根有一部分裸露在外,繁茂的枝叶像华盖一样在院子里投下一片荫蔽。天和云仿佛触手可及,碧蓝的天,大朵大朵银亮的、边缘分明的浮云,看得人如痴如醉。在完整的苍穹之下,光和影折射于屋顶的黑瓦,微风吹过,纤弱的瓦菲瑟瑟摇曳。
我往头上扣一个草帽,伏在椅子上写作业。抄笔记,填词语,偶尔读一两行书。他们去田里了,整个村庄一片寂静。能听见虫子伏在草丛里嗡嗡闹着,雀儿活泼地啾啾,有时候也会安静下来,停在树梢上张望两下,忽然就飞得不见踪迹。
乡村下雨的时候,好像一直在奏一首忧伤的钢琴曲。很静很静,平时的雀子呀,虫儿呀,全都销声匿迹,整座山,整洼村,整个世界都是静寂的,只留下耳边空响着雨声,水声。我蜷在我的椅子里,看着细细的透明的水柱顺着对面屋檐的斜度从瓦缝流下来,也顺着我头顶的屋檐流下来,在我眼前挂上了两道珠帘。地上的水花溅起一朵,又凋零,再开一朵,又瞬间和四周化为一体,直到眼前全是重重叠叠的影子。
四
雨后的第二天,天晴得很好。地是黝黑的,踩上去已经半干了,但仍然有点儿软,很有弹性。院子里舅妈随手栽的一溜儿洋八瓣子花水灵灵的艳。我掐下一朵,留着长长的、细细的、毛茸茸的茎递给外婆。她瘪着嘴,笑眯眯地说:“这个是洋八片呀……你数,真有八个花瓣……”我并不回答,只是无限留恋地看着她雪白的头发。我帮她梳头,当年极浓密的头发现在只剩下一小把,攥在手里,盘成一个小小的髻。
“你这样子梳,睡觉会硌得头痛嘛,我自己来……”她像个小孩子一样嚷嚷,我笑了,把梳子给她。
一转头,刚好瞥见窗台上的空花盆。我很着急,问舅妈:“花呢?”舅妈从厨房里探出半个身子,用围裙擦擦手:“死了,你大姨上个月拿来时还好好的,说你奶奶爱花,可养不活……”那是一盆杏黄的海棠,我见过的。我不再追问,只是让目光逃避了那个空落落的花盆。
阳光真好,我拉过外婆的手,那双手干燥而清凉,能摸到突起的指骨。
五
外婆记不清她是在县城,还是回到了她生活了一辈子的乡村。
“小繁啊,你咋不来看我呢?这都几星期了,我天天盼你来呢。”
“小繁啊,你现在上学忙着呢,咱这山路不好走,你就不用每周来了,闲了再来嘛。”
“咱这是在县城,还是在家里啊?”外婆迷惑地问我,打量着四周,潜意识里,她仍然把这儿称为“家”。
外婆一直在急着找女儿,即使大姨和妈就坐在床边。她狐疑地盯着鬓上已生华发的大姨和妈妈,会不会想——
她们是我的女儿吗?我的女儿不是还很小很小吗?
后来读龙应台的散文集,她说:“妈妈是那个搭了‘时光机器’来到这里但是再也找不到回程车的旅人。”
我看到这儿,泪水盈眶。外婆也是那样的人,只是她身边的人早已忘记了她的故事。穿越时光的幸福,很难把它抓住。
幸好,我们现在的时光列车还没有到站,请牢牢抓住身边那双手。
错过了就回不来了。
六
一天,我掏出钥匙开了门,边换鞋边喊:“妈!”这时候,伯伯家的表姐从厨房里走了出来,身上系着妈不常系的围裙。她手忙脚乱地说:“小繁,放学啦?你爸和你妈回老家看你奶奶去了,我给你做饭。”
外婆的病又发作了吗?我赶快给妈打电话:“妈,奶奶现在好点儿了吗?”
电话那头已是泣不成声,一声一声全是哽咽。
我挂了电话,想起三个月前的场景。我说:“奶奶,我还没去过咱们的园子呢,咱俩慢慢走吧。”外婆扶着我,我们到田里去,我第一次见到黄澄澄的南瓜结在藤上,香菜开着白色的婉约的小碎花,一丛一丛金冠花泼泼辣辣,花瓣儿像红绒布裙子的滚边。
我随手捋了一把,扎了一个小花束,坐在菜园埂子上的一排桃树底下玩。我把淡粉的桃花瓣摘下来,取下袖套装了满满一兜儿给外婆看。外婆看着花儿说,它在梢上长得好好的,摘了多可惜。彼时,我又怎听出那话里满含着对生的渴望?
七
看着外婆下葬后,爸爸带我先离开故乡。
或许以后再也不会回来了。
天阴沉沉的,早上刚下过雨,像悲悲切切的哭泣一样。我安慰过眼睛红肿的妈妈后上了车。车开在盘山公路上,云雾掩映住了山头。我从窗子里寻找那座小院,车一拐弯,一道山梁挡住了视线,山坳里的那片小村落终于不见了。
模模糊糊中,我好像又看见漫山遍野的山桃花开了,绯红的轻云连成一片,不知哪棵树底下坐着一位老奶奶,正望着桃花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