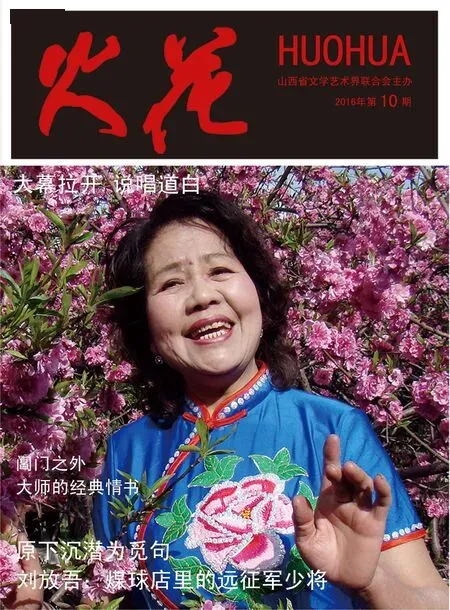密密的青瓦院落
黄绍祝
密密的青瓦院落
黄绍祝

一
这儿其实是靠近大山的山间谷地,那片密密的院子,在这个村的中间,马鞍山的浅丘坡在背后斜下来,有些微高低的起伏,形成一片较平坦的坝子。门前是条小河,有几个山湾,水都流到小河去了,小河拐了几个弯,又顺着山势流走了。河对岸也是片开阔地,是另一个村,叫林头。再远处是高山。有山有水,风水不错。院子是个巨大的院子,由一个家族的几弟兄共同修成,他们都曾是这里有名的大地主,土改时有的被镇压了,有的被迁到了外地。
那院子有九个天井,院坝都用石板做成,柱、梁、檩都是很大的柏木,院中有院,楼上有楼,整幢院子,依着地势的起伏,屋顶始终是平的。院子占据了村子最好的风水和土地,现在被十多户人家住着。
院子的一部分成了小学校和大队办公地。正中的院子里辟出了代销点、医疗点。还有几间成了公办老师的宿舍。代销点在很深的门里,进去先有排凳子,闻到酱油和醋的味道。一排横柜台,里边一排货架,跟街上的一样,只是东西少很多。但油盐酱醋还是有的,水果糖也有,酒有几瓶。
管代销点的叫董友元,他很年轻,三十刚出头,高个子,有些胡子。没事他总在中间的大院子里抱着膀子踱来踱去,或是在青瓦院子里看天,看代课教师在门里进出,听隔壁娃儿们的读书声,和院子里的住家户、隔壁的医疗点打着招呼。有两家住家户的男人在县上区上当干部,董友元很注意对他们的家属客气。
他似乎没什么事。门前最热闹的当然是下课后,娃儿们涌过来,但他们都很穷,不大买东西,一分钱的水果糖也不怎么有人买。所以董友元也不大理小娃儿。最多的是有人来打酱油和醋,那时董友元就慢条斯理地走进里间,也是黑着脸。
大队强主任没事会在那里出现,和他们说笑。
“有好东西没有,搞点给大队会上用?”强主任问。
“没得了呢,有瓶高粱酒,刚刚叫二队的人买走了。”董友元一本正经。
“狗日的,我还不晓得你?”强主任笑着,摸透他的样子。
“真的呢,是真的,哪个哄你做啥嘛?”董友元还绷着劲。
强主任就转过去和医疗点的医生,和刚好下了课的代课教师打招呼,不理他。
“呵,给你留着呢!”董友元突然从柜子底下拿出来酒,他笑了。
他笑起来没绷着脸好看,有些让人不习惯。
大队办公地其实不在院子里,而在院后的礼堂里。但大队几个支委和主任都常来这边,或者是代销点看看,或者和医生打招呼。除强主任外,另有个副主任,叫马恒文,和董友元家离得不远,但这人比较肉,说话半天说不到点子上,董友元有些看他不大起,觉得自己迟早要把马恒文的位置替了。另外一个叫春官,是刚从队长当上来,文书是河嘴上院子里的,不大说话,算盘打得好,好像不大理人的样子;出纳也是这院子里的,却不大露面。
强主任高个子,瘦削,一向在村民中有威信,没有偏私,说理明明白白,谁都服气,平素能让着老人、孩子,所以他一来,都要打个招呼:强主任来了?来了。最不听话的人也服他。他有时爱说笑,但脸要一黑,却很威严。
医生有两个,一个是老医生,远近有名的薛医生,叫薛明懿,是河对面的,另一个是本村的赤脚医生,叫何成建。这人年轻,小脸,笑眯眯的。薛明懿很和善,他的儿科远近闻名,小孩儿们念不清,把他叫成薛明明,他也不恼。他是这四乡八里的名人,有孩子的都知道他。他要把脉,要听诊,把一个听诊器挂在耳朵上,侧歪着头很认真地听。他微胖,头发苍白,笑咪咪的样子,走路略有些气喘。
薛医生一般是回河对面去住,每天下午走,早上来,穿过门前的坡,下过苦河,也就半小时里程。院子里也有间他的房子,他也可以不走,但弄饭就麻烦一点,要么和代销点接灶,要么和公办教师搭伙。他没回去的时候,早上院子里人看到他,都打个招呼:
“薛老师,吃了啵?”
“吃了吃了。”老头笑容可掬的样子,走路有些累。
薛医生医术好,尤其是治小孩子的病,大家都尊敬他。
院子里有两个年轻人有点意思:一个是毛娃子,一个是康林。毛娃子的父亲是个地主,他和他爸两个人过,有时候我们喊地主儿子,他就很不高兴。他不大说话,有时和年轻人在一起,大家也不觉得他有什么不一样。康林就不一样了,他并不是地主,有时却要骂干部,说是“污心子干部”,队上人也懒得理他,说他脑壳有问题。
院子两边不远,还是两个院子:新房子,河嘴上。新房子是相对于九个天井的院落子说的,河嘴上是苦河转弯的地方。新房子住了些土改迁来的外地户,有三户姓谢。河嘴上人家稠密,是另一个聚居区。三个院子都离得很近。新开的机耕道通到河嘴上,手扶式拖拉机突突突地开过去。
这三个院子,就成了这个大队最集中的地方,最热闹的所在。
热闹的是开大会,或者是放电影。大会其实很久不开了,开会的位置在大院子背后新修的礼堂,那是新修的一杆子敞房,九间开,每开间的柱子是条子石的,顶着木过梁。最头上是主席台。村民印象最深的是毛主席去世,台上堆满了白花,下边的人哇哇大哭,但那是好多年前的事了。现在更多的是些孩子在门口的坝子里走操,脸上挂着汗。电影队不常来,来了就在门上把柴油发电机拉得轰轰轰地响。
后来通电了,有人买了电视,要卖票。涌了很多人,看《霍元甲》,接着是《陈真》。连续有很多家买了电视机,想起他家还卖票,不屑地说,他家那屁电视,看都看不大清,尽是麻子点点,还要五分钱一个人。这是后来的事。
院子里一个叫香女子的,已经在谈婆家了。有年清水河发大水,她和对象去上街,河水已经漫过了平桥,人们还在趟着水过,她对象说拉上,她不好意思,结果没踩稳,掉河里叫水冲走,淹死了。另外,毛娃子找大队闹过,说大院子有一大半是他家的房子,连四人帮都抓了,该还他们房产了,被一顿臭骂,也被大家笑了好久。再有就是有年五保户死了,在河嘴上公房里,杀了头不生崽的母猪,宴席摆了一院坝……
鸡叫了,狗也叫了。午饭的炊烟升起来了,一家接一家。
一切是那么宁静。

二
隔壁的小院子里,五年级的学生在大声朗诵课文,他们在读“1947年1月12日,天阴沉沉的,寒风吹到脸上像刀割一样。国民党反动派的军队包围了云周西村……”,声音断断续续传来。他们的墙上,原来的老师在“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之外又写了道勉励的标语:
学习学习在学习
努力努力在努力
当初写好这道标语时,他还立在对面,脑袋歪过来歪过去地满意了小半天。那是个老初小毕业生,叫张生,因村上确实没人,才当了民办教师。后来这标语却被一个高中毕业的代课老师嘲笑了一通,说“再”“在”都分不清,还教什么学生。
张生也曾站在院里高高的台阶上,凭他认字认半边的经验,大声地把“瀑布”念成“暴布”。
他不懂拼音,就常和另一个女民办教师走得近,他想去问那些字怎么读,结果院子里传成了他们在一起说笑,关系暧昧,小学生们看他们的眼光都变了。
张生念“暴布”时,雍老师也在边上,不好意思笑他,后来张生知道该念作瀑布,就在课堂上说,这个字也念作“暴”,以前我们念书时先生就是这么念的,这是个多音字。学生们也就信了。
小院子里以前有个地主的小老婆吵架吊死了。我们看到那很大的梁,总想象那女的吐着舌头的样子,其实那女的当然不可能吊在那么大的梁上。那楼上倒是真有一个孩子摔下来过,那是公办老师雍老师的孩子。雍老师是这里唯一的公办老师,她住的一间屋子用白纸糊了,放些新崭崭的瓷盆、搪瓷水杯、毛巾之类。雍老师不高,她的班里总是传出歌声,让其他班的孩子们心生羡慕:要是在雍老师班上读书就好了。
学校有五个班,老师们带着娃儿在门前的坝子里跳、闹、排队放学,小坝子边上长了竹子,有棵榆树,每年落下的花儿,叫做榆钱,这是这边不多的一种树。这边多的树是柏树、柳树,还有桤木树。猪狗也在操场边上跑,邻居一个老太婆常在那里骂他的小孙子,其他人端着饭碗,稀饭喝出声响,新泡的水萝卜透着红,咬出脆脆的声音。
学校里还有劳动课,老师们会带上孩子们去公房前不远处的一块地里锄草、收麦,然后在六一节前,把麦子磨成面,蒸成馍馍,里边放了糖精,很甜。每个孩子一个,这是他们在家也难得吃到的美食,孩子们在老师的带领下,走过田埂,去半山腰上的公社过儿童节。
代课教师、民办教师们都回去住。
学生和老师都走后,雍老师就在小院子的天井里淘菜、漱口。她的盆子、碗、杯子,和村里人都不一样。她用的都是搪瓷的,雪白。
她漱口时孩子们会看一下,跑来跑去。他们没见过,久了也就习惯了。
雍老师的儿子在她身边,在小天井里站着,在折纸飞机。这是个滋润的孩子,脸上、身上都长得滋润,和这里的其他孩子不大一样。他身上穿的是干净的衣衫,冬天就戴一顶买的皮帽子,那样式这里的孩子没见过。
这孩子从楼上摔下来,把雍老师吓坏了,送到区卫生院去,居然没大事。真是命大。
摔下来后,雍老师就不敢让孩子在这边了,把他送回了老家。雍老师虽然是公办老师,但她的老家这边人都知道,在百顷街边,叫雍家碥。
下雨天,我们散了学,就到不远的新房子院子里的一家看小人书,那家老太爷有很多本《三国演义》的图画书,但他不轻易拿出来。他们家里的桌子、柜子上都叫漆匠描了画,是些花啊松柏的。他高高的个子,站在宽大明亮的屋子里,说要考考我们,三国里谁的武艺最高,哪个杀了颜良文丑。我们都答对,我还说了水淹七军,讲了长坂坡,老太爷笑眯眯地挪动瘦高的身子,去柜子里给我们拿图书。我们津津有味地看着。
门前的水沟里,也涨了很多的水,水一过,那些芦苇怕要露出白白的根吧,那些奇怪的小小的绵竹怕又要被人寻去当药引吧,谢家的几个儿子女儿怕又要拿起篓笆去捞鱼吧,他们高高地挽着裤脚,在石头上蹦来蹦去,一只手去扶着头上的雨帽,然后那风终于把他们的帽子要吹落了,但他们也顾不上管,在高声大叫,“捉到了,捉到了,嘿,好大一条红嘴鲤鱼!”
看完图书,走过田埂,我们会看到沟里水在流淌,隔壁那个叫史有金的石匠正在打石头,他扬起的小锤,一下,一下,传来叮叮当当的声音,他家那个儿子,正在阶沿上走过,在竹林外……
三
院子的左边新开了家代销店,是私人开的,说是要和大队上的竞争。他家门上画了只老虎,是河嘴上一个年轻人画的,他立志要当画家。他常过来,高大、帅气,进出的时候,吸引很多人的目光,特别是年轻女孩子。他进去,又出来。
年轻人们在对门的晒坪里立了架转转秋(一种秋千),和平常挂在房梁上的秋千不一样,是立在地上,架一根木头,用人推,或者是自己用脚支了跑,然后就转起来,坐很多人,女娃儿们衣裳的色彩艳丽,在风中飘得呼呼响,她们哈哈大笑,老远都听得到。有些年龄大点的人看不大惯了,未免说些闲话,但一是年轻人多,根本不管他们的,二则他们慢慢也觉得那转转秋有意思,自己也跑过去坐了。
这院子里住了两家干部家属,这让这院子与其它地方不同一些,每到年节,在外的子女回来,一大家人走过田埂去祖坟上烧纸,带回些新鲜话题见识。这院子有几个姓,也因此显得较为开放。
还是宁静。
不久,却出了件事。
石匠史有金,忽然闹起了离婚。离婚这事不多见,这湾里多年来是娶了嫁了,都是一辈子到老,离婚?连这词儿都觉别扭。离了倒也罢了,这家伙还死活要和河嘴上一个按辈份是他婆婆的女人在一起过,而那女的,也有一大家人,有三个女儿。
这事闹得乌烟瘴气。这村子里就没有听过这样的事,这里大部分人是一个姓,他们族谱上都有着共同的祖先,因而辈份是看得很重的,同一个姓都不能开亲,何况孙子要和奶奶结婚呢,这不乱了套了!
所以说起这事,都感到很不自在,很震惊。
那家的男人始终不发一言,其实那家的男人也是一个石匠,也打得石碑,錾得字,能打石磨,磉礅,还能在碓窝上雕出桃花、莲花(这种花这里没有种过,很少有人见过),这比史有金都要强。而且他们三个女儿都很好看。以前,我们看到他们两口子在田里薅秧,很恩爱的样子,他们怎么会离婚呢?
那女人的三个女儿一个比一个好看,二女儿叫春燕,正读到小学三年级,是我们的同班。春燕聪明,当了副班长,戴个红领巾,穿着新布鞋,布鞋的样子很好看,开口特别乖巧,显得她特别修长。她妈的手艺一定很灵巧。
春燕是班上的乖乖女,白,眉眼传神,系着长发在土场上跳绳,总有些看不起人的样子。她家就住在靠近苦河的院子里,后来自家在对河的地方修了房子,房后有很多坟。他们家三个女儿都明丽动人,他们咋选在那么多古坟的地方呢,我们看到他们的房子,就想到他们家漂亮的女儿。
有回我看到春燕她们几个女孩儿在跳房子(一种游戏,即跳方格),过去打扰,春燕理都不理我,却被另一个女孩子追,用瓦块打了后脑勺,还出了血,在薛医生那里贴了一块白布,很不好意思了几天。
这下,春燕该没那么神气了吧。
果然,她似乎有些蔫。
后来,为一件事,我和春燕吵上了架,“你妈,离婚,和别人!”我终于狠狠地说。
话还没说完,春燕似乎已经哭起来了,我们不敢再说下去。春燕把花布书包抹到前头,垫在桌沿,自己伏在桌上抽泣起来,身子一下一下地动。
春燕哭起来都那么好看,让人心疼。
四
大家觉得是不是还是该管一下,推强主任去教育一下史有金,这家伙闹得太不像话了。强主任也觉得该管一管那个家伙了,但他一开始却在推说,这些事,怕不好管啊,法律上也没禁止。最后还是觉得该去说说他,无论是从辈份(强主任的辈份,史有金得叫祖祖,就是曾祖父),还是作为村主任的份上。
“我不怕,我去百顷街上问了人家,说我们这个不违法。”不想史有金一口就回绝了,他振振有词。
强主任有些悻悻。这个狗日的,看来是谁的账也不买了。
史有金就在我们看图书的那个院子里,大家习惯叫油房头。他在边上,几间瓦房,很整齐,他也会石匠,长得端正。他的女人瘦,但白,长得也挺有几分姿色,梳两个辫子。他有两个女儿,一个儿子。女儿长得还好看,虽然比不上春燕。
史有金,你个狗日的,你也太不道德了嘛,和你婆婆搞到了一起。
她不是我婆婆。只是辈份上是。
辈份上是就是!强主任吓他。
再说了,你也不想想看,这么大一个院子,你以后把脸往哪儿搁?
我不怕球,史有金说,我怕啥子。
确实,这个长相敦笃、五官有神的男人,有的是力气,他会木匠,也会点石匠。他的庄稼,也种得很好,大太阳天里,都看到他在玉米地里锄草。
哟,年成可以嘛,强主任看到他屋檐下挂的腊肉。
可以,他说,现在饭都可以吃得饱了,肉也有得吃。
狗日的,啥时搞到一起的?强主任黑着脸,吓他。
你管球我的。史有金说。
狗日的,叫民兵把你绑了。
凭啥子绑我,我又没犯法。
你闹得四邻不安,就是犯法。
你吓不到我,史有金说,我去问了,他们说这个不犯法。
你娃儿都那么大了,你女人长得还可以,也没做啥子对不起你的事,你狗日的一天在跳啥子跳,跳得四邻不安的。
史有金说了句话,让强主任愣了半天,不好开腔。他说,这世上,女人和女人是不一样的。
强主任呆了半晌,然后咽了咽口水,转身就走。史有金给他散烟,他也没有接。
跟他谈了几回,强主任反而有些喜欢史有金了,他以前就和这个家伙熟悉,知道他其实是一个能干的人,只是没想到这家伙这么固执,这么天不怕地不怕的。
强主任回到大队部,装着没事人一样,其他人都很期待的样子,看着强主任走来走去,就是不发话,张生有些待不住了,他说,强主任,到底咋个的,你不要卖关子了嘿。强主任看看他们,有些似笑非笑的样子,在桌子边坐下来,拿根烟在手上,说:
“咋个?这些是人家自己的事,人家又没犯法,管那么多做啥子。”
这太出乎意料了,村里的人面面相觑,原都指望强主任说出些什么指示性的话来的。
“这个狗日,要收拾他。”董友元还恨恨不平地说。
“为啥子收拾他?”强主任问。
“他狗日的欺负我们董家的人。”董友元说。确实,春燕的爸原是上门女婿,本是董家湾人,原名叫董虎员,和董友元是一辈。
“看球你的!”强主任说,“人家董虎员都没想要收拾,把你急的!他史有金不犯法,你这一去收拾,你就犯了法哦。”
董友元有些悻悻,其实他也只是发泄一下心头之火罢了。再说大队不出面,他也怀疑自己单薄的身子是不是牛一样的史有金的对手。
他黑上了脸。
法?法不管这个?
“法”这个词儿听起来挺生,挺拗口,都觉得很陌生,关键是,法咋会不管这个呢?婆婆和孙子都搞在一起了,法却不管?村里人其实很震惊。
史有金这个家伙又臭又硬,就像毛厕里的石头,他是不是疯了,自己有三个儿女,人家也有三个女儿,都三十多的人了,要搞得那么嚎声波气。
还有的人干脆说,“你两个要相好嘛,阴着好就是了嘛,这些偷鸡摸狗的事也不是没得,两家也睁只眼闭只眼算了,两个人非要死了活了在一起。看弄得,两边娃儿受苦啵。”
确实,这两个人,都不是什么坏人,特别是春燕的妈,平时看上去蛮温和,从不和人争吵的,这是怎么了?到底是什么力量让他们非要在村子里弄得风生水起,不顾一切地要到一起?
村子里都在沉思,陷入了震惊之中。

事情慢慢过去。后来,总还有人要说起,大家都难免愤愤。说真是不叫话,婆婆和孙子搞在了一起,不晓得咋个想的。
薛医生在一边笑眯眯地听着,有些打瞌睡的样子,他突然冒出一句:
“他们,那是火重,内分泌失去平衡。”“火重了总要出!”他又补充道。
现在的事,不好说哦。
大家就微笑。
五
后来我们走过那些田埂,看到史有金,和那个女人在一个秧田里薅秧,很协作的样子。又看到他们在坡地里除草,戴着草帽。
下雨天,我们还去老太爷那里借看三国图书,隔壁的五年级学生还在读课文。
一切如旧,又平静下来,但走过的人都感到,那些密密的青瓦院落,似乎哪里出现了一些裂痕。
(插图:佚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