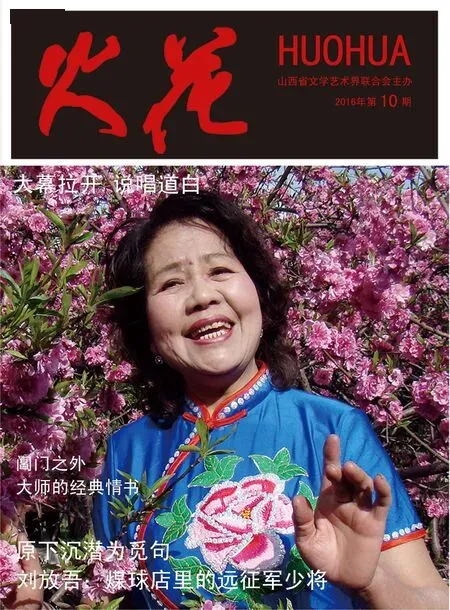人物三题
孙荔
人物三题
孙荔
豆腐西施阿布
阿布会做豆腐,因为阿布的爹就会做豆腐。方圆几十里的人家,都吃过阿布爹做的豆腐,那叫有吃头,嫩而不老,老中含着嫩,炖而香软,炒而不碎。所以阿布家的豆腐坊生意红得像火一样,做多少卖多少,从来不剩下。
阿布闲来无事的日子,喜欢看爹怎样做豆腐,豆粒变成豆腐需要一个过程,就像她的意中人小木匠成为她的意中人,因为有青梅竹马这个过程。再说小木匠的手艺也不差,锛、抡斧、打线、开料、抛光、接榫、上漆,小木匠做得一板一眼,一点也不松懈,小木匠立志要成为一名优秀的木匠。这让阿布笑成一朵花,因为这样小木匠将来养家就没问题了。
木匠是力气活儿,所以小木匠练得虎背熊腰,很健壮,是一名英俊的小伙子。每次出门师傅总叮嘱小木匠,在大户人家做木工,要少与人搭腔,尤其是那二姨太的、三姨太的,这号人物,身上有妖气,挨碰不得,否则,丢了饭碗事小,掉了脑袋连自己都不知怎么回事。于是小木匠变得很木讷,像一根木头,但他心里住着阿布,这就足够了。
阿布有时随爹一起去走街穿巷卖豆腐,阿布是伶俐的,父亲切豆腐放在称盘里,几斤几两,阿布乌黑的眼珠一转,很快钱算出来了。阿布算帐很灵光,阿布爹自叹自己老了,脑子里没油转得慢了,还常常搞错。吴家大院的吴老爷的儿子吴家宝看上了阿布,阿布的皮肤像豆腐似的嫩白,再加一双好看的黑眼珠,美得让人忍不住回头多看两眼。
吴家大院购买豆腐本来是厨房王妈的事,但是吴家宝自动揽下了,吴家宝装作很内行地对王妈说,我知谁家的豆腐好。王妈很得体地夸赞吴少爷是个心细的男人。吴家宝在街头远远地看到阿布和她爹一路走来,刚把车子放稳,吴家宝就很豪气地说,来五斤豆腐。阿布眼皮也不抬,随手一称,五斤豆腐正好。第二天,吴家宝又很豪气地说,来五斤豆腐。阿布依然眼皮也不抬,上称,收钱,一切行云流水。就这样阿布认识了“来五斤豆腐”的吴家宝。
有一天,阿布说话了,对着吴家宝,说你家天天吃豆腐,不怕有一天吃坏掉胃口。吴家宝说,这要看谁家的豆腐,一流的豆腐怎么会吃坏掉胃口呢。阿布笑了,吴家宝也笑了。吴家宝是一个很文雅的男人,他有两个漂亮的姨太太,一个漂亮得像牡丹花,一个漂亮得像梅花,吴家宝天天在牡丹花和梅花之间转悠,总觉得她们缺少一种东西。
阿布怎么也没想到,自己有一天被铜罗寨的陈三炮绑上山了,陈三炮是个脑门上有道疤,悍气十足匪气十足的土匪,那派头不由让人想像他的前世一定是一只狮子,一只凶猛的狮子。陈三炮朝山下放话,说一个月内不拿三百块大洋来赎,就撕票。陈三炮狡黠地笑,心里想,老子怎么会撕票呢,老子不傻,这么漂亮的妞儿,又做得一手好豆腐,藏在山上天天给我做豆腐吃,岂不是很好吗?
阿布爹急得像火烧一样,他跑到小木匠家,说你想想办法,那可是你未婚的媳妇。小木匠恨得咬牙切齿,拳头抡得像铁锤一样。阿布爹怯怯地说,我们万不可拿鸡蛋去碰石头,我们只能想办法凑够三百大洋。三百大洋,小木匠一听,表情像个泄气的皮球。
三天之后阿布却从山上回来了,像是去山上逛了一次集市,吴家宝三天之内就把她赎回来了。这令陈三炮感到意外,陈三炮想阿布爹肯定没那么多钱,至少可以在土匪窝做一个月的美味豆腐吃。陈三炮刚吃上这有嚼头的豆腐没三天,就让吴家宝搅混了。但陈三炮想,不过老子也够本,轻松搞定三百大洋。
阿布说,吴少爷,你为什么赎我回来,我可与你没什么关系!吴家宝说,怎么没关系,我第一次买你爹做的豆腐就有关系了,你爹身边站着一棵野生山茶花,第一眼我就看上了,我家缺少一棵山茶花,你愿不愿意做我的三姨太。阿布笑了,又慢慢地收住笑容,说我可不想做你的三姨太,我只想过清静的日子,我开我的豆腐坊完全可以养活我自己。

阿布又爽气地说,吴少爷,你放心,钱我会慢慢还给你的,我会天天给你吴家送豆腐吃。吴三宝一脸苦涩,说姑奶奶,就是我家的看门狗看见豆腐都闻也不闻了,都是我的不好,我为了讨你欢心,才每天买五斤豆腐,后来的都在我家变成臭豆腐了。阿布噗嗤一声笑了。
阿布回来,小木匠却忧心忡忡,小木匠说,土匪陈三炮没碰你吧?阿布说,没碰我,只是让我做豆腐。小木匠还是满脸疑云,这让阿布很不是滋味。阿布说,你要让我怎么解释你才放心。小木匠不说话,拿眼怔怔地看着阿布,又沉默成一根木头。阿布忽然不怎么喜欢小木匠了,小木匠不太像个男人,至少不像她心目中的男人。
没过多久,阿布又被土匪陈三炮带到山上,不过这次是请,不是绑。陈三炮说话很客气,说阿布,我又想念你做的豆腐了,这口味是别的豆腐坊做不到的,你可不可以教教山上的弟兄。阿布说,我家做豆腐的秘方是祖上传下来的,不可以传给外人,这是祖规。陈三炮说,那你就在山上做几天豆腐吧,让弟兄们过过瘾。陈三炮一脸赖皮地笑,说,我会请你喝花雕,上等的花雕。
阿布说,看你的面子,我就在山上做三天豆腐吧,做完我就下山。我不喝酒的,不管什么花雕不花雕的,我不懂酒。陈三炮说,你不懂酒,应该懂人吧,你走了之后,我心里空荡荡的,呆在这寨上多好,空气新鲜,我还会打野兔给你吃,说完陈三炮眼里有着盈盈的水意。阿布说,你这里不就是个土匪窝吗?陈三炮说,我是义匪。说完,双手一拍,一个精瘦的弟兄送上来一个小包裹,里面有三百大洋,陈三炮说,你还给吴少爷吧。我的本意是请你来山上做豆腐,我在山上转悠时能见到你的身影就满足了。
阿布低下了头,又抬起头说,我爹离不开我的。陈三炮也不难为阿布,说,好,这次就做三天豆腐。阿布忙着往石磨眼里倒进泡好的豆子,磨出浆汁再滤去渣,然后放进大锅里煮滚,翻花后舀进大缸,点上石膏水盖着焖,再揭开就凝成豆腐脑,舀出半缸倒屉层压出薄豆腐,剩下的倒进白布包起来板压成水豆腐。
三天之后,阿布回来,小木匠酸酸地说,那土匪窝快成了你串亲戚的地方了。阿布说,是又怎样,不是又怎样。阿布还了吴少爷三百大洋,吴家宝惊得像只兔子,抓着阿布的手说,你说你怎么这么快搞到三百大洋。阿布说,你可以,我为什么不可以呢?说完转身走了。
日本鬼子像蝗蜂一样横扫同山镇,所过之处,不见人影,小木匠就成了一棵被扫掉的草。这让阿布伤心了很久,她想起他们两小无猜的日子,小木匠说,我背你转圈阿布,扎着小辫子的小阿布趴在小木匠背上闭上眼睛……不一会儿小阿布滑在了地上,咯咯地笑着说,天还在转,地还在转……
陈三炮被新四军收编,摇身成了第十三旅的旅长,阿布也加入了地方游击队,在一次狮子口的战役中,陈三炮杀红了眼,日军像一棵棵树纷纷倒下,最后一声枪响,陈三炮自己也倒在血泊中。阿布跑上来抱着陈三炮说,陈三炮,你不是说让我陪你在山上过日子吗?你醒醒,陈三炮你不醒我怎么陪你,说完满脸炮灰的阿布泪水纵横。
一周后,陈三炮醒来,脸上又多了一道疤。
吹笛手阿昌
沿着胭脂巷走到尽头,往左拐走上十几步就到了雕花戏楼,雕花戏楼建于清咸丰年间。
那时这个镇子是一个码头,时不时的一场微雨,会笼罩住码头,像旧小说里的一个场景,因此这里衍生出一条还算繁华的街,店铺林立,客栈、药铺、布庄、戏楼等应运而生。戏楼是红漆立柱,雕花镂空,叙说着自身的繁华。既然是戏楼,当然少不了美丽的女子,那些女子一举手一投足,有着江南女子的温婉和娇媚,水蛇般的腰段,不知醉了多少客商、老板和观众。
有一天,剧团里的横笛吹手老吴的母亲病重,无奈之下,他只得向戏团班主请假回老家。戏团是少一个角色也不好开演的,这时身着长袍大褂的班主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在台下直转圈,戏要正常开演,少了吹笛手配乐就达不到一定的效果。这时有人推荐附近村里的阿昌,去顶替一下,阿昌那时只有二十来岁,像个文雅的书生,细皮白面,无事时爱在自己木楼上吹笛子,平常不怎么爱与人讲话。那笛声清亮悠扬,如山间泉水汩汩流淌,有时则婉转凄凉,让听的人好不伤感,有时又高亢激越,响彻云霄,让小媳妇小姑娘们心绪久久难以平静。笛声是能摄人心魄的,小姑娘们心里正开着花,在心里多想演绎一场生死相许的爱情。
民国十七年,那场雪下得好凶猛,雕花楼的台上台下都生起了火炉子。戏也正演得如火如荼。《碧玉簪》中玉林唱道:听谯楼已报三更鼓,我玉林洞房花烛小登科。见房中丫环已不在,我不免上前仔细看花容。喔唷,妙呀!果然是天姿国色容颜美,好似嫦娥离月宫……秀英唱道:新房之中冷清清,为何不见新官人?想必他高厅之上伴亲友,想必他到父母堂前去受教训。想必他在筵席之上酒喝醉,想必他身有不爽欠安宁。我左思右想心不宁,耳听得谯楼报四更。
那演秀英的女子真是生得极美,都把村里的小姑娘小媳妇们比下来了,就是有比她漂亮的,但是没有她那气韵。阿昌常常吹着笛子,也忍不住瞟上一眼,满心的爱慕。戏毕,阿昌主动邀请演秀英的女子和她的母亲,一起去他家吃饭。他让母亲把家里正在下蛋的老母鸡杀了,再用上好的腊肉,陈皮黄的肉,很有嚼劲,肥而不腻,散着树木的清香,用心地款待她们。阿昌把鸡肉、腊肉都放在秀英碗里,说你多吃点,唱戏很辛苦,这时阿昌眼神里泛着亮光。阿昌让母亲拿出新的棉被,软软的暖暖的,让秀英娘俩住下来。秀英在那个落雪的冬日睡得很甜,她感谢阿昌家的新棉被,阿昌看着秀英那红润润的脸庞,心酥了,红着脸,低下了头。
天下没有不散的戏,唱了十多天后,剧团要搬往别处。剧团走了,但是阿昌没有能跟着走。阿昌送他们到江边,他望着秀英的影子一点一点消失在江中,直至船影变得模糊,无法看清,回来后,他心里空荡荡的。
日子像风一样掠过,一年一年又一年,雕花楼每年都在演戏,戏班来了一班又一班,独不见秀英那一班剧团,阿昌的心怅怅的。阿昌想,如果那秀英女子再出现在戏台上,是多么激动着他的心,他一定会坚定地走上前去,请求她能为他留下来,至于留下来留不下来,是另一回事,起码他表达过自己的暗慕之心,不会再这样地后悔。
阿昌年龄也大了,到了娶媳妇的年龄。村里阿婆为阿昌做媒,阿昌头摇摇,不说话,以沉默抗拒,再美丽的姑娘,也不前去看一眼。他的心让叫秀英的女子占据了,任何人也住不进去。母亲逼他急了,他就掉眼泪,要不然就去别处躲上几天,无奈的母亲,只有认命了。在母亲咽气的那一天,阿昌仍然一个人过着,母亲带着深深的遗憾走了。
后来阿昌靠村上的红白喜事度日,一根横笛,一曲戏剧,日子倒也过得马马虎虎、逍遥自在,只是阿昌再没有对别的女子动过心。后来阿昌就搬到雕花戏楼去住,他是怀念那叫秀英的女子,这儿曾留过她的影子,顾盼兮兮,眉目传情。
有一天文革开始了,破四旧开始了,带着红袖章的红卫兵趾高气扬地要拆掉戏楼。阿昌愤愤地说,只要我阿昌活一天,戏楼就存一天,拆楼没门。红卫兵们拿他没办法,一个以戏楼为家的单身汉,又能让他去哪儿,古老的戏楼得以保存下来,还要多亏阿昌。
后来村长请阿昌教年轻的女孩后生唱戏,说,没戏的日子过得真是没滋没味。阿昌在雕花戏楼里一句一句教得极认真,包括唱腔、手法和脚步,这时古老落满灰尘的戏楼重新热闹起来了,灰尘在阳光的锋芒中起舞,起舞的还有年轻的男男女女。阿昌的日子除了夜晚,并不冷清。
《碧玉簪》仍在上演,不过剧团的团长是阿昌了,这时《碧玉簪》演秀英的女子叫梅子,梅子一样生得腰姿如水柔软,唇红齿白,妖娆妩媚似江南一朵出水的莲。阿昌常深深地望着,像望着自己一段过往的岁月。不久梅子便与演后生的小哥恋爱,两人台上台下,眉来眼去顾盼生情。不过,阿昌看着很高兴,他不希望他手下的后生,像他这样一生美好的岁月给蹉跎了。
阿昌的剧团办得很红火,那些小女子和后生们已唱得字正腔圆,有板有眼。不久别的村子里陆续也请他们出演,名单排了很长。阿昌一脸的春风,很是得意,他一生总算有得意的地方,没有家庭,但是他有戏班子,戏班子让阿昌忙碌得充实。
一天阿昌和剧团里一位老人走在一个村子里,在村头,阿昌忽然看到一个人,一个女人,一个已经老了的女人,那是当年的秀英。阿昌怔怔地望着,他确认自己没有认错,他眼里的泪花立刻涌出来了。她叫阿眉,当年演秀英的女子其实叫阿眉,阿眉的耳朵有些背了,当年美丽的脸上已爬满了皱纹,当然也多年没有人叫她阿眉,阿眉没有回应。阿昌走上前去说,我是阿昌,阿昌摆出当年吹笛子的动作。可阿眉的眼神仍是木然,像沉睡在一个长长的梦境中,无论她怎样从记忆深处打捞,也打捞不出一个叫阿昌的人。但阿昌仍是激动地望着她,她是阿昌青春岁月里梦了又梦的人啊。
古老沧桑雕花戏楼仍在,只是不堪岁月的重负,通往戏台的木楼梯,已被封死。台上似乎留下了每一个莲花碎步,恍如隔世的戏曲声若有若无地由远处飘过来,游人在触摸一段烟尘,一段历史,用目光细细打量这曾经无尽的繁华,但谁又知繁华背后这一段伤感的爱情故事呢?

棉花匠阿阮
阿阮想学弹棉花,因为弹棉花是一门手艺,手艺靠的是手。阿阮有一双灵巧的手,于是阿阮的手艺学成。
阿阮十七岁就背井离乡出来弹棉花,他一村一村地辗转,肩上挑个担子,一头是大弹弓,另一头是碾饼、弹锤、牵线杆之类的行头,他一路行走,一路京腔式地吆喝:弹——棉花——哟!他到过山东、安徽、云南、贵州等,行迹遍布大半个中国。
有一天他从外地风一程雨一程地赶回家,他赶回来时是夏天,看到了杏花。杏花在院子晾晒湿漉漉的衣服,水滴一滴滴地落下来,这让阿阮心里下了一场雨。因为阿阮的好朋友阿郑,把他的未婚妻杏花变作了自己老婆,这让阿阮的心一抽抽地疼。他想说,阿郑,你真不是个东西,趁我不在的日子,你把杏花哄到手,这叫什么朋友,这叫趁火打劫。
杏花说,阿阮,你回来了,说完眼皮像窗帘一样垂下来了。这时阿郑从堂屋走出来,阿郑阴着脸,说阿阮你回来,是夏天弹棉花没生意了吧?阿阮说,不是夏天没生意,是以后没生意了,现在弹棉花都用机器代替了,我这手艺派不上用场了。阿郑的脸更阴了,说你以后都在家了,不出远门了。
阿郑看了杏花一眼,对着阿阮故作善意地说,你以后到我工厂做工吧,咱俩毕竟是朋友。阿阮看了阿郑一眼笑笑,然后走进夏天的风里,风鼓荡起阿阮白色的衣衫。他眼里的愤怒像夏天的太阳着了火,他对着院子里的枣树说,阿郑你是个小人,阿郑你是个小人,枣树叶子在风中哗哗作响,跟着阿阮说,阿郑你是个小人,你是一个小人。
阿阮白天坐在枣树下喝茶听收音机,晚上坐在床前喝酒听收音机,就这样过了一个夏天。直到秋天像个姑娘,姗姗地走来。阿阮对自己说,我要学一门新的手艺,我要在山里承包一百亩地,种上中草药,种成生态园,春天看花,秋天收草药换作钱。原来整个夏天,阿郑都在收听农业讲座,播音员小霞的声音像晚霞一样的美,阿郑想,小霞一定是个漂亮的姑娘,小霞陪了阿郑整个夏天,不,是小霞的声音。有时阿阮也给小霞打热线电话,咨询有关中草药的种植和有关注意的事项,小霞真是个耐心的姑娘,而且漫长的答复都是免费的。这让隔了时空的阿阮很是感动。
阿阮果真承包了一百亩山地,种下金银花、半夏、白芍、红花,种下铁皮石斛、白芨、金线莲、黄芪。春天来了,阿阮把山上山下变成了花园,清新的山水,峰青峦秀,怪松搭棚,古藤蟠缠,使人心旷神怡,山谷里有水库,有溪水。工作之余,人们驱车而至,行走花草中,接一下地气,走进农家木屋,品尝特色农家土菜和山庄野味,放飞心情,回归乡野,真是感受自然之美的绝佳之地。阿阮创造了一个美好的生态家园,独特的田园风光,让城里人实现了返璞归真的梦想。
村里人说,阿阮能把棉花弹得那么好,还能把草药种得那么好,这个不太说话,见人笑笑的阿阮可真不简单。九斤老太说,阿阮走南闯北可是见过世面的人,九斤老太没有牙了,不过说话的声音大家都听得很清晰。
有那么一天,阿郑被一辆警车带走了,警车的鸣叫声把天空的云彩都给撕碎了。阿郑开的是电车零件加工厂,他需要一个有规模的厂地,他想把早已停产的国营棉织厂盘下来,于是给分管的县领导送礼,县领导出事了,阿郑也跟着出事了,因为阿郑犯的是行贿罪。杏花望着阿郑戴着手铐的背影,哭成泪人儿。阿郑临走前,对着阿阮说,你帮我照看着杏花,毕竟咱们是朋友。阿阮深深地看了一眼阿郑,说,你放心,兄弟。
阿阮经常买东西来看杏花,不过,他每次来都带着他的雇工,每次来他都把大门开得大大的。他说,杏花,你想开,人的一生哪能都顺顺当当的,顺顺当当的不叫人生,一条溪水还九曲十八弯呢。杏花低下头说,你们喝茶,阿阮!阿阮说,杏花,你要照顾好自己,阿郑走了,还有我阿阮呢。说得杏花的心潮潮的,眼睛也潮潮的。
阿阮种植的中药材长势很好,因为他总是虚心地请教合作社的技术指导员,他摸索出了什么地方的土壤,适合什么中药材生长。几年下来,阿阮富了,买了车,盖了乡间别墅。村民们都夸阿阮脑子灵光,都跟着阿阮学种中草药。
一天,那个叫小霞的播音员,带着一群人来参观阿阮的中草园种植基地,这让阿阮兴奋得像喝醉了酒。小霞果然是个漂亮的女主播。阿阮说,谢谢小霞,谢谢你这么多年对我的帮助,我们虽然陌生,但却是熟悉的朋友。小霞说,阿阮,你都三十岁了,为什么还是一个人,你是不是想把自己变成一棵草药。这话说得阿阮的心酸酸的。
这时站在旁边的杏花说话了,她说,小霞记者,你认识的人多,你帮他牵线介绍一个懂农业的女大学生吧!阿阮心地善良得像柔软的棉花,阿阮是个难得的好人。小霞说,好吧。小霞的好吧说得圆润动听,一如在收音机里。
小霞认识读农业大学的阿翠姑娘,她是一位孤儿,是乡亲供养她长大了,阿翠说大学毕业后还是回到乡里,帮助乡亲们脱贫致富,这是她的梦想。阿翠很喜欢阿阮,因为见到阿阮有回到家的感觉。阿翠说,阿阮,听说你以前会弹棉花,你能弹几床新棉被为咱们结婚时用吗,那些太空棉羽绒棉的,好看是好看,不暖和,盖着轻飘飘的!非得用个毛毯压住,一翻身就没了,还是老古董好,我就是喜欢朴实的棉花被。
这话说得阿阮手痒了,在一个下雨的日子,阿阮戴上口罩系上围腰,开始忙活起来,很快大团大团的白云涌现,温暖回来了。这时阿阮把弓弦弹得像吉他一样,嘣嘣嘣的声音,就在他的指间响起来,荡开去,像一首古老的歌,韵律整齐,曲调铿锵。这时阿阮觉得幸福从四面八方涌来,这让他的嘴角有着喜悦的弧度。
阿翠看着刚弹出的棉花,洁白、蓬松,用手摸上去特别温软,像阿阮对她的爱。阿阮对着阿翠说,棉花一生花开两次,你知道吗?你知道吗?
(插图:郭翠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