弋舟:“微妙”地捕捉城市经验
精神和气质直接源自作家的感受,你没有那样的生命感,通篇充斥着咖啡馆也没用,即便生活在城市里,这种生命感可能也不是所有人都会有。
在国内70后作家群体中,弋舟是备受文学批评家和编辑青睐的一位。近年来,他的作品经常刊发在重点文学杂志头条位置,相关推介、评论、访谈文章不断涌现在各种媒体平台上。
弋舟生长在西安,后来长居兰州。不少人谈到他时,仍习惯从地域上分类,将他视为西部文学最新的代表人物。不过,大家也清晰地看到,到了弋舟这一代人,他们再去写西部城市时,不再是自带苍凉寂寥、大气磅礴的文学气质,而更多的是多元的个性化表达,可能还融入了现代主义的体验。
拿弋舟自己的话说,从小就生活在城市,这是自己的宿命。一个没有故乡的人,被扔进“故乡言说”的强大语境里,这一点,在煎熬着他的同时,也恰恰助力着他具体的写作。没法将自己对“西部”的情感上升为眷恋的他,不得不绕开所谓的“西部经验”,去做一个“真正孤独、沉默的人”,也维护了一个小说家应有的立场和自我期许。
事实上,文学界对弋舟更普遍的提法是“新世纪以来专注于城市书写的先锋小说家”。像一些评论家所指出的那样,在相当长的时期里,中国当代文学在乡土叙事方面十分发达,但面对城市经验却显得稚拙。所以,像弋舟这样专注于城市书写、不断寻求当下城市经验的新的可能性,也许更符合文坛对年轻作家的期待。
在城市书写中,“70后”拥有与生俱来的写作优势与潜能。弋舟写过《站立在城市的地平线上》的文章来阐述自己对此的认识。在他看来,“城市文学”直到今天,恰逢其时,才真正成为了我们文学创作的可能。“如果说,我这一代的写作者,‘具备乡土经验’和‘缺乏乡土经验’都显得有些可疑的话,如果说我们依旧在新情况与老传统之间犹豫踟蹰的话,那么,更加年轻的一代,则毫无疑问并无可选择地已经站立在了城市的地平线上。”
就弋舟自己的创作来说,他的小说不拘囿于庸碌生活的琐屑呈现和庸常人伦关系的描写上,而是投射在超验性的哲理的底盘,对都市人的病态心灵进行切片式观察,揭示出城市纠合的诸多矛盾与冲突。一部分小说以猜谜和悬疑方式展开,给人一种在隐秘之处跳舞的感觉,在显现人的精神困惑和游离状态中营造着艺术魅力。
他总能敏锐捕捉到生活中那些卑微敏感、有独特气质的人,并为他们在小说里重塑肉身。比如在《而黑夜已至》中,他写了好几个抑郁症患者。抑郁症正在无可避免地走向和成为“时代症”、“现代病”的隐喻,而弋舟是比较早对此进行探讨的作家之一。《我们的踟蹰》中则通过曾铖和李选的爱情故事,揭示了现代人一种普遍的精神悬空的迷茫状态。
“我始终顽固地认为,所有艺术存在的理由,更多的都是建立在對于人内在的精神性的关照之上,对于人的物质性关注,理应交给其他的行当——这里面无关优劣,仅仅是分工之不同。”弋舟如是说。
“微妙”地捕捉城市经验,追问隐藏在生活外表之下的真相,思索和关照现代都市人的精神境遇,并远眺整个时代,可以说是弋舟一直以来的写作追求。阅读他的多部作品的感受会印证这样的观点:小说不仅仅是讲故事的,在一定程度上,它的文本和形式就是一种哲学思维,是对世界的思考,承载了一个时代或一个阶段的最新思想发现。
忧伤、残酷也是“诗意”赋予我们的重要熏陶
本来是学美术出身,却走上小说之途,有关这个转折是弋舟被人问得最多的问题之一。他解释,这个身后巨大的推手,那个“促使”之力,就是我们每个人所说的“命运”。他写了一篇文章——《我们为什么写小说》,其中提到“我们的写作,是为了将生命的姿势降低”,还说:“十年来,我写了百余万字,归根结底,就是一个不断掉头的过程,不觉得矫揉造作的话,你可以把我的姿势看成是一个回望的姿势。”
在千禧之年,一个敏感的文艺青年过分地感知世界,满怀着羞涩地诉说,于是有了第一批严格意义上的创作。与其他一些同年龄段的作家相比,弋舟的写作呈现出现代主义的美学趣味,更被视为先锋精神的“延续者”。对此,他曾表示,基本上愿意自己是个“先锋”,1970年代的这批作家,谁会真正抵触“先锋”呢?可如今他的确觉得自己越来越像一个“传统作家”。他坚信,文学和艺术在相当程度上就是一个依赖传统的行为,而且不断求新亦是传统。“如果我还有一些‘先锋’的影子,是不是就可以这样说:先锋实际上就是一种回望的姿势。”
卢欢:正如俄罗斯作家康·巴乌斯托夫斯基所说:“对生活,对周围一切的诗意理解,是童年时代给我们的最伟大的馈赠。如果一个人在悠长而严肃的岁月中,没有失去这个馈赠,那他就是诗人或者作家。”首先能否回顾一下,在您的童年记忆里,最难忘的且进入了自己的审美体系的东西是哪些?
弋舟:具体的细节有很多,这里就不一一例数了。我想要强调的是,对那个所谓“诗意”的理解,长久以来我们可能都夸大了它柔美的那一面,事实上,忧伤乃至残酷亦是“诗意”所能赋予我们的重要熏陶。于是,上个世纪80年代初这个国度的种种世相,即便破败,即便依旧残存着物资匮乏的阴影,但它们都会促进和养成我的审美。我个人的童年生活当然首先是笼罩在整个时代的集体生活中的。我越来越不愿意强调生命的特殊,那样风险太大。
卢欢:2000年以前,尚未开始严格意义上的创作时的您大致过着怎样的一种生活?中文系毕业的父母,以及美术专业的出身都给您早期的阅读和写作打下了何种底色?
弋舟:我可能无法将写作前与写作后的生活全然切割,仿佛写作成为了一个重大的转折。可能我这一生都在预备着干这件事情,当它开始了,进行着,亦如河水流淌,无法将之想象为某种截然翻转的事情。父母的专业势必对我形成影响,现在想想,如果他们是学物理的呢?那我做一个作家的可能性就几乎为零了吧。
至于美术专业,这首先是个既成事实,它与写作的关系,有些是不言自明的,但依旧会被人反复地问及,于是我不得不在许多类似的访谈中做出了说明,几近陈词滥调,这里就不说了吧。如果一定还要说,那么,我觉得对于整部艺术史的张望,真的会刺激一个人对美、对做一个艺术家产生出愿望和野心。
卢欢:您多次提到,自己从绘画转入写作,成为一个小说家,是经过严肃的思考和选择的,还是“被选择”的。这个“转”的过程顺利么?后来在小说中所体现的对现代性美学的追求,跟学习欧洲现代美术(以及阅读与之相通的西方现代小说)有关么?
弋舟:“选择”与“被选择”首先就是矛盾的,这恐怕也是许多信仰者的困惑——究竟自己是被遴选成为了神的子民,还是自己主动去追寻了神的脚印。这个过程当然是双向的,有神的美意,亦有人的能动性。片面强调任何一面都是不恰当的,前者会令我们自以为是,后者同样会令我们自以为是。现在,我更倾向于那个“被选择”的选项,因为我越来越感到了自己的有限和无力。至于“转”的过程,可能对我而言,不存在一个一目了然的“转”,因此也无所谓顺不顺利。事实上,我们何曾顺利过?对于现代美学的追求,必然跟自己的教养会有一些关系,就像吃面条长大的人,对面条就会有种无须说明的信任吧。
卢欢:在2008年凭小说《锦瑟》获“黄河文学奖”时,您曾说,对自己的期许是写有教养的小说,而且您所谓的“教养”,很大一部分就是在指那些前辈,那些传统。今年您获得首届“茅盾文学新人奖”时也说起“我们赓续在一个伟大的传统里”这个话题。您一如既往地强调传统,这具体来说是指哪些东西?有中国的也有西方的?
弋舟:有中国的也有西方的,更有一种作为中国人习焉不察的、根深蒂固地打量世界的方式,它藏在你的血液里,成为某种即便你在理性上反对,也会在情感上服从的东西,我们将这个东西,称之为“传统”。
卢欢:我们确实摆脱不了传统,不管是远的还是近的,包括小说也有小说的传统。像作家方方说批判现实主义这条路在中国还没走完,她会沿着这个传统走下去。您在写作中又是如何面对文学传统的?
弋舟:传统这个东西首先就意味着强大和不由分说,否则它何以传而统之?我们很多时候都在强调变革,甚至“反传统”似乎都具有了某种天然的正确性,这其实是荒唐的。文学和艺术,在相当程度上就是一个依赖传统的行为,而且我们都可以说,不断求新,亦是我们的传统。对人性的恳切勘探,对世界的无尽打量,这些传统永远有效。那么好了,当我写作的时候,面对这样的传统,忠诚于它就够了。还要怎样呢?所谓的“扬弃”吗?至少我不能,我没那么傲慢。方方老师所说的那个事实,正确极了,而且我还会认为,文学之事,批判现实主义这条路永远也不应该和没有可能被走完,它甚至就是文学本身的题中应有之义。
卢欢:当年的先锋写作潮流对您有影响吧?您最初接触时对它的态度是怎样的?后来您还跟踪那些先锋小说家的作品么?特别是他们近年来向现实主义转向之后。先锋精神在此后的历史演进中艰难接续,也有人把您视为延续者,您怎么看?
弋舟:有影响,接触到的时候很喜爱。谈论前辈我们得慎重,在其他时候我已经向他们表示过敬意。他们曾经的创作,乃至今天的“转向”,都是非常复杂的文学问题,我不想作为一个噱头般的“现象”来讨论了,那样太轻慢。以一个概念来谈论问题,总是相对容易的,但也必然简单粗暴,可是我们只能以这种方式展开对话。我被视为先锋精神的“延续者”,对此我当然感到荣幸,可是,如今我的确觉得自己越来越像一个“传统作家”了。那么,“传统”与“先锋”就必然地冲突和不能一致吗?
让城市资源进入我们的作品,才是更可靠的态度
有人说,相较于1980年代中后期以文体探索和叙事实验为主流的先锋小说,1990年代以来的先锋文学精神主要体现为向个体生存意义上的原生体验的回归。应该说,弋舟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家之一。
“世俗生活貌似平庸寻常,却囊括着本质上的尖锐与激烈,在这个意义上,它给了我写作的依据。”弋舟对表面千姿百态的城市生活进行了耐心的摹绘,展开关于个体存在与世界关系的探索,由此敞开一个时代浮躁沉郁的内里;但与此同时,“我的写作习性,决定了目前只能更多依靠‘观念层面’来处理现实,即便我渴望自己也能写得烟火气十足。”很长时间是被“虚构的热情”所驱使,从观念中来,到观念里去,這种写作令他体验到了巨大的乐趣。
卢欢:与年长的作家或一些同代作家相比,您从小生活在城市,没有乡土经验,从而铸就了某种特别的气质。从一方面看,这是您的短板,但换个角度,或许摆脱了乡土叙事的包袱,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这会促使您主动地、义无反顾地在城市叙事中越走越远么?
弋舟:我也只能在自己有限的路径上跋涉,所以谈不上“促使”,因为别无他途,已经被限定。每个人都得面对自己的局限性吧。至于越走越远是一个怎样的图景,我自己也无从想象,也只能假设我们往下走,就是一个“越走越远”的态势了。
卢欢:这样好像又是宿命说了,像作家贾平凹总在说“我只能写乡土一类的作品”。作家是有定数的,不是吗?
弋舟:当然是有定数的。这个还有疑问吗?哪个作家要是说自己充满了不确定性,而且对这种不确定性的使然充满了自我把控的信心,我必定怀疑他。
卢欢:您在《而黑夜已至》的创作谈中指出,这篇小说的创作初衷,在技术上有一个格外明确的目标,就是“非常清醒地要求自己写一篇严格意义上的城市小说”。在您看来,如何界定一篇严格意义上的城市小说?
弋舟:首先它当然必须是以城市为背景的,但仅仅以城市为背景显然又不够,它要求某种“腔调”,往深了说,就是那个所谓的“城市精神和城市气质”了。精神和气质直接源自作家的感受,你没有那样的生命感,通篇充斥着咖啡馆也没用,即便生活在城市里,这种生命感可能也不是所有人都会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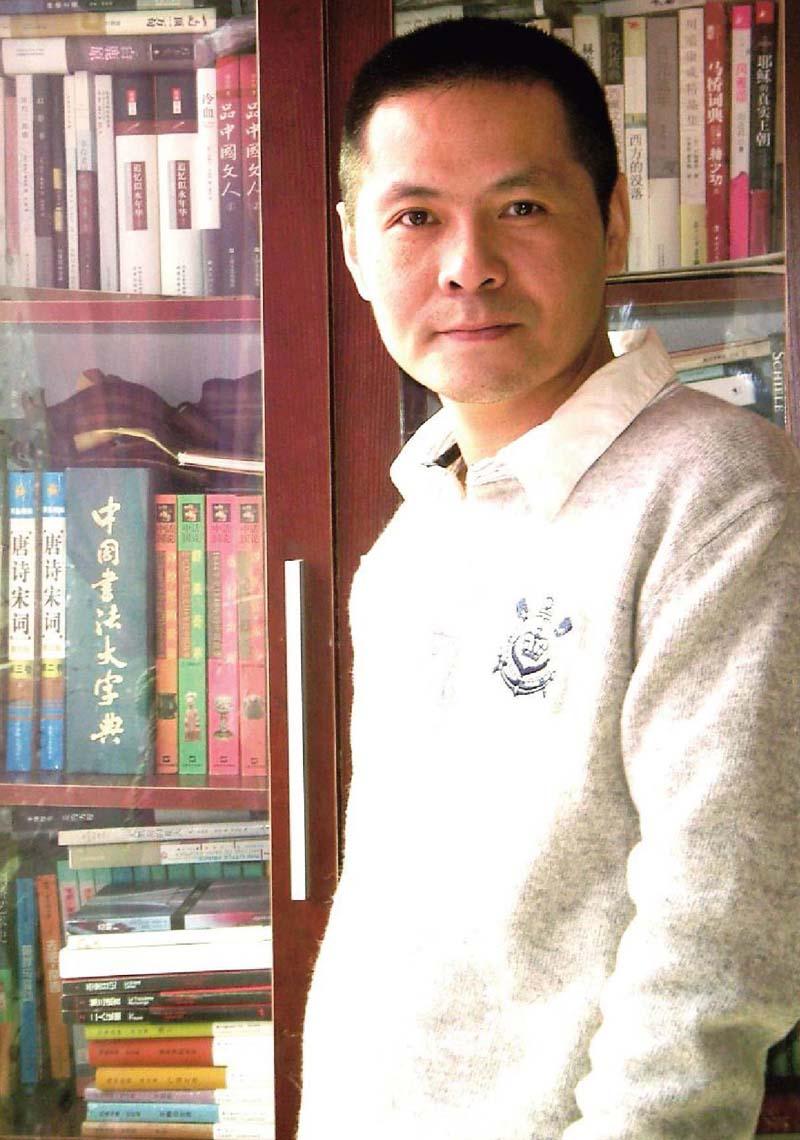
卢欢:我理解的是,相比以城市为背景的故事本身而言,萦绕故事内外的氛围、趣味、情感、味道之类的东西,同样也是您感兴趣去深究的?
弋舟:可能还不仅仅是这样。你所说的这些,仅仅靠“感兴趣”恐怕也未必能够捕捉。那是一种天然的契合,不用格外“感兴趣”,它们本身就萦绕着你。这么说,显得“城市小说”似乎就高级一些,不是这样的,它只是文学的一种样态,只不过中国作家今天格外需要面对这样的样态了而已,因为城市生活已经开始成为我们的事实。
卢欢:在有些人看来,城市文学是沉睡的资源,还没有得到充分的释放。或者说,未来能够成为汉语文学增长点的是以城市为背景的文学。从这个意义上说,您对城市文学的前景作何感想?
弋舟:必然是这样。这里还是无关价值判断和孰优孰劣,只是基本事实。世界变了,翻篇儿了,城市生活是我们未来的基本面,跟着活和跟着写吧。
卢欢:陈晓明老师在接受我采访时说过,中国的城市文学要成就自我,就需要作者用微妙的笔调来写个人,从粗犷的历史、豪放的结构,转化成个人心理的微妙变化的书写。就您的写作经验来说,如何“挖掘”城市文学资源?
弋舟:陈老师总有真知灼见,几乎是用史家的目光在洞察我们文学现象的本质。你所说的“挖掘”,可能也是陈老师所指出的那种“粗犷”和“豪放”吧,好像文学之事真的就是在土地里劳作,那当然只是一个比喻,没有错,在某种意义上也很准确,但是,我们的文学态度,文学理念,长久以来被这种比喻所笼罩,形成的那种范式,如今恰恰和“微妙的笔调”相冲突了。所以,我愿意“微妙”地捕捉,而不是粗犷地挖掘,也许,让城市资源进入我们的作品,这才是一种更可靠的态度吧。
卢欢:您有关城市题材的作品不拘泥于写实。从观念中来,到观念里去,是您长久所依赖的写作方式。这样是否更能揭示城市斑斓景观遮蔽下的生存本质?
弋舟:不能。它只是我的局限,并不是放之四海皆准的利器。
卢欢:相比其他一些作家来说,您对自己的“局限”总是有着某种警惕和反省。但依靠“观念层面”来处理现实真的是写作的一种局限么?有的作家放弃了描写人们的世俗生活,而是倾心于描写刹那的幻念,并且把幻念写得比现实更丰盈。人类精神世界的丰富是物质世界永远难以企及的,或许这也是一种写作理想?
弋舟:老实说,我现在真的对自己、对世界毫无把握,我也不太愿意过度谈论“写作理想”,那样显得自己似乎很有规划,很知道怎么办似的,我只能做我自己能做的,我认为这就是我的局限。“局限”不好吗?事实上,很多时候倒是自以为是的“无限”在蒙蔽我们、损害我们。
身陷失败感之中,
我唯愿自己更能够匍匐在地
“作为一个作家,我写作的理由越来越少(如喜欢文字、对死亡的恐惧、希望出名、创作的喜悦、讨厌坐办公室等等),只为一个首要的理由:我相信最好的艺术表现最多的生命真实。”英国当代著名作家朱利安·巴恩斯的这句话,被弋舟在谈论自己的写作时引用过。
步入老境的朱利安·巴恩斯逐漸看到更加清晰完整的生命真相,着迷于时间、衰老和死亡这类题材,因此有了短篇小说集《柠檬桌子》。而弋舟因为接受了一个写作计划,在2013年的暑假期间和大多数周末,带着儿子频繁地走访空巢老人,聆听着一个个垂暮的故事,于是有了长篇非虚构作品《我在这世上太孤独》。
对于弋舟来说,这是一场事关“孤独”的写作。相较于肉体衰败这样的自然规律,“孤独”,就显得格外沉痛。也是“孤独”这样的存在,令每一位空巢老人彰显了自己的与众不同。不知何时起,“孤独”便成为他写作中的一个重要意象。即便是有关成长的那部分作品,也写出了孤绝、憔悴之美。
卢欢:在您早期的创作中,《跛足之年》是很特别的一部。它是您写作的起点(所谓“跛足之年”是指那个“千禧年”),从一开始就企图和时代有所勾连。但您说原想把它写成预言,没有写好。为什么说对于时代的敏感正是您当时提笔之时最大的动因?
弋舟:我会因此而觉得自己关在屋子里写东西是件不那么无足轻重的事情,它会帮助我克服软弱,克服自以为是,让自己明白自己的那点儿痛苦其来有自,并非无端端的,它和世界建立起的那种关系,能让我变得稍微安静些。
卢欢:慢慢地,您有许多小说的主题涉及到孤独、死亡、虚无、抑郁症、黑暗、贩毒、监狱、癫痫和梦游……取材也很宽,涉及许多完全不同的领域。看起来有些并不是自己熟悉的,也与正常人的生活有点隔,为何不是在自己熟悉的领域深入挖掘呢?
弋舟:小说家以虚构为志业,我还是更乐于想象世界一些。身边事,鸡零狗碎,真的那么值得拿出来描摹与渲染吗?而且,你所罗列的这些项目,对于我们而言,也不是遥远得像是外星球的事一样,它们也是我们的“身边事”。
卢欢:有种声音认为,您的小说擅长借用通俗文学惯用的犯罪叙事来表现社会人生的重要问题。比如说《鸽子》《外省书》等。您怎么看待犯罪事件在小说中的位置,它是否只是您通往精神追问的一个通道?
弋舟:我们能把通俗文学写好就已经很了不起了。犯罪肯定是极端事件,小说有时候是需要“极端”的。这类事件在我的小说里,没位置,起码,我没想着要给它一个什么位置。
卢欢:《等深》《而黑夜已至》《所有路的尽头》三部小说有共同的男性主角——中年知识分子、自我诊断的忧郁症患者刘晓东。他有穷追到底的性格,去找那个突然失踪的青春期男孩;帮助那个受伤害的女孤;找到那个死者的前妻或情人,聊一聊突然赴死的主人公……他是您借以观察世界的一个坐标式的人物?他“以几乎令人心碎的憔悴首先开始自我的审判”与您个人的心理诉求有关?
弋舟:小说家塑造人物,当然是想藉此来向世界发言。诚实的写作,作家自己不免都会有代入感,这些都是文学常识。
卢欢:小说中的人物“竭力抵抗着内心的羞耻”,他们惴惴不安地活着,反省自己的罪恶,并且心怀忐忑地想要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赎罪”,以求让自己生活得更安心。这让我们看到复杂人性中光明的一面。所以您又给予这个时代一些“劝慰性的温暖”,愿意给读者传递光明、温暖的东西?
弋舟:是的,我愿意。生活已经够糟糕了,干吗还要在小说中更加地“描黑”?但这种温暖,只能是劝慰性的,就像我们面对一个不幸的亲人,即便明知道说出的话意义并不大,甚至提供的还是虚假安慰,可我们还是得劝一劝,否则直接鼓励自杀好了。
卢欢:您有一部小说叫《隐疾》,很多评论家由此论述“隐疾”这个词语是揭开您的小说文本深意的密码。如果说,在经济的高速发展下,人们的灵魂没有同步,心灵隐疾越来越没有宣泄的地方,您觉得治愈“隐疾”,实现灵魂救赎的力量从何而来?
弋舟:我没有力量,身陷失败感之中。我不知道那种治愈的力量该从何而来,那是写“心灵美文”的人干的事,我更不是大夫,没有水准开药方,我唯愿自己更能够匍匐在地,那样,我或者会得到些安静的力量。
卢欢:您还有一部长篇非虚构作品《我在这世上太孤独》,这在您以小说为主的众多作品中算是另类吧。您有文章讲到写空巢老人源于自己对孤独感的理解,想探究产生暮年赴死等伤痛的我们这个老龄化时代的构成方式。能讲讲您写作时的具体感悟么?
弋舟:一旦触及这样的题材,你就会清楚地知道,人是会老的,人是会死的。这既让你悲伤,又让你得安慰。
“空巢”现象毫无疑问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重大问题,在某种意义上,我甚至愿意将之视为我们这个时代所有困境的基本“表征”之一,它所涵纳的,除了伦理与社会学的意义,更有某种深刻与复杂的“时代性的悲怆与无力”。
而作为具体的“空巢老人”,他们的形象却因为屡见不鲜而显得轮廓模糊。在我面前出现的这些老人,如果不是因为这样的采访,连我都会将他们混淆在大而无当的概念里,认为他们就只是、也只是生活的本身而已,他们仿佛仅仅只被赋予概念的意味,我们极少能够有机会,甚或有耐心侧耳倾听他们独特的声音。要知道,通过媒体,他们大体也是被同一种叙述范式所描述的。
无疑,老人们都是艰难的,这是自然规律使然,尽管程度各有不同。但我却必须将他们一一分别,让他们成为唯一的那一个空巢老人。在我眼里,让每一个人成为他们自己的,无一例外,都事关“孤独”。是“孤独”这样的存在,令人之个体彰显了自己的与众不同。相较于肉体衰败这样的自然规律,孤独,就显得格外沉痛。因为前者不可逆,所以我们面对起来反而易于接受,而所谓孤独,似乎是一个可以人为调剂的情绪——尽管人之孤独,亦是不可辩驳的生命本质——所以强加于己的时候,才如此令人神伤。
卢欢:这部作品建立在您走访、记录了数十位空巢老人的生活之上,而且是带十三岁的儿子一同采访。这种形式对您来说有什么特别的意义?您希望通过这个给后代带来怎样的一种生命教育?
弋舟:写作《我在这世上太孤独》时,整个写作状态乃至工作方法,还是有别于小说写作的,它令我体验到小说写作无从经验到的一些美好,并且也启发了我对写作之事新的理解;但同时,写就之后,那种完全基于写作本身的、一个小说家的创作“私欲”,却似乎又有了明显的亏欠。于是,我还是需要以小说的方式,再一次翻检一下这笔资源。
我想让儿子对于生命有一种重视,知道人的全部肉体过程。他能有一点点地触动吗?可能很难,我们也是这样过来的,在每一个生命阶段里,无视那个作为整体的生命,似乎自己是可以永远这么着似的。
卢欢:其实您后来的作品多多少少都有延续着对孤独老人的关怀,或者如何面对衰老的思考。比如,短篇小说《出警》表面是写三代警察的繁琐工作,实质上通过“重点人口”老奎和退休老校长多次报假警,揭示鳏寡老人的“孤独感”。《平行》关注的则是人到老年之后在精神上遇到的困窘。这跟您早期写《锦瑟》时靠想象来写老年人的世界相比,发生了什么变化?
弋舟:早期写《锦瑟》,更多的是一种形式上的快感,如今写《平行》,写《出警》,可能情感上更投入了,毕竟,十多年过去,我距离那个遥远的老年,当然是又近了一些。
卢欢:最近的一部书写城市白领爱情的小长篇《我们的踟蹰》广受好评。在如今这样一个讲究实利、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盛行的时代,许多人难以再“葆有磊落的爱意”,也“不再具备契阔的深情”,李选和曾铖也因此爱得踟蹰,直到跌入绝境。这让人想起一度被热议过的都市人群“爱无能”的话题。这是不是说,在被大时代背景“裹挟前行”中,个人的情感看似更加开放和自由了,却并不自主,甚至显得格外犹疑和困顿了?
弋舟:对的,任何事情都会有代价,自由意味着选择的路径多了,而选择的路径多了,人难免会更加犹疑。如今人与人的交往,便捷到可怕的地步,那么好了,蜂拥而至的时刻,“爱无能”等着你。
文学,在一个速朽的时代顽强地镌刻
天赋只关乎“天”,要去做一个合格的作家,我们还必须回到对于自身的训练。弋舟觉得,从多年的写作经验来看,相对于天赋,他更信任某种“工匠精神”,进而指出:“训练重要,首先就从反对陈词滥调训练起吧。”
不少作家认为,艺术家都是工匠,都是做活。在具体的写作过程中,他们正是靠题材的广度,靠材料的深度,也靠毅力与职业性来锻造自己的工匠手艺。弋舟则至今依然保持着每年千万字以上的阅读量,“今天我们从艺之时,人类文明已经为我们储备了浩如烟海的经验。而一个作家汲取这种经验用以训练自己的不二法门,当然便是阅读了。”阅读和写作之余,他还写下一些文学批评文章,进行思想上的操练。
卢欢:一个成熟的作家长年里必定会积累下一些有关写作的经验。我看到您不断有这方面的梳理和总结,特别是您在序言或者后记部分的文字显示出了一位文学批評家的功底。这给人留下的印象是,您专于文学创作,同时又深谙文学批评,您为什么会有您所谓的这种“理论自觉”?它对于您的意义何在?
弋舟:我也不知道我的这种习性是好是坏,也许,在很大程度上,过度“自觉”也会损害写作感觉,但是我想,对于写作的思考还是有必要的,厨子做道菜还琢磨一下呢,我们干的这件事,不思量怎么可以?批评家们在想,作家们当然也在想,这种“思想”的权利,不能拱手相让。
卢欢:其实,您也曾表达过对当下文学评论的不满,比如说“我们的评论如同所有的学科一样,都在无与伦比地趋向教条,评论家们普遍缺乏对于文学那种天赋型的感知能力”。您所期待的理想的文学批评是怎样的?
弋舟:这话我在这里收回。批评家们也够不容易了,事实上,在整体上他们比作家的质量好。如今的文学批评门槛渐高,当然,高学历之类未必一定能兑现成批评能力,但那是另一个话题。我还是觉得,受过严格训练肯定会更好一些,而去当一个作家这件事,今天实际上好像已经没了什么门槛。理想的文学批评有吗?这也许就像我们永远也写不出理想的文学作品。
卢欢:有人说,现在流行的写作是粗糙、简单的写作,与之对应的,我们的心灵感觉也是粗糙的。而对于今天的文学语境中那些失当的粗粝乃至粗鄙,您也深有感触。究竟是什么导致了这一切?
弋舟:流行的总是会有些粗糙和简单吧,但也没错,流行就好。文学却应当反对粗鄙,这是不用说明的。至于是什么导致了今天文学语境的糟糕,我也不知道。人的心灵该是一种怎样的状态,人类已经追问了几千年了,这大概也不是一个专属现代人的困局。
卢欢:关于写作的语言,您说过,“中国式的语言就是中国式的经验,可是今天,我们熟练操弄的词语,离我们的经验真远。这真让人苦恼。”正如德国有歌德和席勒以及康德,俄国有列夫·托尔斯泰、白银时代的诗人们和赫尔岑,当今中国的作家是否也负有建构汉语的使命?
弋舟:没有办法,现代汉语以降,我们就已经进入了这个事实。建构自己的母语,肯定是有抱负的作家的宏愿,当然,实践起来会有多难,我们都能想象得到。
卢欢:新媒体让人们迅速便捷地获知最新资讯,又很快迷失在新的问题中,对被刷过屏的旧问题熟视无睹。作为一种传统的个体手工劳动,文学,特别是叙事文学具有怎样的特质,面对当下这个时代又能做什么?
弋舟:在一个速朽的时代顽强地镌刻,这可能本身已经是价值和意义所在了,它本身就是人类精神的彰显,是美和无辜。
责任编辑 向 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