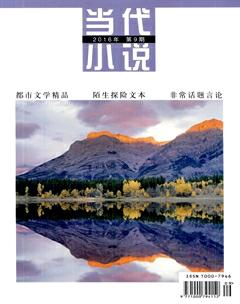昨日金戈铁马
王向晖
已添了许多白发的吴炎,至今还保留着听收音机睡觉的习惯。这个习惯赶跑了好几个本想娶她为妻的情人。一段又一段评书陪着吴炎度过一个个几乎难以承受的分别,虚空里永恒的声音无数次把她从生活的泥泞中打捞出来。
吴炎是八五级的大学生。那一年她仍然用顽强的意志跟遗忘症搏斗。当然除了她自己,没有人认为她是个头脑不健全的人。甚至有人觉得她很聪明。她也不明白自己的大脑究竟怎么长的,别人觉得困难重重的问题,到了她那儿答案像早印在脑子中一样。特别是物理,许多女生一辈子也不能理解的电磁场、压力、压强之类的,她却有剥开果壳品尝到果肉般的惊喜……她害怕记不住东西,从小就养成了考前熬通宵的习惯,一夜间把所有考试内容全部通读一遍,拿到卷子先飞快地把该默写的地方填上;她更害怕记得快的东西也不过是水月镜花,不知哪一天老天会把它们也从自己的脑子中全部一扫而光。那样她成了什么人呢?她靠什么工作、生活下去?
闲散的大学生活让吴炎渐渐养成一个习惯,每天夜里在床上辗转半天后,恍然摸进一个小屋,屋里正在播放刘兰芳的评书。开始是无意识的,不知道这引诱她睡觉的声音什么时候才会出现。后来就有意识地找这个声音,顺着睡梦的绳索往前走,很快就沉沉入睡了。梦中有时也是金戈铁马,喊杀震天,不过她怎么也醒不来。梦中隐约有一个说书人,可那不是刘兰芳,而是李老头。她蜷缩在李老头的怀中睡得看不到窗外的日头,有时还是下铺亲昵地拍着她喊:“起来啦!起来啦!早点打饭去。”
吴炎和她的同屋们殊途同归,最终都在睡觉中度过了青春期的躁动。她们大多有了男朋友,毕业前的急就章,然后就结婚、生孩子,过上了安居乐业的日子。吴炎找了个普通中学当了美术老师。许多人给她介绍男朋友,也有许多同事追求她,可她不敢结婚,大学时期的昏睡治好了她的失眠症,也让心中多了一个秘密,一个不能让任何外人触碰的秘密。
有了秘密就有了过去,这本是吴炎费心寻找的,可没想到找到的却是心理的另一重负担。她的空闲时间不再需要读书了,她喜欢把自己关在屋中细想那些梦,分析哪些过去确实发生过,哪些只是臆想。吴炎的房间对她的同事来说成了一个神秘的黑洞,隔壁左右的同事们常聚在一起,谈论那个总是有人,可总是一个人的屋子。
李老头的屋子也是这样。吴炎每晚都要先经过这个屋子再进入自己的梦中,如同在老家读书时她总先去李老头家再回自己的家一样。
在吴炎的家乡成为一座现代化大城市前,四处都是小河沟,许多人家出脚先过桥,才能到达对面的巷子中。李老头的家有趣的是一边是热闹的街市,另一边是学校、家长禁止孩子们靠近的臭水沟。李老头的家趴在从河沟爬上大街的斜坡上。坡势挺陡,若不是屋前菜地里高高低低的蔬菜形成另一重波涛,屋子大有冲入臭沟的阵势。站在大街上四下张望,只能看到沿街挨挨挤挤的铺面房和颇为体面的门楼,小破瓦房和臭水沟都被屏风样的门楼挡在了外边。门楼洞既是住家们夏天纳凉的地方,也是小商贩们歇脚、躲警察的地方,坏小子们打群架也会转身撤进来,扔了板砖、扎起皮带,很快在破房子中没了人影。
住吴炎家那片街区的孩子上学都喜欢从李老头家门前狭窄的沟边经过,省道倒不是目的,就为了好玩。先别说小臭沟里游着小鱼、跳着蛤蟆、飞着蜻蜓,就是李老头种在门前的那些瓜果蔬菜,也让淘气的孩子们一路上有了打仗的武器。青葡萄、小扁豆、紫姑种子都是上好的子弹,有时连夹着泥巴的小油菜也被他们一路扔得满天飞。当然李老头坐在门口时孩子们是不敢动他的东西的。李老头大部分时间会拿着收音机坐在门楼里,孩子们侦察兵一样从他身边溜开,哄着往臭沟里扔砖头,砸蛤蟆、砸蜻蜓,一齐冲着老头的方向大呼小叫“臭老头、死老头、老不死”,把在学校憋着的一口气发完了才肯走开。
吴炎大多时候回家的路上没有同伴。没有人跟她玩。特别在小学阶段,只有语文、数学两门主课,她的其它才能还没有展现的机会,而语文课文又天天要背,她就成了年级出名的老留生。老师没见过这么不要脸面的女孩子,课上批课下批、放学不让回家、请家长,课文就是背不出来。父母宁可相信女儿比男孩还淘气,心思不在学习上,也不愿相信女儿生理方面有什么缺陷。再说他们除了这个五官漂亮得哪里都不像自己的孩子外,还有一个继承了双方家族所有特点的天才般的小女儿,对大女儿的好坏就一概忽略了。
吴炎成了一个隐形人,她把自己关闭起来了。她不再主动跟外界交流,和她的父亲一样坐在小书桌前,无声地和桌椅融为一体。上学后,她把这种安静带到学校。如果她成绩好,那肯定是学校一顶一的好学生;可惜她成绩开始很差,老师对她这种问半天答一句就很恼怒了,以为是对自己的不尊重。妈妈和老师同在教育战线,和老师说起话来就有了拉家常的亲近,双方当着她的面彼此诉苦,共同重复一句话:“这孩子心机太深,不像个孩子。”对这种一针扎不出血的孩子,老师也放弃了,每天例行公事地留学校,自己该下班了再把她放回去,也算对得起她的父母。
吴炎成了没人管的孩子。老师关照她,天黑了老师还不来就自己回家,把教室门带上就行了。回家后一家人都忙着做自己的事,饭菜放在桌子上,没人理她。吃完了她就到自己的小书桌前做作业。爸爸有时过来看看她的作业,摸摸她的头,转身也无声地坐回自己的办公桌前。有时她觉得自己像跟爸爸比赛谁是木头人,两个一样奇怪的人倒合谋了一场游戏,心里就塌实不少。
李老头是这个小城中的神秘人物,大家说不清他以前干过革命还是干过土匪。反正他上过战场,打过仗,据说有人看到他身上的好几处枪眼。孩子们都愿意他是土匪。在他们看多了战斗故事的小脑子中,人物都分成两类,一类是英雄,另一类是被英雄消灭的敌人。李老头如果是英雄,他就该去学校作报告,戴红领巾,用语重心长的口气给他们讲话;如果他是土匪,情形就正好相反,他们就可以欺负他、骂他、糟蹋他的东西。在学校他们被老师们当做小坏蛋修理,不是骂就是惩罚;出了校门他们自然要修理坏蛋。耍弄敌人既好玩又当了英雄,这是孩子们学得最快的生活准则。
在吴炎眼中,李老头和自己一样,都是内心藏着难言的苦衷的人。当她一个人从李老头家的门楼前走过,看到独自坐在路灯下听收音机的李老头,不知是说书的内容吸引了她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她站在老头旁边不动了。以后老头把收音机放下,进屋又拿了一张凳子,她就坐下来和老头一起听,直到刘兰芳说完“且听下回分解”才起身回家。
每天晚上六点到六点半是说书时间。有时她放学早了,就在老头家做功课。老头在院子里侍弄他的花草,树上有果子时还会摘个下来请她吃;放学晚了她就飞跑到老头家赶个尾巴,来不及听的内容由老头再给讲一遍。可能书听多了,老头讲书时居然用大概齐的普通话,也会学马蹄声、兵器撞击声、人物嘶喊声,声音虽然远不及刘兰芳金钟般洪亮,可也说得跌宕起伏、扣人心弦。她更喜欢听李老头说书,她从来没这么近地、这么长久地听一个人对自己说过话,有时听得着了迷,内心有点暗暗期待,这就是自己的家该多好!有时这样想着脑子就彻底松弛下来,不知不觉地趴在老头桌子上睡着了。她这一觉睡得很甜很塌实,一直到老头把她摇醒,“该回家了,不然父母可不放心了!”在老头粗大手掌的轻拍下,她记起了久违的童年。那时她是幸福的。
她睡眼惺忪地回了家。桌上放着冷饭。爸爸照例会问:“怎么回来这么晚?”她也照例回答:“在教室睡着了。”妈妈照例嘿一声。然后全家就回到原来的秩序中。她吃饭、睡觉。有时不吃饭就睡觉。父母不再管她。她学会想象自己还在河边的小屋中。
就这样听了一段书又听一段,有时是收音机的刘兰芳在说话,有时是李老头在说话,她总安静地听着。一直以来她是他们的听众,不管他们说什么,她总是很开心。生活就这样有了盼头,学习变得不那么辛苦。为了能早点离开学校,她逼着自己上课思想一刻也不开小差,这对于一个孩子很难,她尽量做得越来越好;她还在心里想许多方法把那些乏味的字变得生动起来,大多时候她也做到了。所以上了三年级,她基本可以和别的同学一样早早背完书放学回家了。老师以为自己的劳动有了成效,对她态度温和了许多。她的父母却不知道女儿的这个进步,因为她时常回家很晚,大多时候连父亲都懒得问她,他们早已清楚答案只有一个:留在学校了。
吴炎和李老头像闷在罐子中的两个玻璃球,看似都硬邦邦的,毫不相干,可每天在那么巴掌大的屋里转悠,难免会撞出声响。吴炎起先以为这声音是李老头发出的:你听他说书时宛若战场上的一员大将,时而为自己的战友擂鼓助威,时而勒着缰绳准备冲锋,时而神勇无比和敌人搏斗……她看到的分明是他在叹息、他在吼叫、他在大笑。他是她生命中第一次看到的激动人心的战场!她尊敬他、敬佩他、感激他。她变得快乐了,眼神里有了孩子的兴奋和顽皮,她开始和他说话。她毕竟还是个孩子,不会像一个城府很深的大人一样,用理智死死封住自己的嘴巴。再说生活中有那么多问题她需要寻找答案。那本该是她的父母来回答的。
李老头总用怜爱的目光看着这个没人疼的孩子,如同看那些战争中失去父母的孤儿。吴炎看起来有一个完整的家,实际上比孤儿还可怜,她的父母对她还不如一个普通的陌生人。这个刚十多岁的女孩,满脑子奇怪的问题,“在战场上,你会看见上帝还是死神?”“你是失去了记忆才变得勇敢吗?”“你喜欢当英雄还是活着?”“你是因为受了伤才活下来的吗?”……孩子总拿电影中的战斗英雄和李老头的话比较,老头无言以对时就说:“战争是最诚实的,只有生存和死亡、胜利和失败,至于怎样活怎样死,怎样胜利怎样失败,我也不明白。我只是一个士兵,只知道冲锋。”孩子想想说:“那你也是学生,你要听老师的。”老头点头:“我当了一辈子学生,还没有学好。”孩子有了担心:“原来人不是长大了就可以不做学生了。”老头看着孩子稚气的脸上闪过的忧虑,安慰她:“长大了当学生就可以自己做主了,想学什么学什么,不想学也没人管。”孩子又开心起来。
对大人来说,孩子心中的秘密不过是画在书本上的迷宫,用点心思便一目了然。而大人的秘密却不是不谙世事的孩子所能猜透的。孩子总觉得李老头和周围的人不一样。她从来没看到过他的家人、朋友,可他又是那么一个和善的人。他也很少出门,每天不是看书就是听广播、收音机,要么就在自家的院子中种花种菜。小城的人喜欢串门、拉家常,斜坡上的十来户人家大多你来我往很热闹,惟独老头跟谁都是点头之交。吴炎就这样闯进了这个没有人气的屋子里。屋里就像童话故事中睡着了的城市:菜在地里生长,果实结在树上,收音机在吱呀说话,人却没有醒来。
吴炎上小学五年级的一天,李老头没有像以往那样坐在门口,也没在屋子里。这一天吴炎比以往哪天回家都早。她坐在太阳还没落山的家中,像呆在一个虚假的地方:天空蓝得像电影里的布景,白云像传说中的仙山,金色的夕阳把她的眼睛都染红了。世界仿佛在故意嘲弄她,用那些她一直想闯又闯不进的美丽嘲弄她:“你看到的一切并不真属于你,它们随时会消失。”她恍惚记起这话是李老头说的。此后的好几天,天气难得的晴好,天空总是蓝得透彻心肺,蓝得把地上的美梦席卷而空,而她却流落在地上。夜晚她无故地流着泪醒来,失落地对着夜空张望:李老头的家还在河边,院子里的菜还在生长,果子还结在树上,收音机也还在咿呀地说话……
她还是每天从李老头家门口经过,很快就不再往屋里张望,那个屋子好像和自己再也没有了关联。可她的记性又奇怪地坏起来,语文书总是背不住。爸爸开始关注她的学习,每天晚上不背完课文不让睡觉,家里的墙上开始贴她需要背诵的篇目。墙上的纸贴了一层又一层,旧的纸揭去了,新的又贴上来,她的生活先是被中考填满了,然后又被高考填满了,李老头成了她生活中一个隐秘的问题。这个问题是有答案的,在吴炎看来,这答案就像许多难解的数学题一样,只要自己专心思考,就能发现。读书时吴炎所有时间都必须去面对生活强迫给她的考试,工作以后她要好好想想自己的问题。她确实像一个攻克疑难问题的科学家一样,长久地呆坐在屋子的某个角落,追忆和李老头相处的每一个黄昏、每一个细节。她在那些轻松的、震荡着说书声的黄昏中走近一个人,这人是她的第一个朋友,是她第一次希望生活就这样永远持续下去的人。
考上大学后,她连着两年没有回家。她并不想故意反抗父母,只是想有一次在时间中停下来,好好想想过去,为了自己。过去总像个迷宫,让她曲曲折折地没走几步就神思困顿。她带着一个巨大的问题沉睡在寂寂无声的学校里,四周全是答案,却又全是虚空。她长久盯着随光影移动的墙壁发呆,李老头在她的生活中明明就是这些影子,无缘无故地移进她的生活,又无缘无故地移走了。她在想那些听过的评书,刘兰芳的声音就在耳际,可究竟说了些什么却又全然搞不清楚。她就是这样一个认死理的人,她相信任何问题在时间里都有答案,只要顺着过去的细微末节去探究,就能问问李老头:“为什么离开?”
第三年暑假她回了家,家中的一切发生了令她气愤的变化。过去的两年好像并不是她在拼命往回跑,而是故意给她设置更多的迷障。连父母都变了。他们好像从来都把她当心肝宝贝,而他们好像也早看出妹妹的轻浮。她这一次真生了妹妹的气,第一次对着父母凶凶地责备:“都是你们把她宠坏了!是你们害了她!”母亲抱着大声号啕的她呜呜咽咽,她就这样意外地回到向往已久的怀抱。她几乎忘了李老头这回事了。
吴炎带着使命跟公安局打上了交道,每次都是例行公事地问两句妹妹的最新消息。还真总有,一会儿有人在广州看到她,一会儿又说在西藏,没两年全国都被无形的妹妹游遍了。吴炎更多的时间是跟警察打听一个叫李牧的人。李牧这个名字是她走遍全城找那些以往和李老头住一个大门楼的人问到的。门楼都拆了,小臭沟变成了大马路,以往的住户都分散到了城市的各处,要打听一个人还真如大海捞针。
当吴炎提起小时候常在河边李老头家听说书时,父母都表现出对这个人有深刻印象。母亲甚至提醒父亲:“有一次炎儿回来晚了,我不放心,催你去接她,李老头还请你喝茶来着。”父亲打了个愣,随即附和:“是呀,就是王涵文家旁边的李老头呀!去过!去过!”吴炎真去找父亲教过的那个叫王涵文的学生,结果王涵文的家在城郊,连学校旁边的大街后边就是小臭沟都不知道。倒是王涵文提醒吴炎,可以找以往的同学打听。吴炎还真找到两个没能上大学的中学同学,也记得小时候偷过李老头家的果子。他们放下袜子摊、水果摊,热心地带着这个京城新人找李老头以前的邻居。找人大军越滚越大,几乎把这个城市的下层人群翻了个遍,终于打探到李老头的真实姓名是李牧。
在公安局她找到了这个叫李牧的男人的户口迁移证。是户籍警翻了一个上午才找到的。吴炎又一次沾了北京这个地界的光。户籍警轻易是不会帮人翻动陈年旧事的,吴炎遇到的户籍警是个胖胖的中年妇女,恰巧有个女儿刚去北京上大学,正四处托人给予照顾。当妈的把对女儿的爱心全部放在对一堆旧卡片的仔细找寻上。在吴炎好几次用抱歉的语气对着满脸灰土混着汗水的女警察表示算了的时候,女警察总是用充满信心的话语鼓励她,只要这个城市曾住过这么个人,就能从户口记录中把他捞出来。这个叫李牧的人最终真的出现在女警察母性的肥厚的手指间。户口迁移证上的李牧中年模样,目光严厉,眉头微皱,面色有点阴沉。女警察把被时间捂黄了的李牧捏在手上,拉着吴炎去见她的同事。吴炎理解这位爱心没有落实的母亲为了女儿在掏心掏肺地帮助自己。
老片警一看李牧的照片眼睛发亮,“这个兵痞子,谁给钱替谁卖命。”李牧微蹙的眉头、紧抿着的嘴唇在发黄的相纸上显得更加肃穆,烈士陵园里的照片似的,配上老片警的解说,怎么看怎么听两者也像搭配错了的双簧。女警察天生就是个包打听,一问到底,吴炎倒成了他们谈话的局外人。老片警的大意是李牧是逃兵,逃跑是他为了生存惯用的伎俩。李家本来是大家,因为他吸鸦片把家都败光了,老婆孩子都跟人跑了。后来他卖了屋子去当兵。谁也闹不清楚他究竟跟了几支部队。反正最后他带着伤疤回来了。人民政府可怜他,在河边给他分了间房。他还老实,汇报思想很积极。有一次他听到收音机里一个领导的名字,硬说是他女儿,让公安局给查。没人理他。他还真找过去了。“那领导真是他女儿?”“怎么可能呢?不过他找到了省里的亲戚,考虑到他也该老有所养,就让他迁过去了。”
吴炎在老片警的讲述中越来越后悔自己走错了地方。事情应该结束在它终止的地方。照片上的李牧本来就是和记忆中的李老头不相干的陌生人。女警察倒是很激动,她大口地喝着水,叹息李老头不幸的晚年,夹杂着补述自己女儿的孤苦无依。这样聊了一个下午,她当着自己的同事拉着吴炎的手:“小吴是个重情义的人,她能这样关心一个孤老头子,一定能关照好我的丫头!”吴炎堆起笑容痛快地应承,一并收下女警察写的女儿的地址和那个叫李牧的人的迁入地。
吴炎把两个地址带回北京后,照着一个地址坐了半天公交去郊区的大学领回了个胖妹妹;而李老头的地址则在辗转了几件衣服口袋后,不知道掉到哪里去了。她买来了刘兰芳的全套CD,每天晚上都会歪在沙发上听一会儿。她喜欢刘兰芳中性的声音,特别喜欢听她那底气十足的呼喝,“呀得!金兀术,你哪里跑——”十足的伟丈夫!模模糊糊中她记起李老头的夹杂着吱呀噪音的收音机,那声音就让它在睡梦中回旋吧。
吴炎的同事们发现自从小吴的妹妹考进北京以后,小吴跟换了个人似的。小吴和她的胖妹妹成天打扮得花枝招展,旁若无人地在校园里招摇。小吴原先拒人千里的宿舍现在对所有的人敞开,胖妹妹有时还带着男男女女的同学来,通宵吃喝吵闹。校方多次对吴炎的奇装异服、扰攘四邻提出警告,吴炎和校长大吵一顿之后不辞而别。胖妹妹那时正好期末考试,为了免于补考,一直和同学奋战通宵。等她考完了,睡了几个长觉后再去找吴炎,吴炎已经离校两个星期了。胖妹妹敲了吴炎两个邻居的门,看到的都是厌恶的眼神,听到的都是冷漠的回答:“她早离开学校了。”胖妹妹毕业的时候又来敲了次门,门开了,一个陌生的面孔抛出句话:“你找错人了!”旋即关上了门。
责任编辑:王方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