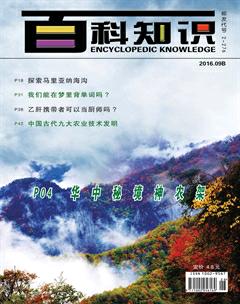盐“道”西沱
胡慧灵
西沱,一座古风古韵犹存的小镇,位于长江南岸的腹心——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作为首批十大“中国历史文化名镇”之一,同时入选的周庄、乌镇早已名扬四海,而西沱却鲜有人知,如今门可罗雀。早年前,“重庆映像·巴渝新十二景”进行大众票选,在票选如火如荼进行期间,古镇排名暂居第一的西沱,留下的却是大众的不解以及“默默无闻”的评价。一个“默默无闻”,就将这自古以来的深水良港、巴盐古道的起点站草草带过,令人感触顿生。其实,旧时的西沱并不似这般寂寞。“北抵江岸,忠万交邻西界沱,水陆贸易烟火繁盛,俨然一都邑也,置塘汛,且设巡检驻之”,清乾隆时期《石柱厅志》上是这样记载的,只言片语就早已勾勒出它熙熙攘攘、欣欣向荣的繁华景象。更有后人如此描绘西沱的百卉千葩:“巴盐古道通川鄂,云梯水埠连川江;千船万帆朝龙眼,三教九流汇乡场;会馆寺院戏楼闹,店铺客栈力夫忙;火龙入江夜喧嚣,灯火云梯架天上。”
时过境迁,奈何繁华笙歌皆落尽,惊艳了岁月,却斑驳了自己。西沱的从容与沧桑,就让盐娓娓道来。
“川盐济楚”商贾集
一代文豪苏轼曾云:“岂是闻韶解忘味,尔来三月食无盐。”可见,盐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正因如此,盐的行销制度格外严苛。在封建社会,盐的行销制度称作“禁榷”,“禁”,止也;“榷”,则为独木桥,也就是此类商品实施专卖制度,产区所产的盐仅限于在某一区域实现行销,不容变通。
后来,随着政治形势的骤变,川盐的行销范围也因势扩而充之。首次“川盐济楚”发生在清咸丰三年(1853),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爆发。太平军定都南京后,阻断了淮盐的行销通道,导致淮盐一时无法运至湘鄂地区。淮盐供应量的锐减,造成了楚岸无盐可食的局面,由此也拉开了“川盐济楚”的序幕。与川盐一样,淮盐也是由产地命名,是指产自淮河南北两岸的海盐,长久以来独占楚岸市场。楚岸,指的是湖南、湖北以及周边州县地区,地域广阔人丁旺,却素不产盐,所食之盐皆靠外援。如此一来,淮盐的供应不畅同时也牵扯住盐课的税收,因此,户部议准:“川粤盐斤入楚,无论商民,均许自行贩销。”清政府饬令“川盐济楚”。在此之后,抗日战争爆发,相继沦陷的沿海一带,其各大海盐生产设备都遭受了严重的破坏,使得食盐的供给与运输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此时,川盐挑起了供应军需的重担,再次济楚,解了楚岸的燃眉之急。
这济楚的川盐不仅解了楚岸的急,迈出了巴盐古道的第一步,同时还为西沱的繁盛助了一臂之力。说起这巴盐古道与西沱,盐总是它们之间最密切的联系和最直接的纽带,因此,也就不得不提它们与盐之间不解的缘分了。一说是因为古时三峡航道的险滩较密集,极容易发生翻船,而食盐又易溶于水,故盐商遂弃水运改陆运,在西沱镇汇集周县济楚的盐,由此地出发,经巴盐古道运达楚岸。《华阳国志·巴志》上载道:“有盐官,在监、涂二溪。一郡所仰,其豪门亦家有盐井。”以产盐而闻名的监、涂两区域正隶属于忠县(旧临江县),与长江明珠石宝寨隔江相望的西沱古镇,咫尺处便是忠县,充分印证了这一说法。还有一说,从西沱济楚的盐并不完全都来自西沱周县,也有长江上游的盐商用船将盐运送至此,再从西沱出发至楚岸。虽众说纷纭,但毋庸置疑的是,西沱古镇因“川盐济楚”成为了巴盐古道的起始处。
乘着盐的东风,丝绸、蜀绣等特产货物也在此地进行流通,于是,西沱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商贾云集地、货物中转站。一时,走卒小贩、富商巨贾都流连于西沱,此处便是一派商铺林立、寺立庙起的蓬勃景象,虽未及“参差十万人家”,但也“商如流水贾如龙”。西沱,自古便繁华。
江天一色云梯街
若“川盐济楚”为旧时人来人往的西沱添了砖加了瓦,那云梯街则是推了波又助了澜,为巴盐古道的盛景添了一笔浓墨重彩。云梯街,始建于汉末,全盛于清中叶,是西沱的场镇,同时也是中国第五大古道——巴盐古道的起点。它西起长江岸边,依山取势,爬上了方斗山山脊,蜿蜿蜒蜒。异于长江沿岸其他建筑,云梯街街道的建制并未采用与江河并行的常例,而是全程垂直于等高线,被誉为“长江沿岸最古老的奇特建筑明珠”。云梯街长约2500米(三峡枢纽工程蓄水后,淹没了其近五分之一的街道),坐百余梯台,拥千余梯步。雾气弥漫时,站在长江岸边仰望,江声呜咽不止,会产生一种云梯街直插云天的错觉,仿佛由此就可以通向天庭仙境,也因此得名“通天街”。
云梯街整体街道皆由三尺青石板铺就,百余个转折梯台如洒落的音符般穿插于其间,抑扬顿挫。千步云梯的两侧是土家族与汉族传统建筑的结晶,既建“吊脚丝檐转角楼”,也造“青砖小瓦马头墙”,层层叠叠,错落有致。两侧的建筑高不过两层,大多都采用了“前店后院”的布局,功能齐备,同时又不失宗法伦理。刻着年轮的木板房,黛瓦粉墙,所有参差不齐的建筑看似连成一片,每一户却有着明显却不突兀的分割,自成一合院。打开泛黄的木板门,堂屋后是负责采光的天井,在天井里,分布着引水池子和洗衣槽子,两侧便是刻着雕花的厢房,再往后则是里屋。在房后,大多都圈了一小块地养猪养鸡,勤快的还利用边角余料种了花果蔬菜,前店热火朝天的商贸氛围丝毫没有掩盖住后院浓厚的生活气息与难得的惬意。
无盐不解淡 千步云梯的起步处,便是下盐店,如今仅存回廊、正厅等遗构。之所以取名为“下盐店”,并非单单依据其所处的地理位置,还得以官办与民办的区别。当年的西沱古镇有两家颇负盛名的盐店,一个是位于山巅的官办盐店,另一个则是位于山麓的民办盐店,当地的老百姓分别以“上盐店”“下盐店”来进行区分。下盐店是由清代举人杨氏修建,除封火墙采用砖石材料外,其余建筑均利用木构,且一概使用楠木等珍贵木材。在云梯街100余家商号中,下盐店的生意颇为兴隆。政治形势动荡下的清政府为了缓解财政压力,将与盐相关的收入作为朝廷重要的财政来源。清代行盐的专卖制度是专商世袭卖引法,也即把食盐行与销的特权通过盐引卖给特定的商贾,禁止一切的私有销售,而特定商贾的选择则是依赖世袭制。在专商世袭卖引制度里,官府可以不收盐不运盐,主要靠授予盐引来获取巨大利润。所谓盐引,又称“盐钞”,商贾若要在白花花的盐里赚取白花花的银子,事前必须在官府获取盐引,否则将无法分到一杯“盐羹”。看似略松动的食盐专卖制度,其实是“无盐不解淡”。
因盐得盛世 相传,现存云梯街两旁的大部分建筑都是因盐而生,云梯街也因盐而盛。伴着“川盐济楚”带来的商贾云集的壮观场面,云梯街两侧的客栈掌柜们为了招揽来往商旅,纷纷在云梯街两旁修屋筑舍,房舍顺着山势一层一层地向上延伸,直达独门嘴山巅,可谓“日暮随处能投宿,鸡鸣随时可启程”。在云梯街的顶端是巴盐古道第一客栈——“生记客栈”,曾名噪一时,今日却躲进了一片碧荫下。客栈前不算宽阔的空地上,随处可见从石板缝隙里窜出的青苔,添了几分生意。客栈旁是因“一树遮三县”而名闻遐迩的古黄桷树。之所以说它是“一树遮三县”,是因为它正处于石柱、忠县、万州三县交界处,虬曲苍劲的枝干也如手臂般指向这三个县。这株古黄桷树已在此伫立了近半个世纪,早已枝繁叶茂,见证了第一客栈的璀璨与黯淡,默然伴随着西沱古镇淌过了历史的长河,消磨了漫漫的岁月。
巴盐古道背二哥
拾级而上云梯街,细看会发现,厚重的青石板上有着或深或浅的杵窝,当地老人说,那是背二哥运盐留下的,这才解了惑。在重庆方言中,称呼下力气的人都带“二”,种田的叫“丘二哥”,挑物的称为“挑二哥”,背货的就被喊作“背二哥”。济楚的川盐要在西沱古镇改水运为陆运,就需要通过巴盐古道将川盐行销至两湖地区,而云梯街依傍着山势而建,蜿蜒曲折,《挑夫谣》里这样描述:重庆不平坦,山城多坡坎。挑担走上坡,腰杆酸又软。挑担下坎坎,脚杆打闪闪。主要意思就是挑着重担上坡下坎十分不便,因此,在巴盐古道上货物的运送全靠专门的人力背运。
从西沱出发,背二哥一路上需要翻越方斗山、楠木垭,经王家乡清龙场、过石家坝、入黄水坝,经锅厂口、青冈坪、坡老巷、回面坡、万胜坝、八角庙、摩天坡、冷水溪,翻过七曜山最终才能抵至两湖地区,数百千米的负重之旅,没有背负的法宝是万万不可行的。民谚里背二哥的形象总是“背上背个大背篼,口里衔个烟锅锅,手上拿个打杵子”,背上的大背篼其实就是背架子。背架子仿造人体的背部曲线,用弯曲的木头作为支架,支架要高出人头,形成一个倒梯形的木墩子,纵向的4个孔上穿过结实的棕片制成背架的肩带。背二哥将装有百余斤食盐的麻袋捆在支架上,利用背部的力量来进行支撑,由于与人体背部贴合,运盐更加稳当的同时还能解放双手。在爬坡上坎中,背负食盐进行运输,其劳动强度之大不言而喻,因而背二哥行业里就有“十步两打杵,五里一哨台”这一说。所谓“打杵”,也就是利用了背二哥的第二法宝——背杵子进行沿途地休息。背杵子是“丁”字形的木棒,虽然造型简单,但背二哥却离不开它。在背盐途中,感到不堪负重时,停下脚步的背二哥将背杵子往身后一杵,背上所有的负重就全部落在背杵子上,得以片刻的喘息。此时,衔着烟锅的背二哥会用小竹篾圈不停地刮去脸上的汗水,在浓烈却不呛人的叶子烟中,忍过穷困的迫切,熬过妻儿的挂念。但背二哥并非被生活的重担压得沉默不语,在喘息的空当还会饶有兴致来一支“背二号子”:“我是巴山背二哥,打一杵来唱支歌。太阳接我上巴山,月亮送我下巴河……”陡峭的石梯间,背二号子荡气回肠,隐隐透露着这一级一梯的艰难沉重,似乎又在吟唱着巴人的坚毅与耐力,总会让思绪飘向远方,让人不禁想起谭继文先生的作品——《巴国盐道》。谭先生是“平行皴”石头画创始人,《巴国盐道》不仅仅是他“平行皴”画石技法的代表作,更是他对故土用情至深的寄托。在他的画笔下,背二哥背负着沉甸甸的盐袋子,沿着石梯蹒跚前行,周围的崇山峻岭愈发的沉重与严肃。巴盐古道,永远都有道不尽的跌宕起伏。
黛瓦粉墙,吊脚小楼,历经斯年的沧桑,却是亘古不变的从容。西沱,实在不该被遗忘。
【责任编辑】王 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