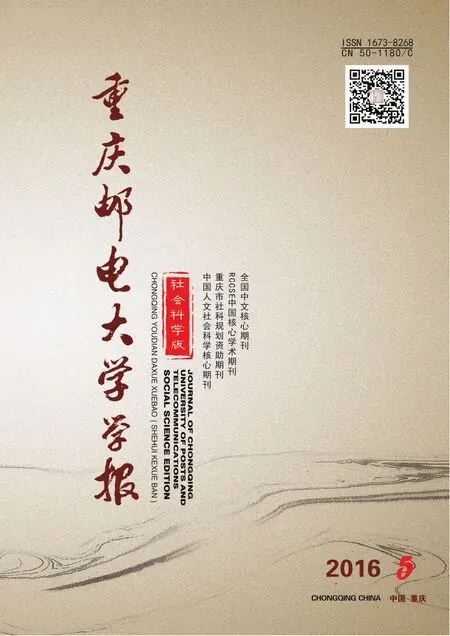童年经验与“六十年代出生作家”小说中的人物形象
宋 雯
(中山大学 中文系,广东 广州510275)

童年经验与“六十年代出生作家”小说中的人物形象
宋雯
(中山大学 中文系,广东 广州510275)
童年经验对“六十年代出生作家”人物塑造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六十年代出生作家”常常以自己童年接触过的人作为小说中的人物原型,他们也常会不自觉地把自己童年时期建构起来的审美倾向和价值观念投射到小说人物的身上。由于他们成长于“文革”时期,他们小说中的很多人物都被打上了“文革”的烙印。他们小说中的少儿形象多是孤独、空虚和迷茫的,且大都拥有浓厚的暴力情结;他们笔下的“右派”及“知青”则都拥有很多的缺点,平庸且世俗;他们小说中的很多“父亲”形象,也不再高大神圣,要么懦弱猥琐、要么残暴变态,和子女的关系都很紧张。不过由于“六十年代出生作家”人数众多,其童年经验世界也存在着种种差异,若想更加全面地把握他们笔下的人物形象,我们还应分析和考察“六十年代出生作家”童年经验世界中的地域、家庭等多方面的因素。
童年经验;“六十年代出生作家”;小说创作;人物形象
作家毛姆说过:“一个小说家只有把自己早年就已经有所接触的人物作为原型时,才能创造出杰出的人物形象。”[1]以鲁迅为例,他外出求学之后就很少回故乡,而是一直在外积极投身于各种政治文化运动,他接触得最多的就是他的学生和挚友,但鲁迅对常围绕在自己身边的人着墨却不多。鲁迅童年虽与农民、佣人有过接触,但对他们的实际生活并没有太多了解,却成功塑造了阿Q、祥林嫂等经典人物形象。也就是说,比起鲁迅的实际生活,“他童年时期对人情冷暖的体验和后来生活中的孤独感对创作更具意义,他的早期经验使他有了某种独特的心理感受,而后来人生经验的溶入又加深加浓了早期体验,生成一种对于世界的基本感受,鲁迅正是从自己的这种基本感受出发来选择生活面、捕捉某些独特的信息而建构自己的作品世界”[2]。
在“六十年代出生作家”的小说创作中,他们刻画得最多、塑造得最成功的,也都是他们童年时接触过的或熟悉的人。由于他们的童年处于“文革”这样一个特殊时期,因此塑造的很多人物如“儿童”“父亲”“右派”“知青”等大都带有鲜明的时代印记。由于“六十年代出生作家”童年经验世界的多元性,“文革”并不是所有作家最深、最强烈的情绪体验。因此,要想更加全面把握“六十年代出生作家”笔下的人物形象,应对他们的童年经验中的时代、地域及家庭等因素有更全面的考察和分析。总的来说,考察童年经验与“六十年代出生作家”小说中人物形象间的关系,在创作心理学的视域下探讨“六十年代出生作家”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将有助于我们更周详地把握“六十年代出生作家”小说中的人物形象特征及其成因。
一、“六十年代出生作家”童年经验影响下的少儿形象
很多“六十年代出生作家”作品中大面积出现的少年儿童,既不像现代文学作家笔下的儿童那样天真、纯洁、稚嫩、单纯,又不像“十七年”文学中“红色接班人”那样意气风发、坚韧顽强,忠于革命忠于党,早早地就扛起了保护国家和民族的重担。他们多在“文革”期间出生和成长,享受着那个时代特有的自由。笔者根据其行为特征和个性特点,大致将他们分为以下三类。
(一)孤独、空虚的“游荡者”
身体孱弱、个性胆小,他们是那个“尚武”时代的弱者,不但被时代主流生活所抛弃,还被同龄伙伴所排挤,再加上学校和家庭教育的缺席、精神生活的匮乏,使得他们产生了很深的孤独感。为了排遣寂寞,他们游荡在城市或乡镇的各个角落,如苏童《怪客》《乘滑轮车远去》中的“我”,《舒家兄弟》中的舒农,王彪《在屋顶飞翔》《病孩》《身体里的声音》中的“我”,余华《在细雨中呼喊》中的孙光林,艾伟《少年杨淇佩着刀》中的杨淇,东西《后悔录》里的曾广贤都属此类。在空虚无聊的游荡中,有意无意地窥视到了成人世界的隐私和不堪,他们的懵懂使得成人最想隐蔽的世界显得更加的赤裸裸。这与作家真实的童年记忆有关,如艾伟在他的小说集《整个宇宙在和我说话》的后记中说:“在我的少年时代,成人世界给我最醒目的印象就是层出不穷的‘桃色事件’。七十年代,因为时代压抑,性反而显得更为耀眼。它震撼我,吸引我,它带着某种神秘而狂欢的色彩,又有那么一点不祥的死亡的气息。事实上,每个桃色事件的主角,他们的命运多少有些离奇和悲惨。这些事件自然以不同的方式进入了这本书。”[3]历史学家也指出,这种性压抑的另一后果,就是物极必反,压抑到难以忍受的时候,偷情者有之,偷窥者有之,偷物(女人胸罩、裤衩之类)者有之,少数人甚至做出性侵犯的傻事来……[4]这些“游荡者”所具备的特征和作家有着高度相似之处,如苏童、余华、王彪、东西等在童年时期都是性格内向、身体孱弱、不太合群的孩子,都是喧闹世界的旁观者。苏童在九岁时曾因病休学,王彪“小时候有头晕症”[5],余华总是被哥哥欺负,东西因家庭成分的问题受歧视和排挤,矮小瘦弱的身体也让他感到自卑。童年的遭遇给他们留下了心灵上的创伤,并在他们的创作中潜在地发挥着作用。
(二)自尊心强、地位卑微的“孤胆英雄”
这方面的主要代表有苏童《刺青时代》中的小拐、《城北地带》中的达生、《独立纵队》中的小堂、《骑兵》中的左林以及艾伟《少年杨淇佩着刀》中的杨淇、《回故乡之路》中的解放。他们跟“游荡者”一样,都是受时代主流和同龄伙伴双重排挤的对象,地位的卑微或身体的缺陷使得他们极度缺乏安全感,会不惜一切手段捍卫自己的尊严。在洋溢着革命力量和英雄豪情的时代,“尚武”是最流行的社会风气,“胳膊上有老虎刺青的三霸”“断了一根食指的阿荣”“练拳击的豁嘴丰收”这样强壮凶悍的恶霸式人物是当时孩子们崇拜的对像,这使得一些遭受排挤和歧视的孩子将“暴力”作为了获得地位和尊严的唯一手段,他们为此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但下场却很悲惨。如《刺青时代》中的小拐,因为瘸腿受尽了侮辱,在他所崇拜的哥哥天平在一场少年“帮派”混战中死去之后,小拐将“重振野猪帮”视为人生的最高理想,他对外谎称是“延恩巷的武林泰斗罗乾”的关门弟子,常随身携带三节棍、九节鞭、月牙刀、断魂枪等武器,并当众展示武艺,终使他获得新“野猪帮”的帮主地位。这种荣耀并没有持续太久,就遭到了更强烈的暴力反击,故事以他的脸上被刻上“孬种”二字、变成孤僻而古怪的幽居者作为结束。《回故乡之路》中的解放,比小拐更加具有“英雄主义情结”,因此当父亲的一次无心举动被打成“反革命”之后,解放决定要做一次万人景仰的“英雄模范”来维护尊严,为此他自导自演,在铁路旁掩埋炸药,出演了一场“挽救列车上的生命”的“英雄壮举”。结果炸残了自己的腿, “英雄”身份也遭到村里人的怀疑,他憧憬的以“英雄”身份上台作报告的梦想破灭了。绝望之下,他在引爆仇人“强牯”家的房屋之后,躲进自己珍视无比的那个巨大的炸弹壳里自杀了。当几天后人们找到他的尸体的时候,发现他“身上覆盖一块红布, 红布是由两块红领巾拼结而成。上面用黄粉笔画着五颗五角星”。除了小拐和解放用极端暴力甚至惨烈的方式来捍卫尊严的“孤胆英雄”外,还有一类儿童用想象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孤胆英雄”梦。他们比前一类儿童更加孱弱,且缺乏行动力,因此他们只能将英雄梦用想象的方式来实现。如《独立纵队》中的小堂因不被任何一个“帮派”所接受,故将自己想象成独立纵队,在受到两个不同“帮派”的侮辱之后,他用“白日梦”般的想象来完成他的英雄梦想:“耳边涌动的是一种类似风吹红旗的声音。……他看见了红旗下排列整齐的队伍,是他的队伍。他看见一条巨大的横幅,横幅上写着威风凛凛的四个大字:独立纵队”。又如《骑兵》中被人嘲笑的“罗圈腿”左林则对骑兵生活产生疯狂的妄想,他骑在墙头、甚至是傻子的身上,将自己想象成威风凛凛的士兵。这些“孤胆英雄”是作家童年时代的战争文化所塑造的产物,折射出那个时代对儿童精神和心理的强力扭曲。
(三)荒诞成人世界的“模仿者”
这里的“模仿者”,除了苏童“香椿树街”上那些力比多旺盛,青春期激情无处发泄,模仿成人歃血结盟、拉帮结派、打架斗殴的少年外,还有一些年纪稍小、不谙世事的孩童,他们靠自己简单的理解,模仿着成人的行为,把残酷的斗争和政治迫害当成了游戏。通过对成人行为的模仿和学习,把他人的姿势、言语、习惯、态度和行为变成自己的一部分,完成了社会学家米德所说的“角色扮演”。如在《独立纵队》中,宋文、小北京等儿童将储藏间作为司令部,召开“叛徒”小堂的公审大会。在《掘地三尺》中,成人们响应号召,平地挖洞,为“抗击帝国主义”作准备,富有庄严的政治意义,但卫东等孩子却将这些凭空而来的沟堑当做战壕,模仿战争片里的战士,展开了他们的战争游戏。在《反标》中,严肃的“打击反革命”运动,也被小波等孩子演变成了紧张有趣的“抓特务”游戏。在《怀念妹妹小青》中,男孩们最爱做的游戏是模仿战斗英雄,以蒲苇棒为武器来发动“战争”。这些作品中的儿童,因涉世未深,故常以不解的淡漠态度应对政治的凶险和危机,将政治性的“大事”化为开心的儿童游戏,表现出一种“错位”的审美意味。此外,“文革”对阶级立场和阶级斗争的强调也使得儿童有了矇眬的阶级意识,随处可见的阶级斗争场景使得他们记住了成人世界的残酷,因此,在《回故乡之路》中,孩子们看到大人批斗“四类分子”有灿,便也学着去教训有灿的儿子;在《水上的声音》中,他们费尽心思捉弄家庭成分不好的瞎老头,嘻嘻哈哈地往他身上砸泥块,将此作为一项好玩的娱乐活动。总的说来,这一类“模仿者”的世界并不像前一类那样充满血腥和恐怖,而是一种无知的快乐,这与他们年纪的幼小和生长的环境有很大关系,如《水上的声音》《回故乡之路》《反标》《掘地三尺》中的孩童,都是生活在受“文革”冲击较小的乡村里。这类儿童形象和作家真实的童年经历有着重要关系,如艾伟、韩东、毕飞宇都是在“文革”时期的乡村成长起来的,没有像余华、王彪、苏童那样亲眼目击过很多血淋淋的暴力事件,他们的童年是比较快乐和宁静的,最难忘的是受战争电影、样板戏、战斗宣传画等熏陶出来的“英雄主义情结”。因此他们笔下的少年儿童,总是充满着“革命理想主义”激情,对英雄无限神往。这种“英雄情结”甚至影响到他们对成年男性人物形象的塑造,艾伟就坦承:“我的内心一直有一个英雄主义情结在的,所以我小说里的男人大都很男人,比较强硬。”[6]麦家也说:“我后来写的那些人,最后都开创自己的一番事业,都成为了一种英雄一样的人物,我觉得也是我小时候对英雄渴望的一种折射吧。”[7]
这些少年儿童形象都是以前文学作品中所没有的,他们是那个特殊年代所特有的存在。他们身上承载的都是作家宝贵而真实的童年回忆。如苏童曾坦言“香椿树街”系列中的南方少年“在实际生活中都有具体的原型”[8]。艾伟也说他的短篇小说集《整个宇宙在和我说话》里的每一个孩子,都是童年时候的他以及他的玩伴们,在故事里,他总是不由自主地让别的孩子去完成他曾经干过的“恶行”。他坦承,故事里面的孩子,“郭昕、鬈毛、李小强、喻军,其实都是我”[3]。
二、童年经验影响下的知青形象
“六十年代出生作家”作品中的“右派”及“知青”形象,虽不及“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及“知青文学”中的多,可是都是从他们自身童年经验出发建构的,因此作家笔下的“右派”及“知青”和“伤痕文学” “反思文学” “知青文学”中的大异其趣。“伤痕文学” “反思文学” “知青文学”的作者本人大都曾当过“右派”及“知青”,是上山下乡以及下放等一系列政治运动的亲历者,因此他们在写到“知青”和“右派”的时候,都带有强烈的情感倾向,都会不自觉地对其进行粉饰和美化。 “右派”是无辜的政治受害者,有着高尚的道德和坚定的信仰,虽然身处逆境,遭受着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却始终不甘于沉沦,并努力改造着,如《布礼》中的钟亦成、《绿化树》中的章永璘、《灵与肉》中的许灵均、《人啊人》中的何荆夫等。他们笔下的“知青”也大都热忧、真诚,富有牺牲精神,责任感强,艰难的环境不但没让他们退缩,反而激起了他们的决心和勇气,使他们明白了成长的真谛。在梁晓声的《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张承志的《金牧场》中都能感受到“知青”们激情澎湃的青春岁月以及“青春无悔”的壮志豪情。总之,“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知青文学”中的“右派”和“知青”都是“受难的英雄”,具有脸谱化、类型化的特点。而在“六十年代出生作家”的笔下,“右派”和“知青”却失去了神圣和崇高的色彩,被还原成了一个个有血有肉的普通或庸俗的人。如在毕飞宇的《平原》中,吴蔓玲从女知青一步步走到村支书的位置,靠的是对权力的强烈渴望以及对领袖意志和政治命令的盲目服从,为此她极力压抑自己的女性意识,从一个俏丽的姑娘变成了一个严肃呆板、女性特质缺失的“铁姑娘”。她喜欢端方,可她却只敢把自己的感情埋藏在心底,在寂寞、压抑中看着自己宝贵的青春一去不返;而南京来的一位男知青刚来王家庄时还是挺活泼的一个小伙子,积极、肯干,可也就是一两年的光景,从“一匹活蹦乱跳的小马驹变成了一头最懒的驴,做什么都磨叽”。看着其他知青一个接一个走了,他却走不掉,索性破罐子破摔,变成了一个吊儿郎当、懒惰无比、没人愿搭理的“混世魔王”。右派顾先生虽然也经历了从精神到肉体的磨难,并且自觉自愿把自己逼成了背诵马克思著作的活书橱,可他并没有“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中右派身上常见的英雄气慨,而是胆小怕事、唯唯诺诺,满嘴的马列主义唯物主义理论,却在女人、鸭蛋等问题上搞得狼狈不堪。李洱在《鬼子进村》中以一个儿童的视角来叙述知青来到村子之后的一段生活,这里的知青并不像“知青文学”中的那样热忱、勇敢,富有责任心和崇高的理想追求,而是一群有着种种缺点的普通人。在村民的眼中,他们 “什么都不会干”“打架闹事的好手”“偷鸡摸狗”“剪猪尾巴”“敢在路上搂着亲嘴”;在孩童的眼中,他们是被兔子追得飞跑的胆小鬼。韩东可以说是“六十年代出生作家”中对“右派”和“知青”着墨最多的一位,在《扎根》《西天上》《农具厂回忆》《母狗》《恐怖的老乡》《下放地》及《知青变形记》中,他都生动描绘了那个年代知青和下放干部在农村的枯燥、压抑、空虚、无奈的日常生活,这些知青和右派面对苦难,并没有将其当作强者成长路上必不可少的炼金石,而是想方设法逃避和自保。如老陶(《扎根》)极力想要同群众搞好关系,总是一副唯唯诺诺的模样,在自己的朋友遭受政治迫害时,他也成了一个失语者。那些知青也都是懦弱、自私、胆小的,他们考虑得最多的,无非是与自己切身利益相关的凡俗之事。总的来说,这类小说颠覆了“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知青文学”的书写模式,解构了右派和知青自我塑造的光辉形象。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六十年代出生作家”在“文革”时期年纪尚小,既没有“右派”被下放到艰苦地区劳动锻炼的经历,也没有“知青”上山下乡,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的经历,这使得他们在塑造“知青”和“右派”的时候,免受意识形态的干扰,喜欢借助自己真实的童年回忆。如毕飞宇和韩东都是当年随父母下放农村的孩子,在他们的童年生活中接触了大量的知青和右派,他们在创作的时候,就不自觉地将此作为创作资源,以自己的真实童年记忆来感受和复原这些形象,比观念先行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和“知青文学”更加真实可信,也使得生活和历史从单一视角的观照下解放出来,显示了新的言说可能性。
三、童年经验影响下的“父亲”形象
“六十年代出生作家”作品中的很多“父亲”形象,多失去了神圣的光环,要么懦弱猥琐,要么残暴变态,和子女的关系也很紧张。《舒家兄弟》《城北地带》《刺青时代》《枪毙》《画皮》《卫川与林老师》《现实一种》《世事如烟》《难逃劫数》《在细雨中呼喊》中的父亲都是如此。如《在细雨中呼喊》里的“父亲”孙广才亲情淡漠、无能自私,暴戾贪婪、野蛮残暴,打骂儿子,责骂失去劳动能力的祖父,抛弃发妻,调戏儿子对象;《世事如烟》中的父亲更是冷漠变态至极,算命先生为了滋补身体,需要采集年轻人身上的“阳气”,不惜牺牲亲生儿子的性命。一方面,这与作家童年的真实经历有关。“文革”时期极左思潮泛滥,社会氛围压抑,人人自危,很多孩子看着自己的父亲被“打倒”或接受批斗,父亲在子女面前展示了人性中脆弱的一面,是紧张的政治氛围和在外界受到的不公待遇让父亲变得暴躁而乖戾。如荆歌作品中那些残忍、变态的“父亲”以及恶劣的父子关系就带有强烈的自传色彩。另一方面,这样的“父亲”形象与“六十年代出生作家”普遍存在的“怀疑主义”倾向有关。喧嚣、破碎、矛盾,变幻不定、动荡不安的童年生活景观让他们学会了怀疑和反叛,再加上成长过程中一直遭遇着时代的变化和价值观念的自我颠覆,因此他们习惯于质疑秩序、权威;而父亲通常在家庭中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是道德伦理权威的化身,所以“父亲”在“六十年代出生作家”作品中常作为权力和秩序的象征被审视、批判和消解。
由此看出,很多“六十年代出生作家”笔下的儿童、“右派”、“知青”、父亲等人物形象和其他代际作家笔下的同类人物有了显著差别,差别形成的主要原因就是“六十年代”,或者说“文革”留给他们的体验过于深刻,这些与时代相关的童年经验左右了他们构建人物的价值观念。
四、不同童年经验影响下的人物形象塑造
由于“六十年代出生作家”童年经验世界的多元性,“文革”并不是所有作家最深、最强烈的情绪体验。如对于迟子建、郭文斌、石舒清等家庭幸福、成长于受“文革”冲击极小的边缘地区的作家来说,他们最乐于塑造,且塑造得最成功的是他们在童年时代接触过的那些友善乡邻和天真可爱的小伙伴。如《北极村童话》里的困境中依然优雅的苏联老太太就给读者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而她正是迟子建姥姥家的邻居,迟子建在北极村姥姥家居住的时候,就对这位“神秘”而特别的人物产生了浓厚兴趣,她观察苏联老太太的生活,甚至还受邀到老太太家里做客,所以在日后创作的时候,她才能将这个人物塑造得如此血肉丰满。由于童年经验的影响,他们笔下很少有英雄式的人物,也很少有苏童、艾伟、余华、韩东等“六十年代出生作家”作品中常见的叛逆少年、心灵扭曲者、“右派”“知青”等人物。迟子建笔下出现得最多的是一些生活在东北黑土地上的平凡百姓,他们是《鱼骨》《逝川》中的渔民,《亲亲土豆》《腊月宰猪》中的农夫农妇,《逆行精灵》中的小木匠、贩卖山货的小商人、住雪山木屋的猎人,《草地上的云朵》中的乡村小姑娘“丑妞”,《日落碗窑》中训练狗顶碗的“关小明”。他们大多善良淳朴、勤劳乐观,坦然承受着生活和命运赋予的苦难,就像东北桦树一样朴实无华却坚韧无比。在郭文斌笔下大量出现的那些儿童,如《吉祥如意》《大年》《农历》中的明明、亮亮、五月、六月,在物质的贫乏和生活的艰难中依然保持着一颗天真快乐的童心,他们都带有郭文斌童年时代的影子,天真无邪、纯真可爱,是五四“金色童年”的延续。从这些作家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写得最好、塑造得最成功的都是乡村人物。虽然他们也塑造过一些城市人物,因大多没有深入到人物灵魂中去,而是急于传达一种思想观念,如《草地上的云朵》中道貌岸然,借下乡检查工作之机胡吃海喝,和新来女大学生玩暧昧的“宋局长”,狐假虎威,只知灌酒拍马屁的司机“张迷糊”,穿着板正,极讲卫生,规规矩矩的城里孩子“天水”和“青杨”,都有较多的理念化痕迹。相比之下,他们笔下的乡村人物,就要鲜活、有力得多,如率真泼辣、古灵精怪,像野花一样生长得自由自在的“丑妞”(《草地上的云朵》);勤劳乐观、情深意笃的乡村伉俪“秦山”和“李爱杰”(《亲亲土豆》);漂亮善良,却能干得没人敢娶的渔妇“吉喜”(《逝川》);懂事体贴,天真善良,纯真可爱,在艰辛生活中挖掘快乐的“明明”和“亮亮”(《大年》),都能够触动读者的心灵,令人久久无法忘怀。
而对于陈染这样童年家庭氛围压抑,缺少关爱的作家来说,世态炎凉和孤独的体验对其个性形成及创作更有意义,内向、忧郁、敏感、孤僻的个性,使得他们笔下的主人公也大多与现实格格不入,特立独行,总是沉溺在个人内心世界,对外面的世界漠不关心,是常人眼中的怪人。如陈染《世纪病》中喜欢逃学、陷到自己制造的世界中去的中文系女生;《嘴唇里的阳光》中做着刻板工作,却惯于想入非非而无法遵守规则的年轻女子;《小镇的一段传说》中独自生活却醉心于布置房间、制作“小鬼”、写毛笔字、在烛光中观看小抽屉里的记忆的丑女“罗莉”;《纸片儿》中每天独自坐在屋门前摔红泥巴、扭小泥人的少女“纸片”;《不眠的玉米鸟》中寡言少语、耽于幻想的古怪女人“蛮索”;《巫女与她的梦中之门》中终日沉醉在书中的“我”;《另一只耳朵的敲击声》中需要紧闭门扇、拉严窗帘才能安心的幽闭症患者“黛二”等。这一类人物形象往往带有创作者强烈的自传色彩,作者、叙述者及人物常常呈现出一致的性格特征和情感价值取向。父母感情不和,经常争吵,在压抑的家庭氛围中,童年的陈染喜欢沉浸在远离现实的音乐世界里,恐惧与外界的接触。这样的童年经历给她带来了心灵的创伤,郁积在心中的痛苦情绪使她产生深深的压抑感。心理学认为,压抑的力量需要及时疏泄,艺术对现实具有补偿作用,驱动着作家通过文学创作释放积压已久的汹涌情感,以达到一种心灵的平衡。正如阿德勒所言:“在很大程度上,童年的经历会对人今后的职业选择产生影响,这个孩子或许会希望通过艺术创作而获得精神和心灵的补偿。”[9]当这些在早年生活得孤独、压抑的孩子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之后,不愉快的早期情绪感受便成为他们独特的生命体验的坐标和出发点,迫使他们后来以艺术冲动的方式发泄出来。
总的来说,童年经验对“六十年代出生作家”人物形象塑造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作品中的很多人物有着“童年的作家”的影子;第二,童年时代接触过的形形色色的人物成为了他们作品中人物的原型;第三,童年经验左右着作家作品中人物价值观念的构建,他们会不自觉地把自己童年时期建构起来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投射到小说人物身上。
[1]毛姆.巨匠与杰作——毛姆论世界十大小说家[M].孔海立,王晓明,金国嘉,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155.
[2]童庆炳.现代心理美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97-98.
[3]艾伟.整个宇宙在和我说话[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4:257.
[4]严昌洪.20世纪中国社会生活变迁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230.
[5]张钧.小说的立场——新生代作家访谈录[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534.
[6]艾伟,何言宏.重新回到文学的根本——艾伟访谈录[J].小说评论,2014(1):142.
[7]麦家:我的主人公全部牺牲在自己的忠诚里[EB/OL].(2014- 03-31)[2015- 07- 01].http://culture.ifeng.com/niandaifang/special/maijia/interview/detail_2014_03/31/35325444_0.shtml.
[8]苏童,王宏图.苏童王宏图对话录[M].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105.
[9]阿德勒.生命对你意味着什么[M].周朗,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0:189.
(编辑:李春英)
Childhood Experience and Character in “Chinese Writers Born in 1960s”’s Novel
SONG Wen
(DepartmentofChinese,SunYat-SenUniversity,Guangzhou510275,China)
The childhood influence of “Chinese writers who were born in 1960s” on their characterization is: they often make the people appear in their childhood as the prototype of the characters in the novel, and these writers often put their aesthetic tendencies and values which they built in childhood into the characters of the novel. Because they grew up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period, many characters in their novels marked the era. In their novels, “children” are lonely, empty and confused, and most children have “violence complex”; “Right-wing” and “Educated youth” have many flaws, normal and worldly; “father” becomes cowardly or cruel, and unhallowed. But we should notice that not all the factors in childhood experience affect writers deeply. We should make a comprehensive and detailed analysis of the writer’s childhood experience in order to fully understand literary characters in “Chinese writers who were born in 1960s”.
childhood experience; “Chinese Writers Who Were Born in 1960s”; character; novel writing
10.3969/j.issn.1673- 8268.2016.05.023
2015-12-15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文学都市审美理论与实践——海派文学的都市叙事方式研究(11FZW021)
宋雯(1985-),女,土家族,湖北恩施人,博士后,主要从事现当代文学和文艺学研究。
I206.7
A
1673- 8268(2016)05- 0131- 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