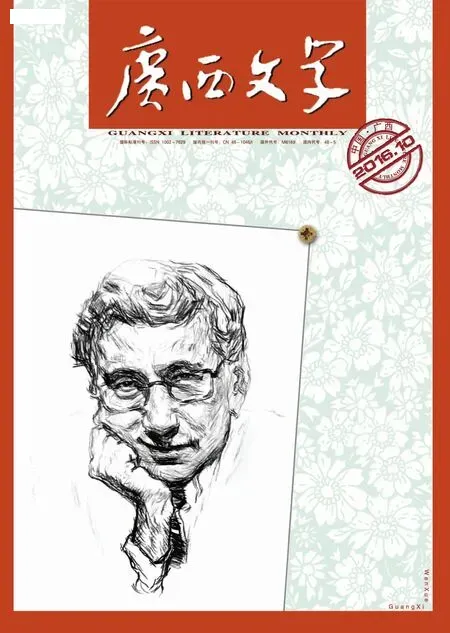寻找消失的火车站
田 湘/著
一
火车再也不会开进这个小站了
不会有钢轨、汽笛
青草覆盖了道床
不会有我父亲挥动的小旗
——《老站房》
诗中的小站就是侧岭火车站,它位于黔桂铁路金城江至南丹之间。在回首我与侧岭火车站的往事之前,有必要先了解一下黔桂铁路。
黔桂铁路是民国政府在抗战期间修建的,当时只修通柳州至都匀。而这段铁路,由于日军入侵损毁严重,没怎么运营就已废置。新中国成立后进行修复,同时动工修建都匀至贵阳段。1959年1月全线通车运营。
黔桂铁路全长六百〇七点八公里,纵联贵州、广西两省区,跨越高原、山地、盆地,地势北高南低,最高海拔一千一百米,最低海拔九十二米。因其极为复杂的自然环境,加上技术条件落后,只能以降低线路标准来适应地形变化,线路傍山贴岭,升降急剧,曲折辗转,跌宕起伏,尤以金城江至麻尾段最为崎岖险峻,火车开起来都气喘吁吁,直冒火花,速度也慢得像蜗牛一般,且非经验丰富的司机根本不敢驾驶。记得有一年执行特殊任务,北京派来司机把火车开到关西站至拉易站区段,吓得停下,不得不叫当地司机来开。2009年初,这条铁路按现代技术标准完成了全面升级改造,线路里程缩短为四百八十九公里,火车速度从原来的时速不到六十公里提升至一百四十公里左右,实现了全线电气化,运能大大提高。因为改线,六甲至南丹间的十多个火车站,包括侧岭火车站均被废弃。

侧岭高速路
这个已经消失的火车站就是我的出生地,我在此读完小学、初中,并沿着这条铁路的轨迹,踏上人生的旅途。毋庸置疑,黔桂铁路和这个小站,留下了我最初的生命记忆。
二
对我影响最大的,当然是父亲。我父亲是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兵,虽然跨过鸭绿江仅几个月,但与他一起去的四百余人,只有十二人回来。父亲能活着回来,还得益于他有点文化,当了师部的通信员,没有上前线打仗,但也因骑马送信摔伤肋骨,造成终身隐痛。父亲1956年转业,回到湖南东安县山口铺乡下,后因铁路招工来到侧岭火车站,成为新中国成立后黔桂铁路的第一代铁路人。母亲从东安嫁到侧岭,随父亲来的还有我的奶奶。父亲出身富农,这对他的仕途和家庭都有一定影响。他读过几年私塾,写得一手好字,工作也很努力,但就是得不到提升。“文革”期间我见他挨过批斗,此事在我幼小的心灵投下了阴影。由于他的原因,子女都受到歧视,我的班主任就公然让同学们远离我,一些同学还合伙欺负我,好在我有个强壮的哥哥,一拳撂倒一个,从此没人敢欺负我了。父亲在侧岭当过扳道员、养路工、值班员,一干就是三十年,直到退休,才迁居到金城江和柳州。顺便说一下,铁路有很多特殊工种,除了火车司机、客运员、列车员、售票员为人熟知外,其他工种大都很陌生。扳道员属于车务部门的一个工种,他的职责是,火车进哪一股道,他就用手工扳动道岔,引导火车进站。这一原始的工种,随着铁路的自动化已不存在。养路工则属工务部门,负责铁路道床的维护,干的是铁路最苦的活,当年铁路企业惩罚职工就是将其调入工务部门。我父亲是在“文革”期间,从车务部门被贬到工务部门的,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又调回车务部门当了值班员。而值班员就是让火车开或停的指挥员,其实也是铁路系统最普通的职工,但在我心目中,父亲就是我的偶像,他在站台上一站,手中的小红旗一举,火车就停了,小绿旗一挥,火车就开了。在我看来,他的手简直就是上帝的手。多年后我曾写过这样一首赞美父亲的小诗:
轻轻地推开那一重山
云深处,便是我的故乡
是我故乡的小站
列车驰骋有铿锵之声
月台之上,那个挥旗的人
是我的父亲,我儿时的偶像
三十年风风雨雨
他就这么站着
他站立的姿势很像将军
而将军是孤独和寂寞的
他养育的儿女都已长大走了
而小站没有长大他不愿走
小站永远也不会长大
只是节奏加强了他更忙了
我担心他会一夜间老去
老去就如故乡的那棵古榕
啊父亲我的父亲
车过小站没有停下
我挥手告别父亲告别小站
眼泪浸湿那朵朦胧小花
——《车过小站》

侧岭火车站老站房
当然,父亲也有过调到城市的机会,但他放弃了,主要是舍不得几亩地。当时父亲的工资虽高,但母亲还是临时工,膝下又有四个小孩,光靠他们的工资要养活一家七口人显然有困难,这也是父亲不愿到城里去的原因。这事我们是工作后才知道的,为此心里还埋怨过他,因为当时我们都想做城里人。从上小学起,我们便成为家里的劳力,每逢周末和节假日都要去砍柴、种菜、捡煤。说到捡煤,这也是当年铁路人特有的活,那时候火车是蒸汽机车牵引,烧的是煤,火力要猛,煤还没烧透就要换新的,于是就有了再利用价值,这些没烧透的煤往往在火车停站后被卸到铁道边,我们就争相去捡回家,大块点的煤可以直接烧,细碎点的就做成煤饼。父亲是铁路职工,吃的是“皇粮”,在家里有较高的地位,因此家务事他是不做的。他性格耿直,得罪过领导,也吃过不少亏。那时小站生活很单调,没有多少娱乐,父亲休班除了睡觉,就是打牌、喝酒。他嗜酒如命,用这种方式来排解自己的孤独,并保持至今。记得八十岁那年我们给他祝寿,他一高兴喝了半斤茅台也没醉,只是前两年得了轻度脑梗酒量有所下降,但现在每天的中晚餐都要喝上几杯。他今年八十六岁了,越来越像个孩子,你不给他喝酒,他就跟你斗气。父亲曲折而倔强的一生,深深地影响了我。
母亲小父亲七岁,她是侧岭小学炊事员。这在那个贫瘠的年代可是个美差,我们因此可以多吃上几丁鲜肉。由于在学校工作,她不仅偷学了一些文化知识,且对小孩读书极为重视,这也是我和妹妹能考上大学和中专的原因。我至今对学校有着特殊感情,且喜爱读书,与母亲的影响是有关的。
我的奶奶慈眉善目,平时言语极少,讲话声音总是很低,连一只蚂蚁也不忍踩死。她做酒饼有绝招,酿出的甜酒很好喝,方圆几里都来找她要。奶奶很有办法调动我们的积极性,每次都从口袋里掏出一两毛钱作为奖励,让我们去劳动。从我有记忆开始,奶奶就驼背了,但她从来不要别人照顾,干一些力所能及的活,每天喝碗自酿的甜酒,直到九十岁辞世。奶奶与世无争、勤劳善良、自食其力的一生对我也有较大影响。
由于长辈都是湖南人,他们的生活当然还保留了家乡部分的习俗,喜欢吃辣椒、干鱼仔、醋血鸭,说话带有湖南口音,有时为了不让我们听出其中的秘密,干脆就讲湖南话,而我们学的是当地土话,湖南话自然是半懂不懂了。父母为了让我记住自己是湖南人,索性给我取名“田湘”,沾了个“湘”字。在籍贯填写上也是有规定的,填的是湖南东安,这几年才按新要求填出生地,所以我们一直把自己当作湖南人。但我们在广西土生土长,却是不争的事实。因此在我的性格中,既有湖南人的刚烈、豪爽,也少不了广西人的诚朴、仗义。
三
父亲常年在小站台挥舞小旗,简单的工作,支撑着全家的生计,背后当然也有全家人对他的支撑。因为他在铁路上班,我们全家都成为铁路家属,成为铁路上的人。

侧岭油菜花开

侧岭市场
其实铁路是自成一体的小社会,有自己的工作生活文化圈。在大一些的城市,会有医院、学校、文化宫、体育场、菜市、派出所等,铁路局、分局所在地还会有公检法机构。所有的铁路单位都有独立的办公和生活区域。有人戏称,铁路除了没有火葬场,什么都有。由于铁路自成体系,往往会形成自己的朋友圈,找工作也更多地愿留在铁路系统,子承父业。后来铁路进行了社会职能移交,这些功能就没有了。我所在的侧岭火车站是个四等小站,当然不具备这些条件。但有供应车,每月都会从柳州运送些城里才有的食品过来,如面条、腐竹、酱油、烟酒等,这在当时都是奢侈品了。还有电影队,每月也会来放一次电影,都是《地道战》《铁道游击队》 《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之类的。那时看电影就像过节一般,铁路地区不大的院子会挤满人,职工家属和附近的农民都会赶来看。那年代文化生活实在太单调,一部电影可以跑到相邻的火车站和生产队去看,且看几遍都不腻。除了看电影,就没有什么娱乐活动了。因此小孩们常聚集在一起,玩躲猫猫的游戏,玩陀螺和烟纸。有时也听大人们讲故事消磨时间,而故事大多跟鬼有关,以致我一个大男人至今怕鬼,走夜路也是怕怕的。卫生所可以看些小病,大病要转到金城江或柳州的铁路医院。职工看病是全免费,家属看病是半费。小孩读书,除非当地有学校,偶尔会在当地读,大多会转到城市的铁路学校去。坐火车也是一样,家属去看病可以开免票,学生凭铁路学生证也不用买票。如果你穿铁路制服坐火车,更没人查你的票了。火车站更是这里的中心,钢轨横贯东西,站房干净明亮,周边的农民经常在站台和候车室聚集,坐火车跑到城里去。在当地农民眼里,铁路职工是最威风的了,笔挺的制服,住房好,工资高,坐火车还不要钱,让他们羡慕死了。铁路职工的优越感在二十世纪80年代更是到了极致。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大潮的到来,中国人口开始大规模流动,一票难求的现象更加严重。铁路作为国家经济命脉的地位更加明显,想跟铁路人攀亲戚的大有人在。举个例子,我有个同学,只是在南宁到北京的列车上当餐车长,一个普通工人,当时竟娶了粮食局局长的女儿做老婆,让多少人嫉妒。正因为铁路的这种优势,那个年代我们都有深深的铁路情结。可是到了90年代,随着高速公路的发展,铁路的优势逐渐消失。直到近几年高铁时代的到来,铁路才又雄风再起。
作为铁路人,我们一直保留着独有的铁路语言风格,即铁路普通话,一方面,上班必须讲普通话,不懂的也要学。另一方面,因职工来自不同地方,同时走南闯北,就有了各地方言的混杂。加上毕竟固定生活在某一地域,更多地融入了本地方言。如在柳州的带有桂柳方言,叫“柳普”,在南宁的带有白话方言,叫“南普”,在广西形成了两大铁路语言体系。2004年我从柳州调到南宁,在铁路人聚居的白苍岭菜市买菜,一开口卖菜的人就知道我是从柳州铁路调来的,多么神奇!说起买菜,我又想起铁路人的另一特性,就是“小气”。铁路人虽然收入不低,但买东西总喜欢讨价还价,不舍得掏钱,铁路菜市的物价总是最便宜的。怪不得老百姓给铁路人起了个“铁公鸡”的外号,就是说铁路人貌似高大上有钱,却是一毛不拔,想来也不无道理,好像总是别人求铁路,铁路不求人。

侧岭高速路收费站

侧岭小学
四
因我从小在侧岭长大,所以,每当忆及故乡、家园,首当其冲,永远是老父亲在老站台挥舞小旗的动态,而在其背影之后,隐藏了我童年一切刻骨铭心的人事和场景。
记得火车站所处的地势较高,是从两边挖出的泥土抬高的,因此车站前后形成了两个较大的鱼塘,鱼塘的水是清澈的,可以游泳、洗衣,还养了不少鱼可供垂钓、捕捞。往西的不远处有一条小河,春夏的雨水季节可以看到流水潺潺,秋冬的枯水季节河床就干了。东南面有座山,我们叫它水塔山,机车用水和家庭饮用水都是从这座山上引来的。南面是侧岭生产队队部(现在是侧岭乡)所在地,也是侧岭唯一的集市,每周的一、四、七是赶圩日,是最热闹的日子,有时也进行陀螺比赛,这里的白裤瑶人玩陀螺的技艺是最精湛的。北面有一个自然村,旁边则是铁路职工办公和居住的地方,都是红砖起的平房,房子旁边辟有菜地,几乎每家每户都种菜、养鸡,甚至养猪,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这里之所以称为侧岭,当然与山有关,除了方圆几里是较大的平地外,它的周围都是山,有几座是独立的,甚是好看,更多的是山连着山,绵延不绝,气势磅礴,古树参天,我们经常到山里砍柴、采果,欣赏美景。
我有兄弟姐妹四人,均在侧岭出生并读完小学、初中(初中后来撤了)。姐姐和哥哥在红卫公社(现在的拔贡镇)读的高中,毕业后回侧岭插队。妹妹初中毕业后到金城江上了卫校。我的运气就没那么好,初中毕业恰逢红卫公社成立五七高中,由于成分不好,就被安置在这所半工半读的学校,根本学不到东西,我读了半年就不读了。但父母说我这么小不读书不行,于是送我到六甲铁中读初三,后又到宜山铁中读高中,这样我就赶上了高考,读了河池师专,与东西、凡一平成为校友。命运就此改变了。我在河池师专爱上了文学,发表了诗歌,并成功地从数学系转到中文系,担任了校报主编,还与凡一平创办了新笛文学社并任社长,凡一平是副社长。东西当时还没有名气,只是文学社的社员,我们毕业后他才当了副社长。在学校的优异表现,使我毕业后分到最好的铁路部门——柳州铁路公安局从事宣传工作,实现了我做铁路人的梦想。
虽然我离开侧岭较早,但毕竟老人住在那里,况且也离得不远,火车也较方便,因此时常回去,感受家的温暖。特别是工作后有了免票,几乎每个月都坐着绿皮火车回家。只是,父母亲退休离开侧岭后,我就很少回去了,尤其是铁路改线后,也难以找到回侧岭的理由。
五
火车改道,父亲和老站台一起退了休,但铁路却一直延伸着梦想。我固执地认为,铁路便是诗意栖居的地方。钢轨、车站、火车,还有这里的山水和乡土气息孕育了我的童年、少年,给我的生命注入了神奇的力量。记得小时候,我经常一个人在站台上发呆,望着延伸的铁路和远去的火车,猜想着火车将要去到的远方,梦想着有一天我也能坐上火车去到北京、上海,甚至更远的地方。侧岭毕竟太小了,容不下我的大志向,而轨道上的火车一直给我一种暗示:我要走出去,我一定能走出去,于是,我真的走出去了。因此侧岭是真正孕育我梦想、诗歌和远方的宝地。必须承认,我对侧岭的感情是比较复杂的,年轻时虚荣心较强,一心向往着大城市,一旦到了大城市工作,就不愿承认自己是小地方的了。随着年龄增大,才摆脱这种虚荣心,敢于承认自己是侧岭人了,且慢慢有了一种特殊情结,越来越怀念起这个小站来,摆也摆不开。不久前,听说侧岭通高速公路了,于是立即驱车前往。我快下高速时,被眼前的景色惊呆了:它变化太大了,我已无从辨认!我欣赏着美丽而陌生的一切,一边走一边问,终于找到了被废弃的火车站:道床还在,可已荒草萋萋,没有了铁轨;站房还在,可已房门紧闭,没有了人迹。然而,它的周边已盖起新房,水泥路修到村村户户,山峦俊美,草木青翠,稻谷飘香,花团锦簇,美不胜收,据说已成为当地有名的风景区。两种景象对比,难以言说的情绪填满心间。特别是那几座老站房,嵌入我脑海。于是我拿起笔,写下这首诗:
落日带走了天边的云霞
老站房站在黄昏里
像一块旧伤疤
更像一座孤独的坟
埋着我的旧情感
老站房的门紧闭

侧岭的大山

多彩侧岭
推不开,叫也不应答
只有门前的野花任性地开
恍如隔世的感觉
也许是我离开得太久,把它伤得太深
也许是我自作多情
它根本不在乎我的牵挂
老站房在自己的世界里
自在地活着
它后面的池塘、水塔、桃林
还有更远处,美得令人窒息的山峦
还和从前一样
火车的远去让它找到了永久的宁静
我一直怀着愧疚
以为是我忘了它
其实是它,早已把我遗忘
——《老站房》
是的,火车站消失了,老站房还在,它像我的老父亲,经历了世事沧桑,见证了黔桂铁路的历史。侧岭虽然没有了铁路,却又通了高速公路。我欣喜地看到,这里的风光更加绚丽迷人,人们的生活更加甜美如蜜,并不因我的惦记或忘怀受到丝毫影响。
我忽然发现,我对侧岭的爱竟是如此深情和深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