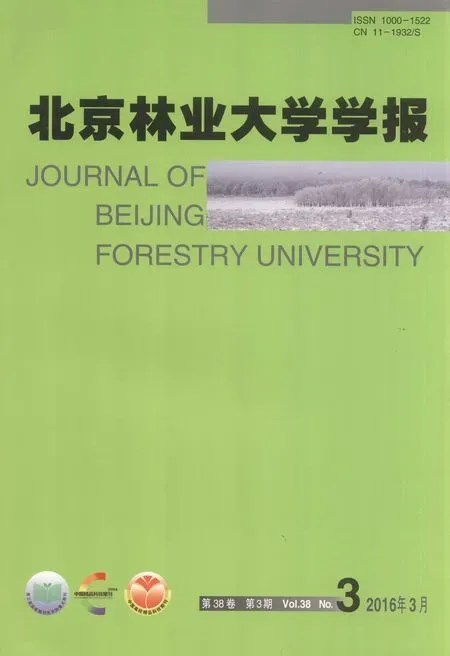注重乡村文化记忆保护与传承的景观设计研究
——以贵阳花溪大塘湿地景观设计为例
张蕾花,何嵩涛,徐英红,王甜甜,冯凤娇
(贵州大学林学院)
注重乡村文化记忆保护与传承的景观设计研究
——以贵阳花溪大塘湿地景观设计为例
张蕾花,何嵩涛,徐英红,王甜甜,冯凤娇
(贵州大学林学院)
文化记忆认同已成为城市现代化变迁中的世界性课题,拯救与活化普遍存在于保护名录之外的富有集体记忆、维系地方文化认同感的乡村场所,急需当下景观设计研究者的重视与研究。以与乡村生活区为邻的贵州省贵阳市大塘湿地景观设计项目为例,以文献研究和实地调查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总结出注重乡村文化记忆传承的“记—探—寻—悟—忆”的设计思路和方法,对乡村文化记忆的保护与传承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乡村文化记忆;保护与传承;景观设计
早在1964年5月,国际文化财产保护与修复研究中心(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the Preservation and Restoration of Cultural Property,简称ICCROM)在巴黎通过了关于历史文物保护的第一个国际宪章《国际保护与修复宪章》,其中首次提出关于乡村环境的文化保护:“文物古迹不仅包括单个建筑物,而且包括能够从中找出一种独特的文明、一种有意义的发展的城市或乡村环境。”[1]而强势的现代化打破了原来相对封闭的地方文化系统的发展,导致产生“表层文化”现象,大量现存的、蕴涵着社区情感与集体记忆的历史性场所正在遭受着前所未有的破坏[2],文化记忆认同已成为城市与乡村现代化变迁中的世界性课题。
有效延续人们的历史记忆与情感依赖,急需深层文化的召唤与回归。一方面,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加强了文化记忆多种形式的保护与传承;另一方面,处于保护名录之外的富有集体记忆、饱含地方文化认同感的乡村场所,却处于被遗忘的角落,相比官方认定的、纪念碑式的建筑遗产或者成规模的历史地段来说,地方性的记忆场所更具普遍性、多样性,更贴近百姓的社会生活与文化情感[3]。这种以乡村文化为主体的记忆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断增加的时间价值和渗透的人文精神,构成了乡村的精神和灵魂,不仅是个体在所属文化群体与其场域内形成归属感的前提,更是获得、保持、创新自身文化的前提,理应唤起学术界对这类文化遗存场所的重视。
关于“文化记忆”,扬·阿斯曼在《集体记忆与文化认同》一文中对其进行了界定:它是每个社会和时代所特有的重新使用的全部文字材料、图片和礼仪仪式的总和[4]。此外,扬·阿斯曼在《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一文中,通过对交往记忆和文化记忆的对比,对“文化记忆”进行了详细总结:以神话传说和发生在绝对过去的事件为内容,以被创建的、高度成型的、庆典仪式性的节日或社会交往为形式,并以文字、图像、舞蹈等媒介进行传统的、象征性的编码及展演的总和[5]。
而由于“乡村文化记忆传承”的景观研究方面的文献相对较少,目前还没有针对“乡村文化记忆”的具体概念,笔者通过大量的资料研究暂给其一个定义:“乡村集体中关于过去共有的并将一致性和独特性的意识建立其上的知识传统,包括物质载体和精神载体两个层面。”笔者于2014年12月主持设计了贵州省贵阳花溪大塘湿地景观设计项目,本文以此为例,总结注重乡村文化记忆传承的景观设计思路和方法。
一、“记”——文化记忆探源
花溪大塘湿地位于贵阳市花溪区政府东3 km的把火村(咸丰年间《贵阳府志》用此名[6])内(见图1[7]),两面山林一面墓林,湿地之水源自两山之间的地下泉水,把火村民国初曾设置大塘乡[6],花溪大塘湿地因此得名。该湿地面积4万m2,位于清溪路东1.1 km、花溪福泽陵墓园南220m处。北邻把火村,南邻大塘寨。西北方向与花溪公园隔路相望。大塘湿地水位常年稳定,犹如一首老歌,静默流淌,情深意长,滋润着把火村全村552户百姓,1 600多人。
无文字文化中,文化记忆并不是单一地附着在文本上,还可以附着在舞蹈、竞赛、仪式、面具、图像、韵律、乐曲、饮食、空间和地点、服饰装扮、文身、饰物、武器等非文本形式之上,群体通过这种文本形式或非文本形式对自我认知进行现实化和确认[5]。而如今的与生活区为邻的花溪大塘湿地所在地——把火村,群体生活方式是少数民族大杂居小聚居,以苗族和布依族为主,其中苗族占少数民族总人口的90%。把火村在空间、地点、乐曲、服饰、饰物、舞蹈等方面给予了湿地丰厚的文化底蕴和内涵,对乡村文化记忆的保护与传承方面的研究起到很好的基奠作用,所以把火村整体文化记忆探寻集中表现在如下3个方面。
(一)民族文化探寻——原始的图腾崇拜与鲜活的仪式场所
首先,远古时代,少数民族对鱼龙文化有所崇拜,是最早的精神文化图腾。地位上,它们都作为司雨之神而受崇拜祭祀;文化内涵上,鱼和龙同为多子之物,都是古代民间乞子、多福之拜物。当今苗族的刺绣、蜡染、银饰等即有以龙凤、鱼为崇拜物的主题样式(见图2[8]、3、4[9]、5)。
其次,从苗族服饰图案符号所代表的文化内涵看,苗族服饰距今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他们将本民族的认同世代口传身授,将流传千年的故事、先民居住的城池、迁徙漂泊的路线等点滴一针一线绣进衣冠服饰,世代“穿”承,永不忘怀。另一方面,从总体来看,不仅保持着中国民间的织、绣、挑、染的传统工艺技法,还穿插使用其他的工艺手法,如挑中带绣,或染中带绣,又或织绣结合,因而,苗族服饰被誉为“无字史书”和穿在身上的“史书”。现今把火村的苗族服式中亦有不同程度的展现(见图2[8]、4[9]、6[10])。
除此以外,《苗族古歌》是苗族聚居区流传下来的唯一非宗教典籍传世记史诗。据史料记载,古老的苗族先民把蝴蝶妈妈——枫香树看成是万物的始祖(见图6[10]),因苗族自古无文字,人们的婚姻恋爱等契约无法记载,便选枫树刻木为证,即让祖先为证。同时从《枫树歌》的记述看,苗族也将枫树视为一种神灵信仰,如以枫树为中柱,就象征祖先与家人同在,保佑后代兴旺发达,平安康乐;田坎边栽种枫树,以求五谷丰登;村寨周围遍植枫树,以保佑全寨安宁等,所以,村民每到新的地方必须在田坎、村寨周围种植枫香树。而现今把火村不仅暗藏古老神秘的枫树神话,也有鲜活的实物代表——湿地南侧的枫香古树,不仅有着百年历史,更重要的是在诸多变迁中较好地保存下来,还伴有藤枝缠绕(见图7、8),有“藤缠树,连理枝”之说,象征并保佑着花溪把火村“男女喜结连理”的美好姻缘[11],并有许多青年在此许愿。
(二)山水文化探寻——神秘的意境传说与温润的自然禀赋
花溪大塘湿地西北、东南临山,如同聚宝盆地,呼吸自然之气;水域源自山下泉水,水位常年稳定。远望:入口西北方向700m处,两山夹道(见图9),犹如龙门,初道窄,行70 m,豁然开朗。渐观:渐行约300m,近现土地屋舍,时有灰鹤起舞;东北又行400余m,阡陌交通,野鸭嬉戏,湿地隐现。近寻:西北紧邻花溪福泽陵园(见图10),梵音袅绕,檀香弥漫的衬托,更能体会到大塘湿地独有的美。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视线处理上,把火村注重空间组织作用,而在选址中,则更偏好隐藏和屏蔽性结构。这也较好地证明了人们亲近山水、自然的同时,也有一定的景观吉凶意识。另外,由于把火村位于苗岭中部“大成山脉”东侧的盆地中,而“大成山脉”是贵州省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创新的重要基地,所以把火村本身就富有浓厚的文化氛围。
(三)生活文化探寻——宁静的田园气息与紧密的家族邻里
湿地早期水质清冽,盛产鲤鱼。当地居民多以渔业为生。湿地边缘乡土植被茂盛,常绿树、落叶树兼备,马尾松姿态古奇,刺楸、构树整体粗犷而充满野趣,夏季漫山的杨梅如披了紫霞一般,湿地与林坡交界处蜿蜒的小道若隐若现之余,还随时伴有野鸭嬉戏、灰鹤起舞的惊喜。时有追寻《桃花源记》之感,又有《桃花源记》不及之处……其潜在的美纯粹、宁静,无时无刻不渗透着原始本真、震撼人心的力量。
同时,把火村内少数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生活方式及文化差异,使生产技能、生活饮食习惯、风俗、语言信仰等方面展现出一定的传统和文化差异,村落中各民族关系由最初的建构、相继的发展变化,到最后的民族关系经验积累、建构与维护,展现出较为和谐、融洽、团结、友好、协助、稳定的家族邻里关系。
二、“探”——文化记忆的“矛盾”认知
笔者亲临现场,为把火村淳朴静谧的自然人文气息感动的同时,也时时刻刻感受到场所内部面容时有伤痕、略显憔悴的身影:湿地岸边时常伴随部分坍塌情况,其水质亦常年受到生活污水及农药残留等的污染,并出现部分断流;场址周边有残破的建筑物和其他构筑物,空间植物单一,略显孤寂。
以Massey等为代表的一些地理学家认为,场所的独特性不仅仅源自场所内部,也反映在它和外界的独特联系中[12]。将大塘湿地置于内外环境对比中,不难发现,场所独有的特殊性恰恰促成了以下3大矛盾的形成。
(一)“静”与“寂”的矛盾
一方面,大塘湿地作为花溪把火村唯一的湿地景观,有一份不同于市中心湿地公园的远离闹市的“静”,又有一份家有良田菜畦、空漫鸟语花香的安宁与和乐;另一方面,该场地正北及西北方向紧邻花溪福泽陵园,其庄重、肃穆的墓园氛围,给场地闲适、纯粹的自然特质提出了挑战。如何更好地展现场地本身的闲适与宁静,而不被福泽陵园的孤寂与墓气掩盖?
(二)“悠”与“游”的冲突
一方面,场地有其本身的闲适与宁静,时有灰鹤起舞,又有野鸭嬉戏;另一方面,随着游人驻足停留日渐增多,难免会受到开发的影响。如何使游人在得到放松、惬意体验的同时,而保持场地不被开发破坏,仍能较大程度地保持原有的自然与本真?
(三)“根”与“枝”的疏离
把火村有汉族和苗族、布依族等少数民族,虽然少数民族人数居多,但少数民族文化渐被汉化和疏离,如何重拾本族文化,有效帮助少数民族文化走向回归,是另一个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
总之,面对诸多矛盾与冲突,如何在符合自然规律、满足社会功能、遵循生态原则的同时,更艺术性地解决文化记忆的传承问题,我国建筑学家冯纪忠先生给出了答案:“文化因素,使环境超越自身的物质结构和基质,形成一种潜在的价值。”[13]这也恰恰成为解决场地内外环境矛盾冲突的坚实后盾和有力突破口。
三、“寻”——传承原则与思想
针对场地的诸多挑战,在尽量不破坏原场址的基础上,如何化“忧”为“喜”,以更好的姿态传承和发展原有的文化记忆。诺伯格·舒尔茨曾提出“场所的变迁不可避免,而回应的方式就是创造性的再诠释”[14]。因此,建构“新”的文化记忆成为本研究最核心的问题。
而创造性的再诠释需要谨慎对待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去做,可以保证能够有效去除表层符号堆砌等自然文化入侵方式,多留一些自然遗产?阿尔多·罗西曾强调,地域历史和记忆对于已知与未来环境具有无可取代的重要意义,如此才能留住自然与文化历史的根,才能在有限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地挖掘、提炼,进而最终结成文化精华,这才是“文化记忆”传承的推动力与核心价值。而地域历史和记忆又根植于生活,生活化的景观内容是文化景观里最真实、接地气,最具活力、且有时效的部分。因此寻求生活化的景观不仅可以巧妙地融合自然,亦可以彰显对自然的敬畏和人文关怀。所以对地域历史和记忆的寻求点,不仅要关注当下风景的使用性,更要关注未来的可持续性,而前者更多关注景观的情感氛围,后者相应更关注思想意义,两者都是“文化记忆”保护与传承的关键点。如此这样才能经受住现代人和未来人们的检验。
基于此,笔者认为设计应该遵守以自然为根,以人性化需求为本,以文化为魂的原则与思想。原场址是寻求文化记忆的见证,也是构建“新”文化记忆最好的蓝本。所以,场址调研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以对原住居民探访为主,对场地早期风貌有所总结;另一方面,调查场址现有风貌。这两方面分别在自然、人与文化之间有不同程度的展现,只有尊重自然基理,以人性化需求为本,以场地原有的文化为魂,在“踏寻”原有文化记忆足迹的同时,才能进一步获得相应的感知与体悟。
四、“悟”——建构新乡村文化记忆
笔者通过运用更多关注景观情感氛围和思想意义的“情景化景观”表达方式,将抽象艺术作为形式语言,在情感和思想上,通过艺术形式去表达对该场地的理解。以更忠实于场地本真的态度和方式去解决问题、创造生活。
(一)场地基理之“悟”——鲤鱼形
一方面,结合上述文中所述的传承原则和思想,该场地以自然“天地”为根,以人性化需求为本,以文化为魂,对应如下:①天地——湿地现有自然水域、沼泽地、人工池塘、农田、桃花林、湿地植物及建筑等土地类型(见图11)。②人——湿地早期水质清冽,且盛产鲤鱼。人们多以发展渔业为生。③“神”——少数民族早期对“鱼”有所崇拜(见图3、4[9]、5)。另一方面,笔者对现有场地进行地形绘制时(见图12),发现地形基理形似鲤鱼,如鳞、背鳍、胸鳍、腹鳍和尾鳍等意象凸显。这与当地早期盛产鲤鱼、渔业发达及鱼的图腾崇拜关系紧密(见图4),正是构建新文化记忆的源泉。
(二)把火村入口之“悟”——龙门
场地入口西北方向700m处,两山夹道,犹如龙门,初行窄而后开朗(见图9)。以把火村入口为界,入口外展现的更多为喧闹的城市生活场景,入口内有一份不同于市中心湿地公园的远离闹市的“静”,又有一份家有良田菜畦、空漫鸟语花香的安宁与和乐。更有两条盘龙似的山脊作为入口屏障,一动一静之间,恰有入世出世之感。
(三)场地功能之“悟”——休憩
大塘湿地作为花溪把火村唯一一个湿地场所,不仅是周边村民日常休息的地方,清明时节,也是去福泽园祭祖拜佛的香客驻足停留之地。由此,更加深刻地彰显了场地本有的宁静气质:人们不仅可让身体得到短暂休憩,更可以深刻表达内心的感恩与释怀。
(四)场地气质之“悟”——禅意
该场地正北及西北方向紧邻花溪福泽陵园,作为高原祭祖拜佛圣地,整个园区重峦叠嶂、梵音袅绕,檀香弥漫、绿树成荫、鸟语花香的氛围,更为大塘湿地增添了一份独有的静谧,也为人们带来一份更近乎修心的体验之美。
基于此,结合对把火村整体文化记忆探寻的3个方面,即具有原始图腾崇拜与鲜活的仪式场所的民族文化,具有神秘意境与自然禀赋的山水文化和充满田园气息与友好的家族邻里关系的生活文化,笔者探寻到村内集中表达的生活方式和人生态度是对自然、静谧、和谐的向往与需求,由此笔者确定了“鲤鱼跃龙门后的憩与禅”的主题定位(见图13)。这不仅是苗族对古老始祖文化保平安、祈幸福的精神寄托,而且也最大程度地符合大塘湿地景观独有的静谧气质,有利于以立体的方式展现并传承当地特有的文化记忆。
五、“忆”——新乡村文化记忆的升华
(一)山水的禅意体悟
侧线处的一池加鱼脊处的三山(景山、镜山、净山)(见图14),位于一池“大塘流鲤”(见图14)的较高处,沿鲤鱼感觉神经最敏感的侧线部位由西向东依次排列,是游人阶段性感官体验(豁然—渐佳—迷离—曲幽)(见图15)驻足之处。
(二)道路的禅意体悟
胸鳍、背鳍、腹鳍、臀鳍、尾鳍处——鳍形思步道,作为湿地内部唯一游憩道,为尽量保护湿地内部环境,场地内没有设车行道。木栈道时而接近草地,时而穿越林中,又或濒临水域,或跨越湿地曲幽,尾鳍处的思步道对面即为瀑布景观——九天银河,山水由上而下,恰如大塘之水天上来,又如锂鱼跃龙门后,“神龙”摆尾,重新潜入湿地的特写镜头。其景观体验由东向西依次为:曲幽—迷离—渐佳—豁然,与上述“一池三山”的景观体验完全相反,于不经意间完成了人世顿悟的感官体验。同时与大塘回廊以及场地原有的自然小道构成完整的步行系统(见图16~21)。
(三)建筑景观的文化追忆——点睛之“风荷楼”
风荷楼位于景山处,幽曲之间,踏级而上,或偶遇农场,或渐入佳境,入口平淡隐现,与道路喧闹隔离(见图22);同时以莲花为山形基底,与佛意相通,寓意风调雨顺,因荷谐音为“合”与“和”,寓意少数民族大融合及生活和睦和美,是苗族始祖文化的追忆与传承。其建筑样式源于苗族独有的民居建筑——吊脚楼,是在对传统文化挖掘、传承的基础上再创新。作为湿地“鲤鱼”的点睛之笔,也是湿地的核心建筑景观,不仅可眺望湿地风景,更具备文史馆藏、交流功能,是村民和游客举行仪式等集体文化活动场所(见图23),有效保证了仪式在空间上的群体聚合性。
(四)小品与植被景观的文化追忆——腹鳍处的古枫香及如意亭
如意亭与古树枫香对望,此处的枫香古树本身不仅有着数百年历史,还伴有藤枝缠绕,有“藤缠树,连理枝”之说,象征“男女喜结连理”的美好姻缘。人们在品味农家乡野之余,坐在如意亭下,回望枫香古树,不仅可以随时寻味祈祷,还能融入到传统民俗氛围和活动中。
六、结 论
本方案在完全保留原湿地的绿色和蓝色基底的基础上,凝练出鱼型概念:沿鱼侧线和鱼脊,布置一池三山,沿胸鳍、背鳍、腹鳍、臀鳍、尾鳍有效提炼出鳍形思步道,并将鱼首作为整个场地的文化活动中心,而鱼目处布置湿地的核心建筑景观,也是构建把火村新文化记忆的核心景观载体,起点睛之用。整体用艺术的形式巧妙解决了场地本身矛盾冲突及根本的文化记忆传承问题。并且以富有民族特色的图腾——“鱼”为文化核心,通过现实语境里的再诠释,使历史传统精神内涵得到延续和发展的同时,也建构了该地特有的新的文化记忆。与此同时,通过对其他仪式和神话的调查、保存和传承,可以进一步辅助巩固并传承集体认同,并由此保证了文化意义上认同的再生产,即新文化记忆的建构与升华。籍此方案,探索注重“传承乡村文化记忆”的景观设计课题的方向。大塘湿地不仅是紧邻乡村生活区的文化聚集场所,同时因其三面山林环抱的自然特质,并富于少数民族早期鱼龙文化、苗族始祖文化及佛教文化的精神,所以它也是人类在森林文化生活传承方面的一个微观展现。而当今林业发展的研究以森林功能、社会功能、生态功能为主,对其文化和精神功能方面涉及较少,鉴于此,笔者希望在森林文化和精神功能表达与传承方面,为林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一定程度的借鉴。
[1] 朱蓉,吴尧.城市·记忆·形态:心理学与社会学视维中的历史文化保护与发展[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3.
[2] 陆邵明.记忆场所: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新趋势[C]∥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广西壮族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人民政府,中国城市规划学会.2012城市发展与规划大会论文集.北京:《城市发展研究》编辑部,2012:8.
[3] 陆邵明.拯救记忆场所建构文化认同[N].人民日报,2012-04-12(23).
[4] 姚继中,聂宁.日本文化记忆场研究之发轫[J].外国语文,2013(6):13-19.
[5] 扬·阿斯曼.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M].金寿福,黄晓晨,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6] 花溪区地方志编撰委员会.贵阳市花溪区志[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7.
[7] 百度地图.贵州把火村[EB/OL].[2016-01-19].http://map. baidu.com/?newmap=1&ie=utf-8&s=s%26wd%3D&qq-pfto=pcqq.c2c.
[8] 中国文化产业艺术网.苗族刺绣幻化多彩[EB/OL].[2016-01-19].http://www.cnwhtv.cn/2012/0229/6045.html.
[9] 中国行业信息网.贵州苗族特色蜡染[EB/OL].[2016-01-19].http://www.cnlinfo.net/info/56735390.htm.
[10] 蝴蝶妈妈与苗族起源[EB/OL].[2015-12-27].http://blog. sina.com.cn/s/blog_698b430101012g5b.html.
[11] 杨正伟.试论苗族始祖神话与图腾[J].贵州民族研究,1985(1):51-59.
[12] MASSEY D B,JESSP.Place in theworld?places,cultures and globalization[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1-4.
[13] 冯纪忠,王伯伟.旧城改建中环境文化因素的价值和地位[J].建筑学报,1987(10):44.
[14] 王燕飞.大学校园景观与场所精神[D].南京:南京林业大学,2009.
(责任编辑 孔 艳)
Landscape Design Em phasizing the 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 of Rural Culture M emory: Taking the Design of Datang W etland in Huaxi,Guiyang as an Exam ple
ZHANG Lei-hua,HE Song-tao,XU Ying-hong,WANG Tian-tian,FENG Feng-jiao
(College of Forestry,Guizhou University,Guiyang,550025,P.R.China)
The identity of culture memory has become a global issue in the transition of urban modernization,saving and activating the rural areas that are rich with collective memories and strong emotional attachments to ordinary people but normally not registered in the protection list of cultural relics,is badly in need of attention and research from the current landscape designers and researchers. Taking the landscape design project of Datang Wetland neighboring of a countryside living area in Guiyang City of Guizhou Province as an example,and combining literature research with field investigation and practice,this paper summarized the design ideas and methods emphasizing the inheritance of rural culture memory,i.e.,a loop of from“remembering to exploring to looking for to realizing and lastly back to remembering”,owing a certain
ignificance for the 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 of rural culturememory.
rural culturememory;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landscape design
TU986.2
A
1671-6116(2016)-03-0021-08
10.13931/j.cnki.bjfuss.2016004
2016-02-19
张蕾花,硕士。主要研究方向:景观设计实践与理论。Email:zhangleihua@126.com 地址:550025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贵州大学林学院。
责任作者:何嵩涛,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山地景观规划与设计。Email:hesongtao@126.com 地址:550025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贵州大学林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