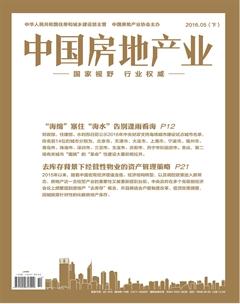胸怀丘壑 情连古今



1、1978年,您入文化部中国画创作组,当时中国画名家荟萃一堂,有黄胄、李苦禅、陆俨少、何海霞等先生,您对哪一位印象最为深刻,又受何启发?
1978年拨乱反正,浩劫之余,剩下的一些老画家就成了宝贝。当时,我们国家跟许多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在驻各国的大使馆中需要展示有中国特色的艺术品。文化部就召集一些老画家,集合在北京友谊宾馆进行创作。当时很多老画家已经接近风烛残年,身体都不太好了。组织这个事情的人是中央美院附中的老校长丁井文,他跟齐白石等一批老画家都很熟悉。当时丁校长在拟定人员名单,听人介绍并看到我的画之后就把我找去,直接留在了中国画创作组。那时候,我还在一个县级市的文化馆。进了这个组之后,就开始接触了这些老画家,看可染先生给外交部画井冈山大画。能看到可染先生画那么大画的恐怕也没几个人,因为先生画画不喜欢别人打搅。
当时像苦老(李苦禅)、何老(何海霞)等老艺术家对年轻画家都是循循善诱。何老是长安画派的中坚人物,那时我跟他住在一个套间里,可以说朝夕相对,所以聆听他的教诲比较多。何老强调中国画不论鉴赏还是创作,应该就讲四个字“笔精墨妙”,即笔法精到,墨法奇妙。他最早是大风堂的传人,在他很年轻的时候就拜到了张大千的门下。大千先生对他耳提面命,临习宋元,传统根基扎实。他跟我说年轻人要多下功夫,吃透宋元绘画艺术。现在回头看看,感觉确实大有深意。所谓文脉和技法的传承,都是有源有流。某一个时候的源发展成下一个地方的流。下一个流铺开太大了,往往被摊薄,稀释,这个时候还得回到源头上来,疏浚河道,才能出现新的流。
我觉得古人有两句诗可以做山水画的规则。一个是石涛说的“搜尽奇峰打草稿”,意识是行遍天下,纵览山川,使之内营于心;还有一句是杜甫的“转益多师是我师”,也就是说在技法上,要向古人多学习。请益的师傅越多,那你的本事也就越大。这两个,还是师造化、师古人,画家自己的境界决定山水的境界,一定要有一个丘壑内营的过程。
2、请刘老师谈谈您对中国文化与书画的认识?
文化其实不是简单的那点字句,而是字句里面贯穿流淌着的一种精神,这个精神滋养了一代又一代人。比如说,一谈到民族氣节,我们就会想到文天祥,想起《正气歌》;谈到抵御外侮,就会想到岳飞,想起《满江红》。这些已经完全是超越表象的东西了,变成一种真正内在的有血有肉的可以充当民族脊梁的东西。它会有一个实指性,就是说它在传承过程中不像水流那样,匀速的,好像是无止的。它更像珠串那样颗粒状的珠圆玉润,但是一脉相承,必须理解到这样,才能增加文化传承的自觉性。在文化的传承当中,特别是像书画这一类最具视觉因素。书画艺术发祥既早,历代也比较辉煌,即使是少数民族统治期间,统治者也在努力学习汉文化。
书画在古代不只是作为一些艺术上的追求,它在文人的笔墨生涯里实际是抒情消遣,体现性灵。作品出来主要是博会心者一笑,不是为了市场价值,也没有想着拿这个来传世。对这些文人来说,诗书画包括篆刻都是小道,但是小道也可以载道。“载道”这个词是贯穿于中国文化一切活动核心的一个词。文人尤其是用来载道的,艺术上的探索创作是载道的,自己的言行无不要求载道,最终还是要归载到大道上的。中国文化的核心是非常理性的,关乎自然、与人性的。中华民族之所以有凝聚力,不是因为武力,也不是因为地缘,而是因为文化。
3、人们说书画有好多境界,如景物之境、笔墨之境、人文之境。您也曾说,书画最高境界在于精神意境。我觉得这跟人文之境也是不约而同的。您觉得要达到这种境界应做何努力呢?
关于这个三境界说,我觉得还是不够准确。绘画应该先有形似,无论你是画花鸟、动物、山水、人,首先都要在这个形上找东西。第一个境界就是“形似”,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第二是境界是“神似”,在表面的东西里找内在的特质。第三就是“意韵”,神还是附着于某一个形上。从形神这两个方面再把它抽离出来,造成一个画家独有的意境,在风格上突出独有的韵致。我觉得这三个境界可能更恰当一些。
古人讲,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都是说必要的历练。但并不是说,这么做了,就能达到我们要求的那个高度,还是在内心要有一个真正的修炼。关于内在的修炼,儒家讲日三省吾身,养浩然之气。一个是反躬自省,一个是克制自己的贪念,这需要持之以恒的毅力。
作为画家要心怀古今,有很强的历史感,然后在现实的当下,有比较强的博爱精神。有了这种精神,你去画花鸟,你的感情就能深入到一枝一叶,一鹊一兔,就像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所言:“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这样放大的感情会更加饱满和充沛,才更容易感染别人。
4、您觉得近百年来中国画的发展轨迹是怎样的?
1840年以后,中国画面临着社会形态的转变,买家和欣赏习惯都有所不同,这在上海和广州尤为突出。北京比较传统,满清官僚仍居统治地位,文人士夫以能和这些人交往为荣,文人墨客也都立志于加入这个圈子。
当时的上海已经由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县城,发展成为英日法等国的租借地。资本家在黄浦江边开辟了大片的土地,建起了高楼大厦,称为“十里洋场”。在那里有治外法权,有洋人的《字西林报》,华人的《申报》等等,人们享有一定的言论自由,商业气息浓厚,整个满清统治已经完全瘫痪,大家不再追求官本位,而是热衷于学习西方语言和文化。就是在这样一个氛围下产生了海上画派,像任伯年、虚谷及后来的吴昌硕都是海派的主要代表人物。
海派是当时最活跃和成就最高的画派,其绘画行情很好。以任伯年为例,每年书画收入不仅可以满足其子科举仕途之路,也能使自己生活宽裕。许多广州商人到上海开店,店铺里都想悬挂任伯年的画。海派画风受到西方绘画的影响,像任伯年的画,有点西洋水彩的味道,从花卉的写生能看出西洋或东洋的那种神韵来。
不能不说起海上画派最后的大家吴昌硕,他是划时代的画家,他见证了满清末年到民国的初年的风风雨雨。他更是把书和画结合起来,笔致从写猎碣碑到把任伯年花卉画法写意化,然后发展成为独具风格的红花墨叶。当时这一风格非常受日本人推崇,凡是来中国的日本人必到上海求吴昌硕的作品。从这些年拍卖就可看出,日本回流的吴昌硕作品不在少数。
中国画的发可以大致上可分上古,中古,近古以及近代。上古书画同源,从甲骨文即可看出,绘画近乎图案,中古绘画已脱离工艺和实用,线条(即笔)色彩并用,发展出工整谨严的工笔画风,如顾恺之、阎立本、李昭道的作品。在中古的下半期,从唐王维开始,创作了一种不假丹青,纯用水墨的画法,可谓文人画始祖,之后宋苏轼、文仝、梁楷、石恪等继承和发展了这一路画风,文人画始大兴,自元四家更为彪炳一代。明以后的脉络就写意而言是青藤白阳,之后发展到八大石涛,入清后发展到八怪,进而是海上画派。海上画派之后是吴昌硕,他的红花墨叶直接影响到齐白石。齐白石未定居北京之前,画风比较冷逸,不受北京人喜欢。在陈师曾的建议下开始研究吴昌硕的画,自创新风。所以,从花鸟来讲这个脉络就很清楚,也就是正脉。所谓“正脉“是指果实硕大,旁枝众多,其影响范围从长江过黄河到北京,遍布了半个中国。在那时京派很多画家都受到齐白石的影响,甚至王雪涛的小写意也是如此。
文人画的发展以八大石涛作为一个高峰,其格调秀逸,冷峻,而继之以起的吴昌硕画风为之一变,雅健雄深,泼辣,酣畅。而恰恰这样的对比和差异才使中国画文人大写意的传承,落到了吴昌硕的肩上。他书画合一的精髓、诗书画三绝的特性传承到齐白石。齐白石的草虫、鱼虾、写生的农具都是前人所没有的。然后再到苦老,这都是吴昌硕,齐白石,一脉传下来的,应该说从富丽堂皇到笔墨齐整,再到笔墨消散,到笔墨简练概括,是这么一路过来的。当然这些东西可能有周期,但是我们还没有看到下一个轮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