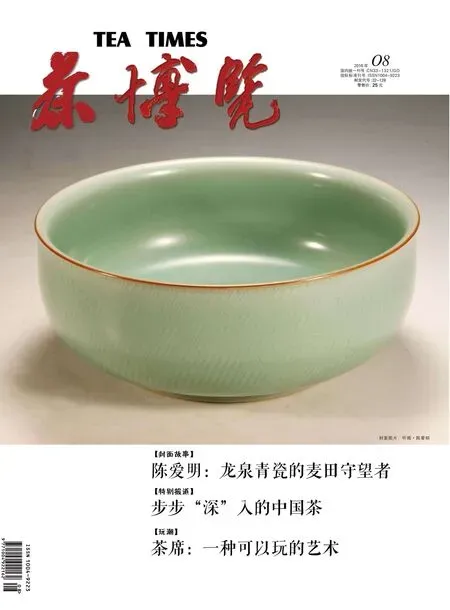茶在罗霄 客家庭院上犹茶
洪漠如
茶在罗霄客家庭院上犹茶
洪漠如
也许,在大多数人内心的茶叶地图上很难出现“上犹”这个地方,但我们还是踏入了这块飘荡着茶香的文化胜地。对于茶,这块土地从来都没有过多的话语去修饰,哪怕它是历史上客家人衣冠南渡的最终定居地。茶,伴随着先祖迁徙的步伐一同在这里停留。即便关于茶的态度已经因年岁悠远而失传,可是透过客家门楣,我们读懂了他们缅怀的高度,似乎尚能嗅到那股久违的茶香。
客家人的漫长迁徙流变,在血液中形成了好客的基因,特别是对于远道而来的客人,那种追溯同一种步调感的共鸣会激发心中留存的乡土故园情。时间久了,也许这种情绪会被稀释,但是他们会把很多情绪凝练在自己家族的门楣之上。那些对于家族历史并不过分的攀附成为鼓励世代子弟的文化象征。因为它既传承着祖先追求仕途的励志精神,同时也透露着耕读传家的志趣。出世入世之间并没有太多的纠葛,一股洒脱的风流名仕气息不经意间流露了出来。
我们在上犹,看到很多客家门楣,也许并不直接与茶相关,可门楣背后指向的人却与茶有莫大的关系。例如欧阳修,其后人在同宗认祖时于门楣之上镌刻着“夜读传芳”——把我们带入到欧阳修的青年时代。由于家境贫寒,欧阳修只有依靠自己的勤奋努力,才能求取功名入朝为官。这一点,是古代所有读书人恒久的主题追求。欧阳修的一生,曾官至枢密副使、参知政事乃至兵部尚书,具备出将入相的能力,可一生依然仕途坎坷。在“庆历新政”中,也曾试图凭借自己的一腔热血为天下谋利,可最终未能如愿。诚如其被贬滁州时在《醉翁亭记》中所言:“醉翁之意不在酒”。步入老年,时常感叹:“吾年向老世味薄,所好未衰惟饮茶。”
《醉翁亭记》确实是欧阳修的代表作,但他自言“饮少辄醉”,可见酒量也不一定大。醉翁亭从某种意义上把欧阳修与“酒”做了紧密的横向联系,但终其一生,我们透过他的笔墨之间却更多的感受到了茶的气息。特别是在晚年所写的《双井茶》一诗中提及:“宝云日注非不精,争新弃旧世人情。”一杯茶里,洞穿了世情冷暖。茶,成为他晚年的陪伴。一杯茶汤,温润着他的喉吻,也开始过滤掉他脑海中过于写意的诗情。于是,坦率地评论道:“唐人‘姑苏台下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说者亦云句则佳矣,其如三更不是打钟时。”在言与意中,有了自己的主张,于是《六一诗话》诞生了。《六一诗话》是他生命中最后一部作品,把人生的思考凝聚在茶与诗中,洞察世情。
一块门楣,浓缩着一段史话。让我们在客家人衣冠南渡的步伐中也能感受到与茶的那些丝缕关联。当然,这种关联只停留于文化底色上,让上犹具备了品咂茶汤滋味的潜能。
在上犹,产茶以绿茶为主,主要集中在五指峰、梅岭、犹石嶂以及陡水湖库区,属于罗霄山脉中段丘陵区。近年来,因为很多触及社会整体蓝图的构思都寄托在了茶产业上,于是我们看到了每年都在不断增长的茶园种植面积。在上犹,茶园大多连接着一个具备综合功能的庄园。我们抵达上犹的第一天晚上,就入住在陡水湖库区边缘的一家茶庄园。老板是遂川人,做茶有几十年时间了,熟悉罗霄山脉中的物候情况。在自己的庄园中,大面积引种了安吉白茶。安吉白茶氨基酸含量高,口感不苦不涩,一度成为市场的新宠。市场的手推动着这个品种在罗霄山腹地安家落户。庄园老板说自己是客家人,他与茶一样,历经流变,最终选择了留在罗霄山。这一片山,接纳了他的世家以及他的茶。
我们在上犹,很少看到当地的群体品种,在梅岭坑,大面积种植着福鼎白茶,福鼎白品种优势突出,芽头肥壮,上犹人将其采摘加工成芽头绿茶,名叫“上犹剑绿”,玻璃杯中,根根挺立,恰如寒光闪烁的宝剑。
上犹这片土地适合种植茶叶,这个问题早在2012年春天陈宗懋院士造访上犹时都已提及:上犹茶产业发展潜力巨大。我们沿着上犹县境内的五指峰、梅岭坑一线考察,所看到的土壤结构以酸性结晶岩类为主,其中花岗岩、花岗斑岩占了绝大多数。从西北部的罗霄山脉中段起,分两支向东南、西南延伸,主要分布在中低山的五指峰、营前、水岩、紫阳、梅水、社溪、东山等乡镇。风化物颗粒粗糙,含石英砂粒和砾石较多,形成酸性结晶岩类红壤、麻石泥土和麻沙泥田。与此同时,在低丘陵地带主要分布着紫色砂页岩类有紫色砂砾岩、紫色砂岩、紫色页岩和紫色泥岩等。这些,都是适宜茶树生长的土壤环境。
也许上犹这片土地原本就是用来接纳漂泊的灵魂,生长在上犹的茶与当地客家人一样,并没有表现出丝毫水土不服的迹象。甚至在上犹的茶园,被客家人精心打造,成为了集合茶旅的文化体验中心。

面对上犹,只要我们稍作留意就不难发现,很多有关客家人的典籍中都记述着梅岭竹溪、枫岸蓼堤的存在。多少年来,迁入上犹的客家人,历经数辈披荆开拓,到南唐建县时,都已然出现了“渔水樵山、野媚川晴”的景象,若干村庄“屋宇如鳞”、“夜琴乍起”。历代躲避战乱的客家人迁居于此,结庐丛林、编竹为篱、砍树作窗、割茅当瓦。当生活安定下来,一切又归于平静,他们并没有因为这种安定而数典忘祖。在竖起的门楣中设定了家族使命,更多的家族习性以记忆为依凭渐次回归。那些名门望族的后人,不管转徙了多远的距离,经历了多少沧桑巨变,血液中遗传的志趣在生活稍事安定后便开始有了诉求。茶,便是这种诉求之一。如今,上犹县境内的茶叶种植面积已然超过10万亩,可他们的消费主体依然是沿着方圆周遭扩散。
茶,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山山水水孕育的风物人情无时无刻不在热情迎接着山外涉足的远客。当我们抵达,当地客家人把我们带入他们的庭院,泡上今年春天制作的上犹绿茶,我们静静地感受着舌尖的试探,窗外的山水像一幅旷世的画作,山鸟飞过,鱼翔潜底,谁也没有意识到,这也许是事隔千年的同宗会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