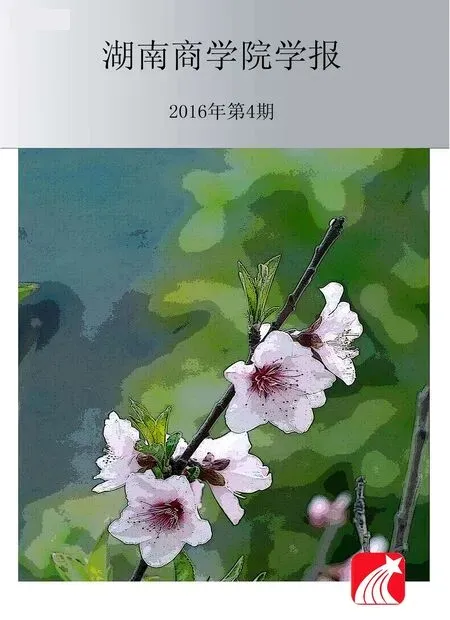温州民间借贷研究:1978~2015年
陈飞翔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广东广州510300)
温州民间借贷研究:1978~2015年
陈飞翔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广东广州510300)
本文从温州民间借贷1978~2015年有关数据出发,通过实地考察及数据整理,研究发现,民间借贷利率的走势及结构的变化与国家市场化改革路径、国家宏观调控、通胀或通缩等因素紧密相连。与此同时,温州当地“低风险实质借贷”与“高风险投机借贷”并存的现象与当地“重商主义”的社会文化有关。研究进一步发现,温州38年民间借贷发展趋势从最先快速发展的活跃阶段进入到现阶段的互联网化、技术化、理性化、转型化“四化”阶段。在论文的最后大胆地做了一个基于方向性的未来预测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民间借贷;利率;借贷风险;重商主义
一、温州民间借贷的信用基础及其缺陷
温州民间借贷异常活跃,引起各方高度关注。温州民间借贷不同于正规金融机构提供的金融服务,它是基于民间信用的一种交易范式,这种交易范式借助于血缘、地缘、业缘、亲缘及社区化的社会资本来完成。在社会资本非常稀缺的情况下,它就必须借助一种“有效形式的载体”提供抵押担保品或者保证人来完成。这种“有效形式的载体”可以是担保公司,也可以是其他形式的撮合中介,还可以由一种“精英信任”机制来扩展交易。所谓的“精英信任”是指当地德高望重之人,被陌生双方都信任。因此,“精英信任”机制成为陌生社会借贷关系的偏差调整,同时也成了一种隐性的社会担保品,替代了道德和契约部分风险,部分有效地抑制了“道德风险”与“逆向选择”的问题。由于民间借贷不完全受国家法律保护,这种完全建立在道义基础上的经济关系,“精英信任”机制有其脆弱的一面,当发生经济纠纷时,存在一定的法律风险。
正是基于这种由血缘、地缘、业缘、亲缘及社区扩展的经济交易网络和广泛存在的“精英信任”机制,温州的民间借贷得以飞速发展。但在考查中也发现,正是这种存在法律风险的交易机制,一旦发生“信任危机”,就很容易导致大规模的民间借贷风波。自改革开放以来至2015年之间,温州民间金融发展史上四次大规模的民间借贷风波就与这种有缺陷的交易机制有关。温州最近一次大规模民间金融风波发生在2011年,导致亲人反目,朋友成仇,这个自发性的民间借贷体系几近崩溃。也正是这次风波,引起温州当地政府高度反思,2012年官方决定成立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正式介入民间借贷,尽可能降低可能诱发的潜在金融风险。据有关媒体报道,自从民间借贷中心成立以来,民间借贷纠纷在法院立案的数量大大减少。以温州市主城区鹿城为例,2014年该法院受理的民间借贷纠纷2268起,到2015年减少到1843起,比14年减少了425起,降幅非常明显。
二、温州民间借贷的资金流向及其发展特点
在温州实地考察中发现,温州民间借贷的资金大部分流向贸易性行业、投机性质的房地产行业、股票基金及债券市场、高新技术型及创业型企业、当地P2P网络借贷平台,少部分资金流向家庭式事务或个人型事务,也有极微弱的资金流入地下“六合彩”和具有投机性质的摇会组织(注:此类摇会类似于传销组织,靠发展下线补充资金来源,层层盘剥,最终形成资金泡沫而倒会,“六合彩”和摇会多在温州苍南等地出现),但真正做实业的企业资金来源主要依靠银行贷款或通过发行股票、债券等有价证券来筹集资金。
形成上述民间借贷资金流去向的原因是贸易性行业、投机性质的房地产行业及股票基金、债券等市场的资金周转期较短,资金缺口很大,商业机会稍纵即逝等客观条件的限制,使得当事人想方设法利用现存的社会网络寻求能够在很短时间内快速聚集大量闲散资金的系统——民间金融体系——服务于自己的商业计划,而银行系统办理信贷的手续烦琐,时间跨度长,甚至要出让很大一部分租金,显然银行的运行机制是无法满足这类行业特殊性和急用性的要求。高新技术型及创业型企业是因为没有和银行建立长期的良好合作关系或者没有足够的抵押担保品无法从银行获得所需资金,只能依靠内源融资和民间借贷来满足自身的资金发展需求。P2P网络借贷平台是互联网金融快速发展的产物,除了温州本地投资者,来自全国其他各地的投资者共同投资了温州当地P2P平台提供的投资项目或理财产品。家庭或者个人通过民间借贷来满足自己的资金需求完全是为了应付生活救急或突发事件。地下“六合彩”的民间借贷带有高利贷性质,投机性质的摇会组织已经演变成金融“三乱”活动,这两类活动受到当地政府的坚决打压。而真正做实业的企业已经在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中逐步壮大,与当地银行建立了长期良好的合作关系,或者由于业绩颇佳已在国内或国外资本市场上市,因此,这类企业主要通过外源融资,较少从民间借贷的途径获取资金。
与此同时,据中国人民银行温州中心支行2005年发布的一份《区域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的比较研究》的权威研究报告指出,从温州民间金融市场26年(1978~2004)的发展脉络来看,温州民间金融正由持续、快速、活跃的发展势头转向增长趋势逐渐放缓、甚至停滞不前的尴尬境地,并且在区域金融结构中逐步边沿化,出现相当部分的民间金融被正规金融替代的不良局面。有关资料表明,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期间,民间借贷在温州中小企业总资金的占比中比例大幅度下降。数据显示,20世纪80年代,温州中小企业总资金来源中,自有资金、银行贷款、民间借贷“三分天下有其一”。但到90年代,三者的比例是60∶24∶16,民间借贷的相对比例下降很大。据温州中心支行2004年4月的调查,2003年末,三者的比例变成为57∶37∶6。由此可见,当地对民间借贷的态度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相比,越来越趋于保守。
温州民间借贷由发展上升到相对放缓的转折期大约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改革开放初期(1978年前后),估计全市民间融资规模约为4.5亿元,全市银行贷款余额7亿元,民间融资约为银行贷款的65%;在1991年左右,估计民间融资规模与银行贷款之间的货币数值之比为40∶50,民间融资约为银行贷款的80%,比80年代初期上升了15个百分点,民间融资规模的绝对量也由4.5亿元增加到40亿元,表明温州民间金融在80年代与90年代初期实现了快速扩张阶段和进入高速成长期;但到了2001年,民间信用规模总计约为300亿~350亿元,银行贷款708亿元,这个比例下降为45%。尽管温州中心支行2004年监控到的民间借贷资金比2003年平均增长17%,资金规模不断在增加,已经超过400亿元,但是民间金融市场发展相对慢于银行贷款市场,比值明显下降。虽然2004年温州民间借贷的规模已逾420亿,但银行贷款市场规模高达1534亿元,接近民间借贷市场的4倍体量,而且这种趋势仍然在继续,直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才出现新的转折。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随着温州当地经济发展方向与金融生态格局发生变化,当地一些非法担保公司不断介入民间借贷,打破了通过血缘、地缘、业缘、亲缘及社区化的传统介入的单一方式,更多的金融掮客出现,形成了“二元”金融生态结构,即传统借贷与专业化、投机性借贷并存。由于民间借贷投机性的扩张,增大了民间借贷的风险,与银行的不良贷款相比,民间借贷的不良贷款余额亦呈现加速累积趋势。在很多情况下,民间借贷由于缺乏有效监管,温州地区各类担保公司数量激增,资质良莠不齐,担保公司违规从事高息融资活动的现象非常普遍,如办理票据贴现(收购光票)、保证金垫资、代还贷款等。很多担保公司具有明显高利贷性质的民间融资行为扰乱了正常的金融秩序,而且其业务操作也不规范,容易产生民事经济纠纷,增加了社会不安定因素。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温州民间借贷虽然在向专业化领域转型,但转型的过程有点乱。
在这个快速转型的过程中,温州民间借贷的规模呈现出爆炸性增长势头。在2011年之前,温州民间借贷规模还不到1000亿元,但到2015年底,民间金融规模已接近7000亿元,短短5年,借贷规模已经翻了7倍。而2015年温州银行贷款余额才7527亿元,7000亿元的民间信用与银行贷款规模之比接近93%。撇开企业的自由资金不说,民间借贷已经占据温州总体贷款额度的半壁江山。从另一侧面也可看出,温州当地对民间借贷的态度早已从保守转变成更加激进。这种态度的转变可以看出千禧年之后温州十多年的社会变迁和环境影响对民间借贷的发展路径及规模起到了很大的改变,这种变化基于三个方面的因素:其一,移动互联网技术及互联网金融的快速发展,加速了匿名化交易网络的扩张,也降低了对传统民间借贷交易机制的依赖,增加了金融风险,交易额呈现井喷式增长;其二,过去十多年,中国城市各地疯涨的房价,改变了温州民间投资的方向,所谓全国各地温州“炒房团”的惊现一点也不奇怪;其三,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渐渐改变了中国国际贸易的世界版图,对于温州“出口导向型”的经济体来说,影响尤甚。
综上所述,温州38年民间借贷的发展趋势最先经历了快速发展的活跃阶段,接着进入相对放缓及在区域金融结构中逐步边沿化的一段时期,然后出现传统借贷与专业化、投机性借贷并存的非理性行为疯狂模式,到最后进入互联网化、技术化、理性化、转型化的“四化”阶段。
三、温州民间借贷利率走势与结构变化
从下表1可以看出,温州民间借贷的年利率先是经历从1978年42%到1988年45%的十年高位震荡期,再从45%的峰值一路降到2003年10.6%低点,随后又进入一个利率逐步爬升的上升期。温州2000年之后的民间借贷利率比80年代末、90年代初之前的利率水平低很多,一方面受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影响很大,另一方面银行的贷款利率偏低,信贷结构正趋于合理化,信贷规模也越来越大,在很大程度上对民间借贷形成“挤出效应”,自然压低了民间利率。
温州民间借贷市场利率自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之后开始持续走低的深层原因源于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自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中国经济市场化程度逐渐加深,特别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由政府提供福利性质的供给转向市场化方向改革,例如:单位福利分房改为货币化住房,个人医疗从单位剥离出去转给社保组织,高等教育由政府的低收费甚至免费开始高收费等。政府大力推行的市场化改革,个人原来享有政府免费或低成本分配的“计划型福利”需要自己的收入来购买,而且这种带有长周期性质的产品购买需要通过个人有一定积累的储蓄分期支付或一次性购买,比如,教育投资、住房、身体健康等都是长周期产品。长周期产品的市场化改革拉动了人们对未来产品购买的储蓄高潮,储蓄高潮必然影响当地银行的信贷供给,温州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全国大环境的影响,则造成温州银行的信贷供给能力大幅度攀升。温州银行丰富的信贷供给压力传递到民间借贷上,迫使民间借贷利率市场化水平下降。其次,央行基准贷款利率的连续下调,导致企业或个人从银行获得贷款的资金成本开始下降,进一步影响民间借贷市场利率水平。尽管民间借贷利率的市场化程度要高于银行贷款利率的市场化程度,但是企业或个人从两者之间获得贷款的机会成本由于基准贷款利率的连续下调开始降低。贷款利率从1995年的12.06%下调到2003年的5.31%,央行在近几年贷款利率连续下调后,首次在2004年10月底调高0.27个百分点,2004年末贷款利率达到5.58%。基准贷款利率的大幅度下降,加快了民间借贷市场利率从高向低进行市场化调整的力度。

表1 1978~2015年温州民间借贷市场利率与银行贷款利率比较水平表 (%)
最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后,中国经济从90年代中后期的通货膨胀转为通货紧缩的状态。1995年温州的物价指数为111.4%,具有较高的通胀率,然而在1997年爆发“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政府实行一系列政策与措施抑制通胀来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并郑重承诺人民币不贬值,一举扭转通胀转而进入通缩阶段,1998年温州的物价指数骤降到97.6%,与1995年的物价指数相比减少了13.8个百分点,经济状态处于通缩趋势已成既定事实,这种经济通缩状态一直延续到2003年为止。如表1数据所示,2001年和2003年温州的物价指数分别为98.1%和98.9%,与1998年温州的物价指数97.6%不相上下。温州物价指数全面下降进一步影响了当地民间借贷市场的利率水平,导致2003年10.6%的年借贷利率为温州民间借贷市场25年来最低。在很大程度上,温州民间借贷利率市场化程度与银行与民间信贷资金不对称力量、央行基准贷款利率的政策调整、通胀或通缩存在很重要的关系。
中国人民银行明确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不超过银行同期基准贷款利率的4倍,就不属于高利贷的范畴,同时这种民间私人借贷合同受法律保护。表1的数据显示,自1990年之后,可观察到的民间借贷利率的数值就一直没有超过央行规定的银行同期基准贷款利率的4倍阈值。这也部分地解释了正常的民间借贷通常双方会互相约定一个合理、可承受的利率水平,只有那些投机和地下金融活动才会滋生高利贷,扰乱社会与金融秩序,最终可能导致“金融风波”,引起社会动荡。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也在表1的数据中体现了出来,自从1997年爆发“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温州当地经济开始转入通缩状态,直到2003年才结束。与此同时,2003年的民间借贷利率也处于历史的低点,但2004年温州当地的物价指数(CPI)开始出现温和通胀,随后通胀就像一匹脱缰的野马,到2015年累计通胀率已达32.5%,对应的民间借贷利率也相应上涨,这也表明民间借贷利率与当地物价指数(CPI)呈现同方向变动关系。如果考虑实际物价(CPI)的因素,通过调整后温州当地民间借贷利率比可观察到的借贷利率高出了很多,表1的数据显示,最高峰值达72.1%,最低值仅为9.5%,排除最高峰值,2004年调整后的利率50.17%数值比一般高利贷还要多出一大截,值得进一步深究。这意味着资金借贷方获取资金成本除了需要付出双方约定的借贷利息,还有隐性的高物价水平对资金成本的抬升,而后者正是很多借贷者所忽视的。
温州民间借贷利率的走势及结构的变化与国家市场化改革路径、国家宏观调控、通货膨胀或者通货紧缩等因素紧密相连。国家市场化改革路径会引起银行与民间之间的信贷资金不对称,也会引发储蓄高潮。
四、温州民间借贷与宏观调控的关系影响分析
温州民间借贷也越来越受国家宏观调控的影响。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宏观调控是2004年开始,以“铁本事件”作为宏观调控最有代表性的案例。2004年国家出台严厉的宏观调控对温州民间借贷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由于国家实现收缩银根的政策,银行信贷供给减少,资金需求依然趋旺,导致民间借贷的规模大幅度上升。中国人民银行温州中心支行在2004年跟踪监测到300户的相关数据表明,2003年300户借贷规模月均5500万元,到2004年下半年上升到6500万元,增长17%。根据温州中心支行资本匡算到的结果,2003年的民间借贷规模基本与2001年持平,在350亿元左右,但到2004年的国家宏观调控措施出台后,民间借贷规模相对增长率增加17%以上,民间借贷规模约为410亿元,是年末金融机构贷款余额的27%。国家宏观调控对温州民间借贷的另一个重大的影响致使利率开始上扬,这与国家银行信贷供给缩小的部分转移到民间借贷上来是有关的。
自从2004年开启国家宏观调控的措施以来,到2015年为止,中国人民银行的官方网站一共记录了27次利率方面的宏观调控历史措施,其中2007年、2008年、2015年在一年之内实施的宏观调控措施分别为6次、5次、5次,这三年之和高达16次,占整体宏调之比近60%。如此频繁的宏调,可以看出2007年、2008年、2015年这三年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遇到了不同寻常的挑战与问题。与此相对应的年份的温州民间借贷规模分别达550亿、630亿、7000亿,利率水平分别为13.97%、14.38%、17.40%。这三个不同寻常的年份民间借贷利率水平虽然节节攀升,波动幅度不到4个百分点,但其借贷规模已从当初550亿的金额急升至7000亿之巨。
在这7000亿之巨的温州民间借贷规模背后,国家宏观调控在里面隐藏了很多不为人知的故事。国家宏观调控引发了温州民间借贷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 宏观调控导致温州当地正规金融机构出现“利率双轨制”,引发民间借贷规模的急剧膨胀,部分地抵消了宏观调控效应。当国家进行宏观调控,降低基准利率时,温州当地的正规金融机构的放贷收益大幅度下降时,它们会想方设法把正规金融机构的一些资金搬到收益更高的民间借贷上去,通过场内和场外资金的“利率双轨制”形成了一条隐秘的资金转移渠道。
(2) 宏观调控导致温州当地民间借贷为了扩展更大范围的借贷收益,倾向于加大金融杠杆率,使得金融风险骤然增多,投机性的金融活动和人群也大幅度增加。据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陈雨露在最近的一次金融街论坛上透露,2015年末全国非金融机构企业的杠杆率已高达160%左右的高水平,企业的市场风险大增。由此可以推断,温州当地的民间借贷的金融杠杆率至少大于200%,最高可能高达1000%。高金融杠杆率虽然降低了资金借贷成本,但带来了超高的金融风险,企业在借贷成本与金融风险之间的选择,更愿意以赌一把的心态加杠杆。
(3) 宏观调控加快了温州当地民间借贷的互联网化的快速发展,通过互联网可以绕开金融监管部门的有形监管,匿名化借贷网络与P2P网络借贷平台异军突起,使其游离在灰色金融与黑色金融的边缘地带上,不仅加大了监管部门的监管难度,还催生了很多潜在的社会不稳定因素。2011年温州当地的大规模民间借贷风波与其有关。
五、温州民间借贷风险的商业文化因素分析
在考查中发现,民间借贷的保全措施越来越丰富,不过在熟人社会中的借贷关系主要还是依靠互相信任和血缘、地缘等因素。有关数据显示,需要借方出具担保和保证金、抵押等措施的比例分别只占全部借贷活动的5%和7%,绝大部分借贷契约靠自律、声誉机制和道义来实现正常的交易。但在生人社会中的借贷关系采用的保全措施很多,如抵押或担保,或者通过考察公司后直接入股的方式参与管理,或者签定扣除一定利息后的借款合同(注:合同借款人实际拿到手的本金比合同本金少了扣除利息的部分,合法有效的私人借款合同受法律保护)等。也就是说,在生人社会里的贷方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不受损失,制度化或人性化的风险防范措施是他们的首选。
外界大多数人认为基于信任交易的民间借贷风险很高。但事实上,民间借贷的高风险是由投机性质的地下金融活动引发的,那些真心实意创业、应付突发事件、大宗消费品等实质性借贷风险并不高。这种“高风险的投机借贷”与“低风险的实质借贷”并存的现象使得很多人对温州当地的民间借贷的风险机制有所偏误。陈飞翔(2010)研究发现,民间借贷中实质性借贷风险不高,很重要的原因与当地商业文化的“重商主义”(其“重商主义”的核心是商业文化契约化)以及互帮互助的邻里文化有关。
在中国人民银行温州中心支行2003年的问卷调查中显示,87.9%的借贷活动既无财产抵押也无他人担保,基本上是一种信用借贷,需要借方出具担保和保证金、抵押等措施的比例分别只占全部借贷活动的5%和7%。调查还发现,仅有10.6%的借贷活动是由他人介绍而成交的,其余的借贷关系51.5%是朋友关系,32.1%是亲戚关系,5 .8%是同业关系。以上数字说明温州民间借贷基于信用交易仍然是主流趋势,纯属高利贷性质或黑色金融的活动并不能替代信用交易。中国人民银行温州中心支行还发现,在2002年全市300亿~350亿元的民间借贷规模中,真正出现社会性风险问题的资金只有2.87亿元,占比不到1%;而当时全市银行的“两呆”贷款率在3%~4%,这组数据表明民间借贷的风险并不像人们普遍理解的高风险,与我们在温州当地观察到的情况大致相吻合。
六、政策建议和未来预测
毋庸置疑,民间借贷对温州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也为温州金融史留下了隆重的一笔。温州民营经济的发达与民间金融的快速发展休戚相关,这种现象同时也被学者誉为“温州模式”。温州的民营经济之所以能够迅速扩张继续发展达到巅峰,是因为温州逐步地形成了自发市场秩序的生成机制并能自由扩展。“温州模式”也可以认为最接近奥地利学派的领军人物哈耶克所阐述的秩序自由扩展的市场经济。自发市场秩序的生成机制中的一个关键变量是民间金融的发展也是自发地演进,使得民间资本的触角深深地渗透到每个经济细胞中去了,同时也为众多的民营企业提供了强有力的金融支持。
20世纪80年代初,温州民间金融能够快速发展,得益于民间开放的心态、民间信用的社会资本化、契约自由交易、企业家才能、地方政府的分权极大化等因素,但随着社会的变迁与现实发展,民间金融开始出现很复杂的演变机制,相关的解释和数据也支持了这个论点。本文认为以上的一些因素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例如,中央政府利率市场化推进、地方政府开始积极介入当地的民间借贷、互联网金融的快速发展、房价的疯涨、国际贸易结构及趋势的变化等影响了民间借贷,同时也对民间金融的演变机制产生了长远、难以估量的力量。民间金融现实发展路径依赖于国家金融改革的市场化推进程度以及自身发育的好坏。
温州的民间金融正面临转型的关键时刻,基于此,从未来发展的角度,本文提出如下相关政策建议:
(1)温州当地政府应借助2011年“民间借贷风波”和互联网金融的快速崛起,推动民间金融在中央层面的立法工作,让其意识到在民间金融与互联网金融立法方面的迫切性,尽快能推出《普惠金融法》或《民间与互联网金融法》。
(2) 温州当地政府在2012年成立的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不仅需要正确引导民间借贷合规、有序地交易,还应该动用财政资金成立一个风险基金,为当地可能出现的大规模金融风险提供最后担保人的角色。
(3) 温州当地政府应该借鉴美国华尔街的“利率走廊调控机制”,在监控民间借贷的市场利率时加入这种调控机制,形成一套有效快速的风险预警系统。
(4)温州当地政府应该借助互联网技术和大数据,建立一个基于信用交易的数据库,引导民间借贷良性发展。
[1]陈飞翔,等.温州民间借贷研究[J].中国证券期货,2010(3).
[2]中国人民银行温州中心支行.区域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的比较研究(内部资料).
[3]单惟婷,沈宏斌.温州民间借贷利率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J].上海金融,2013(10).
[4]陈飞翔.非正规金融利率研究——兼论温州民间金融[D].中南大学硕士论文,2007.
[5]黄益巧.温州地区民间借贷利率问题研究[D].石河子大学MBA硕士论文,2013.
[6]哈耶克(英).自由秩序原理[M].邓正来译.上海:三联书店,1997.
[7]牛慕鸿,马骏等.利率走廊、利率稳定性和调控成本.央行工作论文,2015.
[8]陈明衡.关于民间借贷若干问题的探讨.中国人民银行温州中心支行内部发言稿.
[9]中国人民银行温州中心支行.温州金融生态建设探索与实践.内部资料,2006.
[10]钱报网.http://www.qjwb.com.cn/,温州民间借贷中心有效化解经济纠纷.
[11]金融街论坛.央行副行长陈雨露:企业杠杆率高企,市场风险大增.2016.
[12]毕德富.宏观调控与民间借贷的相关性研究[J].金融研究,2005(8).
(责任编辑:周小红)
Research on Private Lending in Wenzhou:1978~2015
CHEN Fei-xiang
(GuangdongIndustryTechnical College,Guangzhou,Guangdong 510300)
Starting from the relevant data of Wenzhou private lending from 1978 to 2015,and through field investigation and data collation,the paper found that private lending interest rate trend and structure change are closely linked with the national market reform path,national regulation,inflation or deflation and other factors.At the same time,the coexistence of"low substantial credit risk"and"high speculative lending risk"in Wenzhou private lending is related to local"Mercantilism".Further study found that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Wenzhou's private lending in the past 38 years changes from the rapid development at first into present stage of Internet,technology,rationalization,transformation.Relevant policy recommendations are put forward based on future prediction.
private lending;Interest rate;lending risk;Mercantilism
F832.755;F832.479
A
1008-2107(2016)04-0122-07
2016-06-05
陈飞翔(1979-),男,江西永新人,经济学硕士,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民间金融、互联网金融、中小企业融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