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寻找一座木码头
陈迟恩
故乡,一旦离开,便欲返回。奥德修斯为此在海上漂泊了十年。然而今天,时代的藩篱足以阻拦我们的这个念想:有的是在被迫与土地分离之后无家可回,有的是不愿回到那片封闭的天地。
2015年刚入冬,青年诗人苏丰雷就像一只候鸟,从北京寒冷的艺术村飞往深圳一个山间的艺术小镇以躲避寒冬,并在那里度过了一个令友人歆羡的春节。每天醒来,面对的是心无旁骛的读书与写作,是依旧环翠的群山,是这个时代难得的清静:全部的时间、全部的世界都是自己的了。然而在苏丰雷那里,这令友人歆羡的春节背后所需要付出的代价,是我们不能想见的。这种代价不是一个人漂泊在外,无法与家人团聚;而是如今的春节远非团聚那么简单,它意味着对正当婚嫁的青年一年一度催婚大戏的上演,尤其在苏丰雷所生长的青阳县乡村。苏丰雷不愿参演这出大戏,他坚决而软弱地选择了逃避,但他也对由此带给家人的难堪、带给自己的困境心知肚明。正像在《〈父亲〉写作札记》中所说“(我)作为旁观者观察着家庭的变迁,有时候近乎冷漠”,他也清楚自己在这个春节的冷漠选择,会给家人带来难堪的同时,令自己与家人之间的隔阂越来越深。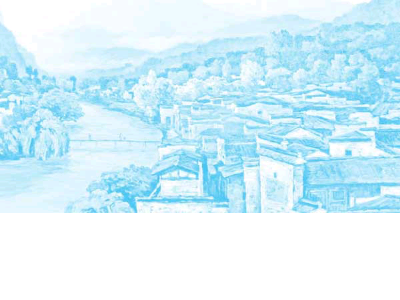
这种隔阂集中地体现在他与父亲的关系中:“我对我父亲的感情有些复杂,不知从什么时刻开始弑父与敬爱就盘结在一起。”(《〈父亲〉写作札记》)这源自西方文化传统的俄狄浦斯情结也许能够解释全部男儿对父亲的情感,却在中国当下部分地失效了,或者说其内涵急需得到丰富——体现的是个人与家庭之间那种对抗却又牵连不断的关系。因此,苏丰雷的困境不是他一个人的,而是更多与他处于同时代的年轻一代所要面对的;所不同的是,作为一个写作者、一个诗人,他将现实生活中的逃避所带来的自责,转化成了诗作中与父亲、与家人乃至与自己所生长的乡村的和解。苏丰雷清醒地意识到父亲、故乡带给自己的“殊异的财富”以及他们的困境,可自己无力为他们做什么改变,只能在诗中重塑他们的形象,借此确保他们得以长久地存在下去。
从苏丰雷近几年的创作中,可以清晰地看到这种和解的迹象。“一阵不知身在何处的苦痛侵略了我/待我艰难爬过了一片迷蒙、苦涩的泥淖/我才确定我是在漂泊途中的一个清冷的异乡”(《南国的雨》),在异乡的苦痛与清冷来得那么强烈,“狭小然而仁慈的床铺”也不能安慰。此时此刻,能带来慰藉的只有安徽西部那个被人情世故充满、带有压抑感、他极力躲避的乡村,多么悖谬啊!然而此时,现实中的弱者拿起笔后就变成了强者,他构筑起一个精神上的故乡,实现了一种精神上的还乡。
与他所推崇的同代诗人李浩的长诗《还乡》相比,苏丰雷诗中的还乡不是对乡村生存经验的再描述,而是一次重新的寻找,一次返回的寻找。由此,苏丰雷在近几年的创作中构筑了一座桃花源,并在长诗《木码头》中引用陶渊明的《桃花源诗》及己作《只要活着》中的诗句“你自身就有桃花源”,来强烈地暗示读者,木码头就是诗人心目中的“桃花源”。诗人在寻找一座木码头。
诗人的寻找在家人、熟人以及女性的身上展开。家人是一切寻找的核心。现实中诗人自觉对家人有多少的愧歉,诗作中他就有多么强烈的和解的欲望。诚如《江南》诗中所说:“我们脆弱的院落是这金湖边/多么简陋、易朽的木码头。”院落是家庭的象征,一个“脆弱的院落”是“简陋、易朽的木码头”,对于寻找木码头的诗人来说,“简陋、易朽”非他想要,因为这意味着木码头的暂时性与瞬间性,不能恒久存在。这与诗人所追求的永恒是冲突的。而与家人达成和解,就意味着家庭作为一个整体不再脆弱,且拥有了抵挡时间、空间、人事侵袭的能力,至少让这侵袭变得迟缓。由此,我们明白了,苏丰雷笔下的“木码头”不仅仅是南方水镇常见的“木质的码头”(《木码头》),架在河口津渡连接着水陆、连接着内外,它还是人与人之间关系进一步升华的催化剂,是(新旧)两个世界之间相沟通的纽带。
由此,苏丰雷完全摆脱了现实中家庭成员之间可能的隔阂,如《〈父亲〉写作札记》中披露的心结:“我更多心思用于学习,作为旁观者观察着家庭的变迁,有时候近乎冷漠,比如对我弟弟失学的事情,没有干涉……”,营造了和谐平等的氛围。在此类诗作中,诗人直呼母亲“像个小媳妇,笑着/与客人们打招呼,然后/走进菜园,把尿桶里的尿倒到某处”(《秘密花园》);甚至以血淋淋之感毫不掩饰地揭露父亲年轻时的艰辛,仿佛将父亲重新放到了岁月的砧板上,一次次折磨:
你让我看你背上一道深沟般的鞭痕
涂抹着滑腻的油膏
你说你已三番被铁钩从背后勾起
……
我知道你已五次翻车
来不及包扎伤口
就继续宵征,血顺着腿
和着浑浊的尿,流淌
——《父亲》
父母被视为神圣的,一般的诗人受限于伦理道德的约束,往往不敢写下这近乎越轨的诗句,更不用说将父母与“尿”等秽物并置。苏丰雷并非无视传统伦理,只是内在的愧疚感与负罪感驱使着他,让他细细品尝父亲身上的苦难与母亲身上的辛勤,他所能做的,“只能单薄地放置几个破碎的句子,立此存证,然后放任想象,吞声痛哭”(《〈父亲〉写作札记》)。
面对弟弟也是一样。诗人非常清楚发生寒门中兄弟之间“争食”等种种纷争,而在堪称苏丰雷近几年最好的诗作之一《兄弟》中,诗人塑造出了一个顽强乐观的弟弟形象。在父亲这位“空怀热情的年轻船夫”驾驭下的简陋“舴艋舟”中,弟弟作为“食量大于马的蚂蚱”之一所得的只是“贫瘠口粮”。尽管“尽情品尝颠簸”,但与作为诗人的哥哥相比,从“颠簸的命运小舟”里爬到岸上的弟弟仍“靠一双勤劳的大手而不是聪慧的脑袋”采摘了属于自己的桂花;而哥哥却像一个一无所成的哲学家,空空地感慨“让一个人命运薄脆是中国大师的拿手”。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在引语中改写了陶渊明的《杂诗·人生无根蒂》中的两句诗:“落地为兄弟,何况亲骨肉!”骨肉之情战胜了既往的一切争执。联系到诗人曾说过对弟弟的失学没有干涉,却将家庭重担撂给他时,这一句改写所带有的深深自责与愧歉就不言而喻了。自责、愧歉、愧疚、负罪,一旦诗人意识到了这些,他与家人之间的和解也就开始了,至少在诗作中如此,在诗人的想象中如此。
与家人不同,诗人和家乡的熟人之间不需要和解。但作为故乡的象征,苏丰雷也在诗中为他们营筑了与全新的世界。在长诗《木码头》第二章,寻找木码头的途中:
当我贸然走进丰常村里的一家饭店,
我发现店主是熟人……
熟人一家在这里过着与此前截然不同的新生活。以前这家人丈夫“又赌又懒”,儿子们“惯于使用鸡鸣狗盗之技”,可在这里他们的生活好生美满,“恪守道理,先前的坏声誉/被勤善的劳动挽救,慢慢被遗忘(也许从没有)”。在该章删去的诗行中,诗人疑心“上帝在创造/世界时(一个测试或实验?)至少设计出两个?/人类自经营的世界和上帝亲营的世界”,其实诗人就是这“上帝”,他正在营筑一座桃花源。
而在苏丰雷所写的熟人中,多次出现了女性形象。这是值得大书特书的。苏丰雷曾写有两首非常出色的女性诗作《邻女》《表姐》,其对象都非常具体,而且在诗中,她们都“回来”了。《邻女》诗中写道:“在少年的码头/我们挥手作别……//你回来是多么稀罕……”,《表姐》诗中也写到“我”到姨妈家“来看望模特样表姐,她在男人河游得太累”。无论邻女,还是表姐,都是男人们幼年时爱慕、倾慕的对象,似乎都寄托了自己的整个人生梦想与爱情期待。而诗人也在诗中给出了强烈的暗示,如“我们,面对,喜悦,如窃/……折进独处的房间/面颊灼热,血液发甜”(《邻女》)、“我和黑马停驻她窗前……//声音漏出慌张,头发、衣袂野性的凌乱”(《表姐》),诗人再次与“邻女”或者“表姐”发生了交集,尽管已时过境迁,但诗人仍赋予了这一切以美好的想象。她们的回来,很明显地构成了一次新的审视故乡、审视乡村生存记忆的契机,诗人在精神上的还乡最终将借此完成。
这就意味着,女性不仅仅是诗人在诗中对幼年梦想的实现,在长诗《木码头》中,她们还将引导诗人最终寻找到那座木码头,就像贝丽亚特齐引导但丁进入天堂、像“永恒的女性”引浮士德飞升一样。可以说,《木码头》与伟大诗篇《神曲》《浮士德》产生了一种同构。整首诗以对话开始:
“骑到那叫做丰常的村子,你打听下,
从那村口右拐,那里有五个码头,
其中第三个就是你要寻找的木码头。”
这里采用了一种预叙的方式,预先呈现了整首诗的寻觅过程。而这个隐藏起来的对方,更成了诗人的向导:“你甚至好心带领着我,骑在前面”,这无疑会让读者想到但丁初入地狱时的向导维吉尔。但他从一开始就将诗人远远地撇下了:
你大概骑得远了,说不定已然找到
你所说的木码头。而我将用我的步奏
寻觅,你已引我至深,我知道
我终会到达那另一种存在……
向导的离开俨然让诗人成了浮士德,他不知道未来会遇到什么,他似乎只知道结果一定美好:“就像一片新天地,仿佛平行宇宙,/对应于我们故乡的另一处故乡,/也许那才是我们真正的故乡,或天堂。”诗人在此无形中透露出所谓的向导,其实也是一个寻觅者,两个人有着不同的步奏,注定不会结伴而行,他也注定不会成为诗人的维吉尔。
在接下来的诗行中,诗人由对木码头的寻觅,转向了对自我的探寻。诗人“没见到那真正的我”,那拥有完美人格的另一个“我”。“他在却不在,一种沉默,一种空白,/构成一种更有力的批评,我扩大了许多”,或者说变得更加豁达,诗人终于意识到“我终得返回,也终将不断回来”。此时此刻,诗人也最终意识到木码头对他而言意味着什么,此前他在寻找,但并不知道寻找的意义。如今他知道了,正像诗作的第三个引语“大海啊永远在重新开始!”(瓦雷里《海滨墓园》)所蕴含的那样:寻找木码头的过程,也正是对自我的再寻觅过程,诗人希望通过再寻觅而重新开始。于是整首诗就带上了接续《神曲》《浮士德》等伟大诗篇寻找自我传统的雄心。当诗人说“看见一座木质的码头在那里静谧地打坐”时,他采用的是拟人的手法,木码头即将于“我”融为一体:
我依然能够回到开头,回到原点。
于是我坐进码头的怀里,残余的夕光笼罩我,
我进入时间源头的平静,如同一只吸管
插入静止的湖中,内在的欢乐让我丰盈。
诗人此时此刻重新寻找到了自我。伟大的女性已经出现,“我感觉又一次回到子宫深处,你是我另一个母亲”。而整首诗以省略号结尾,言有尽而意无穷,给读者一种永恒感,时间在此永恒地静止了。
诗人寻找到了木码头,寻找到了自我,也就完成了一次精神上的还乡。对于苏丰雷来说,这是一次必需的经历,正如诗人所说:“作为从文化沙漠的乡村出来的人,我们要从自身克服的障碍真是太多了!”(《〈父亲〉写作札记》)而他身负的障碍、心怀的愧歉,却又随着时间的流逝、事业的无成而与日俱增。他被俗世不可理解地坚持生活在城市的边缘,去描绘城市边缘的人与事,仿佛是在以一己之力背负城乡之间越来越背离的时代的罪恶。可惜他太脆弱了,他需要一次次返回所从来处,获得精神上的慰藉,只为自己在大都市里继续有勇气地生存下去;而他又太软弱了,现实中的他惧怕还乡、惧怕面对亲人,只能在诗中做着一次次还乡之旅。
啊,乡村的候鸟,飞到都市躲避家乡人情世故的寒冬,纵然危险重重也不愿回去,仿佛寒冬永不退去;但在梦中,它早已伸展着翅膀,飞翔在那片封闭的天地。
2016年8月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