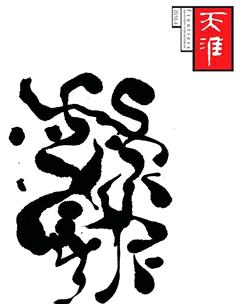民谣漫谈
文艺的坚持与困境
很少有国语歌手会像李健一样,带给我一种平静的体验。
没记错的话,那是2001年。我十三岁,正是开始疯狂地接触各种音乐的年龄,当然,也买了水木年华的卡带,不久后,就在电视节目上看到他们。
卢庚戌是大方开朗的,一直配合主持人回答问题。短暂的对话过后,镜头切换到他身后的李健。没错,李健是站在后面稍稍偏右一点的位置的,与主持人和卢庚戌都保持着不易被察觉的一小段安全距离。他穿着一件淡红色的短袖格子衬衫,背着一把吉他,留着当时流行的那种周渝民式的齐耳外翻的发型。
虽然此前就听过他们的音乐,对李健那优美的吟唱也很熟悉了,但他的眼神仍然吸引住了我,给我一种陌生的惊异感。那是多么干净澄澈的眼神,像两潭不受污染的湖泊,包含着某种既温存又坚定的东西。虽然舞台上吵吵嚷嚷,但他的存在、他所站的位置,仿佛已无声地宣示了一种特殊的立场。
一年后,李健就单飞了。不出我所料,在接下来他的首张个人专辑《似水流年》里,李健所表现的音乐世界,正如他在那一次舞台上给我的感觉。
在这张专辑里,最先吸引我的是《一辈子的十分钟》。就歌词来看,这首歌讲述了一个关于亲情的故事,我更愿意将它看作是一幅死亡之前被拉长的瞬间图景:叙述者即将与母亲分离,选择一条“东去的漫长的路”归去(或者死亡),这时候他们仅有十分钟的告别时间——“短暂的十分钟存放一生”——他们这一别,似乎就是永别了,今后不会再有相见的可能。因此,“这幸福的每一秒钟多残忍”,按理说,他们的告别应该是极其痛苦的,但李健却用一种克制的舒缓,将极致的复杂之情轻描淡写地表现了出来。在战火的硝烟中,叙述者“我”穿过金色的麦田,看到远方“我亲吻的那村落等待我”,他希望母亲“拥抱那一刻答应我,在我离去后好好生活”,在最后的告白里,他对母亲说“听我再为你最后唱一首歌”。我很喜欢李健的这一处理方式,他将“痛苦”这一经验凝固在即将上升到顶点的那一瞬间,并通过音乐,营造出真挚感人、余音绕梁的情景。这种拉奥孔式的手法,我相信是出于李健的本真:他不需要刻意去造境抒情,他的个人性情与艺术才华早已融洽地结合在一起,推动着他自然而然地进行最好的处理。
这张专辑里还有一首歌,《传奇》,近十年后,被王菲在春晚上唱火了。但当年更吸引我的不是《传奇》,而是《八月照相馆》。和李健的很多歌一样,《八月照相馆》也适合在夜深人静时一个人听,歌中时过境迁的感伤,深深地打动了我。早在水木年华时期的《一生有你》这张专辑里,我就特别注意到歌曲的创作情况:卢庚戌几乎包揽了所有的歌词创作,李健则负责其中的部分作曲。《中学时代》就是一首有代表性的歌,回忆那个纯真年代的初恋情结。而到了《八月照相馆》时期,这种具有回忆性质的音乐,逐渐成为李健的创作中一个较为类型化的分类,他的《不知不觉》《风吹麦浪》《想念你》《回到从前》等都与回忆有关。实际上,专辑同名主打歌《似水流年》便已经给出了“时间”的向度:“那年春天燃起的篝火,多年以后泛着泪光闪烁。”在通俗歌曲都面向于“眼前”的时候,李健却在选择了“回忆”,他对时间有一种艺术性的观照。曹文轩在谈论普鲁斯特时说道:“‘流逝这个字眼大概是词典中一个最优雅但却最残酷的字眼。”李健选择了亲近于“流逝”,也就是想通过回忆,找回逝去的时间。而这种回忆性质,在强调“眼前”的流行音乐市场里,受到了一定的遮蔽,这也是情理之中的。
2005年,李健发布了第二张个人专辑《为你而来》。我当然是急匆匆地跑到唱片店,买回了正版CD。这张专辑中,我最喜欢的不是同名主打歌《为你而来》,而是《向往》。第一次听《向往》时,它的前奏就把我带进去了,略带电子感的和弦,配上李健的音乐中少有的鼓点,使我的内心也翻涌起一种温柔的澎湃,我甚至感觉到自己心跳加速。这是一种奇妙的感受:我不是因为歌词而被打动,也不是被任何文化语境所打动,单是旋律、节奏,就激发起我灵魂深处的荡漾——这正是音乐最本质的意义所在。《向往》像一首抒情诗,在反复听的过程中,它的意境让我尤为回味。在这首歌里,李健表现出一种面对生命与自然的固有残缺时的豁达态度。作为人,我们固有“在体性欠缺”,但正是这不完美,才能成就生命的意义。而在悲欣交集的人生过程中,最宝贵的莫过于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关怀与相伴。这首歌,像是伤痛后的舒展、低迷后的吟唱,它不枝不蔓,温婉却有力,灵动地翩然飞翔。
我认为,《向往》还体现了李健的音乐中除“回忆”外的另一个重要维度,那就是“生命”。确实与普通的情来爱去的流行歌曲不一样,李健不仅喜欢回忆过去,还常常思考生命,“我知道并不是/耕耘就有收获/当泪水流干后/生命还是那么脆弱”,生命确实是脆弱的,有着我们每个人都无法通过意志去左右的力量;然而,这一切“却无法阻挡对温暖的向往”,人,应该用一种“默默忍耐的力量”去坦然地面对生活。《向往》是认清了生命本相的觉悟,其间交错着悲伤与淡淡的喜悦。这首歌用艺术化的思维,对“存在”这一重要的文化命题、生命命题,进行了审美的解读。因此,《向往》更加符合尼采对艺术的判断:艺术家以审美的态度洞察人生;面对人生不可解决的难题与悲剧时,艺术呈现出其价值,表现出“快感”与“狂喜”。李健已经直接进入到对艺术本质的把握中,《向往》是“含泪的微笑”,它并不冰冷,反而是温润的,即使阳光再少,它也要努力向上生长。
2007年,我进了大学,李健也推出了第三张个人专辑《想念你》。那时候,我开始写关于李健的乐评,四处投稿,不见回音。有很多人,根本不知道李健是谁。我的同学中,也只有一个人喜欢李健——非常幸运,她是我同宿舍的室友,一名客家女孩。
那时,我们会在一起听李健,聊他的音乐带给我们的感受。在《想念你》这张专辑里,客家女孩喜欢《异乡人》,而我最中意的则是《风吹麦浪》。同是听李健的歌,我俩的差别倒是很有意思。客家女孩历经坎坷,在整个家庭都不支持她求学的情况下,她曾经独自去广东打工,在车间做过电子元件、睡衣、拖鞋,以此为自己筹学费、争取读书的机会。她喜欢《异乡人》完全在情理之中,或许,也与她的客家身份有遥远的历史渊源?
而《风吹麦浪》,与我最初喜欢的《八月照相馆》一样,都有一个“回忆”的原型。“回头看”气质的艺术作品,一直都很能打动我。早在童年时,我就爱阅读一些具有回忆性质的文学作品,并沉迷于它们所表现出的伤惘之中。对我而言,这种审美感受既折磨人,又非常舒适。
李健的歌还有一种地理漂移感,他擅于在歌曲中安插自己的地理坐标。除了写故乡的《松花江》外,我注意到,旅行带给他不少灵感,他记叙旅行体悟的歌曲不少:《什刹海》《抚仙湖》《在海上》《贝加尔湖畔》……我记得,在专辑《为你而来》的CD文案里,李健注明过《在海上》是写于青岛。这是一首很能打动我的歌,在我的想象里,陌生的地方会给人带来新的期待,李健也说“未知的生活,我为它着魔”;陌生的地方也能唤醒沉睡的过往,而李健却要做到“飞越所有澎湃,忍耐一路伤怀”,这无疑是把“回忆”升华了,要让人生境界更加辽阔自如。旅行随感,往往是瞬间的片断,但李健的这一类与行走有关的作品,却将零碎的感悟充分调集起来,塑造成型,提供了一种艺术创作的经验。
总的说来,李健的音乐有一种“日神”化的特征,有内在的平衡与理性。这也许与他是理工科出身有关——即使要表现对过去的伤怀、对未来的瞬间冲动,表现眼下的情感奔突,他也会将它们控制在整饬的秩序里,无形中彰显出一种平静的力量。他通过音乐呈现出来的,不是未知世界的原始冲动、无序、混乱、迷狂,而是对有知世界的把握,是确定性的,并最终走向对“当下”这一时空维度的肯定。李健的歌会安抚我,将我从混杂、跌宕、激烈的现代性体验中拽过来,向我展现出这世界(或许只是虚构的艺术世界)平和、舒缓、温暖的一面。这些充满田园想象的歌曲,与席勒所说的“素朴的诗”有明显的同构性,能使我产生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之情。尼采认为,日神精神(阿波罗精神)与梦有关,酒神精神(狄奥尼索斯精神)与醉有关。李健的音乐确实更符合“梦”的气质:按照弗洛伊德的说法,文艺作品就是“经过改装的梦”,与梦想密切相关。而李健的音乐正是这样的“梦”,它对我的安慰,也就是艺术之梦对我的安慰。
其实,通过水木年华时期的《一生有你》这张专辑,就可看出李健与卢庚戌的音乐理念并不相同。有趣的是,单飞后,他做出了自己想做的音乐,得到了业内的不少认可,却一直未能大红大紫。直到他参加湖南卫视第三季《我是歌手》,才开始迅速地人气飙升,被广大粉丝奉为“秋裤男神”。这一现象,至少说明了艺术追求与市场需求在很多时候并不同步,它们的磨合需要时间,更需要机遇。流行音乐作为一种消费品,需要被市场迅速消费,使消费者的娱乐需求得到满足,这样才能带来商业价值。而“文艺”色彩的作品,则需要消费者去动脑筋思考,并调动起相应的审美储备,这就对消费者提出了更多的要求:你们首先要懂得鉴赏。很明显,后一种消费者,在中国的文化市场里并不占多数。所以,当李健把自己的音乐往“民谣”靠拢时,它们注定无法被这个消费市场迅速消化,从而出现了音乐产出与市场并不同轨的局面。这就是“小众”的市场本质。
李健也谈到过这种情况。在清华大学的一次演讲中,他承认“这个行业涉及到很多因素,你光热爱音乐是不够的”;但他同时也认为,“像我这样在音乐上花费这么多精力的人是少数的”、“环境越差,你只有越努力,越逆流而上,才会有好的结果。当人们都抱怨的时候,你不抱怨,你去更努力地、更认真地做音乐,这样才会赢得真正的尊敬,你也会赢得你所谓的市场。”总之,他认为“我唯一能做的就是保持我一贯的音乐坚持吧”。
在《文青的李健,还是大众的李健?》一文中,媒体人徐鹏远认为,第三季《我是歌手》里,李健才是最大的黑马,他的胜利是一次文艺性的胜利。同时,他也表达了自己的立场:“综艺娱乐节目的观众期待的是即兴的陶醉和廉价的感动,而非多想一层的深刻。所以观众喜欢的只是被当成了情歌的民谣,只是民谣的一次文艺性的虚幻的胜利,民谣依然是边缘的小众的。”他指出“太久的安静总会失之于平淡,这是李健最大的危险”,最后总结道:“李健这一次文艺性的胜利是诗意想象的中产阶级和小资的胜利,真正的中产阶级和小资是不会满足于、甚至不屑于关注一档大众综艺娱乐节目推出的歌手的。而且当李健成为大众偶像时,便再也无法适用于小资和文艺青年们彰显独特品位、区别主流审美的本质需求了——我的李健不能是大家的李健,大家的李健不是我的李健。”
这也正是我所忧虑的:不枉多年的坚持,李健现在已经“由隐入显”了,那么他的音乐今后将何去何从?这个问题不仅是出于市场的考量,也出于音乐本身:他已经创作出了不少民谣风的好作品,甚至无法抗拒地陷入了类型化风格的自我复制之中,那下一步,他是该继续在这条狭窄单一的道上行走呢,还是该另辟蹊径、迎接新的挑战?
最后,我不得不说,在第三季的《我是歌手》总决赛上,李健的表现令我有些失望。在唱《乌苏里船歌》时,他跟着节拍,高兴地向台下观众挥手、互动,显然,对这个舞台,他已由最初的不适,进入到了自在的“表演”状态中。这时,大众以绝对优势胜利了,而我的隐忧更为真实了——我一直很悲观地认为,在当下的中国文化语境中,大众与小众之间不可能存在一座彼此相连的坚实的桥梁。那么,若干年后,人们再想起李健时,是会认定他是一名不错的艺术家呢,还是会像民国风回潮那样,想起他,仅仅等同于想起了张恨水?
妖精在独白
陈粒的音乐,是我2014年在豆瓣上最大的收获。
说实话,那时我已开始对豆瓣有些失望了。听了多年的豆瓣,曾一直认为它是个较为多元化的阵地,但不知从何时起,流行音乐人榜单常常被一些没什么技术含量的小清新所占据,他们打着彰显个性的旗号,内心的媚俗诉求与灵魂空芜却暴露无遗,而追捧者的热烈程度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我不得不怀疑:这些粉丝除了会对肤浅的冒牌货发出“哇哦”的惊叹外,还有什么深度可言。
而个人的成长选择,虽未使我困惑,却提醒我必须在面对俗世压力时保持清醒,保持强大的定力,并不断地自我激励。人真正的成长可能也就是一两年间的事,旧的自我被毁弃,新的自我又被悬置在青春与苍老之间,上面有星空,下面有大地,但你什么都触摸不着,只是被沙漠里刮来的大风无辜地吹着,经受着现实的干涩与粗粝。就在这样的状态下,我听到了陈粒。
那是2014年8月,和往常一样,当我要开始做家务、处理杂事时,就顺便打开豆瓣听一听音乐。当然,那天我原本没抱什么指望的。
偶然中,我看到了陈粒的名字。她的小站,流派是归入“民谣Folk”一类。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她的名字,很文艺的范儿。有一行话首先映入我眼帘:“要挣钱,要养家,要过好日子,当时就那个水平,别人也都那么干,限制太多,给钱太少,社会不开明,市场不成熟,都是理由。但今天谁要听这些理由?大家只看结果,任何理由没有,这就是你干的,你的历史。”——非常现实主义的一段话,让我顿生好感:这女子倒是不装,不叫嚣要为了艺术死啊活的,当然,这可能源于她的坦诚,也可能源于玩世不恭。
我听的第一首是《我只去过东南亚》,果然是清新味儿的民谣,与豆瓣上其他的大众民谣没太大区别,直白地说,就是我觉得这首歌有些“从众”。
不过,这首歌还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它有一个独特的视角,里面游动着俏皮和灵动的东西。于是在接下来的某天我再次打开豆瓣时,仍然在一群音乐人中选择了陈粒。
这次我听到了更多。忘了是在哪一首歌里,我听到她模仿卡百利/王菲的唱腔,唱得很努力,但有点力不从心。我笑了,感觉到了她的努力与认真。仔细听她的声音,发现她比我想象中的年轻多了。
在第三次进她的小站时,我喜欢上了她的歌。或许我有点慢热,但是我想说,这样的节奏,恰到好处地将我带入一个音乐人的世界里,对我来说,正是最好的时机。
其实,在《四方上下》这首没有歌词的随性哼唱的作品中,陈粒的才华已经不言而喻。它让我想到了王菲早年的专辑《浮躁》,这种抛弃语言、直指音乐本体的吟唱,更能彰显人的艺术直觉能力。按照柏格森的说法,直觉能使人“突然地看到处于对象后面的生命的冲动,看到它的整体,哪怕只是在一瞬间”,《四方上下》正是给了我这样的惊喜:它幻化了陈粒的心象,正像是她的音乐世界的写照。
陈粒的作品更新得快,唱得也越来越好,我听得越多,越是感觉到惊喜。我彻底纠正了开始时对她的狭隘判断,而且我坚信:如果谁把她看作是小清新,那完全是在侮辱她。她的音乐气象有一种这个年龄难得一见的宏大,更有一种想突破自己、不屑从众、自成一派的野心,这完全不是坐井观天的“小清新”所能比拟的。在这种诉求的推动下,她的音乐呈现出一种强力,一种尼采式的艺术生命力,甚至说是满满的艺术力比多。她的宏大,不是在人文视野的开阔上,而是在于对自我。对于自我,陈粒有很强的探照感和介入感,在个人情感与情绪的空间里,她能运用艺术强力,将自己掘得很深,直到掘出一个迷惘的自己——而这种没有方向的迷失,正是青春特有的符号。
当代的“民谣”这一体裁,似乎从一开始,就暗含了一个抒情的维度。可以说,陈粒的情感织体是编织得非常密实的,但是,她又不同于一般的民谣抒情歌手。一般的民谣,给人一种整体的“中庸”感,在被“规驯”的抒情的制约下,它们有着古典时期所倡导的“平衡”与“整饬”。而陈粒的“民谣”却让我想到了穆旦在1940年代写下的那些诗歌,充满了极度的不平衡性,有各种各样的力在里面彼此角逐、互相反抗,营造了一个有张力的内部空间,带入了紧张感与迷失感。在这里我还不得不提一下陈粒的声音,她的声音有起落,有开合,正是表现这种情感的绝妙载体。
是的,强烈、冲撞、迷失、挣扎、略带荒芜的矛盾感,是陈粒的音乐不同于当下民谣的最主要特征。当下的民谣界,虽不乏翘楚的人才,但亦有大量半吊子水平的庸才,这导致民谣在思想的转轨上慢了一拍,它没有摇滚的先锋,有时候甚至不及通俗音乐,后者在把握当下生活时更为迅捷与宽阔。但作为新生一代的音乐人,陈粒一出现,就是彻底“当代的”,民谣的那种“慢”对她不构成先天的影响:她的姿态当下,音乐气质当下,散发出来的个体气质,也是当代的产物。
陈粒称自己的新唱片《如也》是“anti-folk”(反民谣)的。这个姿态表明了她对当下无节操无深度滥俗民谣的抵制与悖离。但是,不同于当下民谣,不等于不属于当代。她这种达达式的反对姿态,何尝不是现代性的产物呢?现代性正是最大的现实主义,它推动着人们用不同的立场、方式介入当下。
陈粒自己作曲,有时候自己作词,有时候用别人的词。无论是自己的词还是别人的词,她都能稳妥地驾驭起来,与自己的个性融为一体。作曲与编曲上的优势,使她可以更充分地用好自己的声音,并展现出音色中有美感的一面。从早期的《我只去过东南亚》,到颇受好评的《奇妙能力歌》再到《祝星》,陈粒的演唱在多变中渐渐走向成熟。《奇妙能力歌》《★》一类歌中,她用低吟浅唱表现出惆怅、淼远、略带忧伤的情绪,后者有迷幻与飘逸感;而在唱《祝星》《历历万乡》一类歌曲时,她的声音又变得厚实、明亮,有独特的表现力;《正趣果上果》《性空山》《五言》,则让我想到了中国的戏曲,在她这个年纪,有一种主动向传统回溯的选择,非常难得。
说了这么多,其实陈粒对我最大的吸引力,就在于她的音乐气质,这是真正让我感觉到“迷人”的。在《如也》发行时,我觉得她这一时期的艺术个性已经很明显了,对于一位90后音乐人来说,这实属不易。能取得目前的成绩,不仅基于大量的创作,还需要宝贵的实践(她曾任空想家乐队主唱),最主要的,还是那个老套的说法——艺术是从个人心象里化出的东西,传统的“知人论世”作品论有道理,什么样的人,就会有什么样的作品。从《我只去过东南亚》到《你疯狂画画,我就在你身后弹吉他》《妙龄童》再到《光》,陈粒逐渐摸索出了最适合表现自己个性的唱腔、风格,显示出了她的洒脱、不羁与不俗。她的《走马》唱得随性自如,《不灭》《历历万乡》中则有一种难得的江湖感和大气,而《易燃易爆炸》《光》中,她对细腻的情绪起伏又拿捏得收放自如。多元中有内在的线索,这使得她在立足于一个抒情向度的同时打开了更开阔的空间。
在音乐的世界里,陈粒坦诚,不伪饰。从她早期参加音乐比赛的一些视频来看,那时她还因着表演的需要,追求与台下观众的互动,但是很快,这个悟性极高的女孩就打碎了外在的牵绊,建立起一个自由自在的音乐园地,她有完全的天分,可以一下子抓住艺术的本质;也有足够的勤奋,在半年多的时间里创作了数十首歌曲。
在自己的园地中,陈粒的作品有独白性,她不惮于表达最本真的自我。她的音乐中有很多前意识的元素,整个地充满了本我与自我的纠葛、争战,而她的超我却又有想统摄、改造前两者的控制力,于是,我们看到了一个分裂的、矛盾的形象。这种内在的紧张与对超我规约的不驯,使陈粒的歌里满是横飞的爱欲,有丰沛的血肉感,如《祝星》里唱的:“你掐断了我的时间/你放空了我的无解/亲吻我//你带我乘着宇宙忽快忽慢/你带我看这世界忽明忽暗/你的回忆开始沉没/你的眼神再次清澈/你进入我”。在爱欲的倾诉、享乐与无解面前,“死亡本能”又是她音乐的另一面。在《如也》一歌中,陈粒这样形容自己面临的深渊:“残缺的虚伪的好的坏的……遗留的曾经的活的死的”,她连续使用了几个动宾短语“缠着我”“折磨我”“吞噬我”“惩罚我”“审视我”,以此表现自己被动的困境。死亡本能具有一种破坏冲动,体现在《绝对占有,绝对自由》里,就与对性/爱的占有欲和控制欲结合在一起:“让我占有你/撕碎你然后像风握在我手里/抱着我像空气/想把你收集/泡你在福尔马林盯着你意淫”。这种大胆赤裸的表述,让我想起曹禺《雷雨》里的周蘩漪,这个困兽一样的女人,对待爱情的态度是极端的:她不给爱与恨提供一个中间地带,在她的词典里,只有绝对的爱,一旦爱消亡了,便只剩绝对的恨,而恨又走向疯狂与毁灭。有人说陈粒的音乐里有哥特范,其实我倒并不认为这是哥特。在西方,哥特有很深的宗教背景;而陈粒歌曲里的爱欲与死亡本能,不需要有“宗教”或“文化”这一道桥梁,只需从敏锐的自身体验出发,便能直抵人的原初与本质。
《南都娱乐周刊》这样评价陈粒:“陈粒有一个生错时代的身体和灵魂,歌声里老练达观的冷艳颇为罕见,哲学式思考,哥特式造句,在黑暗里的幽微和自赏,枯涩跳脱的意趣,这些都难以和刚刚二十出头的音乐人挂上钩,然而,所有剑走偏锋的‘怪都是自然而然的流露。”而我认为,陈粒的可贵之处,在于她为民谣提供了一个新的审美范畴:她有冷艳强悍的一面,也有青春的迷惘与真,她像一个音乐的妖精,无所顾忌地运用性情的巫术,将自我、爱欲表现得淋漓畅快。她有一些“怪”,但更多的是“真”。她确实是“剑走偏锋”的——她不是缺乏思考力的乖乖女,对于媚俗,她有自己的判断;她的内心有彷徨,也有孤傲,正是后者支撑着她一直走自己的路。
写下这些文字时,我不时想起美国电影《天鹅绒金矿》,陈粒让我联想到片中的男主角白雪妖——才华横溢,不走寻常路;躁动不安、迷惘,有颓废,也有抗议。然而我有隐忧:但愿陈粒的“剑走偏锋”不会像白雪妖那样,最终伤了才华、也伤了她自己,但愿她不会在短暂的爆发后陷入沉寂与孤绝,但愿她最后会与这个既温暖又冰冷的世界握手言和。因为,我还对她有更多的期待:她已经让我感到惊艳了,在将来,她还有潜力创造出更好的作品;在音乐之路上,她应该越过更多的高山,直到看见海洋。
杨碧薇,诗人,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诗集《诗摇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