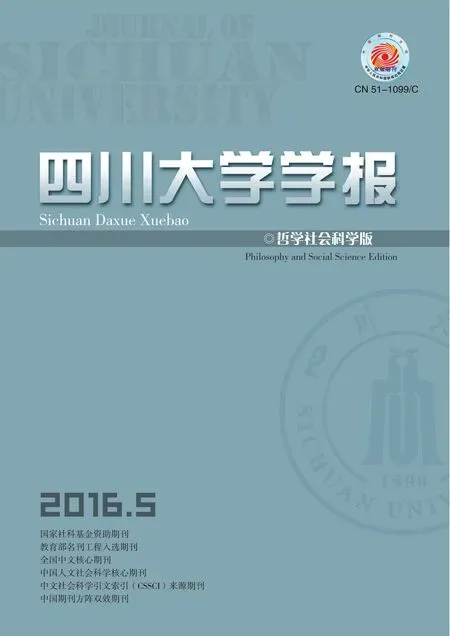感生、异表和胁生
——由纬书及相关文献看西汉时期佛教对中土的影响
孙尚勇
§宗教文化研究§
感生、异表和胁生
——由纬书及相关文献看西汉时期佛教对中土的影响
孙尚勇
汉代纬书及相关文献所见以孔子为代表的感生神话之因梦感生、出生预言、神女沐浴等情节,在先秦文献所载感生神话中均未曾出现,它们当是接受了佛教关于释迦诞生神话的影响。渊源于汉代纬书的孔子四十九种异表的记述,借鉴了佛教所传释迦的形象。上博简《子羔》中所记述的禹和契的胁生神话属于将感生、瑞征式胁生和“生而能言”三者密切结合的文本,这与佛教释迦感生神话的模式完全相同,而与西汉及稍前文献所见胁生神话之事实叙述和凶兆叙述大不相同,它极可能是受到纬书与印度佛教思想影响而写定的文本。这些事实证明,早在西汉中后期,佛教思想已经开始对中土产生局部的影响。纬书及相关文献对佛教思想资源的借用,其目的是服务于汉代的神学政治。
感生神话;圣人形象;汉代纬书;佛教影响
先秦文献所见感生神话,主要为契与稷的感生,而汉代纬书则塑造了大量的圣人感生神话,其中以孔子感生最有代表性,也最为后世所关注。圣人异表,先秦文献和《史记》中皆不多见,而汉代纬书却出现了大量记述,其中仍以孔子异表最为独特。胁生神话,先秦文献稀见,汉代文献则出现了关于禹、契的胁生神话。孔子感生、异表及禹、契胁生神话,既有论述颇多,但其间关涉汉代中土思想与外来佛教思想交汇的问题,前贤未遑论及,今尝试论之。
一、孔子感生
纬书制造的孔子感生神话主要有两则。《春秋孔演图》:“孔子母征在游大泽之陂,睡梦黑帝使请己。已往,梦交,语曰:汝乳必于空桑之中。觉则若感,生丘于空桑中。”*《太平御览》卷三六一,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663页。又见《艺文类聚》卷八八,上海:中华书局,1965年,第1519页;《太平御览》卷九五五,第4239页。此二处“大泽”作“大冢”,余略同。参看安居香山、中村璋八辑:《纬书集成》,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576页。《论语纬撰考》:“叔梁纥与征在祷尼丘山,感黑龙之精,以生仲尼。”*《礼记·檀弓上》孔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275页下。参看《纬书集成》,第1069页。与此相关的一则记载见于《伏侯古今注》:
孔子生之夜,有二苍龙自天而下,有二神女擎香雾,于空中以沐征在。先是,有五老列于庭,则五星之精。有麟吐玉书于阙里人家,云:“水精之子,继商周而素王出。”故苍龙绕室,五星降庭。征在知其为异,乃以绣绂系麟角而去。至敬王末,鲁定公二十四年,鲁人鉏商田于大泽,得麟,以示夫子。夫子知命之终,乃抱麟解绂而涕泗焉*薛据:《孔子集语》卷下,《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09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349页。
《伏侯古今注》的作者伏无忌,生当东汉后期,为汉初传古文《尚书》的济南伏生的十三世孙。据四库馆臣的意见,伏生《尚书大传》在文体上与纬书完全一致;*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47页。又《伏侯古今注》所云“水精之子”,与纬书所说“睡梦黑帝使”“感黑龙之精”属同一性质。故这则材料虽不出于汉代纬书,但实与纬书有着共同的思想基础,很可能是伏无忌自纬书中抄出。
明代孙瑴即对纬书所见孔子感生神话持怀疑态度。他认为:根据《孔子家语》的记载,叔梁纥早年娶妻生长子孟皮字伯尼,七十以后娶颜氏生次子孔丘字仲尼,“是叔梁纥故有妻,而孔子故有兄也。神孔子之生者,则又过奇”;孔子降生时苍龙神女之说,同样“恐或出好奇之口,未敢为信”。*孙瑴在其所编《古微书》卷八《春秋演孔图》“孔子母颜氏征在游大泽之陂,睡梦黑帝使请己往,梦交,语曰:女乳必于空桑之中。觉则若感,生丘于空桑。首类尼丘山故名”下所做按语,济南:山东友谊书社,1990年影印嘉庆丙子对山问月楼重校本,第190-191页。本文认为,对纬书所见孔子感生神话,持怀疑态度是有必要的,但更有必要的是,应该将这些内容与先秦的感生神话作具体的比较,找出其间存在的差异,进而分析这些差异的起源,归结到一个问题就是:“好奇之口”依靠何种思想资源制造了“过奇”的孔子感生神话?
圣人感生神话,传世先秦文献明确记载的只有商始祖契和周始祖稷的感生神话。契的感生神话最早见载于《诗·商颂》之《玄鸟》和《长发》。《玄鸟》曰:“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长发》曰:“有娀方将,帝立子生商。”又屈原《天问》曰:“简狄在台,喾何宜,玄鸟致贻,女何喜。”《九章·思美人》曰:“高辛之灵盛兮,遭玄鸟而致诒。”这些记录较为简单。《史记·殷本纪》有详述:“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相近记述又见《尚书中候握契》《诗含神雾》等诸多晚出文献,其核心内容同为简狄吞(怀)玄鸟卵而有孕,生下了商始祖契。稷的感生神话最早见载于《诗·大雅·生民》和《鲁颂·閟宫》。《生民》曰:“厥初生民,时维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无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载震载夙。载生载育,时维后稷。诞弥厥月,先生如达。不坼不副,无菑无害。”《閟宫》曰:“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无灾无害,弥月不迟,是生后稷。”又《天问》:“稷维元子,帝何竺之,投之于冰上,鸟何燠之。”《史记·周本纪》亦有详述:“周后稷,名弃。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原。姜原为帝喾元妃。姜原出野,见巨人迹,心忻然说,欲践之。践之而身动如孕者。居期而生子。”相近记述又见《春秋元命苞》:“神始行从道,道必有迹,而姜嫄履之,意感,遂生后稷于扶桑之所出之野。”《诗含神雾》:“后稷母为姜嫄,出见大人迹而履践之,知于身,则生后稷。”*本段所引述之《尚书中候握契》《诗含神雾》《春秋元命苞》,见《纬书集成》,第447、462-463、539页。另,本文所用《史记》《后汉书》等史籍均为中华书局标点本,《楚辞》为中华书局点校洪兴祖补注本,《诗经》为中华书局影印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国语》为上海古籍出版社点校本,《左传》为杨伯峻注本,常见文献,不一一标注页码。其关注点为姜嫄履大人迹而怀孕生子。
先秦文献所见圣人感生神话主要为以上两种,*除了圣人感生外,尚有见载于《国语·郑语》和《史记·周本纪》的祸国者褒姒的感龙精玄鼋而生的神话。这是对西周灭亡所作的一种感生神话思维的解释。它们是后来诸多感生神话记录者或制造者的基本依据和主要思想资源。除孔子感生外,汉代纬书记述了十几种感生神话,如华胥履大人迹生伏羲、安登感神龙首生神农、附宝感大电光生黄帝、女枢感瑶光之星生颛顼、赤都与赤龙合昏生帝尧、握登感大虹生帝舜、修己感薏苡或流星生夏禹、扶都感白气贯月生商汤、太任梦长人感己生文王、子路感雷精而生等。*出于《河图稽命征》《河图》《春秋元命苞》《诗含神雾》《春秋合诚图》《礼含文嘉》《尚书帝命验》《论语谶》等,见《纬书集成》,第1179-1181、1222-1223、589、462-463、764、495、369、1083页。《论衡·奇怪》:“谶书又言:尧母庆都野出,赤龙感己,遂生尧。《高祖本纪》言: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见蛟龙于上。已而有身,遂生高祖。其言神验,文又明著,世儒学者,莫谓不然。如实论之,虚妄言也。”*王充:《论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4年。本文所引《奇怪》篇,分见第50、53页,不一一标注。由王充此说来看,纬书所记感生神话,大多出于西汉,并没有先秦中土文献和思想依据。
上述纬书所见上古帝王的感生神话是按照五行相生制造出来的,有着强烈的现实政治指向,其目的就是要证明汉室统治的合法性。*参见杨权:《谶纬文献中的几个政治文化命题》,《周秦汉唐文化研究》第4辑,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年。这些感生神话,极少数带有上古口传神话的印痕,绝大多数则出于汉人的附会。比如其中的黄帝感生就纯属后出附会之说,因为据《国语·晋语四》所载“昔少典氏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反映的事实是少典氏的女子与有蟜氏的男子结合,为氏族外婚,后生了黄帝和炎帝。少典既为黄帝母系,附宝便不可能同样成为黄帝母系,可知附宝感电光生黄帝出于附会。*参见潜明兹:《中国神话学》,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66-367页。联系《后汉书·尹敏传》所言纬书“多近鄙别字,颇类世俗之辞”、《张衡传》“必虚伪之徒,以要世取资”的说法,可以推测,这些感生神话的制造者极可能为出身于通一经的下层儒生,他们的知识视野较为有限,对古典的了解并不全面,更谈不上深刻了。而汉高祖刘邦感生又为尧后的说法,属于与黄帝感生相近的例子,更是汉代伦理观念、政治需要和今古文经学的冲突与妥协等多重因素造成的。*参见钟肇鹏:《谶纬论略》,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100页;杨权:《谶纬文献中的几个政治文化命题》,《周秦汉唐文化研究》第4辑,第158页。
纬书之外,成书于汉武帝后期的《史记》亦记载了几则于先秦文献无征或后起的感生神话。《秦本纪》载有秦始祖大业的感生神话:“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修。女修织,玄鸟陨卵。女修吞之,生子大业。”这与商契的感生神话属同一性质,可能是秦人参照契、稷感生而制造的神话,其来源当为《秦记》一类秦国文献。《高祖本纪》载有高祖的感生神话:“高祖,沛丰邑中阳里人,姓刘氏,字季。父曰太公,母曰刘媪。其先,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蛟龙于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纬书中又记述了与《史记》不同的高祖的感生神话。《诗含神雾》:“含始吞赤珠,刻曰玉英,生汉皇。后赤龙感女媪,刘季兴。”《春秋握诚图》:“执嘉妻含始游雒池,赤珠出,刻曰:玉英吞此者为王客。以其年生刘季,为汉皇。”见《纬书集成》,第463、826页。《外戚世家》载有文帝的感生神话:“薄姬曰:昨暮夜妾梦苍龙据吾腹。高祖曰:此贵征也,吾为汝遂成之。一幸生男,是为代王。”据《论衡·奇怪》所论,这些都是汉代儒生制造的感生神话,其实质是为了给高祖和文帝制造“受命之证”。
以上包括孔子在内的感生神话,无一例外,其核心都在于交待圣人的出生是因缘于某种动物图腾,或天帝,或某种天象,或某五行帝,即“圣人皆感天而生”。其中高祖与文帝的两则神话与《论语撰考》所载孔子感生神话有近似之处,都有父亲角色的参与;而其他感生神话,都只出现母亲,并无父亲的参与。这证明孔子、高祖和文帝的感生神话产生年代比较晚,是后期人为制造出来的,并没有较早母系氏族生活、部族信仰或图腾崇拜的基础。*中外都有关于部族始祖、宗教创始人和政权创建者的感生神话,其中部分是早期人类追述部族起源时出现的,另外一些则是出于政治目的,为了自神其道而人为制造的。参见钟敬文:《晚清革命派著作家的民间文艺学》,《钟敬文民俗学论集》,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52-61页。高祖和文帝的感生神话,虽然都是汉代儒生制造出来的,但二者的指向却大不相同。高祖感生神话忽略了高祖与其父刘公之间的血缘关系,强调的是高祖受命于天。此则神话中,刘公似乎是作为看客,目睹了妻子与龙交配的场景,颇有讽刺意味。文帝的感生神话则是薄姬先梦苍龙据腹,后与高祖交配而生文帝。这则神话既保留了“感天而生”,又避免了“圣人皆无父”的尴尬。*圣人感生、有父无父是汉代经学的重要论题。《史记·三代世表》褚先生补曰:“张夫子问褚先生曰:《诗》言契、后稷皆无父而生,今案诸传记,咸言有父,父皆黄帝子也,得无与《诗》谬乎?褚先生曰:不然。《诗》言契生于卵,后稷人迹者,欲见其有天命精诚之意耳。鬼神不能自成,须人而生,奈何无父而生乎。一言有父,一言无父,信以传信,疑以传疑,故两言之。”许慎《说文解字》(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段注本)女部:“姓,人所生也。古之神圣人,母感天而生子,故称天子。”许慎《五经异义》:“《诗》齐鲁韩、《春秋公羊》说,圣人皆无父,感天而生。《左氏》说,圣人皆有父。谨按:《尧典》:以亲九族。即尧母庆都感赤龙而生尧,尧安得九族而亲之。《礼谶》云:唐五庙。知不感天而生。”对此,郑玄驳云:“玄之闻也,诸言感生得无父,有父则不感生,此皆偏见之说也。《商颂》曰: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谓娀简吞鳦子生契,是圣人感生见于经之明文。刘媪是汉太上皇之妻,感赤龙而生高祖,是非有父感神而生者也。且夫蒲卢之气妪煦桑虫成为己子,况乎天气因人之精就而神之,反不使子圣贤乎。是则然矣,又何多怪。”(见《生民》“以赫厥灵,上帝不宁,不康禋祀,居然生子”孔颖达正义引)其解经指向皆如《三代世表》褚先生补所云“夫布衣匹夫安能无故而起王天下乎,其有天命然”。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亦援引《五经异义》和郑玄之说,曰:“按此郑君调停之说。许作《异义》时,从《左氏》说圣人皆有父。造《说文》则云神圣之母感天而生,不言圣人无父。则与郑说同矣。”高祖为汉政权之开创者,继其法统者必有其血统,故儒生制造了文帝似是而非的感生神话;相较之下,高祖与其父刘公之间则无需血统的纯正,重要的是要证明高祖受命于天。
《诗含神雾》记文王、《春秋孔演图》记孔子、《史记》记高祖和文帝四则感生神话,其共性是,圣人的感生都与母亲的梦相关。这既与汉代文献所记其他感生神话相区别,亦与《诗经》所记契和稷的感生神话相区别。换言之,“因梦感生”在先秦文献中未曾出现过,*文王、孔子、高祖的因梦感生,指母亲在梦中与长人、神或龙性交而生,并非简单地梦见某种祥瑞而生子。《左传》宣公三年:“初,郑文公有贱妾曰燕姞,梦天使与己兰,曰:‘余为伯鯈。余,而祖也。以是为而子。以兰有国香,人服媚之如是。’既而文公见之,与之兰而御之。辞曰:‘妾不才,幸而有子,将不信,敢征兰乎?’公曰:‘诺。’生穆公,名之曰兰。”《国语·周语下》:“成公之生也,其母梦神规其臀以墨,曰:‘使有晋国,三而畀驩之孙。’故名之曰‘黑臀’,于今再矣。”类此二则与梦有关的生子故事,母在梦中均未曾或不可能与神性交,故与本文所说的因梦感生不同,因而它们与感生神话无涉。在汉代制造的诸多感生神话中亦较为独特。王充在《论衡·奇怪》中就已认为,“梦与神遇”云云纯粹是儒生穿凿附会之说。那么,“自神其道”的儒生为什么会以梦的方式去附会,亦即因梦感生的思想资源何在?《伏侯古今注》中“水精之子,继商周而素王出”一句,目的在于告诉人们,感生者是一位圣人。这属于预言,汉代及《诗经》所见其他感生神话则都没有这类预言。顾颉刚《春秋时的孔子和汉代的孔子》所云“他们说孔子生之夜,有二苍龙自天而下,有二神女擎赤雾于空中以沐征在”,*顾颉刚:《春秋时的孔子和汉代的孔子》(1926),《古史辨》第二册,北京:景山书社,1930年,第137页。转述的正是《古今注》的材料,但顾氏对此未作任何分析评论。神女沐浴情节在纬书及更早的感生神话中亦从未出现过。*《国语·晋语四》:“昔者,大任娠文王不变,少溲于豕牢,而得文王,不加疾焉。”(此条亦见《生民》孔颖达正义引,文字稍异)文王生于厕所的记载,当为事实,与孔子降生神话的性质不同。由此,我们的问题是,圣人出生预言以及神女沐浴的思想资源又何在?
既然中国传统经典中没有孔子感生神话的因梦感生、出生预言、神女沐浴等内容,那么,我们可以考虑在张骞“凿空西域”而引发的中西文化交流第一次大繁荣的背景当中去寻求上述问题的可能答案。*《梁书·刘之遴传》:“之遴爱古好奇,在荆州聚古器数十百种。……又献古器四种于东宫。……其第三种,外国澡罐一口,铭云:元封二年龟兹国献。”1969年,德国学者刘茂才撰文认为,澡罐是佛僧用具,证明至迟在元封二年(前109)佛教已传入龟兹(参见耿世民:《古代维吾尔语佛教原始剧本弥勒会见记(哈密写本)研究》注1,《文史》第12辑,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24页)。又有学者认为,佛教传入龟兹在元狩元年(前122)或稍前(陈世良:《关于佛教初传龟兹》,《西域研究》1991年第4期)。又,1930年代丁山在《吴回考——论荆楚文化所受印度之影响》(见其著《古代神话与民族》,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339-389页)一文中讨论了上古至春秋战国楚文化所受印度文化习俗及吠陀的影响。丁山认为,“在史前游牧时代,世界文化的交流,远比我们农业社会人所想像的为利便。……我绝对相信东西文化的交流,不自张骞凿空始”(《古代神话与民族·自序》,第25页)。这些见解极有见地。东汉竺大力、康孟详所译《修行本起经》卷上记述了释迦牟尼的感生说:
于是能仁菩萨化乘白象,来就母胎。用四月八日,夫人沐浴,涂香着新衣毕,小如安身。梦见空中有乘白象,光明悉照天下,弹琴鼓乐,弦歌之声,散花烧香,来诣我上,忽然不见。夫人惊寤,王即问曰:何故惊动?夫人言:向于梦中,见乘白象者,空中飞来,弹琴鼓乐,散花烧香,来在我上,忽不复现,是以惊觉。王意恐惧,心为不乐,便召相师随若耶,占其所梦。相师言:此梦者,是王福庆,圣神降胎,故有是梦。生子处家,当为转轮飞行皇帝,出家学道,当得作佛,度脱十方。王意欢喜。……十月已满,太子身成。到四月七日,夫人出游,过流民树下,众花开化,明星出时,夫人攀树枝,便从右胁生。堕地行七步,举手而言:天上天下,唯我为尊,三界皆苦,吾当安之。应时天地大动,三千大千刹土,莫不大明。释梵四王,与其官属诸龙鬼神、阅叉、揵陀罗、阿须伦,皆来侍卫。有龙王兄弟,一名迦罗,二名郁迦罗,左雨温水,右雨冷泉。释梵摩持天衣裹之,天雨花香,弹琴鼓乐,熏香烧香,捣香泽香,虚空侧塞。夫人抱太子,乘交龙车,幢幡伎乐,导从还宫。*《大正新修大藏经》第3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75年,第463页。
从中可知,在佛教徒制造的释迦牟尼的感生神话中,释迦是乘白象于母亲梦中作胎的。这与汉代中土文献所见“太任梦长人感己”、征在“黑帝使,请己往梦交”、刘媪“梦与神遇”、薄姬“梦苍龙”是相同的。而且,《史记》所云“蛟龙于其上”“据吾腹”云云,亦与《修行本起经》“来诣我上”“来在我上”的记述颇为相似。《修行本起经》“生子处家,当为转轮飞行皇帝,出家学道,当得作佛,度脱十方”的话,与孔子感生神话中“水精之子,继商周而素王出”一句的意义指向也是一样的。二者的差异在于:《修行本起经》的预言出于相师之口,预言的时间在释迦受胎之时;《伏侯古今注》中则为麟吐玉书,时间在孔子诞生之夜。如果考虑到汉代佛教以口头传播的方式介入中土信仰的事实,*《后汉书·楚王英传》载楚王刘英“学为浮屠斋戒祭祀”,而明帝诏书曰:“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絜斋三月,与神为誓,何嫌何疑,当有悔吝?其还赎,以助伊蒲塞桑门之盛馔。”又据《后汉书·襄楷传》所载,刘英之后约一百年,桓帝“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那么这种差异便不会构成前者影响后者的反证。此外,孔子感生神话中“二神女擎香雾,于空中以沐征在”,与《修行本起经》“有龙王兄弟,一名迦罗,二名郁迦罗,左雨温水,右雨冷泉”的情节亦非常接近。
《修行本起经》虽成书于公元前后,译于东汉,但其中所载故事的渊源甚早。巴利文《神通游戏》中已记载释迦因梦感生和出生预言,巴利文《中尼迦耶》亦说:“菩萨出母胎,空中涌两泉,一凉一温,浇灌菩萨和母亲。”*引据郭良鋆:《佛陀和原始佛教思想》,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29-30、28页。此外,《中阿含经》卷八曰:“若世尊初生之时,则于母前而生大池,其水满岸,令母于此得用清净者。我受持是世尊未曾有法,我闻世尊初生之时,上虚空中雨水注下,一冷一暖,灌世尊身。”*《大正新修大藏经》第1册,第470页。这三种经典的产生年代大约在阿育王孔雀王朝(约公元前324年-约前187年)之前,其中所载故事的产生年代则要更早一些。
综上可得出初步结论,汉代纬书及相关文献所见以孔子为代表的感生神话中因梦感生、出生预言、神女沐浴等情节,均接受了佛教关于释迦诞生神话的影响。
二、孔子异表
纬书对孔子异表的记述,以《春秋演孔图》最为集中,大约五十余种:
孔子长十尺,海口,尼首,方面,月角,日准,河目,龙颡,斗唇,昌颜,均颐,辅喉,齿,龙形,龟脊,虎掌,胼协,修肱,参膺,圩顶,山脐,林背,翼臂,注头,阜脥,堤眉,地定,谷窍,雷声,泽腹,修上趋下,末偻后耳,面如蒙倛,手垂过膝,耳垂珠庭,眉十二采,目六十四理,立如凤峙,坐如龙蹲,手握天文,足履度字,望之如朴,就之如升,视若营四海,躬履谦让,腰大十围,胸应矩,舌理七重,钧文在掌。胸文曰:制作定世符运。*参见怀荃堂刻本《黄氏逸书考》第四七册,第二十九至三十叶;《纬书集成》,第577页。
顾颉刚较早引用了这则材料,但他只是说:“还有许多庄严妙相,恕我不钞了。我自恨不会画图,不能照他们说的画出;不然,我们可以看看,在他们的想象中,孔子尚不像一个人。”*顾颉刚:《中国上古史研究讲义》,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260页。
纬书记圣人异表,大多很简单,如《春秋演孔图》中的“伏牺大目”“黄帝龙颜”“仓颉四目”“颛帝戴干”“帝佶戴干”“尧眉八采”“舜目重瞳”“禹耳三漏”“汤臂三肘”“文王四乳”“武王骈齿”“帝喾骈齿”“皋陶鸟喙”“武王望羊”“周公偻背”“伊尹大而短,赤色而髯好”,《论语撰考》中的“颜回有角额,似月形”,等等。稍见复杂者,如《春秋合诚图》记伏羲:“伏羲龙身牛首,渠肩达掖,山准日角,奯目珠衡,骏毫巤鼠,龙唇龟齿,长九尺有一寸,望之广,视之专。”《河图稽命征》记刘邦:“帝刘季日角,戴北斗,胸龟背龙,身长七尺八寸,明圣而宽仁,好任主。”*以上所引分别参见《纬书集成》,第573-576、1069、762、1179页。但与孔子异表相比,这些仍然只能算是简单的。
先秦文献中,《荀子·非相》较早对圣人异表作了记录,如“帝尧长,帝舜短,文王长,周公短,仲尼长,子弓短”、周公“身如断菑”、皋陶“色如削瓜”、仲尼“面如蒙倛”、傅说“身如植鳍”、伊尹“面无须麋”以及“禹跳,汤偏,尧舜三牟子”。*王先谦:《荀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73-75页。汉代文献中,《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记舜、禹、文王的异表:“至舜形体,大上而员首,而明有二童子。……至禹生发于背,形体长,长足肵,疾行先左,随以右,劳左佚右也。……至汤体长专小,足左扁而右便,劳右而佚左也。……至文王形体博大,有四乳而大足。”*曾振宇、傅永聚:《春秋繁露新注》,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149页。《淮南子·修务》提及尧、舜、禹、文王和皋陶的异表。《论衡·骨相》:“传言黄帝龙颜,颛顼戴午,帝喾骈齿,尧眉八彩,舜目重瞳,禹耳三漏,汤臂再肘,文王四乳,武王望阳,周公背偻,皋陶马口,孔子反羽。”*王充:《论衡》,第36页。诸书对圣人异表的记载均要言不烦。作为汉代今文经学的集大成之作,《白虎通·圣人》亦记述了伏羲、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禹、皋陶、汤、文王、武王、周公、孔子的异表,但大体与上引各家记载相近。
孔子有圣人之表,似乎是其当世就有的说法,而孔子本人对此也并不否认。《史记·孔子世家》曰:“孔子适郑,与弟子相失,孔子独立郭东门。郑人或谓子贡曰:东门有人,其颡似尧,其项类皋陶,其肩类子产,然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累累若丧家之狗。子贡以实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状,末也。而谓似丧家之狗,然哉!然哉!”类似记载又见《孔子家语·困誓》。《孔丛子·嘉言》曰:“吾观孔仲尼有圣人之表,河目而隆颡,黄帝之形貌也;修肱而龟背,长九尺有六寸,成汤之容体也。”*引据孙少华:《孔丛子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544-545页。这些关于孔子异表的记载强调的是孔子与古代圣人的近似,亦较为简单。除《荀子》所说“面如蒙倛”和《论衡》所说“反羽”之外,又有《庄子·外物》所云“修上而趋下,末偻而后耳,视若营四海”,*郭庆藩:《庄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922页。《孔子世家》所云“生而首上圩顶”,亦未见繁富。纬书所述孔子异表,主要是综合上述诸书的记述及其他圣人的异表而成,但其中“手垂过膝”一项在其他圣人异表描写中未曾出现过,值得关注。
1949年,季羡林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正史与印度传说》一文中讨论了三国至北朝正史中帝王异表的记载。他将《史记》舜与项羽重瞳、孔子“生而首上圩顶”、刘邦“左股有七十二黑子”等记载视作大人异表的第一类型,以为“颇近事实”;将纬书所记禹“虎鼻河目,骈齿鸟喙,耳三漏”、伏羲“龙身牛首”等视作第二类型,以为“荒诞诡异”;将《三国志》刘备“垂手下膝,顾自见其耳”、《魏书》太祖拓跋珪“广颡大耳”等视作第三类型,以为此类“事实上绝不可能”,但又“不似纬书之荒诞诡异”。结论认为,正史中类似刘备垂手过膝、自顾其耳的记载乃受佛教所说佛陀三十二相八十种好的影响。*参见季羡林:《印度古代语言论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385-391页。在《中印文化交流史》中季羡林对其之前的观点作了强调:
在南北朝的许多正史里都讲到帝王,特别是开基立业的帝王们的生理特点,比如:《三国志·魏志·明帝纪》裴注引孙盛的说法,说明帝的头发一直垂到地上;《三国志·蜀志·先主纪》,说刘备垂手下膝,能看到自己的耳朵;《晋书·武帝纪》,说武帝的手一直垂到膝盖以下;《陈书·宣帝纪》,说宣帝垂手过膝;《魏书·太祖纪》,说太祖广颡大耳;《北齐书·神武纪》,说神武长头高颧,齿白如玉;《周书·文帝纪》,说文帝头发到地上,垂手过膝,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这些神奇的不正常的生理现象都是受了印度的影响。佛书就说,释迦牟尼有大人三十二相和八十种好,耳朵大,头发长,垂手过膝,牙齿白都包括在里面。*《季羡林文集》(第四卷),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450页。
季羡林的意见是可信的。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春秋演孔图》孔子的“耳垂珠庭”、《三国志》刘备的“顾自见其耳”,并不完全来自释迦的形象。因为在《史记》的记载中,老子便是耳朵大而且有毛,在《山海经》之《大荒北经》中有儋耳国、《海内南经》有离耳国、《海外北经》有聂耳国。《汉书·武帝纪》载有儋耳郡,颜师古注:“应劭曰:……儋耳者,种大耳。渠率自谓王者耳尤缓,下肩三寸。张晏曰:……儋耳之云,镂其颊皮,上连耳匡,分为数支,状似鸡肠,累耳下垂。”又,1976年出土的汉昭宣时期洛阳卜千秋墓,墓室西壁中部绘有猪头大耳神壁画。*洛阳博物馆:《洛阳卜千秋壁画墓发掘简报》,《文物》1977年第6期。猪头神壁画见《文物》该期图版壹。这些事实证明,大耳朵自有中国的传统。另外,大洋洲和南美洲一些土著民族中对大耳朵的信仰,*参见萧兵:《大耳朵的老先生——从文化人类学推测老子的名称和身份》,《淮阴师专学报》1992年第1期。也说明“顾自见其耳”是完全可能的。
《春秋演孔图》所见孔子异表的材料,为《黄氏逸书考》据清代流传的清河郡本《纬书》缉存。此《纬书》可能为清人伪作,不尽可信。*余作胜:《清河郡本乐纬辨正》,《中国音乐学》2013年第3期。但宋代孔传《东家杂记》卷下“先圣小影”条载曰:

将此与《春秋演孔图》孔子异表文字相对照,“手垂过膝”虽不见于《东家杂记》所引家谱,但《家谱》明确罗列的孔子“四十九表”,当渊源于汉代纬书,可以肯定它借鉴了佛教所传释迦的形象。
三、胁生神话
胁生是感生神话的分支,因文献所见与前述感生神话及孔子异表无直接关联,相关记述亦不见于纬书,故本文单列一节加以讨论。
中国胁生神话,涉及者主要为陆终六子、禹和契,见于西汉或成书于西汉稍前的文献有:《太平御览》卷三七一引《世本》:“陆终娶于鬼方氏之妹,谓之女嬇,生六子。孕而不育,三年,启其左胁,三人出焉,启其右胁,三人出焉。”*《太平御览》,第1712页。又《太平御览》卷三六一引《帝系》:“陆终娶鬼方国君之妹,谓之女嬇,生六子。孕而不育,三年,启其母左胁,三人出,右胁,三人出。”(第1663页)此则材料与《世本》所载全同,二者显然同源。《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禹生发于背,……契先发于胸。”*曾振宇、傅永聚:《春秋繁露新注》,第149页。《史记·楚世家》:“陆终生子六人,坼剖而产焉。”《大戴礼记·帝系》:“陆终氏娶于鬼方氏,鬼方氏之妹谓之女隤氏,产六子。孕而不粥,三年,启其左胁,六人出焉。”*黄怀信:《大戴礼记汇校集注》,西安:三秦出版社,2005年,第789-790页。更晚的记载见于《蜀王本纪》《吴越春秋》和《淮南子注》。*《蜀王本纪》:“禹本没山广柔县人,生于石纽,其地名痢儿畔。禹母吞珠孕禹,拆堛而生于县。”(《太平御览》卷八二引,第381页)《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禹父鲧者,帝颛顼之后。鲧娶于有莘氏之女,名曰女嬉,年壮未孳。嬉于砥山,得薏苡而吞之,意若为人所感,因而妊孕。剖胁而产高密。”(《吴越春秋》,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93页)高诱注《淮南子·修务训》“禹生于石,契生于卵”曰:“禹母修己,感石而生禹,折胸而出”,“契母,有娀氏之女简翟,吞燕卵而生契,愊背而出”。(张双棣:《淮南子校释》,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977、1978页)据张双棣笺释,感石而生者非禹,乃禹子启。《史通·古今正史》称“楚汉之际,有好事者,录自古帝王公侯卿大夫之世,终乎秦末,号曰《世本》,十五篇”,*浦起龙:《史通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312页。可知《太平御览》所引《世本》最早成书于楚汉之际。《帝系》虽亦为司马迁所信用,但它“很可能是战国晚期的作品”,*裘锡圭:《新出土先秦文献与古史传说》,《中国出土古文献十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6页。“是汉初时儒家后学者利用古史如《世本》之流加以综合改写的结果”,*钱杭:《帝系:传说时代的世系观念及其表达方式》,《天津社会科学》2010年第2期。其最终写定可能更晚一些。故上引诸书都可视作汉代文献。
陆终六子胁生,《史记》仅云“坼剖而产”,《世本》云左右胁各生三子,《大戴礼记·帝系》云六子皆自左胁生。《春秋繁露》说禹生于背、契生于胸;《蜀王本纪》则仅云禹拆堛而生;《吴越春秋》亦仅云禹剖胁而产;高诱注称禹折胸而出、契愊背而出,与《春秋繁露》恰恰相反。诸书记述的差异似乎证明陆终六子、禹和契的胁生神话在汉代未曾定型。
更为重要的是,王充在《论衡·奇怪》中已对上述胁生神话提出了否定意见:“彼《诗》言‘不坼不副’者,言后稷之生不感动母身也。儒生穿凿,因造禹、契逆生之说。”由此可知,《春秋繁露》的记载当缘于附会,董仲舒本人则极可能是这一附会的制造者。王充继而又说:“《诗》曰:不坼不副,是生后稷。说者又曰:禹、卨逆生,闿母背而出。后稷顺生,不坼不副,不感动母体,故曰不坼不副。逆生者子孙逆死,顺生者子孙顺亡,故桀、纣诛死,赧王夺邑。言之有头足,故人信其说,明事以验证,故人然其文。……如实论之,虚妄言也。……案《帝系》之篇及《三代世表》,禹,鲧之子也;卨、稷皆帝喾之子,其母皆帝喾之妃也,及尧亦喾之子。”据王充所论,可推定以下事实:(一)由王充“说者又曰”的表述来看,禹、契胁生神话出于汉代;(二)《奇怪》篇首否定的“禹、卨逆生,闿母背而出”的说法,与《春秋繁露》禹生于母背、契生于母胸不同,与《蜀王本纪》《吴越春秋》亦不同,同样可以证明禹、契的胁生神话在汉代未曾定型;(三)“禹、卨逆生,闿母背而出”的说法,目的是为了解释三代夏商之逆死和周之顺亡,但这一说法没有先秦文献的依据;(四)王充当日所看到的《帝系》似乎没有陆终六子胁生的明确记述。
饶宗颐曾对世界各地的古代胁生神话作过比较研究,他认为“《生民》诗说‘稷之生,不坼不副’,亦是事实。由是言之,似周人写此诗时,禹、契坼疈而生的事,早已为人所传诵,非汉代始有之”。*饶宗颐:《中国古代“胁生”的传说》,《燕京学报》新三期,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2-23页。裘锡圭说:“姜原生后稷十分顺利,‘不坼不副,无菑无害’,应该就是以‘修己背坼而生禹,简狄胸剖而生契’这类神话为背景的。”*裘锡圭:《新出土先秦文献与古史传说》,《中国出土古文献十讲》,第29页。饶、裘二氏都认为《生民》叙后稷“诞弥厥月,先生如达。不坼不副,无菑无害”,是以夏禹和商契的胁生神话为潜在对比来叙述的,预示着周始祖在出生上超越夏商始祖,即周的统治会超越夏商的统治。这与前述王充所论汉代儒生制造禹、契胁生神话的思路完全相同,都不以胁生为吉兆。然《史记·楚世家》“陆终生子六人,坼剖而产”集解引干宝曰:“先儒学士多疑此事。……若夫前志所传,修己背坼而生禹,简狄胸剖而生契,历代久远,莫足相证。……《诗》云:不坼不副,无灾无害。原诗人之旨,明古之妇人尝有坼副而产者矣,又有因产而遇灾害者,故美其无害也。”干宝认为,《生民》之所以赞美后稷“不坼不副,无灾无害”,是因为“古之妇人尝有坼副而产者矣,又有因产而遇灾害者”。可见,与饶、裘二氏不同,干宝分明了解“修己背坼而生禹,简狄胸剖而生契”的传说,但他却没有将后稷“先生如达”与禹和契的胁生神话联系起来。干宝的这一意见值得重视,也就是说,后稷顺产的说法与禹、契胁生神话没有任何关系,《生民》“不坼不副,无菑无害”八字只是事实的陈述。当然,很明显,在《生民》的叙述语境中,坼副菑害的降生不被视作吉兆。《春秋左传·隐公元年》:“庄公寤生,惊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恶之。”可知春秋时生子观念亦然。
讨论胁生问题,有必要将其与圣人感生神话合并观之。《生民》所述后稷的感生神话,着眼点在于姜原履大人迹,以证成周之受命于天,至于后稷如何从母体降生,则并非《生民》所关注的问题。同样,成书于楚汉之际的《世本》以及《史记·楚世家》对陆终六子坼剖而生的记载,与圣人感生的思维无涉,只是中立地叙述一个事实,与降生者是否受命于天没有关联。但据《论衡·奇怪》,汉代儒生制造的禹、契的胁生神话,性质则大为不同。禹、契的胁生不再是中立的事实叙述,而变成了夏商周三代统治命运的象征,其目的在于论证夏商之天命不及周。可见,在汉代纬书的语境中,胁生由中立的事实叙述变成了一种凶兆叙述。《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述禹生于背、契生于胸是对三代质文代嬗而作出的解释,所谓“性命形乎先祖,大昭乎王君”,*曾振宇、傅永聚:《春秋繁露新注》,第149页。亦视胁生为凶兆。
根据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将西汉以前胁生神话分作两类:第一类是以《史记·楚世家》为代表的陆终六子胁生,属于中立的事实叙述,其产生年代大约在战国晚期;第二类是以《春秋繁露》为代表的禹、契的胁生,属于神学政治思维介入的凶兆叙述,其产生年代在汉,系儒生所制造的神话。

出人意料的是,1994年上海博物馆从香港购得一批竹简,其中《子羔》篇记述了禹和契的胁生神话。由于这批竹简来历不明,故其年代真伪遭到质疑。*刘蔚华:《重重迷雾上博简》《关于诠释与证据——再评重重迷雾上博简》,《山东社会科学》2006年第12期、2008年第8期。不过,大部分学者肯定这批竹简的真实性,认为其年代在战国中期或晚期。本文无意于介入上博简真伪年代的争论,但从思想史的发展来看,《子羔》的年代却不太可能早到战国中晚期。关于《子羔》的内容,裘锡圭说:“《子羔》篇的写作采用子羔与孔子一问一答的形式,借孔子之口叙述了禹、契、后稷‘三王’降生的神异传说,说明他们都是‘天子’;又叙述了从事稼穑的‘人子’舜有贤德,尧发现后让位给他的禅让传说,最后以‘舜其可谓受命之民矣。舜,人子也,而三天子事之’之语作结。此篇主旨在说明一个人是否有资格君天下,应决定于他是否有贤德,而不应决定于出身是否高贵;跟《唐虞之道》一样,也是竭力鼓吹尚贤和禅让的。”*本段所引裘锡圭言,分别见《新出土先秦文献与古史传说》,《中国出土古文献十讲》,第19、29页。其实儒家之塑造孔子,也曾利用其殷人后裔之高贵出身,*据《史记·孔子世家》和《论语·子罕》,孔子十七岁时,鲁国孟釐子称其为“圣人之后”,最早将孔子与圣人联系到了一起;之后,鲁国太宰称孔子为“圣者”,子贡则称其为“天纵之将圣”。证明儒家并不完全否定出身的高贵。更重要的是,《子羔》所记禹、契的胁生说颇值得怀疑,其文字如下:
女也,观于伊而得之,怀三年而画于背而生,生而能言,是禹也。契之母,有乃氏之女也,游于央台之上,有燕衔卵而措诸其前,取而吞之,怀三年而画于膺,生乃呼曰钦,是契也。后稷之母,有邰氏之女也,游于玄咎之内,冬见芺,攼而荐之,乃见人武,履以祈祷,曰:帝之武,尚使……是后稷之母也。三王者之作也如是。*引据李学勤:《楚简子羔研究》,《上博馆藏战国楚竹书研究续编》,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第13页。
裘锡圭说:“《子羔》篇的出土,证明见于上引汉以后书的说禹、契生自母背、母胸的降生神话,有颇为古老的来源。”本文认为这一判断未必恰当,相反我们应该认真分析《子羔》与传世文献所见胁生神话记述之间的本质差异。
上引《子羔》一段文字值得注意的有以下几点:(一)它说禹生于背、契生于胸,与《春秋繁露》相同,而与《蜀王本纪》和《论衡》等记述不同;(二)在《子羔》的语境中,禹、契的感生和胁生神话,与后稷的感生并列,被视作瑞征,这与上文分析的传世汉代文献所见胁生神话的中立叙述和凶兆叙述不同;(三)它将禹、契的胁生神话跟二人的感生神话合并,与佛经所见释迦感生神话将感生与作为瑞征的胁生结合起来性质相同;(四)它以禹和契都为“生而能言”者,而在《史记·五帝本纪》中,黄帝不过是“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唯一接近“生而能言”的是“高辛生而神灵,自言其名”,而且汉代纬书亦未见禹、契“生而能言”的记述;*《春秋元命苞》:“神农生,三辰而能言,五日而能行,七朝而齿具,三岁而知稼穑般戏之事。”(《纬书集成》,第589页。)此记神农“三辰而能言”,类似于黄帝的“弱而能言”,与“生而能言”尚有距离。(五)它可以视作将感生、瑞征式胁生和“生而能言”三者密切结合的文本,这与前述佛经将释迦感生、瑞征式胁生和“生而能言”三者密切结合完全相同。由以上五点,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子羔》所记禹与契的感生、瑞征式胁生和“生而能言”,与传世文献所见感生神话、胁生神话大不相同,它极可能是受到纬书与印度佛教思想影响而写定的文本,其产生年代可能在董仲舒之后,亦可能在王充之后。
四、结 论
1958年,季羡林在《印度文学在中国》一文中指出,印度文化之于中国的影响,可以早到战国时期。屈原《天问》中月亮有兔子的传说,《战国策·楚策一》中狐假虎威的故事,都是很好的例证。季羡林还指出,《三国志》所载曹冲称象故事、六朝志怪小说中的部分作品,都接受了汉译佛典故事的影响。然而,季羡林所举的例证却无法与佛教在汉代传入中土这一重大的学术问题取得联系。他的《中印文化交流史》在分析佛教传入中土的时间时,遵从了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所提出的佛教在两汉之际传入中土的结论,在对中印文化交流分期时,以汉朝以前为滥觞期、后汉三国为活跃期、西晋至唐为鼎盛期。*以上参见《季羡林文集》(第四卷),第171-188页。可以看出,他很谨慎,没有明确将西汉列入中印文化交流的某一时期。既然汉朝以前为滥觞期,后汉三国为活跃期,何以在两期之间的西汉为中印文化交流的一个空白点呢?可见这一分期在学理上是留有很大疑惑的。从上述孔子感生、孔子四十九种异表和作为瑞兆的禹、契胁生等问题来看,汉代纬书在战国阴阳五行思想之外,部分接受了外来佛教思想的影响。那么,我们有理由相信,早在西汉中后期,*关于纬书年代所起,历来众说纷纭,学界主要接受的是张衡的意见,以为起于西汉哀帝、平帝时期。然《汉书·李寻传》载成帝时李寻有“五经六纬”之说,证明成帝时纬书已经大体完备(参见李学勤:《汉书李寻传与纬学的兴起》,《杭州师范学院学报》1996年第2期)。《四库全书总目》卷六经部易类易纬后案辨谶、纬之别曰:“儒者多称谶纬,其实谶自谶,纬自纬,非一类也。谶者,诡为隐语,预决吉凶。《史记·秦本纪》称卢生奏录图书之语,是其始也。纬者,经之支流,衍及旁义。《史记·自序》引《易》:失之毫厘,差以千里。《汉书·盖宽饶传》引《易》: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注者均以为《易》纬之文是也。盖秦汉以来,去圣日远,儒者推阐论说,各自成书,与经原不相比附。如伏生《尚书大传》,董仲舒《春秋阴阳》,核其文体,即是纬书。特以显有主名,故不能托诸孔子。其他私相撰述,渐杂以术数之言,既不知作者为谁,因附会以神其说。迨弥传弥失,又益以妖妄之词,遂与谶合而为一。”又,卷三三经部五经总义类《古微书》提要云:“考刘向《七略》,不著纬书。然民间私相传习,则自秦以来有之,非惟卢生所上,见《史记·秦本纪》。即吕不韦《十二月纪》称某令失则某灾生,伏生《洪范五行传》称某事失则某征见,皆谶纬之说也。《汉书·儒林传》称,孟喜得易家候阴阳灾变书,尤其明证。荀爽谓起自哀平,据其盛行之日言之耳。”(分见《四库全书总目》,第47、280页。)徐养原、汪继培、周治平、金鹗、李富孙皆写有《纬候不起于哀平辨》(见阮元订《诂经精舍文集》卷一二,《丛书集成初编》本,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46-353页),俞正燮亦主此说(见《癸巳类稿》卷一四,北京:商务印书馆,1957年,第540-542页)。刘师培《谶纬论》曰:“及武皇践位,表章六经,方士之流,欲售其术,乃援饰遗经之语,别立谶纬之名。”(《刘申叔遗书》,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371页)黄侃《汉唐玄学论》亦曰:“仲舒即阴阳之流裔,亦谶纬之先驱。”(《黄侃论学杂著》,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第482页)综合各家所论,谶纬年代问题应作如下理解:就起源看,其年代在战国邹衍之时;就最初兴起看,其年代在秦汉之间;就发展兴盛看,其年代在西汉中期武帝之世;就结集看,其年代在哀、平间王莽当政之时(参看陈槃:《秦汉间之所谓“符应”略论》,《古谶纬研讨及其书录解题》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84页)。佛教思想已经开始对中国思想产生局部的影响,其最早途径不是通常所理解的融入道教,而是介入儒教。换言之,最早接纳佛教思想的可能是儒教,而非黄老道家。
对此结论,我们还可以补充一个例证。王充在《论衡·恢国》中举了光武帝降生奇异的例子:“光武且生,凤凰集于城,嘉禾滋于屋,皇妣之身,夜半无烛,空中光明。”并且评论说:“五帝三王,初生始起,不闻此怪。”*王充:《论衡》,第301页。具有非凡成就者降生时“空中光明”一类记述在魏晋以后习见,*如司马睿出生时“有神光之异,一室尽明”、桓玄出生时“有光照室”、刘裕出生时“神光照室尽明”、陈顼出生时“有赤光满堂室”,分别见《晋书·元帝纪》《晋书·桓玄传》《南史·宋本纪》《陈书·宣帝纪》。其渊源不在中土,而在前述佛经所见释迦降生时的“应时天地大动,三千大千刹土,莫不大明”。又,《论衡·吉验》曰:“光武帝建平元年十二月甲子生于济阳宫后殿第二内中,皇考为济阳令,时夜无火,室内自明。皇考怪之,即召功曹吏充兰,使出问卜工。兰与马下卒苏永俱之卜王长孙所。长孙卜,谓永、兰曰:此吉事也,毋多言。”*王充:《论衡》,第32页。《东观汉记》卷一《光武纪》曰:“建平元年十二月甲子夜上生时,有赤光,室中尽明。皇考异之,使卜者王长卜之。长曰:此善事,不可言。”*吴树平:《东观汉记校注》,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页。《后汉书·光武帝纪下》论曰:“皇考南顿君阁为济阳令,以建平元年十二月甲子夜生光武于县舍,有赤光照室中。钦异焉,使卜者王长占之。长辟左右曰:此兆吉不可言。”据以上文献所载,光武帝出生时室中现光明一事极可能是建平元年其父刘钦所制造的神话,非光武帝即皇帝位之后所造。由光武帝降生神话可知,建平元年(前6)前后,中土士人对释迦降生时有大光明的神话已经有充分的了解。
若将光武出生室内光明祥瑞与上文所论感生、胁生神话联系起来,进而与哀帝元寿元年(前2)使“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联系起来,*《三国志·东夷传》裴注引鱼豢《魏略》。我们可以相信,佛教在西汉最初影响于儒生,进而及于官员,再及于皇帝,这符合佛教“不得国主,则佛法不立”这一传统的传教策略。我们也可以相信,佛教在西汉实现影响的途径并非通过教义,而是通过宣扬佛教教主释迦牟尼的神异事迹来实现的;在这一点上,佛教适应了汉武帝确立的“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的文化建设理念,它与西汉神学经学的性格潜在相通,二者之间发生密切交流可以说是历史的必然。就中土文化立场来说,纬书及相关文献对佛教思想资源的借用,其目的是服务于汉代的神学政治。汉代纬书中的政治神话是使用文学手段制造出来的,故《文心雕龙·正纬》称纬书“事丰奇伟,辞富膏腴,无益经典而有助文章”。*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31页。由此来看,纬书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文学想象的发展,而佛教于此当有不小的贡献。
(责任编辑:庞礴)
Heaven-Induced Life, Miraculous Appearance and Being Born from the Rib:Influence of Buddhism in Western Han as Reflected in Weishu and Related Documents
Sun Shangyong
Heaven-induced life, birth prophecy, and goddess bathing in heaven-induced lives myths of Confucius in Weishu of Han Dynasty and related documents, which do not appear in the Pre-Qin period, must have been influenced by the heaven-induced life myths of Budda. The forty-nine kinds of miraculous appearance of Confucius from Weishu in Han Dynasty are borrowed from Buddha image in Buddhist documents. Being born from the rib Myths of Yu and Xie in Zi Gao bamboo text preserved in Shanghai Museum, is a text integrating heaven-induced lives, auspicious type of being born from the rib, and being able to speak at birth, which is almost identical to the heaven-induced life myths of Budda, and completely different from the factual or ominous narration in the text in Western Han Dynasty and the Pre-Qin period. Therefore, Zi Gao is very likely to have been influenced by both Weishu and Indian Buddhism. These facts prove that, as early as the late Western Han Dynasty, Buddhist thought has begun to have a local influence on China. To serve the political theology of the Han Dynasty, Weishu and related documents borrow these thoughts from Buddhism.
Heaven-Induced Life Myths, sage image, Weishu in Han Dynasty, the influence of Buddhism
孙尚勇,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特聘研究员(成都610064)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国佛教文学通史”(12JZD008)
B932
A
1006-0766(2016)05-0109-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