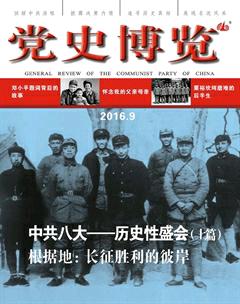没有编制和工资的省妇联副主任
铁竹伟
2015年7月,杭州的二姐给小弟打一电话:今年是妈妈去世20周年,咱们姐弟集体扫个墓吧。小弟在微信亲亲群里一发,杭州的兄弟姐妹一水地同意。原本考虑天气炎热,住在南京的我身体不好,就不要参加了,我没同意,当即买了返杭的高铁票。窗外景物飞闪,往事历历在目。
一
妈妈苏佩兰是山东郯城人。抗战爆发后,13岁的她就当了地下交通员,后来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县委妇联主任李汝佩大姐领导下,负责发动妇女做军鞋、筹军粮支援八路军。19岁那年,经李大姐介绍,认识了独立营政委铁瑛。1944年春节后,她请了五天假,走了几十里路来到部队结婚。新婚当夜,集合号骤响,丈夫二话没说,跳起出门,率部打鬼子,一去三天,打个大胜仗。作为新媳妇的她,帮留守战士拆洗被子,缝补衣服,烧饭蒸馍,整整忙了三天。等丈夫打仗回来,夫妇又共度一夜,她便背上挎包回县工作。年底,第一个女儿呱呱坠地。因为抗战残酷,姐姐是姥娘抱回老家养活的。
解放战争开始后,妈妈调到爸爸所在的华东军区警卫旅。妈妈又生了个白胖小子,满月时乡亲们都去看望,你抱我摸,万没想到村里正流行白喉,哥哥被传染,夭折了。
1948年部队一路南下。当爸爸率部攻打潍县时,属鼠的我在诸城出生。高烧的妈妈没有一滴奶,我靠爸爸派人送来的两斤羊奶撑了两天。第三天望着嗷嗷待哺的我,24岁的妈妈只能默默垂泪。
听到信儿,姥娘从老家赶来,抱过孩子,拿了块窝头在嘴里嚼了又嚼,成糊状,对着嘴喂过去,孩子立即收住哭声,吧嗒着嘴,又吞又吸。姥娘笑了:看,这妮子三天就能吃窝头,命硬,死不了!从此,南下大军马背驮着的竹筐里,甜甜睡着的小丫头枕边,不断出现半个白馒头,半个黄窝头,半块葱油饼,半块米粑粑——都是不知名的部队叔叔阿姨从自己口里省下来的!
也不知是因为干粮底子打得实在,还是叔叔阿姨的百家饭养人,出生时又黑又瘦的我,从此至今,身材“幅员辽阔”,喜爱走南闯北,性格开朗豪爽,为人宽厚善良。
二
2015年7月31日上午8点半,我们姐弟及配偶、儿女和我们的第三代,近20人聚集南山公墓爸妈的墓前,献花篮、摆果品,一人点炷香,集体三鞠躬,微笑合影。
南山下八卦田,荷花满塘,草堂里饭菜飘香。龙井茶水清清,回忆妈妈的话语不断。真没想到,20年过去了,儿女们都在感慨爸爸是“公家爸爸”,职位越高,在家越是“甩手掌柜”,是平凡的妈妈用自己奉献的一生,教会我们怎样做人。
新中国成立后,妈妈在南京从部队转业,原本分在华东军区政治部幼儿园当院长,后因僧多粥少,她把工作让给了别的同志,自己做起了没有报酬的部队家属工作。
1960年,爸爸调到舟山守岛部队当政委,妈妈当上了家属委员会主任。从此,我们七个孩子的寒暑假,都跟着妈妈率领的家属“娘子军”,帮连队战士洗被子,补衣服,参加助民劳动,挖河泥,收稻子。那时粮油肉都要票,我们家饭桌上,总是没油没盐的菜还不够吃,因为有限的肉和蛋,常被妈妈送给烈属和病人家。爷爷曾摇着头对我们说:你爸爸像个耙子往家里耙,你妈妈像个叉子往外叉。
1972年,爸爸被中央调到浙江当省委书记。为陪同接待外宾,妈妈有了省妇联副主任的职务,没有编制和工资。她自己挤公共汽车去上班、开会,参加植树劳动冲在前。逢年过节,家里有什么好吃的,别管月饼、粽子还是橘子、西瓜,妈妈都招呼院里警卫班战士、保健医生护士、扫地师傅一起来吃。工作人员都喜欢她。其实,从“文革”结束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落实政策,她每月才领到100多元的生活费。家里经常寅吃卯粮,家中的第一台彩电,还是我们孩子们凑钱买的。
1994年初春,我们为爸妈办了金婚纪念宴,一向冷静沉稳的爸爸眼圈湿润,声音有些颤:孩子们,50年来,这个家没有你们妈妈的支撑,我不可能全身心地工作。借用一句歌词说出我的真心情:我的一把军功章里,个个都有你们妈妈的一半!
妈妈病重住进浙江医院后,每天下午3点,78岁的老爸像上班一样准点走进病房。他坐在病房,陪妈妈聊聊天,与来看望的朋友说说话,真心实意弥补自己一辈子忙于工作,在感情上对妻子的愧疚。
三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2015年7月31日13点多了,孩子已经分批回家了。我们结好账,正准备离开,突然大雨如注,仿佛在离去的小路拦上一道密密匝匝的水帘,我心一惊,下意识地看表:13点半——20年前妈妈离世的时刻!
莫不是妈妈看见儿女后代聚集膝下,幸福落泪?莫不是妈妈想留大家在她身边多坐一会儿?因为我们都相信好人有好报,草木皆有爱,天地有真情。
我们姐弟几个人不约而同又坐在了草堂外廊,边聊边等。是的,妈妈是平凡的,妈妈一生做的事也是平凡的,但平凡的事她坚持做了一辈子,所以在我们儿女心中,妈妈永远是最伟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