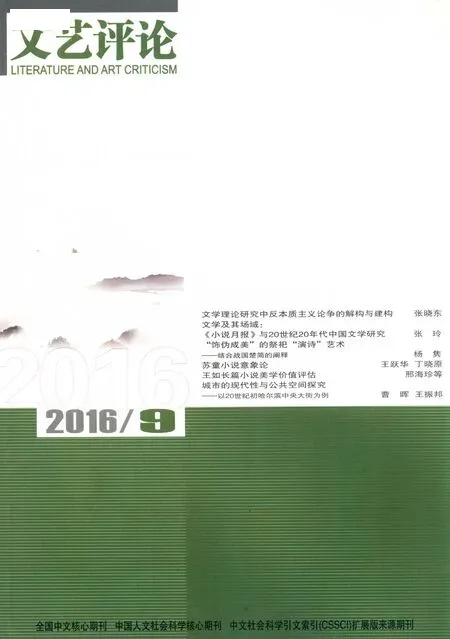苏童小说意象论
○王悦华 丁晓原
苏童小说意象论
○王悦华 丁晓原
一
兴起于上世纪80年代的先锋主义文学浪潮,曾经颠覆了中国传统的文学规范,树立了新的美学理念,具有不可置疑的文学史构成意义。苏童,作为其中重要的参与者和实践者,他的小说创作除了具有先锋作家的典型特点之外,还选择性地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古典叙事传统。他善于在小说中构建一系列的意象群,利用意象背后的巨大张力,在提升小说审美意蕴的同时,极大地拓展文本的思想和文化深度。
“意象一词,在中国语言发展史上,萌芽于先秦,成词汉代,六朝用于文学,唐宋沿用,到明清而大行。”①“意象”成词于汉代王充《论衡·乱龙篇》:“夫画布为熊麋之象,名布为侯,礼贵意象,示义取名也。”有礼仪之表象,文化之意义,即在成词之初“意象”就具有表象和意义的双构性,而后在刘勰的《文心雕龙》中首用于文学批评。发展至今,意象“通常是指创作主体通过艺术思维所创作的包容主体思绪意蕴的艺术形象”②。而杨义提出:“中国叙事文学是一种高文化浓度的文学,这种文化浓度不仅仅存在于它的结构、时间意识和视角形态之中,而且更具体而真切地容纳在它的意象之中。研究中国叙事文学必须把意象、以及意象叙事方式作为基本命题之一,进行正面而深入的剖析,才能贴切地发现中国文学有别于其他民族文学的神采之所在,重要特征之所在。”③进而意象叙事分析成为中国叙事文学独特而重要的研究方法。
苏童热衷于小说中意象世界的营造,这些看似庞杂纷乱的意象实则熔铸了他在现实与虚构、历史与当下的穿梭之间对人生切身而真挚的感悟,而他对意象的偏爱和选择与他独特的生活经历、个性气质以及写作立场是分不开的。苏州的童年记忆、首都京城的读书时光以及古都南京的工作和生活经历都让他在不经意间同时濡染了北方的凝重和南方的细腻,另外苏童性格中独有的温婉情感和浪漫抒情气质,以及民间化的写作立场使他区别于其他先锋派作家,不同于马原的艰涩和迷离、余华的冷漠与简练,苏童更善于选用诗意的、富有古典意蕴或者哲学内涵的意象来构造和丰富小说的精神内涵。
二
苏童早期的作品中有很明显的对现代派甚至后现代派文学创作技巧的借鉴,所以除了实体化的意象之外,半虚化甚至完全虚化的意象也不在少数,而近几年来,他试图用小说直面现实,所以小说中实体意象有增多的趋势。苏童借意象的虚实转换之间产生的巨大的表达力来传递自己对生命价值的思考和理想境界的探寻。
(一)实体意象
1.故乡
“枫杨树故乡”和“香椿树街”是苏童小说中最常见的地点意象,尽管有着城乡之别,但是不管是对于在那里生活着的小说中的角色还是作者而言,这两个地方的意义都在“故乡”的层面上得到了某种程度的统一。
苏童对待“枫杨树故乡”和“香椿树街”的态度是矛盾的。在《飞跃我的枫杨树故乡》《一九三四年的逃亡》《罂粟之家》等等小说中,苏童向读者展现了“枫杨树故乡”的落后腐朽和肮脏罪恶,在小说《米》中,五龙因为极度贫穷和饥饿离开了“枫杨树故乡”,而在城市里攫取了大量的财富之后精神日渐变态和消亡,临终依然希望带着最好的米回到“枫杨树故乡”,他的灵魂在离开故乡之后一直颠沛流离;而“香椿树街”在苏童的笔下一样并不美丽,小说《城北地带》中工业污染甚至威胁居民的生命,“城北的天空聚合了所有的工业油烟,炭黑和水泥的微粒在七月的热风里点点滴滴地坠落”④,可是《米》中五龙至死依然心心念念自己的家乡;《白雪猪头》中张云兰冒雪送来的猪头让往昔充斥着邻里纠纷的香椿树街又一次充满温情;《西瓜船》中一条人命的罪恶也在人情温暖中得到软化,罪恶和温情只有在故乡才能完美融合,在“枫杨树故乡”和“香椿树街”,“逃离”和“回归”是作者和这里生活着的人们同时拥有的愿望。
2.少年
苏童对塞林格有着近乎狂热的执迷,《伤心舞蹈》《午后执迷》等小说都有受到塞林格的影响,所以在他的笔下诞生了一群生活在“香椿树街”“枫杨树乡”张扬跋扈却又脆弱懵懂的少年群像。
这些少年在故事里成长,而成长的代价往往因为动荡的时代、变幻的人情而尤其惨烈,他们厮杀、偷窃、强奸……通过实践暴行、反抗规则来体味存在,在挣脱学校和老师的管教之后又落入更大的宿命的囚网。《城北地带》中红旗因为随身体一起滋长的性欲而犯罪,代价是被锁牢狱9年,达生因为“城北第一好汉”的名号与人斗殴而丧命;《黄雀记》中保润因为参与了柳生的绑架计划而被冤强奸仙女入狱10年,他们用充满朝气的生命在成长的过程中挑战社会规则和法律,并为此付出极其沉重的代价。
追溯这些顽劣少年性格的形成原因,可能就是人性之初性善还是性恶的争辩了,不同于传统小说中对“善”的强调和颂扬,苏童在其作品中对于生命和成长的诠释,往往将重点更大程度地放在“恶”上。这样的“恶”毫无根据,似乎与生俱来,在小说《米》中,织云在还是少女的年纪就可以用肉体去换取一件裘衣;《舒家兄弟》中舒工对待弟弟舒农常常拳脚相加;《城北地带》中小拐小小年纪就残忍杀害冼铁匠的狗。这种根植在生命之初表现为性欲、贪婪、暴力等等的罪恶在苏童几近张扬的描写之下,强力表现了人性的复杂和多变。
3.女性
苏童笔下的女性形象也尤其让人印象深刻,在《红粉》《妻妾成群》《妇女生活》等作品中,苏童塑造了一系列个性鲜明的女性形象,在小说情节的展开和主旨的揭示过程中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作为先锋作家,苏童对社会底层女性的刻画突破了以往的形象禁忌,个性发展更为自由,对“性”和“恶”的表现更为坦诚。《妻妾成群》中的颂莲虽然受过教育但依然在父亲去世之后选择做陈佐千第四房姨太太而不是进工厂做工来继续自己的生活,她来自社会最底层却对自己的女佣也恶言恶语;《妇女生活》中的娴虽然身为母亲,却从小并没有善待女儿,在女儿成人结婚后,她甚至通过窥探女儿夫妻的性生活来满足自己变态的心理;《红粉》中秋仪和小萼因为社会对妓女的偏见和自身好逸恶劳的旧社会恶习而在新中国成立后难以真正融入社会,不得不承认的是,她们的悲剧的产生原因除了她们人性深处的卑劣和周遭的愚昧,显然还掺杂着更深层次的社会的或者是时代的因素。
女性形象作为苏童解读世界的一个入口,是具有极其重要的意象价值的。在小说的撰写中,苏童通过打破传统女性形象,深入了解女性文化历史内涵,通过对女性内心世界深刻的剖析和解读来达成对人性和历史的批判。
(二)半虚化意象
1.河流
河流是苏童作品中重要的意象,苏童自己也表示对河流有着不同寻常的亲切感,不少学者对此作过专门的研究。小说中河流的意象可能不会反复出现,但每次出现都负有情节转折的重要作用或者包含丰富的哲学意味。
《我的帝王生涯》中池州之战,战亡人的尸体被抛进河里,恐惧的逃兵们踏着水上的死尸奔向家乡,全文也隐约闪现着绵绵不断如同河水般向死而生的悲剧感;《刺青时代》中小拐的母亲在冰河之上迎接了孩子的来临,生死如同河流尽管有生命之源的圣名,却常现身边;《河岸》中,大段对河流的描写,暗示了主人公东亮内心世界表面的平静和深层的躁动,这个故事都弥漫着河与岸对立和依存的悖论;《黄雀记》中,祖父寻找了十几年的魂,即装了祖父先人尸骨的手电筒,最终沉睡在了河流里,而白小姐在穷途末路之时也是在河里受到洗礼……在这里,河流的意义远不止是具象的,在情节的勾连里,河流的韵味总是半遮半掩,被虚化的部分才是最深厚的。
在小说中,虽然文本中具象的河流只出现几次,可是隐约地它却时时出现在全文中,成为半虚化的重要意象。它可容纳许多故事和沧桑,不仅潜藏了巨大的生命力,而且流动着的它在时间的维度上也具有丰富的表现空间,苏童更倾向于在作品中对历史和人性进行拷问,在这个意义上,河流总是最合适的半虚化意象。
2.血液
血液也是苏童经常选用的意象之一,而往往在小说中出现之后,接下来的故事都会浸染在淡淡的血色中,给读者带来苏童小说独特的阅读体验。
《西瓜船》的那场凶杀案,福三的血始终留在城北人的眼里,哪怕后来福三母亲来寻船,他们从那双失明的眼睛里感受到的也是沾染了血色的愧意;《城北地带》中红旗从美琪裙子上的血迹看到了自己的罪,从那以后,故事的发展就始终被年少懵懂却无力改变的血色悲哀所牵绊;《碧奴》里蒙面客扔掉了寻子的青蛙,给碧奴留下的只是之前捆裹手的粘了血迹的腰带,那是世界对她的拒绝,那种残忍和无助充斥碧奴的寻夫路……
苏童的小说世界往往充满着神秘,血液在故事的发展中一经出现就很难消逝,而有了淡淡血色作为背景,苏童对于历史和人性的追问就被烙下悲悯的情怀主线,真实和虚幻、情感和命运相互交错,难辨主次,生命承载的追问又多了难以回答的内容。
(三)完全虚化意象
1.季节
在苏童小说中,数字化、具象化的历史时间往往被故意弱化,故事发生的季节反而具有了标志性的意义。
《肉联厂的春天》中用本该春暖花开的春意来反衬肉联厂的冷寂,文本季节——春天让金桥在肉联厂生存的格格不入以及最后在冷库的惨死充满了冷冬的悲剧感;《我的棉花,我的家园》中本该是期待丰收的夏天,书来却亲眼目睹在水患和旱灾的侵袭后家园的一切都消失殆尽,绝望在夏天的渲染里如同热浪一样肆虐;《樱桃》写的是秋天,死在夏天的白樱桃让整个发生在秋风里的故事充满了神秘和凄美……小说《黄雀记》中更是分为“保润的春天”“柳生的秋天”和“白小姐的夏天”三个部分来表达,小说中的季节更大意义上指代的是人生经历的状态,暗示着人事变幻与自然和天道冥冥中有着难以拆解的联系。
虽然没有被具象化地反复提及,但整个小说都沉浸在季节变化人事变迁的氛围之中,季节成了苏童最处心积虑的暗示,对小说主题的揭示起到了强大的推动作用,细心品味之后,季节无疑是苏童小说中的重要的完全被虚化的意象之一。
2.“黄雀”
直到2013年出版的长篇小说《黄雀记》,苏童才明确提出这样一个全篇并没有出现,但是却时时笼罩在全文中的意象——“黄雀”。苏童选择“黄雀记”作为小说名字,取的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意蕴,黄雀是漂亮有灵气的动物,但是在这里却是笼罩在小说人物和故事背后的灾难或者是命运。
“黄雀”的意象并不是《黄雀记》独有的,苏童的小说经常会有这样的宿命感,即便全篇都没有明确出现,可以说被完全虚化,但小说中所有人物命运、情节发展都无法逃脱背后的“黄雀”的操控。就像《黄雀记》中,“罪与罚”的主题是每一个人都逃不过的命运,保润没有犯罪却进了监狱,为此家破人亡,柳生以为侥幸逃过牢狱之灾最终却在新婚之夜被杀,而白小姐颠沛流离最后还是回到香椿树街,《妇女生活》中从娴到芝再到萧,每一个女人都试图脱离自己所处的畸形的家庭关系和母女关系,但是都以失败告终,似乎她们越挣扎,宿命对她们越残忍;《另一种妇女生活》中,妹妹简少芬的出嫁决定让简氏姐妹离群索居的生活出现了幸福的可能,但是姐姐简少贞最后的自杀还是让简少芬的后半生无法真正幸福,抑郁的感情基调始终存在;《我的帝王生涯》中端白虽然在万人之上,但依然要作为傀儡在梦魇和命运中挣扎;《妻妾成群》中颂莲凭借着自己的年轻和学识也在陈家挣扎过,但依然无力于挣脱困兽一般的悲剧命运。
唐北华这样解读黄雀意象:“小说中作者的意图在于阐释因时代而产生的命运与灾难,一种因黄雀造成的命运与灾难。黄雀,一种表现当下自我身份迷失下的一种生存状态,便是作者着力于刻画的意象。”⑤“黄雀”是完全被虚化的意象,却反复出现在苏童小说中,因为时代、性格或是人性,在跌宕的命运安排中像一只“无形的手”来操控人物的命运。
三
杨义认为:“意象的意义与语言的所指和能指的双重性有所联系,但更为复杂,因为它首先是语言和物象的结合,其次是物象对意义的包含,这种包含又不是直说,需要意象本身的展示和暗示,也需要读者的体验和解读。因此意象的意义指涉,具有比单纯的语言的意义指涉更多的浑融性和多层性。”⑥可见,文学意象从抒情文学渗透到叙事文学的过程中,不仅承载了作者的主观情感和思想,在小说情节的发展和人物形象的立体化的同时,还成为了小说人物情感和思想以及小说主旨揭示等多方面的载体。这种“浑融性和多层性”需要读者进一步产生多样化和个人化的解读,进而多方位拓展小说的精神内涵。
苏童的小说文本善于利用象征的方式生成意象化的叙事风格,继而塑造出独特的人物形象,挖掘出文本背后隐藏的精神空间,笔者认为,苏童小说中叙事意象的意义指涉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类:
(一)对母亲原型的追溯
河流这一意象在苏童很多小说中出现过,2009年推出的长篇小说《河岸》更是围绕河流与库文轩父子之间关系展开。河流能够给少年的苏童以安全感,来自远古的河水孕育了人类和悠久深厚的人类文明,在苏童的小说里河流早就超越了其自然属性,具有了特定人格意义——故乡和母亲。
依据荣格的分析,母亲的原型形象可以分为两种,“所有这些象征都会有一个积极、满意的意义,或者一个消极、邪恶的意义”⑦。苏童笔下大多数的河流是肮脏的,“水面上漂浮着一层工业油污,它们在阳光下画出一圈圈色彩斑斓的花纹”⑧,但在河流肮脏、诡谲、邪恶的表面之下,是母亲一样的包容情怀。《黄雀记》中,当仙女走投无路,“她感到岸上的香椿树街在拒绝她,整个世界在拒绝她,只有水在挽留她,河水要把她留下”⑨,这时河水比世界容易亲近得多,她像善良的母亲一样包容所有人。苏童立体化地将母亲的消极与积极的双面性同时建构在河流意向里,使得河流意象具有立体感,获得深厚的人文意蕴和广阔的精神空间。
(二)偶然和宿命相结合的历史观
苏童的新历史主义小说致力于对历史细节和底层人物的刻画,传达了历史往往由偶然性事件决定的具有反传统性的历史观,尽管为他带来解构传统历史的叙事快感,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作为作家逐渐意识到这样的历史观缺乏对历史的反思。
《另一种妇女生活》中简少芬偶然与楼下店员的闲聊最后竟然引起了姐姐的死亡;《人民的鱼》中干部居林生收到的鱼和柳月芳的不喜欢吃鱼头的巧合让很多年后张慧芳的东风鱼头馆红火万分;《碧奴》中岂梁偶然去打桑叶的失踪促使碧奴一路哭泣寻夫等等这些情节和意象无不在昭示着苏童变化了的历史观念:由偶然事件导致的人生无常和历史的不确定性又往往具有宿命性。
他在香椿树街设置人类社会固有的生存困境,街上的人们需要倾尽全力去冲撞命运的桎梏,可最后却依然在宿命面前溃败。作者在文本中通过对个体命运的观照和反思,发现宏大的历史叙事和个体精神选择的互动关系。他借助香椿树街上少年少女的故事试图给我们以启示:历史的推进中,偶然可以改变方向,但似乎对扭转整体命运方向缺乏力度,重要的从来不是结果,而是哪怕明知是失败的宿命或者是失败的目标,依然拼尽全力与命运抗争,在其中定位并体验生命的意义。
苏童站在民间化的历史叙事立场,相比于宏观的历史,他更看重的是细节化、个人化的历史,虽然个人对抗历史的洪流时总是显得无力和苍白,但人类只有在愿意并且坦白地回顾和面对自己的历史的时刻才是真正勇敢地正视人生。笔者认为,在苏童的“新历史主义”的解读中,与其关注所谓解读历史的新方式,我们应该更深入地看到这是个人历史观的深化,即公正地面对过去和他人的历史的同时也要坦白和真挚地面对自己的过去、当下和将来的历史,苏童从不奢望重构历史,而是期待深刻地聚焦自我内心,实现对历史的另一种反省和解读。
(三)超越生死的生命观
苏童小说试图解构传统的生死观,死亡并没有仪式一般的庄重和神圣。死亡是无常的,《灰呢绒鸭舌帽》中父亲老柯是为了抓住被风吹走的帽子而死;《一个礼拜天的早晨》李先生因为追肉贩子少给的两毛钱而发生车祸而死;《园艺》中,孔先生因为与太太吵架被锁在门外而遭到抢劫而遇害,而同时死亡又是宿命性质的;《南方的堕落》中,红菱顺着河流终于脱离了父亲可怖的控制而最后却还是投水自尽;《我的棉花,我的家园》中书来从洪涝灾害的家乡逃离,却在渴望回家的时候被往家乡方向开去的火车撞死;《仪式的完成》中民俗学家试图完成一场逼真的拈人鬼的仪式,自己却被抽中,而终于逃脱之后又死于意外。生死并没有规定的章程、协定的期限,而正是这种无法掌控的感觉让人在面对生命时在内心有最深层次的荒凉和无力。
面对生命的艰难和延续,苏童依然保留了最原始的虔诚。苏童在小说中背景季节意象的选用和主旨对季节基调的内化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一点,《肉联厂的春天》《樱桃》等作品中春夏秋这三个季节虽然有酷热和萧瑟,但是却依然都是生命力旺盛的时段,虽然灾难随着命运齿轮的滚动缓缓而来,但每一个在阴影笼罩下的生命活得都是认真的,这充分体现了作者对于生命的尊重和敬畏。
在新世纪以来苏童的短篇小说中,不管是《白雪猪头》《西瓜船》或是《人民的鱼》,“温情叙事”不断引起讨论,作品主题逐渐显露出苏童相比于其他先锋作家独有的对俗世民众的人道主义关怀。苏童笔下,生死的神圣性被解构的同时,对生命和人情的体悟深度不断深化,显露出其独特的超越生死的生命观。季节交替和人世变幻具有着最为天然的对应关系,人世盛衰变得像四季变幻一样自然,生命的诞生、衰老和死亡被剥去神圣的外衣,不再被区别对待,他们连续而成为生命的整体,生命就像河流一样缓缓流动在不同的状态,甚至不再有刻意区别的过去、当下和未来,所有的一切都融化在河水里,汩汩前行的同时浑然一体。
四
叙事功能的概念最初来源于普洛普的《故事形态学》,他在对俄国民间故事进行整理后,分析出31项叙事功能。显然,叙事功能是可以抽离于具体的文本内容层面的功能项,而叙事功能的相互搭建构成了文本的叙事结构。而考虑到意象作为叙事成分却不具备角色和行动要素的特殊性,在考察叙事作品中意象的叙事功能时自然不能局限于情节或者说角色和行动的关系,还要考虑整体文本的表达效果。
杨义在《中国叙事学》对意象叙事的研究中说道:“意象作为中华民族极有光彩和特色的叙事方式和谋略,从历史的深处走出来,接受了时代的考验和询问,在融合外来的现代思潮和叙事经验中,丰富了自己的形态,深化和更新了原意象的含义,创造了新的意象组织形式和意义形态,从而焕发出更加璀璨的神采了。”⑩可见,意象的叙事功能是传统叙事与现代技巧结合的产物,必然具有多重性。意象的设定不同程度上蕴含着主旨,在情节与情节之间设置意象,可以减少情节转换带来的生硬,而将意象安插在情节与非情节之间,不仅能够在结构上调控叙事节奏,疏通并优化叙事结构,从而有效地提升作品的可读性,还能极大地拓宽作品的精神内涵,产生诗化效果,进而提升审美浓度,形成叙事张力。
(一)疏通叙事结构
先锋派文学在创作中大量借鉴了西方现代派和后现代的叙事手法,经常采用象征、叙事空白、非线性叙述等叙事手法,或通过荒诞的视角,塑造模糊的人物形象,这些技巧和特征在某种程度上会影响读者的理解,阻碍读者和作者进行交流。作为国内先锋派文学的代表作家,苏童的创作习惯也深受影响。
在细节的疏通作用方面,以苏童最近的长篇小说《黄雀记》为例,于京一在其论文《慌乱的野心——评苏童的长篇新作〈黄雀记〉》中从“主体的沉沦”“叙述的破裂”和“意蕴的纷扰”三个方面对苏童在《黄雀记》中试图对自身叙述风格作出的突围提出了全面的批判,其中提到了苏童小说在连贯性方面存在的问题。如果忽略小说意象,于京一的观点不无道理,即小说中类似于电影蒙太奇的片段式叙事缺乏必要的衍生动力,小说内部的情节发展错乱杂生,缺乏统一的主旨,但意象作为中国传统叙事流传至今的重要策略和手段,是不容忽视的。在“保润的春天”和“柳生的秋天”“白小姐的夏天”的时间承接过程中具有10年的叙事空白,开篇用一句“柳生夹着尾巴做人,已经很多年了”⑪模糊盖过了10年岁月。而实际上,如果认真关注意象,便能轻易解读三个人的10年进而贯穿全文。保润家门洞不断被租用祖父房间的店铺侵占,侧面说明10年来香椿树街和时代的变化;柳生因为对保润深怀愧疚被火车上丢下的尼龙绳圈吓得魂飞魄散;仙女10年后再次被保润用绳子捆绑,熟悉的羞耻、疼痛和噩梦竟然瞬间回归,由意象承载的成长和伤痛串联起三位主人公10年岁月的线索,也是理解全文主旨的重要突破口。
除了对行文细节结构的疏通,意象还能起到统罩全文进而疏通整体叙事结构的作用。小说《蛇为什么会飞》中,社会底层人的生活是纷乱、琐碎的,金发女孩的明星梦奢侈又悲凉;冷燕一步一步出卖自己的色相来换取金钱、地位;梁坚因为无力偿还债务而选择死亡。在西方文化里,蛇是邪恶的象征,但是当下的都市生活中,人心都隐含“蛇”样邪恶的欲望,不仅如此,生活本身就如同“蛇”一样难以琢磨。读者在领会作者关于篇名的主题暗示之后,“蛇”作为小说整体意象让故事的展开都笼罩在阴影之下,从而使读者的审美过程更加曲折,审美过程更加畅快淋漓,叙事文本下层脉络也更具有叙事张力。
(二)营造诗化氛围
苏童善于在小说中营造传统诗化氛围,这不仅仅体现在他善于运用传统小说的叙事模式,例如《碧奴》《新天仙配》对民间故事的重塑;《妻妾成群》《红粉》对世情故事的演绎等,还体现在他抒情优美的语言风格,“他的语言在现代白话和日常语言的基础之上,继承了古典诗词的超越性和丰厚的审美意蕴”⑫。此外,这种诗化氛围的营造和小说中意象的设置是分不开的,对此杨义有相似的观点:“意象的运用,是加强叙事作品的诗化程度的一种重要手段。它是中国人对叙事学与诗学联姻所做出的贡献,它在叙事作品中的存在,往往成为行文的诗意浓郁和圆润光泽的突出标志。”⑬
徐岱在《小说叙事学》中总结了三种叙事功能模式:情节模式、情态模式和情调模式。其中情调模式是指并不注重情节和人物的小说叙事,反而着力于刻画一种意境和氛围以追求一种情调感。而与其说苏童的小说追求情节的整体性、时空的秩序,不如说苏童更看重氛围的营造,借助意象将主人公的心理情感的变化作为叙事线索,营造感情化的动人意境。
在文本层面,意象的有效处理,不仅能够作为“文眼”凝缩时空感,提高表达震撼强度,从而形成诗化的表达节奏和层次,营造诗化的氛围。在小说《碧奴》中,泪水是小说中重要的半虚化意象,不仅切实可感,还凝结了桃村千百年的历史,更承载着碧奴千里寻夫的文化苦难。小说中这样描写:“浮云从断肠崖上飘过,在山腰筑城的人有时能看见碧奴,一个小小的人影子,云一退就浮了上来。他们听不清她哭泣的声音,听见的是风声呼啸,从断肠岩吹来的风,每一阵风都在呜咽,那风吹到民工们的身上,是湿润的,像南方的风,有点粘稠。”⑭这样的表达里,虽然不是对泪水的直接描写,但是通过碧奴哭泣的身影的勾勒,碧奴一路走来的艰辛都跃然纸上,语言是诗化的,但是女子的形象却是坚韧感人的。
一部文学作品的完成,仅靠作者的撰写是不够的,还需要在文本中作者、叙述者、以及读者的相互对话来完成。在读者接受层面,诗化氛围的营造因为自身带有较多的审美因素,所以极大提高了读者的审美感受,提升了这种特殊的“对话”效率。
(三)强化主题思想
杨义表示:“意象作为‘文眼’,它具有凝聚意义,凝聚精神的功能。”⑮苏童的小说中,意象的设置经常会起到丰满人物形象、点明主题思想的作用,在意象被反复渲染,读者体悟之后,会达到拓展精神空间,强化主题思想的叙事功能。
《西瓜船》中,人情的质朴与美好围绕西瓜展开,福三因为西瓜而死,因为一条人命,城和乡的隔阂将永远都在,可当一个悲伤的母亲忍着巨大的痛苦质朴地表达她的温情,撑着借来的西瓜船消失在那条连接城乡的河流时,这种隔阂却又似乎有了消解的迹象;在《蛇为什么会飞》中,蛇作为重要意象多次出现,开篇蛇出现在女孩的浴室,篇末克渊看到蛇腾空而起,蛇的意外出现都暗示着人心和社会就像手中的蛇一样难以把握,难以估计;《河岸》中,库文轩为现实所累,在俗世意义上,他几乎是一个彻底失败的人,在没有岸作为生存的依傍的时候,他选择怀抱墓碑沉入水底,河流与河岸的关系是微妙的,他们相互对立却又相互依存,成为彼此存活的意义载体,生活就是孤独、荒谬和无奈的组合。
文本具有神奇的强化情感和思想的力量,而在这种强化过程里是不具有鲜明的逻辑关系的,意象作为往往是解读这种情感和思想的暗含空间的窗口,在不刻意解读主旨的时候,意象总是在不经意间给予读者最深刻的震撼。而苏童小说中,意象尤为如此,正确而深刻地解读意象能够帮助读者了解作者的情感表达、人物的喜怒哀乐,进而体悟作品的宏大的思想空间。
五
上世纪80年代以来,文学因为不再有主题化的概念制约作家进行个人化的思考而进入多元化创作的时代,作家开始享有话语权,能够在对文本审美价值的追求过程中,获得广阔而自由的心灵空间。从共时的角度看,将苏童与同时代的余华、格非等作家进行比较,无疑,苏童在意象营构方面是最具有活力的,他穿梭在传统叙事模式和现代叙事技巧之间,借助意象的营造加大文本的深层叙事动力,并与其独特的解读生命方式相暗合,创造了苏童个人独属的艺术空间。从历时的角度看,苏童的写作某种程度上回归了传统叙事,抒情化的语言,传奇的情节,古典文化的精髓被引入其小说文本意象营构中,形成他独特的艺术风格。就近几年苏童的创作看,“先锋文学”“新历史主义”的标签已经不能满足对苏童写作特色的定义,他是不满足自身的作家,永远试图用创作的笔作出提升性的改变,作为读者,我们还可以满怀信心地期待。
面对当下复杂的社会环境,作家对于文学和自我的选择是困难的,怎样在保留大众化的审美特性的同时,表达自己的人文关怀,又怎样在实现自身创作突破的同时,坚守自己的文学观念,这些都将是苏童作为当代作家需要思考和解决的难题。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文学院常熟理工学院)
①③⑥⑩⑬⑮《中国叙事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87-188页,第187页,第213页,第230页,第220-221页,第222页。
②陈铭《意与境:中国古典诗词美学三味》[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3页。
④苏童《城北地带》[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1页。
⑤唐北华《〈黄雀记〉:转型回归下的意象取向》[J],《小说评论》,2014年第6期,第170页。
⑦[瑞士]卡尔·古斯塔夫·荣格《原型与集体无意识》[M],徐德林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1年版,第67页。
⑧⑨⑪苏童《黄雀记》[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3年版,第298页,第299页,第119页。
⑫吴雪丽《苏童小说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78页。
⑭苏童《碧奴》[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6年版,第2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