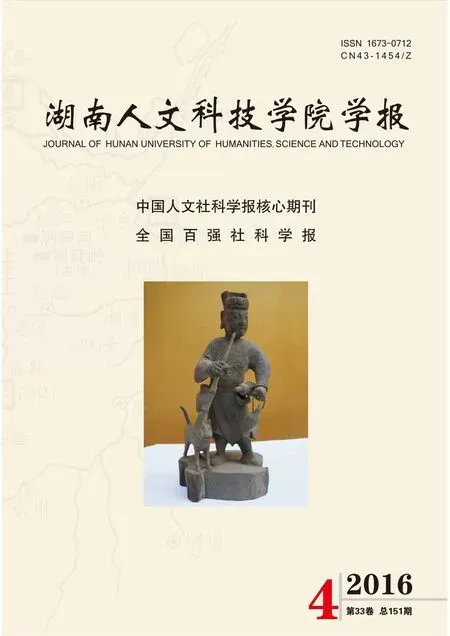“被缚的祖克曼”三部曲的空间叙事
赵智慧
(河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24)
“被缚的祖克曼”三部曲的空间叙事
赵智慧
(河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24)
菲利普·罗斯的“被缚的祖克曼”三部曲蕴含着丰富的空间叙事艺术。链条式的空间叙事结构把围绕着内森·祖克曼而发生的时间跨度很大的复杂事件表现得清楚明了;小说中“灯塔式”空间、“家园式”空间、“牢笼式”空间构成的多层次叙事空间,将家园、城市、国家、全球范围内的大事小事戏剧性地联系在一起,强化了小说的叙事功能。此外,作者在虚构的故事空间中展现了同化、异化、种族冲突、文化冲突等众多主题,形成了主题的空间聚集效应。分析“被缚的祖克曼”三部曲中的空间叙事艺术能为解读罗斯的文学创作思路与文化立场提供新的角度。
菲利普·罗斯;“被缚的祖克曼”三部曲;空间叙事
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1933—)是当代美国犹太文学作家,被誉为“美国活着的文学神话”。近年来,罗斯的中期创作越来越受到学者的关注,尤其是对《鬼作家》《被释放的祖克曼》《解剖课》构成的“被缚的祖克曼”三部曲聚焦较多。但是前人对其相关研究大多注重分析作品的内容,而对作为形式层面的叙事关注不多。笔者发现,“被缚的祖克曼”三部曲在叙事过程中淡化了时间顺序,转向突出空间的重要性,蕴含着丰富的空间叙事艺术。链条式的空间叙事结构把围绕着内森·祖克曼而发生的时间跨度很大的复杂事件表现得清楚明了;小说中“灯塔式”空间、“家园式”空间、“牢笼式”空间构成的多层次叙事空间,将家园、城市、国家、全球范围内的大事小事戏剧性地联系在一起,强化了小说的叙事功能。此外, 罗斯在虚构的故事空间中展现了同化、异化、种族冲突、文化冲突等众多主题,形成了主题的空间聚集效应。
一 链条式的空间叙事结构
链条式的空间叙事结构是以卡尔维诺的“时间零”理论为基础的,因此,理解卡尔维诺的“时间零”理论非常重要。依照卡尔维诺的看法,“时间零”是相对于描写故事的来龙(时间负一)和去脉(时间一)而言的,“时间零”是一个无比丰富的宇宙,其体现出的更多的是空间因素。“被缚的祖克曼”三部曲使用了链条式的空间叙事结构,无论是从单部作品来看,还是从三部曲的整体结构来看,该形式都得到了运用,小说的空间建构与主体的形成同步完成,核心故事中插入了大量的插话,插话之间、插话与主体之间是紧密的链条关系,暗含理性与逻辑,从而打破了传统的线性因果叙事结构。
“被缚的祖克曼”三部曲中的每一部都采用了链条式的空间叙事结构:
第一部曲《鬼作家》讲的是中年作家内森·祖克曼回忆自己年轻时代的故事。在小说的开头,23岁的主人公祖克曼在成名后寻访自己最崇拜的作家E.I.洛诺夫,他前往对方位于伯克希尔山的家中做客,这是“时间零”。在祖克曼与洛诺夫初次谈话时,祖克曼回忆了自己在芝加哥人文学院的求学时光以及在格林威治追求“美国梦”的青葱岁月,这是时间负一。随着与洛诺夫谈话的深入,祖克曼回忆起自己在故乡纽瓦克的成长经历,这是时间负二。祖克曼在伯克希尔山洛诺夫的家中偶然发现洛诺夫与二战屠犹幸存者艾米·布莱特的不伦之恋,这发生在“时间零”之后,因此是时间一。洛诺夫的妻子霍普对丈夫的出轨终于忍无可忍,冒着风雪离家出走,洛诺夫急忙追赶,祖克曼的拜访告一段落,这是时间二。
第二部曲《被释放的祖克曼》的开头承接第一部曲的结尾。祖克曼第四本书《卡诺夫斯基》的出版,让他突然受到世人瞩目,成了家喻户晓的当红作家,这是“时间零”。这本描写某犹太青年浪荡生活的小说让祖克曼从此告别穷苦岁月和多年的伴侣劳拉,开始和女影星出双入对,还时常受到路人的骚扰,这是时间一。成为当红作家并没有使祖克曼感到快乐、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他回忆起父亲中风,父母迁居迈阿密疗养的事,这是时间负一。《卡诺夫斯基》的“半自传体”性质给他的家庭带来恶名,母亲饱受压力,父亲去世,弟弟最后情绪失控对他痛骂,这是时间二。
第三部曲《解剖课》的开头承接第二部曲的结尾,在埋葬父亲之后,渐入中年的祖克曼在身体上突然感受到一种无从诊断的疼痛,甚至精神也备受折磨,他不得不依靠止痛药度日,写作无法继续,连行动都为疼痛所限,这是“时间零”。在焦虑不安中,他回忆起自己几次失败的婚姻经历以及家人之间的关系,这是时间负一。恋旧情绪与忏悔感使祖克曼下定决心返回芝加哥大学攻读医学学位,这是时间一。
总体来看,小说并没有按时间顺序叙述祖克曼的人生经历,而是将现在与回忆里的过去层层交织,环环相扣,整部小说便得以像链条般依次展开。但是,这种叙事模式也导致许多信息和内容枝节横生、旁逸斜出,阻碍了读者一贯到底的阅读与理解,延缓了阅读速度,也使通常的线性时间流中断了,从而营造了丰满的空间感。
链条式的空间结构不仅体现在每部作品的作品内部,还贯穿于三部曲的整体结构,从整体上看,三部曲中的事件围绕祖克曼环环相扣,浑然一体。《鬼作家》发表于1979年,《被释放的祖克曼》发表于1981年,《解剖课》发表于1983年,三部曲的故事空间和话语空间都遵循了时间的因果联系,具有一致性。每部曲都从事件中间开始写,虽然没有按照时间顺序,但暗含理性与秩序,三部曲构成有机的整体,把时间跨度很大的复杂事件通过链条式的空间叙事结构表现得清楚明了(见表1)。

表1 “被缚的祖克曼”三部曲的链条式空间叙事结构
二 多层次的空间叙事意象
小说以链条式的空间叙事结构为支撑,围绕主人公内森·祖克曼追寻“美国梦”旅程中的重要场所展开叙事。这些不同的场所在祖克曼人生经历中的不同时期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并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我们可以将他经历的所有场所概括为“灯塔式”空间、“家园式”空间、“牢笼式”空间等空间叙事意象,它们将家园、城市、国家、全球范围内的大事小事戏剧性地联系在一起,使小说的叙事在多层次的空间展开,具有很强的叙事功能和隐喻功能。
“灯塔式”空间是第一层次的叙事空间,在三部曲中占据着大量的篇幅,尤其是在《鬼作家》和《被释放的祖克曼》中。灯塔是希望的象征,指引我们前行。小说中的芝加哥、格林威治村、曼哈顿、纽约等场所可以归为“灯塔式”空间一类。主人公祖克曼来自纽瓦克犹太社区,他梦想能成为一名像美国上流社会那样生活的作家,他在寻求“灯塔式”空间的过程中实现了自己的梦想。祖克曼追寻的第一个灯塔式空间是纽约。纽约作为世界文化中心,对爱好文学的祖克曼独具吸引力。阿尔弗雷德·科恩在谈到纽约的魅力时说:“生活在艺术诞生之地本身就是一种资本,那里的一草一木都在不知不觉之中影响着你。看到有些艺术作品与城市本身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你会自言自语:‘我也想这么做。’在纽约这样的地方,这种情形出现的概率大大增加。”[1]16岁的虔诚犹太教徒祖克曼从纽瓦克来到芝加哥,很快被西方现代文化吸引,在芝加哥大学人文学院受到的美国式教育促使其价值观和思维模式巨变,很快陷入1950—1960年代的文化狂热。祖克曼以芝加哥大学人文学院为“中心化的空间”,建构起纽约的知识分子文化身份,完成第一次编码。祖克曼追寻的第二个灯塔式空间是格林威治村。“格林威治村是一种理念,是一种强大的文化吸引力。它在文化活动与社会关系上的流动性也是一个显著特征。”[2]其自由开放的文化氛围使祖克曼的“美国梦”得以孕育。在这里,祖克曼追逐着文学创作上的早日成名,这是一种战略,将会使他摆脱生存压力,跻身纽约上层社会。祖克曼追寻的第三个灯塔式空间是曼哈顿。在“美国梦”的路途上,格林威治村只是一块跳板,曼哈顿才是终极目标。《卡诺夫斯基》的发表使内森一举成名,地位也随之提高。他从格林威治移居曼哈顿,不用再为生计发愁,可以专心创作。至此,他实现了梦想,取得了物质层面的成功以及生活品质的提升。这些灯塔式空间体现出主人公祖克曼的性格和命运,为故事情节的安排提供了基点。
小说的第二个叙事空间层次是“家园式”空间。家园是人类的力量之源,是给人以归属和安全感的空间。在小说中,家园式空间主要是指祖克曼的故乡纽瓦克。“纽瓦克情结”早已融入祖克曼的灵与肉,是他的生命之根、灵感之源,启迪他进行艺术创造。祖克曼16岁之前一直生活在纽瓦克犹太社区,深受纽瓦克犹太家庭影响,即便在接受美国文化之后,也没有忘记自己的犹太民族身份。在为梦想打拼的路上,不论喜和忧,他首先想到的都是自己纽瓦克的家园,尤其是当《卡诺夫斯基》的出版备受读者和评论界攻击的时候,他最先想到的是回家保护父母,使其免受骚扰。另外,祖克曼遭遇了三次失败的婚姻,每次失败后他都会回家把事情告诉父母,并寻求精神上的安慰。后来,父亲含恨而死,母亲接着去世,兄弟关系疏远,他也逐渐和犹太传统文化相隔,失去了与他血脉相连的写作题材,他“没有了父亲,没有了母亲,没有了家乡,他也不再是一个小说家。不再是谁的儿子,不再是什么作家。所有曾激励过他的一切都已然消亡,没有留下任何东西可以索取、利用、扩大和重建”[3]。小说的第三层次叙事空间是“牢笼式”空间。小说中空间叙事意象的隐喻意义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情境的变化而改变。在作品中,“家园式”空间和“灯塔式”空间最后都向“牢笼式”空间转换,昔日成全梦想的空间和启迪灵感的空间而今变成束缚。祖克曼自由叛逆,与父亲不和,父子冲突激烈,导致“家园式”空间变成“牢笼式”空间,这也是祖克曼不断追求“灯塔式”空间的原因之一。但是当他实现所谓的美国作家梦之后,原来的家庭、婚姻都因此破裂,他曾经追逐的生活并不是他想要的生活,“灯塔式”空间此时变成“牢笼式”空间。在“牢笼式”空间中,祖克曼饱受身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那间曾使他创作出惊世骇俗的文学作品的书房再也不能给他灯塔一样的希望的指引,而变成了囚禁身体的牢笼之所。
三 空间叙事的主题聚集效应
小说链条式的空间叙事结构、多层次叙事空间的安排实际上是为了帮助作者在立体的空间中塑造人物,表达现代人在现代生存空间中的生存现状,同时也使小说表达了同化、异化、种族冲突、文化冲突等众多主题,而这些主题又都与空间密切相关,形成了主题的空间聚集效应。主人公祖克曼与众多女性的关系以及祖克曼与家庭成员的关系构成了三部曲中人物关系的主要图谱。本来毫无关系的一些人,在罗斯的精心安排下共享一种群体关系,以主人公祖克曼为中心,形成了类似于米切尔森所说的“桔瓣”形空间效果,使许多信息和内容枝节横生、旁逸斜出,阻碍了读者一贯到底的阅读与理解,延缓了阅读速度,使通常的线性时间流中断了,从而营造了丰满的空间感,使得同化、异化、种族冲突、文化冲突等众多主题得以集中表现。
美国犹太青年祖克曼在追求“美国梦”的过程中首先要面对“同化”问题。同化问题是祖克曼在都市寻梦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问题。祖克曼在格林威治村的沉潜式写作是一种“知识战略”,他为融入社会主流群体,选择了主动“同化”,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跻身纽约上层社会空间,享受美国主流群体的权利与自由。
同化的过程给祖克曼带来了精神的异化问题。物质上的成功使祖克曼转向思考形而上的问题,比如民族身份的认同、自我身份的界定等。一方面,美国思维方式的植入,使祖克曼直面犹太文化的“劣根性”,并大胆书于笔端;另一方面,他的写作导致他的犹太家庭发生一系列的冲突,酿成家破人亡的悲剧,也给祖克曼带来永远的精神伤痛。我们不难发现,正是犹太性与美国性、传统性与现代性的交锋,导致以祖克曼为代表的美国犹太作家群体在美国多元文化背景下艰难的生存现状,他们在两种异质文化的夹缝空间里无法逃避被“边缘化”的命运。
精神异化的危机催生出了祖克曼精神衰弱的症状。祖克曼时刻都处于两种文化“边缘空间”的焦虑之中,经历着内在与外在双层意义上的放逐,他最后选择超越犹太性,到布拉格寻找精神之父,这也是美国犹太作家面临精神危机寻求“精神之父”以解脱危机的隐喻。
相对于传统的历时性小说,主题的空间聚集导致读者阅读起来难度加大,但是也促进了读者在共时性的角度思考空间横剖面上共存的诸多问题。纽瓦克、格林威治、纽约等典型空间的选定,促使小说中同化、异化、种族冲突、文化冲突等众多主题巧妙地聚集在同一横剖面上。这对于读者了解和思考第三代犹太移民作家群体在1960—1970年代的生存困境十分有益。
在全球化背景下,文学理论的“空间转向”为我们解读文学作品提供了更加开阔的视野。罗斯的作品情节性弱,空间性强,与同时代的“空间转向”不谋而合。分析“被缚的祖克曼”三部曲中的空间叙事艺术能为解读罗斯的文学创作思路与文化立场提供新的角度。
[1]杰西·祖巴.纽约文学地图[M].薛玉凤,康天峰,译.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11.
[2]艾瑞克·洪伯格.纽约地标:文化和文学意向中的城市文明[M].瞿荔丽,译.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8:133.
[3]菲利普·罗斯.解剖课[M].郭国良,高思飞,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35.
(责任编校:彭巍颐)
The Narratives of Space in Zuckerman Bound Trilogy
ZHAOZhi-hui
(School of Literature, Hebei Normal University, Shijiazhuang 050024, China)
Zuckerman Bound is a trilogy written by Philip Roth. It is characteristic of rich and chain-structured narratives of space, which present clearly the complicated stories of Nathan Zuckerman that spans a long period of time. The multi-layered narrative space-the space of lighthouse, home, and cage-strengthens the narrative function of the novel by connecting in a dramatic manner all the major and trivial events that occur in the home, the city, the country, and the world. In addition, Roth deals with a variety of topics in the fictional space, such as assimilation, alienation, racial and cultural conflicts, thus producing the effect of space aggregation of the theme. The art of the space narrative in Zukerman Bound proves to be a new angle for us to understand Roth′s literary thinking and cultural standpoint.
Philip Roth ; Zuckerman Bound Trilogy ; narrative of space
2016-03-19.
赵智慧(1990—),女,河北清苑人,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在读硕士,研究方向:美国犹太文学、比较文学。
I106.4
A
1673-0712(2016)04-0082-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