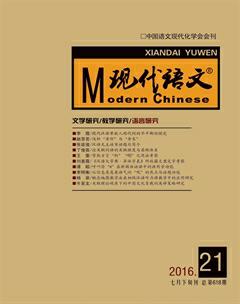男权社会中的女性悲歌
——浅析毕飞宇“玉米”系列小说
○白玉红
男权社会中的女性悲歌
——浅析毕飞宇“玉米”系列小说
○白玉红
曾有评论说毕飞宇是“写女性心理最好的男作家”。毕飞宇在一次访谈中回应说:“说起我写的人物女性的比例偏高,可能与我的创作母题有关,我的创作母题是什么呢?简单地说,是伤害”。[1]伤害,是毕飞宇作品的关键词。他的作品中总是弥漫着一种古典的忧伤,他用平实朴素又暗含讽刺的语言叙述了社会对女性爱的缺乏,乡村女性为生存环境改善所作的艰苦努力,以及男权伦理社会对女性无意识的伤害。
毕飞宇的“玉米”系列展示了20世纪70年代中国乡村和城镇生活的日常情景,描写的是女性被一次次伤害的悲剧。系列中三个女主人公玉米、玉秀、玉秧有着各自不同的性格特征和理想追求,从宏观角度上看,作为王家庄党支部书记王连方家的三姐妹,她们的生存大背景和命运遭际又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都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和对自由的追求;都对自我价值的实现和尴尬生存境遇的改善做出过不懈的努力;作为女性,她们都有着自身难以克服的同性相互嫉妒和倾轧的弱点;而在强大的男权伦理社会和封建旧势力笼罩下,她们无一例外地受到精神和肉体的双重迫害。
一
对毕飞宇来说,玉米、玉秀和玉秧,是血缘相关的三个独立的女子,同时又是他所关注的三个问题。他笔下的女性世界可大致划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类是坚韧宽厚的玉米们。她们是女性中的强者,能干好强,又有城府心计,在女性中处于支配者地位,受到男人和女人共同的尊宠;第二类是漂亮狐媚的玉秀们。她们受上帝的眷顾,有美丽的外表和女人特有的小聪明和机灵劲儿,是男性不怀好意的猎物和女性嫉妒的对象;还有一类是老实纯朴的玉秧们。她们是沉默的大多数,既没有迷人的外表,也没有突出的特长,在公共场合听不到她们的声音,是受忽视的女性人群。毕飞宇对这三类女性命运的思考,表现了他对女性整体命运的无限关注和忧虑。
玉米是毕飞宇创作出来的接近完美的女性,她符合中国传统文化对女性的所有标准:漂亮端庄、要强好胜、勤俭持家,是男权伦理社会的自觉维护者。玉米尽管也有过马缨花(张贤亮《绿化树》)、巧珍(路遥《人生》)一样美丽的爱情,但她比她们有更多的欲望和追求,除了爱情,她还要名,要利,更要权。玉米在父亲丧失权力、两个妹妹被人强奸、自己的爱情也夭折的多重打击下,进一步认识到权力的可贵和神奇。因此,她孤注一掷地用青春、美貌赌权力:义无反顾地嫁给了年龄像她父亲一样大的公社革委会副主任郭家兴做填房。她心目中的女人应该是这样的:一是不能太漂亮,做什么事都要得体大方。你漂亮可以,但不可以招摇,招来了男人的邪恶眼光就是你的错,谁让你是狐狸精?从这里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在小八子出生之后,玉米抱着他挨家挨户对和父亲有染的女人们进行无言的羞辱,“玉米一家一家地站,其实是一家一家地揭发,一家一家地通告,谁也别想漏网”,这样的举动是一种宣战,一种谋略,小八子是她为母亲复仇的“唯一武器”。父亲借助权力犯下的罪恶却让受害的可怜女人去承担,这也是玉米的狭隘之处。二是玉米认为女人还应是理家好手。“女人活着为了什么?还不就是持家”“做姑娘的时候早早学会了带孩子、持家,将来有了对象,过了门,圆了房,清早一起床就是一个利索的新媳妇,好媳妇,再也不要低了头,从眼眶的角落偷偷地打量婆婆的脸色了。”这种传统又普遍的女性认识,玉米是坚决以身作则的。因此,她和玉秀及以柳粉香为代表的王家庄风流女子作了顽强的斗争。她在最终获得了好女人的尊敬、坏女人的恐惧、男人们的敬畏的同时,也吞下了自己酿成的苦果。
玉秀属于女人中最惹眼的一类,有点狐媚子,喜欢把自己打扮得花枝招展,耍女人的小聪明。她的美貌和妖媚使她在父亲王连方倒台后成为第一个受害者。失了贞的美女,漂亮也打了折扣。在传统中国文化笼罩下,她犯了玉米“女人样”的第一条,触犯男权的金科玉律,注定得不到幸福的婚姻。在封建道德教育下长大的玉秀,虽然爱炫耀自己的美丽,却也不能摆脱儒家礼教文化的束缚,自己也认为自己犯下见不得人的罪恶,只能在幸福的边缘打转。红颜薄命,玉秀就像一只善良的小狐狸,她无心伤害任何人,却要处处提防猎人设下的种种陷阱,一不小心就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玉秧是王家的七丫头,她既没有玉米的能干和心计,也没有玉秀的漂亮和机灵,在姐姐们的灿烂光环下,根本无法去享受父母的疼爱,她正如“长江里的一泡尿,有你不多,没你不少。”寂寞的生活中她只有把希望寄托在读书上,凭借死记硬背,考上了镇上的师范学校,长久的沉默使她一瞬间的爆发显得特别地耀眼,连玉米也说“这丫头谁也不靠,硬是凭着一笔一画,把自己送进城里。这就显得特别得过硬,特别得不简单。”可学校里严重的城乡歧视使玉秧的光芒很快散尽,就像昙花一现,可鲜花掌声在玉秧印象中过于深刻,她再无法忍受这种长久的寂寞,希望被人注意的强烈渴望使她在压抑的集中营式的生活氛围和自卑情节等催化剂的催化下,迅速心理畸变,害人害己,逐渐走上精神的覆灭。
二
“玉米”系列小说中的三位女性,无疑都是悲剧人物。毕飞宇用她们每个人不同的人生故事表明,在对权力的高度认同和盲目崇拜中,个人对欲望追逐的不择手段,最终泯灭了人类的自然天性和良知,从而导致了自我人格的沦丧,他通过一系列鲜活人物形象揭示了在传统宗法制度中形成的根深蒂固的权力意识。
王连方是王家庄权力的代表,凭借权力他可以为所欲为,情欲横跨王家庄老中青三代女子。正是在这个权力高度集中的家庭背景下,逐渐滋养着玉米内心对权力的欲望。从对权力的初步认识、发展到成熟,玉米对权力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观点——“权力就像一只拳头”,拥有权力时,玉米家是怎样地风光无限,而当王连方失势了,噩梦便接踵而来,门庭衰落、讥讽的眼光、村民们疯狂的报复、玉秀玉穗的失身、彭国梁的悔婚像一根根毒刺深深刺进玉米的心中,为重获权力的庇护,她委曲求全,怀着视死如归的悲壮向男权的霸道嚣张投降了,屈服了女人隐忍屈辱的命运。“谋求权力的潜意识和维护这种权力的人性与自我天性的悖离,都不自觉地在玉米身上发生”。[2]玉米是被权力意识和男权专制浸染腐化而失却灵魂与尊严的牺牲品。
如果说对权力的追逐是玉米生存的唯一目的,那么玉秀追逐的则是生命的自由和生活的美好。而在现实生活中玉秀却是坏女人的代表,她遭受来自家庭和社会的恶毒攻击,虚伪的道德家们都以传统的伦理成见和所谓的社会道德来谴责她,视她为破坏社会安定、毁灭伦理纲常的罪魁祸首。红颜玉秀没有玉米那样政治家的过硬手腕,她想在强大的命运面前保全自己弱小的生存权力,只有投靠权力。于是,玉秀在王家庄依仗父亲王连方的宠爱,到了镇上拉拢郭家兴及其女儿郭巧巧去对抗姐姐的“强权”,对抗玉米试图对自己命运的掌控。然而这种对抗是不牢靠的,一旦失去了靠山,玉秀只能屈服,比之玉米,玉秀有着女性更为软弱的一面。
同为女人,玉米有为人称道的能干和好名声,玉秀有漂亮的容貌和男人的“青睐”,而玉秧却只有生命中最平庸的色彩,一种沉闷而笨拙的色彩。玉秧的悲剧是一个被世俗世情掩盖了的生活真实的生命存在。在那个到处都充满紧张气氛的师范学校,平凡老实的玉秧是受人欺负的对象,压抑的环境和极度的自卑扭曲了她年轻的心灵。平庸不代表内心没有对生活的热爱,相反,她对别人的注视有着更加强烈的渴望。而此时权力卑鄙地利用了平凡女性的弱点,将玉秧逐渐引向悲剧的深渊。当魏向东以“组织”的名义招玉秧参加“地下工作组织”时,玉秧以为看到了人生的转机。她怀着莫明的兴奋和快乐学会了侦查、分析、推理等手段,仿佛找到了自我价值实现的途径,可怜的玉秧不明白她是被权力实实在在地利用了一回。她被权力伤害,又用权力去伤害别人。《玉秧》对平凡女性的关注,替女性呼喊出了的生命强音:最平庸的生命也包含了最激动人心的内在亢奋和外在欲求。
“玉米”系列看似凡人小事,故事也不过是日常生活的琐碎与变故,但隐约其后的权势和社会差别的阴影里细致地写出了女性的命运,特别是农村女子曲折微妙的心性,串联起来则见到内在同一性,隐喻了女性共同的悲剧。
三
“生存是考验人性和扭曲人性的本原,个体生命因为生存的挣扎和欲望的焦灼而向往天堂,却坠入地狱”。[3]两千多年女性自古不变的悲剧命运的缔造者,除了中国传统文化、男权伦理社会,还有女性自身难以克服的弱点。她们之间为争夺狭窄的边缘生存环境互相争夺、互相倾轧,进行着女人之间的战争。她们之间的争斗不像男人们那样刀光剑影,是心智的较量,智慧的表现,但其激烈程度和杀伤力却并不亚于兵戈相见。“玉米”三部曲真切形象地写出了女人之间的种种冲突。如“玉米”系列中玉米与柳粉香。玉米对柳粉香的攻击不仅仅出于柳粉香与父亲有着见不得人的关系,还有一种她不愿意承认的嫉妒情愫在里面。柳粉香漂亮、风骚又聪明,偷了父亲心的她在骄傲的玉米面前不卑不亢,一直保持着内心的尊贵,更令玉米生气的是庄里已经有一些姑娘开始模仿柳粉香巧笑的模样和走路的姿势了。三次正面唇枪舌剑的交锋,柳粉香都以得体大方的对答使玉米没有占到任何便宜。柳粉香作为一个善良的失足女子,她佩服玉米的能干,欣赏玉米的优点,有点惺惺相惜的意味,决无意与之为敌。而玉米则不然,内心深处对男权制度和家庭的自觉维护促使她恨透了这个风骚的女人,更无法容忍这样受人鄙视的女人有比自己强的地方。
外姓女子之间的斗争犹可理解,而亲姐妹间的斗争则匪夷所思。从玉米第一次在饭桌上掌权开始,她和玉秀之间的战争就拉开了序幕。玉米恼怒玉秀竟敢仗着父亲的疼爱挑战她在家里的权威,而玉秀也不满大姐颐指气使的专制手腕。玉米依靠缜密的心机迫使玉秀不再干涉她在家里除了父亲母亲外说一不二的地位,但不意味着从心里彻底地服从。玉秀失身后,她们的关系有了暂时的缓和,而到了郭家兴家里,她们之间的战争再次打响。可玉米是强硬的,是冷漠的,软弱无力的玉秀在玉米的阴谋中品味了人生的悲苦滋味。
姐妹和其他女性之间的争斗,除了女性自身的弱点外,还说明了因为女性边缘身份的空间狭小与艰难,她们不得不屈服于男性专制的共同悲哀。
四
“玉米”三部曲从人性的角度上透视出酿成女性悲剧的内在基因,暗示出既定命运对女性文化心理、生存境遇的先天塑造及严酷制约。如果说“玉米”三部曲是古老中国关于女性的一曲忧伤的旋律,那么玉米就是贯穿其中的那痛彻肺腑的主调,由她的经历演绎出村中生存在男性阴影下的一个个女性的无奈乃至沉沦。玉米是在中国两千年儒家文化的熏染下长大的,族权、父权、夫权就像是锁链仍禁锢着中国妇女的灵魂,玉米的反抗是狭隘的,斗争目标也是不明确的,她把男性的罪恶归结于女性的诱惑,她的自残自虐自我堕落既悲壮又令人痛心,她的愚惘给女性悲剧添加了浓重的一笔。
女性在社会中不可否认地处于弱势地位,男权社会给予女性生存发展的狭小空间和女性天生对自由的追求和向往形成了尖锐的冲突。从玉米、玉秀到玉秧,她们都在执着的奋斗和艰难的挣扎中试图改变自己的生存环境与既定的悲苦命运。但是,她们又都在追求的过程中失落了自我,而把满足欲望的希冀寄托在某种外部力量上,比如男人、权力、名利等等,认识的局限和自身的不足,导致了盲目的行为,欲望对人性实施了残酷的伤害与扭曲,最终只能上演女性压抑痛楚、失去自我的人生悲剧。“玉米”系列小说在日常化的冷静叙述中写出了乡村女性的世俗生活和普遍命运,从一些稍有权力的男性行为中揭示出人性的丑陋及其对女性的残暴与伤害,以及男性制约下民族文化心理的滞后和集体无意识的悲剧。
注释:
[1]毕飞宇,汪政:《语言的宿命》,南方文坛,2002年,第4期,第29页。
[2]赵玉柱:《传统思想约束与权力欲望膨胀下的生命悲歌——读毕飞宇的中篇小说<玉米>》,名作欣赏,2005年,第5期,第69页。
[3]张宗刚:《诗性的坚守 深度的探求——毕飞宇<玉米>三部曲解读》,名作欣赏,2005年,第5期,第103页。
(白玉红 郑州师范学院中文系 4500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