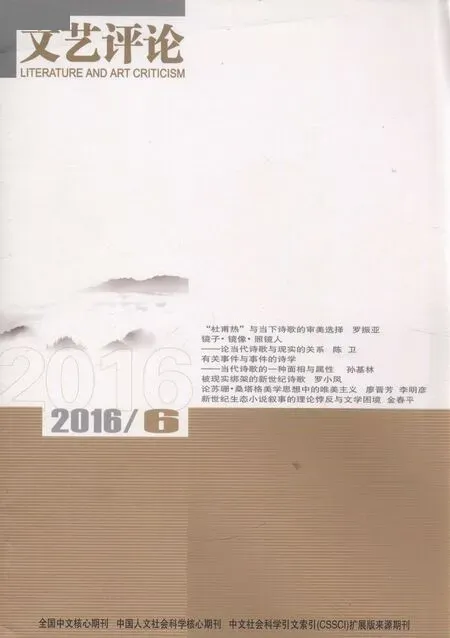超越现代性:“个人化写作”再审视
○陈 雪 刘泰然
超越现代性:“个人化写作”再审视
○陈 雪 刘泰然
在上个世纪90年代,伴随着“告别革命”的呼声,中国文学的书写方式发生了一次普遍的转型:无论在诗歌领域,还是在小说领域,无论是知识分子写作,还是民间立场,文学表现出一种普遍的疏离态度,即试图与1990年以前的写作范式保持必要的距离。这样一种立场既是对“文革”的政治化书写模式的抵制,也是对文学在整个上世纪80年代所承担的社会变革、集体代言功能的怀疑。总之,从集体话语中摆脱出来成为作家们的自觉追求。“个人写作”成为标识和理解整个上世纪90年代文学的重要视角。虽然在不同的语境中“个人写作”以及与之相关的“私人写作”“民间写作”等等概念往往有着不同的含义,但是其所普遍表达的对政治、对总体性、对意识形态的不信任是一致的。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而言,文学的去意识形态化、去政治化是1990年以来的文学的一种普遍趋向。有学者将这种疏离的态度称之为文学的“向内转”。即文学回到文学自身,回到写作自身,从而将社会、历史、政治、国家等等,从文学身上剥离出来。与之相伴随的是重写文学史,即从个人视角,从个体生命体验的视角对文学史进行重构。如果说在1990年前,民族、国家、历史、时代等词具有天经地义、不容置疑的修辞上的合法性的话,那么,在1990年后,这些词却已经不那么让人信服了。就像我们在十多年前所指出的:“从某种意义上说,90年代是一个普遍怀疑和反思的时代,是一个个人从集体的阴影里被努力夺回来的时代。这个时代的书写模式更是具有一种个人主义的气质。”①当然,“个人主义”一词和“个人写作”一词一样,包含着多变的语义,但无论从精神出发,还是从身体经验出发,“个人”始终成为文学得以获救的飞地。但只有时过境迁,当我们从一种更大的视野来重新审视这种“个人写作”,考察它的意义、后果、局限的时候,我们才能对整个上世纪90年代的文学的价值与趣味有一个更清楚的认识。
一、现代性与个人主义话语的兴起
个人、个体的概念在现代性的语境中有着特殊的意义。在我们看来,首先有了现代性的主体意识然后才会有现代性的个体意识。肇始于笛卡尔的我思哲学将自我设定为理解世界的基点。由之才生发出主体与客体、自我与他者、个人与国家等等二元对立式的关系结构。“个体”概念虽然与“主体”概念有着语义上的差别,但是在发生的逻辑上却有着一种先后相承的关系。只有首先从世界中抽离出来,将自我设置为一个认识论的阿基米德之点,才有那种明确的、实体化的个人意识。与这种认识论上的个体意识相关,在法权、公民权、经济等领域,才出现将“个人”作为一个边界明确、意义自足,有行动能力和承担能力的实体。这种个体意识导致了文学领域中“作者”观念的出现。也就是说,在前现代,“个体”没有作为一种话语被发明。只有在近代以来,从笛卡尔、霍布斯到洛克,才逐渐发展出这种强烈的个体性诉求。而这种个体话语的出现,构成了民族国家意识的一个重要前提。或许,我们可以换句话来说,“个体”意识不仅是近代的产物,而且是西方的发明。亨廷顿指出:“‘在西方被视为最重要的价值,在世界范围内最不重要。’西方人和非西方人一再把个人主义视为西方的关键特征。”②
同样,这种个人意识也体现在西方文学领域,小说的兴起及其作为叙述者的“我”的出现都标识着一种完全不同于过去的对于个人化自我的确认。从西方文学史的角度来看,这种体现在文学书写中的强烈的个体性意识恰恰表明统一的文化破碎之后,个体便需要在自我的超验世界中建构某种意义,以弥补世界的无意义性。当自我成为一个与世界相分离、相对立的个体时,史诗便被小说取而代之,“康德的星空现在是更多地在纯认识的黑夜里发光,而不再照亮任何一位孤独漫游者的小路——在新世界里做一个人就意味着是孤独的”③。本雅明也认为小说打破了那种口耳相传的讲故事的艺术的传统,消解了包含在故事艺术中的那种身体性的与世界、他者的接触,作家从世界抽身出来,走向封闭的房子进行孤独的写作,读者同样也在一种孤独的状态中进行阅读:“讲故事的人取材于自己亲历或道听途说的经验,然后把这种经验转化为听故事人的经验。小说家则闭门独处,小说诞生于离群索居的个人。此人已不能通过列举自身最深切的关怀来表达自己,他缺乏指教,对人亦无以教诲。”④可以说,文学上的个体意识以及个人主义诉求都具有深刻的现代性症候。而且与西方文化在近代以来所发生的转型密不可分,它与民族国家观念、印刷文化、版权意识等的兴起交织在一起。总之,“个人”概念与“文学”概念一样,并不是从来就有的,它的产生有着特殊的历史语境,在希利斯·米勒看来,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概念是十七八世纪以后,伴随着现代民族国家、印刷文化、民主制度、现代研究性大学以及与之相关的个人意识等的出现才登上历史舞台,而文学与个人意识的复杂关系也体现出这种历史性:“文学的整个全盛时期,都依赖于这样那样的自我观念,把自我看成自知的、负责的主体。”⑤
因此,当我们审视“文学”与“个人”的关系时,需要以一种历史化的方式将其进行祛魅,从而打破“个人写作”的神话。说“个人写作”是一个神话,是因为不仅在西方,“个人”是一种近代的发明,而且从中国文学的现代历程来看,“个人”也从来不是天经地义的,而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建构。对于中国传统文学而言,我们恐怕很难说哪一部作品具有“个人写作”的特征,“个人写作”具有明显的主观诉求与建构的特征,而且,它与一种近代以来逐渐兴起的现代性的个体意识是息息相关的。
现代性的个人意识在中国的起源与西学的引进不可分割。在1900年以后,“天赋人权”的观念被引进中国,在这之后,更多的与“个人主义”相关的论说被引进。“清末民初时期,中西文化全面接触、交流、融合,造成旧观念的解体和新观念的产生。中国传统的观念因子、意识结构乃至核心价值发生剧烈的动摇变化,西方‘个人’话语以及西方现代个人观念的一些基本要素或理念先后被引入中国。”⑥个人话语在中国的兴起来自西方,而且也和西方一样带有非常强烈的政治诉求的色彩。梁启超、陈独秀、傅斯年、李亦民、鲁迅、胡适、李大钊等等,这些人虽然立场有异,但都赋予个人主义以正面的价值,并都试图在群-己、个人-国家、立人-立国的架构中来理解个人的意义。在当时的语境中,个人意识成为民族国家意识的发动,个人的觉醒与民族的觉醒具有同等的意义。与这种思潮相对应,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也体现出强烈的个人主义诉求,并且这种诉求也具有明显的政治色彩。无论是将文学视为“新民”的手段,还是通过文学的唤醒来告别“铁屋子”,抑或将文学作为自己私人耕种的“园地”,等等,都需要放到一个现代性的“个人-国家”的构架中去获得理解。也就是说,在这种文学理解中,“个人”是相对(无论是“对立”还是“对应”)于“国家”的“个人”,而国家的理想也需要落实到一种“个人”的视野中才能够具体化。这种倾向使得中国文学的发生具有这样几个特征:首先,中国文学从一开始就受西方式的现代性的问题框架所制约;其次,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受制于一种过于强烈的政治诉求;再次,“个人”或“国家”不仅是文学书写的基本视野,也构成中国文学评价与文学理解的一种先验化视野。这样几个特征使得我们在文学写作与文学理解上进入了一个很难跳出来的怪圈,似乎文学存在的所有意义都可以由“个人”与“国家”这两种视野予以穷尽。
个人话语与国家话语所构成的封闭的二元机制总是使得受此机制所制约的文学在两者间来回震荡。个人书写很容易滑向国家叙事,而宏大叙事也很容易被个人性的身体造反所改写。因此,当文学史的风向标一旦转向,批评家们不是热衷于在个人叙事中去发现国家话语,就是在国家话语中去发掘个人抒情。无论如何,文学始终只有预先设置了“个人-国家”的理解框架,阐释才能有效进行。
因此,在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压力之下,文学很快就由个人写作变为一种民族寓言,而一旦国家意识形态出现松动,极端的个人主义的叙事又会带着历史合理性的名义纷纷出场。“个人”与“国家”似乎是两种相互对立的立场,但事实上却同属一种现代性的意识形态机制,它们相互作用,使得整个20世纪的中国文学带上了浓重的政治色彩。即使是那些反政治的写作,也由于这种反抗而受制于这种总体化的政治诉求。“直到今天,好些年轻人仍然如此。他们不知道所谓原子式的绝对独立、自由、平等的个体,正好是走向集体主义、集权主义的通道。这二者是一个钱币的正反面。”⑦而且,个人写作中的个人带有非常强烈的现代性诉求意识,它将个人从世界中抽离出来,变为一个被建构的实体。于是写作便被围绕这种虚设的实体展开,这不仅大大缩减传统文学书写的无限广阔天地,而且使文学被一种新的个人化的意识形态所绑架,进一步造成了人与世界、自我与他者、男性与女性、个人和国家等一系列二元对立的紧张。
二、“个人化写作”的意义与局限
我们不妨重新审视一下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个人化写作”的内在构成形态。“个人化写作”在上世纪90年代的文化话语中至少具有两个层面的内涵。首先是身体、隐私、个人记忆基础上的个人化写作,这种写作并一定指与女性写作相关的私人写作,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包括朱文、韩东等建立在性与欲望分析基础上的写作,甚至还包括后来的更激进的“下半身写作”等。这种写作借助西方后现代的身体话语为自己声张和正名,并不惜以种种极端化的行为来表明自己与传统写作断裂。这种写作将集体话语、国家话语、政治话语当成自己的假想敌,而将身体、性、私人生活、个人记忆作为逃离和抵抗的据点与飞地。林白说:“对我来说,个人化写作建立在个人体验和个人记忆的基础上,通过个人化的写作,将包括集体叙事视为禁忌的个人性经历从受到压抑的记忆中释放出来。”⑧这种将文学的书写限制在私人领域的做法虽然在一定时间内开拓了文学的表现领域,但是一旦将这种写作方式扩展成一种新的集体话语,那么,文学的可能性就会被私人性所架空,而变成一种新的陈词滥调。我们在这些作家这儿,并没有领略到从个人身体上所激发的丰富性和差异性,而是一种身体理解的雷同性:“作家们的主题是千篇一律的欲望、性爱、自恋、挣扎、疲惫、死亡、罪恶,而且叙事上也是众人一面的回忆、梦游、臆想、白日梦,他们在创作观念层面上对于个性的执着和张扬与其作品的模式化和非个人化构成了强烈的反差,这无疑是对他们所标榜的个人化写作姿态的有力讽刺。”⑨这种类型的个人化写作与其说是在反抗一种旧的(国家)意识形态,不如说是在迎合一种新的(国家)意识形态,所谓的“个人”,在这里不过是国家意识形态在一个商品社会中的新的表现形式而已。可以说,统一化意识形态话语在上世纪90年代解体之后,以一种更隐秘、更灵活的方式运作于个人身体之上,国家意识形态与商品美学以一种更人性、更温和的方式联手进入了身体与个人的私密空间。它用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来理解身体,建构身体,将身体重新符号化,变为一个意象,一个客体。而不是从一种原始的身体感受出发,由身体通达世界,让世界进入身体。他们的身体是自我封闭的、刻意建构的,是一种拒绝,一种画地为牢,一种顾影自怜,一种自恋。可以说这种写作从国家话语中逃离出来的同时,却以一种新的方式落入了商品话语的圈套之中。
而且,这种极端的、充满叛逆色彩的对个人身体话语的诉求所体现出来的对抗性思维仍然以一种悖论的方式受制于现代性意识形态,它对政治的反抗本身就使得写作成为一种反抗的政治。这种做法使得文学的领域并没有扩展,而是进一步以一种微妙的方式将文学绑缚在政治领域。也就是说,从现代以来,中国文学要么以臣属于国家话语、民族话语的方式政治化,要么以反抗国家话语、民族话语的方式政治化。这一点使得整个20世纪的中国文学显得过于严肃,也使得文学的功能与意义过于单一化。
这样一种政治化宿命在另一种类型的“个人化写作”中表现得更为明显。相对于身体化的个人写作在自我辩护上的暧昧,另一种存在于先锋诗歌领域的“个人化写作”则在概念的自我阐明上更具有一种理论的自觉。欧阳江河将“个人写作”理解为对群众写作与政治写作的告别:“……在转型时期,我们这一代诗人的一个基本使命就是结束群众写作和政治写作这两个神话:它们都是青春期写作的遗产。”⑩就像在十多年前的一篇文章中所说的,这种写作“对意识形态、群体话语、公共理解、纯粹情结、时间神话等的置疑则确实为90年代的写作注入了一种新的可能性。”⑪“个人写作”最初由这批“知识分子写作”诗人提出,与对身体的自我观照不一样,这种“个人写作”强调的是一种个体的承担:“其意义在于自觉摆脱、消解多少年来规范性意识形态对中国作家、诗人的支配和制约,摆脱对于‘独自去成为’的恐惧,最终达到能以个人的方式来承担人类的命运和文学本身的要求。”在“个人写作”的另一位支持者程光炜那里,个人写作的诗歌“所提出的也是如何在价值沦丧的社会生活中肯定与坚持价值的问题。它与所谓‘国家的守夜人’有极其相似的文化内涵。”⑫很显然,这种对于个人写作的界定中包含着的政治意味是不言而喻的。在以王家新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写作群体中,诗歌成为以一种个人的方式来承担历史使命的方式,成为一种典型的现代性的民族寓言“艺术难道不是为了人民吗?诗人难道不应该忠实于整个民族吗?”⑬他在诗歌中思考的是“如何使我们的写作成为一种与时代的巨大要求相称的承担”⑭。
可以看出,在这一批知识分子写作者这里,诗歌的意义不在于诗歌自身,而在于其所指涉的社会、历史关怀。我们一方面确实看到在上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诗歌静悄悄地将写作技艺的复杂性与想象力的精致推向一种从来未有的高度,但在另一方面,很大一部分诗人的骨子里仍然受制于某种更微妙的意识形态话语,使得诗歌写作变成了一种社会学和政治学的修辞,文学仍然被时代、历史、政治等话语所绑架。诗人们不是在一种更开阔、更自由的领域来处理文学与世界的关系,而是在一种现代性话语的制约中来理解文学的有限可能。由于文学对现代政治话语的反抗本身就在现代性视野之内,因此,中国文学无法超越现代性本身的困境,为此:
这种对个人的强调,对群体话语的疏离又恰恰是以一种群体运动的方式进行的。这不但体现在作为“个人写作”的实践者,其本身依然执著于我无限膨胀的神话,同时更在于这种“个人话语”的操作方法就是以一种“群众神话”运作的,其诗学潜在地受制于一种历史决定论意义上的时间神话,并进而在写作本体论上构成审美理解上的一种普遍认同:叙事、反讽、戏剧性等等手段在90年代诗歌写作中被先验地赋以某种不言自明的绝对价值。80年代的流派运动在90年代有在“个人化”名义裹挟下变成“全民运动”的危机。个人的反叛变成了对个人的反叛;知识分子所倡导的“个人写作”成了自身的掘墓人。⑮
在某种意义上,现代性是作为一种西方文化的后果被转嫁到中国来的,个人主义的文学话语所体现的西方文化资源背景也非常明显。在强调“个人写作”的诗人那里,他们虽然具有非常自觉的中国问题意识,但在处理这种问题时却普遍依托于某种非常驳杂的西方知识谱系。他们在对“个人写作”的阐释上常常以西方现代诗人、作家如布罗茨基、T.S.艾略特、W.B.叶芝、勒内·夏尔、保罗·策兰、卡内蒂等等的言论为立论的依据与支撑。在某种意义上,这种对西方个人主义的借用,仍然是“五四”时期那种追求个性解放、个体独立意识的一种延伸,但这种意识本身所包含的现代性也将现代性危机带入进来。那样一个孤独的、深度意识的自我观念,那样一种从个体的角度生发出来的历史使命感与文化责任感,等等。这种峻切的现实关怀与个人意识曾经产生了F.R.利维斯所谓的“伟大的传统”,也产生了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那样一种感时忧国的传统。但是这种写作所具有的典型的现代性文化特征使得它无法超越自身,甚至本身就成为现代性文化危机的一种症候。以至于有论者指出:“王家新‘个人写作’诗学理论中的关键术语,现实、历史、时代、政治、社会、承担等都并没有什么更额外的含义,依旧是沿着旧传统现实主义的叙事模式运行的。这种‘个人写作’关注的不是诗歌的艺术性,而是构成诗歌审美的外部世界。它是一种有关国家、民族、历史的宏大叙事,从根本上说是反个人的。”⑯
我们无法否认这种个人写作的意义,但也无法不意识到这种写作本身的限度。无论是体现在女性写作意义上的个人化写作,还是在先锋诗歌领域的个人写作,它们共同的思维方式都是典型的现代性的。它们都无法超越这种典型的个人主义的现代性话语。这种现代性话语虚构了一个独立的、自足的个体,并在这种个体与世界、个体与他者的二元关系中来理解文学问题。有论者敏锐地指出:“‘个人’所曾蕴含的积极意义在今天已然耗散,附着在‘个人’之上的‘身体’‘欲望’等叙事力量也随之式微。今天的‘个人经验’已难再聚集成为强劲的话语力量。因为,个人主义虽然驱动了90年代以来的女性写作,并使这一写作潮流形成了一定气象,但个人主义是现代性话语,在终极处它并不对‘现代性’构成颠覆,相反,它服务于‘现代性’这一总体性结构。这就是为什么如前文所述,个人主义表面上为女性写作提供了话语凭借,但最终却将她们引渡到一个更为危重的孤绝境地,引渡到一个弃世并被世界所弃的荒原。”⑰不仅女性主义的个人主义如此,知识分子的个人主义何尝不是如此,他们所声张的那种承担与拯救色彩的个人何尝不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建构,就如同拉康所说的那个镜子中的“理想我”,激发了一种想象情境中的自我认同,却不知道所认同的只是一个虚幻的影像。
从这种镜像化的自我意识,到这种自我意识被一个“大他者”改造为一个历史充满使命感的主体,是一种必然的逻辑。因此,这种个人的修辞又是脆弱的,它很容易被历史、时代、现实、人民等更大的话语所征用。这恰恰体现出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的某种困境:不是个人就是国家,不是私人欲望,就是道德审判。在对个人化写作进行反思的时候,我们需要警惕的正是这种借文学“向外转”之名,将文学重新变为一种新的社会学和政治学修辞。就像有论者在反思个人化写作时提出的“总体论”的设想:“没有总体性的社会学思想视野,批判如何可能?没有总体性视域,叙事伦理学重建与社会文化理论想象的重构如何可能?如何系统地理解和阐释我们时代的处境?又如何重构批判性、想象性和整体性的知识图景?”⑱这样一种以“总体化”之名来质问文学的作法体现的正是一种典型的非此即彼的现代性思维方式,它除了使文坛重新沦为政治厮杀的战场外,不会带来更多的东西。中国人一百多年以来在心智、想象力与热情方面的衰退不能不说与文学的过分政治化有关;这种政治化遮蔽了我们与那一个更源发、更生机勃勃的大千世界的本然的联系。只有超越“向内”与“向外”、个人与总体、政治与抒情等等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才能更本真地来理解文学之为文学,才能开拓文学的新可能性。
三、超越文学个人主义
而要超越这种要么“我执”(个人主义),要么“他执”(社会政治)的循环怪圈,我们需要在一种更灵活的自我意识中来理解“人在世界中”(而不是“人对于世界”,或“人与世界”)的存在论含义。如果说,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动源自一种西方的现代性意识,特别是那样一种被建构起来的个体意识。那么,对现代性的超越就需要我们重新返回我们自身的一种更悠久的传统,在那样一种人生在世的“天-地-人”境域中重新开启中华文运。我们有必要重新激活一种古典的“文”的传统:“文”不是一种个人的意识形态的主观建构,而是一种天地之间的自然发生,就像那自由的运行于天地之间的风一样。“风行水上,自然成文”“诗者,天地之心也”“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天覆地载,清明广大,天地更悠久,更广大,而在这种天地视域中,所需要做的不是去“独自去成为”,不是去获得某种坚硬的立场,而是虚怀万有,与天地间的人、事、物相交接。不是在一种民族国家的视野中来理解天地,而是在一种更恢弘的天地视野中来超越我们非此即彼的价值区分。
这种状态中,作家不是主体,不是极端的个体,而是与人、与事物打交道者、澄怀味象者,是仰观俯察、行走于天地之间的人,而写作则意味着让“真理自行置入作品之中”。
(作者单位:吉首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①⑪⑮刘泰然《没有完成的个人:90年代文学话语之我见》[J],《文艺争鸣》,2001年第4期,第29页,第30页,第30-31页。
②Samuel P.Huntington,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 and the Remaking of Word Order[M],Simon&Shuster Inc.1997,P.71-72.
③[匈]卢卡奇《小说理论》[M],燕远宏、李怀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27页。
④[德]瓦尔特·本雅明《讲故事的人》[A],汉娜·阿伦特编《启迪:本雅明文选》[C],张旭东、王斑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99页。
⑤[美]希利斯·米勒《文学死了吗》[M],秦立彦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4页。
⑥罗晓静《清末民初:从“人”到“个人”的过渡——论现代个人观念与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J],《江苏社会科学》,2008年第6期,第155页。
⑦刘再复、李泽厚《个人主义在中国的沉浮》[J],《华文文学》,2010年第4期,第59页。
⑧林白《记忆与个人化写作》[J],《作家》,1997年第7期,第14页。
⑨李茂民《个人化写作的背景、成就与局限》[J],《东岳论丛》,2000年第3期,第140页。
⑩欧阳江河《’89后国内诗歌写作:本土气质、中年特征与知识分子身份》[J],《花城》,1994年第5期,第205页。
⑫程光炜《骑手在路上——90年代的中国诗坛》[J],《百科知识》,1997年第5期,第33-34页。
⑬王家新《当代诗歌:在“自由”与“关怀”之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3页。
⑭王家新《阐释之外——当代诗学的一种话语分析》[J],《文学评论》,1997年第2期,第68页。
⑯姜玉琴《关于1990年代以来先锋诗歌中“个人写作”的概念研究》[J],《江苏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第45页。
⑰王侃《个人主义、性别结构及现代性》[J],《文艺争鸣》,2013年第8期,第3页。
⑱刘小新《个人化写作、总体论及介入》[J],《学术评论》,2012年第3期,第17页。
2015年湖南省教育厅资助科研项目(编号:15C1145);2013年度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编号:13YBA287);吉首大学2010年度人才引进项目(编号:jsdxkyzz201003)]
——以《文化偏至论》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