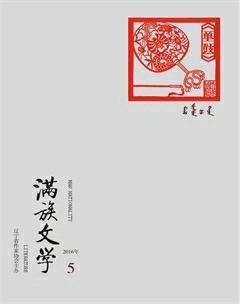大米创业记
魏国松
大米看着眼前的黄豆说:“我咋把你贴到我唇上呢?”随后大米便将指尖轻轻地触向了黄豆,他突然感觉指尖上的黄豆很饱满,也很温暖,他甚至感觉到指尖都有些微微地发胀了,这让他多少有些无所适从。
大米想还是拉上窗帘再说吧。其实这个时间段的房间里并不是太亮,透过窗子往外看,春阳已升起来好久了,可它泼洒出来的光线,每一缕都跟春天的细雨一样,斜织成了这个季节里特有的柔柔的光幕。大米放弃了拉上窗帘的想法,来到了洗手间的一面镜子前,他看到自己下唇上的燎泡足有绿豆大小,而且还不止一个,便想自己这一星期以来过的是个什么破日子呢,被眼下一些事情搞得蒙头转向,别人是急火攻心,我这是急火攻唇,把自己的唇都搞起了一溜燎泡。
大米终于下定了决心,开始咬牙为自己做起了外科手术。他先是找来了缝衣针、酒精棉和刮胡刀片,接下来打着火机将缝衣针的针尖烧红,再用酒精棉消毒,然后就开始挑起了自己唇上的燎泡。挤掉燎泡里的水后,大米就开始找起了黄豆来,找了一圈没找到,就喊起了黄豆来:“黄豆你在哪儿?黄豆你在哪儿?”喊了几声过后,大米哑然失笑,心说黄豆也不会答应,我把黄豆忘在哪儿了呢,我还是自己找找吧。大米是在自己的睡衣兜里找到那几粒黄豆的,他用刮胡刀片将黄豆切成两瓣儿,轻轻地贴在了自己的唇上。“偏方上都说黄豆解毒,看它能不能把我的燎泡快快解下去。”这之后大米摁着下唇上贴着的那溜黄豆,又自言自语起来:“出门办事我也不怕自己这形象好不好了,只要在唇上不长出豆芽来就行呀。”
其实大米在做这件事的时候是非常笨拙的,因为他脖子上一直挎着一根绷带,绷带托着他的左胳膊,X光显示,那上面有一截骨头被他自己刚刚摔劈了,气得他连石膏都没给自己打,就这么胡乱缠几下吊在了胸前。
大米的真名叫米仓,因为从小个子长得高,又好动,周围人就管他叫起了大米。“大米过来,跟我家门前的电线杆子比比个儿”,“大米过来,把那棵树尖上的鸟窝给我捅下来”,“大米过来,帮我打那伙高年级的孙子去”,“大米过来,你跳高不行你跳远总还行吧”。当时的人们就这样叫他。其实大米还有个双胞胎的姐姐叫米囤,他们同在一个娘胎里的时候,他总是抢他姐姐米囤的营养,还把他米囤姐姐踹得哭也不是不哭也不是,想告他的状却又隔着一层肚皮,就这样在娘胎里憋屈了十个月。待到他们两个出生时,大米母亲并没有使多大劲儿就把他米囤姐姐生出来了,可在接下来的几分钟之后又生大米时,大米母亲可就遭了大罪了。米囤无声无息地在那边的保温箱里躺着,大米母亲骂骂咧咧又薅接生大夫又挠助产士地在这边折腾着,终于把大米给折腾出来了。他来到人间亮的第一嗓子,竟把保温箱里的米囤逗得“嘎嘎嘎”笑了起来。这听起来够神奇的吧,连当时产房里的接生大夫和助产士都感到很神奇。后来他们的母亲在床上揽着他们姐弟两个,右胳膊上的是二斤六两的姐姐米囤,左胳膊上的是六斤二两的弟弟米仓,这一大一小的两个亲姐弟,在住院期间都成了产房里的一道稀罕景儿了。
可是三十年后,大米那个从小被周围人叫成小米粒的姐姐米囤,靠自己的打拼,在南方的某座城市站稳了脚跟,聚在她身上的财富真的可以围成一个很大的囤了。而经年生活在辽西老家这座城市的大米,只是徒有米仓的虚名,高高大大的个子上没能挂住多少财富,倒是还时不时地求助姐姐米囤开囤给他这个米仓放钱放物放给养。
由于当年家境原因,大米并没有接受很好的教育。如果上溯到他的爷爷辈,那老哥仨读的可都是张学良办的呱呱叫的东北大学。大米的大爷爷毕业后直接去了美国,去后的第二年便遇上了空难;大米的二爷爷毕业后在当时伪满洲国的新京放送局潜伏下来,后来成了林彪东野的一个活报剧团演员,在一次扮演反派角色的卖力演出中,被一颗来历不明的子弹击中身亡;大米的爷爷行三,毕业后去了戴笠的军统,还没做成一单情报,当地的天就变成了解放区的天晴朗的天。
大米记得有一年他的爷爷端着一把小泥壶对他说:“孙子耶,你知道这把壶谁使过吗?”大米摇起了头。大米的爷爷说:“这把壶我爷爷使过,然后我爹你太爷爷接着使。”大米点起了头。大米的爷爷说:“孙子耶,你知道他们用这把壶泡过什么茶吗?”大米摇起了头。大米的爷爷说:“他们泡过这世间最好最好的茶。”大米点起了头。大米的爷爷说:“孙子耶,你知道你爷爷我现在泡的什么茶吗?”大米摇起了头。大米的爷爷说:“你爷爷我泡的不是茶,泡的是南山上的山枣呀。”大米点起了头之后,又摇起了头。
大米的爷爷从小泥壶里抠出了几粒山枣扔在嘴里,然后将枣核吐在地上,说:“孙子耶,你爷爷我如今泡不起茶了,只能泡山枣了,真瞎了这把壶了。你知道什么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吗?你知道什么是轮回吗?人得相信轮回,不相信轮回你永远活得不自在。”当时大米并不知道爷爷说的后半截话是什么意思,而当他长大后明白事理的时候,便感觉大半辈子活得不自在的爷爷却在最后时刻自在地死去了。
因为爷爷的军统特务身份,在那个年代,大米父亲的命运也没好到哪里,黑五类崽子的帽子被他父亲从小学一直戴到初中,然后又戴到街道火柴盒厂,终于挨到摘帽那一天有自由选择自己职业的权利了,他父亲就义无反顾地选择了煤矿下井挖煤,因为这样能多挣些钱来补贴家用。那年月的井下安全保障不行,运煤的绞车动不动就从井下绞上来一具跟煤块混装在一起的尸体,大米的父亲到最后就是变成一具尸体跟煤块混装在一起从井下绞上来的。
大米的父亲死了之后,大米的爷爷开始出马了,这老军统特务佝偻着身子,穿得破破烂烂地开始满大街拾荒。大米的母亲开始给周围邻居缝补浆洗,大米的姐姐米囤因为思念自己的父亲身体愈加不好,开始吃更多的药。就这样,一个半大小子年龄的大米辞了学,为了支撑这个快要倒掉的家,他开始成了一个地摊的练家子。他从广州贩过来洋人的二手衣服,他从哈尔滨贩过来老毛子的望远镜和大头靴,他从昆明贩过来私加工的白板香烟,他从拉萨贩过来偷猎的野牦牛蹄子,什么利大他贩什么。终于有一天,因为大米的贩功卓著,他的家里慢慢现出了一些生机。他的军统特务爷爷又可以将自己的头发梳得一丝不苟,握着那把小泥壶喝茶了;他的母亲又可以停下手中的活计唱上一段评戏了;他的姐姐米囤又可以静下心来捧着课本读下去了。
一截时光像是在窗户缝中一晃的样子,就将已成为暴发户的大米推到了成家立业的年龄。因为大米是先立的业后成的家,因此他的这个家便成得非常轻松。他非常轻松地娶到了一个远近闻名的漂亮女孩做了他的老婆,紧接着,她的老婆又非常轻松地给他生了个漂亮的女儿。结果呢,当一家三口人看上去其乐融融的时候,她的老婆更是非常轻松地跟着别的男人跑了,给他扔下了这个漂亮的女儿。
大米当时并不因为自己家庭的变故而心灰意冷,恰恰相反,这更激起了他的创业斗志,他告诫自己大丈夫不要儿女情长,如果那样的话就会英雄气短。于是,大米仍然挟着自己腰杆子渐粗的气势,琢磨着要干一番更大的事业。正是在这个节骨眼上,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像天上掉了颗金蛋一样,硬生生地就砸在了他的眼前,看样子都溅了一地的财气。
一天,大米的爷爷又病了,而且这次病得跟以往不同。这个老军统特务看到四十多年后从台湾回来省亲的同学时,人家都是国军的退役少将了,可他却还在大陆被定格成了一个国军的中尉,这不由让他浮想联翩。更让这个老军统特务想不开的是,自己这四十多年就像草虫一样被踩来碾去,无人所知无人所晓,可是人家四十多年后一回到家乡,就被冠之以台胞,陪在人家身前身后的都是这座城市的头面人物,而他这四十多年呢,被整得差点连同胞都没做成。这么一个真真切切恍若一出大戏的现实摆在眼前,横看竖看,怎么都让大米的爷爷想不开,这一想不开,就紧接着让这老军统特务的脑干也想不开了。由于脑干大面积出血,大米的爷爷甚至到临死时都没有清醒过来,还真的无痛无苦自在地走了。
当时大米在医院伺候自己爷爷的时候,对床住着的是一个这座城市的局级领导,这个局级领导的脑供血量不足,总是瞌睡瞌睡再瞌睡,眩晕眩晕再眩晕。大米早早就知道了这个对床病人的身份,他还知道这个局级领导不仅脑供血不足,而且他下边的老二也有毛病,总是尿急尿频尿不尽尿分岔尿等待,龟头都肿得拳头般大小了。大米看着局级领导锃光瓦亮的龟头,心说我得将他提升到伺候我爷爷的标准才行,说不定哪天还用得上他呢。于是,大米的爷爷昏迷在医院的那一周里,他就像伺候爷爷一样伺候这个局级领导。其实大米并不知道局级领导的龟头为什么肿得跟拳头般大小的原因,局级领导也不好意思启口说出这个原因,他能说出那天自己在公园里跟女下属露天野战时,被有毒的细腰大黄蜂蜇到要害部位这个细节吗?不可能、绝对不可能的。
局级领导看样子发自内心地喜欢上了大米,心说这十来天人家伺候完我大头又伺候我小头,谁能做到这一点呀,我亲儿子也不能呀,以后他有什么事儿我得帮帮他。多少天后,还没等局级领导有所表示,大米就主动找上门来。他来到局级领导的办公室,对领导问寒问暖,问完领导大头的暖又问领导小头的暖,把个局级领导问得心里一片敞亮。随后大米话锋一转,说:“项叔,我听说咱们东街的百货公司要承包给个人,你看我能不能接手这个活儿呢?”局级领导揉了会儿裆部说:“你小子的信息怎么这么灵呢,我正在研究合适的人选呢。其实呀大米,你不来找你项叔我,你项叔我也想到了你。你小子放心好了,就凭你对你项叔我在医院期间如此精心伺候,我能不为你着想吗,我就是要把你扶上马,再送上一程。”于是大米就被局级领导的一个手下领着去有关部门盖了一圈戳儿之后,又在一叠纸上签了自己的名字,便由一个摆地摊的练家子,变成了一个商业城的总经理。
可是时间一长,大米总感觉自己这个总经理的头衔是个伸手够不到的虚衔。他的女会计是人家局级领导派过来的,他的女出纳也是人家局级领导派过来的,甚至商业城里那几个部门经理的任免,他都没有决定权,更别说大宗进货、大宗出货的决策权了。他感觉自己这个总经理跟站柜台的售货员并无两样,只是徒有外人看不透的风光而已。于是大米便常常问自己,项叔这是在干什么呢?他是不是看在我没文化的份上在利用我呢?我还是他眼中那个精心伺候他的人吗?我真的感动他了吗?我拿上我的存折和贷款押在这里,我想创业却不能,项叔他这是想干什么呢?最后大米都自言自语地骂出声来了:“项叔你有话明说有屁明放不带这样玩儿人的行不行。”这之后,大米就找到了一个律师,将合同文本递过去给人家看。那律师扫了几眼之后把合同文本推了过来,说:“先生你不认识字吗?”大米说:“认识倒是认识,可我文化浅,有些字面下的意思理解不了。”律师说:“合同上的哪一条对你都不利,你还是个总经理呢,说白了你就是个比较高级些的打工仔而已,告诉你那个商业城不是你的。”大米听到这儿,一股火腾地一下子从脑袋上就冒了出来。
大米开始琢磨起了他项叔来。我明的整不过你我跟你来暗的行不。大米这样一想之后,便马上付诸了行动,他开始偷偷跟踪起他项叔来。一段跟踪时间过后,大米发现他项叔喜欢往一个宾馆里跑,而且总是往这个宾馆的同一个房间里钻。这期间让他有更大更震惊的发现是,他的商业城女会计和女出纳也喜欢往这个宾馆里跑。于是大米就买了一套当时最新版的偷拍设备。大米用了差不多一个星期的时间,才将这套偷拍设备玩儿转了,那天他瘫坐在椅子上,对自己说了一句感慨万千的话:“文化底子薄真是害死个人呀。”随后的某一天,大米找了局级领导出差在外的一个空当,用了一整个晚上,才在那个房间里完成了他的偷拍设备安装任务。
大米如愿以偿地搞到了局级领导的证据,然后像欣赏A片一样,如饥似渴地欣赏起了自己偷拍到的画面来。可是视觉疲劳过后,大米又对偷拍的同步录音感兴趣起来。同步录音里经常听到局级领导问“这屋子里有蜂子吗”这句话,而不同的女人们总是回答他“屋子里哪有蜂子,野外才有蜂子呢”这句话。惟独女会计听到局级领导这句话时,总是嘻嘻笑了几声,然后哄起局级领导来:“噢不怕不怕,以后咱再也不去公园打野战了。那次蜂子蜇了你,肿在哥哥鸡鸡上,疼在妹妹心窝窝里,以后咱再也不去了噢噢噢乖。”直到这段录音被大米听过十遍之后,他才一拍脑袋明白了过来,随后又感慨万千地对自己说了一句:“文化底子薄真是害死个人呀。”
有一天,大米找到了局级领导,说自己不想承包这个商业城了,说想把自己投进去的钱拿出来去干别的事了。大米说:“项叔,我也老大不小了,你知道我是个离婚男人,我还上有老的下有小的,有几张嘴等着我去喂呢,我把属于我的钱拿出来,也好投在别处创业呀。”局级领导说:“这可不行,你才承包几天就想撤出,你现在撤出就是违约知道不,你的钱不仅拿不到而且你还得往里面搭钱知道不,因为你撕毁了合同。”出现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冷场后,大米直直地看着眼前陷在沙发里的局级领导,终于亮出了他的杀手锏来,他将调子调得稳稳的,而且像一根钢丝一样邦硬,然后瞄了局级领导的裆部一眼,说“项叔,你那地方好了吗?蜂子蜇在那地方,若想彻底去毒,可是件很麻烦的事呀。”局级领导正在闭目养神之时,突然听到大米这句话,差点从沙发上出溜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