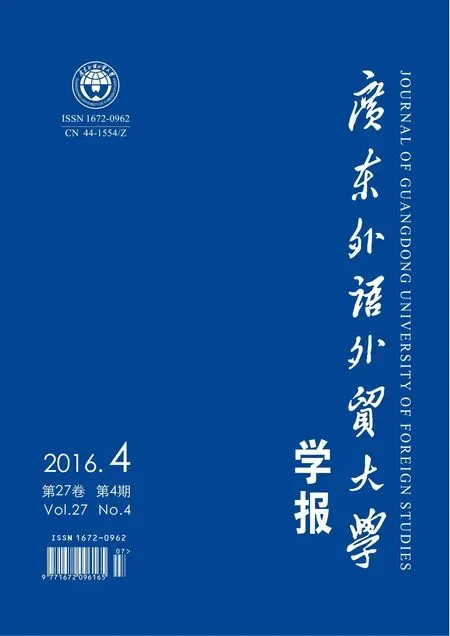文本世界话语世界与第一人称短篇叙事的阐释空间
唐伟胜 龙艳霞
(1.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英语语言文化学院, 广州 510420; 2. 南方医科大学 外国语学院, 广州 510515)
文本世界话语世界与第一人称短篇叙事的阐释空间
唐伟胜1龙艳霞2
(1.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英语语言文化学院, 广州510420; 2. 南方医科大学外国语学院, 广州510515)
在很多第一人称短篇叙事中,读者至少可以建构三个世界:首先读者将零参照点投射到两个层次的文本世界,即作为行动者(enactor)的“我”的世界(enactor-I world)以及作为叙事者(narrator)的“我”的世界(narrator-I world),最后读者将零参照点转移回到“此时此地”的话语世界。这三个世界既可以被表征为统一体,也可以被表征为各自分离,从而形成丰富多彩的第一人称叙事。雷蒙·卡佛的《孩子,这是为什么?》、尤多拉·威尔蒂的《我为什么住邮局》及爱伦·坡的《一桶白葡萄酒》三个第一人称叙事文本都(或明或暗地)鼓励读者将零参照点投射到“叙事者-我”的世界,并识别该世界与“行动者-我”及话语世界之间的各种反讽距离,从而极大提升了这些短篇叙事的阐释空间,而这也从某种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这些作品成为经典短篇的原因之一。
文本世界; 话语世界; 第一人称叙事; 阐释空间; 经典
一、文本世界理论与第一人称叙事的表征
“文本世界”(text worlds)是近年逐渐兴起的认知诗学的一个关键概念,由保罗·沃斯(Paul Werth)在其1999年出版的《文本世界:表征话语中的概念空间》(TextWorlds:RepresentingConceptualSpaceinDiscourse)中率先提出,随后由乔安娜·加文斯(Joanna Gavins)在其2007年的《文本世界理论入门》(TextWorldTheory:AnIntroduction)加以深入讨论和阐发。“文本世界理论”认为,语言理解的过程就是为语言建构心理表征的过程。“文本世界理论”主要关注这些心理表征如何形成,概念如何组合以及我们如何应用它们等问题(Gavins,2007: 2)。该理论既关注文本本身,也关注文本写作与消费的环境,包括处于具体历史文化语境中读者的既有知识和经历,着重考察文本世界如何在语境的参与下得以建构。为此,文本世界理论的首创者Werth区分了三个感知层次:“话语世界”层(discourse world)、“文本世界”层(text worlds)、“次文本世界”层(sub-text worlds)。其中,“话语世界”层涉及的是交际的直接情景,考察交际各方如何使用(在语言、经验、感知、文化等方面的)知识结构,通过“推论”(inferencing)来理解话语输入;“文本世界”层考察作为“话语世界”参与者(discourse participant)的读者表征文本时的心理结构和认知效果;“次文本世界”层则指读者借用“文本世界”的参与者(text enactor)这一参照点对嵌入在“文本世界”层中的其他世界的表征(Werth,1999: 20-29)。
第一人称是古今中外十分常见的一种叙事现象:由“我”来讲述一个关于“我”自己或者别人的故事。面对第一人称叙事(通常也称为人物叙事),叙事学通常区分两个“我”,即叙事之我(narrator-I)和经历之我(character-I),并探讨二者之间的关系。比如,詹姆斯·费伦(James Phelan)认为人物叙述是“一种间接艺术:通过让人物叙述者与其受述者交流,作者与其读者进行交流”(Phelan,2005: 1)。如果使用文本世界理论确立的术语,我们可以说,读者在阅读第一人称叙事时,会建构一个“话语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作者和读者是参与者)和一个“文本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叙述者“我”和受述者是参与者),而叙述者“我”创造的那个世界则会被表征为“次文本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物“我”和其他人物是参与者)。这几个世界之间可能存在多种距离关系,但这些距离关系可能在文本中显性化,也可能隐性化。借用皮特·斯多克威尔(Peter Stockwell)论述的叙事阅读“指示转移”过程理论(Stockwell,2002:47),我们可以将第一人称的认知阅读过程描述为:读者首先将零参照点投射到人物“我”世界,然后转移到叙述者“我”世界,最后移回话语世界,并识别和定位叙事的反讽意义。然而,从认知的角度看,我们阅读第一人称叙事的无标记情况是将零参照点仅仅投射到人物“我”世界(尤其当人物“我”世界和叙述者“我”世界之间的距离是隐性关系),并将其等同于叙述者“我”世界乃至话语世界,从而大大限制了第一人称叙事的阐释空间。本文拟用雷蒙德·卡佛的《孩子,这是为什么?》、尤多拉·威尔蒂的《我为什么住邮局》及爱伦·坡的《一桶白葡萄酒》三个经典短篇叙事为例,论述读者如何突破第一人称叙事的认知阅读规约,从而进入更广阔的文本意义空间。
二、《孩子,这是为什么》中的母亲:“我”为什么害怕?
《孩子,这是为什么?》(以下简称《为什么》)是20世纪70-80年代蜚声美国文坛的“极简主义”代表作家雷蒙德·卡佛创作的一篇书信体短篇小说。故事的基本骨架是一位老太太给一个陌生人写信,讲述他儿子(现在已经被选为州长)青少年时期的所作所为:撒谎、杀人、不尊重父母等。初读《为什么》,读者很容易联想起马克·吐温的《竞选州长》(RunningforGovernor):两篇小说都涉及州长,都试图揭露州长的不良行径。不同的是,讲述《竞选州长》的是一位州长候选人,而《为什么》则是州长自己的母亲;《竞选州长》是在选举中揭露丑闻,而《为什么》则是儿子被选为州长之后揭露丑闻。那么,一位州长的母亲为什么要写信来揭发儿子15岁左右时的行径,尤其是当这位母亲连读信人的身份都无从知晓?老太太回忆完儿子的种种劣迹后,这样结束自己的叙述:
我老了。我是他的母亲。我本应是世界上最自豪的母亲,但我却只感到害怕。
谢谢您的来信,我本来就想给人说说这些事情。很惭愧啊!
我也想问问,您是怎么知道我的姓名和地址的?我一直都在祷告别让人知道。可您还是知道了。您这是为什么?请告诉我为什么。
按照前面论述的第一人称叙事阅读规约,我们很自然地将零参照点投射到人物“我”的世界。这个世界的行动者包括人物“我”、“我”在读高中(后来变成州长)的儿子及其他人物,发生的与儿子相关的事件包括:(1)邻居认为他杀死了自家的猫,但他却轻描淡写地说那猫已到该死的年龄;(2)他挣到的第一笔钱是28美元,但他告诉母亲自己挣了80美元;(3)他的车后备箱里有带血的衬衣,但他说那是他流的鼻血;(4)当母亲问他为什么不说实话,他表现得十分粗鲁无礼,并从此离开家门,再没回来过;(5)后来,他当选了州长,而“我”由于担忧他报复而隐姓埋名。这样,按照“我”的讲述逻辑,作为州长的儿子不讲真话,有暴力倾向,而且可能杀过人。正因为“我”了解他的所有劣迹,“我”十分担心他会采取一些不利于“我”的行动。事实上,在“我”看来,这种威胁已经实际存在了,比如盯“我”的那辆车和没有回音的电话。“我”一定会猜想,这均来自于自己的儿子。这样,选择将零参照点投射到人物“我”的世界的读者不难理解“我”在结尾的叙述:“我本应是世界上最自豪的母亲,但我却只感到害怕”。
然而,如果我们将参照点从人物“我”的世界转移到叙事者“我”的世界,我们就能觉察到这两个看似无缝衔接的世界之间隐约存在的距离。在叙事者“我”的世界中,行动者包含正在写信的“我”以及书信隐含的读者(一个陌生人)。那么,当“我”说“我”隐姓埋名,“一直在祷告别让人知道”自己的姓名和地址,为什么却对一个根本不认识的人和盘托出这么多年来一直隐藏的秘密?把儿子的故事讲完之后,才去追问别人写信的目的,这是否符合常理?此外,“我”讲述的故事发生在儿子15岁左右,而“我”的讲述则发生在儿子当选为州长之后,虽然这之间到底相隔多少年,我们无从知晓,但一定是经过了很长时间。也就是说,这位母亲叙事者现在年事已高,而且多年离群索居,长期生活在(或许是没有来由的)担忧恐惧中,那么,这样一个“我”的讲述是否可靠呢?如果转换角度,我们完全可以对“我”的叙述做出逆转式的解读,并从中构建一个完全不同的真相。比如,在杀猫事件中,儿子轻描淡写的态度可能是为了安慰母亲;将28元说成80元可能是为让母亲高兴;儿子生气并离家出走则可能是因为不堪忍受母亲实施的严厉监视。这样的解读让读者意识到,那位儿子不过是一个正常的、具有叛逆性格的高中青年,而“我”则是一个缺乏理解和判断能力、喜欢探问儿子私事、没有自省能力的母亲。如此看来,“我”向一个陌生人讲述可能伤害自己的儿子的往事,讲完之后才追问对方的身份,这也是“我”缺乏判断能力的一个标志。
这样,在《为什么》中就存在两个相互抵牾的世界。如果选择走进叙事者“我”编织的人物世界,读者看到的是一个什么坏事都干得出的美国州长,并能理解“我”为什么担惊害怕;另一方面,如果选择走进卡佛编织的叙事者“我”的世界,读者则看到一个被儿子抛弃、对过去念念不忘却又无法理解世界的老太婆,也许我们对她生活在误会中无法自拔的生活境遇会寄予些许同情,但对她的担惊害怕,我们可能心生嘲讽。能够获得如此复杂的认知、美学和伦理体验,正是读者将零认知参照点不仅投射到小说中人物“我”世界,还投射到叙事者“我”世界的结果。
三、《我为什么住邮局?》中的姐姐:“我”为什么愤怒?
《我为什么住邮局?》(以下简称《邮局》)是尤多拉·威尔蒂的一篇著名短篇,几乎被所有短篇小说集收录,比如McGraw-Hill的《小说选集》(Yanni,1995)以及《小说100篇:短篇小说选集》(Pickering,1995)等等。故事的情节比较简单:叙事者“我”的妹妹史黛拉被与其私奔的男人怀特克尔抛弃,带着私生子谢利-T回到娘家。史黛拉对家人说,谢利-T是她领养的孩子。“我”当然不相信史黛拉的谎言,并公开质疑她的说辞。然而,史黛拉却成功地说服了家里所有人,包括爷爷、妈妈、舅舅等,并使他们与“我”公开反目。在一次又一次遭遇史黛拉的谎言和家人的责难后,我自尊心(self-pride)受到极大打击,忍无可忍,独自一人搬到我工作的邮局,并发誓再也不想见到史黛拉及家人。
看起来,小说已经完美解决了标题中提出的问题。“我”为什么住邮局?因为史黛拉的谎言那么明显,但家人不仅不理会“我”的解释,还偏听偏信(one-sided),与史黛拉一起来与“我”作对。于是,如果读者选择走进叙事者建构的这个人物“我”世界,我们无疑会与叙事者站在一起,对史黛拉及家人的滑稽可憎的行为表示可笑和愤怒。
然而,如果读者止步于这种“push-in”(推入),而放弃“pop-out”(弹出)的认知过程,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不尝试把认知零参照点从人物“我”世界转移到叙事者“我”世界,我们就可能无法完整理解《邮局》的复杂性。在这个叙事者“我”世界里,除了讲故事的“我”之外,还有一位正在听“我”讲述的受述者。在小说的最后部分,“我”这样讲到:
整整五天了,那是我看我家人的最后一眼,也是他们看我的最后一眼……
……你瞧,我这里什么都备齐了,我喜欢的方式……
如果此刻史黛拉-隆多来到我面前,双膝跪地,想给我解释她与怀特克尔先生的来龙去脉,我就用手指捂住耳朵,一句也不会听。
从这里,我们很容易看到,人物“我”世界与叙事者“我”世界之间已经相隔5天,但“我”余怒未消,仍不肯原谅史黛拉和家人。虽然“我”也深知,“这镇上有些人支持我,也有些人反对我”,但“我”非常自信,“知道谁跟谁。总有人不再来我这里买邮票,不过是为了站在爷爷一边”。那么,如果我们完全接受叙事者“我”的叙述,为什么小镇里还有人反对“我”呢?在叙事者“我”世界与人物“我”世界的这个缝隙里,仔细聆听的读者会突然发现,隐含作者眼中的这个“我”与叙事者眼中的那个“我”其实大不一样。叙事者“我”一再声称自己有“自尊”,容不得家人的“偏听偏信”,但其实,她自己就没有尊重史黛拉及家人的自尊,更没有做到“兼信则明”。史黛拉被人抛弃,带着孩子回家,对一个传统的男方黑人家庭来说,这是一个难以启齿的奇耻大辱,史黛拉和家庭其他成员试图掩盖这个秘密,于是假装相信谢利-T是领养的,同时对受到伤害的史黛拉也给予了更多安慰和信任。然而,“我”相信,怀特克尔先生首先是喜欢“我”,后来才被史黛拉给抢走,为了这个原因,“我”不顾史黛拉和妈妈的请求,多次提及孩子谢利-T和怀特克尔先生,完全无视史黛拉和家人的“自尊”;与此同时,“我”一味相信史黛拉是给“宠坏了”,家人则是被史黛拉所欺骗,因而根本没有理解他们的苦衷,这表明“我”其实是一个被偏信蒙蔽心智的女孩。最为可怕的是,在离家住到邮局5天以后,“我”仍然没有反思自己被家人如此对待的原因,在小说的最后一句还在给自己的受述者(很可能是镇上的某个居民)提及怀特克尔先生,丝毫没有意识到这是在伤害史黛拉和家人。
如果以上分析是正确的话,我们在《邮局》中就能读到两个不同的故事:如果我们将认知参照点投射在人物“我”世界中,我们读到的是一位诚实而可怜的女孩如何被误解和谎言所害,被迫离家出走;如果我们转移认知参照点到叙事者“我”世界中,我们读到的却是一位被偏见蒙蔽的女孩如何在情感上与家人走向决裂而不自知。在第一个故事中,读者虽然可以理解为什么“我”会离家出走,却无法解释为什么家人那么轻易相信史黛拉的话,并那么决绝地对待“我”;在第二个故事中,我们能更好地理解家人的行为逻辑,同时也对离家出走的“我”产生更加复杂的判断:她既是家庭缺乏交流的牺牲品,同时也是她个人偏见与理解力缺乏的牺牲品。不难看出,将认知零参照点从人物“我”世界转移投射到叙事者“我”的世界,极大地释放了《邮局》的阐释潜力。
四、《一桶白葡萄酒》中的蒙特利梭:“我”为什么恐怖?
爱伦·坡的短篇小说《一桶白葡萄酒》是一篇典型的哥特小说,如果坡想在该小说中营造某个“统一效果”,这个效果一定是“恐怖”。因为福图纳多曾经言语轻慢过“我”,叙事者发誓要复仇。福图纳多自诩自己是葡萄酒鉴赏行家,于是“我”谎称自家地窖有一桶白葡萄酒请他去鉴赏,一步步将酒醉的福图纳多引至昏暗恐怖的地窖深处,用铁索将他绑到角落,然后在他周围砌墙,在他一声声绝望的惨叫中将他活埋。

如果我们将认知零参照点从蒙特利梭叙述的人物“我”世界转移到隐含作者建构的蒙特利梭叙事者“我”世界,我们会立刻发现这个世界的一些特征。小说的最后部分,“我”讲到,“在这新砌成的墙上,我把那些残肢断骨重新堆上。半个世纪了,再也没有一个活人去打扰过它们。愿他安息吧!”从这里,我们突然发现,原来“我”讲述的事情发生在50年前,这就意味着,当“我”讲述这个故事时,“我”已经是一个年纪很大的老人了。这样,读者就可以概念化出如下一个有趣的场景:一个垂死老人正在给一个相识的人吹嘘50年前他如何聪明地杀死了一个侮辱过他的人,而且自己还“没有受到任何惩罚”。詹姆斯·费伦正是从这里出发,富有逻辑地论证了叙事者的不可靠性,因为事实上,叙事者“我”是在为自己当年杀人感到内心不安而寻求忏悔,因此他已经受到内心的惩罚。那么,如果我们将零参照点再次转移到小说的话语世界,我们就会追问:坡为什么要安排这样一个老人来做一次不成功的忏悔叙述呢?答案是,这样安排可以增添作品的“恐怖感”。垂死老人忏悔的目的是寻求救赎和心理解脱,以便死后升入天堂(小说最后一句“愿他安息吧”清楚地表明了叙事者的忏悔意图),然而,蒙特利梭的叙述表明,他无法得到救赎,也无法真正实现心理解脱,这就意味着,他死后注定不会得到“安息”。这样一种结局,对生活在天主教文化背景的读者来说,无疑会令他们毛骨悚然,产生比蒙特利梭杀人更入木三分的终极恐怖。
这样,在《一桶白葡萄酒》中,我们就能读出坡营造的双重“恐怖”感:第一种恐怖感来自于叙事者建构的人物“我”世界,另一种恐怖感则来自于隐含作者建构的叙事者“我”世界。笔者认为,这两重恐怖感都是坡特意安排的,因为在他的艺术信条中,“无助于预先确立的设计的词,一个也不用”。如果没有阅读出这第二重恐怖感,我们就相当于把坡的艺术丢失了一半。
五、结 语
认知诗学中的“文本世界理论”区分的话语世界、文本世界和次文本世界有助于解释我们的认知阅读过程。在第一人称叙事中,我们至少可以区分三个世界,即由真实作者建构的话语世界,隐含作者建构的叙事者“我”世界以及叙事者建构的人物“我”世界。从这几个世界的层次性质来看,我们可以把叙事者“我”世界等同于文本世界,而把人物“我”世界等同于次文本世界。正如上文分析的《孩子,这是为什么》、《我为什么住邮局》及《一桶白葡萄酒》显示的那样,在第一人称叙事中,作者往往会艺术地运作这两个世界的时空距离,从而使作品呈现出立体的姿态,如果读者将认知零参照点游弋在作品中不同的世界,就能突破认知规约,大大拓展第一人称叙事的阐释空间。笔者认为,正是由于作者在这些作品中运作了不同世界之间的关系,才使这些作品具有丰富的阐释潜力,从而成为被一代又一代读者阅读的经典作品。
注释:
①笔者曾在教师和学生中做过本篇小说的阅读试验。绝大多数受试者都“自动地”选择进入人物“我”的世界,认为卡佛这篇小说揭露了美国政客的六亲不认和虚伪无情。
詹姆斯·费伦. 2008.修辞阅读的若干原则:以爱伦·坡的《一桶白葡萄酒》为例[C]∥唐伟胜,译.叙事(中国版):第一辑.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
彭欢. 2013. 骗人面具的背后 ——对爱伦·坡的《泄密的心》和《一桶白葡萄酒》中主人公的不可靠叙述研究[D]. 广州: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张继芸. 2015. 对爱伦·坡的《一桶白葡萄酒》中主人公的不可靠叙述研究[C]∥外语教育与翻译发展创新研究:第四卷.成都:四川师范大学电子出版社.
Gavins J. 2007. Text World Theory: An Introduction[M].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Phelan J. 2005. Living to Tell about It: Rhetoric and Ethics of Character Narration[M]. Ithaca: Cornell Univ. Press.
Pickering J H. 1995. Fiction 100: An Anthology of Short Stories[M]. 7th edition. New York: Prentice Hall.
Poe A. 1984. Essays and Reviews[M]. New York: The Library of America.
Stockwell, P. 2002. Cognitive Poetics: An Introduction[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Werth P. 1999. Text Worlds: Representing Conceptual Space in Discourse[M]. New York: Longman.
Yanni R D. 1995. Book of Fiction[M]. ROMPF K(eds.). New York: McGraw-Hill.
[责任编辑:许莲华]
Text Worlds, Discourse World and the Interpretive Space in First-person Short Narratives
TANG Weisheng1LONG Yanxia2
(1.FacultyofEnglishLanguageandCulture,GuangdongUniversityofForeignStudies,Guangzhou510420; 2.SchoolofForeignLanguages,SouthMedicalUniversity,Guangzhou510515,China)
In face of many first-person short narratives, we as readers can construct at least three worlds: our zero reference point is first projected to the enactor-I world and then to the narrator-I world before shifting back to the discourse world. The three worlds could be represented as a unified one without significant distances among them or as separate ones with one standing in ironical opposition to another. The close reading of three canonical short narratives (i.e. “Why, Honey?” by Raymond Carver, “Why I Live at the P.O.” by Eudora Welty and “A Cask of Amontillado” by Allan Poe) suggests that they all encourage the reader to project her zero reference point to the narrator-I world and explore its ironical relationships with the other two worlds, thus lending themselves much wider interpretive spaces, which might just as well be one of the many reasons why they have been received as canonical.
text worlds; discourse world; first-person narrative; interpretive space; canon
2016-03-09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后9/11美国短篇小说的叙事形态与文化内涵研究”(15YJA752013)。
唐伟胜(1969-),男,重庆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英语语言文化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叙事和美国短篇小说。龙艳霞(1978-), 女,重庆人,南方医科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
I313
A
1672-0962(2016)04-001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