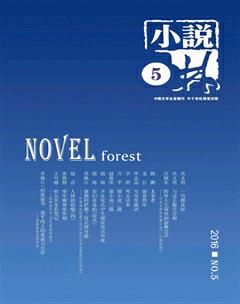不在仪式中生就在仪式中死(短篇小说)
天慧说她弟弟天鹏长得像美国影星汤姆·克鲁斯,我头一次见到他冷眼看上去确实长得有点像。我是和天慧在大三搞对象时认识的她弟弟天鹏。那时天鹏总是隔一段时间换一个女友。他的爱好不光是频繁换着女友,还爱收藏她们送给他的Zip打火机。天鹏收藏了一橱柜前女友们送给他的各式各样的Zip,估摸得有五六十个之多。听天慧说天鹏的打火机都是他跟女友分手前送给他的。可为什么一送完打火机就要分手,我却不得而知。况且,最近一个女孩送给天鹏打火机也没有跟天鹏分手呀。而且天鹏最近总把这个女孩带回家,这时我和天慧才知道,她是一个独来独往的韩国女孩,来中国旅游认识的天鹏。她的名字叫金喜善。
这段时间,天鹏常跟喜善去泡夜店,整宿夜不归宿。当然夜不归宿也不能全怪他俩。这里面有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我们四人只拥有一间十平米不到的小屋,不大的小屋再加上一大堆家什,几乎容不下我们四个同时存在。不得已我们便这样约定:天鹏和喜善每晚待在夜店坚守到清晨再回家,那时我和天慧也该去学校上课了。
有一天,天鹏莫名其妙地对我说:他喜欢这个韩国女孩,女孩对他也没有什么太多的要求(我想,一个打韩国来的女孩对你一个穷光蛋小子能有啥要求?还不是因为你长得像汤姆·克鲁斯吗)。而且天鹏还告诉我,他想跟喜善回韩国,离开他姐姐和这个破地方,一辈子都不想再回来。说完这话,我们又不知不觉地在一起相处了一年,这期间天鹏没有再提及跟金喜善回韩国的事。等到一年之后,便发生了这件令人伤感、触目惊心和令人难以置信的事。
本来约定好我和天慧走后天鹏和喜善才回来。可是他们俩总是在天蒙蒙亮的时候就跑回家。一听到门外有动静,我和天慧就赶忙从被窝里爬起来迅速穿好衣裳。这时,他们俩的小脸早已贴在脏兮兮的玻璃窗上,朝屋里探头探脑地看,看我和天慧赤身裸体穿衣服时的情景。接着就传来喜善金丝雀般的嗓音和咯咯咯的坏笑声。
时间过得飞快。日子就这么零打碎敲地过着。眼看我和天慧就要大学毕业了,而在毕业论文答辩的那天,一早起来,天慧就突然告诉我,她怀孕了,并且不顾我的反对迫不及待地就要去医院做人流。不得已,我陪她到了一家远离学校的医院,待天慧做完人流,我们论文答辩也随之流产了。接下来,我们就盼星星盼月亮盼着补考。补考那天终于盼来时,我和天慧因为熬夜准备论文凌晨才睡却睡到了晌午,又错过了这次补考的机会。眼看我和天慧大学毕不了业,没办法我们只得天天到系主任办公室里磨。我们围着系主任整整磨了一个星期,系主任才勉强同意再给我们一次补考的机会。可是直到领毕业证书的那一天,我们都没有等来补考。可想而知,我们等来的只是两张肄业证书。就这样,我和天慧灰溜溜地离开了这所大学,一无所获地结束了我们大学时代的美好时光。
肄业后的那年秋季,白天天空总是万里无云晴朗无比。等到夜间就大雨滂沱。一到清晨,天又放晴。这段时间,我和天鹏总为一点小事喋喋不休地争吵,直到有一天我们俩真的闹翻了。翻脸后我和天鹏谁都不理谁,像仇人似的别别扭扭地待在一起。有一天,我和天慧正猫在屋里看杂志。天鹏领着喜善突然间闯了进来。门被天鹏一脚踹开了一个大洞,吓得我和天慧猛然从床上立起来,紧接着天鹏就朝我扑过来,我不知所措地便跟他大打了一仗。
从那天开始,天鹏和喜善也不再去泡夜店了。整天跟我和天慧糗在这间巴掌大的小屋里。困了我们就分头倒在沙发或床上睡,醒来无事,就听温拿五虎的磁带,玩任天堂的游戏机。
雨总在夜里开始下。下雨的时候,我们就背靠背坐在床上,八只眼睛一同盯看头顶上空的屋顶。前些日子这个屋顶没能顶住暴风骤雨的袭击,一场大暴雨过后,整个屋顶漏得一塌糊涂。那天午夜暴雨狂泻的时候,我和天慧光着脚冒着瓢泼大雨跑到胡同里去捡砖头,然后把床、沙发和橱柜都垫高了。当我和天慧像老鼠搬家一样忙活着的时候,那个平时看上去温文尔雅的喜善却一反常态,光穿着胸罩和内裤,跟天鹏跑到胡同里去淋雨。那晚的暴雨下得出奇的大,黑咕隆咚的胡同里近乎汪洋,只见喜善光着大腿、袒露着白白的胸脯和小鹿一般的细腰,顶着暴雨在胡同里胡喊乱闹。
就这样我们恍恍惚惚百无聊赖地过着,等到转年开春,我和天鹏就爬上屋顶把上面的碎石乱瓦收拾利索,然后买来油毡,请房管站的师傅帮我们熬了一锅沥青,然后我们便像模像样地蹲在屋顶上铺开了油毡。油毡铺完之后,天慧和喜善觉得不放心,又捡来许多砖头,让我们压在油毡上面。就算这样,我们还是担心它能否扛得住今年的大暴雨。
近日夜里下了几场小雨,每次我们都担心屋顶会像去年一样四面漏雨。但总算还好,几场雨水过后,只有屋顶一个角落阴湿了一大片,总体来说还算说得过去。有一天晚上,好像凌晨四点钟,放在窗台上的电话突然响了起来。可恶的铃声把我们四人的好梦都给打断了。天鹏蒙头在被窝里骂道:“哪个狗娘养的三更半夜打来电话?准没好事!”天慧跳下床,光脚跑到窗台边上抄起电话。电话里传来照顾天慧爸爸的老护工的声音:“是小慧吗,你和你弟弟赶快来一趟,你爸爸,快,快不行了。”
上学的时候天慧跟我说过,她爸爸从她八岁那年就拉扯她和她弟弟单过。后来他们租房搬过四五次家,再后来她爸爸的单位盖了家属楼,分给他一间十来平方米的小单元房才安顿下来。可是这间把山墙的小单元房,朝向和楼层都不好,一到冬天西北风嗖嗖地能穿透墙壁,屋里冷得像冰窖。夏天又晒得要命,燥热得让人苦不堪言。反正一年四季哪个季节住在里面都不舒坦。另外,这间小单元房跟我们现在住的小屋一样,一下雨就漏,外面下大雨,屋里下小雨,外面不下雨,屋里还跟女人来例假似的,哩哩啦啦滴答个没完。就算房管站年年来人修,修了快二十年还没有修好。常年阴湿的屋顶现在已霉迹斑斑。另外天慧爸爸还是一个老烟枪,天天烟不离手,把整间屋子熏得蜡黄。再有这个单元房一直是她爸爸一个人住,所以屋里又脏又乱,被褥长年堆在床上一角,凡是亮在外面的物件,电视机、高压锅、沙发、大衣柜……上面永远盖着一层尘土。还有那个生锈的衣帽架,那一捆捆的废旧报纸和杂志也都堆在屋子的一角。那个一碰就嘎嘎作响的大衣柜,上面的镜子也裂开一个大口子。最惨的一大堆书籍,金庸和梁羽生的武侠小说、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曹太庸的《中国菜谱》《普希金诗选》《怎样养花》……它们也都变黄发霉。窗台上一盆垂死的君子兰和一束永远盛开不败的塑料插花,跟一堆杂物放在一块儿。据我所知,天慧爸爸天生胆子小,每天下班回家,先要把屋里的门统统锁上。连厕所的门在外面都安上了插销(因为厕所有一扇小窗户,小窗下面是一条楼与楼之间的夹过道,为防小偷所以在厕所门的外面也安了插销)。甚至天慧爸爸胆小到每天晚上要我和天慧去帮他关上卧室的窗户才能睡觉(后来有了护工就不用我们关了),因为窗外马路对过是人民医院的停尸房。endprint
天慧说,她弟弟七岁那年得了传染病乙肝,爸爸在单位忙工作晚上总不回家。于是照顾弟弟的任务就交给她(实际上是爸爸怕传上乙肝不敢回家)。一连数月,天鹏总是高烧不断,天慧就陪在弟弟身边给他喂水喂药,洗衣服和做饭。有一次,爸爸买来几块排骨,叫天慧给弟弟炖了吃。等弟弟吃完,爸爸又要天慧把弟弟吃剩下的骨头再啃干净不准浪费。还有日常家务也由天慧来做,尤其到冬天给爸爸洗衣裳,这可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天冷水凉,洗衣服前天慧想烧点开水,可是爸爸不准,说是烧水就要浪费煤,冷水一样洗干净。就这样,衣裳泡在冷水里,天慧搓也搓不动,只得光脚丫站在冷水里踩。冬天冰冷刺骨的水,冻得天慧双脚痉挛般地疼,小腿还经常地抽筋。天慧说,像这样的事情她干得很多,以后慢慢讲给我听。当我问及天慧,爸爸为什么对你不好?不心疼你?天慧就讳莫如深般闭口不答,不再理我。
天慧一撂下电话就喊我们起床,然后我们一窝蜂地跑出了小屋。这时东方的天际线已微微泛白,周围的一切还沉寂在昨晚的睡梦中。此时此刻我们身后好像有一双无形的大手推着我们前行。一阵阵清风划过我的耳际,仿佛在我的脸颊两侧擦出许多火花——这时忽然打我脑海里萌生出一个念头,这个念头好像一下子让我觉得,我所见到的一切都在逐渐地消退,而且从这些消退的事物身上仍让我察觉到,眼前所发生的一切竟是如此的简单和寻常,仿佛所有人和所有事物都会终止在这半明半暗的街道上。同时,我们所面临的一切,似乎只有一种可能会与另外一种可能相遇,而我们却看不到也摸不着它。到头来,所发生的一切又恢复如常,又都在这无声无息和无色彩的状态中恢复平静。我们一路小跑,气喘吁吁地跑向天慧爸爸的住所,跑得我们浑身热气腾腾一脸通红。上楼时,喜善走在我前面,突然她把左手伸到身后,张开五指,楼道里虽然漆黑,但我仍看到她掌心上写着一行小字。我下意识地扫了一眼,紧接着她就合拢五指攥紧拳头。
当我把天慧爸爸的身体翻转过来时,天鹏正在楼道里训斥那个失职的老护工。我听见天鹏扯破嗓子骂老护工不尽职,这忽然让我想起,天慧曾经对我说过,有朝一日爸爸要是死了,她才不会难过……我走到门外,看见天鹏嘴上叼着香烟,手指正激动地打着喜善送给他的Zip。此情此景好像Zip一旦打着,天鹏就要一把火将老护工烧死似的。忽然,宽阔的火苗打Zip里跃出来,而那个可怜的老护工这时才忽然想起:快,赶快叫救护车。
医院就在马路对过,打完120,工夫不大,救护车便驶到楼下。很快,两名年轻的医生快步上楼走进屋,然后蹲在天慧爸爸的身前做心肺复苏的急救。自始至终我都守候在他们的身边,亲眼目睹两名年轻的医生卖力气地为已死之人做起死回生的努力。结果天慧爸爸还是没有抢救过来,初步诊断结果死于心肌梗塞。
接下来我们便手忙脚乱地将天慧爸爸的遗体运下楼,抬上救护车。救护车再次穿过马路,眨眼间就开进人民医院停在停尸房的门前。天慧没有跟我走进医院,她一个人坐在马路的便道上,眼睛痴呆呆地望着地面。
停尸间里空荡荡的什么都没有,我原以为那里应该有一个一面墙的大冰柜。冰柜由许多排列整齐的不锈钢四方门组成。随便打开哪一扇门,都会打里面冒出让人毛骨悚然发白的冷气。现在天慧爸爸的遗体就停在屋子中间一个四轮车上。说老实话,我害怕死人,但绝不像天鹏,连自己爸爸的最后一眼都不敢看。现在这个胆小鬼也不知去向!所以我孤身一人待在停尸间里守着这具遗体。不一会儿,殡葬人员以为我是死者的儿子,便告知我如何给死者净身,接着拿来一身寿衣,指导我给死者穿上。一切安顿停当之后,我便浑浑噩噩地走出停尸房。
后来我走出医院的大门,看见天慧一动不动地坐在马路的便道上,而让我意想不到的是,她正用一种充满怨恨的眼光盯着我看,我不知何故,穿过马路走向她。其实我心里也在埋怨她,她像一个冷血动物,对自己父亲的死没有一丝一毫的伤感,甚至连一滴眼泪都没有掉。忽然,我听到站在不远处的金喜善发出笑声,而天鹏正把她拽到楼与楼之间的夹过道,接着便是一顿痛揍。
三天后,我们把天慧爸爸的后事料理完毕,天慧这才主动又冷漠地对我说:“他不是我的亲生父亲,那时妈妈怀我时稀里糊涂地嫁给了他。生下我两年之后又生下天鹏。再后来妈妈得了绝症去世了,继父就虐待我……”
待一切恢复平静之后,我们又开始担心起小屋漏雨的事。这一段时间老天爷只下了几场小雨和中雨。每次下雨,我们便竖起耳朵静听雨点砸在屋顶上的声音。一天夜里,起风了,后半夜风越刮越大,接着就电闪雷鸣。我和天鹏本能地从床上和沙发上爬起来跑到屋外,看房顶上面的油毡是否牢靠。果不其然,大风已把油毡掀开几道大口子,细看油毡接口的地方虽还服帖在上面,但已被风刮走了样。有些地方的油毡已被大风撕碎,藕断丝连地挂在屋顶上随风飘荡。又过了一会儿,樱桃大小的冰雹便从天而降,叮叮当当地砸在屋顶上。冰雹的重量加上它的速度,很快把我们的小屋砸得千疮百孔,屋顶墙角还给砸出一个拳头大小的洞。窗户也给砸碎了,玻璃碴溅到床上和沙发上。就在这倒霉的节骨眼上,不知为何,天鹏又开始跟我发起火来,气势汹汹地要跟我动手。
这间小屋我们实在待不下去了。雨过天晴后,屋外秋高气爽,屋内却狼藉满地。一大早,天慧和天鹏就搬到他们爸爸的单元房去住。本来我和喜善也要去,却遭到他们姐俩沉默式地反对。
天慧这是怎么了?我不大理解,好端端的她为什么会对我这样?她怎么能拒绝我跟她一起住?当天慧拒绝我的时候,我的心都凉了碎了。另外她离开我时还以嘲弄的口吻说:“你懂得什么叫真爱?”我一时被问愣,半天张嘴结舌没弄清楚她说这话的意思。难道我不爱她?我对她的爱不是真的?还是她不爱我了?我们之前的爱情不算是爱情?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和天慧之间到底出现了什么裂痕或问题?
还有那个韩国女孩跟我现在的处境几乎相同,但她似乎比我更坚强一些,也显得更沉稳和冷静。他们姐弟俩走后,我和喜善整个下午都在收拾屋子,直到傍晚,我们才拖着疲惫的身体分别倒在床和沙发上。现在又静下来了,我脑海里忽然闪现起一件事,便冷不丁地问喜善:“你那天手上写的是什么?”喜善头枕着床帮,仰视屋顶上的洞穴,呆呆地说:“我忘了记不清了。不过,你察觉到没有,他们姐弟俩都挺怪怪的?咱们俩就像他们俩的宠物……要是我没有猜错的话……”喜善犹豫了一下没有继续往下说。这时我觉得口干舌燥,起身斟了两杯水,递给喜善一杯,同时傻傻地对喜善说:“来,为咱俩各自的爱情,干一杯——”随后我碰了一下她手上的杯口。endprint
就是这样,我和喜善整晚都在昏昏沉沉无所事事当中度过的。当天夜晚天空是那么的晴朗,成群结队的星星亮得像萤火一样撩人。璀璨的群星眨动着眼睛,打屋顶上面的洞穴窥视进来,一时竟让我有一种前所未有的舒适和惬意感。今夜星光无比灿烂,我还是头一次,在天慧和天鹏不在的情形下,跟一个女孩独处。临近午夜,半梦半醒之间,我似乎听到喜善在对我小声地说话。冥冥之中让我想起同样在这个魔幻般的小屋里,有多少个夜晚,我和天慧也是在同样情形下窃窃私语。到了后半夜,我还是睡不着,转身冲向喜善。喜善似乎也是整宿没有合眼,她看见我在看她,不由咧开嘴,我也咧开嘴——我们两人的样子,就像两个落魄的乞丐,正准备讨论某件重要的事情之前,忐忑在脸上的那种诡异、叵测,和故弄玄虚的表情,不约而同地为下面要说的话在做着准备似的。
“你是谁?”我忽然问她。喜善笑着说:“那你得先告诉我你是谁?”我也笑了。是啊,我们俩谁都不知道对方的底细,何必非要现在弄清楚呢。
“那你说说你跟楚天鹏是怎样认识的吧。”我说。
“很简单,”女孩说,“我们在北京爬香山时认识的。他一个人爬,我也是一个人,就这样认识了。咯咯咯。”女孩说着开心地笑了起来。笑声里充满某种让人不知所措的伤心与失落的感觉。同时也让我感受到某种独特,或者说非常意外的新奇感。觉得过去那些平淡的夜晚,倏然间化为乌有,或成为不复存在而又确凿存在的事实。
“有些事不知道你知道不知道?不知该不该对你说?”我说。
“好像没有我不知道的事情啊,如果你愿意说,我倒是愿意听。”女孩狡黠地说。
“楚天鹏在你之前有过很多女友,你知道吗?”
“是吗?你怎么知道的?”
“他姐姐说的,柜子里面的Zip全是他前女友们送的。”
“哦,是吗,我不在乎。”
“不是问你在乎不在乎,我是说这个足够证明他对你不专一,说不定他哪天也甩了你。”
“我知道这些Zip的事,我还知道这些女孩都想跟他上床。可是他不愿意。就是这样,所以……”
“所以什么?”
“所以——被甩的是他,而不会是我。”
“什么?到底谁会甩谁?你把我说糊涂了。”
“他不想跟人家女孩上床,人家还不甩了他。”
“我还是有点糊涂。那楚天鹏招惹那些女孩想干什么?而且他不跟人家上床却跟你上床?”
“没有。谁说他跟我上过床!”
“——那我就更糊涂了,那你为什么不甩了他?”
“嗯,可能是因为我太爱他,爱他——爱他你懂吗!”
女孩突然情绪激动起来,继而抽抽噎噎饮泣地哭起来。
“可是,我实在搞不懂,他说过,他还想跟你一块儿回韩国生活?”我安慰女孩说。与此同时,女孩的一番话让我想起天慧也是这样对我的。我和天慧相处两年,她只允许我抚摩和亲吻,从来不准我和她做爱。而上次她怀孕的事,我也搞不懂是不是在她睡熟时,我一时冲动造成的——对啊,也就是在天慧堕胎之后,天鹏就开始跟我过不去,没事就找茬打架,拿我当仇人似的……
这时女孩抽噎着反问我:“你爱她吗?”
“爱。”我斩钉截铁地说。
“她爱你吗?”女孩又问。
“爱。”我又斩钉截铁地说。
脸上还挂着泪花的金喜善却突然地笑了,飞快的笑声把我弄得有点茫然无措。她笑了,不该笑的时候她却笑了,这个令我匪夷所思的韩国女孩,真担心她会把今晚的事告诉天慧。与此同时,我对这个女孩也警觉起来。
“我真的全心全意爱着天慧。”我忍不住又说了一遍。说完,我不错眼珠地看这个变幻无常的女孩。
她没有看我,也没有任何别的举动。过了老半天,她才说:
“等着瞧吧,总有一天会水落石出的。感觉发生的一切像梦一样。”
“为什么这样说,难道你知道了什么?”我问。
“不知道,像你一样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只是猜测,心里总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也可能是太紧张了吧。谁知道呢。”说完,女孩的眼神里隐现出某种奇异的目光。
“什么啊?你预感到了什么?”我晕头转向地问。
“没有,说不上来,只是一种预感而已。不过,我可以告诉你,像你爱天慧一样,我也是真心爱着天鹏,或许他骗我,也可能他从来就没有爱过我。”
女孩说得很干脆,但是说完眼泪又流了下来。随后她挺直腰坐在床上,好像自言自语地说:
“他从来没有跟我做过爱,当初没有,现在也没有。他好像从来都没有对我冲动过,我就像他的瓷娃娃——”
这时的金喜善看上去比我还茫然,而且有好多到嘴边的话又给她抽噎回去。
天亮时,女孩从床上跳上沙发,蜷缩在我膝上。而我心事重重地将手撂在她的肩头,脑子里一会儿空白,一会儿又想到她夜里对我说过的话。
就这样,我和金喜善神不知鬼不觉地在小屋里独处了一宿。天大亮时,她说她想去找天鹏,但工夫不大,她又说:“算了,既然这样,今天你陪我好吗?”我没有说话。之后我把门锁好,我们俩一前一后走出了小屋。
“本来我一直想告诉你,”女孩犹犹豫豫地说,“那天你一个人在停尸间里……”
“嗯,怎么了?发生了什么事?”我说。
“天慧一个人坐在马路便道上,后来天鹏走过去坐在她旁边,”女孩说,“我从他俩身后走过去。当时他俩没有发现我在后面——”
我和女孩走在腊肠般的胡同里,看见居委会的人正拎着白漆桶正往墙上刷字:一个老大的“拆”字又在上面画了一个老大的圆圈。“看样子,这儿要拆迁了。”我兴奋地说。女孩也兴奋地说:“太好了,早该拆了,简直就不是人待的地方。”我问女孩:“你们韩国没这个吧?”“没哪个?”女孩问我。
“现在没人了,”走到胡同口,我说,“刚才你说他俩没看见你在后面。”endprint
“我不是有意的,”女孩眨着闪电般的眼睛,说,“我听见天慧跟天鹏说,‘你爸死了,咱俩可以搬走了,以后再搬得远远的……放心……我没有对他……当时他俩说话的声音很轻,而且断断续续地听不大清楚。”
“后来我从医院出来,听到你在笑,楚天鹏还打了你,这是为什么?”
“不为什么,因为你呗,”女孩说,“天鹏以为我在后面偷听他俩谈话,问我听到了什么?还威胁我不许对你说。我说我什么也没有听见,我以为天鹏在跟我开玩笑,所以我就笑了。没想到他就打了我。”
金喜善说完,让我更糊涂了,我也不想再问下去,我们俩就漫无目的地走在大街上,彼此之间隔着一小段距离,好像两个陌生人各走各的路。我们好像一下子无话可说了,脸上也没有多余的表情,只是若无其事地一个劲儿地往前走,似乎知道彼此要去的地方似的。其实我和喜善除了刚刚离开的那间小屋,实在没有别的地方可去。
我和喜善不知不觉地走到天慧继父生前的住所。我觉得这不是偶然,而是我们两人心里都存在同样一个谜,都想快点把它解开,弄清楚这个谜底到底是什么。虽然昨晚金喜善对我说了许多她臆想或者猜测的话。但我还是想当面问清楚天慧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现在金喜善放慢脚步,慢吞吞地走在我身后,我们一同走进黑咕隆咚的楼道。一进楼道,外面的世界一下子变得出奇的静,几乎停滞下来。而楼道里更是静得能让我听到女孩的呼吸和心跳加速声。楼道真是又脏又黑,喜善在我身后扭动着身子迟钝地迈上每一级台阶。倏然,我感到从四面八方扑来许多离奇古怪的阴影,把我和金喜善团团地包裹在里面。
这座破败不堪的筒子楼四四方方像个超级火柴盒。走进楼里,就像走进黑暗冗长的矿井。天慧继父的单元房在顶楼最里面的那间,我虽然熟悉,但和金喜善还是费了老半天工夫才摸黑找到。
我们俩悄无声息地摸到单元房门口,然后把头凑过去耳朵轻轻贴在房门上。我和金喜善就像两个鬼魂偷听屋里面的动静。过了老半天,屋里没有任何声响。我转身想走,金喜善一把把我拽住,压低声音说:
“等一下,再听听,等一会儿嘛。”
“走吧,屋里没有人,他俩要是回来撞见咱俩多难堪哪。”我说。
“有什么难堪,”金喜善说,“咱俩又没做亏心事。我一定要弄清楚这里面名堂,凭什么把咱俩给甩了?”
我抬手摸了一下门鼻儿,“咦,门没有锁啊。”我说。
“那他俩一定在里面。”金喜善说。说完她攥紧我的手,把耳朵凑在门上——
没想到这次我和金喜善不小心把门顶开了一道缝儿,光线立马打屋里射了出来。我和金喜善下意识地往旁边一闪——
“乖乖,他们真的没有锁门啊。”
“是呀,他们到底在没在屋里,怎么没有锁门呢?”
我猫腰,喜善两只手撑在我肩上,我们俩的眼睛再次挤对到门缝。穿过虚掩的门缝,我看到屋里面的陈设跟以前差不多。我以为他们姐弟会把屋子重新收拾一下,换一换家什,请人修修屋顶,粉刷一下墙壁什么的。可是从现在来看,屋里跟过去一样,几乎没有任何变化,屋顶上面的霉斑好像又扩大了,密密匝匝堆积着许多恶心人的小霉点。墙壁的颜色还是老样子,只不过多了一幅他们爸爸的遗像,挂在蜡黄的墙面上极不协调也不顺眼。
屋里唯一跟以前不一样的是那张床,主要是床上的被褥全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堆堆码得像一座小山丘似的废报纸、旧书和旧杂志,一沓沓乱糟糟地摊开铺在上面。这时,我猛然看到天慧蕾丝花边的胸罩,这个胸罩还是我送给她的生日礼物,现在却耷拉在满是灰尘的电视机上,天慧的裤子则挂在电视机旁的缝纫机上,上面还撂着一本《普希金诗选》。另外生锈的衣帽架上挂着天鹏的裤子和外套。
突然床铺嘎吱吱地响了一声,一只脚从金庸和梁羽生的武侠小说里面钻出来,接着一只手拨开摊在头顶上面的废报纸、旧杂志,紧接着放在床边的《中国菜谱》《青年近卫军》《怎样养花》《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妮娜》《普希金诗选》……稀里哗啦地掉在地上,里面还夹杂着两只臭袜子。
刚才那只手把压在身上的书、杂志、报纸拨掉之后,一个人的大手拍在另一个人的脸上——
“你打疼我啦!往里边挪挪,我快要掉地上了——”
“天哪!是天慧和天鹏哪!——”金喜善几乎叫出声来。我赶紧捂住她的嘴,我俩同时把脑袋和眼睛缩了回来。
“啊!——他俩!怎么睡在一张床上?”我诧异地说。
“嘘,——”金喜善嘘了一下,让我闭嘴。
“该不会他俩——变态?”金喜善愣愣地说。
“怎么会?”我说。
“不会,还睡在一张床上?!”金喜善怒道。
“就是不会!不睡一张床上睡哪儿?”我反驳道。
不过,当我看到即便是同母异父的姐弟俩,睡一张床上委实有点别扭和疑惑。不管怎样他俩也不能不管不顾把我和喜善抛在小屋,自己关起门来睡安稳觉。至今,我都不愿相信喜善当时的猜测。我当时的感觉就像如鲠在喉,惴惴不安地做了一场虚梦。
喜善催促我走,“鬼才相信那不是真的!不能饶了他俩,得让他知道我的厉害!”喜善眼圈红得像兔子一样,气鼓鼓地说。
“没搞清楚前,你先不要瞎猜,也不要轻举妄动,弄不好……”
“弄不好什么呀,天慧对你这样,你还护着她!”
“我没有,我是说怕你惹是生非对你不好。”
“你们中国男人真没骨气!怕这怕那,不管你说什么我必须教训他一下,有什么好怕的!”
“你有骨气,这可是中国,作奸犯科一样逮你!”
“我不怕,不会牵连你——”
我长吁一口气,用舒缓的口吻对喜善说:“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
她没理我,摸黑走下楼,跑到大街上。我们就在川流不息的马路中间跑,汽车喇叭疯狂地朝我们呐喊,我们一切都不去理会装作没有听见,我们两人一前一后只顾向前跑。我的脑海里翻江倒海般回放所目睹的一切。我们一路狂奔,五脏六腑都要被自己的脚步颠碎了。而我的脑子里一片空白,只觉得天慧不该骗我,也不会骗我,我是一心一意爱着她啊。endprint
而在我前面跑着的金喜善,一会儿显得极度冷静和自信,一会儿又怒不可遏地用韩语自说自话。如果真如金喜善所猜测的那样,恐怕我也更难以压抑心中的怒火。
我不知该如何劝慰她和我自己,当时恐怕我们两人都不知道,这到底是对我们未成熟身心的禁锢还是释放?
我和金喜善跑回小屋。一跑进这阴凉阴暗潮湿的小屋,一下子又让我想起,我和天慧夜夜缠绵于此的情景。他妈的,难道我们之间全是瞎扯淡!全是假的!我不敢相信,也不愿相信,但我一气之下,将屋里可摔的不可摔的东西乱摔了一气。摔完之后,我觉得好累好憋屈和委屈,真想闭上眼睛、关闭心扉倒在沙发上一睡不醒。
当我重新起身时,金喜善正盘腿坐在床上。面前摆放着楚天鹏橱柜里的全部打火机。金喜善正逐个给这些打火机注油。她注油时的神态,显得专注和痴迷,漂亮的脸蛋上好像还挂着那么一丝丝的笑容。
“你在干什么?”
“你甭管,一会儿就好。”
“你摆弄它们干什么?”
“咱们两人都是爱情的牺牲品!你说是吧?”金喜善说。
“我不知道,也许是也许不是。”我说。
后来,金喜善不再说话,一心往打火机里灌油。一个钟头后,金喜善忽然叫我:“过来,躺在我身边。”
我犹豫一下,从沙发跨到床上。
“躺下!抱着我!”女孩用命令的口吻说。
我躺下,抱着她,越抱越紧。这时,她腾出一只手把身边的Zip挨个打着,将这些Zip稳稳摆放在我们两人的头顶和身体两侧。Zip腾出的火焰跳跃着燃烧着,它们有时会碰到我们的身体,灼热的温度却给我们带来前所未有的刺激体验。现在我和她一同闭上眼睛,像体验一种仪式一样,让火舌无情地舔舐我们裸露在外的肌肤,很快火烧火燎的刺痛感霎时刺痛我的皮肉和神经。
“要烧着了!”我吼道。
“叫它们烧!再烧一会儿。”女孩镇定地说。
“你疯了!”我说。
“他俩才疯了。”女孩平静地说。
“我受不了了!”我再次吼道。
“再等一会儿,一会儿就好。”女孩说。
我真的给烧着了,我迅速跳下床。燃烧的Zip被我碰倒。我以为女孩会惊声尖叫。让我吃惊的是,她非但没有叫,还突然把所有燃烧的Zip全部拨倒——火立马烧着了床单,火苗一下蹿起很高。这时女孩才从容跳下床。火很快蔓延到枕头和被褥。几十个燃烧的Zip顿时把床铺吞没成火海。火越烧越旺,紧接着我触目惊心地看到,这个几近发狂的女孩将沙发上的衣物,橱柜里的书、杂志,隔板、五斗橱的抽屉,还有她和天慧的化妆品、镜子、梳子、剪刀、毛巾……一切可燃、不可燃之物统统丢进火海。之后,她又歇斯底里地把衣柜推倒在床边,把窗台上的电话机扔进火里,把暖水瓶、玻璃杯、锅碗瓢盆、拖鞋、沙发靠垫,全部扔进了火里……这个名字叫金喜善的韩国女孩,这才心满意足地,以胜利者姿态拽着我跑出屋,跑到院子里。一支烟工夫,小屋便笼罩在浓烟滚滚、红舌蹿舞的另一个世界里。
这会儿,天空变得阴暗起来,大朵大朵的云块,正往我们头顶上空聚集,赶在暴雨来临前,女孩攥住我的手,冲出了密集嘈杂的人群。
作者简介:震海,本名王震海。诗人,也写小说。1970年代生于天津,天津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现在天津市作家协会工作,《天津文学》编辑。鲁迅文学院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学员。第七届全国青创会代表。小说、诗歌散见省市级文学期刊,有作品被选载、转载、入选多种年度选本。曾获《芳草》“第三届(2010-2011年)汉语诗歌双年十佳”、《大家》“大航海”诗歌一等奖金帆奖等多种奖项。出版作品集《蓝镜》《我飞越海洋》《万世沧海》等多部。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