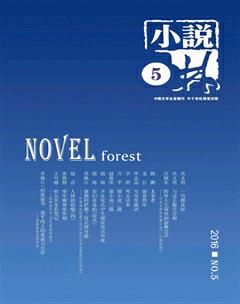死去活来
1
楼就在那里,它在等着把你装进去。黎华在往这幢楼里去。这幢楼造就了他,现在似乎要把他毁掉。
这是新河县城最高的一座楼,一层一层往上去,有一十二层。在它对面,也有一座十二层高的楼。一个叫铁拐子的泰籍华人盖的宾馆。几年前,铁拐子还在这里开一家骗子公司,专骗外地的货。到外面转了一圈,回来就成了泰籍华人。他的宾馆作为县城最大的一个外资项目,很快就站得跟对街的县信用联社一般高。不仅如此,他还在楼顶盖了一个皇冠一样的东西,一下高了一米多。
铁拐子要压倒对方。他忘了,站在对面的是全县最大的金融机构。工农中建四大国有银行,它们在全国最大。到了新河县,最大的还是信用联社。二十六个亿的存款,十六亿多的贷款,点多面广线,全县三十五个乡镇,每个乡镇都有信用社,四百八十三个村,村村都有信用站。没有哪家银行可以同它相比。执掌县联社的是大名鼎鼎的方总,方大林。他正暗暗使劲,准备在换届选举时,竞选副县长。他当然不允许铁拐子坏了他的风水。
一天,那个泰籍华人突然发现,对面楼顶多了一根高大的火炬。玻璃钢做的火把,既不歪向左,也不歪向右,红红火火直往高处走,比他的皇冠足足高出一米多,一下把风头抢了回去。铁拐子赶紧去请风水先生。地方上最有名最灵验的风水先生就这一个。他刚指点过信用联社的火炬,又被请来指点如何破这支火炬。楼不能再加高,也不能依葫芦画瓢,在皇冠上装一根火炬。最后,铁拐子在楼顶装了一门水炮,对着街对面的火炬。信用联社那边心领神会,围着火炬挂了一层玻璃幕墙。有了一层反光的镜子,那边的水炮最终发现,它对准的是它自己。幕墙上面,火把高高举起。除了朝它仰望,谁也奈何不了它。最后,铁拐子主动拆了那门水炮,还请方总吃了一顿饭。他说自己回乡办企业,说不定哪天就需要联社支持。于是两座楼就这样站在那里,好像它们一直这样,从来没动过。
这时候,黎华的那双鳄鱼牌皮鞋正载着他往联社的办公大楼去。他去六楼,603。这是整幢大楼的核心部位。联社的老总、副老总都在这一楼。最初,方总准备把核心安在八楼。谁都知道,八发。可风水先生说,八字倒下来就是一副手铐,还是六好。六顺。六字颠一个个儿,也是九,久发。方总从善如流。
黎华刚从方总那儿来。不是601,是另一座楼,304。那座楼总共六层,没有电梯,房间号也不好,跟联社这边没法比。可它是县政府。在县政府的304,方副县长瞪着眼睛朝他拍桌子:这点事都办不好,养着你们做什么!
2
他用的是“养着”这个词。就像养牛为了耕田,养猪为了宰肉,养狗为了摇尾巴,为了叫你咬什么就咬什么。按书本,当然不是他养着他们。可实际上,他是老板,老板就是养着他们。
那时候他黎华在哪里?城郊一所学校的一个楼梯间里。楼梯在上面由高到低,一直低到只有老鼠蟑螂才能去的地方。那张床,假如不是一头没有靠背,就没法放。他在高的这一头靠背,脚伸向低矮的地方。竖起来的两只脚板,颇有些顶天立地的意思。他喜欢窝在这里写诗。写天上的星星,也写地上的萤火。写萤火画乱一池塘的星星。写他躺在运稻草的拖拉机上,用一车稻草摇晃星空。家里的母大虫来过,又是骂又是嚷,有两次还在他身上留下好些抓痕。他铁了心,一定要在这些水泥板下面写出一片天地来。直到有一天晚上十点多,他的女儿哭到这里来找他要生活费。第二天,他待在屋子里,有很多脚步在他上面,从头踩到脚,从脚踩到头。他感到,在水泥夹缝里,诗歌这条路似乎走到了尽头。
正好碰上信用联社招聘。与黎华谈过,又看过他写的那些诗和散文,方总当即拍板:就是他。他一进去,就是办公室副主任。没多久,主任被调走。他当了一段主持,就顺理成章成了主任。后来又成了联社副老总。眼下的情形,谁都看得明白:方副县长人在那边304,依旧占着这边的601。602的唐总眼看就要到点退线。他黎华虽然还在603,再往前,要去的就不是602。好多人都闹不懂,方总究竟为什么如此宠着黎华。
一开始,黎华的想法很简单:方总把他招进来,就是叫他写稿。诗是写不下去了。就先把它放下,一个劲地写材料,写报道。材料往县里市里甚至省里报,报道往报纸上去,往电视上去。方总在这方面舍得投入,他也舍得写,舍得跑。方总和他的联社很快红起来。士为知己者死,说得有些严重。知恩图报而已。后来才知道,他的想法有些简单。
成了办公室主任之后,第一次跟方总出去。不知道要跟什么人打牌,方总手一挥,叫他回去拿十万块钱。坐到车上之后,他还在发愣,不知道这十万块上哪儿去拿。他离了婚又结婚,五十万贷款还没还,他拿不出。他拿不准是不是上方总家里去拿。司机笑了:你上财务室去呀!找到财务室,财务室二话没说,就给了他十万。他轻轻吐了一口气。跟方总出去得多,他经常往财务室去。他明白了,财务室的会计、出纳和主管,全是方总信得过的人。
年终决算,财务室问他:拿走的那八十五万怎么处理?
八十五万,全是他经手。他们记在那里,最后还是要处理的!他有些坐不住。他上601转悠,瞅着方总高兴,就问那八十五万怎么办。方总仰在大转椅上,那张国字脸表情有些诡异。粗黑的眉头皱了皱,最后又往上一扬,笑了:你问我怎么办!你说怎么办?等你成了联社副老总,总该知道怎么办吧?办公室副主任的副字刚刚拿掉,第一次听方总这么说,他有些合不拢嘴。那时他还不知道,方总把他的提问看成了提醒。方总是痛快人,就把话挑明了。看到他愣头愣脑合不拢嘴,方总笑起来。
那八十五万,财务室跟他商量,就挂在那里。挂在那里它就一直在那里。是的,他没有打条子,没有签名。可那上面一笔一笔记着,他是经手人。这还不算,上面的数字还一笔一笔在增加。一百万很快就越过去了,接下来是二百万,三百万也在一步步逼近。
这次在304,方大林拍着桌子问他要二百万。有人写信告这位新上来的副县长,说他买票贿选。他得摆平。
从304出来,他在外面胡乱转悠了半天,才回到联社。他上到六楼。他走到603门口。603过去是602,跳过602就是601。他怎么办呢?endprint
3
603已经够大了,差不多有八九个楼梯间那么大。他现在的办公桌,比那时的床要大。桌子后面的大转椅,转过来转过去,就是两个楼梯间。还有一大半,摆着沙发和茶几,相当于客厅。601比这还要大。
他把转椅转过去一百八十度,面前是一排大书柜。住在里面的,一半是新贵。它们无一例外地穿着漂亮光鲜,许多还裹在一层透明的塑料里。大概它们天生就不是给人翻阅的。它们原封不动立在那里,充当礼仪先生、礼仪小姐。有一半是跟他从那边楼梯间过来的,有些像进城来的乡下亲戚。以前多半塞在床底下,现在住得好了,依旧懒懒散散一副邋遢样子。屈原在里面投了江,雪莱也溺水而亡。海子自杀,食指发了疯,说他为了变成一条疯狗,宁愿放弃神圣的人权。他大多背对着它们,面朝沙发和茶几。世界在那里走向他,说的都是:钱!钱!钱!
这一次,他朝那些已死和注定要死去的诗人扫了一眼,眼光落到墙角的一只保险柜上。他没有办法。现在,他就是想回到楼梯间去,也不容易回去了。那本有着黑色封皮的《圣经》早就说过,那水势比山高过十五肘,山岭都淹没了。十二层楼高的火炬,顶多是一个浪头。难怪那些新书要穿上塑料防水衣。
保险柜底层有一只小抽屉,里面一张卡片。台胞居住证,也就是这个人的身份证。他拿在手上,看了又看。有关这个人的一切,就在这张卡片上。身体被齐胸剪断。胸以下大半截,统统不要。留下上面这一点,代表他来到卡片上,眉眼,眼睛与眼睛之间的距离,鼻子的摆放,嘴与下巴,这些足以让这个世界将他认读。有一些方块字标明是男是女,上厕所该去哪一边,住在什么地方。还有一些阿拉伯数字,是说这张脸哪一年哪一月哪一天来到世界上。
这个人现在是他舅爷。听舅爷说,这上面的阿拉伯数字是错的。他本是1931年出生,办证的时候,填那张台胞登记表,填的就是1931。证件发下来,一看才知道,31变成37。1很容易变成7,只要上面多一点墨水,或者看的时候眼睛花一下。那时候他还不是他舅爷。一个人把一包中药带在身上,一带就是四十年,他无疑是个认真的人。那时候的人,似乎什么都较真,好像是1还是7很要紧似的。他找到派出所。仿佛不把1字改回来,弟弟妹妹就会变成哥哥姐姐。他妈要在他五岁的时候,才会怀上他。仿佛要等日本人朝这边打了炮,他才会生下来。好像他回大陆以前的那些日子。全都成了谎言。他要让7回到1。可派出所说,已经上了网不好改,改不了。以后填出生年月,就按这上面填。谁都想年轻,一下年轻六岁,不是很好吗?后来办房产证什么的,他填上1931,人家告诉他:老人家,您填错了,与身份证不符。还算礼貌。他不好说什么。他只能改过来。要不,事情就没法往下走。好在1字改7字,好改。
他叫洪自达出生年月就这样了。死的时间,这上面没有。这几个阿拉伯数字,得看他这个外甥孙女婿的?
4
他想起刚来联社的时候。七楼,靠影剧院那边,很小一间屋子。依旧是写。他只是把一些方块字,也包括阿拉伯数字写到纸上。与诗相距十万八千里,可也不用去管纸以外的事情。总有写不完的东西,晚上多半在加班。他一加班,打字员就得跟着。静悄悄的大楼,给人的感觉,整个世界就是两个人:一个是男人,一个是女人。男的已婚,脚上多多少少还拖着一双鞋。女的是自由的。男的多半把头埋在纸上,有时也会抬起头,说他现在不能写诗了,只能写这些。女的朝他笑笑:等你写到方总那样,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女的年轻漂亮,还善解人意。假如为她写诗,可以啊哦呀一大片。可生活不是写诗。生活只是把一大堆方块字配上数目字,填到方格稿纸上。再由她打到电脑上。电脑通往该去的地方。
生活就不能美好一些吗?
那天,他坐在椅子上校稿。她在旁边站着。他把打错的地方指给她看,她弯下身。一样东西在后颈和耳廓扫了扫,最后来到他脸上。有一阵,他没有动。他怕那种痒痒的感觉从他脸上跑掉。她的头发总是绑成马尾。他不止一次看到,那条马尾随着手在键盘上的动作轻轻晃荡。灯光落到上面就像水一样在流。有一次他看到一只蛾子绕着电灯飞了几圈,居然停在上面。那时候他真希望自己是那只蛾子。绑在脑后的头发,怎么突然披散下来了?
第二次,事情来到手肘那儿。这一次,他是坐在她刚坐过的椅子上。她留在座椅上的热气,就在下面蒸腾。他右边的手肘,顶到一件软乎乎的东西。他当然知道那是什么。他装作不知道,停在那里。接下来,事情接着往下发展。在写过很多材料之后,他写了一回诗。用的是身体某处地方。事情之后,他在窗子前面站了好一阵。窗子外面,影剧院里上演的故事无非是这些: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的起因,经过和结果。他知道,有一个故事已经从他身上开始。因为这个故事,他将更加依赖这幢楼。
家里那条母大虫,每天看着他吃过晚饭踏一双拖鞋出门。拖鞋似乎在告诉她:他不是去卡拉OK,不是去跳舞,是去办公室加班。以前这个男人又穷又酸,丢到街上都没有人捡,她只操心钱。现在她开始操心人。
第一次到办公楼,刚好方总过来审他的讲话稿。黑暗中的母大虫把他吓了一跳。还没有人在他的办公楼吓他一跳。他很生气:这是办公楼,你一个家属跑到这里来做什么!这是一个比她哥哥的教育组长要大许多的人,她懂得怕。
她好久没来办公室。再来是嗷嗷叫着冲进来的。他站起身,等着她一头撞过来。他不再是那个躲在楼梯间写诗的人。他立足的地方是一幢十二层的楼。他是这里的主任。掌握这幢楼的方总需要他,信任他。她没有冲过来。她转向旁边那张门。打字室里,两个女人的声音同时响起:一个发出猛兽扑食的长嗥,一个叫声里带着哭腔。他奔进打字室。打字员洪小乐的马尾辫正在另一个手上。洪小乐用手护住发根,只是叫。他担心洪小乐的身子。那里面多了一件他的东西。他朝母老虎的屁股踢了一脚。被踢的女人随即在地上打起滚来,摊开一地的哭闹。另一个缩在椅子上,只是嘤嘤地哭。他一时没了主意。办公室的几个年轻人,除了搓搓手就只会干瞪眼。最后还是方总过来收场。
方总说:黎华,把那女人离掉。方总说这话的时候,像在说信用社一笔贷款,一次人事调整。endprint
他记得,那女人要五十万,方总就给他批了五十万贷款。想起哭着来找他的女儿,他心里有些酸楚。事情闹到这一步,他能做的也就是这五十万。问题是,他一年的收入也就五万多一点。这边不算吃饭穿衣,那边不算利息,也得十年。方总不是这么看的:你除了把一十二个月加到一起,拿五十万去除,还能做什么?人是活的,活人还能让尿胀死!
他还记得,他找到信贷部经理黄大丰时,黄大丰是这么说的:公安局有枪有铐子可以捉人,法院可以判刑也可以减刑,劳动局可以招工。我们只有这个,不贷款还能做什么?他把表填上递过去,黄大丰一笑:你填自己名字?他不解:我自己贷款,不填我的名字,填谁的名字?大丰说行,填你也行。
5
黎华在等候市里的作协主席。他派了那辆巡洋舰越野车去接主席他们。这车以前归方总用。司机打电话说快到了,他下了楼来等。他的背后是联社办公大楼,在好些人看来,在姓过方之后,这幢楼很快就会姓黎。摆在他面前的,是一个喷水池,一般是在天黑以后,配上灯光,把水喷成彩色。从风水的角度,有这么一个水池,得水聚气,就有了生气。就算对面楼上的水炮不拆掉,那又怎样?水只能顺着玻璃幕墙流下来,归入水池之中。就连那座楼,也倒栽在水中。方大林信这个,他坐到304去了。黎华不知道该不该信,抱着信信无妨的态度。这时候还没喷水,他伸头朝水池看了看,他看到一只反过来往上看的头。一只老鼠在游水。还有一只。拖在身后的波痕就像随风飘动的裙裾。它们应该是昨天晚上进到水池里的。大概是路人随手抛下的面皮屑吸引了它们,要不就是喷泉时逐光入水的飞虫。水池里的水不够满,它们没法越过高高的池壁爬上岸。水不够浅,它们没有办法踩到池底站在那里。踮起脚竖起身子都不行。它们只能不停地游,绕着池子游。从入水的时候起就一直游,从昨天晚上游到今天早上,又从早上游到傍晚,还将这样游下去。它们显然又饿又乏,游不动了。一些面包屑已经融水散成小点,就在身边浮动。它们没法吃,它们只能不停地往前划。划水的脚眼看就慢下来。可是不能慢,一慢水就从口鼻里灌进来。这样绕着池子游,永远也游不完,永远没有尽头。池子里浮着一根塑料棒。一只老鼠实在游不动了,试图爬上塑料棒休息一会儿。哪怕喘上一口气。可塑料棒一转,它翻到下面,喝了几口水。池子里的水太多,怎么也喝不完。它只能赶紧往前游。最后的结果只有一个,游与不游都一样。迟一点早一点有什么区别?
两只老鼠的绝境打动了他。他甚至想找一样东西,把它们捞上来。可是作协主席坐的车子到了。主席说,没想到金融系统还藏着这么优秀的诗人。他把作协那本刊物的主编带来了,准备给黎华发一个专辑,重点推出。当然,要刊出的那些诗都是在楼梯间的时候写的。在这里,他没写过诗。他写的是与这幢楼有关的一些东西,现在,连那些也不写了。只写“经研究”“同意”之类的字眼。
第二天,在对面宾馆吃过早餐,他把主席他们送走。横过马路之后,他朝水池看了看:两只老鼠装了一肚子的水,浮在那里不动了。刚好两只!他心里一动,到办公室,他拨通信贷部经理的电话,告诉他:对面那个泰籍华人的贷款得缓一缓。央行开会了,宏观调控,农村信用社只能姓农。黄大丰说:这是县里重点要保的项目。先期放两百万,后头再追加三百万,方总签了字的。
他很干脆:方副县长那里我去说,先把它压下。
6
那时候,他不知道这个叫做洪自达的男人和他本人还有什么关联。娶了洪小乐,这个人才成为他的舅爷。后来才知道,这个人跨越台湾海峡,回到大陆来,和他关系大着呢。
跟洪小乐结婚的时候,才知道她跟舅爷一起过。舅爷一个人,在县城有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
母亲卧病在床,洪自达出门给母亲抓药。回来的路上被过路的军队抓壮丁,去了台湾。那是一九四八年,回来是在四十年以后。母亲没能等到抓药去的儿子,至死还在念叨。带着四十年以前那包中药,年近花甲的儿子当下哭倒在母亲坟前。中药散了一地。
和许多去台湾的老兵一样,洪自达没能在那边娶到女人。他比许多人幸运的是,总算把一把老骨头送回老家。靠着独身一人积下的那点钱,他在离老家不远的县城买下一套房子。他在这里住下来。妹妹怕他一个人寂寞,就让自己的小孙女改姓洪,跟了舅爷做孙女。洪小乐从乡下进了县城,先念书,后来学打字,最后成了信用联社的打字员。
他是在快到八十岁的时候走的。四十几年前抓的药已经送到母亲身边,跟着他的外甥孙女也有了着落,他安然而逝,在那张卡片上,他只有七十四岁。可卡片管不到阎王爷那里。
这个人丢下的卡片到了黎华手上。一开始,他只是想办一笔安葬费。后来,他改变了主意。他觉得,这个叫做洪自达的人,这个归来的台胞不应该就这样死去。为了他的外甥孙女、孙女婿,他得活过来。他活过来,还可以做一些事情。何况,那张卡片还欠他六岁。前头欠的,后头得给他补上。补多少是多少。当然,在他复活过来以后,他的外甥孙女不应该再跟他姓洪。她应该回过去姓刘。
7
他从火葬场开始。洪舅爷并不想火化,他想象他父母一样,把带回来的骨头葬在父母身边。可是县城有规定,他的外甥孙女找了一个有公职的,外甥孙女跟着也有了公职。
隔了不到七个月时间,有七大本,每一页都是一个被火化掉的人。黎华找到火葬场的主任,主任又找到那个值班的。值班的找到洪自达所在的那本名册,翻到那一页。一个人进到这里,被烧成灰之后,剩下来就这一页纸。骨灰与骨灰,已经看不出有什么不同。所有的不同,都在纸上:有姓名、性别、出生年月和死亡时间,有编号,还附了一张死亡证明。还有火化的时间和火化师的签名。要让洪自达从这里退回去,得把装订好的这一大本拆开,把那一页取下来。因为有了编号,这一页不能空,得另外补上一张。因此,得有另外一个人在那之前死去(以死亡证为准),在那个时间点上火化。最好的办法是补上一具无名尸,没有任何后顾之优。火化无名尸,得由公安出具证明。此外,火葬场还得保留骨灰。主任说,证明他可以去弄。只是得去找人。黎华懂他的意思:我们是朋友,这些都好说。只是骨灰从哪里来?主任一笑:火葬场别的没有,还怕没有骨灰。endprint
离开火葬场的时候,他想:难怪人死了要火化。人身上有病毒有细菌有癌细胞,烧成灰就干净了。
医院院长是同乡,一见面就告诉他:死亡证明的存根已经拿掉了。病历换了,转院上头得有亲属签字。他说那好让小乐来签。签她奶奶的名。
最后,他来到余所长那里。余所长说:“其实,有好多都是人死了,身份证还在用。”他说:“你这鸟人,做些冇屁股的事。这后来还有县领导呢!”余所长笑得很开心:“有县领导,还有你这个在联社当家的,这么说,我女儿进信用社有戏啦?”“你先把这事办好!”“行,我马上作差错申请改正。年终考评要扣分呢!”他叹了一口气。余所长跟着叹了一下,带些讨好的意思。
洪自达一路活转来之后,办了一家公司,叫龙翔公司。开业庆典由一家礼仪公司承办。他们回避了开业这个词,叫做龙翔公司落户新河县庆典。给人的印象,仿佛公司早已存在,而且规模不小。庆典活动在县政府招待所的小礼堂举行,一改本地庆典活动的铺张喧腾,不到一个小时。先是公司代表冯先生,一个戴墨镜的年轻人,操着台北腔发表讲话,称他们公司落户新河县,是要通过公司加农户的模式,实现产供销一条龙,带动产业转型升级。接着,副县长方大林致词,除了称赞台胞热爱家乡,建设家乡,他还希望有关各方支持这种符合产业政策,能够带动经济发展的龙头企业。最后,信用联社坐在602的老唐代表联社,也代表金融系统表态,必要时可以提供贷款支持。之后,信用联社两次向龙翔公司贷款一千万。后来,因为公司台湾老板意外死亡,这笔贷款成为呆滞贷款。
8
从那张卡片上活过来,洪自达最终只活到七十六岁。据说他死于一瓶药酒。那是一只能装五六斤酒的玻璃瓶。酒里面泡着中药,还有一条蛇。说是去风湿。人把蛇身泡在酒里,蛇头在瓶盖下面的空处等着。人打开瓶盖,蛇头伸出来,在人手上咬了一口。洪自达就是这么死的。
黎华拿到601的钥匙。601他不知来过多少次,从没有像现在这样打量它。它比六楼其他房间都要大。大就大在那张老板桌那把大转椅。坐在上面,往左转一下,往右转一下,就觉得自己庞大了许多。把手肘放桌上一摆,发现来到桌面上的世界也很大。还有就是后面的洗手间。一个人在这样一幢楼房里,还有一处专门给你拉撒的地方。能有一个自自在在屙尿的地方,也算是人生一幸。吃饱了,喝足了,有几个人能痛痛快快屙上一回呢?
他还记得那次在304,人家朝他拍桌子,他红着脸还在赔着笑。人家可以拍桌子,因为他是304。可是你完全可以不笑。
他把自己对着304用过的那件东西。陶制的便器,一张打开的嘴。每一只张着的嘴都一样,喂什么都得吞下。一阵水响,他把603喝下的水丢进601。摁过之后,一阵可恶的吞咽声。
他能给的,就这些了。他关上门,走了。
单位找他找不到,找到家里。方大林好像也在找他。刘小乐一直在找他。那个手机号已经不再是他。它对谁都嘟嘟响。
有许多传闻。有的说他已经被谋杀。纪委在调查,谋杀是为了保全自己。也有的说是自杀。有人对自杀一说嗤之以鼻。说人家早已插翅高飞,住洋楼泡洋妞去了。也有的人说他只是避避风头。时过境迁,等他回来,说不定就成了泰籍华人,甚至美籍华人。还有人说他在昆仑山深处的洞穴里面壁。还说他走以前在作协的刊物上发过一首诗,说他是一只陶制的器皿,要想改变,就只有把自己打碎。有人从刊物上找到那首诗,署名是黑陶。
黑陶是他吗?他不走不行吗?他去了哪里?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
作者简介:学群,湖南岳阳人。1962年出生于洞庭湖边一个农民家庭。当过农民,教过书,现栖身于一家金融机构。在多家刊物发表过小说、散文和诗歌。主要著作有《两栖人生》《生命的海拔》等。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