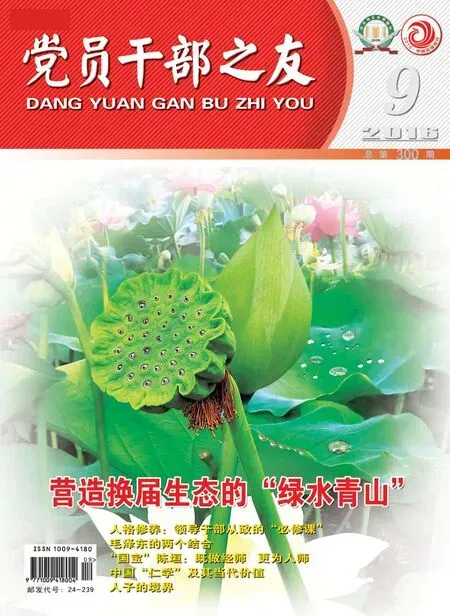『国宝』陈垣:既做经师 更为人师
□ 王震亚
『国宝』陈垣:既做经师更为人师
□ 王震亚

古人云:“经师易遇,人师难遭。”在20世纪的中国教育界,却有一位堪称经师与人师合一的史学家陈垣。他不仅精通经史子集、诗书画艺、历史学、版本目录学,而且在他从教70多年的岁月里,培养了众多才华出众的弟子,可谓桃李满门。毛泽东誉其为中国的“国宝”。
不为乾嘉作殿军
1880年出生于广东新会的陈垣既不同于陈寅恪,系名门之后,有家学渊源,亦不同于胡适等人,有游学欧美的经历,他完全是靠持之以恒的苦读,得以自学成才。
自小,他“不喜八股,而好泛览”;两次参加科考,都以落第告终;编辑过《时事画报》《震旦日报》,撰写了大量反清的政论文章;一度学医,并与人合办光华医学专门学校;民国成立后当选为众议院议员,担任了5个月的教育部次长,然而“眼见国事日非,军阀混战连年”,遂失望于政治的污浊而逃离政界,转以治学,以从教为其一生的志业。
其父陈维启虽经商却重教育,在陈垣求学的最初阶段给予了足够的财力支持。因此,自16岁起,陈垣就能自行购买《四库全书总目》《十三经注疏》等书籍加以研读。当然,史学典籍与大量资料不可能都自行购买,所以他还是利用一切机会去国家图书馆、档案馆查阅。从1915 年开始,他每天早起从北京西南角的住所绕过紫禁城,赶往国立京师图书馆,至下午闭馆才离去,持续达10年之久,成为国内遍阅、研究《四库全书》的第一人。其间,他还于1922 年春夏之际,以一日百卷的速度,历时三个月,尽览馆藏的八千余卷敦煌文书。有了这样自觉、自主的刻苦研读,成功也就水到渠成了。
1917年,陈垣在通阅《元史》,遍查相关的笔记、典章、方志、碑帖、书画谱后,写成了他的史学成名作《元也里可温考》。1923 年,他又推出了专著《元西域人华化考》,通过元代西域人来华后“舍弓马而事诗书”,学习并接受儒家文化,以至逐步“华化”的过程,来展示文明古国的民族融合与文化魅力。彼时的中国,外有东西方列强的歧视,内有全盘西化思潮的涌动,该书的出版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被北大校长蔡元培视为“石破天惊”之作。
陈垣的史学地位是十分明显的。他既继承了清代乾嘉朴学讲究目录、版本、校勘、辑佚、避讳、辨伪等考据的治学路数,又拓宽了文献史料的网罗范围,重视并利用方志、碑版、语录及各种新发现、新开放的材料,对以宗教史、蒙元史、中外关系史为主要方向的中古以来民族文化之历史展开研究。因此,亦为史学家的邵循正在悼念陈垣的挽联中评价其“不为乾嘉作殿军”。
芬芳桃李人间盛
从18岁起,陈垣就开始了他的执教生涯,陆续教过私塾、小学、中学、大学。其间,主要从事高等教育,先后担任辅仁大学副校长、校长,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长达46年之久。
20世纪的前半叶,我国曾有教会大学20余所,如燕京大学、之江大学、圣约翰大学、东吴大学、金陵大学、震旦大学等,而辅仁大学是其中的佼佼者。毫无疑问,教会出资办大学,意在吸引青年,进而“把他们置于基督教和基督教文明影响之下”。但出任辅仁大学校长的陈垣是位民族意识极强的史学宗师。在他主持下的辅仁,具有了“中国化”特色,深深打上了陈垣的印记:提倡信仰自由,宗教不作为必修课程。
一方面,陈垣广揽名师大家,尤其是国学方面的一流学者;另一方面,加强中外学者的交流与合作。由此,辅仁的国学,特别是史学方面的研究成果,在国内名列前茅,在国际汉学界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此外,学校重视一专多能、全面发展的通才教育。规定各院系一、二年级的国文、英文、体育均为公共必修课,不及格就不准升级。而且,陈垣还亲自为大一学生讲授国文课,并郑重告诫西语专业的学生:“四年读下来,勤奋者,略得真谛;怠惰者,则极易变得横竖不通(意指横写的外语和竖写的汉语)。”因此,辅仁的各科毕业生,不仅本专业知识学得扎实,而且英语极好,国文亦佳。
如果说,抗战之前的辅仁大学已在陈垣校长的主持下办成了名校,办出了特色,那么抗战开始后的辅仁则借助德国圣言会的背景,在沦陷区的北平竖起了一面不倒的旗帜,为中国现代教育史谱写了一曲民族的正气歌。1938年5月,日伪政府强迫北京全市悬挂日本国旗,并强令群众上街游行,庆祝他们的侵华胜利。辅仁大学及其附属中学坚决拒绝。当时,被日伪接管的北平其他高校都被迫实行奴化教育,唯有辅仁大学坚持了“三不”原则:不挂日本国旗,不用日文课本,不以日语为必修课。他坚信:“一个民族的消亡,从民族文化开始。没听说,民族文化不消亡,民族可以消亡的。”并以此鼓励青年教师:“我们要做的是,在这个关键时刻保住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把这个继承下去。”
建校之初,辅仁仅有国文、史学、英文、哲学(当年未招生)四个系,在校生140余人;到1949年前后,已发展到四个学院(文学、理学、教育、农学)、 十五个系、三个专修科(美术、贸易、保险)、六个研究所(文史学研究所、人类学研究所、经济学研究所、物理学研究所、化学研究所、生物学研究所),在校生3000余人。1951年11月,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后,毛泽东在怀仁堂举行国宴时,与陈垣同席。在向别人介绍陈垣时,毛泽东说:“这是陈垣,读书很多,是我们国家的国宝。”
1962年春,北师大60周年校庆时,陈垣曾写过一首《今日》诗,其中的两句“芬芳桃李人间盛,慰我平生种树心”,真切地抒写了他献身教育的人生感怀。的确,他是可以感到欣慰的。因为辅仁的学生,的确是桃李芬芳,遍布政经文理各个领域。特别是史学界,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全国各著名大学的历史系教研室主任,几乎都曾就学于他,比如燕京大学的齐思和、北京大学的邓广铭、北京师范大学的白寿彝、南开大学的郑天挺、南京大学的韩儒林等。
言传身教为人师
“学为人师,行为世范”是陈垣的私淑弟子启功为北京师范大学拟订并亲笔题写的校训。从某种意义上说,这8个字,也正是陈垣校长的人格写照。
论做事,他以认真、负责、严谨著称。
身为“清室善后委员会”的实际主持人,他在清朝遗老遗少与北洋军阀的各派各系争相接收的角力中,勇于负责,巧于应对,提出:“接收一定要做到三点,故宫所有藏物:一、不能还给溥仪;二、不得变卖;三、不能毁灭。”为此,他无惧宪兵的逮捕、软禁,也要保护好民族的文化遗产不受损失。
身为辅仁大学校长,各种事务繁忙,但他仍坚持为本科学生授课,而且兢兢业业,一丝不苟。比如,他开设“史源学实习”课程,凡是布置学生做练习、写考释,他自己会先写一篇,于事后印发或张贴出来,以作示范。他还乐于将自己的治学经验与学生分享,告诉他们写笔记是治学的一种好方式,读书有得,就记下来,集腋成裘,就是一篇文章。
身为史学大师,声名早已远播,但他治学始终刻苦、严谨,力求专精。凡有论文写成,陈垣总要多置时日,从不急于发表,为的是听取直谅多闻的同道的意见,加以修正;或是能发现新的材料有所补充。他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影响学生:“治史学在史料的搜集和运用上来不得半点马虎,一定要使用第一手材料。搜集材料时一定要‘竭泽而渔’。”
论做人,其品格、风骨都令人景仰。
他无私。陈垣生活一向俭朴,不抽烟,不喝酒,甚至不喝茶,把积蓄多用来购买研究所需的书籍和文物。按说,这是私产,可以留给子孙,他却立下遗嘱,把所藏4万余册书籍和千余件书画文物等全部捐献给了国家,并将4万元稿费作为党费上交。
他仁爱。他曾创办平民中学(即今北京第四十一中),免收贫苦学生的学杂费,曾亲自出面,保释参加民主运动的被捕学生。尤其是他对有为青年,更是给予多方面的帮助与关爱。当年启功初登讲台时,从如何备课、板书到文章分析、作业批改,他都逐一指点,还悉心指导启功完成了最初的几篇学术论文。
他坚贞。抗战爆发、北平沦陷,日本人想要他出任大东亚文化同盟会会长,月薪数千元。他断然拒绝:“不用说几千元,就是几万元我也不干。”有一次,学校礼堂放映的一部体育新闻电影里出现了中国国旗,顿时在场师生鼓起掌来。事后,日本宪兵来校追究,要校长交出鼓掌的学生。而陈垣的回答掷地有声:“是我鼓掌,要逮捕就把我逮去!”
许多人都惊讶于他读书之多、之广。其实,他读书是有绝招的,即根据书的内容和用途,或泛读,或精读,或记诵。于是既有了浏览的广度,又有了研读的深度。而那些记诵下来的内容,往往不需翻检原文即可引用,给治学和研究工作带来了极大的便利。据说 90 岁时,他还能把骆宾王的《讨武檄》从头到尾背得一字不差。
1971年6月,91岁的陈垣离世。《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登载了他逝世的消息,称赞他“虽老而志愈坚,年虽迈而学愈勤,为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做出了贡献”。